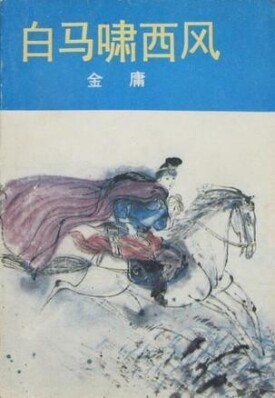共找到3條詞條名為白馬嘯西風的結果 展開
- 金庸創作中篇武俠小說
- 1982年姜大衛主演台劇
- 張紀中製片電視劇
白馬嘯西風
金庸創作中篇武俠小說
《白馬嘯西風》是作家金庸創作的中篇武俠小說,1961年10月—11月連載於香港《明報》。
《白馬嘯西風》是一篇著力寫“情”的小說。這篇小說以金銀小劍三娘子上官虹和白馬李三先後遇害拉開序幕,通過“呂梁三傑”追尋高昌迷宮的地圖,展開了李文秀與蘇普、馬家駿、瓦耳拉齊等人之間的愛恨情仇,同時穿插了蘇魯克與盜賊漢人、瓦耳拉齊與車爾庫之間的糾葛。全篇緊扣“高昌迷宮”這一情節焦點,展開了一場場漢人同哈薩克人之間的情與欲的角逐。
小說並不側重武功的描寫,而似乎在表達一種意念:人人追求的東西,往往並不一定珍貴;而把握住自己所有的幸福,才是人世間難得的境界。
在黃沙莽莽的回疆人漠之上,塵沙飛起,兩騎急馳而來。前面是匹高腿長身的白馬,馬上騎著個少婦,懷中摟著個七八歲的小姑娘。後面是匹棗紅馬,馬背上伏著的是個高瘦的漢子,背中長箭。他們身後數裡外,黃塵滾滾,大隊敵人正在追來。
這男的胡人稱白馬李三,少婦是他的夫人“金銀小劍三娘子”上官虹,小姑娘是他們的女兒李文秀。因為他們夫婦尋找到了高昌迷宮的地圖,被呂梁三傑帶了六十餘人,從甘涼一直追殺到了回疆。對方一共六十多人,卻帶了一百幾十多匹健馬,只要馬力稍乏,就換一匹馬乘坐。李三回過頭來,已經看見了敵人的身影,再過一陣,連面目也看得清楚了,只得咬牙強求妻子帶著女兒和地圖逃命,他則提身縱起,大叫一聲,摔下馬來。後面追趕的人看見李三落馬,一陣歡呼,十餘人縱馬同了上來,其他人繼續追趕上官虹。一人挺起長槍去刺,白馬李三仍是不動,兩人上馬想去搜李三之身時,李三長刀迴旋,將兩人砍翻在地。眾人縱馬同上,刀槍並舉,劈刺下去。
上官虹看見丈夫死去,也不願留戀人世。從懷中取出一塊羊毛織成的手帕,塞在女兒懷裡,揮鞭抽馬,自己則留F待敵。呂梁三傑中的老二史仲俊和上官虹原是同門師兄妹,心中一直愛著小師妹,師父也有意從中撮合,因此同門的師兄弟們都把他們當作是一對未婚夫婦。豈知上官虹無意中和白馬李三相遇,竟然一見鍾情,家中不允他倆的婚事,上宮虹便跟著他跑了。史仲俊對師妹始終余情未了,也一直沒娶親。只是一別十年,再次重逢,竟為了爭奪一張地圖而動起手來。史仲俊妒恨交迸,出手尤狠,李三背卜那枝長箭,就是他暗中射的。上官虹假意與史仲俊親近,實則衣衫中晴藏雙劍,一劍向外,一劍向己。史仲俊一抱上她,兩人同時中劍,先後身死。
眾人在李三和上官虹身上沒有搜得地圖,急忙去追李文秀。眼看就要追上時,風暴突起,直到第二火甲晨,才算平息,文秀得以逃入哈薩克人的部落,被計老人救起。剩下的呂梁二傑雖然帶人洗掠了此處,但文秀因為計老人的保護,並未被認出。就這樣,李文秀住在計老人的家裡,幫他牧羊煮飯,兩個人就像親爺爺、親孫女一般。晚上,李文秀有時候從夢中醒來,聽著天鈴鳥的歌唱,又在天鈴鳥的歌聲中回到夢裡。她夢中有汀南的楊柳和桃花,父親的懷抱,母親的笑臉……過了秋滅,過了冬滅,李文秀平平靜靜地過著日子,她學會了哈薩克話,學會了草原上的許許多多事情,也認識了蘇普。
日子一天天的過去,在李文秀的夢裡,父親母親出現的次數漸漸稀了,她枕頭上的淚痕也漸漸少了,臉上有了更多的笑靨,嘴裡有了更多的歌聲。當她和蘇普一起牧羊的時候,草原卜常常飄來遠處青年男女對唱的情歌。李文秀覺得這些情致纏綿的歌曲好聽,聽得多了,隨口便能哼出米。聽她唱歌最多的,是蘇普。他也不懂這些草原情歌的含意,直到有一天,他們在雪地里遇上了一頭惡狼。
一番纏鬥,蘇普刺死了惡狼。而趕來的父親蘇魯克,看見他和李文秀在一起,勃然大怒,“唰”地就給了蘇普兩鞭。原來他的妻子和大兒子一夜之間都給漢人強盜殺了,所以他恨透了漢人,因而也讓蘇普世世代代都要憎恨漢人,而蘇普卻偏和漢人的女孩兒玩,而且還為了保護她流了血。
看著蘇魯克抱起暈倒的辦普離去時看向她的惡毒的眼神,文秀心中一片空虛,知道蘇普從今之後,再不會做她的朋友,再也不會來聽她唱歌、來聽她說故事了。文秀茫茫然地趕了羊群回家,晚上就發了高燒,說了很多胡話。這一場病一直生了一個多月,到文秀起床時,寒冬已經過去,天山上的白雪開始融化,雪水匯成小溪,流到草原上來。原野上已茁起了一絲絲的嫩草。這天文秀起來,想出門去放牧,卻發現門外放著一張大狼皮,做成了墊子的模樣。她吃了一驚,看這狼皮的毛色,正是那天在雪地中咬她的那頭大灰狼。她俯下身來,見狼皮的肚腹處有個刃孔。她心中怦怦跳著,知道蘇普並沒忘記她。她將狼皮收在自己房中,不跟計老人說起,趕了羊群,便到慣常和蘇普相會的地方去等他。但一直等到日落兩山,蘇普也沒有出現。
這天夜裡,文秀終於鼓起了勇氣,走到辦普的帳篷後面。她不知道為什麼要去。她躲在帳篷後面,蘇普的牧羊犬識得她,過米在她身卜嗅了幾下便走開了,一聲也沒吠。帳篷中還亮著牛油燭的燭光,蘇魯克邊大聲咆哮著,邊拿鞭子抽打蘇普,問是不是將狼皮送給了文秀。原來蘇魯克不見了狼皮,猜測兒子是將它送給了文秀。文秀以前在聽蘇普講故事時說過哈薩克人的習俗:每一個青年最寶貴自己第一次的獵物,總是拿去送給他心愛的姑娘,以表示情意。這時,她聽到蘇魯克這般喝問,小小的臉蛋兒紅了,心中感到了驕傲。他們兩人年紀都還小,不知道真正的情愛是什麼,但隱隱約約的,也嘗到了初戀甜蜜的苦澀。李文秀見辦普挨父親的毒打,把他送給自己的狼皮送到哈薩克美麗的少女阿曼的門口,再也不見蘇普。
時日一天一天的過去,三個孩子給草原上的風吹得高了,給天山腳下的冰雪凍得長大了,會走路的花更加裊娜美麗,殺狼的小孩變成了英俊的青年,那草原上的夫鈴鳥呢,也是唱得更加嬌柔動聽了。只是她唱得很少,只有在夜半無人的時候,獨自在蘇普殺過灰狼的小丘上唱一支歌兒。她沒一火忘記過這個兒時的遊伴,常常望到他和阿曼並騎出遊,有時,也聽到他倆互相對唱,唱著情致纏綿的歌兒。這些歌中的含意,文秀小時候不懂,這時候卻嫌懂得太多了。
一個深春的晚上,李文秀騎了白馬,獨自到那個殺狼的小山上去。她偷偷觀看蘇普與人比武摔跤,卻發現了阿曼對蘇普的愛情,又是高興,又是凄涼。在她傷心而去時,被一直在回疆尋找她的呂梁二傑的手下發現。這些人確知李三得到了高昌迷宮的地圖。這張地圖既然在李三夫婦身上遍尋不獲,那麼一定是在那小女孩身上。高昌迷宮中藏著數不盡的珍寶,這些人誰都不死心,在這一帶到處遊盪,找尋那小女孩。這一呆便是幾年,他們不事生產,仗著有的是武藝,牛羊駝馬,白有草原上的牧民給他們牧養。他們只須拔出刀子來,殺人,放火,搶劫。
文秀想起父母仇恨,欲將他們帶入戈壁之中,同歸於盡,卻巧遇隱藏在此的一指震江南華輝,在他的指點下,用勉強學會的一招武功與毒針,殺死了圍追的敵人,並幫華輝挖出了背上的毒針,拜他為師。兩年時間,李文秀常去華輝那裡學藝,不知不覺間已成為了武林高手。

《白馬嘯西風》
李文秀為關懷、照料自己的兩位親人的死而傷心,更為自己所愛的蘇普愛別人而傷心,她只有騎著白馬,回到中原。白馬已經老了,只能慢慢的走,但終是能回到中原的。江南有楊柳、桃花,有燕子、金魚……漢人中有的是英俊勇武、倜儻瀟灑的少年,但這個美麗的姑娘就像古高昌國人那樣固執:“那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是我偏不喜歡。”
1961年,是《明報》困難的一年,金庸不斷發動武俠小說攻勢,同時連載兩部武俠小說,與《神鵰俠侶》、《倚天屠龍記》同時,短篇武俠小說《鴛鴦刀》、《白馬嘯西風》相繼登場。同年10月,《白馬嘯西風》開始與《倚天屠龍記》同時連載,安排在另一副刊版面,到11月結束。該書原是金庸1960年為電影公司創作的一個劇本。
李文秀
李三與上官虹之女,瓦耳拉齊(華輝)之徒。溫柔仁善,天真美麗。其父母為保護高昌迷宮地圖雙雙喪命后,孤苦伶仃的她有幸為避居於哈薩克族內的“計老丈”所救。二人相依為命,以賣酒、放牧為生。后又與自稱“華輝”的瓦耳拉齊相識,幫其拔去毒針,救其性命,不得已之際拜其為師,學得一身武藝。她對哈薩克小伙蘇普一廂情願。矢志不渝。當其得知蘇普與阿曼彼此相戀后,設法成全二人。“呂梁三傑”為奪得高昌迷宮地圖,曾多次派人查其下落、滅其性命,終未得手。在搞清“高昌迷宮”之真相后,騎自馬返回中原。
蘇普
哈薩克人,蘇魯克的二兒子。他比李文秀大兩歲,長得高大威武,性格粗獷豪放。幼時曾與文秀兩小無猜,一塊放牧,一塊嬉戲,並將自己生來第一次獵得的狼皮做成墊子贈予文秀。長大后,他與本族最美麗的姑娘阿曼相戀。他雖然惦記文秀,但只是朋友之情而已。他曾與父親蘇魯克、車爾庫、李文秀等人尋至高昌迷宮,勇斗惡鬼瓦耳拉齊(華輝)。
阿曼
哈薩克人,車爾庫與雅麗仙之女。其身形裊娜,面目姣好,族人皆稱她是“草原上一朵會走路的花”。桑斯兒曾對其心生愛慕,她卻與蘇普如膠似漆,並甘願為其而死。
馬家駿
漢人。三十多歲,面目英俊。他曾是瓦耳拉齊的徒弟,只因不願助紂為虐,幫師父毒害哈薩克族人而與其反目成仇。其後偽裝為“計老丈”避居於哈薩克族人地域,意外救得命在旦夕的李文秀,並將其撫養成人。最終為保護李文秀,出手與瓦耳拉齊過招而喪命。
蘇魯克
哈薩克人,蘇普之父。他滿臉鬍子,模樣很是讓人害怕,是公認的“哈薩克第一勇士”。由於其妻子與大兒子被漢人強盜殘殺,對漢人恨之入骨,李文秀和蘇普這對鴛鴦也因此被活活拆散。后因李文秀屢次冒險救其性命,對人之好壞有了嶄新的認識,並在高昌迷宮中及時出手相助李文秀。
作品主題
《白馬嘯西風》故事平凡而簡單,一個以德報怨、以愛化解仇恨的愛情悲劇,夾雜了一些懸疑、打鬥和趣味性的情節,是一部有著濃烈的血腥味的寓言,一則悲慘哀傷的童話故事。《白馬嘯西風》故事的背景,原本遠離刀光劍影的武林、是非恩怨的江湖,到了回疆大漠,高昌古國,但仍是一樣暗藏殺機,腥風血雨。然而由於文字十分的好,使得這篇小說流露出一種的同情,而且洋溢出一種至高至深的善念。
《白馬嘯西風》里最重要的人物是李文秀這個女孩子,全篇故事都是圍繞著她發展,她目中所見,心中所想,全成為故事的情節。她充滿了善意和善心,喜歡幫助人,寬恕別人的過錯。但扮演著一個“犧牲者”的角色,表明了作者的態度是對人性的善意有一種悲天憫人的情懷。
作品中的“天鈴鳥”是善的化身,“狼”是惡的象徵。另外還有兩個重要的象徵,一是高昌古國,吸引貪婪者的所在;二是白馬,隱喻著歲月的滄桑,心境的哀傷,是李文秀善良而悲寂的成長里惟一的見證。
《白馬嘯西風》其實是漢家少女李文秀傷感悲情的故事。它的主題具有一種普遍意義:“如果你深深愛著的人,卻深深地愛上了別人,有什麼法子?”或“你心裡真正喜歡的,常常得不到。別人硬要給你的,就算好得不得了,我不喜歡,終究是不喜歡。”——說到底,這是一個無可奈何的人生悲劇。是一種普遍的愛情悲劇,也是一種普遍的人性的悲劇。——如前所述,小說中不但詳細地敘述了李文秀愛而不得其所愛的傷感的悲劇,而且還插入了兩個富有意味的與之類似的悲劇故事。一是漢人史仲俊與其師妹上官虹的悲劇故事,史仲俊固然是深愛上官虹,但奈何上官虹卻並不真愛史仲俊。任史仲俊傷心大病,十年獨身,亦是於事無補,最後殺死了上官虹的丈夫李三,但卻又被上官虹親手所殺,而上官虹自己亦自殺身死,這一故事發生在小說的開頭,可以說是意味深長的。而在小說的結尾處,作者又給讀者揭示了另一個愛情悲劇故事:即哈薩克人瓦耳拉齊愛上了雅麗仙,而雅麗仙卻並不愛瓦耳拉齊而是愛上並嫁給了車爾庫。至使瓦耳拉齊性格陡變,毒死雅麗仙還不說,還要想毒死將他驅逐出族的全族同胞,當然,他自己也因此而毀掉了一生,終於死在沙漠的迷宮之中。
由是觀之,深深愛著的人卻深深地愛上了別人,這樣的事是不分民族、不分時代都有可能發生的。從而,小說《白馬嘯西風》中的李文秀與蘇普這一對異族少年,由兩小無猜到相逢陌路而不識,並不是象小說中表面上昕寫的那樣,是由於蘇普之父蘇魯克痛恨漢人、從而決不允許蘇普與李文秀來往。實際上,這固然也可能是一個具體的原因,但小說所寫,尚要比這明顯的表面因素更為深刻。小說中的蘇普並沒有把他少年時與李文秀的相交當作“愛情”,從而李文秀亦並非他記憶中的情侶,只不過是他少午時的一個“朋友”罷了,蘇普所愛乃是阿曼。從而可以設想,即便沒有蘇普之父蘇魯克從中作梗。蘇普愛上李文秀的可能性還是比不上他之愛上阿曼的可能性大。
除此之外,小說中還寫到了馬家駿在與李文秀長期相處中,他化妝成“計爺爺”但他本人實際上還只是青壯年——對李文秀也是情愫暗生不能自己。乃至於到最後明知陪李文秀去迷宮會碰到瓦耳拉齊從而會白白送死,但他還是毅然隨李文秀而去,最終真的為李文秀而犧牲。——在探訪迷宮的隊伍中,蘇普是為阿曼而去,李文秀卻是為蘇普而去;而馬家駿則又是為李文秀而去……總之這是一幅令人感動而又神傷的圖景。是人類生活中經常地普遍地發生的令人悲傷的圖素。甚至連小說中的天鈴鳥的歌唱也是那樣的悲傷,而當地傳說中的天鈴鳥則正是愛而不得的少女變成的。
小說寫的是“愛而不得”的感傷故事,在這些類似的故事中,不同的主人公卻有不同的選擇,從而凸現出各自不同的性格。史仲俊是痴迷妒忌,瓦耳拉齊是由愛生恨,李文秀是暗自神傷,馬家駿則是默默犧牲,甚至至死也沒有來得及表達。
作品風格
《白馬嘯西風》的寫法是用一種平易近人、平鋪直敘的方式,人物與人物之間的糾葛並不複雜,全篇瀰漫著一種淳樸的古風。《白馬嘯西風》的又一特色是全文中的對白,洋溢著一種哈薩克人說話的質樸和真誠,連同描述的文字也流露出這樣的風格。
《白馬嘯西風》錯落有致地綴合著兩種生命敘事—江湖敘事與牧歌敘事。前者具有自足的空間建構,並在這一淡化官方色彩、“驅使俠客上路”、遵循江湖義法、以武行俠的“民間亞社會”中,確立了以草莽恩怨為引線,以武功打鬥、快意恩仇為語法的敘事一打情模式,讓人們在類型化的敘事倫理中感受“俠”的崇高正義。後者的敘事空間幽靜自然、遠離塵囂,在“情緒的散步”中伏藏物理人情,匯展物我兩諧的自在、優遊之美。因此,《白馬嘯西風》引俗入雅的結果,是作家“反武俠”敘事情念的彰顯。這在《白馬嘯西風》中主要體現為江湖模式的“隱退”與牧歌敘事的膨脹,這種對武俠傳統的反撥使作品發生了從“俠”向“無俠”、由尚武到主情的藝術轉折。
具體而言,小說中粗筆勾勒的江湖敘事,講述的是一個關於奪寶、復仇的血腥慘劇,它賦予作品以刀砍斧削的稜角與峻急熾烈的色調。在回疆大漠的兇悍追殺中,父母催難、身藏高昌迷宮地圖的漢族女孩李文秀,僥倖在大漠風暴中脫逃,被白馬馱至綠草茵茵的哈薩克部族,與同屬漢族的“計老人”相依為命,在似水流年、草長風吹中長大,但喪心病狂的仇家仍是一種“惘惘的威脅”,女孩最後意外習得一身出色武功,終於完成了復仇天職,洞見了藏寶真相。從整個故事結構上看,主人公的歷險與復仇固然殺氣騰騰、險象環生,但貫穿其中的卻是“武”的退場與“俠”的缺席。這裡沒有義薄雲天、輕生重諾的大俠(瓦耳拉齊毒辣,馬家駿怯懦,李文秀則似水柔情、清冷寂寞),沒有出神入化的曠世奇功與異彩紛呈的武功打鬥,作品也一改作家將“武”境界化、道德化、人文化的一貫意圖,更重要的是,可歸入復仇原型的李文秀也沒有像一般武俠小說那樣為故事提供復仇的敘事動力。那麼李文秀無疑是值得注目的特例。所以,“江湖”這一原本在其他武俠故事中最具合法化的敘事空間不僅在此沒有得到擴張,反而被充盈其中的兒女情長所擠占,使文本呈現出另類風姿。
《白馬嘯西風》中關於李文秀在回疆草原成長、生活的段落優美如畫、別具風味,它不僅最大限度地疏離了“豪放”的江湖世界,自成一個相對獨立的“嫵媚”時空,而且通過作家優美舒緩、典雅多情、充滿熱度的敘述,讓人們看到了武俠文本超越單一文類,獲得多元創作基質的文體彈性。可以說,自1929年顧明道的《荒江女俠》面世以來,“武—俠—情”三位一體的模式就已泛化為武俠文類不可或缺的結構要素,但能夠懸置對愛情之深、之廣、之奇的探索,而以描敘邊地情韻、縹緲之戀來墾闢武俠詩化意境的,除金庸的《白馬》之外,放眼武俠寰宇當舍此無它。在飛翔著天鈴鳥、蕩漾著民謠風俗的草原綠洲,流落至此的女孩李文秀重新走入了一片溫馨明亮的感情天地。這裡有與“計老人”“像親爺爺、親孫女一般”的親情,有和哈薩克男孩蘇普的純真友情,也有學會了哈薩克話,學會了草原上的許許多多事情的無比歡快,所以,令人迷戀的“第二故鄉”讓女孩兒枕頭上的淚痕漸漸少了,“臉上有了更多的笑靨,嘴裡有了更多的歌聲”。也是在這片原始放達的土地上,那個為救她而殺死大狼,並送給她大狼皮的男孩蘇普,初次讓女孩兒比水般的內心流出了絲絲情愫……而長大后,李文秀對蘇普剪不斷、理還亂的痴戀,以及馬家駿對她“潤物細無聲”的暗戀,無疑構成了整部小說最感人的一條打情線索,在這個含蓄內斂的三角戀故事中一種柏拉圖式的純情愛戀優美流淌、感傷瀰漫。
武功設定
靈蛇吐信:“青蟒劍法”中的招式。陳達海攻擊李文秀時所使。
青蛇出洞:“青蟒劍法”中的招式。此招用來勢道甚是勁急,陳達海斗李文秀時所使。
聲東擊西:左手一揚,右拳跟著疾劈而下。瓦耳拉齊(華輝)與李文秀、馬家駿激斗時均曾用此招。
五霄轟頂:瓦耳拉齊(華輝)用此招將馬家駿擊斃。
墨月爭輝:瓦耳拉齊(華輝)授於李文秀的禦敵絕招,所用兵器為流星錘。此招使來左錘打敵人胸腹之交的“商曲穴”,右錘先縱后收,彎過來打敵人背心的“靈台穴”,雖只一招,但其中包含著手勁眼力、盪錘認穴的各種法門,又要提防敵人左右閃避、借勢反擊。避敵於一山洞的華輝,危急時刻想出此法:用兩個連著長藤的葫蘆作為兵器,后將此招授於李文秀。李文秀只練習了一個多時辰便出洞攻敵,在華輝的相助下終於大功告成。
葉底飛燕:華輝的絕招之一。此招用來輕巧迅捷,甚是了得。李文秀為保護蘇普等人,為替慘死的父母報仇,施展此招迎擊陳達海。
作家倪匡《我看金庸小說》:《白馬嘯西風》中描寫師、徒之間的爾虞我詐,是《連城訣》的前身,在《白馬嘯西風》中未曾得到發揮的,在《連城訣》中得到發揮。白首相知猶按劍,朱門早達笑彈冠。這一聯,是《白馬嘯西風》的主題。金庸原意,可能想通過華輝的遭遇,寫出世情的險惡,但是短篇完全不給金庸以發揮的機會,無可奈何之至。

白馬嘯西風
作家陳墨《陳墨評金庸系列 1 賞析金庸》:這部小說的妙處,不在其武,而在其情;不在其俠,而在其孽;不在其善,而在其美;不在其事,而在其人;不在其熱鬧,而在其淡雅;不在其轟動,而在其感傷;不在其曲折,而在其深沉……可以說是平淡無奇卻大有韻致。

金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