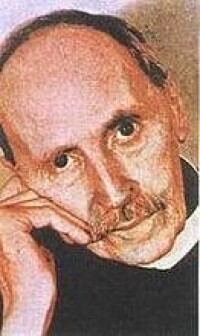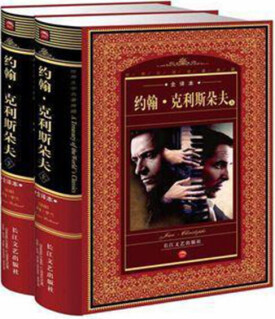約翰·克利斯朵夫
法國羅曼·羅蘭所著長篇小說
《約翰·克利斯朵夫》(Jean-Christophe)是法國作家羅曼·羅蘭於1912年完成的一部長篇小說。
該小說描寫了主人公奮鬥的一生,從兒時音樂才能的覺醒、到青年時代對權貴的蔑視和反抗、再到成年後在事業上的追求和成功、最後達到精神寧靜的崇高境界。通過主人公一生經歷去反映現實社會一系列矛盾衝突,宣揚人道主義和英雄主義的長篇小說。
1915年,羅曼·羅蘭憑藉《約翰·克利斯朵夫》一書獲諾貝爾文學獎。
作品主人公約翰·克利斯朵夫出生在德國萊茵河畔一個小城市的窮音樂師家庭里。其祖父和父親都曾是公爵的樂師,但此時家庭已經敗落。老祖父很喜歡小克利斯朵夫,向他灌輸了不少英雄創造世界的觀念,這使他從小就產生了要當大人物的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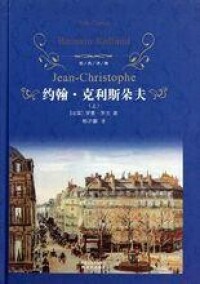
其他版本的《約翰·克利斯朵夫》
此後,克利斯朵夫經歷了兩次失敗的愛情,他的心緒煩亂,意志更見消沉,整天和一幫不三不四的人在酒館里泡。在這個時候,自小就教他安貧樂道、真誠謙虛的舅父再一次指引他走出了情緒的低谷,使他重新振作起來。有一次,克利斯朵夫去聽音樂會,他忽然感覺到觀眾都是百無聊賴,而演奏也是毫無生氣。他回到家裡,把他所景仰的幾位音樂大師的作品拿出來看,竟發現其中同樣充滿了虛偽和造作。桀驁不馴的克利斯朵夫隨即發表了對大師們的反面意見。結果可想而知,他失去了公爵的寵愛,把他所在的樂隊和觀眾也全部得罪了。一個星期日,他在酒館里借酒澆愁時替一位姑娘打抱不平,和一幫大兵發生衝突闖下殺人大禍,他只好逃到巴黎去避難。
在巴黎,克利斯朵夫陷入了生活的困境之中。最後,他終於在一個汽車製造商家裡找到了一個教鋼琴的工作。製造商善良的外甥女葛拉齊亞對他的命運充滿了同情。克利斯朵夫繼續著他的音樂創作,他用交響詩的形式寫成了一幕音樂劇。然而,他拒絕一個聲音庸俗肉麻的女演員演出自己的音樂劇,又給自己惹了麻煩,演出被人搗亂搞得一團糟,他氣憤得中途退場。由於這次不成功的音樂會,他教課的幾份差事也丟了,生活又一次陷入窘境。深愛他的葛拉齊亞因無法幫助他而傷心地離開巴黎回到了故鄉。
在一個音樂會上,克利斯朵夫結識了青年詩人奧里維,二人一見如故,從此住到一起。不久,克利斯朵夫創作的《大衛》出版了,他再次贏得了“天才”的稱號,生活也出現了轉機。但不諳世故的克利斯朵夫仍被人利用,捲入一個又一個是非之爭,逐漸身心疲憊,狼狽不堪,幸得葛拉齊亞的暗中幫忙,他才又一次脫身。然而,在一次“五一”節示威遊行中,他的好友奧里維死於軍警的亂刀之下,他出於自衛也打死了警察,最後不得不逃亡瑞士。
在瑞士,克利斯朵夫思念亡友,悲痛欲絕。一個夏日的傍晚,他外出散步時與喪夫的葛拉齊亞不期而遇,兩人沉浸在重逢的喜悅中。然而,由於葛拉齊亞的兒子仇視克利斯朵夫,二人始終無法結合。
歲月流逝,克利斯朵夫老了,葛拉齊亞去世了,充滿激情與鬥爭的生活也遙遠了。當克利斯朵夫從瑞士的隱居生活重新回到法國的社會生活中時。他的反抗精神已完全消失,他甚至和敵人也和解了,並反過來譏諷像他當年那樣反抗社會的新一代。晚年,他避居義大利,專心致力於宗教音樂的創作,不問世事,完全變成了一個世故老人,進入了所謂“清明高遠的境界”。
| 卷首 | 原序 |
| 卷一 | 黎明 |
| 第一部蒙蒙曉霧初開,皓皓旭日方升 | |
| 第二部天已大明,曙色倉皇飛遁 | |
| 第三部日色喉嚨微晦 | |
| 卷二 | 清晨 |
| 第一部約翰·米希爾之死 | |
| 第二部奧多 | |
| 第三部彌娜 | |
| 卷三 | 少年 |
| 第一部於萊之家 | |
| 第二部薩皮納 | |
| 第三部阿達 | |
| 卷四 | 反抗 |
| 卷四初版序 | |
| 第一部鬆動的沙土 | |
| 第二部陷落 | |
| 第三部解脫 | |
| 卷五 | 節場 |
| 卷五初版序 | |
| 第一部 | |
| 第二部 | |
| 卷六 | |
| 卷七 | 戶內 |
| 卷七初版序 | |
| 第一部 | |
| 第二部 | |
| 卷八 | 女朋友們 |
| 卷九 | 燃燒的荊棘 |
| 第一部 | |
| 第二部 | |
| 卷十 | 復旦 |
| 初版序 | |
| 第一部 | |
| 第二部 | |
| 第三部 | |
| 第四部 |
羅曼·羅蘭生於1866年,卒於1944年,他的一生穿越了法國第三共和國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幾十年間法國的經濟雖然得到發展,但是經過普法戰爭和巴黎公社起義,拿破崙分子和封建殘餘勢力仍然很有市場,加上兩次世界大戰以及德雷福斯事件,社會激烈動蕩,思想混亂,人心浮動,世風日下,個人主義泛濫,享樂之風盛行。文學上出現萎靡不振、矯揉造作、缺乏生氣的所謂后象徵主義的特徵。作為人道主義作家、思想家的羅曼·羅蘭面對嚴酷的社會現實,關注社會問題,參與政治生活,他的思想傾向和價值取向在文學作品中皆有所表現。羅曼·羅蘭認為真正的藝術該是有高尚道德,富有戰鬥性的,它能觸動世界各國數代人的良知,有助於他們站得更高,看得更遠。關於創作意圖,羅曼·羅蘭在《致約翰·克利斯朵夫的朋友們》中寫道: “我該介紹我在整體規劃這部書時的背景。我是孤獨的。我像法國許許多多人一樣,在與我的道德觀對立的社會中備受壓抑;我要自由呼吸,要對不健全的文明,以及被一些偽劣的精英分子所腐蝕的思想奮起抗爭⋯⋯為此,我需要一個心明眼亮的英雄,他該具有相當高尚的道德情操才有權說話,具有相當大的嗓門讓別人聽見他的話。我十分耐心地塑造了這個英雄。”他宣稱“我的《約翰·克利斯朵夫》並不是寫給文人們看的”,“但願他直接接觸到那些生活在文學之外的孤寂的靈魂和真誠的心”。
《約翰·克利斯朵夫》是部耗時20餘年之久的長篇巨著,羅曼·羅蘭從1890年就開始醞釀構思,1902年2月《半月叢刊》發表了小說的第一卷《黎明》,而直到1912年才刊行了第十卷即最後一卷《新生》。
約翰·克利斯朵夫
克利斯朵夫出生於一德國小城。小城那種閉塞的空氣使他窒息,如同關在籠里的困獸,他獷野奔放的激情之火一天天熄滅。而最令他氣喘不過的還不是這缺乏自由的天地,而是泛濫了的理想主義。每個人都陶醉在自己偉大力量的幸福之中,宣講著理想和勝利,整個德國充斥著一種自命不凡的軍人式傲慢,而這些在藝術中則表現為一種感傷主義的希冀。藝術家在說謊,不敢直面人生。
克利斯朵夫看透了德國人的虛偽,他恨這種理想主義,他進出全部的生命力嚮往太陽。然而,人人如此,每個角落都演著同樣的一齣戲,克利斯朵夫寒顫了,於是他逃了,他跳上了開往法國的火車。當他的腳剛剛踏上他嚮往已久的那塊土地時,他的心在喊:“噢,巴黎!巴黎!救救我罷。救救我的思想!”
初到巴黎,混亂,這是克利斯朵夫第一個也是最深刻的一個印象。在這兒,任何人都想做自由人,都不願遭捆縛,而巨大的力量就因缺乏約束而消失彌盡。為了了解這個民族,克利斯朵夫在高恩的引導下挨個拜訪藝術界人士。拜訪之下,他大吃一驚。“七天之內人家就給他十五個音樂會,一星期中每個晚上都有,往往同時有兩三個……音樂會的頻繁使他驚異,令他不知所措。他再也沒想到“巴黎那些小鳥兒有這樣大的音樂胃口”。然而,大量的音樂會其內容少得可憐,且都散發著一種脂粉香味,華而不實。法國是被自由灌醉了!當然,他也發現了某種極為精緻的藝術,然而它太小了,令人錯愕,難以把握,因為創造它的人太聰明了,他們雖然離開大路而勇敢地撲向森林小徑,“但他們都是挺乖的孩子,怎麼樣也不會迷路”。他們早就看到了結果,於是,為保持內心的獨立,他們理智地放棄了行動,放棄了追求。他們缺乏德國人的理想和熱情,且不願被人組織、聯合,只是孤零零地淡泊溫和地表現自己對生活和藝術的理解。與法國的接觸,使克利斯朵夫認識到德國的偉大。法國人的混亂和對命運的屈從使他開始意識到應尊重德國人的毅力和樂觀主義。
克利斯朵夫在研究了德法之後,又去研究義大利。義大利純潔而美好的理想主義熱情深深地吸引住了他。這兒既沒有德國過於普及的理想主義所造成的浮誇,也沒有法國因泛濫了的自由而引起的藝術中個性消失或僅僅表現在獨立思考中的傾向,這裡有的只是安寧平靜的氣氛和徹底迷戀傳統的溫情。克利斯朵夫覺著自己需要這種溫情,需要這個國家,以便在創作中把自己狂放不羈的情感協調得平和些。於是,他開始刻意地尋找這三合音中每一個聲部所表現的實質,揉和它們的長處,把德國的深奧、神秘的思想,和義大利的熱情溫存的曲調,以及法國細膩而豐富的節奏溶合在一起,創作出了他一生中最偉大的作品:《平靜的島》和《西比翁之夢》。
這位桀驁不馴的青年人曾滿懷偏見去審視民族,然而,“一切民族都使約翰·克利斯朵夫備嘗痛苦,也使他受到恩惠;一切民族都使他感到失望,也使他受到讚揚。他日益清楚地認識了他們的面目。在他旅遊結束時,一切民族對這位世界公民來說,都不過是靈魂的祖國,而這位音樂家幻想創造一部崇高作品,一部偉大的交響樂,在那裡,各民族的聲音擺脫了刺耳的不和諧,而以最動聽的人類和諧響徹雲霄”。
奧里維
他頭腦清楚但身體虛弱,彷彿生下來就是為了與克利斯朵夫相配的。這位面色蒼白、感情細膩、敏感而又膽怯的小布爾喬亞內心裡雖有著火樣的熱情,可骨子裡卻對暴力懷有莫大的恐懼。他的生命力不像他的同伴那樣來自強壯的軀體,而是來自他的意識。他具有法國人的廣博的修養和洞察人類心理的本領,頭腦清晰,雙眼明亮。他批判人沒有朋友那樣的盲目,也無普通人那種自以為是的幻想,而是把事物看得明明白白,實實在在。他和他的朋友一樣,蔑視不公,痛恨腐朽,不屈就於任何成就。他並不逃避內心思想上的鬥爭,但他太瘦弱了,也太清醒了,太正直了,他知道打破的東西還會復原,因此不願在行動上耗費無效的精力,而只是用超然物外的心情去愛人生。“一方面是軟弱而騷動的身體,一方面是無掛無礙而清明寧靜的智慧,雖不能完全控制那騷亂,卻也不致受它的害——在擾攘不息的心頭始終保持一片和平,這就是奧里維。
葛拉齊亞
真正把這兩極銜接起來的是創造性的現實——葛拉齊亞。這位始終帶著蒙娜麗莎似的溫柔微笑的義大利女子,在這喧嘩與騷動的世界里悄悄走來,“像一道清澈的陽光”,奉獻給人類以和善靜謐的美。這是一個真正的拉丁女性,對於她,藝術可以歸納到人生,再從人生歸納到愛情。她沒有奧里維的騷亂心緒以及得不到公正而引起的失落與茫然。她很少抑鬱,很少感傷,她只關心現實。那些悲壯的交響樂、英勇犧牲的思想與她毫不相干,她親切地與人交談,與人共處,但絕非一團熾熱的烈火,而是以一腔柔情包圍著人們,使人極度的惶惑猶如西去的浮雲悄然而逝。她是一種創造性的現實,她使得創造性的力量和創造性的思想在和平氣息的籠罩下溶合了。“噢,人生,有些東西原來是你不能給的,為什麼要怪怨你呢?你的本來面目不是已經很美很聖潔了嗎?育公特,我們應當愛你的微笑……”。
安納德
作為耶南家族最年輕的一代,童年的她全身心地沉浸在自己夢想的世界里。在這裡,她就像生活在伊甸園裡的亞當那麼自在自由、無憂無慮,身心和土地、和自然萬物和諧、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父親的縱容與疼愛,讓她如同生活在溫室中的花朵,對於這個現實的世界沒有一絲一毫的戰鬥準備。她的秘密花園裡,完全脫離了貧民世界的陰鬱沉重,漫天都是盛開的鮮花和純潔的天使。她最初的愛情錦上添花一般裝飾了她的十六歲,少女的迷夢。但是父親生意上的錯誤決斷導致的嚴重後果。父親舉槍自殺,家族破產,債主蜂湧而至,一切不幸的麻煩好像都在同一時間爆發,安納德甚至還來不及整理失去親人的痛苦心情,便跌進了更加屈辱和苦難的深淵。安納德要用更多的時間結束自己以往那些美好的幻想,重新面對這險惡的世界。父親冷清的葬禮,親友詛咒的侮辱,周圍漠視的眼光,讓迷夢中的安納德逐漸清醒。“她的眼睛睜開了,看到了人生;她把父親,母親,兄弟,統統批判了一番。”她終於明白,自己一無所有了,一無希望,一無靠傍:不用再想倚仗誰。
移居巴黎以後,善良而驕傲的母親,在遭遇親戚的白眼和借債的尷尬之後,拋下了貴夫人的虛名,艱難地維持著一家人的生計。母親的改變,弟弟的軟弱,進一步激勵了安納德的蛻變。她知道自己應該堅強,於是用自己生命的勇氣不厭其煩地鼓勵弟弟,鼓勵弟弟要生活下去,不要輕易地想到死,不要輕易地放棄生活。三個人都憑藉著對生命的愛而活了下來,在孤苦無依的巴黎,在眾叛親離的巴黎,愛成為他們維繫生存的最大的力量。然而命運之神並不眷顧他們的堅持,在連續的勞累和沉重的心理負擔之下母親終於倒下了。帶著對安納德和奧里維未知的生命的憂慮,滿眼惶惑地睡去,再也沒有醒來。
安納德接替了母親的責任,開始全心全意地照顧弱小的弟弟。她的形象變的更加厚重高大。一方面,她抵禦著內心的掙扎和苦痛,四處做工,忍受他人的刁難和非議,辛勤勞作支付弟弟的生活費用;一方面,她用自己高貴的靈魂和對生活的熱愛,鼓勵弟弟失落的情緒,消除他對未來的恐懼,確保他可以堅強地活下去。更為重要的是,她還要隱藏自己那年輕的生命力所引發的對於愛情的渴望和物質的慾望,讓自己像一個清教徒一樣,拒絕社交和娛樂活動,在狹窄的圈子裡維繫親情的平衡。她那溫情脈脈的眼光,就是她內心女性光輝的最佳寫照,正是這默默隱忍又飽含深情的眼睛,成為了約翰·克利斯朵夫注意的焦點,也成就了安納德隱秘的愛情的靈光一閃。
安納德承載著精神和肉體的雙重壓力,承載著奧里維的信仰和依附,她自己同樣需要救贖。這個並沒有強大到可以對抗一切不幸的女子,在無依無靠的精神領域裡尋求到了另一種解脫,那就是宗教的歸依。“她遭了橫禍,卻始終相信基督的愛,相信跟你一起受苦,將來有一天會安慰你。”將解決苦難的希望寄托在上帝的身上,這或許並不是真正的強者的選擇。可是對於安納德這樣一個貴族出生,少不更事的女子而言,這是可以理解的。在物慾橫流的巴黎,她只能是在社會最底層的為生計苦苦掙扎的個體。用血汗換取的有限的金錢,甚至不能滿足姐弟兩人一起看音樂劇的卑微要求,她沒有社會地位,沒有年輕人的消遣,沒有對於自身發展的任何規劃和憧憬。她的堅持只是來自於柔弱的,出於對兄弟的愛。這種用柔弱的身軀彰顯的強烈的愛,讓人看到了她的高貴和偉大,也更加認同她的不完美和缺陷。
安納德是《約翰·克利斯朵夫》裡面重要的女性角色之一,這個牽引著約翰·克利斯朵夫與奧里維相識相知的女人,對於約翰·克利斯朵夫的心理的成熟,奧里維的性格的成長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她那短暫又充滿著苦難的一生,同樣是一曲憂傷而美好的法國鄉村小調,給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無限的想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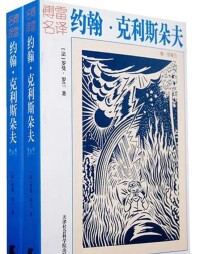
約翰·克利斯朵夫 封面
小說的豐富思想伴隨著約翰·克利斯朵夫從小到大,其中對自由生命的嚮往與追求一直隱藏和貫穿於他一生的坎坷經歷中,涉及的範圍也由個人過渡到整個社會,愈來愈成熟,愈來愈深廣。
自由生命更是約翰·克利斯朵夫人生追求的強大動力。它的動力又來自何方呢?羅曼·羅蘭認為,動力來自於宇宙間普遍存在的那種神秘的,但又是強大的生命力。少年克利斯朵相信自己就是上帝,認為上帝就在他心中,“它(指上帝)透過卧室的屋頂,透過四面的牆壁,把生命的界限推倒了,它充塞於天地之間,宇宙之間,虛無之間。他醉了……深不可測的上帝!那是生命火把,生命的颶風,求生的瘋狂——沒有目的,沒有節制,沒有理由,只為了轟轟烈烈的生活!”那麼是什麼讓他產生這樣的念頭?是他的信仰。那麼什麼是他的信仰呢?他的信仰就是熱愛生命,追求自由,融入大自然。當克利斯朵夫躺在萬物滋長的草地上時,在昆蟲嗡嗡作響的樹蔭底下,看著忙忙碌碌的螞蟻,走路像跳舞般的長腳蜘蛛,在斜刺里蹦跳的蚱蜢,笨重而匆忙的甲蟲,還有光滑的、粉紅色的、印著白斑、身體柔軟的蟲,他感到他和千千萬萬的生靈原是同一血統,它們的快樂在他心中也有友好的回聲:他們的力和他的力交融在一起。他認為在大自然中,他是自由的,上帝無處不在,自由無處不在。同時,他也認識到人類所追求的自由也並非完全沒有約束,他所謂的自由也是要受到大自然法則的約束。他看到世界上沒有一個生物是自由的,連控制宇宙的法則也不是自由的。看來,自由也是相對的,人追求期待的自由也是受到不自由的宇宙法則的約束的。但是年輕的他有種不受約束的衝動,帶著“還來不及認識新的牢籠的界限”的熱情與幹勁在有限的自由環境中呼吸。
面對不自由的社會現實他開始反叛。他厭惡空洞的道德、責任,厭惡專制和淫威,憑著強烈的叛逆性格,桀驁不遜的克利斯朵夫在年輕的生命力的支撐下一步一步爭取更多的自由空隙。他天真、專橫、過激地揮舞著堂·吉訶德式的長矛,抨擊前輩宗師,抨擊德國民族的矯飾和感傷性,在他的小城裡樹立敵人,和大公爵衝突,為了精神的自由喪失了一切物質上的依傍,終於亡命國外。在巴黎,他同樣橫衝直撞地去征討當時社會與藝術的謊言。但隨著慢慢的成長,他追求自由的方法也由否定一切過渡到慢慢接受一些現實,最終,他也只能在大自然法則中做著合乎情理的事。從這個意義上講,克利斯朵夫不僅僅是個個人奮鬥者,也是自我生命的體驗者、思考者和追求者。
真理的生命在於創造。約翰·克利斯朵夫在擺脫了情慾的束縛之後,又找到了“創造”這朵生命之花,將自己融於音樂創作中,“創造,不論是肉體方面的或精神方面的,總是脫離軀殼樊籠,捲入生命的旋風,與神明同壽。創造消滅死。”
真理拒絕虛偽。他低頭摸索前進,飽受矛盾衝擊,在其創作過程中,他發現了德國人的虛偽。他冷言冷語地諷刺道:“人的精神非常軟弱,擔不起純粹的真理。必須由他的宗教、道德、政治,詩人、藝術家,在真理之外包上一層謊言。”他批判那些貌似對音樂恭敬虔誠的人。看到這些人的作品,使他最氣惱的是謊言。看到將音樂這門崇高而艱辛的事業,輕鬆地置於酒杯間的談笑的虛偽的民族,克利斯朵夫再也抑制不住,發出了大笑。一個“笑”字,寫出克利斯朵夫對這種虛偽的譏諷、蔑視,顯示自己保持清醒的頭腦和堅持真理、不同流合污的立場;一個“笑”字,是要警醒那些仍沉醉於麻木狀態的人們,激發他們追求真理、擺脫虛偽音樂束縛的情緒。一笑破天驚,克利斯朵夫開始了與虛偽鬥爭的歷程。
真理就是為藝術而藝術。那麼真理的判斷標準是什麼呢?克利斯朵夫提出“心靈美重於技巧美,內容重於形式”的創作觀點。徒有其表而無實質的文學,在克利斯朵夫看來,這是一些老小孩的玩意,喜歡畫而不會畫,便信手亂塗一陣,還挺天真地在下面用大字寫明,這是一所房子,那是一株樹。這樣的作品只會離真理愈來愈遠。文學家如此,哲學家如此,社會學家也是如此,他們只喜歡討論,而不製作,偶爾製作,也是空洞的軀殼,沒有實質的內涵。藝術應該來源於真實生活,來源於生活的最底層。為藝術而藝術和為金錢而藝術是一對矛盾體。正如奧里維對克利斯朵夫說:“倘使藝術真有什麼疆界的話,倒不在於種族而在於階級。我不知道是否真有一種藝術叫法國藝術,另外一種藝術叫德國藝術;但的確有一種有錢人的藝術跟一種沒有錢的人的藝術。”如何取捨,本書給出了答案。就是要做到為藝術而藝術。他列舉了當時法國流行的各文學體裁中有很多偽造藝術和濃厚的享樂主義。如詩多抄襲,小說多淫穢,戲劇成為法庭上的道德。他認為一切的思想,一切的精力掉在這種泥淖里,都變得無影無蹤。這“泥淖”就是指不尊重現實,那種不深入生活的浮躁、虛偽的地方。他通過自己的種種行動來與這種為金錢而藝術的局面對抗,並呼喚著一個充滿活力、真誠、有內容的藝術境界早日到來。
《約翰·克利斯朵夫》彷彿是一個時代的“精神的遺囑”。羅曼·羅蘭也因為夢想著重構西方精神而被尊稱為“歐洲的良心”。本書最有影響力的還是通過克利斯朵夫、奧里維、葛拉齊亞三者為代表的德、法、意三國的歐洲“三重奏”,這是人類和諧精神的整體象徵,也是作者重構西方精神的具體表現。克利斯朵夫代表德意志的狂放不羈、強悍有力,具有創造性力量;奧里維代表法蘭西的自由清新,具有先進思維;葛拉齊亞代表義大利的和諧柔美,具有現實精神。三者雖具有不同特質,但創造、思維、現實三者是相輔相成的,不可分割,相互影響的。作者在突出位置描寫了克利斯朵夫與奧里維結下的親密友誼,與葛拉齊亞富於詩意的“柏拉圖”式的愛情,這一微妙的人物關係,正是作者反對軍國主義和民族歧視、主張人類和諧一致的人道主義理想的象徵性體現。同時,對這三者也有所批判。如:德國——意志堅定但理想主義的幌子下是自私自利;法國——四周都是腐敗的藝術;義大利——他們的理想主義永遠忘不了他們自己,缺乏寬闊胸襟。這裡只需引述羅曼·羅蘭在1925年1月所寫的《約翰·克利斯朵夫給他在中國的弟兄們的公開信》就很可以說明問題了:不管他們來自何方,他們都是我的朋友、我的同盟和兄弟。我的祖國是自由的人類,偉大的民族是它的省份,而眾人的財產是它的太陽神。
《約翰·克利斯朵夫》不是一部小說,應當說不只是一部小說,而是人類一部偉大的史詩。它所描繪歌詠的不是人類在物質方面,而是在精神方面所經歷的艱險,不是征服外界而是征服內界的戰跡。它是千萬生靈的一面鏡子,是古今中外英雄聖哲的一部歷險記,是貝多芬式的一曲大交響樂。主人公約翰·克利斯朵夫,既是一個超人,也是一個凡人,他有自己的情慾,有自己的過錯,有內心中的矛盾、軟弱與痛苦,但也有自己的追求、夢想、愛和為愛百折不撓的精神。
《約翰·克利斯朵夫》是一部多主題小說。在小說的扉頁上,羅蘭將小說題獻給“各國的受苦、奮鬥、而必戰勝的自由靈魂。”可見,對“生命力”的歌頌是作品的核心和靈魂,作者將貝多芬的音樂精神和“力”的特質融於克利斯朵夫的性格之中,借用了一個音樂家的奮鬥經歷來倡導其英雄主義、人道主義和理想主義,表現了作者“和諧”、“統一”的藝術思想和美學理念。對生命力的歌頌是通過克利斯朵夫反抗命運和戰勝內心,通過音樂對比衝突來體現的。比如通過對克利斯朵夫愛的力量和恨的力量的對比,通過克利斯朵夫與自身內心軟弱鬥爭的對比等,而達到生命的澄明之境——和諧。羅蘭讓克利斯朵夫成為了人類和諧精神的本體象徵,在對立矛盾中達到神聖的“統一”。不僅人物個性、人物配置上體現復調的對比和統一,而且從各個側面豐富克利斯朵夫性格的發展,反映了作者對人類精神完善發展的美好願望。
對自然音響的細膩描述是《約翰·克利斯朵夫》這部作品最具藝術特色的地方,文學史上可能還沒有多少作家像羅蘭一樣把自然當成人類的一部分而如此動情的潑墨。小說中萊茵河、聖馬丁教堂的鐘聲的多次出現就如音樂中的主導音響一般,成為貫穿作品,照應首尾的紐帶和橋樑。將自然音響與樂聲、人聲相比擬,不僅使人物形象更加鮮活,而且為作品創造了詩一般的意境。作品中的藝術音響可分為音樂場景和音樂性場景。有音樂出現的音樂場景體現了風俗民情和歷史背景,為人物活動創造一個適合的場所,而沒有音樂出現,但本身卻如同音樂一般的音樂性場景,如《節場》一卷的描寫可以深化主題思想,加強批判力度。用音樂環境營造背景和氛圍,是作品獨具魅力之處,不僅展現了紛繁複雜的社會場面,又細微地刻畫了人類的思想感情。
小說中一個獨特的表現手法就是。整部小說以“河”這一意象貫穿始終。“河”這一意象在小說中出現了近百次。在小說的開篇,寫克利斯朵夫出生,就對孕育克利斯朵夫成長的母親河——萊茵河,進行了聲響的描寫:“江聲浩蕩,自屋後上升。”結尾又是以萊茵河來為主人公一生的總結。萊茵河伴隨了克利斯朵夫的一生,他出生在萊茵河畔,結識朋友在萊茵河畔;身處異國時,眼前浮動的是萊茵河;臨終彌留時,耳邊聽到的是萊茵河的濤聲。作者把各種現象比作河流,“河”之意象如同晴朗夜空中的點點繁星,在整部小說中閃爍若粗眼的光芒。
其他象徵比如風和雨,有著掃蕩一切,摧毀一切的萬鈞之力,每次出現都預示著約翰·克利斯朵夫歷經磨難后的重生與自由。“他無羈無絆了,孤身一個……一個人!一個人存在,回歸自我是多麼幸福啊!”小說中多次出現對風和雨的描寫,使其賦予一種吐故納新的意義。風和雨的每次出現,都是在克利斯朵夫精神危機出現之時。在 《歐萊一家》一節的末尾,有這樣一段:“倏然間,閘門打開了。在他身後的院子里,大雨如注,傾盆而下……在閃光之中,他看見黑暗的盡頭,他看見了,看見有個天主。他就是天主的化身……他打破了生命的界限……生命的烈火!生命的颶風!瘋狂地求生……僅僅為了轟轟烈烈地活下去。”在 《流沙》一節的開頭,文中寫到:“轉回城裡,凜冽的寒風在巨大的城門下旋轉……克利斯朵夫卻歡欣地笑了。他顧不上眼前的風暴,卻在想著他剛剛掙脫出來的另一場風暴。”經歷了和安娜的戀情之後,克利斯朵夫隱居在瑞士的汝拉山上,失去奮鬥動力的克利斯朵夫在復活節下山去尋找生命。一天夜裡,吹來了“春天的焚風”,它溫暖了大地,融化了冰,孕蓄著雨,吹在克利斯朵夫的臉上,終於為他帶來新生命的活力。
《約翰·克利斯朵夫》是20世紀的一部“長河小說”,它反映了世紀之交風雲變幻的時代特徵和具有重大意義的社會現象,它具有豐富的思想文化內涵與人格魅力。其中對自由生命的嚮往,對理想真理的追求及對西方精神的整體反思是其主要內容。
羅蘭因此書獲得了1913年度的法蘭西院士文學獎和1915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
翻譯家傅雷:“我們尤須牢記的是,切不可狹義地把《約翰·克利斯朵夫》單看做一個音樂家或藝術家的傳記。藝術之所以成為人生底酵素,只因為它含有豐滿無比的生命力。藝術家之所以成為我們的模範,只因為他是不完全的人群中比較最完全的一個。而所謂完全並非是圓滿無缺,而是顛豈不破地、再接再厲地向著比較圓滿無缺的前途邁進的意思......這部書既不是小說,也不是詩,據作者的自白,說它有如一條河。萊茵這條橫貫歐洲的巨流是全書底象徵。所以第一卷第一頁第一句便是極富於音樂意味的、包藏無限生機的"江聲浩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