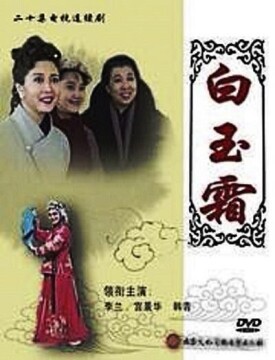共找到2條詞條名為白玉霜的結果 展開
- 評劇表演藝術家
- 1994年白唐執導唐電視劇
白玉霜
1994年白唐執導唐電視劇
電視劇《白玉霜》講述的是一代評劇大師白玉霜的故事,角色生動、感人,包括白玉霜的愛人長生,養女小白玉霜,白玉霜的養母李卞氏等等。
電視劇《白玉霜》講的是一代評劇大師白玉霜(李蘭飾)的故事,角色生動、感人,包括白玉霜的愛人長生,養女李再雯(就是小白玉霜),白玉霜的養母李氏等。
白玉霜從小就被賣給李氏學戲,長大后在天津唱紅了,也捲入很多麻煩,不得不陪睡,中間一段時間厭倦了這種生活,就跟長生私奔了,可是後來放不下唱戲,就又回來了。最後慘死的時候才35歲。記得有一段她和長生逃跑到長生的老家的一段,還有一段是被人潑了糞。
片尾曲:世間儘是不平事,好夢難圓太凄迷,一代紅顏多薄命,有情之人難相聚。春水東流去,黃沙永不息,一枕黃粱夢,苦淚點點滴,苦淚點點滴。
演員表
| 角色名 | 演員名 | 配音 | 備註 |
|---|---|---|---|
| 白玉霜 | 李蘭 | ||
| 李長生 | 韓青 | ||
| 李卞氏 | 宮景華 | ||
| 小白玉霜 | 張潔 | ||
| 合適樂 | 郭濤 | ||
| 袁養齋 | 趙汝彬 | ||
| 賽芙蓉 | 呂自敏 | ||
| 長生娘 | 鄭幼敏 | ||
| 風姑爹 | 李翔 | ||
| 石榴紅 | 許娣 | ||
| 游護士 | 夏立言 | ||
| 老警官 | 黃少泉 |
職員表
| 總導演 | 白唐 |
|---|---|
| 製作人 | 牛富強 |
| 副導演 | 盧廷蘭、呂武霖、馬慶欣、趙艷君 |
| 監製 | 李廷芝 |
| 發行 | 北京電視台北京電視藝術中心 |
| 造型設計 | 王松美 |
| 編劇 | 郭啟宏 |
| 服裝設計 | 呂自敏 |
| 攝影 | 李越華 |
| 錄音 | 段自輝 |
| 配樂 | 馬丁 |
| 剪輯 | 宋志鵬、董愛軍 |
| 場記 | 於淑軍 |
| 道具 | 劉長林 |
| 布景師 | 張瑞清 |
| 燈光師 | 胡小濱 |
評論家童道明先生說:復原一個不太久遠的歷史,比復原一個遠古的,象戰國時期那樣的歷史難度更大。而電視連續劇《白玉霜》主要是反映三、四十年代的舊社會藝人生活。雖不是今天,但歷史也不久遠。因此在場景選擇上,困難可想而知!
劇中的兩個重要場景:一個是白玉霜在上海灘大紅大紫后的住處——上海麗都旅社。它不僅要像30年代舊上海的建築,還要豪華氣派;另一處是白玉霜從天津鄉下返回天津后的居室,是一個既應有那個年代氣氛,又有北方建築風格的私人寓所。這兩個場景的戲佔了全劇四分之一的鏡頭,高潮戲也發生在這兩個重要的居住地點。導演和美術師對這兩個場景十分重視,四處去看景、選景、足跡遍布津、滬兩地,所到之處,都覺得不夠理想。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導演、美工,捨棄津滬,就在北京打了主意。經多方打聽,得知在北京圓恩寺附近的友好賓館,是蔣介石過去在北平的私人官邸,與劇情要求大體相同。導演和美工師看后,高興得立即拍板,基本不用裝飾,搖身一變,變成了上海麗都旅社白玉霜的居室和客廳了。不知三十年代,委員長和白老闆是否相識,反正這次委員長為《白玉霜》出力了。
劇組中的“編輯部”
一部影視作品中,一個細節,有時會對片子的藝術質量有很大的影響。如果失真,能降低整部片子的藝術水準;相反,則會有畫龍點睛之妙。例如:一盤大煙槍器具能把劇情推向高潮;一筒“綠炮台”香煙成為了白玉霜與李長生愛情信息的傳遞。而有時卻為一瓶“衡水老白乾”找遍了半個京城,這一切的背後,又蘊含著多少鮮為人知的故事呢?
《白玉霜》中需要許多的文字史料,特別是舊時的報紙、有名有姓、來不得半點虛假。如:《申報》、《新天津報》、《大公報》、《庸報》、《戲劇報》和《大晚報》,再加上《北洋畫報》、《三六九》畫刊等十多種報刊雜誌,既要讓觀眾覺得是那個時代的報紙,又是按照劇情提供的要求,把有關的內容編排在裡邊。說白了,就要“編輯”一批三、四十年代的報紙,談何容易!美工人員,得到各大圖書館從一疊疊的“故紙堆”中翻閱,查詢出有關的報紙及畫刊,把有用的版面複印下來,根據劇本要求,在一張同原版報紙大小相同的白紙上,把複印的史料和做好的文字,圖片再粘貼和剪裁,重新排版。這樣由眾多“補丁”拼貼在一起,亦真亦假的、但卻是劇情要求的舊報紙,經過道具部門的艱苦“編輯”誕生了。這樣一份一份地編輯,幾十份形態各異的道具報紙、雜誌在二十集連續劇中,可能會給您留下點印象,也可能是稍縱即逝,但在這每一份“報紙”“雜誌”的背後,凝聚著多少創作人員繁雜、辛苦的工作,恐怕是許多觀眾想不到的吧!
“意外的”鏡頭
在《白玉霜》中,有一場流氓給白玉霜扣馬桶的戲。由於牽扯到化妝、服裝等原因,只能實拍一次。而這一次又“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為此,現場進行了周密的安排。反覆排了三、四遍后,隨著“預備、開始”的發出,流氓把滿滿的一馬桶“糞便”扣在了演員的頭上。劇情要求演員邊喊“我的瞼、我的臉毀了”,邊跑向恩派亞劇場的大門。但誰也沒想到,演員的腳踩到了撒在地面的“糞便”上,轉身奔跑的一剎那,“咚”的一聲重重摔倒在地。見此意外的“表演”在監視器前導演立即大喊:“別關機,繼續拍!繼續拍!”就這樣,演員在摔破膝蓋的情況下繼續演戲,攝像繼續拍攝,一個出乎意料、卻在情理之中的鏡頭出色地完成了。後來,許多人看到這一場戲時,都不禁讚歎:“這一跤,摔得好,摔得太真實了”。
而拍攝“趙老西與小白玉霜泛舟”的戲,卻是另一番景象了。船劃到了湖中心,趙老西從搖搖晃晃的小船上掉入水中,待他重新露出水面時,奇妙的事情發生了:在船上時,趙老西還是滿頭黑髮,而從水裡鑽出時,滿頭黑髮都離頭而去,露出了演員光禿禿的腦袋,原來演員藏的是假髮套。現場攝製組人員以及眾多的圍觀群眾禁不住嘩然大笑——沒辦法,只好重拍。
“大穿幫。重拍吧!”
“小酸棗”唱《小酸棗》
《白玉霜》中,有一首清純、優美,有著濃郁民族特色的插曲《小酸棗》。由它延伸出來的多首變奏曲,統領在“白玉霜和李長生”的主題音樂下,為劇情的發展、深入,起到了很好的鋪墊、襯托作用。加上旋律易於傳唱,作曲馬丁不無得意地宣布:《小酸棗》要成為電視劇音樂的“主題歌”。
這首歌是由剛從日本學習歸來,頗具發展潛力,曾為《戲說乾隆》一劇配唱面聞名的張繼紅演唱的。進錄音棚前,她告訴導演和作曲,“我特別喜歡這首歌”。尋問其因,答曰:“無巧不成書”,啊!否則也就沒有了“小酸棗”演唱《小酸棗》這樣有趣的題目了。
更有意思的是,李娜為電視劇配唱的第一首歌,正是由《白玉霜》的導演白唐執導的電視劇《小鎮總理》的主題歌,今天她又來為電視劇《白玉箱》演唱片頭歌《說不盡人間悲喜事》。無論是從演唱技巧,還是感情處理,乃至聲音的運用,都已是今非昔比,給整部片子增色不少。再加上片尾曲郭公芳那饒有韻味的演唱,彼此交相輝映,情趣頓生。到時候,要是誰產生了“轟動”效應的話,恐怕也是不足為怪的。
天公相助
影片的拍攝已近尾聲,只剩下冬天的一部分外景鏡頭了。萬事已備,只欠“冬風”白雪了。說也巧,恰在這時,滿天陰雲密布,“千里冰封,萬里雪飄”。老天爺彷彿也加入了攝製組的行列,用那神來之筆,把整個京城裝點成了一個白色籠罩的世界,任攝製組盡情隨意地去拍攝。
風雪中帶過街樓的老北京衚衕;
雪地中正在覓食的麻雀,呆立雪中的喜鵲;
大雪夜蓋的前門箭樓;
白玉霜和李長生私奔,從上海回到北方鄉下,雪原里驅馬車行走;
白玉霜與李長生在銀裝素裹的北方村集買豆腐……
這一組組鏡頭,都在天公的幫助下,順利完成了拍攝,讓人情不自禁地發出《白玉霜》劇組真是“天時地利與人和”的讚歎。
拍李長生家的小院時,房東大娘特別熱情,一大早起來后,就把整個院子的雪掃得乾乾淨淨,本想是為攝製組拍攝提供方便,可實在是弄巧成拙。導演望著打掃過的院子,發出了命令,讓全體人員收集白雪“撥亂反正”重新裝飾院子,恢復滿地白雪的本來面目。一場白玉霜初見婆婆的戲,就在這用白雪鋪蓋院子的勞動中,拉開了序幕。
雪地里,拍完全劇最後一個鏡頭時,全體攝製組人員想起這一百多天的日日夜夜,抑制不住內心的喜悅,大家一擁而上,奔嚮導演,在一片歡笑聲中,把老導演拋向了空中。不知是誰說了一聲“大家別接著,都撒手”,又引來了眾人的歡快大笑。就在這一片嬉笑聲中,《白玉霜》的拍攝任務完成了。老天爺適時無私的贊助,給這部電視劇的拍攝劃下了一個精彩而畫滿的句號。
荒野中的孤女墳
——評劇皇后白玉霜之死
白玉霜,我國著名評劇演員,電影明星,曾被譽為“評劇皇后”。1942年被黑暗的社會迫害致死。白玉霜出身藝人家庭,從小學藝,一生受盡磨難,在她紅極一時時,曾想隱退山村,過平民生活,但未能成功,人們由此又把她稱為“豆腐西施”。
一霎時,她——傾國傾城的一代名伶,氣息微微,眼神散亂,沉重的軀驟然變得像紙一樣的輕薄,一縷香魂飄飄悠悠地向永恆的黑暗裡墜落下去。頑疾已經用痛苦的枷鎖將她捆綁一年多了,她像古希臘悲劇中的墨勒格,被一種超自然的毒火日夜地焚燒著,無休止地承受著浸入骨髓的痛楚折磨。每逢痛到極點全身麻木之後,她孱弱的身軀才得走入無知的夢境,得到了暫時的解脫,在睡夢中略微恢復一下疲竭的體力,然後再去忍受那無法忍受的折磨。團團灰暗陰冷的迷霧從她身邊擦過,意識的火花忽暗忽明。她回首望望,她所走的是一條淚痕斑斑的曲徑、凄楚迷亂的人生,這使她更加無望,更加情絕。她孤零零地來到了這個涼冷的人世間,如今,又孤零零地從這個冰冷的人世間離去。她慢悠悠地又睜開了眼睛,在暗淡的光線里搖晃著幾個人影,她痴滯地凝視著那些似曾熟悉但又陌生的面孔。
白玉霜的繼母胖李奶奶還俯在她的身上,用手帕為她擦拭著額角滲出的汗珠。她微微地仰起了頭,用畏怯和乞憐的眼光在灰暗的屋子裡搜尋著。她搜尋到了,在屋角里坐著一個三、四十歲的中年人,滿臉憂傷,一身淚痕。他也是個風塵中蹈蹈獨行的旅客,租籍廣東,為了避災弭難來到了北平,寄寓在王府井美白理髮館經理、他的乃叔的門下。白玉霜第二次回到北平唱戲,在美白理髮館里理髮時結識了他。從此,便在罪孽的人寰里建立起感情。“媽媽!”她聲音顫抖地說。
“孩子,你還有什麼話?”胖李奶奶湊過身來。
“媽媽,我為您出了一輩子的力,現在,我只求您一件事,希望您能夠答應我⋯⋯”
“什麼事?”
“我想要結婚!”
“啊?!”老太太驚呆了,屋裡的人也都驚呆了,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這是病人昏迷中的囈語,還是那倍受侮辱的生命所迸發出的痴情的絕唱。
“我想要結婚!我想要結婚!”她又尋望了一下坐在屋角里的中年人鄺某,期待地問:“你同意嗎?你同意和我結婚嗎?”
屋子裡的人都沉寂無聲,心頭上比壓著一塊石頭還要沉重。中年人走到她的跟前,默默地拉住了她的手,向她點了點頭,酸心的淚珠籟籟地滴在她的手背上。
她滿意地笑了,眼裡滾動著感激的淚花:“你,還算是個有良心的人!”
“咳,我活到了今天,總算有丈夫了,有自己的丈夫了!這不是演戲,不是在舞台上,不是與人假扮夫妻!”她咳嗽了一陣子,氣息越來越微弱,但嘴裡仍在呢喃:“不是演戲,不是假扮夫妻⋯⋯”
人們哀嘆、傷心、悲泣,用難以描述的複雜感情,為她操辦著婚禮和葬禮所需用的物品。
她為什麼在臨終之前,又驀地想起要結婚呢?
難以理解的事,說起來也很容易理解。評劇舞台上另一朵奇異的名花,自號為“評劇大王”的劉翠霞病死了。在那個社會裡,一個女伶不管名聲有多大,才藝有多高,但雨打飄萍的生活和凄涼卑微的身世,使她們幾乎沒有一個得到好的結局。劉翠霞看到了這一點,臨死前曾向與她同居的陳某提出了正妻的身份問題。那個姓陳的還算是個仗義的男子,劉翠霞死後果然以正妻的名份厚葬了她。一些老藝人看到了無不感嘆地說:“劉翠霞總算有眼睛,找到了個有良心的人,死後沒有被葬到孤女墳里去!”什麼是孤女墳?在有鬼神的世界里,那是個荒涼凄冷的海隅,被人遺棄的孤島。按照封建禮教的世俗規定,一個成年而未嫁人的女人,就不能埋列祖墳里去,只能在荒野的地方孤零零地起個孤女墳。
白玉霜在彌留之際想到了這可怕的結局,全身嚇出了冷汗。她真的要像戲曲里唱的“天盡頭,何處覓香丘”嗎?她為了尋覓一杯凈土,尋覓一杯不被遺棄在荒野的角落裡的凈土,才在生命最後的剎那,做這一番絕望的掙扎。
她在鄺某的手裡,滿意地合上了眼睛。但是,等待她的不是笙管笛簫的花燭洞房,而是夜暗掩泣、陰風慘慘的靈堂。她還沒有來得及細想做新娘子的甜情蜜意,魂魄便已飛到虛幻的鴻蒙太空。人生!多麼短暫的人生呀!1942年8月10日,這個評劇皇后便悄然離開了人間。
命運之神是不肯輕易向人妥協的。白玉霜生前竭力掙扎想要擺脫掉的悲劇,死後依然落到悲劇之中。沒有哪家的黃土壟中,肯收留她那副“輕賤”的骨頭,沒有哪家的墳塋肯收留她那蕩蕩孤魂。她到底還是作為孤女墳主而被埋在天津公墓里,墓前一塊小小的石碑不明不白地記著:“李桂珍之墓”。甚至連評劇演員或者是白玉霜的字樣都沒有留下。僅僅這一塊荒涼的石碑,就給人一片荒涼之感。
“咳,又是一個無親無故,孤苦伶仃的女人!”路經此處的人不免要唏噓感嘆地說有誰知道,她就是那紅盛南北、赫赫有名的評劇皇后,電影明星白玉霜呢?
1937年2月,正當白玉霜紅得發紫,人人傾羨的時候,一條奇特的新聞又在白玉霜身上發生了!白玉霜與人私奔了!
白玉霜在藝術上有所追求,並為這種追求付出了沉痛的代價。如今她唱紅了,人們看到她紅衫翠袖,車接車送的好不福氣,可是人們看不到她內心裡的痛苦。不知道在那歡歌笑語的生活里一個女伶所受到的蹂躪和摧殘。她的身心無時不在污濁中淌著血、淌著淚。在那個年月,一個女戲子越是唱得紅,越遭來更多的妒忌、中傷、暗算和煩擾。
最使她感到痛苦不堪的,還有她與繼母李卞氏之間的關係。李卞氏生得胖乎乎的,一身是肉,因此外面都叫她胖李奶奶。她視財如命,刁狠貪諂四個字讓她都佔全了。白玉霜戲班表面上掛的是白玉霜的名字,實際上是她一人當家作主。她把白玉霜當成搖錢樹,一心只想摟住這棵樹不斷地給她搖下錢來,至於女兒的婚姻、戀愛、個人幸福,她則一概地遮攔。
1937年,白玉霜已經整整30歲了。在那年月里,對於一個女人來說這是一個很可怕、很難聽的歲數;特別是像她這樣身世的女人。在生活上,她也曾有過熱烈的追求。女性的柔情、傾心的愛慕、顫抖的激情,她不只是在舞台上才有,在戲裡面佯裝,奔放的個性不會饒過她在這方面的渴求。她渴求女人的一切,她要有女人所應當有的一切權利。可是胖李奶奶不會輕易地放過她,就像安徒生童話里的巫婆,她知道該用什麼魔法纏住海的女兒,纏住她那顆奔放的女人的心。
“你不能嫁人!有丈夫就別想唱紅了,那些有錢有勢的人誰會花錢去捧一個有丈夫的旦角?”她用無數的實例攔住女兒一顆奔放的心。
對於藝術上成功的渴望,還有那些浮淺的虛榮之心,緊緊地羈絆住她,羈絆住她在生活上勇敢追求的思念。久而久之,內心的失望形成了巨大的壓力,使她必須毀棄自己,毀棄藝術,毀棄她嘔心瀝血所爭得來的一切。成功、名望、虛榮,都不能滿足她,她要追求生命的真諦,要求返本歸原於自然的本體。
她被俗念的灰塵蒙遮的心靈得到了凈化,眼前的景物豁然開朗。於是,她不顧一切地與人私奔了。舊曆年底封箱后的那一連串表演,一半是用來掩飾她內心的慌亂,一半是用來遮人眼目賭中安排好她出逃的計劃。更為出人意料之外的是,與白玉霜私奔的人,既不是風流小生,也不是洋場闊少,而是白玉霜戲里班裡的一個樂工——打鐃鈸的李永起。李永起是個鄉下人,自小就來到戲班裡做事。他的一對饒鈸打得有聲有色,很受人歡迎。他為人老實厚道,對於母親極其孝順。有一次母親生病,他背負著母親步行了幾十里路出外投醫。白玉霜喜歡這個淳樸的人,她浪跡江湖幾十年,什麼風雨沒經過,什麼樣心腸的人沒見過,與那些口蜜腹劍、朝秦暮楚、信口雌黃、指山賣磨的人相比,她在李永起的身上找到了人的本性。她要衝出那絲竹粉墨的牢籠,虛情假義的巢臼,不正是要依託在這個人的身上嗎?
“勘破三春景不長,素衣頓改昔年裝。”白玉霜與李永起回到了他的農村老家,在依傍田野的小屋子裡,在爬滿青藤的瓜棚架下,在崎嶇狹窄的田壟上,心境平和地去尋覓那青春的殘陽。白玉霜換了一身村婦打扮,隱姓埋名,想在這個被人遺忘的恬靜角落裡,過一個普普通通的女人生活。他們夫妻兩個開了一個豆腐坊,李永起做豆腐,白玉霜賣,倒真的做起“豆腐西施”來了。這也是她的一種追求,是對她過去受侮辱受損害的身世的洗滌。總之,她想憑藉自己的大膽和夢幻,來創造一種新的生活。
一個紅遍南北的名伶,本來就不容易隱匿起來,而她自己又不注意隱匿。任性、大膽和過於潑辣,又破壞了她那恬靜的鄉間生活。然而,最使她得不到安生的,還是她自己內心裡的煩躁。她曾下定決心要拋掉藝術,告別舞台,那是她在兩種追求中間所做的無可奈何的選擇。如今冷靜下來了,一種追求得到了滿足,那丟掉了的一種刮心絞腸地牽惹她的心思。她的生活不能沒有戲,雖然她早已厭倦了那逢場作戲的人生。
自從白玉霜出走之後,胖李奶奶在上海單靠一個小白玉霜支撐不起門面,幾天之後就收拾起戲裝返回天津老家了。小白玉霜逐漸成長起來了,她吸收了養母的許多長處,唱得也很好聽,觀眾逐漸喜歡起她來。白玉霜聽到小白玉霜漸露頭角的消息,心裡就更不是滋味了。田間的小路,潺潺的流水和屋角的桑榆,再也留不住她勃然興起的雄心。1937年夏天,她又自動地返回故里,找到了她的戲班,登上了已經久別的舞台,和廣大觀眾見面了。
但是,在那個污濁邪惡的社會裡,不會因為一個女演員是個名人、紅角,她的地位就可抬高几尺,黑暗勢力就會放鬆對這個柔弱可欺的女子的侮辱與欺凌。相反,他們還正因為她有錢、有名、有姿,要想著法兒來討她的便宜,像欺侮一個小尼姑那樣的勇敢。示阿Q們的在舊社會裡那些唱戲賣藝的人除了要受官紳土豪的欺壓之外,還要受一些報屁股文人和下流記者的敲詐勒索。哪一個關節沒有打發好,他們就會搬弄起事是非無中生有地給你登上那麼一小段。等你出來抗議,他們過兩天再來一個更正或闢謠。可是這種事情是更正不了的,一般的人看那些無稽之談的得多看那些闢謠和更正的少。而且謠言一出,輿論大嘩,你的人格、名譽以及營生都要受到損害,所以,一般的藝人寧可自己省吃儉用一點,也要按時按節地把銀子送到報界那些老爺手裡去。
有一次,白玉霜不知怎地忽視了這個關節,沒有按時把銀子孝敬過去,無形之中得罪了一些人。於是,在《新民報》上就登出了一篇半誣半罵的狗屁文章。白玉霜自知得罪不起,便託人請《新民報》總編輯吳菊痴到前門外同和軒里去吃飯。這真是那座廟不燒香也不行,哪位菩薩不拜也不靈。白玉霸只好認了這場破費,恭恭敬敬地請了酒席,並在席上遞過去一個不大不小的錢包。吳總編輯接受了這雙重的厚意,誰知得意沒有多久,剛剛離去那裡不遠就被抗日除奸的人開槍把他打死了。
總編輯該死該活,是他自己的氣數。他花了昧心錢,做了昧心事,死心塌地給日本鬼子效勞,被打死是他的報應,原本得不著花錢請他吃飯的白玉霜的事。可是當天,白玉霜就被抓走了,扣押了一天之後,被當作政治犯給監禁在沙灘紅樓的日本憲兵隊里。
白玉霜演過《可憐的秋香》、《可憐的芸娘》,可是誰也沒有她自己可憐。她在日本憲兵隊里受到了慘不忍睹的酷刑。日本人把她的下身扒光,由兩個兇手用棕毛繩子拉磨她的陰道,血流滿地,白玉霜凄厲地慘叫了幾聲,就昏倒過去了。
白玉霜在日本憲兵隊里關押了很長一段時間,受盡了折磨,不僅使她花也似的容顏被摧殘得不像人樣,而且那次酷刑,竟使她落下了致命的病根。
舊社會的藝人都有自己一部酸心的血淚史,但還沒有聽說過誰,比白玉霜受到的摧殘和凌辱更多。她那頂皇后加明星的桂冠,給她帶來的卻是更多的不祥和災准。
後來又是花了很大一筆錢,買通了憲兵隊里一個姓金的人,才算把她從獄中解救出未。白玉霜出獄之後,身體便孱弱下去了。從前那豐腴膏潤的肌膚已蕩然無存,鮮艷的臉色也黯淡下去,只剩下一雙大眼睛空空蕩蕩地轉動者,讓人看了更感到心酸,可憐。她還是照樣地唱戲,一天兩場風雨不停。
這一方面是她繼母胖李奶奶利欲熏心、貪得無厭,不讓她空過一天地給她掙錢,另一方面,也是她自己剛強,不肯向命運低頭。一旦不登台演戲,她也覺得生活空蕩無味,沒意思。有時,她渾身沒有一點力氣,要靠人攙扶走上台去。可是一旦上了台,她就完全變了樣,對藝術的酷愛會把她生命中最後一點力氣調動出來。
1942年,自玉霜徹底地病倒了。摧殘和勞累,衝垮了她體內最後一道健康防線。她住進了東交民巷的一家德國醫院,經醫生檢查,得的是子宮癌。當時的人們對於癌的可怕性還不甚了解,因此,白玉霜在醫院裡住了一段時間,病情稍微穩定之後就出院了。回到天津之後,她仍然照樣堅持演戲。不僅演出,還要排練新戲。那時,尚小雲正在上演《梅玉配》,她看了戲后便想法子託人找來了本子,自己每天背台詞,練身段,甚至連唱腔都設計出來了,要不是因為後來病危,她一定把這齣戲移植過來。
有一天,她正在天津北洋戲院里演《閨門勸婿》那齣戲,還沒演到一半,癌細胞突然破裂,血流了一腿,藝人們看她實在可憐,勸她底下的戲就別唱了。白玉霜慘淡地對大家笑了笑,有氣無力地接過人們遞給她的一杯水。喘吁了一陣子之後,仍然讓人將她攙扶到戲台上。她說:“我死,也要死在戲台上!”
不久,白玉霜病情就惡化了,重新住進了醫院。生命,跌落到無望的深谷里。她病體枯槁,形消骨立,在病床上忍受著痛心的折磨,忍受著痛心的毀滅。
她曾幾次昏迷過去,一身無主地向那永恆的黑暗中沉落下去。
最後,她終於在那灰茫茫的無垠中消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