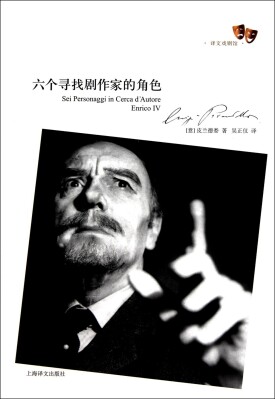六個尋找劇作家的角色
六個尋找劇作家的角色
《六個尋找劇作家的角色》是義大利劇作家路易吉·皮蘭德婁創作的戲劇。作品引進傳統的“戲中戲”的寫法,在劇中安排了一主一副兩條線索。表面上,戲里演的是劇團排練,實際上,以一個家庭的悲劇為主。
作品運用“戲中戲”的形式,平行地展開了兩個主題:“角色”的故事是主要主題,這個主題不是為了講述一個陳舊的悲歡離合的人間故事,而是為了對造成“角色”悲劇的原因進行探討:最深刻的原因就在於人性和人本身的存在。另外一個主題即對於戲劇本質的探討,一舉澄清了舞台與真實、形式與本質的關係。
某話劇劇場的舞台上,經理兼導演與幾個演員正準備排練皮蘭德婁的《各盡其職》一劇,六個臉色蒼白,幽靈似的的人物突然闖進來。他們自稱是被作者廢棄的某個劇本中的人物,但劇作家不願意或沒有能力使他們成為“藝術世界的實體”。他們想獲得舞台生命,請求導演把他們的戲排出來。開始時,經理以他們干擾排演和自己不是作家為由,拒絕了他們。後來,出於好奇,就詢間他們在劇中的戲究竟是什麼。其中的父親、繼女等起先是講述他們之間的故事,繼而,經理以為有趣,就讓他們演示,並令劇院的演員們一對一地向劇中人學習以便準備以後也表演這個故事。
這是一對離異的夫妻和四個同母異父的兄弟姐妹之間的故事:父親和母親是合法夫婦,但感情不和。母親和父親的秘書情投意合,被父親逼迫私奔。父親和母親所生的兒子被送到鄉下去撫養。母親同秘書移居他鄉,生下一男兩女。父親由於孤獨,想起過去與妻子的生活,又後悔自己的懷疑和粗暴,就去看望已經上學了的繼女。後來秘書病故,一家人無以為繼,母親只好帶著孩子們回到故鄉。她生活困難,就從帕奇夫人的縫紉店裡領些針線活來做,維持生活,因而誤入了帕奇夫人的圈套。說母親把活做壞了,要她賠償,逼替母親做活的繼女在她家后室當妓女。繼女為了替母親賠錢和生活,就開始了賣淫。有一次父親去妓院廝混,差點與繼女發生了亂倫關係。這時母親趕來說明情由,父親得知秘書已死,便接母親和三個私生子女回家團聚。而兒子憎恨母親當年拋棄他同秘書遠走,並且仇視三個弟妹。繼女趾高氣揚,蔑視玩妓女的父親。小弟妹非常怕大哥,而且嚇得不會說話,家中十分不和。一次小女孩掉入花園池中淹死,大家搶效,而小男孩躲在一顆大樹背後,眼睜睜看著小妹妹淹死,隨後掏出一支手槍,把自己打死。經理和劇院見習的演員們奔忙慌亂,繼女瘋了一般尖聲大笑,越過觀眾席,跑齣劇場不見了。
《六個尋找劇作家的角色》寫於1921年,皮蘭德婁生活在義大利獨立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這一段歷史時期,這正是義大利政治形勢急劇變化的時代。由於連年征戰,窮兵黷武,加重了義大利人民的負擔,人民生活極端貧困,與統治者之間的矛盾進一步加深。獨立后的義大利,以它的軟弱無能和貧窮落後,顯示出與民族復興運動所提出的理想的義大利毫無共同之處,在一般資產階級中造成一種普遍的“復興后的失望情緒”。而代表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墨索里尼上台後,法西斯的控制無孔不入地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方面,整個社會被禁錮得像罐頭一般的嚴密,令人感到窒息的痛苦。一些正直的藝術家對這種殘酷的現實有著較為清醒的認識,自覺或不自覺地站到了反對派的立場上。皮蘭德婁通過作品訴說出普通資產階級的危機意識、孤獨感覺和絕望情緒,彈出了一個時代的悲愴的失望之音。
繼女
繼女從出場開始就渴望成為完整劇本中的一員,她直接對導演要求:“我們就可以做您的劇本”。她作為被作家拋棄的一員十分明白自己失去歸宿,因此她不斷地對導演重複“我們是六個很有趣的人物”,正是她在場上率先透露出六人過去的複雜關係才使導演同意看他們在劇場中重現過去的場景。同時,繼女的行動又是矛盾的,她的不可變性將她放置在一個尷尬的境地—她並不願意正視過去的某些既定事實,比如當年母親離家的原因和差點和父親發生“亂倫”這一事件,顯然後者令她更為羞愧。當最後她決定將過去完完整整表現出來卻得到了經理的一句:“真實性是有限度的!”這讓深陷“人生中最殘酷,最卑鄙經歷”中的繼女所不能容忍。她只想要真正地還原過去,以祈求在當下的時間獲得超脫,但最終劇情以小男孩自殺為結局,這顯然是令其不能接受的。所以最後繼女只能再次逃離劇場,依舊停留在過去的戲劇情節中無法自拔。
父親
父親的這一角色顯然帶有作者本身的意志。他並不遵循一個角色的本分,甚至有時成為作者思想的傳聲筒。他竭力指出自身的真實性,認為自己是一個“活人”。劇作家沒有能力讓他們成為藝術世界里的實體。他說道:“因為幸運地降生為“角色”的人能夠嘲笑死神。他是不死的人,劇作家,作為創造的工具,是得死去的,他的創造物確不會死,得到了永恆的生命。”他在某些情景下確實超脫了角色的限制,但他並沒有在創作,他也在為找不到作者而痛苦。他的悲劇是良心的悲劇:“我們都認為‘良心’只有一種,其實不然,有許多種‘良心’,人們的良心是各式各樣,形形色色,應有盡有的。”遭受了妻離子散,家庭不睦,又差點和繼女發生“亂倫”,他只能竭盡全力與命運搏鬥,以尋求和解。因此,父親這一角色是最堅持表演六人的過去,以獲得真正的生命。這樣就能從戲劇層次跳躍到敘述層次,完成一種作為角色的完滿。對他來說,“事實只是一隻口袋,它空著的時候立不起來。要使它豎起來,必須往袋子裡面裝上支配行動的理智和情感。”儘管父親一直在做不停的嘗試,仍然心甘情願的接受了作家賦予他的生存理由,並且毫不遺憾的放棄他自己的生存理由,所以他妄圖打破當下與過去的間離依舊是失敗的。和繼女一樣只能停留在過去。
帕奇夫人
帕奇夫人這一角色是劇作中戲劇層次和敘述層次的連接點,真是這一人物形象的出現讓過去和當下不再向易卜生戲劇中無法跨越橫亘在過去和當下之間無法逾越的鴻溝。因為帕奇夫人作為角色一開始在戲劇層次就沒有被拋棄,通過父親、繼女和母親的轉述使得這一形象跨越了過去,在當下的敘述層次得到了實體再現。帕奇夫人的出現和離開都是充滿自由和驚喜的:當經理問帕奇夫人在哪裡時,父親的回答是:她還活著,但她沒有同我們一起來。這就昭示了其角色的特殊性。父親解釋只有在情景真實的情況下帕奇夫人才會出現,舞台布景構成了一個真實的環境,它的魔力就是招致奇迹出現。作為最真實的角色,她甚至比場上的演員都要真實(因為人與角色是統一的)。在她出場后,重頭“亂倫”戲才得以展開,不過帕奇夫人的出現並不意味著過去和當下的完全打通,因為她受到了來自經典戲劇形式里母親角色的攻擊。帕奇夫人說:有你母親在場我什麼也不幹了。然後便拾起被打掉的假髮匆匆離開。這一角色在場上停留時間最短,卻顯示出本劇的最特殊之處—在戲劇危機下作者通過對戲劇形式的探索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形式與內容中的主客體關係的不同。帕奇夫人用在表面上違反邏輯,卻是真正需要的方式與整個作品的生命有機的聯繫在一起。
母親
母親這一角色從來不把獲得生活看成人物自身的目的,或者說她本身並沒有這個自覺性,因為她從未片刻離開她的那個“角色”,不知道自己還需要演戲。這是一個所謂“經典的戲劇形式”下,即自亞里士多德起,一直到啟蒙時期的歌德、席勒等理論家所構想的一個“超歷史的”、“絕對的”、“原生的”戲劇形式中應該出現的人物。是一個完全被動的角色,她所有的一切都是被劇作家安排好的,而她本身卻不自知。她被帶到導演面前的高興並不是因為她希望從導演那裡獲得生活,而是能讓她與兒子演一齣戲,儘管這場戲本身是沒有存在過的。她的生活經歷來自於別人的講述,她僅有的反抗也是由於一個出於母親的本能而不是打破所謂的過去回到當下。她不知道自己身為一個劇中人,但是這並不妨礙她成為一個劇中人物。導演讓她將一切事情看做過去,她的回答是:“不,事情沒有過去,它正在發生,而且永遠不會過去。先生,我的痛苦不是假裝的,我是個活人,時時刻刻感受到我的痛苦。它是不會過去的,它將永遠存在。”生活形式的固定在她身上得到了體現,她既活在過去,又活在當下;或者她既不活在過去又不在當下。
兒子
兒子作為一個幾乎不講話的人物活在戲劇層次,但他在劇中製造了有機的,符合自然規律的混亂。他的不配合和軟弱幾乎導致了小女孩溺水而亡,他是唯一一個作為尋找作者的角色而生存的。他雖然沒有跨越到敘述層次,但給這一層次製造了符合邏輯的混亂,是作者對於戲劇形式的一個大膽創新。而小男孩和小女孩作為不說話的“旁觀者”,沒有過去,因而自然地被歸為敘述層次的一員,小女孩的溺水加速了六人之間的戲劇衝突,小男孩更是以一聲槍響改變了劇情走向,在情節上給本劇劃上了句號。兩個層次最終合併為一與戲劇形式和解。
《六個尋找作者的劇中人》1921年在羅馬進行首演時曾引起兩極反應;這部兼具劇中劇和即興表演的戲碼,加上作者刻意借劇本反映出真實生活的語言等,都徹底顛覆了當時大家對戲劇的理解。一個舞台上同時有兩組人馬:一組是正在排演的劇團演員,一組是找不到劇作家的角色,兩方無法進行溝通、總是各說各話搶著演出自己的故事,彷彿自己才是真實的人物。劇中劇的父親和繼女是兩個發展最完整的角色,藉由他們從不同的角度回憶同一個事件,讀者可以看到真相是非常主觀的,而真實的人物也不只有一種人格。此外,皮蘭德婁更借著父親之口,說齣劇中角色比演員更真實,因為對角色而言“幻相和實相是一體的”,更可視為劇作家自己對藝術本質的詮釋。
《六個尋找劇作家的角色》的“戲中戲”結構揭示了一個對立系統,這個對立系統既是兩大人物集團的對立,也是兩種藝術形態的對立。此外,還映射著生活現象與生活本質的分歧與統一。
劇團成員代表著人生的表象,體現著現實與不定。人生其實是在掩蓋了許多毛病和弊端的情況下進行的,這才是生活的現實。那些毛病無論大小,集中體現為人與人的無法理解與難以協同。這可以用文本中出現頻率非常高的兩個符號來歸納:“?”和“~”。問號意味著理解的乏力,透露著個體對另一個體的真實意圖的不解與艱難探尋:布景員問舞台監督什麼時候幹活,導演問女主角是否有戲份,提詞員詢問是否要念人物動作,男主角問是不是非得戴上廚師帽,經理問女主角是否明白他對角色的解釋,這些頻繁的發問以及隨之而來的不滿意的回答共同暴露了劇團成員之間缺乏默契的事實。感嘆號則同時意味著對自我聲音的堅持和對非我聲音的排拒,它包藏著人與人之間或明或暗的較量:布景員說“也得有我幹活的時間!”是在與舞台監督爭奪工作場所;舞台監督說“別跳了!經理先生來了!”暗含著下級員工對上級經理的畏俱;男主角說“對不起,這很可笑!”表達著他對導演要求的不贊同……毫無疑問,這是個漏洞百出的劇團,可令人驚異的是,即使內部一再變得不和諧,他們的工作仍然在一瘸一拐地向前進行。
劇團成員的行為還表現了人生的捉摸不定與無法把握,體現出生活的變化。布景員在該排演的時候還沒完成工作,青年男女演員們在開工之前翩然起舞,女主角帶著一隻狗遲到,經理不懂劇本的意義卻仍然繪聲繪色地解釋……劇團成員工作時的這些表現表明他們始終處於一種“不在狀態”的瑣碎當中,這揭示了生活的動態及其無奈:人們永遠在演戲,卻永遠無法進入角色。
生活本質與生活表象的不同在於,它以絕對真實反抗遮蔽行為。未完成的劇本的角色代表著生活的本質一面,堅持真實的他們從不掩飾其內部問題,生活的本相在他們身上明朗無疑。“父親”、“母親”、“繼女”與“兒子”之間鮮有共識,他們對彼此的陳述不斷發出“不是這樣!”“不是真的!”(繼女語)“不對!不對”(母親語)“這是胡說!”(兒子語)的否定,“父親”雖沒有這樣激烈的措辭,卻更直接地戳穿了這些措辭的真實意指:“我們自以為了解了,其實根本就不了解。”在這些人物之間,“謊言”只是由於無法理解對方而造成的誤讀,而非虛偽的產物。“父親”對妻子心理的誤解使他謀劃了秘書與妻子的“私奔”事件,並導致了後來的亂倫、溺水、自殺等一系列悲劇。但更具悲劇性的是,他們絲毫不去迴避溝通失敗所釀成的苦痛,他們的言詞表明,他們明確地意識到了彼此隔膜的存在卻無法消除,因為人與人之間從本質上難以具備真正理解的可能,因此,痛苦的真實無法躲避,更無法掩飾。
與劇團演員相比,未完成的劇本中的角色更能夠把握自身,他們面對劇團演員對真實的扭曲,不斷發出“那不是我”的呼籲。他們很清楚自我是什麼,卻不清楚別人是什麼,以至於在四面碰壁后又陷人了對自身的拷問。“父親的悔恨、繼女的報復、兒子的輕蔑、母親的痛苦”都根源於此。再者,角色們所代表的永恆是一種命運的永恆。正如母親所說:“事情正在發生,永遠發生著!我的痛苦是無窮無盡的。”在這一點上,生活的表象與本質趨向是一致的,它們都要求持續下去。因此,角色們的不幸不可能被阻擋,男孩終究要自殺,女孩終究要溺死,繼女終究要消失,一切都按他們自己所說的那樣進行。這提醒人們,人生的劇情無法被打斷,悲劇卻是唯一的主題。
作者將被捨棄的角色放置在舞台上,既通過角色的對話展現出角色過去的故事,又讓他們之間的關係處於當下。他們在找尋劇作家的同時又要處理各自人物內部的矛盾衝突,為了能將這些衝突調和在一起,作者只有捨棄現有的戲劇的形式,在主題中貫徹這種矛盾,產生不是原來計劃的作品,取而代之的作品講述了原來作品的不可能。皮蘭德婁在《六個尋找劇作家的角色》里設置兩層經典戲劇形式:一層為當下(作為敘事層),另一層是過去(戲劇主題)。這裡的“過去”不像《博克曼》那樣被逐入內心,而是和當下互相映照、彼此滲透。之所以會有這樣戲劇形式的產生涉及到了“戲劇的危機”的發現和如何解決的問題。
《角色》採用戲中戲的雙重敘事,混淆現實與戲的界限,顛覆真實。劇本說明舞台的布景與沒有排戲時一樣,布景員一上舞台就在釘釘子,卻被舞台監督給趕下去。這些本來在舞台背後的事情,卻被搬到舞台上表演,從一開始就試圖混淆現實與戲的界限,讓讀者或觀眾弄不清楚虛構與現實間的距離。在戲劇的整個演出過程中,經理指揮演員的演出過程,把舞台背後的編排過程拉到舞台上表現,這些都具有後現代主義自我指涉的特點。從經理到演員的對話,我們得知他們排演的是皮蘭德婁的劇本《各盡其職》,劇作家跳出來說明自己的劇本在被排演,本身的敘事就具有自我指涉性。然而在排戲的過程中,又來了六個劇中人,帶來了他們的故事,演員根據劇中人的故事又開始排演。甚至在戲中戲中,經理還與劇中人父親探討演員與角色的真實性、永恆性,現實生活與戲劇哪個更具有真實性的問題。六個劇中人自稱是作家沒有完成的劇本中的人物,他們的故事卻比現實生活還真實。這種從布景、人物對話、故事內容,都把讀者或者觀眾帶進一種現實還是戲的模糊混沌狀態中。這種本真的敘事,不僅說明了戲劇的虛構過程,模糊了現實與戲的界限,更顛覆了現實的真實性。
《角色》一開始就是開放的結構。不僅語言含混,語義具有開放性,隱喻性;敘事的雙重結構也具有開放性。在經理指揮劇團人員排演“各盡其職”的過程中,語言莫名其妙,情節也是支離破碎,本身就具有極強的隱喻暗示性。如:經理“還把小狗帶來!好像這裡的狗還嫌少。”“根據劇中各個角色的作用,您代表理智,您的妻子代表本能”“您扮演這個角色時,應當有意識地使”這些語言明顯的話中有話,具有極強的隱喻性。六個劇中人即六個角色自己走來,要求排演他們的故事。這六個劇中人來的莫名,走得也奇妙。他們的故事怎麼發生的,我們可以通過他們的敘述得知,然而他們每個人的敘述,對同一事件具有不同的看法,因此,讀者不僅要產生疑問,什麼才是事實真相。比如父親送走妻子的真實心理,真實原因真的如他所說嗎?他自己曾這樣的表述,“對於一樁無法名言的事實,對於一件已經鑄成的大錯,找一個能夠平心靜氣的含糊的措辭,豈不使大家心裡都好受一些嗎?”使得他送走妻子的無私心態,又具有可疑性。這樣敘事也就具有開放性,具有多重解讀方式。這種開放性的結構,使得劇本顯得神秘,離奇,更適宜表現作者想要說明的人生的不確定性,荒誕性。
《六個尋找劇作家的角色》是皮蘭德婁戲劇的扛鼎之作,皮蘭德婁把角色的心理活動直接搬上舞台,清晰地看到了角色自身的抗拒,於是在自身對戲劇形式的抗拒下在創作方法中組織雙重層次,即戲劇層次和敘述層次,就此揭開了戲劇史上新的一頁。
路易吉·皮蘭德婁(Luigi Pirandello,1867—1936),義大利戲劇家和小說家,一生創作了40多部劇本,主要劇作有《誠實的快樂》、《是這樣,如果你們以為如此》、《並非一件嚴肅的事情》、《像從前卻勝於從前》、《六個尋找劇家的角色》、《亨利四世》、《給裸體者穿上衣服》、《各行其事》、《讀者今晚即興演出》、《尋找自我》等,其中《六個尋找劇作家的角色》和《亨利四世》已成為世界戲劇史上的傳世傑作。1934他因“果敢而靈巧地復興了戲劇藝術和舞台藝術”榮獲諾貝爾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