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傑克·鮑莫爾
威廉·傑克·鮑莫爾
威廉·傑克·鮑莫爾,1922年2月26日-2017年5月5日出生,美國經濟學家,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榮譽教授、退休高級研究員,紐約大學經濟學教授。他的個人著作包括《微觀經濟學》、《超公平主義》、《企業家精神》、《管理學》、《支付結構》以及《資本主義的增長奇迹-自由市場創新機器》;在他和別人合編的著作中,包括《好的資本主義,壞的資本主義》、《生產力和美國的領先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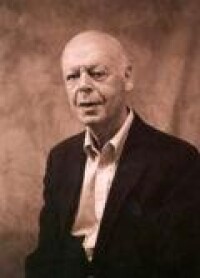
William Jack Baumol
威廉·傑克·鮑莫爾的理論頗具原創性,在經濟學領域很有影響力。在超過半個世紀的時間裡,他一直保持著旺盛的創作精力和廣泛的興趣,他長期在普林斯頓大學任教,在企業行為理論、產業結構理論、通貨膨脹理論、藝術品市場、環境政策以及競爭政策領域,都有傑出的貢獻。80歲高齡的時候,鮑莫爾出版了《資本主義的增長奇迹-自由市場創新機器》一書,將其持續了三四十年的創新研究進行了系統總結,這本書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論證寡頭壟斷的自由市場,創新將不可避免,經濟增長將自動得到保證,顯然這是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當年提出來的命題;第二部分對微觀經濟學理論的一些工具進行了改造,來適應處理創新問題的需要;第三部分用長期宏觀經濟學方式研究歷史上的經濟增長。
鮑莫爾較廣為人知的研究有可競爭市場、交易性貨幣需求的鮑莫爾-托賓模型、鮑莫爾成本病、庇古稅等。
2006年,美國經濟學會的年度會議特別地以鮑莫爾的名字為名召開,會中更介紹了鮑莫爾教授12篇有關企業家精神的論文,以推崇尊敬他多年來在這方面的研究貢獻。
威廉·傑克·鮑莫爾認為,“資本主義”一詞沒有太強的意識形態可言,它只是一種客觀陳述,說明了生產資料的大部分或相當大部分掌握在私人手裡而不是由政府擁有或使用的事實狀況。從這一定義中,人們並不能推出資本主義不主張和謀求社會利益,但至少是以優先確保私有資本的訴求為前提。不過,同樣是資本主義,卻對經濟的組織方式、政府職能的界定,以及各種其他要素也大有不同。在《好的資本主義,壞的資本主義》一書中,鮑莫爾和兩位合作者便將資本主義分成了四種模式:國家主導型資本主義、寡頭型資本主義、大企業型資本主義和企業家型資本主義。
鮑莫爾等人在書中詳盡介紹了資本主義的四種形態,簡單概括為:國家主導型資本主義是政府試圖支配市場,其代表性政策是扶持某些有望成為競爭勝利者的產業;寡頭型資本主義表現為權力和財富主要是由個人和家族組成的小型集團所控制;大企業型資本主義主要經濟活動都由那些指定的巨頭企業來實施;企業家型資本主義是指中小型創新性企業在經濟中佔據主要地位。儘管這四種經濟體制各有利弊,而且沒有一種模式可以完全涵蓋一個國家,但是在鮑莫爾等人看來,好的資本主義最佳形式應當是大企業型資本主義和企業家型資本主義的混合。實踐證明,在過去的二十多年裡,美國經濟總體上創造了“生產力的奇迹”,而它正是這種混合模式的結果。
另外,鮑莫爾等人也對如何實現經濟增長提出自己的觀點。他們認為,一個國家要實現領先性增長需要滿足四個條件:
1、易於創設和發展企業;
2、生產性企業家能夠得到良好回報;
3、非生產性活動受到抑制;
4、迫使市場競爭的贏家繼續保持創新勢頭。
此外,對於如何釋放欠發達國家的企業家才能,他們的看法是:
1、減少創辦生意的障礙,如簡化企業註冊程序;
2、使法律體系正規化;
3、改善資本的可獲得性;
4、擴大勞動者受教育的機會。
不難發現,鮑莫爾對於那種似是而非,宣稱經濟增長主要是由地理或文化所決定的論調持反對立場,後者是以戴維·蘭德斯的《國富國窮》和賈雷德·戴蒙德的《槍炮、病毒與鋼鐵》為代表。在鮑莫爾等人看來,地理或文化會對經濟的好壞有所影響,但最根本的原因還是政策、制度的正確與否。
作為當今世界上最有影響、最具原創性的經濟學家之一,現年87歲高齡的鮑莫爾是繼熊彼特之後無可辯駁的經濟革新領域的思想大師。他所支持和提出的一些觀點正是發展經濟學中最為主流的思想。例如,支持經濟增長論,否定“反增長論”和“增長極限論”;承認經濟增長是好的而且是必要的,這是所有論述的前提條件;對於經濟增長動因的認識,經濟增長取決於幾個主要要素:資本、勞動、技術和制度,這幾個要素數量的擴大和質量的提高是經濟增長的關鍵要素;對於熊彼特的創新理論和新制度經濟學主要觀點的認同,像技術創新和制度變革、企業家精神、破壞性創造對於經濟增長具有決定性的推動作用等等,它們也都是《好的資本主義,壞的資本主義》一書的立論基礎。
在該書之前,鮑莫爾曾出版了《資本主義的增長奇迹-自由市場創新機器》一書,將其持續了三四十年的創新研究進行了系統總結,這本書的主題宗旨很明確:增長的發動機最終依賴於制度規則,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或許不是最優的技術進步體制,但和其他的經濟制度比,卻是最不壞的制度。鮑莫爾還特別指出,也許人們都有創新的本能,但這些企業家創新能力卻可能因過高的稅收、政府過多的干預、過於繁雜的法律、低下的行政效率,而被引導到尋租或其他非生產性活動上去了,他還特別引用了羅馬、中國宋朝以及歐洲中世紀的例子。反過來說,增長最終依賴的是公平的規則和習慣,這些規則和習慣能夠將人們的創新能力引導到正確的方向上去,這樣才能有持續的增長。可以看出,鮑莫爾對“好壞資本主義”命題的論述承繼了《資本主義的增長奇迹》一書的知識系譜,鮑莫爾試圖在保留現代經濟學的主要成果的同時,將創新和企業家行為納入到其發展經濟學理論的中心地帶。
事實上,在熊彼特之後,研究創新的經濟學家大都走上激烈批判主流經濟學的演化經濟學道路,而主流經濟學則又在引入創新方面進展緩慢,鮑莫爾在兩者間取得了完美的均衡。如果說他上一本《資本主義的增長奇迹》只是繼承熊彼特的遺願,對其當年努力的一個致敬、回應的話,那麼到了《好的資本主義,壞的資本主義》,鮑莫爾顯然是將熊彼特的理論範式運用於資本主義創新增長的實踐,是又一次新的深入和拓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