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詩話
中山詩話
《中山詩話》是北宋時劉攽撰寫的中國詩歌評論的書。共一卷,計六十六則。
《中山詩話》是成書較早的詩話,因此在形式和內容上都有粗疏之處。在內容上,除了進行詩歌評論外,還有不少篇幅是記載和詩歌評論、欣賞沒有多少關係的朝野軼聞,如“景?中羌人叛”記載,“景?羌人叛,詔遺士獻方略,率皆得官,有題關西驛舍曰:弧星熒熒照寒野,漢馬蕭蕭王陵下,廟堂不肯用奇謀,天子徒勞聘賢者。萬里危機入燕薊,八方殺氣沖靈夏。逢時還似不逢時,已矣吾生真苟且。”在這裡劉頒是講一首詠懷詩的產生過程,但在記述中就流露出對北宋仁宗皇帝的不滿,認為自己“逢時還似不逢時,已矣吾生真苟且。”
劉攽,字貢父,臨江新喻人。與兄長劉敞原父同登慶曆(公元1041年至1048年)進士第。劉攽仕途一直不順利,在州縣任地方官達二十年,才至汴京任國子監直講。后受歐陽修、趙概等人推薦,擔任館職,因為與當時的御史丞王陶有夙憾,王陶就聯絡侍御史蘇■一起排擠劉攽,劉攽當時已官至員外郎,因受王陶的排擠,只做了個館閣校勘。到了宋神宗熙寧(公元1068至1077年)年間,才升任判尚書考功,同知太常禮院。
當時神宗皇帝下詔封太祖趙匡胤的孫子輩中品行端正的為王,以供奉趙匡胤。劉攽上疏反對,“按照禮信,諸侯不得以天子為祖宗,應該供奉其封國的祖先。應尊崇德昭、德芳的後代,讓他們世世代代爵位不降,宋廟祭祀時,讓他們列位陪祭,這才是褒揚太祖的正確方法。”後來皇帝就按照劉攽的建議辦理。熙寧年間,是王安石變法的歲月。王安石在神宗的支持,大量地實行一系列改革變法的措施,如青苗法、保甲法、保馬法、方田均稅法等。在變法進行的過程中,準備改革學校貢舉法,而學校貢舉的改變,將會影響一大批讀書人的前途和命運,於是遭到了包括劉攽在內的一些人的反對。劉攽上疏說:“本朝選舉士人的制度,已經實行了近百年,歷朝的將相大臣,名公名卿,都是由這種制度選拔出來,而實行新法的人卻說這種制度埋沒人才,這豈不是誣衊嗎?希望朝廷繼續實行過去的學校貢舉法,不要輕意變動。”
當時王安石也擔任皇帝的侍講官,請求讓侍講的官員坐著講課,這也受到劉攽的非難,他上疏認為:“侍讀大臣在皇帝面前講課,不能坐下來講,而是離開座位,站著講課,這是古來就有的禮制。王安石讓侍講官坐著講課,好像是表示皇帝尊德樂道,但這應該由皇帝提出,而不應由臣子請求。”當時的禮官們也都同意劉攽的意見。
劉攽曾經主持考試開封府的舉人,在考試過程中,與該院的考官王介因故爭執,互相罵詈,被監察御史彈劾而罷去禮院官職。開始,主持變法的呂惠卿任考官時,把支持新法的應試者列在高等,而把不支持新法的人放在下等。劉攽擔任考官后,又重新覆核,重新排定名次,因此得罪了支持新法的呂惠卿、王安石等人。劉攽又曾經給王安石寫信,信中反對王安石實行新法,論述新法的種種不便,引起王安石的不滿,再加上以前的種種過失,一怒之下,王安石把劉攽貶為通判泰州,不久又貶為以集賢接理、判登聞檢院、戶部判官、知曹州。曹州就是今天的山東菏澤地區一帶,是盜賊橫行的地方,嚴法重刑也不能制止。
劉攽認為嚴法重刑並不能制止盜賊,“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到任之後,實行寬惠的治民政策,盜賊也就沒有了。不久,劉攽又調任開封府判官,又復出任東京轉運使。在任期間,寬厚待人,對部屬中才能低下的人也心存仁厚,務為保全。不久,劉攽又調任兗州、亳州三地知州,吳居厚接替劉頒擔任京東轉運使。吳居厚到任后,嚴格按照朝廷的法令辦事,使政府的財政收入大大增加,而吳居厚又揭發劉攽在任時的種種措施,上奏朝廷,於是劉頒又被貶為監衡州鹽倉。
哲宗初年,政局發生了變化,新法被廢除了,支持新法的人被貶黜了,劉攽又被起用為襄州知州。不久,劉攽又到汴京擔任秘書少監,但地不久,就因病要求辭職,於是朝廷任以直龍圖閣的頭銜,擔任蔡州知州。擔任給事中的孫覺、胡宗愈,中書舍人蘇軾、范百祿等人上疏皇帝,認為劉攽“博記能文章,政事侔古循吏,身兼數器,守道不回,宜優賜之告,使留京師。”這時,劉攽才到蔡州幾個月,又被召回汴京擔任中書舍人。任職后即上書請求恢復舊制,建紫微閣於西省。不久,因病逝去,終年六十七歲。
劉攽學問淵博,著述豐富,特別精通史學,對於兩漢歷史尤其熟悉。著有《東漢刊誤》四卷。這部書是劉攽任國子監直講時撰寫的,因為英宗皇帝在閱讀《後漢書》時,經常見到墾田字被寫成“懇田”,於是下詔國子監刊正。劉攽奏詔刊正,撰成《東漢刊誤》四卷,於治平三年(公元1067年)上奏英宗皇帝,受到皇帝的褒揚。
因為劉攽精能兩漢歷史,故司馬光修撰《資治通鑒》時,邀請劉頒兩漢部分的撰寫工作,劉頒與司馬光等人一道,用了十九年的時間,完成了這部卷帙浩繁的編年體史學名著,為中國史學的發展作出了貢獻。在編撰《資治通鑒》的同時,劉攽又根據自己所掌握的材料,撰寫《編年紀事》十一卷,自注是“因司馬溫公所撰編次”。應該是縮寫本之類的書籍,今已不傳。
劉攽的著作除了上述的《東漢刊誤》、參編《資治通鑒》,另撰《編年記事》外,還有《五代春秋》十五卷,《內傳國語》二十卷,《經史新義》七卷,都已經佚失了。存下來的有《中山詩話》和《彭城集》。
劉攽既是一個史學家,也是一位詩人。他一生中曾寫下不少詩篇,其中的不少詩篇富有現實主義精神,充滿著對國家、民族的關切和對百姓痛苦生活的同情。在《幽州圖》一詩中,劉攽寫道,“鄙夫平居常嘆息,薊門幽都皆絕域;安得猛士守北方,為排敵人復禹跡。”表達了詩人對燕雲失地的關切之情。在《自古》詩中,他對皇帝因嬖倖而封侯加以無情的嘲諷;而在《京北流人》等詩中,對陷於痛苦的流亡生活中的勞動人民則充滿了真摯的同情。
劉攽還對詩歌發表評證,寫有《中山詩話》,又稱《劉貢父詩話》。詩話是我國古代詩歌評論的主要體裁,唐朝末年已經出現這種形式。現在的詩話中,以歐陽修的《六一詩話》、司馬光的《續詩話》和劉攽的《中山詩話》為最早。《中山詩話》的主要內容是記載當時文壇的一些掌故、趣聞、軼事,如“楊大年不喜杜工部詩”條記載,“楊大年不喜杜工部詩,謂為村夫子,鄉人有強大年者,續杜句曰:‘江漢思歸客’,楊亦屬對,鄉人徐舉‘乾坤一腐儒。’楊默然苦少屈。歐公亦不甚喜杜詩,謂韓吏部絕倫,吏部於唐世文章未嘗屈下,獨稱道李杜不已,歐貴韓而不悅子美,所不可曉,然於李白而甚賞愛,將由李白超卓飛揚,為感動也。”
於此可以了解宋初文壇上存在著宗韓、宗杜、宗李的區別以及文壇領袖歐陽修的欣賞傾向。在文學理論上,劉攽推重“質願宏壯”、“含蓄深遠”的詩歌,反對為追求平淡而陷入“質多文少”的誤區,主張作詩應該除去鄙俗。劉認為作詩的要務是立意,如果立意不高,辭藻再美也算不上上稱之作,“詩以意為主,文詞次之。或意深義高,雖義詞平易,自是奇作。世效古人平易句,而不得其意義,翻成鄙野可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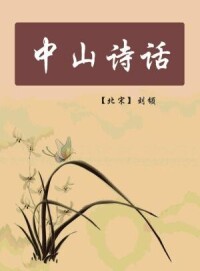
中山詩話
劉頒生性詼諧幽默,說話口不擇言,寫書撰文也是如此,他的《中山詩話》就是因為在談論詩歌時順便把北宋時期朝廷的一些陰暗面給暴露出來,因此當徽宗崇寧二年(公元1103年)下詔禁毀元佑黨人的書籍時,《中山詩話》也就難逃禁運了。當然《中山詩話》的被毀,除了書中的內容外,作者參加元佑黨首領司馬光編撰《資治通鑒》,並在政治上反對新法,是一個重要原因。
太宗好文,每進士及第,賜聞喜宴,常作詩賜之,累朝以為故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賜詩尤多,然不必盡上所自作。景祐初,賜詩落句云:“寒儒逢景運,報德合如何?“論者謂質厚宏壯,真詔旨也。
劉子儀贈人詩云:“惠和官尚小,師達祿須干。“取柳下惠聖之和,師也達,而子張學干祿之事。或有除去官字示人曰:“此必番僧也,其名達祿須干。“聞者大笑。詩有詩病俗忌,當避之。此偶自諧和,無若輕薄子何,非筆力過也。
景祐中,宋宜獻上《楊太妃輓詩》云:“神歸梁小廟,禮祔漢餘陵。“文士稱其用事精當。梅昌言詩曰:“先帝遺弓劍,排雲上紫清。同時受顧托,今日見昇平。“雖不用事,意思宏深,足為警語。
景祐末,元昊叛,夏鄭公出鎮長安,梅送詩曰:“亞夫金鼓從天落,韓信旌旗背水陳。“時獨刻公詩於石。
僧惠崇詩云:“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然唐人舊句。而崇之弟子吟贈其師詩曰:“河分岡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偷古人句,古人詩句似師兄。“杜工部有“峽束蒼江起,岩排石樹圓“,頃蘇子美遂用“峽束蒼江,岩排石樹“做七言句。子美豈竊師者,大抵諷古人詩多,則往往為己得也。
王元之《謫黃州詩》曰:“又為太守黃州去,依舊郎官白髮生。“在朝與執政不相能,作《江豚詩》以譏之曰:“江雲漠漠江雨來,天意為霖不幹汝。“俗雲,豚出則有風雨。又曰:“餐啖蝦魚頗肥腯。“譏其肥大。
人多取佳句為句圖,特小巧美麗可喜,皆指詠風景,影似百物者爾,不得見雄材遠思之人也。梅聖俞愛嚴維詩曰:“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固善矣,細較之,夕陽遲則系花,春水漫何須柳也。工部詩云:“深山催短景,喬木易高風。“此可無瑕纇。又曰:“蕭條九州內,人少豺虎多。少人慎莫投,多虎信所過。飢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若此等句,其含蓄深遠,殆不可模效。
詩以意為主,文詞次之,或意深義高,雖文詞平易,自是奇作。世效古人平易句,而不得其意義,翻成鄙野可笑。盧仝雲“不即溜鈍漢“,非其意義,自可掩口,寧可效之邪?韓吏部古詩高卓,至律詩雖稱善,要有不工者,而好韓之人,句句稱述,未可謂然也。韓云:“老公真箇似童兒,汲水埋盆作小池。“直諧戲語耳。歐陽永叔、江鄰幾論韓《雪詩》,以“隨車翻縞帶,逐馬散銀杯“為不工,謂“坳中初蓋底,凸處遂成堆“為勝,未知真得韓意否也?永叔云:“知聖俞詩者莫如某,然聖俞平生所自負者,皆某所不好;聖俞所卑下者,皆某所稱賞。“知心賞音之難如是,其評古人之詩,得毋似之乎!
潘閬字逍遙,詩有唐人風格。有云:“久客見華髮,孤棹桐廬歸。新月無朗照,落日有餘暉。魚浦風水急,龍山煙火微。時聞沙上雁,一一皆南飛。“《歲暮自桐廬歸錢塘》仆以為不減劉長卿。
太宗晚年,燒煉丹藥,潘閬嘗獻方書。及帝升遐,懼誅,匿舒州潛山寺為行者,題詩於鐘樓云:“繞寺千千萬萬峰,忘第二句。頑童趁暖貪春睡,忘卻登樓打曉鍾。“孫僅為郡官,見詩曰:“此潘逍遙也。“告寺僧呼行者,潘已亡去。
王益柔勝之為館職,年少亦頡頏。張掞叔文亦新貼職,年長而官已高,每群聚輒居上座。王密於屏風題云:“四十餘年老健兒。“此唐徐州節度王智興《自詠詩》句。翼日會食,張正坐詩下,眾無不哂。
李絢公素有詩贈同姓人曰:“吾宗天下者。“王勝之輒取注之曰:“居甘泉者以謳著,京施名倡李氏居甘泉坊善謳。賣葯者以木牛著,京施李家賣葯,以木牛自表,人呼為李木牛。圍棋者以憨者,李乃國手,而神思昏濁,人呼為李憨子。裁襆頭者以拗著,李家襆頭,天下稱善,而必與人乖刺,歲久自以拗李呼。作詩者以豁達著。“豁達老人喜為詩,所至輒自題寫,詩句鄙下而自稱豁達李老。嘗書人新素牆壁,主人憾怒,訴官杖之,拘執使市石灰更圬漫訖,告官乃得縱舍,聞者哂之。此數人因勝之有雲,遂自托不朽。
梅昌言出鎮太原,黃覺送詩曰:“五馬雍容出鎮時,都人爭看好風儀。文章一代喧高價,忠直三朝受聖知。帳下軍容森劍戟,門前行色擁旌旗。雲龍古戍黃榆暗,雪滿長郊白草衰。出去暫開貔虎幕,歸來須占鳳凰池。鬢間未有一莖白,陶鑄蒼生固不遲。“梅雅自修飾,容狀偉如,大喜之。
黃覺仕官不遂,嘗送客都門外,不及寓邸舍,會一道士取所攜酒炙呼飲之,既而道士舉杯摭水寫“呂“字,覺始悟其為洞賓也。又曰:“明年江南見君。“覺果得江南官。及期見之,出懷中大錢七,其次十,又小錢三,曰:“數不可益也。“予葯數寸許,告覺曰:“一以酒磨服之,可保一歲無疾。“覺如其言,至七十餘,葯亦垂盡,作詩曰:“床頭曆日無多子,屈指明年七十三。“果是歲卒。
李商隱有《錦瑟詩》,人莫曉其意,或謂是令狐楚家青衣名也。
祥符、天禧中,楊大年、錢文僖、晏元獻、劉子儀以文章立朝,為詩皆宗尚李義山,號“西昆體“,後進多竊義山語句。賜宴,優人有為義山者,衣服敗敝,告人曰:“我為諸館職撏扯至此。“聞者懽笑。大年《漢武詩》曰:“力通青海求龍種,死諱文成食馬肝。待詔先生齒編貝,忍令索米向長安。“義山不能過也。元獻《王文通詩》曰:“甘泉柳苑秋風急,卻為流螢下詔書。“子儀畫義山像,寫其詩句列左右,貴重之如此。
楊大年不喜杜工部詩,謂為村夫子。鄉人有強大年者,續杜句曰“江、漢思歸客“,楊亦屬對,鄉人徐舉“乾坤一腐儒“,楊默然若少屈。歐公亦不甚喜杜詩,謂韓吏部絕倫。吏部於唐世文章,未嘗屈下,獨稱道李、杜不已。歐貴韓而不悅子美,所不可曉;然於李白而甚賞愛,將由李白超趠飛揚為感動也
孟東野詩,李習之所稱:“食薺腸亦苦,強歌聲不懽。出門如有礙,誰謂天地寬。“可謂知音。今世傳《郊集》五卷,詩百篇。又有集號《咸池》者,僅三百篇,其間語句尤多寒澀,疑向五卷是名士所刪取者。東野與退之聯句詩,宏壯博辯,若不出一手。王深父云:“退之容有潤色也。“
張籍樂府詞,清麗深婉,五言律詩亦平澹可愛,至七言詩,則質多文少。材各有宜,不可強飾。文昌有《謝裴司空馬詩》曰:“乍離華廄移蹄澀,初到貧家舉眼驚。“此馬卻是一遲鈍多驚者,詩詞微而顯,亦少其比。
白樂天詩曰:“請錢不早朝。““請“作平聲,唐人語也。今人不用廝字,唐人作斯音,五代已作入聲,陶谷雲“尖檐帽子卑凡廝“是也。白曰:“金屑琵琶槽,雪擺胡騰衫。“琵琶與今人同。杜曰“皂雕寒始急“,白曰“千呼萬喚始出來“,人皆謂語病。事之終始,音上聲,有所宿留,今甫然者音去聲。二公詩自非語病。
唐詩賡和,有次韻,先後無易。有依韻,同在一韻。有用韻,用彼韻不必次。吏部和皇甫《陸渾山火》是也,今人多不曉。劉長卿《餘干旅舍》云:“搖落暮天迥,丹楓霜葉稀。孤城向水閉,獨鳥背人飛。渡口月初上,鄰家漁未歸。鄉心正欲絕,何處搗征衣。“張籍《宿江上館》云:“楚驛南渡口,夜深來客稀。月明見潮上,江靜覺鷗飛。旅宿今已遠,此行殊未歸。離家久無信,又聽搗砧衣。“兩詩偶似次韻,皆奇作也。
管子曰:“是無終始,無務多業。“此言學者貴能成就也。唐人為詩,量力致功,精思數十年,然後名家。杜工部云:“更覺良工用心苦。“然豈獨畫手心苦耶!
真宗問進臣:“唐酒價幾何?“莫能對。丁晉公獨曰:“斗直三百。“上問何以知之,曰:“臣觀杜甫詩:‘速須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亦一時之善對。
海陵人王綸女,輒為神所馮,自稱仙人。字善數品,形制不相犯。《吟雪詩》云:“何事月娥欺不在,亂飄瑞葉落人間。“說云:天上有瑞木,開花六齣。他詩句詞意飄逸,類非世俗可較。《題金山》云:“濤頭風捲雲,山腳石蟠虯。“常謂綸為清非孺子,不曉其義。亦有詩贈曰:“君為秋桐,我為春風。春風會使秋桐變,秋桐不識春風面。“居數歲,神舍女去,懵然無知。嫁為廣陵呂氏妻。
鞠,皮為之,實以毛,蹙蹋而戲。見《霍去病傳》註:“穿城蹋鞠。“晚唐已不同矣。歸氏子弟嘲皮日休云:“八片尖皮砌作球,火中燂了水中揉。一包閑氣如常在,惹踢招拳卒未休。“今柳三複能之,述曰:“背裝花屈膝,屈,口勿反。白打大廉斯。進前行兩步,蹺后立多時。“柳欲見晉公無由,會公蹴球後園,偶迸出,柳挾取之,因懷所業,戴球以見公。出書再拜者三,每拜,球起複於背膂襆頭間,公乃笑而奇之,遂延於門下。然弟子拜師,常禮也,獨球多賤人能之,每見勞於富貴子弟,莫不拜謝而去,此師拜弟子也。術不可不慎,此亦可喻大雲。
洪州西山與滕王閣相對,一僧盡覽詩板,告郡守曰:“盡不佳。“因朗吟曰:“洪州太白方,積翠倚穹蒼。萬古遮新月,半江無夕陽。“守異之,遣出。閩僧有朋多詩,如“虹收千嶂雨,潮展半江天。“又曰:“詩因試客分題僻,棋為饒人下著低。“亦巧思也。
王丞相嗜諧謔。一日,論沙門道,因曰:“投老欲依僧。“客遽對曰:“急則抱佛腳。“王曰:“‘頭老欲依僧’,是古詩一句。“客亦曰:“‘急則抱佛腳’,是俗諺全語。上去投,下去腳,豈不的對也。“王大笑。
孟蜀時,花蕊夫人號能詩,而世不傳。王平父因治館中廢書,得一軸八九十首,而存者才三十餘篇,大約似王建句。若“廚船進食簇時新,列坐無非侍從臣。日午殿頭宣所鱠,隔花催喚打魚人。““月頭支給買花錢,滿殿宮娥近數千。遇著唱名都不語,含羞急過御狀前。“
山東二經生同官,因舉鄭谷詩曰:“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王徭。“一生難之曰:“野鷹安得王徭?“一生解之曰:“古人寧有失也?是年必當索翎毛耳。“
刁景純有見無類,必往複,歸每至三鼓。宋祁判館,集僚屬,而刁或連日不赴,因邀而譙讓之。王原叔戲改杜《贈鄧廣文》云:“景純過官舍,走馬不曾下。驀地趁朝歸,便遭官長罵。“李獻臣曰∶“我為足之雲∶‘多羅四十年,偶未識摩氈。時西戎唃氏子名摩氈。近有王宣政,時時與紙錢。’“刁嘗為王宣政作墓銘。以古文篆隸加褾軸,密掛刁聽事。會一日大雨,不出,周步廳廡間,始見此圖。問之從者。曰:“掛此已數日矣,先造者往往能通念也。“
蘇子美魁偉,與宋中道並立,下視之,笑曰:“交不著。“京師市井語也。號為“錐宋“,為其穎利而么么雲。贈詩曰:“譬如利錐末,所到物已破。“后倅洺州。洺本趙地,有毛遂冢,聖俞遂舉處囊事為送行詩戲之。
司馬溫公論九旗之名,旗與旗相近。《詩》曰:“言觀其旗。“《左傳》:“龍尾伏辰,取虢之旗。“然則此旗當為芹音。周人語轉,亦如關中以中為蒸,蠱為塵,丹青之青為萋也。五方語異,閩以高為歌,荊、楚以南為難,荊為斤。昔閩士作《清明象天賦》,破題云:“天道如何,仰之彌高。“會考官同里,遂中選。荊、楚士題雪用先字,后曰“十二峰巒旋旋添“。反讀添為天字也。向敏中鎮長安,土人不敢賣蒸餅,恐觸中字諱也。
楊安國判監,集學官飲,必頌《詩譜》以侑酒。舉杯屬客,曰:“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且飲酒。“裴如晦亦舉杯曰:“古之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不能飲矣。“一座皆笑,而楊不悟。
泗州塔,人傳下藏真身,后閣上碑道興國中塑僧伽像事甚詳。退之詩曰:“火燒水轉掃地空。“則真身焚矣。塔本喻都料造,極工巧。俗謂塔頂為天門,蘇國老詩曰:“上到天門最高處,不能容物只容身。“以譏在位者。
古詩曰:“袖中有短書,欲寄雙飛燕。“以燕時物,故寓言爾。蜀人自京以鴿寄書,不浹旬而達船,船浮海,亦以鴿通信,非虛言也。史以陸機“黃耳“為犬,能寄書,恐不然。自洛至吳,更歷江、淮,殆數千里,安能諭人而從舟楫乎?或者為奴名,不然,當為神犬也。
史著赫連勃勃之暴,蒸土築城,意謂釜甑熟之。然不知北方土工,用春首聚土,陽氣蒸發,用築則堅牢特甚故爾。近有獻策築吳江為瓮堤,土人慾以巨瓮實土,稍稍下之。不思土實則瓮重不可致,虛致水中則泛,泛曷可止。雖執政亦惑之。然治河皆有瓮堤,形似瓮耳,不用陶器也。
汪白為《平詩》刺時病云:“穴垣補牆隙,牆成垣已隳。斷屨補穿履,履成屨亦虧。“
晏元獻尤喜江南馮延巳歌詞。其所自作,亦不減延巳。樂府《木蘭花》皆七言詩,有云:“重頭歌詠響璁琤,入破舞腰紅亂旋。“重頭、入破,皆弦管家語也。
歐陽文忠公見張安陸,迎謂曰:“好,雲破月來花弄影。“
《韓吏部集》有李習之兩句云:“前之詎灼灼,此去信悠悠。“若無可取,鄭州掘一石,刻刺史李翱詩曰:“縣君愛磚渠,繞水恣行游。鄙性樂山野,掘地便池溝。兩岸植芳草,中間漾清流。所向既不同,磚鑿名自修。從他後人見,景趣誰為幽。“王深父編次入習之集。此別一李翱爾,而習之不能詩也。吏部讀皇甫湜
詩,亦譏其掎摭糞壤。梅聖俞謂尹師魯以古文名而不能詩。
陳亞以藥名詠白髮云:“若是道人頭不白,老人當日合烏頭。“
員外郎上官佖嘗勸石少傅中立慎緘,石勃然曰:“上官佖如下官口何!“
韓吏部《贈玉川詩》曰:“水北山人得聲名,去年去作幕下士。水南山人又繼往,鞍馬僕從塞閭里。少室山人索價高,兩以諫官征不起。“又曰:“先生抱材須大用,宰相未許終不仕。“王向子直謂韓與處士作牙人商度物價也。古稱駔儈,今謂牙,非也。劉道原云:“本稱互郎,主互市。唐人書互為□,因訛為牙。“理或信然。今言萬為方,千為撇,非訛也,若隱語爾。
陳文惠堯佐以使相致仕,年八十,有詩云:“青雲歧路游將遍,白髮光陰得最多。“構亭號佚老,后歸政者往往多效之。公喜堆墨書,游長安佛寺題名,從者誤側硯污鞋,公性急,遂窒筆於其鼻,客笑失聲,若皇甫湜怒其子,不暇取杖,遂齕臂血流。
今人呼禿尾狗為厥尾,衣之短後者亦曰厥,故歐公記陶尚書詩語末厥兵,則此兵正謂末賊爾。世語虛偽為何樓,蓋國初京師有何家樓,其下賣物皆行濫者,非沽濫稱也。世語優人為何市樂,說者謂南都石駙馬家樂甚盛,詆誚南市中樂人,非也。蓋唐元和時《燕吳行役記》,其中已有河市字,大抵不隸名軍籍而在河市者,散樂名也。世謂事之陳久為瓚,蓋五代時有馬瓚,為府幕,其人魯憨,有所聞見,他人已厭熟,而乃甫為新奇道之,故今多稱瓚為厭熟,京師人貨香印者,皆擊鐵盤以示眾人,父老雲,以國初香印字逼近太祖諱,故托物默喻。
梁周翰,真宗即位,始知誥,《贈柳開詩》曰:“九重城闕新天子,萬卷詩書老舍人。“時楊大年、朱昂同在禁掖,楊未及滿三十,而二公皆老,數見靳侮。梁謂之曰:“公毋侮我老,此老亦將留與公爾。“朱昂聞之,背面搖手掖下,,謂梁曰:“莫與,莫與!“大年死不及五十。
余靖兩使契丹,虜情益親,能胡語,作胡語詩。虜主曰:“卿能道,吾為卿飲。“靖舉曰:“夜宴設邏厚盛也。臣拜洗,受賜。兩朝闕荷通好。情感勤。厚重。微臣雅魯拜舞。祝若統,福祐。聖壽鐵擺嵩高。俱可忒。無極。“主大笑,遂為釂觴。漢史有《盤木白狼詩》,譯出夷語,殆不若靖真胡語也。劉沆亦使虜,使凌壓之,契丹館客曰:“有酒如澠,系行人而不住。“沆應聲曰:“在北曰狄,吹《出塞》以何妨。“仁宗待虜有禮,不使纖微迕之,二公俱謫官。
古人多歌舞飲酒,唐太宗每舞,屬群臣。長沙王亦小舉袖,曰:“國小不足以迴旋。“張燕公詩云:“醉后懽更好,全勝未醉時。動容皆是舞,出語總成詩。“李白云:“要須回舞袖,拂盡五松山。醉後涼風起,吹人舞袖環。“今時舞者必欲曲盡奇妙,又恥效樂工藝,益不復如古人常舞矣。古人重歌詩,自隋以前,南北舊曲頗似古,如《公莫舞》、《丁督護》,亦自簡澹。唐來是等曲又不復入聽矣。近世樂府為繁聲加重疊,謂之纏聲,促數尤甚,固不容一倡三嘆也。胡先生許太學諸生鼓琴吹簫,及以方響代編磬,所奏惟《采蘋》、《鹿鳴》數章而已,故稍曼延,傍邇鄭、衛聲,或問之,曰:“無他,直纏聲《鹿鳴》、《采蘋》爾。“
梅聖俞幼《戲謝師直詩》曰:“古錦裁詩句,斑衣戲坐隅。木奴今正熟,肯效陸郎無?“師直小名錦衣奴,至十歲讀此,方悟之。
石曼卿獨行京師,一豪士揖之而語曰:“公幸過我家。“石許之,同入委巷,抵大第,藻飾宏麗,錦繡珠翠,殆非人間所擬。歌舞歡醉,丐書,為揮《籌筆》、《驛詩》數篇。以金帛數百千贈之,復使騶從送還,恍然不知其誰。翼日,殆無復省所居矣。他日,遇諸塗,以遺以白金數兩,謂曰:“詩中‘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最為佳句。“
趙少師初在漣水守館,不數年後,以學士知漣水,繼來者名其堂為豹隱。曼卿有詩曰:“熊非清渭逢何暮?龍卧南陽去不還。年少官游今郡守,蔚然疑在立談間。“后莫偕者。
曹參嘗為功曹,而杜詩云“功曹無復嘆蕭何“,誤矣。按光武嘗謂鄧禹,“何以不掾功曹?“陳子昂云:“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麑翁。“放麑,本秦西巴,孟孫氏之臣,謂之中山,亦誤矣。唐韓皋鼓《廣陵散》,其說謂毋丘儉、諸葛誕刺揚州,舉兵討晉,不成而散於廣陵爾。劉道原謂漢、魏時揚州刺史治壽春,儉、誕皆死壽春,是時廣陵屬徐州,至隋、唐始為揚州,不可不察也。
景祐中,羌人叛,詔遺士獻方略,率皆得官。有《題關西驛舍》曰:“弧生熒熒照寒野,漢馬蕭蕭五陵下。廟堂不肯用奇謀,天子徒勞聘賢者。萬里危機入燕、薊,八方殺氣沖靈、夏。逢時還似不逢時,已矣吾生真苟且。“
宋次道《次西都詩》,以狐落對五鳳樓,言野狐落,唐人名宮人所聚也。
太宗時,同年數輩取名似姓者為句云:“郭鄭、鄭東、東野絳,馬張、張夏、夏侯璘。“熙寧初,有崔度、崔公度,王韶、王子韶,又有章君陳、陳君章,如以西門豹對東方虯也。王丞相云:“馬子山騎山子馬。“馬給事字子山。穆王八駿有山子馬之名。久之,人對曰:“錢衡水盜水衡錢。“錢某為衡水令。人謝之曰:“正欲作對爾,實非有盜也。“
永州何仙姑,不飲食,無漏泄,世傳其神異。岳州天慶觀柱以震折,有倒書“謝仙火“字。仙姑云:“雷部夫婦二人,長闊各三尺,銀色。“莫不駭信。有熟於江湖間事者,曰:“南方賈人各以火自名,一火猶一部也。此賈名仙,刻木記己物耳。“是亦不可知也。嘗有道人,自言隋、唐間人,談黃巢事甚悉,因曰:“黃六晚節至此。“張安道尚書云:“巢六兄弟,而巢最小,當第六。“由是推之,則道人之言信然乎?
江州琵琶亭,前臨江,左枕湓浦,地尤勝絕。夏、梅詩最佳。英公、公儀。夏云:“年光過眼如車轂,職事羈人似馬銜。若遇琵琶應大笑,何須涕泣滿青衫!“梅云:“陶令歸來為逸賦,樂天謫宦起悲歌。有弦應被無弦笑,何況臨弦泣更多!“又有葉氏女名桂女,字月流。詩曰:“樂天當日最多情,淚滴青衫酒重傾。明月滿船無處問,不聞商女琵琶聲。“
詞人以也字作夜音,杜云:“青袍也自公。“白公云:“也向慈恩寺?游。“不可如字讀也。
張湍為河南司錄府,當祭社,買豬以呈尹,而豬輒突入湍家,湍即捉殺之。湍對尹云:“律雲,豬無故夜入人家,主人登時殺之勿論。“尹笑之,為別市豬。
張介以命術游公卿間,寓居錢塘西湖上。嘗自京師南歸,士大夫率為詩贈之。呂許公王沂公時方執政,亦皆有詩。夏鄭公留守南京,為詩寄二公曰:“上公詩筆千金重,逋客歸裝一舸輕。莫到青山更招隱,且留賢哲為蒼生。“鄭公在朝,數為御史糾劾,疑時宰諷旨,作《青雀詩》:“青雀孤飛毛羽單,卑棲豈敢礙鵷鸞。明珠自有千金價,莫為他人作彈丸。“
自唐以來,試進士詩,號省題。近 年能詩者,亦時有佳句。蜀人楊諤《宣室受釐》落句云:“願前明主席,一問洛陽人。“滕甫《西旅來王》云:“寒日邊聲斷,春風塞草長。傳聞漢都護,歸奉萬年觴。“諤有詩名,《題驪山詩》云:“行人問宮殿,耕者得珠璣。“最為警策。
唐人飲酒,以令為罰,韓吏部詩云:“令征前事為。“白傅詩云:“醉翻襴衫拋小令。“今人以絲管歌謳為令者,即白傅所謂。大都欲以酒勸,故始言送,而繼承者辭之,搖首挼舞之屬,皆卻之也,至八遍而窮,斯可受矣。其舉故事物色,則韓詩所謂耳。近歲有以進士為舉首者,其黨人意侮之,會其人出令,以字偏傍為率,曰:“金銀釵釧鋪。“次一人曰:“絲綿紬絹網。“至其黨人,曰:“鬼魅魍魎魁。“俗有謎語曰:“急打急圓,慢打慢圓,分為四段,送在窯前。“初以陶瓦乃為令耳。
陳文惠善為四句詩,在江湖有詩云:“平波渺渺煙蒼蒼,菰蒲才熟楊柳黃。扁舟系岸不忍去,秋風斜日鱸魚鄉。“文惠年六十餘,才為知制誥,其後遂至真宰使相致仕。文惠喜堆墨書,深自矜負,號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與石少傅同在政府,石欲戲之,政事堂有黑漆大飯床,長五六尺許,石取白堊,橫畫其中,可尺餘,而謂陳曰:“我頗學公堆墨字。“陳聞之歡甚。石顧小吏二人,舁飯床出,曰:“我已能寫口字。“陳為悵然。
江鄰幾善為詩,清淡有古風。蘇子美坐進奏院事謫官,后死吳中。江作詩云:“郡邸獄冤誰與辯?皋橋客死世同悲。“用事甚精當。嘗有古詩云:“五十踐衰境,加我在明年。“論者謂莫不用事,能令事如己出,天然渾厚,乃可言詩,江得之矣。江天質淳雅,喜飲酒、鼓琴、圍棋。人以酒召之,未嘗不往,飲未嘗不醉,已醉眠,人強起飲之,亦不辭也。或不能歸,即留宿人家,商度風韻,陶靖節之比。江嘗通判廬州,有酒官善琴,以坐局不得出,江日就之,郡中沙門、羽士及里氓能棋者數人,呼與同往。郡人見之習熟,因畫為圖:前列騶導,有一人騎馬青蓋,其後沙門、羽士、褐衣數人,葛巾芒屩累累相尋,意思蕭散。惜時無名手,此畫不足傳后,何必減嵇、阮也。
道人張無夢,在真宗朝,以處士見除校書郎。無夢善攝生。梅昌言知蘇州,無夢求見之,先與詩云:“壼中一粒長生藥,待與蘇州太守分。“好為大言,處之不疑,自比李少君。然無夢年九十死。無夢語人,少時絕欲,屏居山中十餘歲,自以為不動。及出見婦人美色,乃復歉然。又入山十餘年,乃始寂定。勸人飲食毋用鹽醋,煮餅淡食,更自有天然味。無夢老病耳聾,其死亦無他異。
蜀人李士寧,好言鬼神詭異事。為予言,嘗泛海值風,廣利王使存問己。又嘗一夜,有人傳相公命己,及往,燕設甚盛,飲食醉飽。既寤,乃在梁門外。疑所謂相公者,二相神也。人皆言士寧能佗心通。士寧過余,余故默作念,侮戲之竟日,士寧不知,烏在其通也!士大夫多遺其金帛錢物,士寧以是財用常饒足。人又以為有術能歸錢,與李少君類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