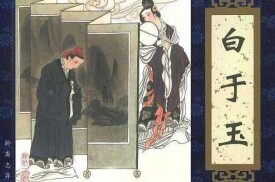白於玉
清代蒲松齡創作的文言短篇小說
《白於徠玉》是清代小說家蒲松齡創作的文言短篇小說。
吳青庵,筠,少知名。葛太史見其文,每嘉嘆之。托相善者邀至其家,領其言論風采。曰:“焉有才如吳生,而長貧賤者乎?”因俾鄰好致之曰:“使青庵奮志雲霄,當以息女奉巾櫛[zhì]。”時太史有女絕美。生聞大喜,確自信。既而秋闈[wéi]被黜,使人謂太史:“富貴所固有,不可知者遲早耳。請待我三年,不成而後嫁。”於是刻志益苦。
一夜,月明之下,有秀才造謁,白皙短須,細腰長爪。詰([jié],追問)所來,自言:“白氏,字於玉。”略與傾談,豁人心胸。悅之,留同止宿。遲明欲去,生囑便道頻過。白感其情殷,願即假館,約期而別。至日,先一蒼頭送炊具來。少間,白至,乘駿馬如龍。生另舍舍之。白命奴牽馬去。遂共晨夕,忻然相得。生視所讀書,並非常所見聞,亦絕無時藝。訝而問之,白笑曰:“士各有志,仆非功名中人也。”夜每招生飲,出一卷授 生,皆吐納之術,多所不解,因以遷緩置之。他日謂生曰:“曩([nǎng],從前)所授,乃‘黃庭’之要道,仙人之梯航。”生笑曰:“仆所急不在此。且求仙者必斷絕情緣,使萬念俱寂,仆病未能也。”白問:“何故?”生以宗嗣為慮。白曰:“胡久不娶?”笑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白亦笑曰:“‘王請無好小色。’所好何如?”生具以情告。白疑未必真美。生曰:“此遐邇所共聞,非小生之目賤也。”白微哂而罷。次日,忽促裝言別。生凄然與語,刺刺不能休。白乃命童子先負裝行。兩相依戀。俄見一青蟬鳴落案間,白辭曰:“輿已駕矣,請自此別。如相憶,拂我榻而卧之。”方欲再問,轉瞬間,白小如指,翩然跨蟬背上,嘲哳而飛,杳入雲中。生乃知其非常人,錯愕良久,悵悵自失。
逾數日,細雨忽集,思白綦切。視所卧榻,鼠跡碎瑣;慨然掃除,設席即寢。無何,見白家童來相招,忻然從之。俄有桐鳳翔集,童捉謂生曰:“黑徑難行,可乘此代步。”生慮細小不能勝任。童曰:“試乘之。”生如所請,寬然殊有餘地,童亦附其尾上;戛然一聲,凌升空際。未幾,見一朱門。童先下,扶生亦下。問:“此何所?”曰:“此天門也。”門邊有巨虎蹲伏。生駭俱,童一身障之。見處處風景,與世殊異。童導入廣寒宮,內以水晶為階,行人如在鏡中。桂樹兩章,參空合抱;花氣隨風,香無斷際。亭宇皆紅窗,時有美人出入,冶容秀骨,曠世並無其儔。童言:“王母宮佳麗尤勝。”然恐主人伺久,不暇留連,導與趨出。移時,見白生候於門。握手入,見檐外清水白沙,涓涓流溢;玉砌雕闌,殆疑桂闕。甫坐,即有二八妖鬟,來薦香茗。少間,命酌。有四麗人,斂衽鳴,給事左右。才覺背上微癢,麗人即纖指長甲,探衣代搔。生覺心神搖曳,罔所安頓。既而微醺,漸不自持,笑顧麗人,兜搭與語。美人輒笑避。白令度曲侑觴[yòu shānɡ]。一衣絳綃者,引爵向客,便即筵前,宛轉清歌。諸麗者笙管敖曹,嗚嗚雜和。既闋,一衣翠裳者,亦酌亦歌。尚有一紫衣人,與一談白軟綃者,吃吃笑暗中,互讓不肯前。白令一酌一唱。紫衣人便來把盞。生托接杯,戲撓纖腕。女笑失手,酒杯傾墮。白譙訶[qiáo hē]之。女拾杯含笑,俯首細語云:“冷如鬼手馨,強來捉人臂。”白大笑,罰令自歌且舞。舞已,衣淡白者又飛一觥。生辭不能酹,女捧酒有愧色,乃強飲之。細視四女,鳳致翩翩,無一非絕世者。遽謂主人曰:“人間 尤物,仆求一而難之;君集群芳,能令我真箇銷魂否?”白笑曰:“足下意中自有佳人,此何足當巨眼之顧?”生曰:“吾今乃知所見之不廣也。”白乃盡招諸女,俾自擇。生顛倒不能自決。白以紫衣人有把臂之好,遂使被奉客。既而衾枕之愛,極盡綢繆。生索贈,女脫金腕釧付之。忽童入曰:“仙凡路殊,君宜即去。”女急起,遁去。生問主人,童曰:“早詣待漏,去時囑送客耳。”生悵然從之,復尋舊途。將及門,回視童子,不知何時已去。虎哮驟起,生驚竄而去。望之無底,而足已奔墮。一驚而寤,則朝暾([zhāotūn],剛升起的太陽)已紅。方將振衣,有物膩然墜褥間,視之,釧也。心益異之。由是前念灰冷,每欲尋赤松游,而尚以胤續為憂。過十餘月,晝寢方酣,夢紫衣姬自外至,懷中綳嬰兒曰:“此君骨肉。天上難留此物,敬持送君。”乃寢諸床,牽衣覆之,匆匆欲去。生強與為歡。乃曰:“前一度為合巹,今一度為永訣,百年夫婦,盡於此矣。君倘有志,或有見期。”生醒,見嬰兒卧褥間,綳以告母。母喜,佣媼哺之,取名夢仙。生於是使人告太史,自己將隱,令別擇良匹。太史不肯。生固以為辭。太史告女,女曰:“遠近無不知兒身許吳郎矣。令改之,是二天也。”因以此意告生。生曰:“我不但無志於功名,兼絕情於燕好。所以不即入山者,徒以有老母在。”太史又以商女。女曰:“吳郎貧,我甘其藜藿;吳郎去,我事其姑嫜:定不他適。”使人三四返,迄無成謀,遂諏日備車馬妝奩,嬪於生家。生感其賢,敬愛臻至。女事姑孝,曲意承順,過貧家女。逾二年,母亡,女質奩[lián]作具,罔不盡禮。生曰:“得卿如此,吾何憂!顧念一人得道,拔宅飛升。余將遠逝,一切 付之於卿。”女坦然,殊不挽留。生遂去。
女外理生計,內訓孤兒,井井有法。夢仙漸長,聰慧絕倫。十四歲,以神童領鄉薦,十五入翰林。每褒封,不知母姓氏,封葛母一人而已。值霜露之辰,輒問父所,母具告之。遂欲棄官住尋。母曰:“汝父出家,今已十有餘年,想已仙去,何處可尋?”后奉旨祭南嶽,中途遇寇。窘 急中,一道人仗劍入,寇盡披靡,圍始解。德之,饋以金,不受。出書一函,付囑曰:“余有故人,與大人同里,煩一致寒暄。”問:“何姓名?”答曰:“王林。”因憶村中無此名。道士曰:“草野微賤,貴官自不識耳。”臨行,出一生釧曰:“此閨閣物,道人拾此,無所用處,即以奉報。”視之,嵌鏤 精絕。懷歸以授夫人。夫人愛之,命良工依式配造,終不及其精巧。遍問村中,並無王林其人者。私發其函,上云:“三年鸞鳳,分拆各天;葬母教子,端賴卿賢。無以報德,奉葯一丸;剖而食之,可以成仙。”后書“琳娘夫人妝次”。讀畢,不解何人,持以告母。母執書以泣,曰:“此汝父家報也。琳,我小字。”始恍然悟“王林”為拆白謎也。悔恨 不已。又以釧示母。母曰:“此汝母遺物。而翁在家時,嘗以相示。”又視丸,如豆大。喜曰:“我父仙人,啖此必能長生。”母不遽吞,受而藏之。會葛太史來視甥,女誦吳生書,便進丹藥為壽。太史剖而分食之。頃刻,精神煥發。太史時年七旬,龍鍾頗甚;忽覺筋力溢於膚革,遂棄輿而步,其行健速,家人坌[bèn]息始能及焉。逾年,都城有回祿之災,火終日不熄。夜不敢寐,畢集庭中。見火勢拉雜,侵及鄰舍。一家徊徨,不知所計。忽夫人臂上金釧,戛[jiá]然有聲,脫臂飛去。望之,大可數畝;團覆宅上,形如月闌;口降東南隅,歷歷可見。眾大愕。俄頃,火自西來,近闌則斜越而東。迨火勢既遠,竊意釧亡不可復得;忽見紅光乍斂,釧錚然墮足下。都中延燒民舍數萬間,左右前後,並為灰燼,獨吳第無恙,惟東南一小閣,化為烏有,即釧口漏覆處也。葛母年五十餘,或見之,猶似二 十許人。
領:領略;意為觀察得知。
致之:傳話給吳生。致:致意,轉達。
奮志雲霄:指奮發立志取得科舉功名。
奉巾櫛:侍奉盥沐:以女許婚的謙詞。
秋闈被黜:鄉試落選。秋闈,指鄉試。
刻志益苦:更加刻苦勵志。
與:此從二十四卷抄本,底本作“於”。
豁人心胸:使人心胸開朗。
假館:借宅寄居。館,房舍。
另舍舍之:出別院給白生居住。
共晨夕:朝夕相處。陶潛《移居二首》之一:“聞多素心人,樂與 數晨夕。”
時藝:相對於古文而言,明清稱科舉考試所用的八股文為時藝,又 稱“舉子業”、“四書文”。
吐納之術:舊時方術家養生健身的法術,類似於深呼吸。參卷一《靈 官》注。
迂緩:迂闊而不切於實用。
黃庭:《黃庭經》。道教經典《上清黃庭內景經》和《上清黃庭外 景經》的總稱。兩書皆以七言歌訣講述養生修鍊的原理,為歷代道教徒及修 身養性者所重視。要道,指養生修鍊的重要原理。
梯航:梯子和渡船,喻成仙的憑藉。
萬念俱寂:一切世俗雜念都歸於寂滅。
仆病未能:我怕做不到。借用枚乘《七發》楚太子回答吳客用
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借用《孟子·梁惠王》齊宣王搪塞孟子的話。下句“王請無好小色”,借用同篇孟子誘導齊宣王的話。
遐邇:遠近;謂一方周圍。
目賤:眼光庸陋,鑒賞力低下。
嘲晰(zhāo zhā):象聲詞,又作“嘲”、“啁哳”。形容聲 音繁細。此指蟬鳴聲。
錯愕:倉皇驚詫。
慨然:嘆悔貌。《詩·王風·中谷有》;“有女仳離,其 嘆矣。”集傳:“,嘆聲。”
桐風:鳥名,即桐花鳳。店李德裕《李文饒集》別集一《桐花風扇 賦序》:“成都夾岷江,磯岸多植紫桐。每至暮春,有靈禽五色,小於玄鳥,來集桐花,以飲朝露。及華落則煙飛雨散,不知其所往。”
廣寒宮:月宮。詳卷一《勞山道士》注。
兩章:兩株。大村曰章,見《史記·貨殖列傳》索隱。
亭宇:亭子和房屋。《楚辭》宋玉《招魂》:“高堂邃宇,檻層軒 些。”註:“宇,屋也。”
王母:王母娘娘;古代神話中“西王母”幾度變后的形象。在《山 海經》中,西王母是半人半獸職掌瘟疫、刑罰的怪神。在《穆天子傳》、《漢武內傳》里,她被人化為美婦人型的女仙。在《墉城集仙錄》里,她成為掌 管女仙名籍的神仙領袖。經歷長期民間傳說,她的住處由西方搬到了天上,而仙桃或蟠桃盛會,成為西王母——王母娘娘形象的重要特徵。
桂闕:即月宮。因相傳月中有桂樹,故名。
斂衽鳴:謂近前禮窖。斂衽:整斂衣襟。婦女行拜禮的動作:指對 客人致敬。鳴:走動時腰間玉飾相碰擊,琅作響。
給事:供役使,侍奉。
兜搭:搭訕。
度曲侑(yòu)觴:唱曲勸酒。
引爵:斟酒。
敖曹:義同“嗷嘈”,聲音喧鬧。
嗚嗚雜和:伴唱者曼聲相和。嗚嗚,拖著長腔。《漢書·楊惲傳》 報孫會字書:“仰天擊缶,而呼嗚嗚。”
吃吃(qī qī七七):忍笑聲。
譙(qiào 俏)訶:同“譙呵”,申斥。
“冷如鬼手馨”二句:手涼得象鬼手,硬要來抓人的胳臂。《世說 新語·忿狷》:“王司州(胡之)嘗乘雪往王螭(恬)許。言氣少有牾逆於 螭,便作色不夷。司州覺惡,便輿床就之,持其臂曰:‘汝詎復足與老兄計?’ 螭撥其手曰:‘冷如鬼手馨,強來捉人臂。’”馨,晉人用作語助辭。
飛一觥:疾忙斟滿一杯。飛觥,通常叫“飛觴”,對方剛剛飲完前 杯,又急速為之斟上,意在讓對方多飲。
翩翩:形容風采美好超逸。
尤物:本指特異超俗的人或物。后多指絕色美女。
群芳:群花,喻成群的美女。
真箇銷魂:俞焯《詩詞餘話》:詹天游風流才思,不減昔人。宋駙 馬楊鎮有十姬,皆絕色,其中粉兒者尤美。楊鎮召詹次宴,出諸姬佐觴。詹 看中粉兒,口佔一詞:“淡淡青山兩點春,嬌羞一點口兒櫻,一梭兒玉一雲。白藕香中見西子,玉梅花下遇文君,不曾真箇也銷魂。”楊鎮乃以粉兒贈之,曰:“天游真箇銷魂也。”后詩文多以真箇銷魂指男女交合。
巨眼:意 思是眼力高,識見超卓。恭維別人有眼力的說法。
顛倒:反來覆去。
綢繆:這裡義同“纏綿”。形容男女歡愛,難捨難分。
金腕釧:金手鐲。
待漏:百宮黎明入朝,等待朝見皇帝。這裡指等待朝見玉帝。
朝暾(tūn 吞):朝陽。
振衣:抖動上衣。起床的動作。
膩然:細柔滑潤的感覺。
赤松:赤松子,傳說中的仙人。為神農時雨師,服水玉以教神農,能人火不燒。后至昆崙山,常入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見劉向《列仙傳》 及干寶《搜神記》。《史記·留侯世家》:“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
胤續:後代。胤,嗣。
綳:柬裹小兒的布幅,即襁褓。這裡意思是用布幅束裹著。
骨肉:指親生兒女。
有志:指有志於修鍊成仙。
二天:兩個丈夫。《儀禮·喪服傳》:“夫者,妻之天也。”
藜藿:藜與藿,貧者所食的兩種野菜。《韓非子·五蠹》:“糲粢[lì zī]之食,藜藿[lí huò]之羹。”
成謀:成議,協議。
諏(zōu)日:選擇吉日。諏,諮詢。
嬪(pīn ):新婦嫁住夫家,俗稱“過門”。此句謂吳生未行親 迎之禮,太史主動送女完婚。
質奩作具:典押妝奩,為婆母治葬具。
一人得道,拔宅飛升:《太平廣記》十四《許真君》引《十二真君 傳》:許遜,字敬之,東晉道士:家南昌。傳說於東晉寧康二年(374),在 南昌西山,全家四十二口拔宅飛升。
遠逝:遠去。逝,往。
井井:有條理的樣子。《荀子·儒效》:“井井兮其有理也。”
神童:指特別聰慧的兒童。唐宋科舉有童子科,應試者稱應神童試。明清無 此科,謂以少年參加鄉試中舉,如古之膺神童舉。
霜露之辰:《禮記·祭 義》:“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凄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后因以霜 露之辰指祭祖的日子。
祭南嶽:岳,又作“”。漢宣帝時曾定安徽天柱山為南嶽。后改定 湖南衡山為南嶽,相沿至今。漢時五嶽秩比三公,唐玄宗、宋真宗封五嶽為 王、為帝,明太祖尊五嶽為神。歷代封建帝王多親往致祭,或按時委員代祭。
各天:各在天之一方。
端賴卿賢:確實仰賴夫人賢慧。
妝次:意思是奉達妝台左右。舊時致平輩婦女書信的一種習慣格式。
家報:家信。
拆白謎:又叫拆白道字。用離析字形來說話表意的一種修辭格式。因為所拆字夾雜在語句中間需要辨測,近於謎語,所以叫拆白謎。
甥:女兒的子女。《詩·齊風·猗嗟》:“不出正號,展我甥兮。”傳:“外孫 曰甥。”
誦:念;口述。
龍鍾:身體衰憊步履蹇滯的樣子。
坌息:呼吸急促,喘粗氣;此謂急行氣促。坌,噴涌。
回祿之災:火災。回祿,我國古代神話中的火神。《左傳·昭公十 八年》:“鄭禳火於玄冥、回祿。”註:“玄冥,水神。回祿,火神。”
徊徨:徘徊,彷徨。
月闌:月亮周圍的光氣,其形如環。通稱月暈。
降:座落。
有一個書生叫吳筠,字青庵,少年時就很有名氣。當地葛太史曾看過他的文章,給以好評。因喜歡他的文才,就托與吳筠要好的人請他來交談,以觀察他的言談與文采,並說:“哪裡有像吳筠這樣的才學還長期過窮日子的呢?”並叫鄰居們傳話給吳筠:“要是能奮發上進,考取功名,我就把女兒嫁給他。”
葛太史有一個女兒,長得很漂亮。這話傳到吳筠耳朵里,他非常高興,也很有信心。可是第一次考試就落了榜。他就託人轉告太史:“我能富貴那是命中注定,只不過不知道是早是晚。請等我三年,我實在不能成功,他的女兒再另嫁。”由是他更加刻苦學習。
一天夜裡,明月之下,有一個秀才來拜訪他。這人長得白凈臉,短頭髮,細細的腰,長長的手。吳生有禮貌地問這人從哪裡來,有什麼事。那人說:“我姓白,字於玉。”兩人又稍稍說了幾句話,吳生覺得此人心胸開闊,心裡很是賞識,就留白生同宿一處。白生也不推辭,睡到天明才走。吳生再三囑咐,順便時再來敘談。白生也覺得吳生誠實熱情,就提出要在吳生家借住。吳生非常同意,約好搬家的日子,就分手了。
到了搬家的那天,先是一個老頭送炊具及其它用具來,隨後白生才到。他騎一匹白龍馬,吳生迎接進來,忙命家人打掃房間安排住下。白生也打發跟來的人牽馬回去。
從此以後,兩人朝夕相伴,互相研討學問,各有收益。吳生見白生讀的書不是常見的書,也沒有八股文一類的文章,便奇怪地問白生。白生回答說:“人各有志,我不是求功名的人。”晚上還經常請吳生到他屋裡喝酒,拿出一卷書來給吳生看,書中都是些氣功方面的事,吳生看不懂,便信手放在一邊。又過幾天,白生對吳生說:“那天晚上給你看的書,書中講的都是些《黃庭經》的要術,是羽化登仙的入門教材呀。”吳生笑著說:“我對成仙不感興趣。成仙得斷絕情緣,沒有雜念,這我是做不到的。”白生問他:“為什麼?”吳生回答是為傳宗接代。白生又問:“為何這麼大年紀還不娶親呢?”吳生笑道:“‘寡人有疾,寡人好色’。”白生說:“‘王請無好小色’。你想娶個什麼樣的意中人?”吳生才把等葛太史女兒的事告訴了白生。白生懷疑葛家女子未必真美。吳生說:“這女子美是遠近都知道的,不是我自己眼光淺。”白生一笑了之。
第二天,白生忽然整理行裝,對吳生說是要走。吳生依依不捨,難過地與白生絮絮話別,不忍分離。白生就叫童子背了行李先走,自己與吳繼續說話。忽然見一個青蟬叫著落在桌子上,白生告辭說:“車子已經來了,我告辭了。以後你著想我,就掃一掃我睡的床,躺在上面。”吳生聽了剛想再問什麼,轉眼間,白生就縮小得像指頭一樣大,一翻身騎在青蟬背上,吱地一聲飛走了。漸漸消失在彩雲中。吳生這才知道白生不是平常人。驚愕了很久,才悵然若失地回房。
過了幾天,天上忽然下起濛濛細雨來。吳生很想念白生,就走到白生住的房間。一看白生住的床上布滿了老鼠的爪跡,嘆了口氣,用條帚掃了一下,鋪上一張席子躺下休息。不多時,就見白生的書童來請他,吳生非常高興,跟了童子就走。一霎時,見一群小鳥飛來,童子捉住一個對吳生說:“黑路難走,可騎小鳥飛行。”吳生顧慮這麼小的鳥能擔負得動嗎?童子說:“可以騎上試試。”吳生就試著騎在上面,見鳥背非常寬綽,童子也騎在他身後,只聽嘎的一聲就飛上了天空。
不多時,眼前出現一座紅門。鳥落了地,童子先下,扶吳生也下來,吳生問:“這是哪裡?”童子回答說:“這是天門。”門兩邊有一對大老虎蹲在那裡,吳生很害怕,童子護著他領著進去。只見處處風景與世間大不相同。童子領他到了廣寒宮,宮內都是水晶台階,走路像走在鏡子上一般。兩棵大桂花樹,高大參天,蔭翳天日,花氣隨風飄來,香氣襲人。房屋、亭子都是一色紅窗紅門,時常有美女出出進進,個個端莊秀美,人間無比。童子說:“王母宮的宮女更漂亮。”因怕白生等久了,沒能多留,童子匆忙領他走出廣寒宮。
又走了一段路,就看見白生在門口等他。白生一見到吳生,忙上前來握住他的手,領他進了院子。吳生見屋檐下清水白沙、涓涓流淌,玉石雕砌的欄桿,好像月宮一樣。剛進屋坐下,就有妙齡女子前來獻香茶,接著就擺上酒宴。四個美女,金佩玉環、叮噹作響,侍立兩邊。吳生剛覺背上有點痒痒,就有美人伸入細手用長指甲輕輕搔癢。吳生直覺心神搖曳,一時平靜不下來。不一會兒,就喝得有點醉意,漸漸掌握不住自已,笑著看看美人,殷勤地與美女說話,美女每每笑著避開他。白生又命美女唱歌佐酒。一紅紗女子端著酒杯獻酒,一面唱動聽的歌曲,眾美女也都隨著一起演奏起來。奏完,一個綠衣女子一面唱歌,一面獻酒;一個穿紫衣的和一個穿白紗衣的女子嗤嗤笑著,暗中互相推讓,不敢向前。白生又命她們一人唱歌,一人敬酒。於是紫衣女便來敬酒。吳生一面接杯,一面用手撓女子的手腕。女子一笑失了手,把酒杯掉在地上打碎了。白生責備她,這女子含笑撿杯,低下頭細聲說:“冷如鬼手馨,強來捉人臂。”白生大笑,罰紫衣女自唱自舞。紫衣女舞完后,白衣女又來敬一大杯,吳生謝絕;白衣女捧酒不快,吳生只得又勉強喝了。吳生用醉眼細看這四個女子,都風度翩翩,沒有一個不是絕世佳人。吳生忽然對白生說:“人間的美女,我求一個都很難,你這裡這麼多漂亮的美人,能不能讓我真正快樂快樂?”白生笑著說:“足下不是有意中人嗎?這些你還能看上眼?”吳生慚愧地說:“我今天才知道我見識得太少。”於是白生就召集起所有美女讓吳生選擇。吳生看看哪個也好,一時拿不定主意。白生因為紫衣人曾和他有過捉臂之交,便吩咐她抱了被子去侍奉吳生。
吳生與紫衣女同床睡覺,盡情歡樂,恩愛無比。事後,吳生向紫衣女索取信物,她就摘下金手鐲贈給他。忽然童子來說:“仙人凡人有別,請吳先生馬上回家。”女子急忙起床出門去了。吳生問童子白生哪裡去了,童子說:“早去上朝了,他吩咐我去送你。”吳生悶悶不樂,只好跟童子按原路返回。到了天門,一回頭,童子不知何時已不見了,門邊的兩個老虎張著大嘴一起向他撲來。吳生急忙快跑,眼前卻是一條無底的山谷,想住腳巳來不及了,一頭扎進了山谷,吃了一驚,出了一身冷汗。一睜眼,原來是做了個夢。太陽已紅彤彤的了。拿起衣服一抖,覺得有件東西掉在床上,一看,正是那金鐲子,吳生心裡好生奇怪。
從此,吳生想陞官發財、娶美女的心思,全部沒有了,心灰意冷。對人間不感興趣,一心嚮往名山大川,拜尋赤松子,得道成仙。然而他還一直沒有忘記傳宗接代。
又過了十幾個月,有一天,吳生白日睡覺正濃,忽然夢見紫衣女子自外邊進來,懷裡抱著一個嬰兒,對吳生說:“這是你的骨肉。天上難留這個孩子,所以抱來送還你。”說罷,把孩子放在床上,又用衣服蓋好,匆匆就走。吳生一把拉住她,要她再住一夜。紫衣女說:“上次同床為新婚,這一次同床為永別,百年夫妻就到這裡。若郎君有志,或者還能相見。”吳生醒來,見嬰兒睡在身邊被褥之中。趕快抱著去見母親。他母親高興得不得了。於是雇了奶娘餵養這個嬰兒,起了個名字叫夢仙。
吳生有了孩子,就托入轉告葛太史,說自己要去隱居,請他女兒另嫁。太史不肯,吳生固辭,太史便告訴了他女兒。女兒說:“遠近沒有不知道我已許配吳生了,今又改嫁別人,這不是嫁了二夫嗎?”於是葛太史又把這話轉告了吳生。吳生說:“我不但已經不圖功名,而且也絕情於男女了。我所以沒有馬上進山,只是因為尚有老母健在。”太史又把吳生的話告訴女兒。女兒說:“吳郎窮,我甘心跟他吃糠咽菜;吳郎要去,我就在家侍奉婆母,定然不另嫁他人。”如是再三,商量不妥,葛太史最後還是擇了日子,用車馬把女兒送到了吳家。吳生感念妻子的賢惠,特別敬愛她。女子侍奉婆母非常孝順,也不嫌家裡貧窮。
徠過了兩年,吳母死了,葛女賣了嫁妝,安葬了婆母,盡到了禮節。吳生對妻子說:“我有像你這樣的賢妻,還有什麼憂愁!只是聽說一人得道,拔宅飛升,所以想離家出走,家中一切就拜託給你了。”葛女也坦然答應,一點也不挽留。於是吳生就辭別妻子出走了。
吳生走後,葛女外理生活,內訓嬌兒,治家井井有條。夢仙也漸漸長大,學習聰明過人,十四歲中了秀才,人稱神童;十五歲又入翰林。每次皇上褒封,不知他的生母是誰,只封葛氏一人。每次有祭禮,夢仙總是問父親在哪裡?他的養母就實話告訴了他。夢仙想辭官不做,去找父親。養母說:“你父親已走了十幾年了,想來也已成仙了了你哪裡去找?”
後來,夢仙奉旨去祭南嶽,路上碰到一夥強盜,正在危急之時,來了一個持劍的道士,強盜被嚇跑了,為他解了圍。夢仙很感激他,贈給道士銀子,道士不要,只拿出一封信託夢仙捎回,囑咐說:“我有個朋友與大人是同鄉,托你代問個好。”夢仙問:“你朋友叫什麼?”回答說:“王林。”夢仙想來想去村中沒有這個人。道士說:“他是個老百姓,大人可能不認識他。”道士臨走拿出一隻金鐲子說:“這是閨閣之物,我拾了來沒有用,就送給你作為捎信的報答吧!”夢仙拿著手鐲細看,做工精細,鑲嵌精美,就拿回家去給了他夫人。夫人很珍愛,叫能工巧匠照樣再造一隻配成對,怎麼也造不了這麼好。
夢仙遍問村中百姓,並沒有王林這個人。實在無法找到,就打開信看,信中寫著:“三年鸞鳳,分拆各天。葬母教子,端賴卿賢。無以報德,奉葯一丸。剖而食之,可以成仙。”後面寫著:“琳娘夫人妝次。”念完了仍不知是什麼人,就拿著去問他養母。養母一看便哭了,說:“這是你父親的家書,琳是我的小字。”夢仙才恍然大悟,王林是琳字的拆白,悔恨得不得了。又拿出鐲子請母親看,母親說:“這是你生母的遺物。你父在家時,常拿出來給我看。”又看藥丸,有豆子那樣大。夢仙高興地說:“我父親是仙人,吃了這丸子一定長生不老。”他母親沒有立刻吃,暫時藏了起來。等葛太史來看外孫時,便給他念了吳生的信,並奉上丹丸給他添壽。太史一分兩半,與女兒分吃了,頓時精神煥發。太史已七十多歲老態龍鍾,吃了丹丸忽然筋骨強壯,不坐車馬,步行走得很快,家人跑路才跟上他。
又過了一年,城裡發生了火災,大火終日不滅,全城人都不敢睡覺。夢仙家的人都在院子里看,見大火漸漸漫延過來,一家人無計可施。忽然夫人手上的金鐲子嘎然作響,自行脫手飛上天空,逐漸擴大,圓圓地蓋在宅子上,鐲子口朝東南。眾人都驚呆了。一霎時,火自西來,燒到鐲子邊就轉向了東。等火勢燒遠了,眾人認為鐲子不會再回來時,忽見紅光一下收斂起來,鐲子當地一聲掉在夫人足下。這次城中大火燒了民房幾萬間,前後左右都成灰燼,只有吳宅安然無恙。只有東南角一小閣被燒,正是鐲子口處沒蓋住的地方。
葛女年五十多歲時,有人看見,還像二十多歲人一樣。
紀曉嵐:“才子之筆,莫逮萬一。”馮鎮巒〈讀聊齋雜說〉:“聊齋非獨文筆之佳,獨有千古,第一議論醇正,准情酌理,毫無可駁。如名儒講學,如老僧談禪,如鄉曲長者讀誦勸世文,觀之實有益於身心,警戒頑愚。至說到忠孝節義,令人雪涕,令人猛醒,更為有關世教之書。”陳廷機《聊齋志異》序:“亦以空前絕後之作,使唐人見之,自當把臂入林,後來作者,宜其擱筆耳。”魯迅評論《聊齋志異》:“《聊齋志異》雖亦如當時同類之書,不外記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描寫委曲,敘次井然,用傳奇法,而以志怪。變幻之狀,如在目前;又或易調該弦,別敘崎人異行,出於幻滅,頓入人間;偶敘瑣聞,亦多簡潔,故讀者耳目,為之一新。……明末志怪群書,大抵簡略,又多荒誕不情;《聊齋志異》獨於詳盡之處,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是人情,和易可親,忘為異類,而又偶見鶻突,知復非人。”
蒲松齡(1640-1715),清代傑出的文學家,字留仙,一字劍臣,別號柳泉居士,世稱聊齋先生,山東淄川(今山東淄博市)人。他出身於一個沒落的地主家庭,父親蒲槃原是一個讀書人,因在科舉上不得志,便棄儒經商,曾積累了一筆可觀的財產。等到蒲松齡成年時,家境早已衰落,生活十分貧困。蒲松齡一生熱衷功名,醉心科舉,但他除了十九歲時應童子試曾連續考中縣、府、道三個第一,補博士弟子員外,以後屢受挫折,一直鬱郁不得志。他一面教書,一面應考了四十年,到七十一歲時才援例出貢,補了個歲貢生,四年後便死去了。一生中的坎坷遭遇使蒲松齡對當時政治的黑暗和科舉的弊端有了一定的認識,生活的貧困使他對廣大勞動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有了一定的了解和體會。因此,他以自己的切身感受寫了不少著作,今存除《聊齋志異》外,還有《聊齋文集》和《詩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