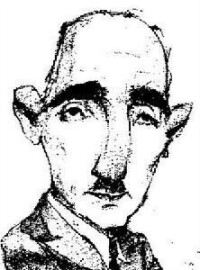徠弗朗索瓦·莫里亞克(法語:François Mauriac,1885年10月11日-1970年9月1日),法國小說家,1952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里亞克在法國波爾多出生,1905年在波爾多大學文學系畢業。他的主要作品有詩集《握手》、小說《愛的荒漠》等。

弗朗索瓦·莫里亞克
弗朗索瓦·莫里亞克(Francois Mauriac,1885—1970),一八八五年十月十一日生於法國波爾多市一個銀行家家庭,幼年喪父,由虔誠的天主教徒母親撫養成人。他早年在當地的教會學校學習,后入波爾多文學院攻讀歷史,並曾一度在巴黎文獻典籍專科學校學習,但他志在文學創作。一九九年發表第一部詩集《合手敬禮》,翌年,詩集《向少年時代告別》問世。此後轉向小說創作,有《身戴鐐銬的兒童》(1912)和《白袍記》(1914)等。一戰爆發,他參加了傷兵救護工作,戰後恢複寫作,發表了小說《血肉斗》(1920)、《優先權》(1921)等。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三九年是莫里亞克創作生涯中最重要的階段。

1933
一九徠二二年發表《給麻風病人的吻》,贏得較大聲譽。隨後又相繼發表了《火流》(1923)和《吉尼特里克斯》(1923)。兩年後發表的《愛的荒漠》,獲得法蘭西學院的小說大獎,奠定了他在法國文壇的地位。一九二七年,《苔蕾絲·德斯蓋魯》的發表,引起了很大反響,於是他又寫了三個續篇:《苔蕾絲看病》、《苔蕾絲在旅館》和《黑夜的終止》。《蝮蛇結》(1932)被大多數評論家公認為是他最成熟和最完美的作品。小說在人物的心理方面有著絕妙的描寫。一九三三年到一九四一年間,莫里亞克寫了五部小說,如自傳小說《弗隆特納克家的秘密》(1933)、《黑天使》(1936),其中最著名的是《法利賽女人》(1941)。在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五一年間,他還以濃厚的興趣投身於戲劇藝術,創作了以反映靈和肉鬥爭為主題的《阿斯摩泰》(1938)、《錯愛的人們》(1945)和《地上的火焰》(1951)等四個劇本,頗受觀眾好評。
政治、文藝思想
在莫里亞克生命的最後十八年中,他寫出了大量政論文、傳記作品和回憶錄,如傳記《戴高樂》(1964)、日記體回憶錄《內心回憶》(1959)、《新內心回憶》(1965)、《政治回憶錄》(1967)等,詳細記載了許多歷史事件,表達了他的政治觀點和文藝思想。一九六九年,他還發表了最後一部小說《往日的青春》。

簽名
莫里亞克在長達六十年的創作生涯中,寫了一百多卷各種體裁的作品,其中有小說二十六部,詩集五本,劇作四部。他深受帕斯卡爾、拉辛、波德萊爾、蘭波的影響,作品中表現了古典主義的文學傳統與現代主義潮流之間的矛盾和交融。
莫里亞克由於“在小說中深入刻畫人類生活時所展示的洞察力和藝術激情”,於一九五二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一九七零年九月一日,莫里亞克在巴黎病逝。

弗朗索瓦·莫里亞克
莫里亞克一貫致力於描繪一個明確的環境——人們能在法國地圖上指出的一角。他的小說情節展開的背景,幾乎總是在紀尤德省波爾多地區,或者在朗德省。前者是古老的葡萄之鄉,布滿大大小小的葡萄園;後者是松林和牧場之鄉,寂寞的空間顫動著蟬兒的歌聲,大西洋傳來遠方的雷鳴。這是莫里亞克的故鄉。他把描繪這個獨特的地區和人民,尤其是那些土地佔有者,看做是自己內心的召喚;可以說,他的個人風格是嚴謹和無情的透徹,猶如扭轉葡萄藤的控制力和從灼熱的天空撒下的光線。在此意義上,這位讀者遍布全球的作家,明顯地、無可否認地是一個鄉下人,但是,他的鄉下氣並不排斥世界範圍內的重大人類問題。誰要想開掘得深,他就必須首先和始終有一塊他能下鎬的基地。在莫里亞克的一系列小說中,充滿令人難以忘卻的情景、對話和緊張場面,它們的啟示如此神秘和殘酷。同一主題的重複可能會產生某種單調感,但是,他那敏銳的分析和真實的筆觸,隨同每種新的衝突,喚起同樣的欽佩。莫里亞克的語言無可匹敵,簡潔而富有表現力。他的散文能以暗示性的短短几行,說清楚最複雜和最困難的事情。他的最著名的作品都具有邏輯的純正和古典式的措辭簡練。

弗朗索瓦·莫里亞克
莫里亞克從小受到特別嚴格的管教;他是在一個強烈地受母系影響的環境中長大的,這種影響不斷地對他青少年時期的敏感性發生作用。有理由相信,他後來一旦與外界接觸,曾產生一種痛苦的驚駭。在此之前,他接受虔誠的教誨,從未料到罪惡支配現實達到這樣一種程度,以至遍及一切單調和瑣碎的日常生活。他生來就是天主教徒,在天主教的氣氛中長大;這種氣氛成了他的精神之鄉,總之,他從無必要對教會作出抉擇。但是,他有幾次重新審查和公開說明他的基督教立場,主要是為了探討現實主義立場對於作家的要求能否與教會的戒律協調一致。撇開這些不可避免和無法解決的二律背反,莫里亞克作為一個作家,他利用小說闡明人類生活的一個特殊方面,其中,天主教的思想和感受,既是背景,又是要旨。因此,他的非天主教的讀者,或許在某種程度上感到自己在觀看一個陌生的世界;但是,若要理解莫里亞克,必須記住這一事實:他不屬於改變信仰的作家群,否則,對他的理解就不可能完全。他本人意識到賦予他那些根底的力量;當他探究被錯誤的重擔壓倒的人們的靈魂,考察他們的秘密意圖時,那些根底允許他引證一個偉大而嚴厲的傳統。

莫里亞克雕塑
莫里亞克如此長久和如此毫無疑義地在現代文學領域確保中心地位,以致
教派的隔閡幾乎已經全然無足輕重。由於他那一代許多曇花一現的作家今天幾乎已被忘卻,他的形象在這幾年中越來越鮮明突出。就他的情況而言,名聲的取得不是以遷就為代價的,因為他那憂鬱和嚴峻的世界觀很難取悅他的同代人。他始終懷抱高遠的目標。他竭盡全力,堅忍不拔,在他的現實主義小說中繼承諸如帕斯卡爾[(]、拉布呂耶爾和博蘇埃這樣一些偉大的法國道德家的傳統。對此,可以補充一點:他代表一種宗教靈感的傾向;這種宗教靈感,尤其在法國,一向是精神結構中的極端重要的因素。如果我可以在這裡提一下作為著名新聞作家的莫里亞克,那麼,為了歐洲思想的利益,我們一定不要忘記他在這一領域的工作,他對日常事件的評論,他的值得公眾尊重的文學活動的這一側面。無聲的青春焦慮、罪惡的深淵及其呈現的永恆威脅,虛妄的肉體誘惑,物慾橫流,自滿和偽善泛濫,這些是經常出現在莫里亞克筆下的主題。不足為怪,由於他使用這樣一套顏料,有些人便指責他無故醜化主題,像厭世者那樣寫作。而他的答覆是:相反,如果一個作家以聖寵作為他的世界觀基礎,認為人類的最高庇護是上帝的愛,那麼,他會感到自己懷著一種希望和信任的精神從事創作。我們無權懷疑這一表白的真誠,但是,在實踐中,邪惡顯然比清白更引起他的注意。他憎惡訓誨;他不知疲倦地描繪沉溺罪惡、遭受天罰的靈魂,但是,一旦靈魂意識到自己的苦難,即將懺悔和得救,他一般就喜歡在這時拉下帷幕。這位作家將自己的見證作用限制在這種進化的否定方面,而將肯定方面全部留給未必會寫小說的牧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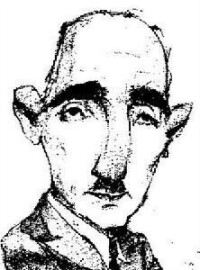
莫里亞克漫畫像
莫里亞克本人曾經說過,人人都可以在一種美化生活和允許我們逃避現實的文學中尋求滿足,但是,大多數人對於這種文學的偏愛,不應該造成我們歧視那些以了解人類為天職的作家。惟獨那些不敢正視生活、從而歪麴生活的人,才仇恨生活。真正熱愛生活的人,熱愛生活的原貌。他們逐一剝去生活的假面,把心交給這個最後被剝得精光的怪物。在與
安德烈·紀德的一次論爭中,他回到他的思想基點,斷言徹底的真誠是與作家行業相聯繫的榮譽形式。通常,答爾丟夫被穿上宗教的服裝,但是,莫里亞克肯定表示,這類人物更經常出現在那些支持
唯物主義進步理論的人們中。嘲笑道德原則是容易的,但是,莫里亞克反對這種嘲笑。他曾經十分簡要地宣稱:“我們每個人都知道自己能夠變得比目前更少一些罪惡。”這句簡短的話語或許是個關鍵,能揭開莫里亞克創作中的善的秘密,憂鬱的熱情和微妙的失調的秘密。他縱身人類的弱點和邪惡之中,並非出於追求藝術絕技的狂熱。即使在他無情地分析現實的時候,莫里亞克也始終確信,有一種超越理解的愛。他不提倡絕對;他知道它並不有效地存在於純粹狀態,因而他不以寬容的眼光看待那些自稱虔誠的人。他忠於已經化為自己血肉的真理,竭力按照人物的本來面目看待他們,描寫他們;這些人物將會悔恨交加,希望自己變得即使不是更好,至少更少一些罪惡。他的小說可以比作是窄口的深井,在底部能看到一泓神秘的活水在黑暗中閃爍。
1952年作品《愛的荒漠》獲諾貝爾文學獎。獲獎理由: “因為他在他的小說中剖析了人生的戲劇,對心靈的深刻觀察和緊湊的藝術” ("for the deep spiritual insight and the artistic intensity with which he has in his novels penetrated the drama of human li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