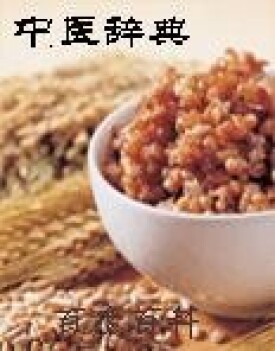五病
五病
五臟氣逆而為病的癥候,這不包括五臟氣機失調的複雜癥候,心為噫;肺為咳;肝為語;脾為吞;腎為欠為嚏,對臨床辨證治療有指導意義。
《素問·宣明五氣篇》:“五氣所病:心為噫;肺為咳;肝為語;脾為吞;腎為欠為嚏;胃為氣逆、為噦、為恐;大腸、小腸為泄;下焦溢為水;膀胱不利為癃,不約為遺溺;膽為怒,是謂五病。”張志聰謂“五氣所病”,乃是“五臟氣逆而為病”,故不能包括五臟氣機失調的複雜癥候。又:五病當指五臟病,故從“胃為氣逆”至“膽為怒”可能是後人注語,誤入正文。
五臟氣逆的臨床癥狀的描述,五臟之氣失調,各有所主的病症:心氣不舒發為噫氣,肺氣不利發為咳嗽,肝氣鬱結髮為多語,脾氣不和發為吞酸,腎氣衰憊發為呵欠。五臟氣又名五氣所病。
心為噫
《素問·宣明五氣篇》其所論“五氣所病”首論“心為噫”。“噫”,《說文》言“飽食息也”,故今人多以噯氣言,歸於脾胃氣機上逆而致。但《素問·脈解篇》云:“所謂上走心為噫者,陰盛而上走於陽明,陽明絡屬心,故曰上走心為噫也。”可見,心為噫,噫歸心主,是因為太陰(脾經)陰氣較盛而上走於陽明經(胃經),而陽明經通過絡脈與心臟相連屬使然。
由是觀之,噫(噯氣)之治,當不僅僅有和胃降逆一途。在和胃降逆的同時,結合開心竅,補心氣,溫心陽,滋心陰等法,皆為治噫(噯氣)之良法,特別是臨床上治療頑固性噯氣以和胃降逆法治療無效的,皆可從“心”治“噫”而每獲良效,此亦為治“本”之道。臨床治療頑固性噯氣、呃逆諸證,大多在辨證論治的基礎上,佐以開心氣、通心竅、入心經、清心火之品如遠志、石菖蒲、鬱金、黃連等而每獲良效。其他芳香開竅葯如麝香、冰片、蘇合香、樟腦、蟾酥等雖然亦有此功效,但由於其性味過於辛香燥烈走竄,且多入丸散之劑內應用。
具體到臨床常用方劑,如胃中寒冷而噫(噯氣)者,予丁香散;胃氣上逆而噫(噯氣)者,予竹葉石膏湯;氣滯痰阻而噫(噯氣)者,予五磨飲子;脾腎陽虛而噫(噯氣)者,予附子理中湯;胃陰不足而噫(噯氣)者,與益胃湯等。臨床治療噫(噯氣),首先應在辨證論治的基礎上進行立法處方,然後再加減化裁,其中以遠志、石菖蒲、鬱金為治呃逆之特效藥與通用藥,對頑固性呃逆、噯氣、噫氣、甚至噦證都有較好療效。
肺為咳
《黃帝內經》多處論述咳嗽,其《素問·咳論篇》已將“咳”之機理盡述,如從整體觀念出發提出“五臟六腑皆令人咳,非獨肺也”一論後人多有發揮。《素問·宣明五氣篇》中“肺為咳”以言其常,如《素問·咳論篇》言:“皮毛者肺之合也。皮毛先受邪氣,邪氣以從其合也。其寒飲食入胃,從肺脈上至於肺,則肺寒,肺寒則外內合,邪因而客之,則為肺咳”,又如“肺咳之狀,咳而喘息有音,甚則唾血”。臨證需要抓主症,方能正確把握病機。
肝為語
“肝為語”是一個病理生理概念,《內經》對肝已經有了較為詳細的論述,但其所述之“肝”,並非是單純的解剖學概念,而是一個病理生理概念。因此,“肝為語”也應該是一個病理生理概念,提示“肝”的生理狀態、病理表現和功能調節與“語”有著密切的關係。
生理上,喉是人的發音器官,與言語密切相關。就經絡循行部位而言,《靈樞·經脈篇》:“肝足厥陰之脈,……屬肝絡膽,上貫膈,布脅肋,循喉嚨之後,上入頏顙……其支者,從目系下頰里,環唇內”。在《靈樞·經脈篇》十二經脈中,肝經是被明確描述為“循經喉嚨”的經絡之一(另有足陽明胃經和足少陰腎經循行經喉),可見肝與“語”有著密切的關係。
病理上肝與語有以下幾點聯繫:
1、肝熱可引起狂言。“肝熱病……熱爭則狂言及驚。”(《素問·刺熱論篇第三十二》)
2、“厥逆在肝”、“肝氣鬱”可引起譫語。“厥陰厥逆,……譫言,治主病者。”(《素問·厥論篇第四十五》)
3、多語與少語又可以交替出現。“厥陰之脈……其病令人善言,默默然,不慧,刺之三。”(《素問·刺腰痛論篇第四十一》)
4、“語”是一種病“證”。“春刺冬分,邪氣著藏,令人脹,病不愈,又且欲言語。”(《素問·診要經終篇第十六》);
5、驚駭可失語。“肝脈騖暴,有所驚駭,脈不至若喑,不治自已。”(《素問·大奇論第四十八》)。喑,不能言也(緘默,不做聲)。說明驚駭可以使肝氣亂而脈伏而不能言。此證是“因為受了驚恐,就不需要治療,待其自行恢復”;
6、針刺刺中肝后“語”有異常是危侯。“刺中肝,五日死,其動為語。”(《素問·刺禁論第五十二》)。《素問·刺禁論》論述了針刺禁忌的要點,“刺中肝,大約五日即死,其變動發生“自言自語”的癥狀,提示肝在氣為語,“刺中肝”后,若見“語”有異常之證,是為死之徵兆。
臨床運用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1、“語”是“肝”病的癥狀。“語”是足厥陰肝病而引起的臨床癥狀。患者如出現“語”的異常時,臨床上需要考慮足厥陰肝經之病,應該注意辨別肝所主藏血、主筋、主疏泄、主藏魂、開竅於目等生理功能的異常與否。足厥陰肝病所致“語”的異常,臨床癥狀不僅僅是“多語”,還應當包括:“默默少語”、“緘默(甚或不語)”、“自言自語”、語態的異常及語義的錯亂(甚或狂言、譫言)等等。
2、“語”的異常可從“肝”論治。“語”是足厥陰肝病而引起的一種病“證”。患者如出現“言語”異常之證時,臨床上可從肝論治。通過藥物或其他方式,採用養血柔肝、疏肝理氣、清肝瀉火、平肝潛陽等治法,調節肝主藏血、主筋、主疏泄、主藏魂等功能,從而來治療“語”之病證。
3、“肝鬱”可用“語”來調治。姚止庵《素問節解》在註解“肝為語”時說:“語者,所以暢中之郁也,肝喜暢而惡郁,故為語以宣暢氣機之郁。”提示:“言語”可作為肝的自我調節形式,通過“言語”方式,能夠宣暢氣機而疏解肝鬱。“肝鬱”與現代多種心理、精神以及心身疾病的中醫認識密切相關;因此,《素問》“五氣所病”的“肝為語”理論,在現代中醫心理治療學臨床實踐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其與現代心理學臨床常用的“疏導療法”有著異曲同工之處。
脾為吞
因脾主運化水液,其性惡濕,在液為涎,開竅於口。涎為口津,是唾液中較清稀的部分,在進食時分泌較多,具有保護口腔黏膜、潤澤口腔、幫助食物吞咽和消化的作用。《素問·宣明五氣》說:“脾為涎”,故有涎出於脾而溢於胃之說。《素問·玉機真臟》說:“然而脾善惡可得見之乎?岐伯曰:善者不可得見,惡者可見。”此雖為論脈法而設,但同樣也可以解釋在正常情況下,涎液上行於口,但不溢於口外,所以不會出現異常的吞咽動作。若脾氣失調、脾胃不和,導致涎液分泌急劇增加或大量減少,臨床則出現以頻頻“吞咽”為特徵的諸多病變,故云“脾為吞”,即指脾病時易於出現吞咽異常癥狀。
濕盛“吞涎”
《黃帝內經素問集注》曰:“脾主為胃行其津液,脾氣病而不灌溉於四臟,則津液反溢於脾竅之口,故為吞咽之證。”是指脾氣病口涎增多所致的“吞涎”證。凡外感、內傷諸多原因,若病見口中多涎,頻頻吞咽,當責之於脾,從中焦論治。
濕熱蘊脾“吞涎”
脾與胃共居於中焦,兩者納運相得,升降相因,共為後天之本。《類經·藏象類》說:“上焦不治,則水泛高原;中焦不治,則水留中脘;下焦不治,則水亂二便。”脾胃虛弱,水濕失於運化,痰涎留滯胃脘,上溢咽喉,則頻咽不休,甚則嘔惡清水痰涎。水留胃脘之“吞涎”證多見於小兒,並且夜間癥狀明顯。
痰凝“吞引”
《中西匯通醫經精義·臟腑為病》云:“脾主化谷生津,凡口中津液少者,時常作吞引之狀。反吞為吐,又是水谷不下之故,皆屬脾病。可以互勘。”說明脾病運化失常,津液失於布散,涎液不足,口腔失潤,也會時常吞咽以緩解咽部不適癥狀。
脾主“吞酸”證
對於“脾主吞”,《素問識》解釋說:“吞,即吞酸酢吞之謂(平脈法云:噫而吞酸,食卒不下。又云:上焦不歸者,噫而酢吞)。龔廷賢云:吞酸,與吐酸不同。吞酸,水刺心也;吐酸者,吐出酸水也。”認為吞酸證歸屬於脾病。所謂吞酸,是指胃內酸水上攻口腔、咽溢,不及吐出而下咽的證候,又稱咽酸。《醫林繩墨·吞酸吐酸》曰:“吞酸者,胃口酸水攻激於上,以致咽溢之間,不及吐出而咽下,酸味刺心,有若吞酸之狀也。”所以,吞酸患者自覺癥狀為酸水由胃中上泛,隨即咽下,咽喉食道灼熱嘈雜,若吞食酸物之狀。同時,臨床觀察發現,很多患者發病時喜歡少量吞飲食物以緩解咽喉食道的刺激癥狀。吞酸的病因病機,歷代醫家多有論述,《壽世保元·吞酸》說:“飲食入胃,被濕熱郁遏,食不得化,故作吞酸。”吞酸與吐酸不同,吞酸有郁遏凝斂不通之象,屬於陰,為寒濕困脾,郁久作熱,苔多薄白而膩。至於其治療,《證治匯補·吞酸章》說:“吞酸為中氣不舒,痰涎郁滯,須先用開發疏暢之品。”《景岳全書·雜證謨·吞酸》云:“凡胃氣未衰,年質壯盛,或寒或食,偶有所積而為酸者,宜用行滯溫平之劑,以二陳湯、平胃散、和胃飲之類主之。”故當以調理中焦脾胃氣機為主,兼以燥濕散寒清熱。
腎為欠
本句在“五氣所病”中最有爭議。《黃帝內經》所言“欠”者計有11處之多,如《靈樞·九針論》所言:“五臟氣”病中“腎主欠”,“為嚏”未見,恐為衍文。另《素問·瘧論》之“瘧之始發也,先起於毫毛,伸欠乃作”,是言倦而伸腰,再《靈樞·口問篇》言:“陰氣積於下,陽氣未盡,陽引而上,陰引而下,陰陽相引,故數欠”,此處“欠”當作呵欠解。常人疲倦之時多見呵欠伸腰,但若經常如此實為腎氣不充,精不養神之“腎主欠”之症,應當引起醫患的高度重視。
“欠”有兩種含義。一是證名,出自《靈樞·口問》。又稱呵欠、欠伸、呼欠,有生理性和病理性之別,生理性多見於疲勞時的伸腰呼氣;病理性則不拘時間,頻頻而作,稱數欠。二是不足、短少之意。如《靈樞·經脈》:“小便數而欠。”那麼病理性的“欠”又是如何產生的呢?《靈樞·宣明五氣篇》明確指出“腎為欠”,《靈樞·九針》亦載:“腎主欠”,《金匱要略·腹瀉寒疝宿食病篇》則有“中寒家喜欠”之說。歷代醫家多沿此說,認為“呵欠”系陰盛陽衰、腎氣不足所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