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納
中國作家
李納,原名李淑源,雲南路南人。中國共產黨黨員。1948年開始發表作品。1949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
大事件
1920-05-22
出生
1920年5月22日出生於雲南省路南縣。
1948
創作首部短篇小說《煤》
1948年根據礦山生活的直接觀察和一些間接材料,創作了第一個短篇小說《煤》。
1951
因小說集《煤》奠定藝術風格
1951年由工人出版社出版小說結集《煤》,收錄了表現東北人民在艱苦的歲月里忘我支援東北抗日聯軍的短篇小說《父親》和《不願做奴隸的人》,以工人生活為題材的《出路》《姜師傅》以及她早前創作的《煤》。這幾篇小說都是反映重大社會主題的,語言樸實,流利敘事、對話平實自然,筆墨乾淨,生活氣息極濃。在短篇小說集《煤》中,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藝術風格。
1981
因《刺繡者的花》獲人民文學獎
1981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長篇小說《刺繡者的花》,出版后獲1977-1984年人民文學長篇小說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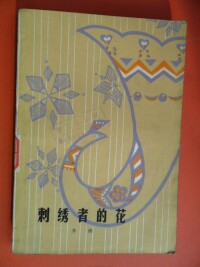
2019-04-29
逝世
2019年4月29日,李納在北京逝世,享年99歲。
1920年5月22日(陰曆四月五日),就出生在雲南省路南縣城內一個封建大家庭里,原名李淑源。李納降生時,祖父是當地的鄉紳。他是一位性格複雜的人,在家裡享有絕對的權威,但平時對任何人總是和藹可親,從不大聲呵斥孩子,高興時,還讓李納搬他的長指甲。他衣著樸素,不穿綢緞,但他是孔子的信徒,孔子的語言是他畢生遵守的信條,腦子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界限。
幼小的李納,感受最深的是家裡"男尊女卑"。她家叔伯五人,又有弟、妹,雖是一家人,但吃飯男女不能同席,男子那一桌的菜,要多要好。祖父每日嚴格監督叔叔們攻讀四書五經,背誦唐詩。至於女孩子,他深信"無才便是德",能認識幾個字就可以了。所以,李納只能讀"大狗跳,小狗叫,小孩子,哈哈笑"一類被祖父譏笑的課本。
父親的早逝,給李納一家帶來了不幸。當時,留下她和一個妹妹,母親還正懷著孕。祖父極希望生下一個男孩,以延續其後代。一個夏天的傍晚,家裡正宴請從遠方回鄉的叔叔,客人都在歡樂的飲酒舉署,忽然傳來嬰兒"呱呱"的哭聲。祖父警覺地問:"是男是女?"李納的嬸嬸早已查看清楚,隨即幸災樂禍地回答:"姑娘。"祖父立即沉下了臉,撂下筷子,揚長而去,同桌的外公像被擊中了頭頂,輕輕放下筷子,回到家裡,放聲痛哭。
痛苦的刺激就這樣強加給了年幼的李納,她回憶說:"這件事,在我心上投下不可磨滅的陰影。在舊中國,我最痛恨重男輕女,我憧憬著男女平等的生活。我對這個越長越可愛而又不受歡迎的妹妹,寄以極大的同情。有時把她抱到祖父面前,總是被她嫌惡地用"走開"二字趕走。母親因為絕望沒有奶,我小小的年紀,就不能不擔負起保姆的責任了。"
生活在一個動亂的時代,她的童年生活是寂寞的,而那美麗的大自然,卻是她童年的夥伴。在那偏鄉僻野里,除了山水以外,沒有正常的精神食糧,家裡的書,有的她看不懂。這時,一位遠房伯母,便成了她第一個文學啟蒙者。
這是一個善良的勞動婦女,年輕時便死了丈夫。這位伯母,性格豪爽,是一位路見不平敢於挺身而出的女性,她不知道"害怕"二字,就是在至高無上的族長面前,也敢據理抗辯,毫無懼色。在家裡,她承擔著牛馬般的勞役。當她轉完沉重的石磨時,便領著李納去看戲。戲場是大眾化的,觀眾都是短打扮的勞苦大眾,人們站在既無電燈照明,又不講究的露天底下,頭頂著星星,聚精會神地聽那《三國演義》《瓦崗寨》《水滸》的戲。這位伯母看戲認真,每次都同戲里主人公的感情一同升沉,愛憎感情異常分明。她最喜歡張飛、程咬金和李逵。
再暗淡的生活,也會有亮光。對李納來說,這亮光就是這些下層的勞動人民。她說:"我永遠懷著感激之情懷念他們。他們不但給過我快樂,更重要的是讓我看到生活中真正的美。這些人,就是頸項上拴著鐵鏈,也過得高高興興,從不對生活絕望。這些人是善良的,純樸的,對別人充滿了同情心。後來,我有幸接觸許多平凡崗位上的人,在眾多人物中,除少數之外,都各自帶著優美的素質走進我的世界。尤其是中國的女性,在舊社會,她們受著比男人更沉重的壓迫,一旦覺醒,對於舊生活的拋棄,義無反顧;對新生活的執著,捨死忘生。她們最高的道德準則,就是人民利益。有時,她們表現得比男人更勇敢,思想比男人更單純。我愛這些人。無論在戰爭年代,在和平建設時代,"就是在"四人幫"橫行的寒冷日子裡,她們的光輝都照亮了我,想到她們,心中充滿了溫暖、"(《李納小說選·自序》)這就是為什麼,李納在自己的筆下反覆歌頌她們。
中國的封建勢力是一條給人民製造了無窮苦難的繩索,中國雖然經歷了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和北伐,但那根繩索仍然束縛著當時的少男少女們,他們最感痛苦的還是婚姻不自主。李納也不例外。在高小時,她已經朦朧地意識到有一副沉重的枷鎖無情地綁縛著她。對方是什麼人?她一點也不知道。不知有多少次,她與同命運的小女友在校園裡的鳳仙花下偷偷哭泣。李納說:"像我們那樣的家庭,要提倡退婚是家庭的奇恥大辱。死,比退婚還容易。"
小學畢業后,在昆明讀書的叔叔回來了,他和李納有著同樣的痛苦。她向叔叔傾吐了自己的苦惱之後,叔叔要她爭取出去讀書,還指著牆上的一幅對聯說:"讀好了書,便可以"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了。"
母親同情女兒,贊成她出去念書。那時,她的家鄉只有一所女子小學。由於軍閥混戰,土匪出沒,滇軍來,川軍往,很不太平,她家不是逃到鄉下,就是躲進昆明。自從她受了叔叔的啟發和鼓勵,外出讀書"便成了她夢寐以求的願望。祖父最初不同意,一個女孩子,遠離家長的約束,在他看來是不可想象的。但經過母親的苦苦哀求,由於他憐憫她從小沒有父親,考慮再三,終於答應將她托給一家親戚。
聰明、勤奮的李納考取了昆明唯一的一所女子中學。以後,她曾多次提到《亞利安娜》給她的啟示。她說:"這件事,已經過去幾十個寒暑,可是至今想來,還清晰如同昨日。那時候,我是一個初中學生,寂寞總是籠罩著我。有一天,無意中看到一本厚雜誌,讀到《亞利安娜》。這篇小說,向我展示了一個全新的世界,我被一個為真理獻身的女性感動得熱淚迸流。在我稚氣的心靈中,它不啻是一束火把,它長久地在我心中燃燒,長久地成為鼓舞我的精神力量。"
李納所在的這座中學,在大革命時期十分活躍,出了不少共產黨員,還犧牲了幾位女英雄。但在李納入學時,空氣已經頗為沉悶,學生們在幾個老處女的監視下,如被幽囚的小鳥,連她們和男子一起走路也要開除。她們每天按部就班地上課,圖書館里有幾本不像樣子的書,只有冰心的《寄小讀者》還能稍稍滿足一點學生求知之心。一個偶然的機會,李納曾讀到巴金使之耳目一新的《亞利安娜》,但這種書在那裡是找不到的。
矛盾百出的大家庭分開了,她母親領著三個女兒開始單獨生活,日月艱難。不久,李納考入同樣腐敗、守舊的女子師範。她不喜歡數理化,而獨愛好語文。她的語文老師雖然年輕,卻很守舊,專教學生讀古書和寫作舊體詩。這時候,她接觸了屈原、陶淵明、李白和杜甫。李納說:"至今,我尚能背一些古文,不能不說這是那位年輕的語文教師的功勞。"
中國,近百年來受盡了敵人的欺凌。抗日戰爭的爆發,人民奮起抗戰,使苦難的祖國從黑夜望見了黎明的曙色。這時,李納同千百萬中國青年一樣,從個人的哀傷中奮起。國家正在死亡線上抗爭,用生命拯救她,是兒女的神聖責任。李納說:"在這偉大的時候,如果誰還僅僅想著個人的幸福,那便是犯罪!"當時不少雲南青年男女,得知抗戰的爆發,都浸沉在悲喜交集之中。幾天之內,許多有志之士離開家鄉上了前線。女學生也不肯後人,組織了"婦女戰地服務團",也要奔赴前線。李納興奮地參加了這個團,到昆明西山進行軍事訓練。但是,她母親反對,親自跑到昆明,終日形影不離,拉著她不放,使她沒有走成。
1938年,紛紛傳說敵機要轟炸昆明。一天早上,蔚藍的天空像平常一樣透明,院子里飄著陣陣花香。體育教師領著她們跑步之後,忽然異常嚴肅地叫她們立正。他激動地面向學生,用顫抖的聲音說:"同學們,敵機要轟炸,迫使我們不得不停止升旗。"他望望天空:"這是我們祖國神聖的領空,卻不能讓自己的國旗飄揚……"他哽咽著,淚水沿著他粗糙的臉頰滾了下來。國旗在沉默中升起。淚水從許多學生的眼裡涌流出來,最終形成一陣哀哭……這時,李納胸中的熱血在奔流,在燃燒,她回憶說:"我彷彿經歷了法國都德《最後一課》的情景,每每想起那難忘的一幕,我的心就激動起來,好像又置身於抗日的烽火之中……"
國難當頭,在許多青年看來,讀書已成為多餘。飯館和火車站,經常傳來出征的歌聲;酒杯相碰,淚流滿面,心向祖國,同發誓言:"不收復失地,誓不回家!"
不久,西南聯合大學的學生徒步來到雲南。他們帶來了進步文化,進步書店日益增多,宣傳抗日的書籍在學生中廣為流傳,學生的精神狀態更加高昂起來,使昆明成為全國救亡運動的中心。
正當雲南的抗日救亡運動不斷發展之時,李納的姨夫從上海來到昆明,受聘於雲南大學附中擔任教導主任。他在路南縣家鄉人的心目中,是不折不扣的共產黨。他團結進步教師,搜羅進步教師,楚圖南就是頗受學生愛戴的一位。昆明被敵機轟炸后,附中疏散到路南縣。李納由於家庭困難,又羨慕該校的自由空氣,便請求姨夫介紹到圖書館工作。這個圖書館有許多進步書籍,周圍又有不少具有進步思想的教師。多年來,她渴望讀書,在這個知識寶庫里她得到了滿足。在瀏覽了"廣闊的世界"之後,她懂得了人應該怎樣生活。尤其讀了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使她對延安充滿了激情,認為那種生活是人生真正的生活,中國的希望在延安,延安是黑暗中的燈塔,心中的詩。
那時,去延安,須有不怕殺頭的膽量。李納說:"我認為,為了真理,任何困難都無所畏懼。屠格涅夫的散文詩《門檻》中那位女主人公給了我勇氣。我充滿著同舊生活決裂的精神,決定闖出雲南。但云南離延安實在太遙遠了。當時交通困難,我又從沒有出過遠門,再加上我有婚約的束縛,萬一被發現,他們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將我抓縛回來。我姨父說服母親,她心軟了,決定讓我走,並向我提供路費及一切需要的方便……"於是,在1940年春天的一個早晨,她離開了四季如春的昆明,奔向革命聖地延安。汽車在大路上跑,兩旁的加利樹向後面飛,她激動地站起來,但心裡沒有離情別緒,只有幸福!她微笑著,眼裡充滿了淚水,她覺得自己是一隻飛出樊籠的自由鳥!
延安,像陝北高原健壯的母親,張開雙臂,擁抱一位熱烈地愛著她的青年!
李納到了延安,被分配到培養婦女幹部的中國女子大學學習。那裡的生活緊張而艱苦,一切強調集體。她們穿布軍裝,同睡一鋪大炕,坐在露天底下上課,集體學習《新民主主義論》,討論為什麼到達社會主義必須分兩步走……
李納是抱著一種浪漫的幻想投奔革命的。但很快,她發現這個革命集體里一部分規定死死地限制了她的自由。同學們找她談心,鼓勵她進步,熱情地幫助她克服那些不切實際的幻想。她,慢慢地,慢慢地,習慣了,進步了……
延安,那是個革命家庭,組織上很注意大家特長的發揮。她和幾個愛好文學的同學被送到魯迅藝術學院文學系學習。她說:"那時是我求知慾最強的時期。我很喜歡這個環境。這兒學術空氣很濃,讀書成為共同的需要。魯藝圖書館藏有許多世界文學名著,我貪婪地讀了俄羅斯作家從普希金到高爾基的重要作品、差不多讀完了屠格涅夫作品的全部翻譯本,我覺得他的作品像露水一樣晶瑩。這些作品有的是手抄本,放在半山坡的資料室。每天早上,草草吃完小米稀飯便往資料室奔去,資料室還上著鎖,門口已經排了長隊,等管理人員一開門,大家一擁而上,以便搶到一本好書……"在光線暗淡的資料室里,大家如饑似渴地讀著;泥做的凳子佔滿了,就站在牆角閱讀。陝北的冬天,異常寒冷,實在伸不出手,就將磚頭燒燙,塞在棉被裡,蓋著半截身子讀書。李納在艱苦的條件下學習著,但這樣的日子不長,幾個月後,延安整風開始,一切課程停下來,圖書館和資料室封了門,讀古典文學名著成為被批判的行為。每天召開批判會,寫檢查、寫自傳,這樣持續了幾年,直到1943年底才告結束。魯藝辦學方向和辦法被批判為"關門提高"。音樂系和戲劇系合併,變為秧歌隊,文學系實際上已不存在,有的去三邊,有的去隴東,都改了行。魯藝變成了延安大學的一個組成部分,下屬工業合作社和農業合作社,一部分學生參加工會和農會,專門紡線、種莊稼。李納被分配到延安中學教語文。她是帶著革命虔誠的感情去從事教育工作的。當時,年輕的李納,思想單純,腦子裡沒有多少私心雜念,只要對革命有利的事,她就去做;她覺得,為革命培養新一代是一項神聖的任務,甚至決定要把自己的一生都貢獻給孩子。當時,她每周六小時語文課,除了備課,批改作文,就是管理學生的生活和思想。李納回憶說:"這些孩子都很聰明、活潑,多是經歷過不少苦難才輾轉來到延安的有名的烈士的遺孤和幹部子女,也有參加過長征的連級幹部,我和他們結成難忘的夥伴,我教他們,但也從他們那裡受到教育。後來,他們大多都曾在蘇聯學習技術,成為中國後來許多單位或企業里的技術骨幹,有的當了大領導。如果說,我也有點安慰的話,每每想起他們,便是我的最大安慰……"在延安中學,她一直工作到抗日戰爭結束,度過了一生中甚為難忘的日日夜夜。
1945年8月15日那天深夜,大家才得到日本投降的消息。不用召喚,人群從各個山溝和窯洞里湧來,毫不吝惜地撕下棉襖,扯出棉花,蘸了油,點上火把,匯成光明的河流一起涌到新市場、橋兒溝的街上。賣果子的叫著:"吃果子,吃果子,不要錢啦!"狂歡的人群中有的吼著:"回老家啦!回老家啦!"火把照亮了延安的山山水水,直到東方破曉,遊行才算結束。她有一位同學高度近視,一刻也不能離開眼鏡,但回到窯洞才發現,狂熱的遊行中,不知什麼時候失掉了鏡片而竟沒有察覺。
抗日戰爭的勝利給延安帶來了新的變化。"到新區去!""到最艱苦的地方去開闢工作!"就是當時的戰鬥口號。大批大批的幹部涌到前方,李納也懷著迎接新生活的豪情,在"八·一五"的後幾天便動身去東北。
李納不是東北人,但她和東北人一樣,那首著名的流亡歌曲《松花江上》一直響在她心裡。
東北的十月是美麗的,雖然那裡處處有侵略者鐵蹄蹂躪的傷痕。
經過革命生活鍛煉的李納,胸懷廣闊了,感情濃烈了。東北山水的粗獷美和雲南那種四季如春的細膩美,在她心裡織成一幅遼闊、壯麗的畫卷,這就是偉大的祖國!
到了東北,她分配到《東北日報》當副刊編輯,一同工作的還有作家陸地,領導是嚴文井。那時,她在嚴文井和陸地的鼓勵下,開始到鐵路工人和市民中採訪,也採訪關於東北抗日聯軍的戰鬥生活。楊靖宇將軍的事迹和他的壯烈犧牲使她無比感動,於是寫了幾篇關於抗聯的散文,發表在《東北日報》副刊上,這是她創作生活的最初嘗試。1946年,國民黨軍隊在美國的支持下,開始向各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當時,他們住在佳木斯,力量弱,加上土匪的搔擾、破壞,解放區很不鞏固。中共中央發出"鞏固東北根據地"的指示后,東北局由各機關抽調一萬二千名幹部,下鄉搞土改。李納被分配在哈爾濱近郊,了解了農民的苦難,把她所目睹的農民鬥爭惡霸地主、分配勝利果實,送子參軍等令人激動的場面,用散文、報告丈學等形式寫出來,發表在《東北日報》和《東北畫報》上。
1948年,東北召開了文藝工作會議,提出應該有反映工人生活的作品產生。當時東北局宣傳部長凱豐更具體地提出:好作品應該用兩把尺子來量,一是群眾喜歡,二是幹部喜歡。這些話,對李納產生了影響,她認為,這就是普及與提高的統一,就是趙樹理的《李有才板話》和《小二黑結婚》那樣的作品。於是,她以記者的身分到東北最邊遠的雞西煤礦採訪,隨身帶了趙樹理的作品,還有菡子的《糾紛》,力圖從這些作家的作品中汲取營養,寫出群眾喜歡的作品。
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的雞西煤礦,設備落後,天天有大小事故發生,他們只要煤,不要人,不管中國工人的死活。李納當時在一所專門為提高礦工階級覺悟而辦的礦工學校里住了兩個月,遇到過兩次訴苦課。她回憶說:"每次訴苦,有的捶胸頓足,有的放聲痛哭。訴完苦一兩天內,工人飲食減少,飯總是剩下大半桶。有一天,我聽說煤礦"冒頂",即刻趕去,才到礦口,便看見從礦內抬出幾個燒焦的屍體。啊,多麼讓人心碎!我忍不住背過身去,痛哭失聲!這些為了給別人光明而自己在黑暗中生活的人,使我終生感激!直到現在,幾十年過去了,只要看到煤炭,仍然憶起那燒焦的身體。煤,是用生命換來的!"
礦工最受壓迫,苦大仇深。在礦山解放后,礦工們拿起日本殺他們用的刀槍,紛紛參加了解放軍,礦工少了,但人民要煤,解放軍要煤,於是補充新工人,改造新工人,便成了重要任務。李納根據礦山生活的直接觀察和一些間接材料,創作了第一個短篇小說《煤》(1948年,《東北日報》)。這篇優秀小說就是寫哈爾濱一個有名的小偷黃殿文。外號叫"無人管"。他蹲過好幾次監獄,但他毫不在意,他說:"監獄就是我的家,長久不來還想它呢!"他行竊的人生哲學是:"皮襖誰穿誰暖和;吃飯誰吃誰飽。"這名小偷被判刑后,送到礦山勞動改造,經過工會主席和群眾的反覆耐心的教育和幫助,終使好吃懶做的小偷成為新人——工人階級的一員,認識了煤的價值:"咱們現在吃煤、穿煤,國家用的是煤,那一家離得了煤?煤真是寶啊!"這也證明了"能使廢鐵化成鋼"的真理。當時這篇不可多得的描寫工人生活的作品發表后,好像一朵迎春的奇葩,引起了文壇的注意,總工會負責人李立三打電話給她,表示祝賀,並找人寫評論文章,作家舒群給予鼓勵和關注。這篇小說被香港的文學刊物《小說》轉載后,著名作家葉聖陶和端木蕻良都寫了評介文章,肯定了她在人物刻畫和群眾語言的應用上所取得的成功。美國的雜誌《群眾與主流》、蘇聯及東歐國家的雜誌也都譯載了《煤》。解放后,這篇小說一直被全國各家選本所選用。以後,她相繼發表了表現東北人民在艱苦的歲月里忘我支援東北抗日聯軍的短篇小說《父親》和《不願做奴隸的人》及以工人生活為題材的《出路》和《姜師傅》,這五篇小說結集為《煤》,列入"收穫文藝"叢書,於1951年由工人出版社出版。這幾篇小說都是反映重大社會主題的,語言樸實,流利敘事、對話平實自然,筆墨乾淨,生活氣息極濃,顯示了李納的創作才華和藝術風格。
解放后,李納到北京,在中央文學研究所(文學講習所前身)學習。她的同學多是經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洗禮,並寫過一些文章的人,後來多是中國文壇的中堅。在戰火紛飛的歲月里,他們沒有機會讀書,迫切要求讀些中外文學名著來豐富自己。可惜兩年的時間有一年多是在"運動"中度過的,真正的讀書時間不到半年。畢業后,她被分到中國作家協會當駐會作家。1953年,到紗廠深入生活,擔任車間黨支部書記,做人的靈魂的工作,使她看到"女人在怎樣地改造著世界,也在吃力地扔掉舊社會加在自己身上的沉重的負擔"。在紗廠一年多,她默默地生活著,觀察著,體味著,逐漸熟悉了社會這一角世界的人和事,以女工生活為題材,寫了些散文和小說。
1958年,反右鬥爭之後,"大躍進"開始了。這時,中國作協作家支部解散,駐會作家下放到各省市,她到了安徽,在宣城雙橋農業合作社落戶,並擔任支部書記。這一年,是多事的一年,起初澇,後來旱。夏天,為了抗旱,農民日夜車水,好不容易用辛勤的汗水換來了莊稼結籽,待到要開鐮收割,卻不能不扔下成熟的莊稼,違背意願地去煉鐵、修馬路,大搞"三天車馬化"、放"衛星"、報喜。浮誇風吹暈了領導的思想,他們干盡了令人痛心的蠢事,莊稼爛在田裡,金燦燦的稻穀長了"白鬍子"。李納說:"看著這些,真叫人心疼得落淚!但農民的勇敢、勤勞、善良等高貴品質,追求美好生活的願望,卻深深感動了我。這時期,我寫了歌頌人民和大自然鬥爭的小說,描寫了他們的善良和犧牲精神。"
1963年,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了她的第二個短篇小說集《明凈的水》,收入她發表過的十二個短篇,除幾篇外,大部分寫於1958年和1959年。那時期,她和農民一起生活和勞動。李納在這個集子的《後記》中說:"他們的淳樸、堅忍不拔、為公忘私的精神給我終生難忘的教育!我總是懷著崇敬的激動的感情來寫他們。"這些作品,從不同角度描寫了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有的寫普通人在新社會裡的成長,有的寫受壓迫的婦女和少數民族中受剝削的奴隸。《撒尼大爹》通過一個孩子的眼睛寫出了撒尼大爹深沉的階級友愛和仇恨。《婚禮》通過一個可歌可泣的故事,寫出一對青年男女為革命的自我犧牲的精神。《姑母》主要描寫村婦對惡霸地主的反抗情緒,寫得真切感人,邊遠地區的風習和傳說,描寫得委婉有致,極富地方色彩。
每個作家的作品,都有自己的風格,如同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個性。李納在短篇小說集《煤》中,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藝術風格,而到《明凈的水》,其風格則臻於成熟。文學評論家黃秋耘說,李納的短篇小說集《明凈的水》,"文如其人,書如其名,她的藝術風格真有點像《二十四詩品》中所說的"娟娟群松,下有漪流,……如月之曙,如氣之秋",使人讀起來有明快清新之感;而精緻的描繪和委婉的筆致,亦足以顯示女性作者的特長。"
李納的不少小說,寫得乾淨利落,精細而不繁冗,明麗而不雕琢。像《撒尼大爹》《明凈的水》《兒子》各篇,無論敘事、對話,還是寫景、抒情,都顯得晶瑩剔透,堪稱上品。李納在她的作品中,既能給讀者以清新,明凈,細膩的美感,又能抒寫火熱的生活,闡發嚴峻的主題,並把二者熔為一爐,這就是李納的小說所能達到的藝術境界。
1963年和1965年,她在離別多年的家鄉深入生活,到過好幾個兄弟民族地區,開闊了眼界,豐富了生活。從雲南回來,她打算以雲南生活為背景,寫一部小說。結果,小說還沒有寫出來,十年動亂便開始了,她的一部用心血鑄成的未完成的書稿在抄家時被抄去,至今下落不明。那個瘋狂時期,一切都使人絕望,她一怒之下,索性焚毀了所有的手稿和多年搜集的素材,並決定"洗手"不再寫作。
"文化大革命"中,安徽省文聯副主席陳登科被江青點名為國民黨"特務",於是李納等二十六人都成了"特務"集團的黑班底,安徽省文藝界的重點罪犯,通通打入牛棚。而李納比其他作家的"罪行"更重,因為她的丈夫——詩人、畫家朱丹,與作家方紀的友誼頗深,因此和馮牧等人同被誣為文藝黑線回潮的代表人物。被"紅衛兵"關押和拷打的朱丹,必然要株連李納,再加上有人向當權者告發她"攻擊中央首長江青",致使她成為集中營中的重犯。這些"罪犯"由合肥文藝界聯絡站管理,並於1968年押到合肥農具學校。李納回憶說:"我沒有蹲過法西斯的集中營,我想大約不會比我門的處境更慘吧。我們幾十個人同睡一個地鋪,門頭高懸"鬼棚"的牌子,門上寫著"罪犯"的姓名。早上起來第一件事就是"請罪",旁邊有人拿著"水火棍"監督。稍有不慎,就挨懲罰——胸前掛上恥辱牌,讓你抬土、掃地;無論走到哪裡,任何人想幹什麼就幹什麼,不知挨了多少石頭。睡眠時,一百瓦的燈泡懸在頭上,使人無法休息。一人"犯罪",所有的人同被處罰。"李納還講到一個靈魂極其殘忍的高幹的兒子,是一個文工團員,他經常提著皮帶任意捉弄"犯人",並以此為樂。李納是他最不順眼的,一舉一動都會成為他侮辱的材料。背誦"老三篇",他問李納"老三篇"里有幾個"但是";《愚公移山》中,為什麼有的用"山",有的用"大山"。有時,他糾集一幫嘴裡叼著煙捲的人,要李納跑步、不停地向後轉,而他們在一旁縱聲大笑。"遇到這情景,我只想哭,哭這些可憐的愚昧無知的青年,哭我們的國家、我們的黨!"說這些話時,李納的眼睛里還閃著淚光,這是何等沉痛的感慨!
當李納差不多感到絕望的時候,光明的翅膀駕著她在黑暗中起飛,她遇到了人類中美好的靈魂,心,得到了安慰。
"我永遠不能忘記,"李納說,"當那個文工團員侮辱我時,一個年輕的會計便挺身而出保護我;當我被斗后,回到爬滿蟑螂、潮濕、陰暗的小屋,我睡在床上,不吃不喝,又是這位會計,悄悄端來一碗飯,還有醬肉和豬肝。她溫情脈脈地站在我的床前,像是乞求,我無法拒絕她的好意……"李納還講到一個同她只有過幾次談話的女同志,"常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去看她,給她勇氣、信心和溫情。一天晚上,她要去我在北京的住址,說打算到北京代我看看母親。因為同情我,還和丈夫吵了架。最後她對丈夫說:"我決不相信李納是特務,如果是,一人做事一人當,也決不連累你!"當時我感動得不能自己,在那樣渾沌的世界,沒想到還有這樣的好人!"
1968年,毒火正在中國的大地往縱深處燃燒;那年的嚴冬,李納被押解到舒城縣的小山溝里。她的任務是大雪天,到飄著冰凌的河裡為全機關洗菜。她的手,一觸到透心澈骨的冰水,就不停地顫抖。有時上山挑石頭,還要在田頭地埂上挨斗。不過農民並不買工宣隊的帳,房東從不說李納的不是,凈是好話,遇到鬥爭她時,房東的女兒——雖然她是青年隊長——從不去參加。
疾風知勁草!這句古詩,是人生哲理的真諦。十年動亂,對一般人來說,尤其對那些受了衝擊、打擊、迫害的人來說,生活使他們認識了許多人,美和丑,在疾風、急流中,變得徑渭如此分明,李納對此感觸尤深。
一天早上,李納挑著石頭,在狹窄的田埂上邁著沉重的步子,由於她深度近視,更增加了行走的困難。這時,迎面走來一個挑石頭的人。此人以前曾再三表示自己是她的朋友,如何關心她的生活和創作,李納似乎也從不懷疑他的"友情"。在田埂上,李納為了給他躲路,往旁邊一閃,不料腳一軟,人和石頭一起摔到田裡。這位與她共著命運的"朋友",僅僅看她一眼,便挑著石頭過去,連停一下都不敢。而這時,另一位不熟悉的"朋友"卻慌忙丟下竹筐,把她從田裡拉了起來,李納說:"我發現,他眼裡湧出了淚水。那一剎那,我突然加深了對人的認識……"
在那些黑暗的日子裡,李納每晚都要到工宣隊的隊部"學習"。她的住地離隊部很遠,路兩面是河,夜裡常有野獸出沒。一到夜裡,近視的李納,什麼也看不見,山路坡陡路滑,積雪又深,這使她寸步難行。一位好心的工宣隊員可能出於同情之心,所以提議每晚派兩名"棚友"送她回住地。這份差事雖苦,但在"棚友"們看來卻是美差,所以爭著送她。李納回憶那段生活時說:"我走在雪地里,沒有"董超""薛霸"之流的押解,我們可以自由地呼吸,自由地仰望夜空的群星,自由地開幾句玩笑,自由地背誦唐人詩句……"在沒有真理和正義的時代,人生旅途中那一小段坎坷的山路,竟成了他們"囚犯"生活中的快樂之旅。
當嚴寒殘酷地襲擊人間的時候,偌大的世界,總有春溫的存在,總有好人用光明之心去溫暖被冬天囚禁的人。在安徽農村,李納有許多農民朋友。宣城縣一位農村婦女遠道來看她,一見到李納,抱住她便痛哭起來;那感天動地的哭聲使李納鼻子一酸,也淚如雨下。後來,李納說:"人類,除了少數惡棍,具有更美好靈魂的人,總是多數。人民是偉大的,可愛的,如果我寫作,一定要寫普通人身上的美好素質,歌頌他們大公無私、克己忘我及富於同情心的精神。我覺得,將他們可愛的靈魂揭示給今人和後代,是我一輩子的任務。"
1976年,10月,是黑夜的結束,黎明的開始。這年的回月,痛苦使她欲生不能;而"四人幫"的覆滅,使她的心經歷了比抗戰勝利時那種喜悅還大的喜悅。擱筆多年的李納又拿起筆來,1978年發表了《涓涓流水》,她的生命像流水一樣又歡樂地在祖國的大地上奔騰起來。這期間,她修改、完成了寫於1963年的長篇小說《刺繡者的花》(1979年連載於《清明》雜誌,1981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出版后獲1977-1984年人民文學長篇小說獎;同菡子合作,創作了電影文學劇本《江南一葉》(發表於1979年《鐘山》第一期),還寫了一些短篇小說。1982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納小說選》。
《刺繡者的花》是李納創作生涯中極為重要的作品。它是反映本世紀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發生在雲南一偏僻小縣——航遠縣的故事。小說通過女主人公繡花工葉五巧的成長,展示了這個小縣急劇的歷史變化。
在創作的道路上,李納整整跋涉了將近五十年。她的作品不算多,已經出版的只有兩個短篇小說集,一個選集,一部長篇小說,一部電影文學劇本(與人合作)及一些未輯集的短篇小說和散文。1979年,在全國第四次文代會上,她對我說:"我很難過,我的作品太少……"這句由一分謙虛、一分真情、一分自勉組成的話,她對我講過多次。但每次都使我痛苦地思索很多:社會應該給作家創造條件,讓他們寫出無愧於時代的作品……然而她的生命無故地被減去了十歲。
她在《李納小說選·自序》中也說:"重新翻閱我的短篇小說,我真是惶恐不安,好像一個母親,看到久別的兒女竟是那麼孱弱,那麼醜陋,心裡有說不出的難過。說真話,自從我發表第一篇小說起,……我多次感到我走的是一條力不勝任的路。走這條路,不但需要刻苦,還需要才能。我後悔挑選錯了,應該及早回頭。可是愛上這一行的都知道,既然愛上了,就永遠也放不下這份感情。"她還把作家們比做去趕集的人,說"和我一同起步的早已跑到前面去了;比我後起步的也已趕到前面去了。我懷著喜悅和感激目送他們。"
一個作家,當他成名之後,很需要這份謙虛,永不固步自封,時時想著無止境地貢獻自己的精神。李納正是懷著一顆藝術家的良心去進行創作的。她是在用"心"寫自己的人物,"描寫普通人的生活,揭示他們的精神美"的。"作家應該尋找人們心靈的珍珠",李納正是這樣一位踏踏實實、兢兢業業的尋找者。當這篇文章結束時,我又想起了李季的話:"李納是有才華的,但才華的發展並不順利。你看這場"革命"(指"文化大革命"),幾乎把她扼殺。現在好了,你瞧吧,她一定會寫出佳作,以饗讀者……"
1984年12月,第四次中國作家代表大會,她被選為第四屆理事會理事,那時她是作家出版社的編審。離休后在家讀書、寫作,相繼寫出了紀實長篇《朱丹傳》及一些散文。1995年4月11日她在給我的信里說:"自朱丹去世,接著相依為命的母親又撒手離我而去,我的生活中一下少了兩根支柱,在情感上簡直有點難以承受。但,人總要活下去,而且既然活著,就要活得像個樣子,所以也努力拿筆,寫點什麼。這倒不是為了出版,而是為了安慰自己。"
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著名彝族女作家,原作家出版社編審李納同志,於2019年4月2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9歲。
| 作品名稱 | |||
| 《煤》 | 《撒尼大爹》 | 《明凈的水》 | 《李納小說選》 |
出版圖書
| 作品名稱 | 作者名稱 | 作品時間 | 出版社 |
| 刺繡者的花 | 李納 | 1981年 | 人民文學出版社 |
| 李納小說選 | 李納 |
| 獲獎時間 | 獲獎作品 | 獎項名稱 |
| 1986年 | 《刺繡者的花》 | 人民文學首屆長篇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