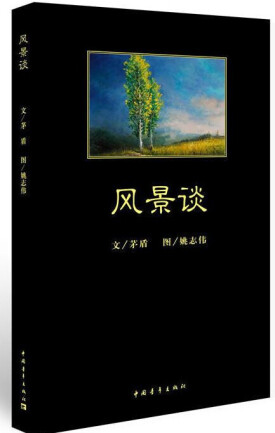風景談
風景談
.《風景談》就是談風景,這裡的“風景”,不僅包括自然景觀,而且包括人們的活動。表面上談的是自然“風景”,實際上是在寫主宰“風景”的人。
《風景談》,作者茅盾(1896年7月4日-1981年3月27日)
文章主要描繪了以下六個場景
第一個場面:沙漠駝鈴
第二個場面:高原晚歸
第三個場面:延河夕照
第四個場面:石洞雨景
第五個場面:桃林小憩
第六個場面:北國晨號
《風景談》是茅盾抒情散文的代表作之一,與稍後寫的被譽為姐妹篇的《白楊禮讚》成為現代散文發展史上有口皆碑的名篇,也是被選入中學或大學語文中的典範篇章。然而,對《風景談》主題思想的分析,幾十年來一直停留在:文章通過描繪六幅內容不同而相互聯繫的風景畫,熱情謳歌了延安軍民的火熱的戰鬥生活,讚美了延安軍民的崇高精神面貌這一闡釋上。這種強調革命性、政治性的主題思想分析,不能說是毫無道理,但至少可以說是有些概念化、表面化,或者說是較為籠統的。它不僅沒有接觸到《風景談》內涵的主旨,而且對讀者尤其是學生欣賞這篇散文會產生一種錯誤的誘導,由此,對《風景談》的主題就有進一步探討之必要。
筆者以為,《風景談》表現的不僅是謳歌延安軍民的戰鬥生活和崇高精神,更重要的是表達了茅盾對根據地這種和諧生活的熱愛、嚮往和追求。失去了這一前提,什麼“謳歌”“讚美”就會成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就會變成缺乏感染力的概念化的東西。因此,《風景談》的主題思想應該這樣概括:文章通過描繪六幅內容不同而相互聯繫的風景畫,深深地表達了作者對解放區和諧生活的熱愛、嚮往和追求,謳歌了延安軍民為創造和諧生活表現出的崇高精神。
文章主題的表現,一般離不開一定的寫作背景和作者世界觀的制約,想辦法弄清文章是作者在怎樣的時代背景之下,怎樣的社會環境之中,處在怎樣的心境之時寫出來的,是我們探索散文主題的重要途徑。《風景談》一文寫於一九四〇年十二月,此時的茅盾已離開延安置身於國統區重慶的白色恐怖之中,這裡沒有創作的言論自由,要謳歌延安抗日根據地軍民更是不可能的。那麼,是什麼驅動作者不畏險惡環境,另闢蹊徑,採用含蓄的藝術表現手法,抒發了對根據地軍民和諧生活的讚美之情呢?這就是茅盾在經歷了十多年的動蕩不安的生活后,對延安軍民和諧生活的熱愛、嚮往和追求使然。
有人說,與二三十年代的那些抒情散文相比,《風景談》及其姐妹篇《白楊禮讚》,是茅盾抒情散文創作以及全部文學創作的新起點。這種說法是有道理的。因為從一九四〇年五月抵達延安,到同年十月離開延安,這五個月的新生活的經歷,使茅盾有機會親眼看到了新的社會、新的人民、新的精神面貌,親身感受到這種新的和諧生活,尤其是使他清楚地認識到決定這一切的是中國共產黨及其建立的新的社會制度。這正是他十多年來在動蕩不安的生活中所苦苦追求的,因此,他不能不滿懷激情地去謳歌它、讚美它。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后,茅盾成了蔣介石政府的通緝犯,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繫,開始了長時間漂泊動蕩的不安生活。先是蟄居上海景雲里,足不出戶,整整十個月,對外則說:“雁冰去日本了。”當時他對於革命失敗后的形勢感到迷茫,認為“在經歷了如此激蕩的生活之後,我需要停下來獨自思考一番”①。為了維持生活,不得已賣文為生。這期間茅盾主要創作長篇小說《蝕》三部曲,抒情散文雖然只寫了一篇《嚴霜下的夢》,卻也表述了他對革命遭遇的悲痛而激憤的感情。文章採用象徵的手法,憑藉現實的折光——幾個怪誕的夢構成象徵形象,含蓄地抒發了作者對革命高潮的留戀,對反革命政變的鞭撻,對“左”傾盲動的唾棄,對光明前景的憧憬與嚮往。
第二年七月初,他亡命日本,陷入了苦悶、彷徨、焦灼、憤怒的境地,繼續運用象徵手法寫作抒情散文。《霧》《虹》《賣豆腐的哨子》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文章的基調固然過於低沉,但我們仍然能夠聽到作者渴望光明和戰鬥的心聲,看到作者並沒有因革命落入低潮而沉淪。
一九三〇年四月,茅盾從日本回到上海,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並擔任領導工作。這期間抒情散文的象徵性描寫與前期相比,表現出既能準確地反映現實,又能充分展示前景,一掃苦悶、消極的基調,代之以信心十足的追求和開朗樂觀的情懷。代表作有《雷雨前》《黃昏》《沙灘上的腳跡》等。
及至“八·一三”上海戰爭爆發后,茅盾“帶著一顆沉重的心”,離開上海,像一葉失去重心的小舟,浮蕩顛簸,浪跡於長沙、漢口和香港。后應杜重遠之請,茅盾全家離開香港前往新疆,去新疆學院任教。本想在新疆過個安穩的生活,沒想到作為新疆各族文化協會聯合會主席的茅盾,仍然過著提心弔膽、擔驚受怕的動蕩生活,並且差點葬身異域。這一時期,他幾乎沒有寫抒情散文。
一九四〇年五月,茅盾離開新疆來到延安,就像是來到了闊別多年的家鄉一樣。他呼吸著清新的革命氣息,目睹了根據地蓬勃發展的景象,很快融入到延安的新生活中,並激起了對根據地新生活的熱愛。他原想在延安住下去,為黨和人民做一點實實在在的事情,因為延安的新生活正是他多年動蕩奔波所追求的和諧生活。然而,組織決定讓他去重慶國統區開展工作,那裡更需要他。延安之行雖然短暫,但在茅盾的人生歷程、寫作歷程中卻產生了轉折點的作用。這在他後來抒情散文的象徵性描寫中可以得到驗證。如《風景談》《白楊禮讚》《開荒》《霧中偶記》等。在這裡,作者把象徵性描寫和哲理的思辨熔於一爐,表現出一種樂觀向上、充滿信心的思想情感。如果說,在這以前茅盾在動蕩生活中追求的和諧生活還是比較模糊的,理想化的,那麼,此時已是具體明確的,並對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軍民取得最終勝利充滿信心;如果說,在這以前寫的抒情散文還含有悲觀、消極的情感,那麼此後的抒情散文所抒發的則是一種樂觀向上、革命必勝的積極情感。儘管此後的工作生活從重慶到香港,從香港到桂林,從桂林到重慶,從重慶再到香港,輾轉反覆,動蕩不安,儘管他在後來的詩文中常常表現出對北方抗日根據地和諧生活的嚮往:“落落人間啼笑寂,側身北望思悠悠。”“桓桓彼多士,引領向北國。”②但這都是為了一個明確的目標——讓全國人民都過上和諧的生活而努力。
《風景談》與《白楊禮讚》雖然同是讚美延安根據地人民精神風貌的,但相比較,《風景談》則更富於生活的情趣和新生活中所閃出的詩情畫意。文章從《塞上風雲》影片引起的聯想開篇,藉助豐富的藝術聯想,縱橫馳騁,給我們描繪了六幅和諧優美、寓意深邃的風景畫。
第一幅畫沙漠駝鈴,寫的是猩猩峽外沙漠的“風景”。作者先從沙漠的荒涼,“茫茫一片”,沒有一個“坎兒井”,“純然一色”,“寂靜”等方面,將大自然最單調最平板的一面展現在讀者眼前,這是“風景”的背景,是靜景。接著採用由靜而動、由遠而近的筆法,描繪了人類駕馭著“那些昂然高步的駱駝,排成整齊的方陣,安詳然而堅定地”行進,“而且大小丁當的諧和的合奏充滿了你耳管”的動景。作者在這空曠荒涼、四顧蒼茫的畫幕上,在用“更多的黑點成為線,成為隊”進行配色的同時,特別注意描繪了“領隊駝所掌的那一桿長方形猩紅大旗”。原來單調平板的畫面,由於有了這“一桿長方形猩紅大旗”,而變得富有生機、充滿活力。紅色是一種暖色,它能表達出作者內在的堅定和有力的強度,它能讓人感受到一種鮮活搖曳的生命力。作者借這一“猩紅大旗”含蓄地表達了對共產黨領導根據地軍民取得最終勝利的熱烈、堅定而又嚴肅的情感,也使畫面充滿和諧與生機。在貧瘠單調的沙漠背景與安詳然而堅定行進的駝隊映襯中,在死寂荒漠與“猩紅大旗”色彩的調配上,畫面雖有邊塞詩中的蒼茫荒涼,卻沒有徵戍者的幽怨纏綿,相思憂傷,有的是“昂然高步”,“安詳然而堅定地”去創造新的社會、新的生活的鬥志和信心。
應該說“沙漠駝鈴”寫的還不是真正的根據地的風景,後面的五幅畫才真正寫出了富有根據地特色的和諧優美的風景。如第二幅畫高原晚歸,寫的是延安人種田晚歸的“風景”。這實際是一幅“剪影”,是一幅藍天明月下伴著粗朴歌聲出現的晚歸種田人的“剪影”。這幅“剪影”在高原夜景的襯托下顯得格外美麗。你看,在三五明月之夜,“在藍的天,黑的山,銀色的月光的背景上”,“遠看山頂的穀子叢密挺立,宛如人頭上的怒發”,可謂豐收在望。這時候,晚歸的種田人掮著犁,趕著牛,後面還跟著小孩,哼著粗朴的短歌,姍姍而歸。這可說是一幅優美的田園風俗畫。這樣的田園生活不僅是一般隱士所嚮往的,也是一般老百姓所追求的。然而,在這裡,作者的命意絕不同於“田園詩人”的感受,而在於讚美那些創造新生活的人,用自己的勤奮在禿頂的山上,造起層層梯田,種上“頎長而整齊”高稈植物,不只是為自己,也為他人創造一種和睦新生活的精神風貌,從而表達了作者對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創造和諧生活的嚮往之情。
第三幅畫延河夕照,寫的是魯藝學院師生參加生產勞動歸來的“風景”。對這一景色的描繪,作者十分講究色彩的搭配。我們看,畫面的主色調與前一幅畫相比顯得更為明亮,夕陽將“它的餘輝幻成了滿天的彩霞”,給整幅畫面塗上了一層暖色,烘染出詩一般美的意境。在滿天彩霞映照之下的是“干坼的黃土”,“雪白”的河水泡沫,還有那“金黃的小米飯,翠綠的油菜”,整個畫面呈現出一種明麗而又溫馨的情調。顯然,作者並非只是為寫自然而描繪自然之美,而是為突出人類的活動,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你看,人們勞動歸來的“爽朗的笑聲,落到水上,使得河水也似在笑”;“人們把沾著黃土的腳伸在水裡,任它沖刷,或者掬起水來,洗一把臉”。大自然是優美的,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更給人以美妙的幻想。從這明麗、溫馨的畫幕上,我們不僅看到了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還看到了人與人之間的和睦相處。我們從“生產”歸來者興奮的談話中可以聽到,“至少有七八種不同的方言。忽然間,他們又用同一的音調,唱起雄壯的歌曲來了。”我們從另一群人的勞動也可以看出,他們“已經將金黃的小米飯,翠綠的油菜,準備齊全”,以此來慰勞“生產”歸來的人們。在這裡,人們雖然來自四面八方,雖然各有一技之長,但人與人之間是平等相處的,只有分工的不同,沒有高低貴賤之別,大家只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就是為創造一個新社會,開創一種新生活——一種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和睦相處的和諧生活而努力。這當然也是作者所嚮往和追求,並為之不懈努力的。
對第二、三幅畫的處理,作者是從根據地人民以自己的勞動改造自然,創造新生活這一角度著手描繪,而第四、五幅畫則是以根據地青年努力學習,為創造美好未來的精神面貌為中心展開描繪。石洞雨景,寫的是雨天石洞中一對男女促膝而坐,認真學習的“風景”。如果說,前一幅畫是從大處著眼來描繪魯藝學院師生勞動歸來的歡樂和諧場面的,那麼這裡的石洞雨景則是從小處落筆來描畫根據地青年在雨天的石洞中互幫互學、和睦相處的生活圖景。一對青年男女被雨趕到了石洞,他們促膝而坐,“現在是攤開著一本札記簿,頭湊在一處,一同在看”。利用大自然恩賜的石洞,在躲雨間隙,爭分奪秒地學習,這不僅反映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和諧共處的重要,更表現出根據地青年不同於一般城市青年的崇高精神境界。原本這“沉悶的雨天,寂寞的荒山,原始的石洞”的暗淡背景,也因兩個“生命旺盛的人”,“清楚明白生活意義的人”而頓生光輝。桃林茶社,則是寫人們在桃林茶社休息的“風景”。與前一幅畫相比,前者寫雨中靜景,畫面幽靜,後者寫林中談話,畫面熱鬧;前者寫“點”,後者寫“面”。兩幅畫從不同角度反映了根據地青年和諧融洽的學習與休息。
如果說,在《白楊禮讚》中,作者還只是托物寄意,以白楊的形象來象徵革命的人民,在這裡,則以濃墨重彩,從正面勾勒出神采奕奕的抗日戰士形象。第六幅畫北國朝霞,寫沐浴著北國朝霞的抗日戰士的雄姿。作者是這樣來描寫戰士形象的:“朝霞籠住了左面的山,我看見山峰上的小號兵了。霞光射住他,只覺得他的額角異常發亮。”“離他不遠有一位荷槍的戰士,面向東方,嚴肅地站在那裡,猶如雕像一般。”在粉紅色的霞光中,顯現出嚴肅和剛毅。“晨風吹著喇叭的紅綢子,只這是動的,戰士槍尖的刺刀閃著寒光,在粉紅的霞色中,只這是剛性的。”對小號兵和哨兵形象的描繪,作者不僅注意動靜搭配,更注重色彩的調配。畫面以五月北國朝霞滿天的清晨為背景,粉色的霞光與喇叭的金黃色、綢子的大紅色、軍裝的土黃色及刺刀的寒光交融在一起;朦朧的與鮮艷的,冷色的與暖色的,柔性的與剛性的色彩的相互融合,構成了表現抗日戰士嚴肅、堅決、勇敢和高度警覺形象的畫面,從而表達了作者對抗日戰士保衛新社會、新生活的堅決、勇敢、高度警覺的讚美之情,對黨領導的根據地軍民和諧生活的熱愛嚮往之情。
概述
茅盾的作品,往往是以深厚豐滿見長的。同樣,他的散文表現的雖然是某個生活斷面,某種生活景象,但卻是取精用宏,他會調動整個的生活積累,來充實它,使之更加集中完滿。《風景談》從表面看,只是從不同角度描繪了六幅風格各異的風景畫,但仔細品味卻可以發現它們相互之間並不是孤立的、散亂的,而是和諧統一的。
內容是緊密相連
首先,每一幅畫面的內容是緊密相連的。
因為文章的題目是“風景談”,所以作者描寫的每一幅畫都落筆於繪景,無論是寫沙漠還是寫溪流,寫朝霞還是寫夕照,寫晴天還是寫雨景,都是不離文章談的主要內容——風景。然而作者表面上寫自然風景,但其意並不“在於山水之間”,而在於突出主宰風景的人,風景中的人的活動。這些人的活動,看似隨意寫下的一鱗半爪的生活景象,卻莫不是經過作者精心選擇,閃出光澤的藝術表現。從沙漠中駕馭駝隊的人,到黃土高原上勤勞耕作晚歸的人;從具有“慣拿調色板的”,“拉著提琴的弓子伴奏著《生產曲》的”,“經常不離木刻刀的”,“洋洋洒洒下筆如有神的”,“調珠弄粉的”手的人,到手持喇叭的號兵,荷槍實彈、槍尖刺刀閃著寒光的哨兵;從雨天躲在石洞里學習的人,到天晴在桃林茶社休息的人。原本荒涼死寂的沙漠,因為有了人的活動,而頓生活力;原本沉悶,靜穆的石洞、桃林,因為有了人的活動,而頓放光彩;原本色彩明亮的朝霞和晚霞,因為有了“彌滿著生命力的人”的活動,而變得更加美妙無比。可見,六幅風景畫描寫的著眼點雖然不同,但相互之間在對人類與自然的和諧相處,人類相互之間的和諧相處,對人類偉大的讚美這一內容上,卻是和諧統一的。
議論是和諧一致
其次,每幅風景畫結尾的議論是和諧一致的。
有人因為《風景談》的六幅畫是用敘述的筆調記敘的,因而就把它當作敘事散文來進行分析;有人則因為每一幅畫的結尾都有幾句議論的句子,因而就把它當作議論散文進行分析,這種做法顯然有失偏頗。因為《風景談》是一篇熔敘述、寫景、議論、抒情於一爐的文情並茂的優美散文,任何單從某一表現手法進行的分析,都是不符合客觀實際的。更何況在對風景畫內容描述之後,引出幾句議論,這不僅是對前面描述內容的深化,更是一種水到渠成的點睛之筆。如第五幅畫描繪的是人們在桃林茶社休息的情景。原本貧乏、簡陋的桃林卻因人的活動而變得豐富熱鬧起來。在結尾處作者這樣說道:“人類的高貴精神的輻射,填補了自然界的貧乏,增添了景色。”這是作者從心靈深處發出來的,一種真正的、毫不做作的、富有美感的議論。前面的描敘與後面的議論的有機結合,是顯得那樣的和諧一致。
並且,每一幅畫結尾的議論相互之間也是密切聯繫的。如第一幅畫結尾“自然是偉大的,然而人類更偉大”的議論,確定了作者讚美的主基調,第二、三幅畫結尾的議論則是對前者“人類”內涵的進一步充實和豐富。如果說前者的人類還是比較籠統的、泛指的,那麼在這裡已經明確起來,它是特指那“充滿了崇高精神的人類”,它們才是“偉大中之尤其偉大者!”第四、五幅畫結尾的議論重在說明,人類既是“風景”的構成者,更是“風景”的主宰。是人類創造了第二自然。由於“人類的高貴精神的輻射填補了自然界的貧乏”,才使“風景”增添了奇妙的景色。這與前面“充滿了崇高精神的人類活動”相比,無疑使其內涵得到了進一步的充實。在最後一幅畫的結尾,作者將對人類偉大的讚美具體物化到兩名抗日戰士的具體形象上。“我看得呆了,我彷彿看見了民族的精神化身而為他們兩個”,這才是“真的風景,是偉大中之最偉大者”的議論,較之前面的議論,就顯得更為深刻了。這些議論乍看起來似乎差不多,都寫了自然與人的關係,但仔細玩味,就可感受到其議論的含義是逐步深化、和諧一致的。
結構布局也是和諧統一
再次,每一幅風景畫的結構布局也是和諧統一的。
與《白楊禮讚》相比,在結構布局上,《風景談》似乎不如前者那麼謹嚴凝練,完好集中,然而卻以跌宕多姿,揮灑自如見長。在這裡,作者充分發揮了散文寫作藝術自由活潑、無拘無束的特點,向讀者展示了多種“風景”的片斷:時而沙漠風光,時而高原夜色;時而晨光普照,時而晚霞滿天;時而剪影似的寫意的“大場面”,時而精工的“小鏡頭”。但又絕非事無巨細,物無輕重,撒得開,收得攏,看似散散落落,實則錯落有致。③作者不僅對那掌著一桿猩紅大旗的駝隊,對那荷鋤晚歸的種田人,對那親密無間的文藝工作者,對那石洞中促膝而坐的年輕男女,對那圍坐在桃林茶社的生機勃發的青年,對那如雕像一般挺立在山巔的高度警覺的戰士傾注了深情厚誼,而且對根據地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和諧相處的新生活表達了無限的熱愛和嚮往之情。六幅“風景畫”的寫法大致相同,先寫自然景觀,次寫人的活動,最後通過議論揭示“畫”旨。文章在結構布局上層層深入,步步推進,按照作者對人類與自然,人與人之間關係的認識逐一深化的順序,把六幅風景畫有機地組合在一起,使之顯得既舒展自如,又謹嚴有序,表現出整體和諧統一,完滿無缺,真正做到了“形散而神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