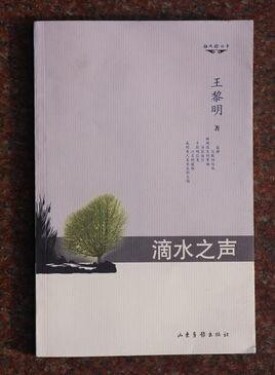滴水之聲
滴水之聲
《滴水之聲》是王黎明著作的。
王 黎 明 著

滴水之聲
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年10月出版
寂 靜
夜深人靜的時刻,沒有比滴水之聲更幽深、更觸動聽覺的了。滴水之聲!可能是你昨晚忘記了擰緊自來水管上的閥門,那使人心緒不寧的迴音,攪亂了你的睡眠;也可能是恍然入夢的一場小雨,淅淅瀝瀝敲打著窗欞……嘀嗒,嘀嗒,連續不斷的水滴,通過空氣滑動的聲音多麼奇妙,彷彿旋轉的風鈴。滴水之聲,讓我禁不住放下手中的筆,走出屋外,天空多麼幽靜啊,那些水珠般懸掛的星子,似乎隨時都可能滴落下來,像雨水那樣,落在我的頭上、手上和眼裡,而它們安靜的樣子,卻像在喃喃自語,在樹梢和屋脊之上,在飄渺的銀河兩岸,是一群不安分的,而又相互遙望的鳥兒的眼睛,閃閃眨動。一位遠在台島的詩人說,看,星子們聚集在屋頂汲水呢!
滴水之聲,讓我傾聽,如同置身於一眼深井之中,被一汪泉涌的心境湮沒,被沉思和回憶的細沙無聲地覆蓋,又被汨汨的水流衝散。遠處的燈火,近處的光線,以及視覺之內的各種事物,都局限在相同的方向。相對於白晝里浮光掠影的景象,寂靜,猶如鏡中的水銀,它是生活的秘密,深藏於事物的內部。一個人在深夜裡獨自沉思,說明它與這個世界建立了不同一般的聯繫。我想起梭羅的一句話:“當你窺望井底的時候,你發現大陸並不是連綿的大陸,而是隔絕的孤島。”
庭院里那棵秋天的樹,再也遮掩不住自己濃重的陰影,它的軀幹,它的落葉,它的根系,密布在我的周圍,在它的身邊,我聽到簌簌顫動的風聲,和環流全身的水聲,我在喘息中暢飲風中的涼意。“為了接近一種寂靜,我不得不把鍾也給停住(福斯特)”,其實我的腳步已經放得很慢,甚至不敢輕易挪動,我的脈動也是這樣放慢了速度,幾乎每一下跳動,都讓我感到強烈、清晰,聲音比平常也擴大幾倍,比我聽見的滴水之聲,還要清脆、響亮。彷彿內心深處,安裝了傳播聲音的放大器。讓我聽見自己的心跳和大地的脈搏相互回應。我聽見誰在說,人類的時間是用心跳計算的。
秋 水
當山岡上空的“藍色”,被帶著金屬聲的秋風吹得透亮,我看見了那些磨擦翅膀的昆蟲:蟋蟀、蟈蟈和草叢中起飛的紅腿螞蚱;想起中秋之夜被母親擦凈的各種器皿:瓷碗,茶杯,酒壺。菊花開了,葡萄熟了,木工房裡做好了尚未染漆的新木傢具。泥土中散發著刨花和木屑的香味。剛出爐的陶罐、磚瓦,整齊地擺放在泥土之上。父親的咳漱聲,使遠處的曠野變得悠遠而開闊。大地和山巒的輪廓,呈現靜態,一幅素描,勾勒出突兀的局部、濃重的陰影。
這陰影覆蓋了我身後一座龐大的水庫、一座電站,縱橫的道路,和密布的電網……這陰影,省略了我認識世界的過程,把生命和自然萬物融為一體。讓我的心境平和,拂去雲煙和風塵,讓我只看見光和影,人和事,夢和真。讓我看見樸素和根本。讓我看見了大地和天空相連的部分,看見了想象力不能抵達的時空。在那裡,只有翅膀可以佔據,只有心靈才能俯瞰,只有靈魂得以遨遊。
午後的光亮,像一泓越來越深的秋水。光線,漸漸地薄弱下來。視線的盡頭縮小成一個聚焦,如果沒有日影和樹陰的移動,它的亮度將繼續縮小,直到接近消失。白晝里所的事物都在縮小,包括巨大的岩石和微小的蟲卵。黑暗中秘密糾集的飛蟲,在不斷地滋生、擴大,悄無聲息。由於樹枝的遮掩,使我看見了光線中的塵埃,飛絮中的纖維,以及隱藏在枯枝敗葉下面的幽靈。它們也在陰影的幫助下,悄悄地顯形,恢復了面目,白天里看不見的星星,突然間掛滿了夜空。
那秋水映照的天空,曾經是一座綴滿甘露的石榴園,它神秘的果實,為幽靜的山谷帶來了古老的光輝,彷彿銷聲匿跡的泉流粲然重現,讓一群迷途的羔羊找到了回家的路。
落日,像一個挑著水桶下山的人,我想喊住它!然而,我卻感到兩腿生根,不能移動半步。我聽見山那面有人喊,喊什麼,可沒有聽清。深黯的天空像一池平靜的湖水。
落 葉
誰見過飛翔的大樹,誰見過行走的森林?山川、河流、大海都不能阻擋它們生命的根脈。秋風吹亂了大地的羽毛。一棵迎風挺立的大樹佔據了整個荒涼的曠野,萬物凋零,天高雲遠。一片落葉慷慨地走完了它一生的路程。
很少有人留意樹上的葉子何時飄落。當陽光透過林隙,照射在林蔭大道上,金燦燦的落葉,像美麗的裝飾品,鋪展在腳下,層層疊疊不斷延伸,展開。那些踩著落葉走來的人,他們步履輕快,悄然離去。遙遠的背影,猶如一幅油畫:深秋的北方,夢幻般的楊樹林,微風奏起抒情而恬靜的音樂。此刻,那些仍然掛在林梢、留連枝頭的葉子,就像一年之中剩下的為數不多的日子。只有掃落葉的人知道,它們總是落不盡、掃不完的。即使到了第二年春天,當樹上的新葉長出來的時候,仍有零星的葉片,像孤兒一樣四處流浪。落葉讓人傷感,但落葉本身並不孤單,無論走到哪裡,總有它們相遇的夥伴團聚在一起。它們隨風走動的樣子是快樂的!
一個揀拾落葉的孩子,在白楊樹林里奔跑,嘩嘩啦啦的樹葉在奔跑,孩子手裡拿著一根針,針上系著一條麻線,麻線上串滿了玉米餅一樣金黃的楊樹葉。風呼呼地吹,孩子的臉頰像經霜的水果,紅里透亮。他的腳步追逐著落葉,他的眼睛里閃爍著初冬的陽光,他頭上的棉帽被一陣旋風吹落,滿地亂飛。孩子愣住了,弄不清該去揀拾帽子,還是該去追逐落葉。他想把所有的落葉都運回家,堆成高高的柴禾垛,他看見屋頂上飄動的炊煙,他想起了灶火旁做飯的媽媽……
很多年之後,他老了,眼睜睜地看著樹上的葉子,一片接片地跌落下來,一片接一片,像沙漏,風蝕,刀削,像自己身上的某個地方,連枝條也不剩,一片接一片。他看見了,那雙被預謀驅使的手,他看見這一切,卻無能為力。不能阻止,不能挽救,甚至連憐憫也不能。剩下的光陰不多了。他放棄了抵抗的想法,俯下身子,閉上眼睛。就這樣他第一次聽到落葉叩擊大地的聲音,就像滴水落在鐘乳石上一樣動聽。他安詳陶醉的神情,使一片墜落的葉子放慢了飄失的速度,在空中起舞,舒展……最後,落在他身邊的空地上。
一個成熟的生命,就像全部長滿葉子的一棵大樹,等到秋風吹來的時候,它完整的群體轟然解散。這不是衰敗,也不是終結,而是繼續,是自然的輪迴和交替。這時那個彎腰揀拾落葉的人,又回到他的童年,他想把大地上的落葉,一片不漏地收集起來,重新排列、拼貼在一起,讓它們與長在樹上時的形狀一模一樣,不,他要創造一棵永不凋謝的大樹。這也許是一個無所事事的人,一生所做的惟一件最了不起的事。他知道,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恢復並重建一個逝去的夢想。但這項工作本身是瑣碎的,徒勞的,單調而乏味,沒有想象中的神聖,更少為人所知,但他願意在寂寞中做下去。一位名叫瓦·洛扎諾夫的俄羅斯人提前拎著背筐走來了,他起的太早,一個世紀仍在大夢中沉睡未醒,以致他的咳嗽打破了路上的寂靜:
大地的各種聲音漸漸微弱下來……
用不著了。
只有一個微弱顫抖的聲音將永遠拌和著我的眼淚。
當它止息時,我願變成聾子和瞎子。
關於記憶
1
只有一種神奇的力量可以使人類免除失語的痛苦,那就是記憶。
人類從結繩記事起,一刻不停地勞作,建築,計算,以至繪畫,使用文字,編撰歷史,吟詠詩歌,等等。其實都是為了延續同一件事:增加記憶,尋找彌補失憶的辦法,或者藉助有形的物體,使有限的生命求得永恆和不朽。
培根曾經說:“當上帝創造宇宙的那幾日,他創造的頭一件東西是光明,他創造的末一件東西就是感官的光明,他創造的最末一件東西就是理智的光明。”這裡所說的理智的光明,我以為就是記憶。
人類肯定有更美好的記憶,遺忘在史前,遺忘在了人猿階段。不然,人類不會在黑暗之中,把最初的記憶想象成一束光。一束光,比想象的還要久遠。
上帝是怎樣為人類創造了記憶?人類在伊甸園時期又是如何在無憂無慮的童年時光里幸福地成長?這一直是無法再現的秘密。
我們只知道,上帝說要有光,就有了光。至於潘多拉是如何打開災禍之匣的,恐怕只有傳說而沒有史實。沒有可靠的見證幫助我們想起:人類從何處來,又到何處去。
然而,當孔子站在河流上浩嘆:逝者如斯夫。我不禁為這一跨越時空的幽思而感觸:究竟是什麼穿透了我?如果沒有文字的記載,孔子的話,是否真的存在過呢。也許早已隨風而去了。
我彷彿聽見一種來自茫茫宇宙的聲音。
對於過去和未來,人類缺乏的不是想象而是記憶。
2
當人類在失去的夢幻之中看見記憶之光,神,出現了。始祖的面孔一閃而過。誰見過神,神在人類的記憶之中是怎樣到來,人對神的崇拜源於何時?
你相信什麼,什麼就可能存在,這是神對人的許諾。
上帝沒有死,事實不是尼采所說的那樣。上帝的原型分解了,是因為上帝由一個變成了無數個。就像今天廣告說的,人人為上帝,上帝為人人。我由此看見一個人造的、易於改變和模仿的世界正在到來。人們痛惜的不是衰亡的事物,而是尚未到來的一切。
難怪普魯斯特在寫出巨著《追憶逝水年華》之後,遺憾地說:連想象力都無法幫助我們的記憶力,來重建被遺忘之事。福斯特說的更貼切:平靜已在地球上消失,只是存在於它之外的地方,即我的想象尚未成熟得能夠隨之而去的地方。蒙田則在《論說誑》一文中告誡人們:記憶力不強的人切勿說謊。
為什麼我們生活中的許多人熱衷於道聽途說,勝過相信事實本身?
為什麼訛傳和謠言傳播的速度,比任何名譽來得都快?
為什麼光到來的時候,陰影卻提前到達?
假如不是因為記憶力的空缺,而使人類遺忘了自身的起源的話,那麼,現在看來,上帝造人的虛構,就可能淪為說誑。“人一思考上帝就發笑”,這句現代格言是否可以翻譯成:人一開口,上帝就嚇跑了。
3
聰明的博爾赫斯把書——比作記憶。他說書是記憶力和想象力的延伸。書是記憶,圖書館便是記憶的中心。
無止境的書排列在書架上,就像記憶的拷貝展開於回憶者的手上,活著的人窮其一生的時間,只是在夢幻的屏幕上看到連貫的活動的有生命的影像,而死去的人就可能在某一片斷里定格,靜止。書是記憶的載體。“每一本書,都滿載已逝時光的含義”。如果人能看見每時每刻、每分每秒的消失,就會看見記憶的儲存是那樣的美妙和奇異。看見,光,在一片葉子上的變化——由綠轉青,由青變黃,同樣也能看見“光和作用”的全部過程。為了加深記憶,人們才不斷地重溫舊夢。
把記憶作為工具,這使我想起槓桿的力量。人們用它撬動肉體和精神上的重負,搬動遺恨之石,橫渡忘川之水。
記憶的負擔愈重,肉體的承受力愈輕。
記憶不是穿舊的衣裳,而是身上的傷疤。
從心理上分析,心——用來記憶,而腦,則用來想象。記憶和想象猶如琴和曲子的關係,二者結合在一起,才能使一個生命完整,自足。
有人說,最令人驚奇的記憶力是熱戀中的女人的記憶力。然而,誰能否認,旺盛的記憶力不會使人失去理智呢。
4
在歷史的廢墟上,和時光一起埋入地下的,不僅有文明的垃圾、精神的污染品、瓦礫和沉積的污泥,而且還有死亡,以及破碎的記憶。因此,當人們走進博物館的時候,不妨把腳步放鬆一些。
過於沉重的歷史已不容許我們記住太多的東西,這或許是人類記憶力衰退的根本原因。腦滿腸肥,使人習慣於健忘,是非模糊,讓人拒絕記憶。
我曾向一位鶴風仙骨的老者求教增強記憶的方法,答曰:減肥!
(1996年4月25日)
貓眼一線日當午
這是一句中國民間諺語。
我從一冊巴掌大的小書上讀到這句話。書出版於五十年代,樣子很像尚未色染的舊粗布,除了樸素之外,還帶有民間版本的特別味道。
“貓眼一線日當午”,起初,我被其中的意象所蠱惑,深感妙不可言。後來我才知道,它是出自很普通的日常生活經驗。而非帶有學究氣的典故。
也許因為理解的障礙,或者其中詞意的組合頗費琢磨,恐怕這條諺語現在已鮮為人所知了。而且隨著它的實用價值的消失,這條諺語只保留了它的詞義美。好像成了一句徒有其表的書面語。我寧願把這看作一種損失。
如果把這句諺語當成一首中國的現代派詩歌來讀解的話,將遭到怎樣慘重的冷遇,會可想而知。況且,即使最現代派的詩歌也無法和這句諺語的奧義相比擬。
人的讀解力的減弱,不僅表現在對古文、外文和專業術語的漠視,對現代語也莫不如此。
“這是什麼意思呢?”這樣的質問如果不是來自民間,那肯定是來自官方。
“中國人從貓的眼睛里看時辰。”這是法國人波德萊爾在《鐘錶》一文中開頭的一句話。他寫道,有一位傳教士走在南京郊區時,忘了帶表,於是,便向一個淘氣的男孩問幾點了,男孩跑去抱來一隻大貓,看著貓的眼白說:“還沒有完全到中午呢。”原來,這諺語早就為西方人所知,並且寫進了為人所熟悉的名篇傑作里了。
然而,波德萊爾自己看時間的方法,遠不僅限如此。“如果我俯身去看漂亮的費利娜(Feline:原為貓科動物總稱。這裡可能暗指一位心目中的女性。)——她既是女性的光榮,又是我心中的驕傲和撫慰我精神的芳香——我總是在她迷人的眼睛深處清晰地看出時間,那是永遠不變化的時間,是寬闊、莊嚴、博大如宇宙、無分秒刻度的時間——這靜止的時間,在鐘錶上是找不到的,然而卻如一道嘆息,疾如一道目光。”誰能否認,波德萊爾不是從一個女性的眼睛看懂時間的呢。他的想象,他的迷醉,幾乎只剩下對靈魂的佔有了。
如果說從貓眼裡看時間,體現了中國人的聰明和智慧。那麼,波德萊爾從時間裡看到女性的芳香,則又是更深意味的滿足。說不定還有“葡萄酒和印度大麻”的氣息呢。可以說缺乏靈感的人,決不會品嘗到這樣墮落的享受。
提起“貓眼”,有人馬上就會想起一種名貴的寶石。假如從這種東西里看時間,不知看到的是慾望,還是幻覺。反正,我從一種叫波斯貓的眼睛,讀到過兩種不同的眼色。沒有見過狼眼,據說是綠的,和貓眼一樣,夜裡發光。
我們不乏對美好事物的想象,但缺少對想象的尊重和認同,理解不到的事情,更多的是嘲弄。七十年代初期,我們的中小學校園裡,上演過一出荒誕的滑稽短劇,相信很多人會記憶猶新。說是有兩個童子,走在路上,甲說,早晨的太陽離人最近,乙卻堅持中午。正當兩人爭喋不休,恰逢孔子路過此地,於是,二童子連忙向聖人求教。孔子一副無奈,搖頭不語。此劇意在諷譏孔子無知。當然,如果當時童子抱來大貓也肯定無用,因為貓眼只能計算時間,而不能測量距離。
我現在想來,這個小故事非常美,一個哲人,兩個童子,在古代的路上,談論太陽和人的關係。
若是在今天重演這出鬧劇,我會把它看作美麗的童話,不,它比童話更抽象、更具有象徵意義。它使我想起西方人的現代派短劇《等待戈多》。而當時我們是出於何種心態看待這一幕的,只能暗自發笑了。
古代有許多奇特的計時工具,比如日晷,漏斗,滴水等等,與現在的機械鐘,電子鐘,核子鍾比起來,原始的方法或許更接近人類對時間的把握。東西方人對時間概念有微妙的差異,最明顯的不同點是西方人精確,中國人形象。
我已經有十多年沒有帶表了,我對模糊計時法很有研究,比如有人提到“永恆”這個詞,我就會認為用倒計時的方法做事是殘酷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件計時的工具。早就有人說過,人體是只沙漏,裡面裝著計時的沙子,最後沙漏也將成為沙子。
所以,我更希望從貓眼裡看時間,以便更深地體會一种放松和悠閑。
既然從貓眼裡看時間是中國人的發明,那麼,何不製造一種“貓”牌鐘錶呢,那一定會比瑞士、日本以及任何一個國家的洋牌產品都暢銷。如今,誰不願意使緊張、有限的時間,變的舒緩一些呢。我申請這項專利。
(1996年5月9日)
瞬間消失的事物
記 憶
人的一生是靠記憶連綴起來的──童年、青年、老年……記憶是一種能力。記憶的消失──有時是緩慢的,像核輻射后的殘留物,它的傷害在同時代人身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痕迹。相同的記憶,就像流行的服飾和髮型,特定的辭彙,類似的行為,已經遺忘的曲調被某一個人唱出,引起眾多的回應和共鳴;記憶的消失有時又是迅猛的,像雪崩、旋風,像乾涸的河床。我們的記憶無法移植在另一代人身上,只有靠間接的事物傳遞下去,比如文字,遺跡,或保存下來的一些信物。對個體生命而言,記憶只存在於心靈之中,就像在物質世界里死亡只存在於肉體一樣。一個短促的冬天令人萌生對舊事物的懷念,一場太薄的雪──讓人想起對光陰的憐惜:慢點,不要讓雪溶化的太快!
遺 忘
遺忘是記憶的暫時性中斷或部分喪失。當記憶終止於一座墳墓,墳墓就會變成一個人生命的證據,遺忘隨之成了一種不可忽略的存在。它可能被置於角落,也可能被埋沒。但事情並不這麼簡單,記憶要延續、傳達,在對未知的想象中,人類渴望恢復已逝的記憶,死去的人,會在遺忘中再生,在看不見的空間里說話。為了聽到他們的聲音,我們必須找到對話的途徑,留在書本上的文字已經凝固,技術手段錄製的聲音和影像已經模糊不清,聲音、影像已辨別不出性別和年齡。這種時候,一個被人遺忘的詩人通過我們的嘴在說話:死者的道路在生者中間,我們都是影子的江河。(翁加雷蒂·義大利)
閱 讀
閱讀使一個人的內心平靜下來。以前我以為,不寫作就會有充分的時間去閱讀,現在我才知道寫作對閱讀的需要,須臾不可或缺。閱讀是加深記憶的最好的方法,閱讀是一種自省的過程,一種胃口和慾望,閱讀使內分泌增加。閱讀使人背上沉重的負擔。閱讀使我厭倦,和那些看不見的事物在一起,令我窒息。許多人把軀體埋藏在墓地,卻把名字留在書本中。不朽的經卷消磨掉多少人的時光,堆積如山的文字如此沉悶,過剩的閱讀使一個人變得瑣碎、凌亂,暮氣沉沉,一塌糊塗,懺悔,然後自言自語說,寫作是宿命,寫作是天意,寫作是不幸(洛扎諾夫)!所以,在火車上,在飛機上,那個憑窗遠眺的人,輕輕吁了口氣:鳥翼馱不動黃金,此生轉眼即逝!我想起蕭伯納喜劇中的一個片段,當大火快燒到亞歷山大圖書館時,有人大叫:“人類的記憶就要付之一炬了。”但凱撒大帝聽后卻說:“讓它們燃燒吧,那些書只不過是一派胡言!”
物 質
有些物質是無法稱出重量的,比如陽光。怎樣計算出一噸煤等於多少陽光的重量,有誰知道一朵雲帶來多少雨水。陽光的計量單位是非物質的,它的名字叫光年!
鑽石是不會凋謝的
有這樣一個故事:一個男人捧著一束玫瑰捧向一個女人求愛,女人懷抱鮮花,吻去花瓣上的露珠,閉上眼睛,露出一副陶醉的神情:“多美的花啊!——可惜,很快就會凋謝了……”那個男人魔術般地把手中的另一件東西,雙手遞上:“親愛的,你看,這個不會凋謝吧。”女人驚喜的眼睛一亮:“真的?”一顆碩大的鑽石旋即閃耀在女人手中,而那束玫瑰卻無聲地散落在地上……
窮人為什麼窮?
上帝對節儉的人說:“你的所求不多,因此給你的也不應太多。”所求不多,這也許就是窮人為什麼窮的原因?
靈魂是物質的
拉丁詩人、哲學家盧克萊修(公元前93—約50年)在一首長詩中表述了古希臘詩人伊璧鳩魯的原子論,認為靈魂是物質的,由細微的原子構成,與軀體同生死。這也許是唯物主義人生觀的原型。古希臘詩人巴克基利在《人生》一詩中寫道:
世上少有人能終身
得神明賜予
幸運,直到白頭
年老,未曾遭遇不幸
他認為,人只要活著,就會有遭遇不幸的可能。“沒有任何人終生幸福。”這是索福克勒斯的《奧狄浦斯王》中的最後一句話:“當我們等待著一個凡人的結局時,且勿說他幸福,他還沒有超過人生的終點,也沒有受過苦難。”一位古希臘詩人品達說得更清楚:“不,親愛的靈魂,別期望什麼無限的生命,而相反要窮盡你從現實中所能完成的一切。”我相信,今天活著的人,便是對來世的佔有。
我們中國人向來缺乏明確的靈魂概念,人們常說“生死由命”,命,其實就是物質的。
純 酒
一生在修道院里隱居的希爾德加德修女說:“一杯純酒可以潔凈飲者的血液”。我想,這杯純酒肯定不是糧食做的。
炮彈、金錢、詩歌和玫瑰
一天在街上,遇到很久不見的好友L,看到他擠在路邊的人群里買彩票。L驚喜。我說,剛在某刊物上讀到你的詩……他急忙岔開話,別損我了,寫了20年,早把我折騰毀了。不談寫作,買彩票,等著吧,我要中了大獎,500萬啊,設立中國最高詩歌獎,有你一份。L撇下我揚長而去。
興奮和苦惱的事情,往往接踵而至。只要留心,說不定哪個石頭縫裡,就會爆出新聞。最近讀到南方某報一篇報道,一位叫王強的企業老總,個人出資50萬,在大連搞了一個“中國當代詩歌討論會”,很多國內名牌雜誌助陣,不少知名人物到場。據稱,該贊助人還將出資200萬,在與會刊物上設立28個獎項。
在回答記者提問時,那位寫過詩的老總說,“某刊前段時間向我約稿,我沒答應。當年我給它投稿,沒用。我以後再也不投它了,你現在看到麥城出息了就來了。我不寫了,但是我認為我的狀態是委託寫作,比如委託于堅、委託張棗,還有其他一些人,我看了他們的詩好,就拿到這些欄目上發了。我對詩人的贊助也會通過貨幣和實物的方式體現,比如柏樺,是個天才,我可以不帶任何目的贊助他一台IBM手提電腦,並不是可憐他,而是覺得他的詩寫得好。我只希望中國詩歌過上好日子。”
吃飯咯牙,看事不順眼,關鍵是不要太較真。
我為好友L惋惜,當他空頭許諾還在水上漂著的時候,有人已捷足先登了。
其實,以個人名義為詩歌做點事情的人早有先例。前幾年,畫家石虎就曾資助過幾位詩人。
我主張人應該自食其力地活著。對那些救濟寫作者的人,並不以為然。我相信這句話:“多餘的錢只能買多餘的東西。”
很久以前,讀過這樣一則故事:說是有一位窮詩人,天知道叫什麼名字,他應邀參加一位富貴婦人的晚會。與會中有一位將軍,不喜歡詩人,在晚會上態度冷淡。貴婦人一會兒說將軍勇武有力,一會兒說詩人才華橫溢,但氣氛總是熱烈不起來。於是貴婦人生出一計,說:“現在請我們的好朋友,詩人先生,為大家朗誦他新近為我而作的十四行詩吧。”詩人向大家微微一笑,說:“還是請我們的將軍給諸位來一發炮彈吧!”這話一出口,笑得人仰馬翻……
假設,這樣的場合,邀幾個不同時代、不同國家的詩人出席宴會,肯定會更熱鬧。請允許我將他們的詩句拼湊起來,給這個故事再虛構些情節吧。
……就在這時,捷克人賽弗爾特端著酒杯走來,當即幽了一默:“如果讓女人開大炮,落到人間的肯定是玫瑰。”
俄國人諾索夫也會趁機來上一句:“要是把軍銜授給飛禽的話,企鵝理當榮膺海軍將銜。”
眾人在鬨笑中打住。
智利人帕拉在竊笑、自嘲:“什麼是反詩人?一個販賣棺材和骨灰盒的商賈……一個什麼也不信仰的教士……一個對自己懷疑不定的將軍……一個嘲笑自己的流浪漢……一記打在作家協會主席臉上的耳光?”大家對這一席瘋話,不知所然,面面相覷,沉默。帕拉突然又獅口大開:“我以世界上最大的痛苦,收回我說的一切。”
一位不苟言笑的中國人(大概是經常混入宴會、吃飯不花錢且一人向隅舉坐不安的那種人)在一旁喝醉了:“一隻蚊子(可能是燈光太曖昧)提著從我身上打撈的一桶血漿(也許是葡萄酒)在玻璃器皿中飛舞……我在豪華和奢侈的面孔中吸吮到自己的腥味。今夜的盛宴持續了百年……向一朵玫瑰談論愛情多麼幼稚……在獻媚的人面前讀詩,多麼無聊!”
將軍不耐煩了:“別胡說了!我準備用販賣軍火的錢,給你們發詩歌獎。”
貴婦人連忙說:“好,我當評委!”眾人鼓掌。
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幸參加這樣的盛會。詩人Y,因為沒有資格被邀請,忿忿不平。當夜詩興大發:“餓死你們狗日的詩人。”好像還不過癮,Y來個更大的幽默:如果請我出席諾貝爾授獎宴會,我不拒絕。我當然要接受這筆賣炸藥的錢,我要把它完全買成炸藥,尊敬的女士們先生們,尊敬的國王陛下,請你們準備好,請你們一齊——卧倒。
對此耿耿於懷的人肯定不在少數,他們中間的一些人,如我的好友L那樣,在心裡暗暗發狠,也想搞個名堂。一位詩友當年下海經商時,對我說過,試試把鈔票鋪在稿紙下面寫詩的感覺如何?
唉,詩歌和金錢,本來就是兩回事,怎麼能混為一談呢?如果真活得沒勁,還是多一些幻想,浪漫一點好:“誰若覺得無聊,就讓他愛上——比如英國女王。那有什麼不可以呢?她的肖像印在每一張古老王國的郵票上。(塞弗爾特)”
寂靜的田野
陽光久照的夏天過去了,時光在一片葉子里走完了一生的路。我需要一個下午,到田野上走一走。疾風牽引著我的腳步,想停留下來是多麼不容易啊,在一棵樹下,我站了一會兒,幾片樹葉奔跑過來,我沒有耐心等所有的葉子都跑過來,只有一邊走,一邊看。田野——像一本打開的書,記敘了我看見的一切。
我拾起一片微微泛黃的葉子,在手上展開。反覆觀察它的紋絡,偶然發現了田野的地形圖。一隻手和一片葉子,或許有更多的相似之處。這隻樹的手,索取了太多的陽光,也經歷了一生的辛勞。如今衰竭了,變得粗糙,蒼涼,就像人的手一樣。因為手的索取,土地貢獻了它的果實,只剩下荒涼。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類自古在土地上耕作,播種,採集。因為收穫得太多了,手和手有了分工,人和人有了高低貴賤之分。世上沒有兩片相同的葉子,手和手又是多麼的不同。一個放大的指紋可以辨別不同的身份:罪惡、善良、命運、權力、占卜和星象。你看那些奔跑的蹄印,它們可以佔據大地的遼闊,但沒有跑出人的手心。我多麼羨慕會飛的翅膀——倘若會飛,我們要手幹什麼?一雙謀生的手,把人和牛馬栓在同一根樁上。“我永遠不要手,如果長了手,奴役便將使你走得太遠,誠實行乞又使我痛苦(蘭波)。”樹枝毫無痛苦地把手扔在地上,它就這樣放棄了無謂的忙碌、忘記勞累,靜靜地休息了。
一隻螞蟻從另一片葉子上,爬上來又爬過去,它爬得很慢,翻過一條水溝,就像逾越一條峽谷。為一隻螞蟻著急有什麼用呢?幾十分鐘,我走到了一座村莊的地界。如此眾多的村莊,我曾在哪裡居住?
鳥在天空無法逗留,它們成群地落在地上,揀拾一些遺落的種籽,鳥是最後的收穫者,但它們永遠不會把食物儲存起來,田野就是它們的糧倉。人們總以為鳥偷吃糧食,其實除了麻雀之外,更多的鳥生活在人煙稀少的地方,以捕食害蟲為生。鳥之所以能輕盈地飛翔,因為他們每次只需要很少的食物就能活著。
貪婪的鼠類則不同,它總是把吃不掉的糧食囤積在黑暗的洞穴。秦相李斯說過,人生如鼠,不在倉,即在廁。曾是糧倉看守的李斯一日如廁時,見一老鼠枯瘦可憐,既而想到糧倉的老鼠,個個肥頭大耳非等閑之輩,不免頓悟——人之賢不肖如鼠矣,在所處耳!這些田野上的老鼠,怎能與糧倉的鼠相比呢?比上不足,比下有餘,與廁內的老鼠相比,它們活得自由自在,衣食不愁。我鄙視所有的鼠類,卻不敢小看它們的能力。然而,如李斯之人何異於鼠類,雖然卑微可憐,但卻面目可憎,令人恐懼。在動物界,老鼠被人認為是生命力最強的一種。誰敢說將來有一天,地球會不會是鼠類的世界呢?我不禁想起童年的一件往事。
記得小時候,村裡有一個又懶又饞的人,平時熊事不幹,每到農閑,就抗著鐵鍬來到田野上亂逛,有時蹲在地上挖半天,誰也不知道他挖些什麼。有一次,我隨著幾個大人在田野里追趕野兔。一群孩子,十幾條狗,在秋茬地里跑了整整一天,又累又餓。突然,一隻野兔躍出地面,我們的腳步頓時像非洲鼓般急促地敲響,塵土飛揚,殘陽如血。翻過一座土窯,野兔眨眼不見蹤影。這時,我們發現那個懶人,在土坡上刨開了一個大坑,他停下挖掘,低頭坐在土堆上,目光幽暗,緊瞅著我們,坑底用袋子蓋住,好像有什麼可疑的東西。有人不顧一切,撩開遮掩,只見下面一攤飽漲的黃豆,旁邊躺著幾隻被弄死的老鼠,還冒著熱氣呢,原來這是個鼠穴,真讓人噁心!懶人握起鐵鍬,憤怒地盯著我們。然後,拚命地滾到坑底,身體死死地護著“戰利品”。懶人光棍一條,誰也不敢惹他。我們鄙視地看了一眼,一鬨而散。傍晚,懶人背著一大袋東西,灰遛遛地回到村裡。他從鼠洞里挖回來多少糧食,誰也不知道。反正,每當街上響起買豆腐的吆喝,懶人就偷偷地從家裡跑出來,然後,手捧熱豆腐興奮地關上門。那年冬天,很多人挨凍受餓,我好像聽見懶人咯咯地偷笑,就像老鼠在啃東西……多年後,那聲音折磨著我的睡眠,如同指甲在牆壁上磨擦……
疾風遛著地皮,吹得野草簌簌作響。我的腳步驚動了那些變色的螞蚱,幾天前,它們還撲閃著翅膀,在草尖亂飛,這時卻連蹦噠一下都懶得動彈。大地變得枯黃,草根與泥土貼得更緊了。平原上,很難找到眺望四野的高地。除了遠處隱約可見的山巒,天邊的白雲,附近沒有更高的地形。
如果我願意,可以沿著田間小路,再往前走,前面有一座荒廢的窯場。那是我曾逗留過的一個景點。穿過稀疏的樹林,可見大片燃燒過的紅土,荒涼的窪地,周圍遺留下掘土的痕迹,日晒雨淋,露出幾種不同顏色的地層,從灰黃到褐色再到沙層,窪地里積滿了夏天的雨水,清亮可鑒。從水裡看見磚窯的倒影,像一座荒涼的“古堡”。我曾經邀畫畫的朋友到這裡寫生,可惜沒有成行。在我眼裡,“古堡”就像一幅無法用語言描述的油畫:斑剝的土牆,不用撫摸,落下風蝕的塵土,燒灼的釉滓,帶著雨水沖刷不掉的灰燼,像凝固的油彩一樣堅硬。多少年了,土窯變得越來越蒼老,有的部位坍塌了,長滿了野草,變成蛇、狐、兔隱身的洞穴,高處則是各種鳥雀做巢的地方。至於,這座窯場何時修建又何時廢棄,我從未打聽過。它能夠保留下來是幸運的,或許人們已把它遺忘,不然早就把它剷平變成耕地了。
每當我登上窯頂,俯瞰萬物,頓覺心胸開朗。隨著時光的流逝,它也許會變得面目全非。風吹雨打,物換星移,在這片易於改變的土地上,它為我保留一處原始的景象。不管它是否有過榮耀,在我的心目中,它永遠是大地上一座無名的紀念碑!
大約再走三五里路,是一條古老的河流,蜿蜒的河堤,由東向西延伸而來。在那裡可以望見很多密布的溝渠,像葉子上的脈絡那樣清晰。“看見蛛網就看見了回家的路”,一位懷鄉的詩人道出心中的隱秘。而今,我到哪裡再去尋找那些隱蔽的河流、消失的流水呢?在回憶里,還是在地圖上?荒蕪的河床平靜地躺在天空下面,不見金黃的沙灘,青青的水草,光滑的鵝卵石,清澈的流水,纖小的游魚,只有蘆葦、野蒿和臭氣熏天的沼澤……
不可否認,走在河堤上,依然可以領略到兩岸特有的風光。在秋陽夕照的河岸上,仍有一些不知名的飛鳥,在附近起落。河堤上的空氣,有一種激活人心的力量,它使我神清目爽。無法想象古人登高望遠的心情。而我望著對岸一片的人工林,竟像看見了古木參天的森林。那些自然生長的野生草木,只有在偏僻的被人遺忘的角落裡,自生自滅。到處都是人造的易於磨滅的事物,比如一條橫空架設的高速公路,迅速改變了那裡平緩的地貌特徵,一片塌陷的礦區形成了積水的湖泊……
走近一片新生的田野。翻耕過的泥土,鬆軟,新鮮,剛剛播下麥種,踏上去有些溫熱。落葉,飛絮,乾草,果實和秫秸腐爛的氣息迎面撲來。麥苗很快就會長出田壟,田野從來沒有休息的功夫,也許它可以湊空打個盹兒。也有一些閑置的空地,裸露著渾圓的脊背,像一個巨大的樹墩。
大地從來沒有顯露過它真實的面目,只有一個隆起的背影。暮色蒼茫,起伏的遠山就是大地的化身。在土地上,你已看不到一個真正躬身耕作的人:那手扶犁犋揮鞭趕牛的形象已經消失了。牛在工廠里產奶,雞在流水線上下蛋。現在農民是最忙碌的人,他們一邊種田,一邊在城裡打工。“耕種”本身,其實並沒有多少實際的意義可言,它是勞碌的象徵,就像螞蟻為一塊搬不動的骨頭聚集在一起。田野上的勞動並不像人們讚美的那樣誠實可靠,十分付出有時只有一份收穫,汗水換來的更多的是辛苦,不勞而獲可能得到的更多。不為名利的寫作者,也許是一個默默耕耘的人。但那些不求奢華、以簡樸的方式走向自然的人,更值得我尊敬。
無謂的勞作將違背大自然的旨意,古人追慕的自由自在的田園生活,實際上最接近人生的本意,今天,人們製造的所謂繁華和文明,離生活的本質相去甚遠。“這個大地變得暗淡無光的大部分過錯,都是那些靈魂不寧、貪慾無度的人造成的,他們使這個世界變得日益嘈雜喧囂。”人類所需要的東西,哪樣不是從地球上索取的呢?煤炭、石油、鋼鐵、鑽石、混凝土,高樓大廈的每一塊磚石,甚至餐桌上豐盛的食物,透光的玻璃器皿等等,除了樹葉採集的陽光,人類從宇宙獲得的能量微乎其微。人,為什麼不能活得簡單一些?房屋可以寬敞,但設施不必奢華,食物可以講究,但不必浪費。為什麼不能以最低的需求滿足最大的願望呢?
經過一片寸草不生的亂石崗,那裡有幾座孤零零的墳墓。我想起那些化作泥土的人,死去的人總比活著的人多,他們也曾經活著。以前,每個村莊都有幾片大面積的墓地,佔據著風水最好的土地,墓地上栽種著各種林木,松柏、野藤、楝子、薔薇、古槐……鬱鬱蔥蔥,神秘可畏,為人們留下了刻骨銘心的記憶。後來,為了擴展耕地,鄉村墓地被全部挖掘一空。這些零星的孤塋,只有躺在不為人所知的荒野。我見過許多高貴者的墓地和靈堂,雖豪華奢侈,但軀體終究是一搓泥土。死亡對每個人都是公平的。人世的所有的煩憂和恐懼,已是過眼煙雲。想到這些,我為那些終生勞累而不得片刻享受的人感到安慰。
今天春天,我回老家為祖父祖母掃墓,他們的骨灰葬在一片青青的麥田裡。沒有墳塋,沒有墓碑,家人只能對著那片拔節抽穗的麥地,席地跪拜。那是我家的祖地,對於祖父祖母來說,沒有比“葬於此地”更幸運的了。這裡雖然沒有松柏常青的陵園,但卻能年年看到大地的豐收。我祈禱他們在天之靈永久地安息。
不止一個人說過,世間沒有比死亡更尊嚴了。對於那些流浪在外最終找不到歸宿的人來說,也許一片樹蔭,一方潔凈的陰涼,將是他最安靜的去處。“死者,在綠蔭下的寂靜中,似乎對尚留在世上的人,耳語著鼓勵之詞:我們這樣,你們也將這樣,瞧瞧我們安息的多麼寧靜!”這是一生窮困潦倒的英國作家喬治·吉辛的晚年遺言。願人們善待生命。
*
天色漸晚,柔和的光線與土地的顏色融為一體。遠近不同的景象,罩上了一種曖昧的過度色,有時候,我喜歡這種不太明朗的色調,它似乎可以隱去多餘的背景——比如可以排除時間、歷史和時代的痕迹,只呈現自然現象中最微妙的最細微的那一部分。於是,地上的樹葉安靜下來,低矮的灌木端坐一旁,高過地面的任何一種事物,投下了自己的淡淡的陰影,遠處的陰影更重一些,與天上的雲塊連成一片,那片映著金光的地方,肯定是一片水溏。四周的村落並不比樹上的鳥巢更清晰可見,一條追著自己影子爬行的蜥蜴,是不是忘了回家的路。此刻,我可以暫時忽略視覺,讓聽覺靈敏起來。放慢腳步吧,你聽,唧唧,噓噓,那些隱藏在泥土中的蛐蛐叫了,還有微弱的風聲,機警的鳥鳴……在這漸漸沉寂的秋野中,我感到一種說不出的孤單,又不免生出幾分凄涼。我所熱愛的土地已經疲憊了,塵埃落定,塵歸塵,土歸土。夕光里,我長長的影子,像細流一樣不斷地延伸,消失,融入植物的根脈。一個久遠的夢,撫摸著永恆的事物中永不改變的慈祥的大地。我感到大自然正在它的聖殿里鋪好了眠床。剎那間,迷漫的霧氣從四野升起,大地蒙上神秘的面紗。落日總是先行一步,讓歸來者走在夜色籠罩的路上。
(2000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