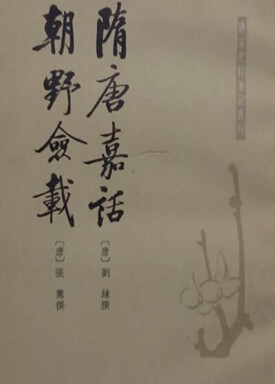朝野僉載
唐代張鷟撰寫小說集
唐代筆記小說集。此書記載朝野佚聞,尤多武后朝事。唐張鷟撰。六卷。記隋唐兩代朝野遺聞,對武則天時期的朝政頗多譏評,有的為《資治通鑒》所取材。其中亦多怪誕不經的傳說。今本已非原書。張鷟死於玄宗開元年間,書中有若干條記載開元以後事,當系後人所竄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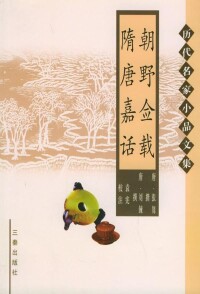
朝野僉載
《朝野僉載》為作者耳聞目睹的社會札記,內容十分廣泛,記述了唐代前期朝野遺事軼聞,尤以武后朝事迹為主。書中反映了當時有關人物事迹、典章制度、社會風尚、傳聞逸事,也站在反對派的角度對武后朝的政治黑暗、吏治腐敗、酷吏橫暴、民生疾苦有所揭露,暴露了"賄貨縱橫,贓物狼藉"的現實世相。因屬時人記時事,所載內容,多為第一手資料,所以頗有參考價值,為《太平廣記》、《資治通鑒》以及後世治唐史者廣為引用。但因作者紀事好追求諧謔,致使書中所載失之荒怪、瑣雜,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史料文獻價值,為後人所詬病,如洪邁《容齋續筆》卷12就曾說:"《僉載》記事,皆瑣尾擿裂,且多媟語。"
此書《新唐書》、《宋史》均著錄為20卷,另有《補遺》3卷。尤袤《遂初堂書目》疑《補遺》乃後人附益,凡闌入中唐後事者,皆應為《補遺》之文。余嘉錫《四庫提要辯證》推測《僉載》亡於明代,今所存者是明人輯本。此書明代以後流行有1卷本和6卷本,《說郛》、《歷代小史》、《古今說海》、《畿輔叢書》等本為1卷本系統;《寶顏堂秘笈》、《叢書集成》等本為6卷本系統。1979年中華書局趙守儼校點本,以《寶顏堂秘笈》本為底本,又從《太平廣記》、《通鑒考異》等書中輯出近百條遺文,作為"補輯"附印,較勝於舊本。
據《新唐書》和《宋史。藝文志》著錄為二十卷,今傳六卷。主要記隋唐兩代朝野逸聞,尤以武則天當政時的事迹為多。《資治通鑒》亦曾取材於此。間有鬼神怪異,瑣語瑣聞。作者死於開元年間,書中載開元以後唐敬宗、宣宗時事,當為後人增入。
●卷一
貞觀年中,定州鼓城縣人魏全家富,母忽失明。問卜者王子貞,子貞為卜之,曰:“明年有人從東來青衣者,三月一日來,療必愈。”至時,候見一人著青糹由襦,遂邀為設飲食。其人曰:“仆不解醫,但解作犁耳,為主人作之。”持斧繞舍求犁轅,見桑曲枝臨井上,遂斫下。其母兩眼煥然見物。此曲桑蓋井之所致也。
周郎中裴珪妾趙氏,有美色,曾就張璟藏卜年命。藏曰:“夫人目長而漫視。准相書,豬視者淫。婦人目有四白,五夫守宅。夫人終以奸廢,宜慎之。”趙笑而去。後果與人奸,沒入掖庭。
杜景佺,信都人也。本名元方,垂拱中,更為景佺。剛直嚴正,進士擢第,後為鸞台侍郎、平章事。時內史李昭德以剛直下獄,景佺廷諍其公清正直。則天怒,以為面欺,左授溱州刺史。初任溱州,會善筮者於路,言其當重入相,得三品,而不著紫袍。至是夏中服紫衫而終。
瀛州人安縣令張懷禮、滄州弓高令晉行忠就蔡微遠卜。轉式訖,謂禮曰: “公大親近,位至方伯。”謂忠曰:“公得京官,今年祿盡,宜致仕可也。”二人皆應舉,懷禮授左補闕,后至和、復二州刺史。行忠授城門郎,至秋而卒。
開元二年,梁州道士梁虛州,以九宮推算張鷟云:“五鬼加年,天罡臨命,一生之大厄。以《周易》筮之,遇《觀》之《渙》,主驚恐;后風行水上,事即散。”安國觀道士李若虛,不告姓名,暗使推之。云:“此人今年身在天牢,負大辟之罪乃可以免。不然病當死,無救法。”果被御史李全交致其罪,敕令處盡。而刑部尚書李日知,左丞張廷圭、崔玄升,侍郎程行謀咸請之,乃免死,配流嶺南。二道士之言信有徵矣。
泉州有客盧元欽染大瘋,惟鼻根未倒。屬五月五日官取蚺蛇膽欲進,或言肉可治瘋,遂取一截蛇肉食之。三五日頓漸可,百日平復。又商州有人患大瘋,家人惡之,山中為起茅舍。有烏蛇墜酒罌中,病人不知,飲酒漸差。罌底見蛇骨,方知其由也。
則天時,鳳閣侍郎周允元朝罷入閣。太平公主喚一醫人自光政門入,見一鬼撮允元頭,二鬼持棒隨其後,直入景運門。醫白公主,公主奏之。上令給使覘問,在閣無事。食訖還房,午後如廁,長參典怪其久私,往候之,允元踣面於廁上,目直視,不語,口中涎落。給使奏之,上問醫曰:“此可得幾時?”對曰:“緩者三日,急者一日。”上與錦被覆之,並床舁送宅,止夜半而卒。上自為詩以悼之。
久視年中,襄州人楊元亮,年二十餘,於虔州汶山觀佣力。晝夢見天尊云: “我堂舍破壞,汝為我修造,遣汝能醫一切病。”寤而悅之,試療無不愈者。贛縣裡正背有腫,大如拳,亮以刀割之,數日平復。療病日獲十千,造天尊堂成,療病漸無效。
如意年中,洛州人趙玄景病卒五日而蘇。雲見一僧與一木,長尺余,教曰: “人有病者,汝以此木拄之即愈。”玄景得見機上尺,乃是僧所與者,試將療病,拄之立差,門庭每日數百人。御史馬知己以其聚眾,追之禁左台,病者滿於台門。則天聞之,追入內,宮人病,拄之即愈,放出任救病百姓。數月以後,得錢七百餘貫。后漸無驗,遂絕。
洛州有士人患應病,語即喉中應之。以問善醫張文仲,經夜思之,乃得一法。即取《本草》令讀之,皆應;至其所畏者,即不言。仲乃錄取葯,合和為丸,服之應時而愈。一雲問醫蘇澄雲。
郝公景於泰山採藥,經市過。有見鬼者,怪群鬼見公景皆走避之。遂取葯和為“殺鬼丸”,有病患者服之差。
定州人崔務墜馬折足,醫令取銅末和酒服之,遂痊平。及亡后十餘年改葬,視其脛骨折處,有銅末束之。
嶺南風俗,多為毒藥。令奴食冶葛死,埋之土中。蕈生正當腹上,食之立死;手足額上生者,當日死;旁自外者,數日死;漸遠者,或一月,或兩月;全遠者,一年、二年、三年亦即死。惟陳懷卿家葯能解之。或以塗馬鞭頭控上,拂著手即毒,試著口即死。
趙延禧雲,遭惡蛇虺所螫處,貼之艾炷,當上炙之立差,不然即死。凡蛇嚙,即當嚙處灸之,引去毒氣即止。
冶葛食之立死。有冶葛處即有白藤花,能解冶葛毒。鴆鳥食水之處即有犀牛,不濯角,其水物食之必死,為鴆食蛇之故。
醫書言,虎中藥箭食清泥;野豬中藥箭豗薺苨而食;雉被鷹傷,以地黃葉帖之。又礬石可以害鼠,張鷟曾試之,鼠中毒如醉,亦不識人,猶知取泥汁飲之,須臾平復。鳥獸蟲物猶知解毒,何況人乎被蠶嚙者,以甲蟲末傅之;被馬咬者,以燒鞭鞘灰塗之。蓋取其相服也。蜘蛛嚙者,雄黃末傅之。筋斷須續者,取旋復根絞取汁,以筋相對,以汁塗而封之,即相續如故。蜀兒奴逃走多刻筋,以此續之,百不失一。
永徽中有崔爽者,每食生魚三斗乃足。於後飢,作鱠未成,爽忍飢不禁,遂吐一物,狀如蝦蟆。自此之後,不復能食鱠矣。
國子司業、知制誥崔融病百餘日,腹中蟲蝕極痛,不可忍。有一物如守宮從下部出,須臾而卒。
後魏孝文帝定四姓,隴西季氏大姓,恐不入,星夜乘鳴駝,倍程至洛。時四姓已定訖,故至今謂之“駝李”焉。
張文成曰:乾封以前選人,每年不越數千;垂拱以後,每歲常至五萬。人不加眾,選人益繁者,蓋有由矣。嘗試論之,祗如明經、進士、十周、三衛、勛散、雜色、國官、直司,妙簡實材,堪入流者十分不過一二。選司考練,總是假手冒名,勢家囑請。手不把筆,即送東司;眼不識文,被舉南館。正員不足,權補試、攝、檢校之官。賄貨縱橫,贓污狼藉。流外行署,錢多即留,或帖司助曹,或員外行案。更有挽郎、輦腳、營田、當屯,無尺寸工夫,並優與處分。皆不事學問,惟求財賄。是以選人冗冗,甚於羊群,吏部喧喧,多於蟻聚。若銓實用,百無一人。積薪化薪,所從來遠矣。
鄭愔為吏部侍郎掌選,贓污狼藉。引銓有選人系百錢於靴帶上,愔問其故,答曰:“當今之選,非錢不行。”愔默而不言。時崔湜亦為吏部侍郎掌選,有銓人引過,分疏云:“某能翹關負米。”湜曰:“君壯,何不兵部選?”答曰:“外邊人皆雲‘崔侍郎下,有氣力者即存。'”
景龍中,斜封得官者二百人,從屠販而踐高位。景雲踐祚,尚書宋璟、御史大夫畢構奏停斜封人官。璟、構出,后見鬼人彭卿受斜封人賄賂,奏雲見孝和,怒曰:“我與人官,何因奪卻。”於是斜封皆復舊職。偽周革命之際,十道使人天下選殘明經、進士及下村教童蒙博士,皆被搜揚,不曾試練,並與美職。塵黷士人之品,誘悅愚夫之心,庸才者得官以為榮,有才者得官以為辱。昔趙王倫之篡也,天下孝廉、秀才、茂異,並不簡試,雷同與官,市道屠沽、亡命不軌,皆封侯略盡。太府之銅不供鑄印,至有白版侯者。朝會之服,貂者大半,故謠雲“貂不足,狗尾續”。小人多幸,君子恥之。無道之朝,一何連類也,惜哉!
天后中,契丹李盡忠、孫萬榮之破營府也,以地牢囚漢俘數百人。聞麻仁節等諸軍欲至,乃令守囚?等紿之曰:“家口饑寒,不能存活。求待國家兵到,吾等即降。”其囚日別與一頓粥,引出安慰曰:“吾此無飲食養汝,又不忍殺汝,總放歸若何?”眾皆拜伏乞命,乃紿放去。至幽州,具說飢凍逗遛。兵士聞之,爭欲先入。至黃麞峪,賊又令老者投官軍,送遺老牛瘦馬於道側。仁節等三軍棄步卒,將馬先爭入,賊設伏橫截,軍將被索糹?之,生擒節等,死者填山谷,罕有一遺。
景龍四年,洛州凌空觀失火,萬物並盡,惟有一真人巋然獨存,乃泥塑為之。后改為聖真觀。
西京朝堂北頭有大槐樹,隋曰唐興村門首。文皇帝移長安城,將作大匠高熲常坐此樹下檢校。后栽樹行不正,欲去之,帝曰:“高熲坐此樹下,不須殺之。”至今先天百三十年,其樹尚在,柯葉森竦,株根盤礴,與諸樹不同。承天門正當唐興村門首,今唐家居焉。
永徽年以後,人唱《桑條歌》云:“桑條{艹吊},女韋也樂。”至神龍年中,逆韋應之。諂佞者鄭愔作《桑條樂詞》十餘首進之,逆韋大喜,擢之為吏部侍郎,賞縑百匹。
龍朔以來,人唱歌名《突厥鹽》。後周聖歷年中,差閻知微和匈奴,授三品春官尚書,送武延秀娶成默啜女,送金銀器物、錦綵衣裳以為禮聘,不可勝紀。突厥翻動,漢使並沒,立知微為可汗,《突厥鹽》之應。
調露中,大帝欲封中嶽,屬突厥叛而止。后又欲封,土番入寇,遂停。至永淳年,又駕幸嵩岳,謠曰:“嵩山凡幾層,不畏登不得,只畏不得登。三度徵兵馬,傍道打騰騰。”岳下遘疾,不愈,回至宮而崩。
永淳之後,天下皆唱“楊柳,楊柳,漫頭駝”。后徐敬業犯事,出柳州司馬,遂作偽敕,自授揚州司馬,殺長史陳敬之,據江淮反。使李孝逸討之,斬業首,驛馬駝入洛。“楊柳,楊柳,漫頭駝”,此其應也。
周如意年中以來,始唱《黃麞歌》,其詞曰:“黃麞,黃麞,草里藏,彎弓射你傷。”俄而契丹反叛,殺都督趙文翙,營府陷沒。差總管曹仁師、張玄遇、麻仁節、王孝傑,前後百萬眾,被賊敗於黃麞谷,諸軍並沒,罔有孓遺。《黃麞》之歌,斯為驗矣。
周垂拱已來,《苾拿兒歌》詞皆是邪曲。后張易之小名苾拿。
景龍年,安樂公主於洛州道光坊造安樂寺,用錢數百萬。童謠曰:“可憐安樂寺,了了樹頭懸。”后誅逆韋,並殺安樂,斬首懸於竿上,改為悖逆庶人。
神龍以後,謠曰:“山南烏鵲窠,山北金駱駝。鐮柯不鑿孔,斧子不施柯。”此突厥強盛,百姓不得斫桑養蠶、種禾刈谷之應也。
景龍中,謠曰:“可憐聖善寺,身著綠毛衣。牽來河裡飲,踏殺鯉魚兒。”至景雲中,譙王從均州入都作亂,敗走,投洛川而死。
景雲中,謠曰:“一條麻線挽天樞,絕去也。”神武即位,敕令推倒天樞,收銅併入尚方,此其應兆。
景龍中,謠曰:“黃柏犢子挽蚓斷,兩腳踏地鞋<麻需>斷。”六月,平王誅逆韋,欲作亂。鞋<麻需>斷者,事不成。阿韋是“黃犢”之後也。
明堂主簿駱賓王《帝京篇》曰:“倏忽搏風生羽翼,須臾失浪委泥沙。”賓王后與敬業興兵揚州,大敗,投江而死,此其讖也。
麟德已來,百姓飲酒唱歌,曲終而不盡者號為“族鹽”。后閻知微從突闕領賊破趙、定。後知微來,則天大怒,磔於西市。命百官射之,河內王武懿宗去七步,射三發,皆不中,其怯懦也如此。知微身上箭如猥毛,銼其骨肉,夷其九族,疏親及不相識者皆斬之。小兒年七八歲,驅抱向西市,百姓哀之,擲餅果與者,相爭奪以為戲笑。監刑御史不忍害,奏舍之。其“族鹽”之言,於斯應也。
趙公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為渾脫氈帽,天下慕之,其帽為“趙公渾脫”。后坐事長流嶺南,“渾脫”之言,於是效焉。
魏王為巾子向前踣,天下欣欣慕之,名為“魏王踣”。后坐死。至孝和時,陸頌亦為巾子同此樣,時人又名為“陸頌踣”。未一年而陸頌殞。
永徽后,天下唱《武媚娘歌》,后立武氏為皇后。大帝崩,則天臨朝,改號大周。二十餘年,武后強盛,武三王梁、魏、定等並開府,自余郡王十餘人,幾遷鼎矣。
咸亨以後,人皆云:“莫浪語,阿婆嗔,三叔聞時笑殺人。”後果則天即位,至孝和嗣之。阿婆者,則天也;三叔者,孝和為第三也。
魏僕射子名叔麟,讖者曰:“'叔麟',反語'身戮'也。”後果被羅織而誅。
梁王武三思,唐神龍初改封德靖王。讖者言:“德靖,'鼎賊'也。”果有窺鼎之志,被鄭克等斬之。
天后時,謠言曰:“張公吃酒李公醉。”張公者,斥易之兄弟也;李公者,言李氏大盛也。
孫佺為幽州都督,五月北征。時軍師李處郁諫:“五月南方火,北方水,火入水必滅。”佺不從,果沒八萬人。昔竇建德救王世充於牛口谷,時謂“竇入牛口,豈有還期”。果被秦王所擒。其孫佺之北也,處郁曰:“飧若入咽,百無一全。”山東人謂溫飯為飧(音孫),幽州以北並為燕地,故云。
龍朔年已來,百姓飲酒作令云:“子母相去離,連台拗倒。”子母者,盞與盤也;連台者,連盤拗倒盞也。及天后永昌中,羅織事起,有宿衛十餘人於清化坊飲,為此令。此席人進狀告之,十人皆棄市。自后廬陵徙均州,則子母相去離也;連台拗倒者,則天被廢,諸武遷放之兆。
神武皇帝七月即位,東都白馬寺鐵像頭無故自落於殿門外。自后捉搦僧尼嚴急,令拜父母等,未成者並停革,后出者科決,還俗者十八九焉。
開元五年春,司天奏:“玄象有眚見,其災甚重。”玄宗震驚,問曰:“何祥?”對曰:“當有名士三十人同日冤死,今新及第進士正應其數。”其年及第李蒙者,貴主家婿,上不言其事,密戒主曰:“每有大游宴,汝愛婿可閉留其家。”主居昭國里,時大合樂,音曲遠暢,曲江漲水,聯舟數艘,進士畢集。蒙聞,乃逾垣奔走,群眾愜望。才登舟,移就水中,畫舸平沉,聲妓、篙工不知紀極,三十進士無一生者。
夏侯處信為荊州長史,有賓過之,處信命仆作食。仆附耳語曰:“溲幾許面?”信曰:“兩人二升即可矣。”仆入,久不出,賓以事告去。信遽呼仆,仆曰: “已溲訖。”信鳴指曰:“大異事。”良久乃曰:“可總燔作餅,吾公退食之。”信又嘗以一小瓶貯醯一升自食,家人不沾餘瀝。仆云:“醋盡。”信取瓶合於掌上,餘數滴,因以口吸之。凡市易,必經手乃授直。識者鄙之。
廣州錄事參軍柳慶獨居一室,器用食物並致卧內。奴有私取鹽一撮者,慶鞭之見血。
夏侯彪夏月食飲,生蟲在下,未曾瀝口。嘗送客出門,奴盜食臠肉。彪還覺之,大怒,乃捉蠅與食,令嘔出之。
鄭仁凱為密州刺史,有小奴告以履穿,凱曰:“阿翁為汝經營鞋。”有頃,門夫著鞋者至,凱?前樹上有鴷窠。鴷,啄木也。遣門夫上樹取其子。門夫脫鞋而緣之,凱令奴著鞋而去,門夫竟至徒跣。凱有德色。
安南都護鄧祐,韻州人,家巨富,奴婢千人。恆課口腹自供,未曾設客。孫子將一鴨私用,祐以擅破家資,鞭二十。
韋莊頗讀書,數米而炊,秤薪而爨,炙少一臠而覺之。一子八歲而卒,妻斂以時服,庄剝取,以故席裹屍,殯訖,擎其席而歸。其憶念也,嗚咽不自勝,惟慳吝耳。
懷州錄事參軍路敬潛遭綦連輝事,於新開推鞫,免死配流。后訴雪,授睦州遂安縣令。前邑宰皆卒於官,潛欲不赴。其妻曰:“君若合死,新開之難早已無身,今得縣令,豈非命乎?”遂至州,去縣水路數百里上,寢堂兩間有三殯坑,皆埋舊縣令,潛命坊夫填之。有梟鳴於屏風,又鳴於承塵上,並不以為事。每與妻對食,有鼠數十頭,或黃或白,或青或黑,以杖驅之,則抱杖而叫。自余妖怪,不可具言。至四考滿,一無所失,選授衛令,除衛州司馬。入為郎中,位至中書舍人。
周甘子布博學有才,年十七為左衛長史,不入五品。登封年病,以驢輿強至岳下,天恩加兩階,合入五品,竟不能起。鄰里親戚來賀,衣冠不得,遂以緋袍覆其上,帖然而終。
太常卿盧崇道坐女婿中書令崔湜反,羽林郎將張仙坐與薛介然口陳欲反之狀,俱流嶺南。經年,無日不悲號,兩目皆腫,不勝凄楚,遂並逃歸。崇道至都宅藏隱,為男娶崔氏女未成,有內給使來取充貴人,崇道乃賂給使,別取一崔家女去入內。事敗,給使具承,掩崇道,並男三人亦被糾捉,敕杖各決一百,俱至喪命。
青州刺史劉仁軌知海運,失船極多,除名為民,遂遼東效力。遇病卧平壤城下,褰幕看兵士攻城。有一卒直來前頭背坐,叱之不去,仍惡罵曰:“你欲看,我亦欲看,何預汝事?”不肯去。須臾城頭放箭,正中心而死。微此兵,仁軌幾為流矢所中。
任之選與張說同時應舉。后說為中書令,之選竟不及第。來謁張公,公遺絹一束,以充糧用。之選將歸,至舍不經一兩日,疾大作,將絹市葯,絹盡疾自損。非但此度,余處亦然,何薄命之甚也!
杭州刺史裴有敞疾甚,令錢塘縣主簿夏榮看之。榮曰:“使君百無一慮,夫人早須崇福以禳之。”崔夫人曰:“禳須何物?”榮曰:“使君娶二姬以壓之,出三年則危過矣。”夫人怒曰:“此獠狂語,兒在身無病。”榮退曰:“夫人不信,榮不敢言。使君命合有三婦,若不更娶,於夫人不祥。”夫人曰:“乍可死,此事不相當也。”其年夫人暴亡,敞更娶二姬,榮言信矣。
平王誅逆韋,崔日用將兵杜曲,誅諸韋略盡,繃子中嬰孩亦楻殺之。諸杜濫及者非一。浮休子曰:“此逆韋之罪,疏族何辜!亦如冉閔殺胡,高鼻者橫死;董卓誅閹人,無須者枉戮。死生命也。”
逆韋之變,吏部尚書張嘉福河北道存撫使,至懷州武陟驛,有敕所至處斬之。尋有敕矜放,使人馬上昏睡,遲行一驛,比至,已斬訖。命非天乎,天非命乎!
沈君亮見冥道事,上元年中,吏部員外張仁禕延生問曰:“明公看禕何當遷?”亮曰:“台郎坐不暖席,何慮不遷。”俄而禕如廁,亮謂諸人曰:“張員外總十餘日活,何暇憂官職乎?”后七日而禕卒。
虔州司士劉知元攝判司倉,大?甫時,司馬楊舜臣謂之曰:“買肉必須含胎,肥脆可食,余瘦不堪。”知元乃揀取懷孕牛犢及豬羊驢等殺之,其胎仍動,良久乃絕。無何,舜臣一奴無病而死,心上仍暖,七日而蘇。雲見一水犢白額,並子隨之,見王訴云:“懷胎五個月,扛殺母子。”須臾又見豬羊驢等皆領子來訴,見劉司士答款,引楊司馬處分如此。居三日而知元卒亡,又五日而舜臣死。
率更令張文成,梟晨鳴於庭樹,其妻以為不祥,連唾之。文成云:“急灑掃,吾當改官。”言未畢,賀客已在門矣。又一說,文成景雲二年為鴻臚寺丞,帽帶及綠袍並被鼠嚙。有神靈遞相誣告,京師及郡縣被誅戮者數千餘家,蜀王秀皆坐之。隋室既亡,其事亦寢矣。
儀鳳年中,有長星半天,出東方,三十餘日乃滅。自是土番叛,匈奴反,徐敬業亂,白鐵余作逆,博、豫騷動,忠、萬強梁,契丹翻營府,突厥破趙、定,麻仁節、張玄遇、王孝傑等皆沒百萬眾。三十餘年,兵革不息。
調露之後,有鳥大如鳩,色如烏鵲,飛若風聲,千萬為隊,時人謂之“鵽雀”,亦名突厥雀,若來突厥必至,后至無差。
天授中,則天好改新字,又多忌諱。有幽州人尋如意上封云:“國字中‘或',或亂天象,請□中安‘武'以鎮之。”則天大喜,下制即依。月余有上封者云: “‘武'退在□中,與囚字無異,不祥之甚。”則天愕然,遽追制,改令中為“八方”字(圀)。后孝和即位,果幽則天於上陽宮。
長安二年九月一日,太陽蝕盡,默啜賊到并州。至十五日夜,月蝕盡,賊並退盡。俗諺曰:“棗子塞鼻孔,懸樓閣卻種。”又云:“蟬鳴蛁??喚,黍種糕糜斷。”又諺云:“春雨甲子,赤地千里。夏雨甲子,乘船入市。秋雨甲子,禾頭生耳。冬雨甲子,鵲巢下地。”其年大水。
長安四年十月,陰,雨雪,一百餘日不見星。正月,誅張易之、昌宗等,則天廢。
幽州都督孫佺之人賊也,薛訥與之書曰:“季月不可入賊,大凶也。”佺曰: “六月宣王北伐,訥何所知。有敢言兵出不復者斬。”出軍之日,有白虹垂頭于軍門。其夜,大星落於營內,兵將無敢言者。軍行后,幽州界內鴉烏鴟鳶等並失,皆隨軍去。經二旬而軍沒,烏鳶食其肉焉。
延和初七日,太白晝見經天。其月,太上皇遜帝位,此易主之應也。至八月九日,太白仍晝見,改元先天。至二月七日,太上皇廢,誅中書令蕭至忠、侍中岑羲;流崔湜,尋誅之。
開元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夜,大流星如甕,或如盆大者貫北斗,並西北小者隨之。無數天星盡搖,至曉乃止。七月,襄王崩,謚殤帝。十月,土番人隴右,掠羊馬,殺傷無數。其年六月,大風拔樹髮屋,長安街中樹連根出者十七八。長安城初建,隋將作大匠高熲所植槐樹殆三百餘年,至是拔出。終南山竹開花結子,綿亘山谷,大小如麥。其歲大飢,其竹並枯死。嶺南亦然,人取而食之。醴泉雨面如米顆,人可食之。後漢襄楷云:“國中竹柏枯者,不出三年主當之。”人家竹結實枯死者,家長當之。終南竹花枯死者,開元四年而太上皇崩。
開元五年,洪、潭二州復有火災,晝日人見火精赤燉燉,所詣即火起。東晉時,王弘為吳郡太守,亦有此災。弘撻部人,將為不慎,后坐?事,見一物赤如信幡,飛向人家舍上,俄而火起,方知變不復由人,遭爇人家遂免笞罰。
開元八年,契丹叛,關中兵救營府,至澠池缺門,營於谷水側。夜半水漲,漂二萬餘人,惟行網夜樗蒲不睡,據高獲免,村店並沒盡。上陽宮中水溢,宮人死者十七八。其年,京興道坊一夜陷為池,沒五百家。初,鄧州三鴉口見二小兒以水相潑,須臾有大蛇十圍已上,張口向天。人或有斫射者,俄而雲雨晦冥,雨水漂二百家,小兒及蛇不知所在。
洛陽縣令宋之遜,性好唱歌,出為連州參軍。刺史陳希古者,庸人也,令之遜教婢歌。每日端笏立於庭中,呦呦而唱,其婢隔窗從而和之,聞者無不大笑。
卷二
(惡官)
北齊南陽王入朝,上問何以為樂,王曰:“致蠍最樂”。
遂收蠍,一宿得五斗,置大浴斛中。令一人脫衣而入,被蠍螫死,宛轉號叫,苦痛不可言,食頃而死。帝與王看之。
隋末荒亂,狂賊朱粲起於襄、鄧間。歲飢,米斛萬錢,亦無得處,人民相食。粲乃驅男女小大仰一大銅鐘,可二百石,煮人肉以喂賊。生靈殲於此矣。
周恩州刺史陳承親,嶺南大首領也,專使子弟兵劫江。有一縣令從安南來,承親憑買二婢,令有難色。承親每日重設邀屈,甚殷勤。送別江亭,即遣子弟兵尋復劫殺,盡取財物。將其妻及女至州,妻叩頭求作婢,不許,亦縊殺之。取其女。前後官人家過親,禮遇厚者,必隨後劫殺,無人得免。
周杭州臨安尉薛震好食人肉。有債主及奴詣臨安,於客舍遂飲之醉,殺而臠之,以水銀和煎,併骨銷盡。后又欲食其婦,婦覺而遁之。縣令詰,具得其情,申州,錄事奏,奉敕杖一百而死。
周嶺南首領陳元光設客,令一袍褲行酒。光怒,令拽出,遂殺之。須臾爛煮以食客,后呈其二手,客懼,攫喉而吐。
周瀛州刺史獨孤庄酷虐,有賊問不承,庄引前曰:“若健兒,一一具吐放汝。”遂還巾帶,賊並吐之。諸官以為必放,頃庄曰:“將我作具來。”乃一鐵鉤長丈余,甚銛利,以繩掛於樹間,謂賊曰:“汝不聞‘健兒鉤下死’-”令以胲鉤之,遣壯士制其繩,則鉤出於腦矣。謂司法曰:“此法何似-”答曰:“弔民伐罪,深得其宜。”庄大笑。後庄左降施州刺史,染病,惟憶人肉。部下有奴婢死者,遣人割肋下肉食之。歲余卒。
周推事使索元禮,時人號為“索使”。訊囚作鐵籠頭,冪(原註:呼角反)其頭,仍如楔焉,多至腦裂髓出。又為“鳳曬翅“、“獼猴鑽火“等。以椽關手足而轉之,並斫骨至碎。又懸囚於梁下,以石縋頭。其酷法如此。元禮故胡人,薛師之假父,后坐贓賄,流死嶺南。
周來俊臣羅織人罪,皆先進狀,敕依奏,即籍沒。徐有功出死囚,亦先進狀,某人罪合免,敕依,然後斷雪。有功好出罪,皆先奉進止,非是自專。張湯探人主之情,蓋為此也。
羽林將軍常元楷,三代告密得官。男彥瑋告劉誠之破家,彥瑋處侍御。先天二年七月三日,楷以反逆誅,家口配流。可謂“積惡之家殃有餘“也。
周補闕喬知之有婢碧玉,姝艷能歌舞,有文華,知之時幸,為之不婚。偽魏王武承嗣暫借教姬人妝梳,納之,更不放還知之。知之作《綠珠怨》以寄之,其詞曰:“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此日可憐偏自許,此時歌舞得人情。君家閨閣不曾觀,好將歌舞借人看。意氣雄豪非分理,驕矜勢力橫相干。辭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袂傷鉛粉。百年離恨在高樓,一代容顏為君盡。碧玉讀詩,飲淚不食,三日,投井而死。承嗣撩出屍,於裙帶上得詩,大怒,乃諷羅織人告之。遂斬知之於南市,破家籍沒。
周張易之為控鶴監,弟昌宗為秘書監,昌儀為洛陽令,競為豪侈。易之為大鐵籠,置鵝鴨於其內,當中取起炭火,銅盆貯五味汁,鵝鴨繞火走,渴即飲汁,火炙痛即回,表裡皆熟,毛落盡,肉赤烘烘乃死。昌宗活攔驢於小室內,起炭火,置五味汁如前法。昌儀取鐵橛釘入地,縛狗四足於橛上,放鷹鷂活按其肉食,肉盡而狗未死,號叫酸楚,不復可聽。易之曾過昌儀,憶馬腸,取從騎破脅取腸,良久乃死。后誅易之、昌宗等,百姓臠割其肉,肥白如豬肪,煎炙而食。昌儀打雙腳折,抉取心肝而後死,斬其首送都。諺雲“走馬報”。
周秋官侍郎周興推劾殘忍,法外苦楚,無所不為,時人號“牛頭阿婆”,百姓怨謗。興乃榜門判曰:“被告之人,問皆稱枉。斬決之後,咸悉無言。”
周侍御史侯思止,醴泉賣餅食人也,羅告準例酬五品。於上前索御史,上曰:“卿不識字。”對曰:“獬豸豈識字但為國觸罪人而已。”遂授之。凡推勘,殺戮甚眾,更無餘語,但謂囚徒曰:“不用你書言筆語,但還我白司馬。若不肯來俊,即與你孟青。”橫遭苦楚非命者,不可勝數。白司馬者,北邙山白司馬坂也;來俊者,中丞來俊臣也;孟青者,將軍孟青棒也。后坐私蓄錦,朝堂決殺之。
周明堂尉吉頊夜與監察御史王助同宿,王助以親故,為說綦連耀男大覺、小覺云:“應兩角麒麟也。耀字光翟,言光宅天下也。”頊明日錄狀付來俊臣,敕差河內王懿宗推,誅王助等四十一人,皆破家。后俊臣犯事,司刑斷死,進狀三日不出,朝野怪之。上入苑,吉頊攏馬,上問在外有何事意,頊奏曰:
“臣幸預控鶴,為陛下耳目,在外惟怪來俊臣狀不出。”上曰:“俊臣於國有功,朕思之耳。”頊奏曰:“於安遠告虺貞反,其事並驗,今貞為成州司馬。俊臣聚結不逞,誣遘賢良,贓賄如山,冤魂滿路,國之賊也,何足惜哉!”上令狀出,誅俊臣於西市。敕追於安遠還,除尚食奉御,頊有力焉。除頊中丞,賜緋。頊理綦連耀事,以為己功,授天官侍郎、平章事。與河內王競,出為溫州司馬,卒。
成王千里使嶺南,取大蛇八九尺,以繩縛口,橫於門限之下。州縣參謁者,呼令入門,但知直視,無復瞻仰,踏蛇而驚,惶懼僵仆,被蛇繞數匝。良久解之,以為戲笑。又取龜及鱉,令人脫衣,縱龜等嚙其體,終不肯放,死而後已。其人酸痛號呼,不可復言。王與姬妾共看,以為玩樂。然後以竹刺龜等口,遂嚙竹而放人;艾灸鱉背,灸痛而放口。人被試者皆失魂至死,不平復矣。
朔方總管張仁亶好殺。時有突厥投化,亶乃作檄文罵默啜,言詞甚不遜。書其腹背,鑿其肌膚,涅之以墨,炙之以火,不勝楚痛,日夜作蟲鳥鳴。然後送與默啜,識字者宣訖,臠而殺之。匈奴怨望,不敢降。
殿中侍御史王旭,括宅中別宅女婦風聲色目,有稍不承者,以繩勒其陰,令壯士彈竹擊之,酸痛不可忍。倒懸一女婦,以石縋其發,遣證與長安尉房恆奸,經三日不承。女婦曰:“侍御如此,若毒兒死,必訴於冥司;若配入宮,必申於主上。終不相放。”旭慚懼,乃舍之。
監察御史李嵩、李全交,殿中王旭,京師號為“三豹”。
嵩為赤黧豹,交為白額豹,旭為黑豹。皆狼戾不軌,鴆毒無儀,體性狂疏,精神慘刻。每訊囚,必鋪棘卧體,削竹籤指,方梁壓踝,碎瓦搘膝,遣仙人獻果、玉女登梯、犢子懸駒、驢兒拔橛、鳳凰曬翅、獼猴鑽火、上麥索、下闌單,人不聊生,囚皆乞死。肆情鍛煉,證是為非,任意指麾,傅空為實。周公、孔子,請伏殺人;伯夷、叔齊,求其劫罪。訊劾干塹,水必有期;
推鞫濕泥,塵非不久。來俊臣乞為弟子,索元禮求作門生。被追者皆相謂曰:“牽牛付虎,未有出期;縛鼠與貓,終無脫日。妻子永別,友朋長辭。“京中人相要,作咒曰:“若違心負教,橫遭三豹。”其毒害也如此。
京兆人高麗家貧,於御史台替勛官遞送文牒。其時令史作偽帖,付高麗追人,擬嚇錢。事敗,令史逃走,追討不獲。御史張孝嵩捉高麗拷,膝骨落地,兩腳俱攣,抑遣代令史承偽。
准法斷死訖,大理卿狀上:故事,准《名例律》,篤疾不合加刑。孝嵩勃然作色曰:“腳攣何廢造偽。”命兩人舁上市,斬之。
周黔府都督謝祐兇險忍毒。則天朝,徙曹王於黔中,祐嚇雲“則天賜自盡”,祐親奉進止,更無別敕。王怖而縊死。后祐於平閣上卧,婢妾十餘人同宿,夜不覺刺客截祐首去。后曹王破家,簿錄事得祐頭,漆之題“謝祐“字,以為穢器。方知王子令刺客殺之。
周默啜之陷恆、定州,和親使楊齊莊敕授三品,入匈奴,遂沒賊。將至趙州,褒公段瓚同沒,喚庄共出走。庄懼,不敢發,瓚遂先歸。則天賞之,復舊任。齊莊尋至,敕付河內王懿宗鞫問。庄曰:“昔有人相庄,位至三品,有刀箭厄。庄走出被趕,斫射不死,走得脫來,願王哀之。”懿宗性酷毒,奏庄初懷猶豫,請殺之,敕依。引至天津橋南,於衛士鋪鼓格上縛磔手足。令段瓚先射,三發皆不中;又段瑾射之,中。又令諸司百官射,箭如蝟毛,仍氣殜々然微動。即以刀當心直下,破至陰,割取心擲地,仍趌々跳數十回。懿宗忍毒如此。
楊務廉,孝和時造長寧、安樂宅倉庫成,特授將作大匠,坐贓數千萬免官。又上章奏聞陝州三門,鑿山燒石,岩側施棧道牽船。河流湍急,所顧夫並未與價直,苟牽繩一斷,棧梁一絕,則撲殺數十人。取顧夫錢糴米充數,即注夫逃走,下本貫禁父母兄弟妻子。牽船皆令系二釽於胸背,落棧著石,百無一存,滿路悲號,聲動山谷。皆稱楊務廉“人妖“也,天生此妖以破殘百姓。
監察御史李全交素以羅織酷虐為業,台中號為“人頭羅剎”,殿中王旭號為“鬼面夜叉”。訊囚引枷柄向前,名為“驢駒拔橛“;縛枷頭著樹,名曰“犢子懸車”;兩手捧枷,累磚於上,號為“仙人獻果“;立高木之上,枷柄向後拗之,名“玉女登梯”。考柳州典廖福、司門令史張性,並求神狐魅,皆遣喚鶴作鳳,證蛇成龍也。
(異事)
陳懷卿,嶺南人也,養鴨百餘頭。後於鴨欄中除糞,糞中有光 龠々然。以盆水沙汰之,得金十兩。乃覘所食處,於舍後山足下,因鑿有麩金,銷得數十斤,時人莫知。卿遂巨富,仕至梧州刺史。
周長安年初,前遂州長江縣丞夏文榮,時人以為判冥事。張鷟時為御史,出為處州司倉,替歸,往問焉。榮以杖畫地,作“柳“字,曰:“君當為此州。”至後半年,除柳州司戶,后改德州平昌令。榮刻時日,晷漏無差。又蘇州嘉興令楊廷玉,則天之表侄也,貪狠無厭,著詞曰:“回波爾時廷玉,打獠取錢未足。阿姑婆見作天子,傍人不得棖觸。”差攝御史康訔推奏斷死。時母在都,見夏文榮,榮索一千張白紙,一千張黃紙,為廷玉禱,后十日來。母如其言,榮曰:“且免死矣,后十日內有進止。”果六日有敕,楊廷玉改盡老母殘年。又天官令史柳無忌造榮,榮書“衛漢郴“字,曰:“衛多不成,漢、郴二州,交加不定。”後果唱衛州錄事。關重,即唱漢州錄事。時鸞台鳳閣令史進狀,訴天官注擬不平。則天責侍郎崔玄暐,玄暐奏:“臣注官極平。”則天曰:“若爾,吏部令史官共鸞台鳳閣交換。”遂以無忌為郴州平陽主簿,鸞台令史為漢州錄事焉。
周司禮卿張希望,移舊居改造見鬼人,馮毅見之曰:“當新堂下有一伏屍,晉朝三品將軍,極怒,公可避之。”望笑曰:“吾少長已來,未曾知此事,公毋多言。”后月余日,毅入,見鬼持弓矢隨希望后,適登階,鬼引弓射中肩膊間。望覺背痛,以手撫之,其日卒。
周左司郎中鄭從簡所居廳事常不佳,令巫者觀之,果有伏屍姓宗,妻姓寇,在廳基之下。使問之,曰:“君坐我門上,我出入常值君,君自不好,非我之為也。”掘之三丈,果得舊骸,有銘如其言。移出改葬,於是遂絕。
周地官郎中房穎叔除天官侍郎,明日欲上。其夜有廚子王老夜半起,忽聞外有人喚云:“王老不須起,房侍郎不上,后三日李侍郎上。”王老卻卧至曉,房果病,數日而卒。所司奏狀下,即除李回秀為侍郎,其日謝,即上。王老以其言問諸人,皆雲不知,方悟是神明所告也。
北齊稠禪師,鄴人也,幼落髮為沙彌。時輩甚眾,每休暇,常角力騰<走卓>為戲。而禪師以劣弱見凌,紿侮毆擊者相繼,禪師羞之。乃入殿中,閉戶抱金剛足而誓曰:“我以羸弱為等類輕侮,為辱已甚,不如死也。汝以力聞,當佑我。我捧汝足七日,不與我力,必死於此,無還志。”約既畢,因至心祈之。
初一兩夕,恆爾,念益固。至六日將曙,金剛形見,手執大缽,滿中盛筋,謂稠曰:“小子欲力乎“曰:“欲。”“念至乎“曰:“至。”“能食筋乎“曰:“不能。”神曰:“何故“稠曰:“出家人斷肉故。”神因操缽舉匕,以筋食之。禪師未敢食,乃怖以金剛忤,稠懼遂食。斯須食畢,神曰:“汝已多力,然善持教,勉旃!”神去且曉,乃還所居。諸同列問曰:“豎子頃何至“稠不答。須臾於堂中會食,食畢,諸同列又戲毆,禪師曰:“吾有力,恐不堪於汝。”同列試引其臂,筋骨強勁,殆非人也。方驚疑,禪師曰:“吾為汝試之。”因入殿中,橫塌壁行,自西至東凡數百步,又躍首至於梁數四。乃引重千鈞,其拳捷驍武勁。先輕侮者俯伏流汗,莫敢仰視。禪師后證果,居於林慮山。入山數十里,精廬殿堂,窮極壯大,諸僧從而禪者常數千人。齊文宣帝怒其聚眾,因領驍騎數萬,躬自往討,將加白刃焉。禪師是日領僧徒谷口迎候,文宣問曰:“師何遽此來“稠曰:“陛下將殺貧僧,恐山中血污伽藍,故此谷口受戮。”文宣大驚,降駕禮謁,請許其悔過。禪師亦無言。文宣命設饌,施畢,請曰:“聞師金剛處祈得力,今欲見師效少力,可乎“稠曰:“昔力者,人力耳。今為陛下見神力,欲見之乎“文宣曰:“請與同行寓目。”先是,禪師造寺,諸方施木數千根,卧在谷口。禪師咒之,諸木起立空中,自相搏擊,聲若雷霆,斗觸摧折,繽紛如雨。文宣大懼,從官散走,文宣叩頭請止之。因敕禪師度人造寺,無得禁止。後於并州營幢子未成,遘病,臨終嘆曰:“夫生死者,人之大分,如來尚所未免。但功德未成,以此為恨耳。死後願為大力長者,繼成此功。”言終而化。至后三十年,隋帝過并州見此寺,心中渙然記憶,有似舊修行處,頂禮恭敬,無所不為。處分并州大興營葺,其寺遂成。時人謂帝“大力長者“雲。
(異族風俗)
真臘國在驩州南五百里。其俗有客設檳榔、龍腦香、蛤屑等,以為賞宴。其酒比之淫穢,私房與妻共飲,對尊者避之。
又行房不欲令人見,此俗與中國同。國人不著衣服,見衣服者共笑之。俗無鹽鐵,以竹弩射蟲鳥。
五溪蠻,父母死,於村外閣其屍,三年而葬。打鼓路歌,親屬飲宴舞戲一月余日。盡產為棺,余臨江高山半肋鑿龕以葬之。自山上懸索下柩,彌高者以為至孝,即終身不復祀祭。初遭喪,三年不食鹽。
嶺南獠民好為蜜唧。即鼠胎未瞬、通身赤蠕者,飼之以蜜,釘之筵上,囁囁而行。以箸夾取啖之,唧唧作聲,故曰“蜜唧”。
(果報)
梁有磕頭師者,極精進,梁武帝甚敬信之。后敕使喚磕頭師,帝方與人棋,欲殺一段,應聲曰:“殺卻。”使遽出而斬之。帝棋罷,曰:“喚師。”使答曰:“向者陛下令人殺卻,臣已殺訖。”帝嘆曰:“師臨死之時有何言“使曰:“師云:‘貧道無罪。前劫為沙彌時,以鍬剗地,誤斷一曲蟮。帝時為蟮,今此報也。”帝流淚悔恨,亦無及焉。
建昌王武攸寧別置勾使,法外枉征財物,百姓破家者十而九,告冤於天,吁嗟滿路。為大庫長百步,二百餘間,所征獲者貯在其中。天火燒之,一時盪盡。眾口所咒,攸寧尋患足腫,粗於瓮,其酸楚不可忍,數月而終。
乾封年中,京西明寺僧曇暢將一奴二騾,向岐州棱法師處聽講。道逢一道人,著衲帽弊衣,掐數珠,自雲賢者五戒講。
夜至馬嵬店宿,五戒禮佛誦經,半夜不歇,暢以為精進。一練至四更,即共同發,去店十餘里,忽袖中出兩刃刀矛,便刺殺暢。其奴下馬入草走。其五戒騎騾,驅馱即去。主人未曉,夢暢告云:“昨夜五戒殺貧道。”須臾奴走到,告之如夢。時同宿三衛子被持弓箭,乘馬趕四十餘里,以弓箭擬之,即下騾乞死。縛送縣,決殺之。
後魏末,嵩陽杜昌妻柳氏甚妒。有婢金荊,昌沐,令理髮,柳氏截其雙指。無何,柳被狐刺螫,指雙落。又有一婢名玉蓮,能唱歌,昌愛而嘆其善,柳氏乃截其舌。后柳氏舌瘡爛,事急,就稠禪師懺悔。禪師已先知,謂柳氏曰:“夫人為妒,前截婢指,已失指;又截婢舌,今又合斷舌。悔過至心,乃可以免。”
柳氏頂禮求哀,經七日,禪師令大張口,咒之,有二蛇從口出,一尺以上,急咒之,遂落地,舌亦平復。自是不復妒矣。
貞觀中,濮陽范略妻任氏,略先幸一婢,任以刀截其耳鼻,略不能制。有頃,任有娠,誕一女,無耳鼻。女年漸大,其婢仍在。女問,具說所由,女悲泣,以恨其母。母深有愧色,悔之無及。
廣州化蒙縣丞胡亮從都督周仁軌討獠,得一首領妾,幸之。
至縣,亮向府不在,妻賀氏乃燒釘烙其雙目,妾遂自縊死。后賀氏有娠,產一蛇,兩目無睛。以問禪師,師曰:“夫人曾燒鐵烙一女婦眼,以夫人性毒,故為蛇報,此是被烙女婦也。夫人好養此蛇,可以免難。不然禍及身矣。”賀氏養蛇一二年,漸大,不見物,惟在衣被中。亮不知也,撥被見蛇,大驚,以刀斫殺之,賀氏兩目俱枯,不復見物,悔而無及焉。
梁仁裕為驍衛將軍,先幸一婢,妻李氏甚妒而虐,縛婢擊其腦。婢號呼曰:“在下卑賤,勢不自由。娘子鎖項,苦毒何甚!”婢死後月余,李氏病,常見婢來喚。李氏頭上生四處癉疽,腦潰,晝夜鳴叫,苦痛不勝,數月而卒。
荊州枝江縣主簿夏榮判冥司。縣丞張景先寵其婢,厥妻楊氏妒之。景出使不在,妻殺婢,投之於廁。景至,紿之曰婢逃矣。景以妻酷虐,不問也。婢訟之於榮,榮追對之,問景曰:
“公夫人病困,說形狀。”景疑其有私也,怒之。榮曰:“公夫人枉殺婢,投於廁。今見推勘,公試問之。”景悟,問其婦,婦病甚,具首其事。榮令廁內取其骸骨,香湯浴之,厚加殯葬。
婢不肯放,月余而卒。
左僕射韋安石女適太府主簿李訓。訓未婚以前有一妾,成親之後遂嫁之,已易兩主。女患傳屍瘦病,恐妾厭禱之,安石令河南令秦守一捉來,扌旁掠楚苦,竟以自誣。前後決三百以上,投井而死。不出三日,其女遂亡,時人咸以為冤魂之所致也。安石坐貶蒲州,太極元年八月卒。
王弘,冀州恆水人,少無賴,告密羅織善人。曾遊河北趙、貝,見老人每年作邑齋,遂告二百人,授游擊將軍。俄除侍御史。時有告勝州都督王安仁者,密差弘往推索,大枷夾頸,安仁不承伏。遂於枷上斫安仁死,便即脫之。其男從軍,亦擒而斬之。至汾州,與司馬毛公對食,須臾喝下,斬取首級,百姓震悚。后坐誣枉流雷州,將少姬花嚴,素所寵也。弘於舟中偽作敕追,花嚴諫曰:“事勢如此,何忍更為不軌乎“弘怒曰:
“此老嫗欲敗吾事。”縛其手足,投之於江。船人救得之,弘又鞭二百而死,埋於江上。俄而偽敕發,御史胡元禮推之,錮身領回。至花嚴死處,忽云:“花嚴來喚對事。”左右皆不見,惟弘稱“叩頭死罪”,如受枷棒之聲,夜半而卒。
餘杭人陸彥,夏月死十餘日,見王,云:“命未盡,放歸。
”左右曰:“宅舍亡壞不堪。”時滄州人李談新來,其人合死,王曰:“取談宅舍與之。”彥遂入談柩中而蘇,遂作吳語,不識妻子,具說其事。遂向餘杭訪得其家,妻子不認,具陳由來,乃信之。
天后中,涪州武龍界多虎暴。有一獸似虎而絕大,日正中,逐一虎直入人家,噬殺之,亦不食其肉。自是縣界不復有虎矣。
錄奏,檢《瑞圖》乃酋耳,不食生物,有虎暴則殺之。
天后中,成王千里將一虎子來宮中養,損一宮人,遂令生餓數日而死。天后令葬之,其上起塔,設千人供,勒碑號為“虎塔”。至今猶在。
傅黃中為越州諸暨縣令,有部人飲大醉,夜中山行,臨崖而睡。忽有虎臨其上而嗅之,虎鬚入醉人鼻中,遂噴嚏,聲震虎,遂驚躍,便即落崖。腰胯不遂,為人所得。
陽城居夏縣,拜諫議大夫;鄭鋼居閿鄉,拜拾遺;李周南居曲江,拜校書郎。時人以為轉遠轉高,轉近轉卑。
袁守一性行淺促,時人號為“料斗鳧翁雞”。任萬年尉,雍州長史竇懷貞每欲鞭之。乃於中書令宗楚客門餉生菜,除監察,懷貞未知也。貞高揖曰:“駕欲出,公作如此檢校。”守一即彈之。月余,貞除左台御史大夫,守一請假不敢出,乞解。
貞呼而慰之,守一兢惕不已。楚客知之,為除右台侍御史,於朝堂抗衡於貞曰:“與公羅師。”羅師者,市郭兒語,無交涉也。無何,楚客以反誅,守一以其黨配流端州。
黃門侍郎崔泰之哭特進李嶠詩曰:“台閣神仙地,衣冠君子鄉。昨朝猶對坐,今日忽雲亡。魂隨司命鬼,魄遂閻羅王。
此時罷歡笑,無復向朝堂。”
尚書右丞陸餘慶轉洛州長史,其子嘲之曰:“陸餘慶,筆頭無力嘴頭硬。一朝受詞訟,十日判不竟。”送案褥下。餘慶得而讀之,曰:“必是那狗。”遂鞭之。
周定州刺史孫彥高被突厥圍城數十重,不敢詣廳,文符須徵發者於小窗接入,鎖州宅門。及賊登壘,乃入匱中藏,令奴曰:“牢掌鑰匙,賊來索,慎勿與。”昔有愚人入京選,皮袋被賊盜去,其人曰:“賊偷我袋,將終不得我物用。”或問其故,答曰:“鑰匙尚在我衣帶上,彼將何物開之“此孫彥高之流也。
姜師度好奇詭,為滄州刺史兼按察,造搶車運糧,開河築堰,州縣鼎沸。於魯城界內種稻置屯,穗蟹食盡,又差夫打蟹。
苦之,歌曰:“鹵地抑種稻,一概被水沫。年年索蟹夫,百姓不可活。”又為陝州刺史,以永豐倉米運將別征三錢,計以為費。一夕忽雲得計,立注樓,從倉建槽,直至於河,長數千丈,而令放米。其不快處,具大杷推之,米皆損耗,多為粉末。兼風激揚,凡一函失米百石,而動即千萬數。遣典庾者償之,家產皆竭;復遣輸戶自量,至有償數十斛者。甚害人,方停之。
岐王府參軍石惠恭與監察御史李全交詩曰:“御史非長任,參軍不久居。待君遷轉后,此職還到余。”因競放牒往來,全交為之判十餘紙以報,乃假手於拾遺張九齡。
御史中丞李謹度,宋璟引致之。遭母喪,不肯舉發哀,訃到皆匿之。官寮苦其無用,令本貫瀛州申謹度母死。尚書省牒御史台,然後哭。其庸猥皆此類也。
王怡為中丞,憲台之穢;姜晦為掌選侍郎,吏部之穢;崔泰之為黃門侍郎,門下之穢。號為“京師三穢”。
陽滔為中書舍人,時促命制敕,令史持庫鑰他適,無舊本檢尋,乃斫窗取得之,時人號為“斫窗舍人”。
國子進士辛弘智詩云:“君為河邊草,逢春心剩生。妾如堂上鏡,得照始分明。”同房學士常定宗為改“始“字為“轉“字,遂爭此詩,皆雲我作。乃下牒見博士,羅為宗判云:“昔五字定表,以理切稱奇;今一言競詩,取詞多為主。詩歸弘智,‘轉’還定宗。以狀牒知,任為公驗。”
杭州參軍獨孤守忠領租船赴都,夜半急追集船人,更無他語,乃曰:“逆風必不得張帆。”眾大哂焉。
王熊為澤州都督,府法曹斷掠糧賊,惟各決杖一百。通判,熊曰:“總掠幾人“法曹曰:“掠七人。”熊曰:“掠七人,合決七百。法曹曲斷,府司科罪。”時人哂之。前尹正義為都督公平,后熊來替,百姓歌曰:“前得尹佛子,后得王癩獺。
判事驢咬瓜,喚人牛嚼沫。見錢滿面喜,無鏹從頭喝。嘗逢餓夜叉,百姓不可活。”
冀州參軍麹崇裕送司功入京詩云:“崇裕有幸會,得遇明流行。司士向京去,曠野哭聲哀。”司功曰:“大才士。先生其誰“曰:“吳兒博士教此聲韻。”司功曰:“師明弟子哲。”
滑州靈昌尉梁士會,官科鳥翎,里正不送。舉牒判曰:“官喚鳥翎,何物里正,不送鳥翎!”佐使曰:“公大好判,‘鳥翎’太多。”會索筆曰:“官喚鳥翎,何物里正,不送雁翅!”有識之士聞而笑之。
作者張鷟,字文成,號浮休子,史稱“青錢學士”;深州陸澤(今河北深縣北)人。生卒年不詳,大致在武則天到唐玄宗朝前期,以詞章知名,下筆神速,當時連新羅、日本等國也頗聞其名。今存著述除此書外,張氏尚有《龍筋鳳髓判》和《遊仙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