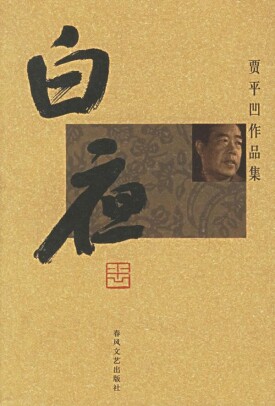共找到7條詞條名為高老莊的結果 展開
高老莊
賈平凹所著長篇小說
《高老莊》是中國當代現實主義作家賈平凹的長篇小說之一。小說敘述了教授高子路攜妻西夏回故里高老莊給父親弔喪,於是與離婚未離家的子路的前妻菊娃、地板廠廠長王文龍、葡萄園主蔡老黑以及蘇紅等發生了錯綜複雜的感情糾葛。書中寫了大生命、大社會、大文化三個空間,又溶入最底層、最日常、甚至有些瑣屑的生活流程。
講述了大學教授高子路回到高老莊與往昔故人之間所發生的錯綜複雜的情感糾紛,體現了封閉守舊的環境所導致的人的退化和改革開放對人的改良。高老莊是一個具有傳奇色彩的村莊,據說那裡的人是最為純正的漢人,可是卻偏偏矮小而粗俗,甚至一代不如一代,這些與高子路的妻子對村莊的退想形成了強烈的反差。高老莊是高子路的故鄉,為了給父親做三周年的祭奠,高子路同妻子西夏從省城回到了故鄉。原本接受高等教育成為大學教授的他回到村子后,再次接觸到舊的文化、舊的環境和舊的人群立刻使他回到了從前,開始變得保守、自私。此時的高老莊儼然成了一面魔鏡,照出了高子路骨子裡所固有的習慣,各種衝突和矛盾接踵而至。
在二十世紀末與二十一世紀初之交,中國內陸陷入改革困境與轉型困境,深蓄已久的社會矛盾與衝突轉入顯性層面與頻發勁發時期,人和社會將前往何方,改革前途何在,農村前景何在,民族前途又何在,作家對這一特殊時期的種種社會現象進行了獨立思考。在這一種世紀末情緒下,現時代之人的精神困境和生存困境、人種困境、文化困境、資源開發和環境保護問題、社會分化和潰敗問題進行了整體觀照,並體現出相當的深度與前瞻性。社會上網路上新聞媒體上熱議的諸多焦點問題,或可一窺端倪,如崇拜下的政績工程、基層政權的貪腐問題、權利與市場的奇異結合、現代企業與資源消耗的衝突、現代工業造成的環境污染、貧富差異過大及其衍生物仇富行為、弱小的社會力量與強大的政治經濟力量之間的博弈與較量、傳統社會道德基礎被摧毀而新道德信仰未引進下的道德冷漠與墮落。
高子路
十五年前,父親送子路到省城去上學。他帶著高老莊人特有的矮體短腿,在省城讀完了大學,也在高老莊男人的矮體短腿的自卑中培養了好學奮鬥的性格,成為一位教授。文化身份和生活環境的改變,城鄉生活方式和文明形態的巨大反差,使他在心理情感上更傾向於認同城市文明,力圖遠離乃至擺脫鄉土文化的羈絆,此時的子路甚至可以說產生了一種逃避鄉土、尋求精神突圍的焦慮。小說寫子路大學畢業留在省城后,便開始看不慣菊娃的神態舉止,數說她不注意打扮,恨不得按照城市女人的標準一下子把她改造的盡善盡美。菊娃不能接受這種改造,認為是子路在開始嫌棄她,於是彼此的感情裂痕日益擴大。子路在精神苦悶與焦慮中戀上了一個城市女人,初嘗了城市現代女性的滋味,喜不自禁。菊娃發現了他的婚外戀,無法容忍,大鬧不止,結果乾脆離了婚。子路發誓要找一個自己最滿意的讓外人企羨的老婆,以此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心理思維和族種,正巧就認識了西夏。他窮追不捨,終於達到了目的。西夏高大漂亮,開朗熱情,是非常富有現代感的城市女性,這使子路感到很得意、很滿足,在情感生活上非常投入。然而城市生活並沒有完全改變子路的文化心理,在他的意識深處,仍然潛存著深深的自卑感:從表面看是來自於形體上的作為高老莊人矮體短腿的自卑;從深層看則是根源於鄉土出身的文化身份的自卑。雖然他的戶籍關係是城裡人,他的文化身份是大學教授、高級知識分子,但在精神上卻依然漂泊無歸,並沒有能尋找到安妥自己靈魂的精神家園。因此仍然會時時想到高老莊,想到菊娃和兒子,時時感到靈魂不安。
蔡老黑
蔡老黑從性格、行為到遺傳基因,全面呈現了“黑”的多向指征。是一個有家事妻妾的人,但是卻喜歡上了二菊,二人偷偷私下發生了姦情,由於二菊和子路是夫妻,最後又因蔡老黑與妻子離婚,於是二人最後走到了一起。在滿是“矮子”、“矬子”的高老莊,“凶神惡煞”的蔡老黑不僅“顯得高”,而且“長得黑”,“很囂張”,像“黑社會頭兒”,是人們“惹不起”的“惡人”。且不論普通村民,即使是這幾年“勢做得大”的村支書順善,同樣不敢也不想“得罪”失了勢的蔡老黑。信用社主任老賀對“土匪”式欠賬、賴賬的蔡老黑也唯恐避之不及。不光活著的怕蔡老黑,死了的也怕蔡老黑。“老實疙瘩子”得得的鬼魂上了“殺豬佬”雷剛媳婦的身,雷剛儘管殺氣滿身卻束手無策,但蔡老黑一來,三言兩語,就斥退了鬼魂。蔡老黑就這樣以一個黑惡分子的面目在眾人敬佩、畏懼的目光與心理期盼中登場亮相。
西夏
城市中的美女,身材高大苗條,為人傲嬌,喜歡有本事的人,然後陰差陽錯的走進了高子路的生活,高子路為了自己的慾望,由於高子路是教授,也還挺有本事,在他花了各種辦法的下成功追到了西夏,於是西夏和高子路回到了高老莊,西夏在高老莊很快就淪陷,丟棄了城市中所謂的節操,陷入了各種情事和權利的爭奪中,思想逐漸腐化,最終落魄的離開了高老莊。
蘇紅
《高老莊》開篇,蘇紅未見其人先聞其聲的出場方式,頗得《紅樓夢》里“鳳辣子”的真傳。子路攜西夏回高老莊剛到鎮街,“忽聽得有人叫他”,扭頭看時,街面上並沒有個熟人,轉身要走,那聲音又是兩下,這才看到街對面的二層木樓上站著一個女人是蘇紅,轉眼間,蘇紅就“噔噔噔”地從樓梯上跑了下來了。而在全書的高潮部分,蘇紅孤身守廠的行為,首當其衝地讓湧來轟廠子的人群大吃一驚,“他們壓根兒沒有想到廠里還敢有人,而且竟然是蘇紅!”面對瘋狂失控的局面與凶神惡煞的蔡老黑,蘇紅毫不畏懼,響應蔡老黑的“激將”,毅然下樓走出廠大門,瀟灑地站在了老黑的面前。這一舉動讓一向膽大包天的老黑“也明顯地愣了一下,舉止有些失態”。老黑惡語辱罵、揭她老底的時候,蘇紅更是無視力量的懸殊,“一下子撲過去抓破了蔡老黑的臉”。對朋友的熱辣,對敵人的毒辣,這兩極“火”一般的熱度,成為蘇紅的性格氣質標籤。一個弱女子在男性社會的叢林中闖蕩,要想成功,必須對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瞭然於心,並具備超出一般女子的生理和心理素質。毫無疑問,蘇紅具備了這一軟實力。毫無背景的“農二代”蘇紅,其事業的風生水起與財力的暴發猛增,取決於她所具有的能幹、堅強、勇敢、開朗、豪放、柔媚等個人素質。當然,物極必反,一旦這些素質被蘇紅推向極致,就開始反向運行,無限靠近潑辣、放蕩、不擇手段、為富不仁等負面性,為其蒙上了一層遭人詬病的曖昧色彩。故而,受官場寵幸和群眾巴結的蘇紅,人前是名副其實的紅人,人後卻備受非議。
《高老莊》中畫家西夏和大學教授高子路是一對恩愛夫妻,西夏隨子路回子路的故鄉高老莊給父親過三周年祭日。在高老莊生活的日子裡,溫文爾雅、感情細膩的大學教授高子路逐漸暴露出背負官方和民間雙重傳統文化重負的知識分子的弱點:心胸狹窄,做事粘糊,缺乏勇氣和魄力,遇事趨利避害,不敢挺身而出,主持正義。而高老莊農民蔡老黑卻逐漸讓西夏領略到了“農民英雄”的魅力。他敢做敢為、敢愛敢恨、敢出乖露醜、敢承受失敗,優秀民間傳統文化給予他的粗獷、活力、勇氣和胸懷最終贏得了西夏,使西夏寧可為了他滯留在高老莊,而讓子路一人孤獨傷心地返回省城。這些人物之間關係的變化,實際上反映了幾種文化的碰撞交融及其各自的命運走向。西夏最初選擇子路的原因雖然作品交待不多,但從菊娃(子路前妻)對子路離而不舍、蘇紅對子路有所傾心可以看出,她們共同傾心的是子路才學豐富、感情細敏、心地善良,這是民間和官方雙重傳統文化積極一面影響的結果,所以說,西夏最初選擇的是子路身上的傳統文化中積極的一面。最後她寧可為了蔡老黑與子路鬧崩,也不是她想拋棄因襲傳統文化而致虛弱的子路,實在是她更想幫助代表優秀民間傳統文化的雖有多種弱點但卻充滿活力和勇氣的蔡老黑。從子路這一面說,他選擇離開西夏和高老莊,而且對著爹的墳哭著說:“我也許再也不回來了”,這說明,一方面,因襲了雙重傳統文化重負的他無法面對優秀民間傳統文化那逼人的力量,另一方面,他對自己身上已經烙印上的一切無能為力。如果說子路的前途讓人感到擔憂的話,那麼西夏和蔡老黑的前途卻讓人不由得歡欣鼓舞。作品通過西夏最後為了幫助蔡老黑而不惜失去工作的態度表達了這樣的文化含義:蔡老黑身上的來自民間優秀傳統文化的勇氣、力量加上西夏身上精英文化的開闊的視野,以及他們所共同具有的正直、善良的品質,一定能使兩種文化共同飛升到一個新的境界,那或許會成為一股改造中國現實,創造中國未來的了不起的力量。
在高老莊人眼中,命運的力量無所不在。高子路離異了菊娃,再娶了西夏,子路娘認定“這都是命”。菊娃也對高子路說:“咱倆走到這一步都是命,我現在信了命了。”蔡老黑這樣的硬漢子在一旦經歷一連串不如意的事之後,也感嘆“實在是天要滅我哩么”。這說明在人的背後,一種個人力量無法控制的東西在主宰著人生。在大自然、社會面前,個人的力量往往顯得微乎其微。在人與天即自然、社會的關係中,人既可以勝“天”,“天”亦可以勝人。它們之間的關係是錯綜複雜的。而在人類還不能完全征服自然之前,人類勢必受到“大自然的力”的左右。石頭的畫和迷胡叔的醜醜花鼓也是作品中體現濃厚的社會、人生哲理意味的意象。石頭的畫“羅列人生種種,如吃飯,挖地,游水,打獵,械鬥,結婚,生育等等,最後走進墳墓。埋人墳墓之後的`死人,又爬山,趕驢。人都是侏儒。”形象地再現了人的生命過程以及人的缺陷,寓哲理於平淡之中。迷胡叔唱的“人無三代富,清官不到頭”,短短的十個字,卻包含了無限的哲理意味,體現出濃重的歷史感和蒼涼感。俗話說:“三窮三富不得到老”。這是就單個人的一生而言的。說明人生命運無常,貧賤窮達難以自料,人的一生總要幾經沉浮。放寬到一個家族而言,富貴榮華也不是不散的誕席。強盛的家族最終要走向衰敗。強盛時,勢不可待,衰敗時,勢不可擋,一個家族的命運也必然在幾經衰榮的歷史循環中受到前定。歷史總是無情地與人類鬧彆扭,給人類留下的往往是悲哀。至於“清官不到頭”溉蘊含有人生哲理,又包孕著社會哲理。清官首先要好人做,然而無論如何,清官卻做不到頭,結果不是被撤換,就是被殺頭。歷史上的清官往往沒有好下場,他們的命運可悲可嘆。從社會看,清官儘管為普通老百姓所擁戴,然而他們卻不能為黑暗勢力所容忍,他們的力量極其有限,在與邪惡的抗爭中屢屢失敗,成為悲壯的犧牲品。社會生活部是那樣的複雜,正義的一方往往鬥不過邪惡的一方,理性的力量往往被醜惡的黑暗現實所踐踏,古往今來,人類的歷史多是在這樣的一種非理智、非正義的狀態下運轉而來,使人類自身困惑不已。迷胡叔在許多高老莊人看來是瘋子,實際上他卻是最清醒的一個人,他對社會、對歷史、對人生有一種極其深邃的洞見。因此他的醜醜花鼓竟象遠古歌謠那樣沉重、蒼涼、令人泣下石難怪作者一而再、再而三地把這首蒼涼的歌謠貫穿於整個小說之中,使整部小說都打上了濃厚的悲劇色彩。它既是人生的悲涼,也是社會的悲涼。高老莊這一意象顯示的第三層涵義,在於它從人類與自然、社會的關係上,展示了人類命運的他律性,特別是呈現了由人類自身的局限性帶來的人類命運的悲劇性,充滿了哲理的睿智。這同時是一種深刻的人類意識,體現了人的自覺意識的進步,是主體意識高揚的結果。
《高老莊》敘述從還鄉始,離鄉終,構成了一個顯形的圓形結構。其間,又分別以子路和西夏為支點,進行了多重圓環形的亞敘事。作為主要的聚焦人物,高子路的雙重身份帶出小說敘事框架的兩個圓:第一個圓是作為農民的子路,他的還鄉與離鄉;第二個圓是作為知識分子的子路,他的離城和返城。這兩個圓環環相套,彼此交錯,填充著豐滿著作品整個的大圓。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農民,子路在高老莊長大到考上大學才離開家。這裡的風土人情、生活習慣、審美愛好、價值判斷都給他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成為他終生難以去掉的胎記,而他對於故鄉又是帶著知恩必報的虔誠之心。所以,子路一踏上高老莊的土地,就感到那樣熟稔和親切。他帶著炫耀和自誇的口吻興緻勃勃地向西夏介紹家鄉的地形風貌、千年古柏。在和堂兄弟們聊家常時,他自覺地把自己還原為高老莊的農民,那樣本色、質樸。若不是他身邊時時出現美麗現代的妻子西夏,你從外形和言談舉止上,都難以把他和周圍的農民區分開來。這裡既有樹高千尺、不忘根本的赤子之情對他的理性約束,更有他天生就是一個高老莊人的天性流露。在為亡父做三周年祭日的事情上,他甚至帶著感激之情聽從順善的布置安排,虔誠地按照鄉俗禮節,做著每一項繁瑣的事情。極盡人倫的責任和義務。在為南驢伯選墓址時,他耐心地“陪著陰陽師跑了一天”。選地形看風水,出錢出力,盡心盡責。他所受到的現代科學教育讓位於血濃於水的親情。農民哄搶太陽坡林子,子路知道“這是要犯法的”,但儒家的中庸之道使他只是勸兄弟不要去,“別人砍伐讓別人砍伐去”,這樣無力的勸阻自然沒有人肯聽他的,包括他的妻子。等第二天他知道了別人都砍了很多樹時,潛伏在內心深處的那種農民的佔有慾被重新激活,他躍躍欲試地對妻子說:“我要是還是農民,我昨晚能弄回來個屋大梁,”農民砸搶地板廠是一起惡性事故,而子路卻畏首畏尾,不敢挺身而出。他的猶豫軟弱使他失去了村民們和西夏的信任,也給他帶來了更大的矛盾和苦惱。面對排解不開的紛擾,他唯一的辦法只有出逃,逃離高老莊。至此,賈平凹完成了小說的第一重圓形敘事。與之相聯繫相重疊的還有第二個圓,這就是子路的第二重身份。
在《高老莊》中,賈平凹的藝術理念是藉助人的倫理關係的淡化,還原出人的社會性存在的本質一般來,由此他強化了對變化不居的生活形態的“本色”繪摩,以便削弱主體對敘事的干擾和控制,寫人狀物於是留下了大量富有“暗示”性的筆觸以及鮮活的象徵、隱喻化的筆墨。晨堂這個人物的敘事描畫和勾勒就非常傳神,體現了賈平凹獨到的創作技巧。他是形、神兼備,因為他常常不經意地出現,尤其是在敘事漸趨平淡之際,表面上看,他無非是供人展覽、增添笑料,其實起到了活躍氣氛、盤活全局的敘事調度效果,巧妙地促成文本的場景轉換及其情節的更迭。而他具體發揮的這重作用,乃是由他的可鄙和醜陋的性格所引發的。舉凡他足跡所至,議論蜂起,他都會對特定的生活場景造成“反諷”似的敘事壓力。對生活秩序的維護者,對風俗習慣的醜陋處,對人心世道予以意想不到的調侃。他擔著糞筐參與“哄搶”地板廠的行為本身,即含蓄地道明了敘事人看待高老莊這樁大事件的意識和看法。賈平凹對高老莊人文生態環境本色似的總體化還原,多是藉助這種敘事技巧實現的。
《高老莊》的作者於意象中凸出的現實關懷與歷史反觀已使作品的思致顯得相當厚重,可他並不滿足於此。在高老莊這一意象里,作者還灌注了他對人類命運的哲理沉思。意象化了的高老莊,透示著濃厚的形而上意味。在大自然面前,人類的力量是弱小的。人類餐常處於一種無形的外在力量的控制之中`直到如今,高老莊人還沒有擺脫這種神秘的氛圍。被甲嶺的崖崩、白塔的倒塌均暗示著冥冥之中有一種看不見的神秘力量存在。這種神秘力量讓高老莊人感到好奇和有趣,更讓他們深感困惑和恐怖。高老莊人認為,這些奇怪的現象將給他們帶來災禍。對於這種力量,高老莊人至今還處在未知狀態,深感無可奈何。可是高老莊人又不能也無法否認這種神秘力量的存在,不能簡單地將它歸結為迷信或者荒誕無稽。這種力量可以被人感受,但卻無法使人捉摸。在這種神秘力量面前,人類顯露出它自身的弱點和悲劇性。作品中作者從未對它進行過正面的敘寫,但通過多次側面的渲染,白雲鍬便顯得異常神秘。在高老莊人中,去過白雲漱探險的人微乎其微。高子路爺爺的爺爺去過,可是“去了再沒有回來”。蔡老黑耍本事,領著省里的一個人去了一下白雲揪前溝口的白雲寺,結果省城的人再沒回來,蔡老黑“差點也沒要了他的命”—陰差陽錯地坐了二年牢。迷胡叔僅到過白雲寨下邊的山溝,回來后竟精神失常,變成了瘋子。白雲揪對高老莊人來說,簡直是一個聳人聽聞的所在,是一個不祥的所在,高老莊人故而對它諱莫如深。
《高老莊》作整體考察和深層透視,不難發現,賈平凹以“黑”、“紅”、“白”作為敘事色線、色塊與色帶,勾畫出了世紀之交中國鄉村政治經濟文化生態的整體形貌與色彩。隨著深陷其中的各類色彩主角蔡老黑、蘇紅、王文龍等人物的命運走向,這三種色彩力量在高老莊這一特定敘事語境中展開了糾纏、博弈與交鋒。民間的“黑”力量守護的中國傳統鄉村面臨著必然的衰敗,新生官商組合的“紅”力量也在市場化與現代化進程中染上了數度積累的社會經濟沉痾,神秘的“白”力量的天然威權則面臨著現代理性的挑戰。三色力量均處在一種與現代的緊張關係之中,無法徹底消滅對方,只是在複雜的交互作用中不斷延展傳統與現代、城市與鄉村、情感與理性、現實與超驗之間的張力。
《高老莊》中以文化寓言的方式繼續訴說著自己無可挽回的沉淪。首先,高老莊人矮體短腿的形態特徵預示著漢民族人種的退化。小說中西夏不止一次嘲笑高老莊人的矮小。她戲言子路娶她是為了換種,而兩人在高老莊打算生育的計劃卻一再遭遇障礙,子路性能力的退化恰恰是漢民族文化無法得到拯救的寓言。其次,小說中子路的兒子石頭,具有某種神秘的預知本領,他超人的智慧與殘廢的雙腿組成了另一則文化寓言。石頭雖是高老莊人,但由於他無法站立,因此不具備高老莊人短腿的外形特徵,這是否意味著殘廢的雙腿與超常的智慧存在著邏輯上的因果關係,只有放棄高老莊人,也就是漢民族短腿的形態特徵,才會實現真正意義上的人種進化,即擁有超常的智慧。高老莊作為傳統文化的象徵,它的封閉自守已經讓它走入了絕境。小說安排了一個頗有寓意的結尾,作為儒家文化化身的子路在經歷了“精神還鄉”的種種洗禮之後急於想回到城市,他撕掉了記載高老莊方言土語的筆記本以示他與精神家園的決裂,與傳統文化的決裂。看來,傳統文化在現今不僅不能抵抗現代文明的進攻,而且它的某些合理成分的喪失還預示著它必將為現代文明所吞噬。
《高老莊》既有困窘的一面,又有焦灼的一面,愈來愈觸及到歷史的深層,很多作家,具有一種大家風範的作家,並不是能給故事按部就班的進軍,而是在無序的人生中經歷相互衝撞的分化,大浪淘沙,最後成為以新代舊,完成新時代的更替。賈平凹的《高老莊》比起以往的作品有所超越,正是在這一點上有所領悟,對多種使人類困窘的境遇滲透其中,然而對未來的召喚都是鮮活的有生氣的,這才是深沉有致的作品。
————青海編輯社編導李雪梅
《高老莊》中最吸引人的地方莫過於人物之間的性格衝突。此書中所寫的人物繁多,卻雜而不亂,以致於雖然都是寫這些社會最基層的卑微的人,卻又能像蘆溝橋上的獅子一樣,各有自己的獨到之處,且能反映出其共同的特徵──愚昧和倒退。在人物的選排上,作者也頗費心思。
————山東大學文學系教授劉階耳

賈平凹
1973年,開始發表作品。1975年,畢業於西北大學中文系。1982年起,從事專業創作。1986年,出版長篇小說《浮躁》 。1987年,出版長篇小說《商州》 。1988年,憑藉《浮躁》獲得第八屆美孚飛馬文學獎銅獎。1992年,創刊《美文》。1993年,出版長篇小說《廢都》 。1995年,出版長篇小說《白夜》 。1996年,出版長篇小說《土門》 。1997年,憑藉《廢都》獲得法國費米娜文學獎。1998年,出版長篇小說《高老莊》 。2000年,出版長篇小說《懷念狼》 。2002年,出版長篇小說《病相報告》 。2003年,擔任西安建築科技大學人文學院院長、文學院院長。2005年,出版長篇小說《秦腔》。2007年,出版長篇小說《高興》 ;同年,憑藉《秦腔》獲得第七屆茅盾文學獎。2011年,出版長篇小說《古爐》 。2014年,出版長篇小說《老生》 。2018年4月,出版長篇小說《山本》 ;同年,當選西咸新區作家協會名譽主席。2019年9月23日,長篇小說《秦腔》入選“新中國70年70部長篇小說典藏” 。2020年9月,出版長篇小說《暫坐》和《醬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