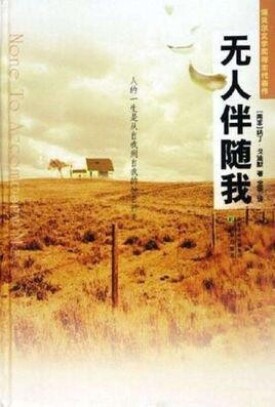無人伴隨我
無人伴隨我
《無人伴隨我》是南非女作家納丁·戈迪默於1994年發表的一部長篇小說。從故事層面看,小說的情節並不複雜,它主要圍繞女主人翁維拉·斯塔克展開,描述了白人斯塔克一家以及他們的黑人朋友迪迪穆斯·馬庫馬一家在南非從種族隔離制度到白人統治即將滅亡的這一歷史過渡時期的命運,充分展示了人物在他們所生活的那個時代和社會中的複雜性和多樣性。
故事描述了描述了白人斯塔克一家以及他們的黑人朋友迪迪穆斯·馬庫馬一家在南非從種族隔離制度到白人統治即將滅亡的這一歷史過渡時期的命運。
從社會屬性看,維拉是一名資深的白人律師,她不僅同情黑人,支持他們的解放運動,而且她經常通過法律的手段爭取為黑人們贏得土地和生存的權利。在種族隔離期間,她曾冒著被逮捕的危險藏匿過黑人解放運動的骨幹,幫助他遞送過信件。在黑人解放運動獲勝、新政府即將成立的時期,她積極參與政治活動,是國家憲法問題技術委員會的委員。她曾一針見血地指出,“一部憲法是一種權利法在法律上的實踐?是的,我已經發現實際上公正的意思是聆聽那些人想出來的主意,這些人想要繼續抓住校力、欺騙的權力,為了得到合法性他們會不擇手段”由此可見,她在政治上十分敏銳,並且堅持公正的立場和原則,是深受他人尊重的律師。
但是,從生物的屬性看,她又是一個放蕩的女人。在她第一個丈夫出去打仗期間,她被另一個美貌的男子貝內特(簡稱本)引誘,在山區度假時就開始與他做愛。等她的丈夫征戰回家時,他發現原本的那個家已經不屬於他。離婚後,維拉保留了前任丈夫的房屋。但在她與她第一個丈夫最後一次在深夜會面時,她又剋制不住自己的情慾,與他做愛,結果她與第二個情人—丈夫貝內特正式結婚時,腹中懷的孩子卻是第一個丈夫的孩子。貝內特原本想當一名雕塑藝術家,但終究未能如願以償。為了給他心愛的女人維拉提供錢財,他放棄了對藝術的追求,轉向經商,開辦了一家名叫“推銷的行李”的公司,銷售高檔皮箱等商品,但最後也以破產告終。
斯塔克夫婦生有一男一女,第一個是兒子伊凡,他實際上是維拉第一個丈夫的孩子,第二個是女兒,取名阿尼克。由於在她少年時期得不到真正的母愛(那時候她母親正忙著與別的男人做愛),她產生了強烈厭惡男人的感覺,這最終導致她成了一名女同性戀者。兒子伊凡去英國倫敦發展,成了一名很成功的銀行家,但在個人生活上,也因感情問題而離異。可以說,斯塔克一家並不是一個幸福的家庭。貝內特早就知道維拉一直與別的男人有性關係,但由於他深愛著妻子,所以一直無法離開她。他反覆強調,沒有她,他無法生活。直到最後,在他經商以破產而宣告失敗后,他才真正意識到維拉對他其實沒有多少感情,他終於在孤獨中離開了維拉,到倫敦去找兒子(其實伊凡並不是他的兒子)。
小說描述的另一個家庭是迪迪穆斯·馬庫馬之家。迪迪穆斯(簡稱迪迪)是黑人為奪取政治權力而開展的解放運動的領導人之一。他和妻子西邦賈伊爾(簡稱賽莉)長期在國外流亡。迪迪從事的地下工作連他的妻子都不十分清楚。他們可以說是一對同志/伴侶的夫妻,他們為了共同的事業而奮鬥。他們的女兒姆福,出生在英國,操一口流利的英語。
在黑人解放運動取得勝利后,他們一起凱旋歸來。父親迪迪穆斯擔任了國家行政高級官員,母親西邦賈伊爾也開始在政府部工作,女兒姆福上的是當地一所好學校。夫妻之間生活上互相關心體貼,事業上互相信賴支持。在婚姻生活和個人情感方面,黑人馬庫馬夫婦與白人斯塔克夫婦似乎是鮮明的對比。同時,馬庫馬一家似乎是一個幸福的家庭。
但事情並未就此結束。在解放運動獲得勝利后的選舉中,迪迪穆斯落選了,而西邦賈伊爾卻進入了高層領導之中。這是因為時間和場所改變了,現在解放運動需要的不是滲透和破壞,而是談判、重建以及獲得國際承認和資助。這樣的角色,迪迪穆斯已不再勝任,而西邦賈伊爾以她的熱情和能力,正好大有用武之地。此時,迪迪穆斯不僅有種失落感,而且解放運動處於政治需要,為了證明自己有能力對過去所做的事情進行反省和自我譴責,竟然要求迪迪穆斯公開為自己過去在扣留營中當審訊官時所做的事情認罪,他成了政治鬥爭所需要的犧牲品。在丈夫遇到困難的時候,妻子西邦賈伊爾非但沒有十分體貼地去安慰丈夫,反而對他表示出某種嫌惡的情緒,因為她對自己的政治地位十分敏感。
西邦賈伊爾最終擔任了政府部門的要職,但她同時被一些白人極端組織列入暗殺者名單,一直處於有生命危險的狀態。女兒姆福也遇到了麻煩,在斯塔克太太舉行的一次晚宴上,她認識了維拉在法律基金會的一位名叫奧帕的同事,他是一個黑人青年(同時也是維拉的情人)。姆福瞞著父母與這位已有妻子和孩子的年輕黑人交往,並懷上他的孩子。事發后,這對青年男女被強迫分開。維拉與賽莉的關係也因此一度冷卻了下來,直到維拉與奧帕在一次活動中遭遇搶劫受傷后,她們才開始恢復交往。
在貝內特離開后,維拉賣掉了那幢伴隨了她幾十年的房子,搬到一位名叫澤夫·拉皮尤拉納的黑人朋友家中,在他房屋的附屬建築里獨自走完了在這個世界上的人生之路,無人伴隨著她。
20世紀80年代,南非國內黑人民族解放運動如火如荼,國際社會不斷向種族隔離政府施壓,再加上持續十多年的經濟停滯,南非國民黨的統治已是四面楚歌,窮途末路。1989年,長期鼓吹種族隔離制度的總統波塔辭職,戴克拉克上台,新總統很快宣布南非“政府準備廢除允許地方當局在公共場所執行種族隔離的分離設施法”。
1990年2月2日,戴克拉克又宣布解除南非解放運動組織的禁令。9天後,曼德拉獲釋。這標誌著種族隔離制度在南非正式廢除,南非進入后種族隔離時代。
隨著南非由種族隔離社會向後種族隔離社會的轉變,長期關注南非現實的戈迪默於1994年發表了長篇小說《無人伴隨我》。
維拉
女主人公維拉是資深律師,支持黑人解放運動,經常通過法律的手段乃至冒著生命危險為黑人們爭取土地和生存的權利,但她的私生活卻極不光彩,出軌成性,最後只能獨自走完人生之路。
迪迪穆斯
《無人伴隨我》里最為孤獨的人該是迪迪穆斯——一個心懷夢想卻最終無法實現的人。迪迪穆斯是南非反對種族隔離政策的鬥士,解放陣線的重要革命者。可是在勝利后的新政府機構選舉中,他出乎意料地落選。不僅如此,他隨後還又成為新政府自我反省自我譴責的犧牲品。
作為南非文壇的巨肇,戈迪默展示給讀者的是一個處於特殊的時間與場所中的複雜世界,其中的人物也是複雜的、多樣的。由於各種政治、種族、信仰等原因,他們似乎無法真正地溝通,彼此信任與關愛。政治鬥爭、種族偏見、信仰危機始終伴隨著小說中的人物,使他們感到孤獨與絕望。他們中不少人都是在孤獨中走過他們的生命之旅,這就是這部小說展現給我們的那個世界中的人間故事。顯然,戈迪默在這部小說中流露出的悲觀色彩與她生活的時代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可以說,它是她生活其中的那個特殊國家和時代的藝術寫照。
從《無人伴隨我》看,在戈迪默的思想中,新南非政治正義的實現,不僅要求白人的物質妥協與現實努力,也不僅要求建構黑人女性的主體性,給予黑人女性以性別正義,更要求政治上勝利的全體黑人正確處理即將到來的權力,避免新南非陷入黑人自己製造的另一種壓迫中。
對於戈迪默來說,維拉這一虛構的人物身上,恰恰寄寓了現實白人在新南非存在的政治合法性。戈迪默相信,后種族隔離時代的南非白人,不可能僅僅通過真相與仟悔來獲取寬恕與和解。南非白人應該還南非黑人以物質正義;他們必須選擇站在黑人一邊,為黑人的權力而鬥爭。南非白人的典範只能是維拉這樣的人,而不是那些天天在教堂里和電視上懺悔自己罪惡,又在現實中抓住既得利益不放的人。戈迪默相信,只有有了維拉這樣的人,“白人們儘管在過去胡作非為,仍被未來所接受”;只有有了維拉這樣的人,“膚色和種族可以算不了什麼,坐在(政府)座位上的代表們可以是不同的膚色,而不是純黑色。”
小說中,西邦賈伊爾是一個具有非洲之母色彩的原型人物,她是非洲民族文化的保存者和傳承者。雖然長期流亡歐洲,但是這位具有祖魯族和索托族血統的黑人女性,依然頑強地保存著對南非傳統文化的熱愛。當女兒姆福已經能熟練地把倫敦時尚和非洲風情在自己的服飾上熔為一爐時,西邦賈伊爾卻堅持要她學習古老的祖魯族語。她對女兒說:“我們已經遠離了我們的根,不僅僅由於流亡……接受你的語言吧。”在西邦賈伊爾看來,無論全球化的趨勢如何大潮洶湧,歐洲的時尚如何絢彩奪目,南非的文化和傳統都必須一代代傳承下去。在敘述手法上,戈迪默沒有對文化傳承這樣的宏大命題施以濃墨重彩,而是舉重若輕地將其置於一對黑人母女貌似不經意的對話間,這種微言大義反倒更能提醒讀者去反思黑人女性對於南非的意義。
戈迪默在塑造主人公維拉,反映其內心世界時,採用的主要技巧是自由聯想。自由聯想是意識流技巧中員常見的表現形式。意識流,確切地說是—個心理術語,意識是人腦對客觀物質世界的反映,是感覺、思維等各種心理過程的總合。在現代英美小說中,意識流被用來表現西方人的複雜心態與悲觀情緒,通過揭示那個痛苦的“自我”來反映社會生活的現實”。自由聯想“並非脫離實際的胡思亂想”。恰恰相反,它往往受到某種客觀對應物的刺激和影響。此外,它與人物的個人經歷和心理狀態有著密切的聯繫。
作者採用的另一敘述技巧則是自由間接引語和自由直接引語的大量使用,並且在使用過程中將它們大量的交錯並置。
由於自由直接引語和自由間接引語的形式特徵,使得它們可以和敘述者的敘述語自然流暢的融合在小說里,讀者能隨著敘述者敘述視角的轉換而自由出人人物的內心世界,頻繁的穿梭於三個世界——作者所處的現實世界、小說人物所處的文本世界以及人物的內心世界。同時,這也凸現了維拉思維意識的跳躍性。現實的存在物和其他人的談話隨時都可能打斷維拉的思緒,從而使她做出聯想和回憶,以及對現實與存在作一系列的思考。這也正是南非社會的動蕩性和不確定性在維拉思想意識里的反映。
在直接引語中,作者摒棄了傳統的引號而代之以破折號。在戈迪默看來,雙引號給人的感覺就是“把人物實際所說的與小說框架分離了”,而破折號的好處就在於“破折號更快捷,更深刻恰當”。在她看來,在說話人說話和聽者做出反應之間有一個“停頓”,破折號這一視覺象徵比引號更能表現這一停頓”。破折號除了標誌人物對話以外,它在小說中還起到了闡釋說明的作用。在需要解釋說明的地方,戈迪默直接採用破折號引入評論語或是解釋性的語句。破折號的大量使用,使得敘事者的評述語、敘述語和人物的內心想法混在一起,在形式上使得讀者無法區分出哪些是人物的談話,哪些是人物的內心獨白,哪些是敘述者的評述,必須要做細緻的分析。這使得讀者很“迷惑”,他們往往需要“倒回去重讀一兩行。才能明白”。正因為此,讀者在閱讀時才不得不努力在這三個交替並置的世界中,做出自己的理解和闡釋,從而加深了對作品現實意義的理解。
戈迪默是一位語言大師,作品中經常出現一些詩一般的描寫、繪畫一般的情景:“夜裡她躺在她所選擇的男人的懷裡,帶著在黑暗中想象出的她可能會有的各種生活,重複著那些她正在學習的精確的法律陳述,而這些陳述猶如彩帶在她去夢鄉的路上從她的頭腦中愉快地飄過。”
納丁·戈迪默,1923年11月20日生於約翰內斯堡附近的礦業小鎮斯普林斯。父親是立陶宛人,母親是英國人,均系猶太裔。戈迪默先後在一所修道院學校和維特沃特斯懶得大學讀書。她從小個性獨立,九歲就開始學習寫作,十五歲時便在南非的一家刊物上發表短篇小說。十年之後,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說集《面對面》(1949)問世。幾年之後,首部長篇小說《說謊的日子》(1953)亦出版。戈迪默的主要作品包括十部長篇小說和十部短篇小說集。同時她還著有三部評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