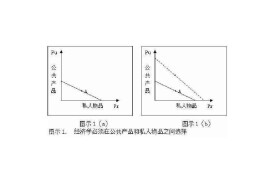燈塔經濟學
燈塔經濟學
燈塔出現在經濟學家的著作中,是因為它可能有助於理解政府的經濟功能問題。它常被作為必須由政府提供而不是由私人企業提供的物品的一個例子。經濟學家們通常似乎認為,由於不可能向受益於燈塔的船隻的所有者收取可靠的費用,任何私人或企業建造和維修燈塔就不可能遍及贏利。
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在他的《政治經濟學原理》一書的“自由放任或不干預原理的基礎和限制”一章中寫道:
……為了確保航行的安全,建造和維修燈塔、設置浮標等屬於政府適當的職責。由於不可能向受益於燈塔的海上船隻收取使用費,沒有人會出於個人利益的動機而建造燈塔,除非由國家的強制徵稅給予補償。
亨利·西奇威克在他的《政治經濟學原理》一書的“生產關係中自然自由的體系”一章中這樣寫道:
……在大量的各種各樣的情況下,這一論斷(即通過自由交換,個人總能夠為他所提供的勞務獲得適當的報酬)明顯是錯誤的。首先,某些公共設施,由於它們的性質,實際上不可能由建造者或願意購買的人所有。例如,這樣的情況經常發生:大量船只能夠從位置恰到好處的燈塔得到準備處,燈塔管理者卻很難向它們收費。庇古在《福利經濟學》中借用了西奇威克的燈塔例子作為非補償性服務的例子:在那裡,“邊際凈產出小於邊際社會凈產出,因為它會給技術上很難向其索取報酬的第三方帶來額外的服務。”
保羅·薩繆爾森在他的《經濟學》一書中,比那些早期作家更直截了當。在“政府的經濟作用”這一節中,他寫道:“政府提供某些無可替代的公共服務,沒有這些服務,社會生活將是不可想象的。它們的性質決定了由私人企業提供是不合適的。”作為“簡明的例子”,他列舉了國防、國內法律和秩序的維持,以及公正的契約的執行,並在一個腳註中進一步寫道:
這是政府服務的最新例子:燈塔。它們保全生命和貨物。燈塔管理者很難向船主收取使用費。因此,這部高深的著作將說明:“私人利益和貨幣成本”(正如一個想靠建燈塔發財的人所看到的)與真正的社會利益和成本(將被保全的生命和貨物與(1)燈塔的總成本和(2)讓更多的船隻看到警告燈塔的額外成本相比較)是存在差異的。哲學家和政治家一般都承認在“私人利益和社會利益存在外部經濟差異”的情況下政府的必要作用。
後來,薩繆爾森再次提到燈塔“由於外部經濟效應而成為政府的合理活動”。他寫道:
考察上面提到的為了警告礁石而設置的燈塔。它的光亮有助於每個看到它的人。企業家不會為了贏利而建造它,因為要向每個使用者收費會引起極大的困難。這肯定是政府要從事的一種事業。
薩繆爾森並沒有到此為止,他還用燈塔來說明另一個論點(一個早期作家沒有論述過的論點)。他寫道:
……在燈塔的例子中,應該注意一件事:燈塔管理者不能很容易地以銷售價格的形式向受惠者收費這一事實使燈塔成為某種社會或公有物品。但即使燈塔管理者 ——假定通過雷達跟蹤——能向每一個附近的使用者收費,這一事實本身並不能保證燈塔服務能象根據市場價格而提供的私有物品那樣,以社會最優的方式提供出來。為什麼?因為容許更多的船隻使用燈塔的社會成本是零附加成本。因此,由於避免付費而遠離燈塔水域的任何船隻代表著社會的經濟損失——即使向一切船隻收費,其價格的總和也並不會大於燈塔的長期開支。如果燈塔從社會的觀點上看來是值得建造和維修的——它不一定是應該的——較為高深的著作能夠說明為什麼這種社會的物品應該以最優的方式給予一切人。
在薩繆爾森的論點中有一個悖論。因為私人企業不可能為它們的服務收費,所以必須由政府提供燈塔。但如果私人企業收費是可能的,也不允許它們這樣做(這也假定應由政府來做)。薩繆爾森的立場完全不同於穆勒、西奇威克和庇古的立場。讀了這些作家的著作,我發現收取燈塔使用費的困難是對燈塔政策產生重要影響的關鍵所在。他們不反對收費,因此,如果能夠這樣做,他們也不反對私人經營燈塔。然而,穆勒的觀點有點模稜兩可。他認為,政府應該建造和維修燈塔,因為既然不可能讓受益的船隻支付使用費,所以私人企業就不願意提供燈塔服務。但是他附加了一個限制性的短語:“除非由國家的強制徵稅給予補償。”我認為,“強制徵稅”是一種向受惠於燈塔的船隻施加的壓力(實際上,強制稅就是使用費)。穆勒的說明模稜兩可的根本之處是,他的意思到底是“強制徵稅”使出於個人利益動機建造燈塔成為可能,因而不必由政府經營,還是對私人企業家來說是不可能的(或不值得的),所以“用強制徵稅來補償,因而需要由政府經營”。我的觀點是,穆勒是持前一種解釋的。如果這是正確的,那它代表著他的建造和維修燈塔是“政府的適當職責”觀點的一個重要的限制條件。在任何情形下,似乎很明顯,穆勒原則上並不反對收取使用費。西奇威克的觀點並沒有解釋上的問題。然而,它的含意也非常清楚。他寫道:“這樣的情況經常發生:大量的船只能夠從位置恰到好處的燈塔得到益處,然而卻很難向它們收費。”這並不是說收費是不可能的。它的意思恰恰相反。它是說受益於燈塔的大部分船隻逃避付費的情況很可能發生,而不是說不可能出現這樣的情形:燈塔的受益大部分由比較容易向其徵稅的船隻享用,它意味著在這些情形中,收取使用費是合乎需要的——這使私人經營燈塔成為可能。
我認為,如果沒有關於英國燈塔制度的知識,就很難確切理解穆勒、西奇威克和庇古的意思,因為雖然這些作者可能不熟悉英國燈塔制度如何運行的細節,毫無疑問,他們知道它的一般性質,而且在寫作有關燈塔的內容時,他們心中肯定意識到這一點。有關英國燈塔制度的知識不僅能使我們更好地理解穆勒、西奇威克和庇古,而且可以為評價薩繆爾森有關燈塔的論述提供背景材料。
英國建造和維修燈塔的機構是領港公會(在英格蘭和威爾士)、北方燈塔委員會(在蘇格蘭)和愛爾蘭燈塔委員會(在愛爾蘭)。這些機構的開支由通用燈塔基金撥出。這項基金的收入來源是由船主繳納的燈塔稅。燈塔稅的繳納和報表管理由領港公會負責(在英格蘭、威爾士、蘇格蘭和愛爾蘭均可繳納),而具體的徵稅由港口的稅務局完成。從燈塔稅得來的錢屬於通用燈塔基金,由商業部控制。燈塔機構向通用燈塔基金領取它們的開支。
商業部和各燈塔機構的關係有些類似於財政部和英國政府部門的關係。這些機構的預算必須經商業部批准。三個機構的預算方案必須在聖誕節期間提交給商業部,而且需要每年在倫敦召開的燈塔大會上加以審議。除了這三個燈塔機構和商業部外,出席大會的還有燈塔諮詢委員會——即代表船主、水險商和貨運者的船運協會(一個商業協會)的委員會——的成員。燈塔諮詢委員會儘管沒有法定的權力,然而在討論過程中卻起著重要的作用。燈塔機構在制定預算時,商業部在決定是否通過預算時都要考慮它的意見。燈塔稅的標準由商業部決定,以使在某一年限內的稅收收入足夠維持支出。但是在制定工作規劃和改變原有安排時,大會的參加者,特別是燈塔諮詢委員會的成員必須考慮新的工作規劃和改變原有安排對燈塔稅標準的影響。
徵收燈塔稅的根據在1898年頒布的商業船運(商業船舶基金)法的第二細目表中有說明。雖然後來理事會條例對燈塔稅標準及其中的某些方面作了修改,目前的徵稅結構基本上是1898年確定的。對於在英國到港或離港的一切船隻,每個航次每噸的納稅標準有極大的不同。“內航”船隻一年內10個航次之後就不再繳納燈塔稅。“外航”船隻6個航次之後就不再納稅。這兩類船隻的收稅標準不同,如果船的體積相同,“內航”船隻10個航次所繳納的稅額近似等於“外航”船隻6個航次所繳納的。某些船隻每噸納稅率比較低,如超過100噸的帆船及巡航船。拖船和遊艇按年納稅而不是按航次納稅。而且,有些船隻可免繳燈塔稅:屬於英國或外國政府的船隻(運載貨物或乘客的除外),漁船,底卸式船和挖泥船,小於100噸的帆船(遊艇除外),小於20噸的所有船隻(包括遊艇),只裝底貨的、等待燃料煤的、裝補給品的和避免海險的船隻(拖船和遊艇除外)。所有這些條例都有限制條件,但它們足以說明條例的性質。
目前的情況是,英國燈塔服務的支出由通用燈塔基金撥出,該基金的收入來源於燈塔稅。基金除用於大不列顛和愛爾蘭的燈塔開支外,還用於某些殖民地的燈塔維修和建造、清除殘骸的支出,雖然這隻佔總支出的很小一部分。燈塔也有一部分開支不是由基金撥出的。如果“地方性的燈塔”只使某些使用特定港口的船隻受益,它的建造和維修開支就不由基金支出,基金被限於通常為了“一般航行”的燈塔的財政開支。“地方性的燈塔”的支出通常由港務局撥款,由港口稅彌補。
英國燈塔制度的演變歷史
穆勒在1848年的著作和西奇威克在1883年的著作中,就他們心目中存在的英國燈塔制度而言,他們肯定想到的是早期的情況。為了理解穆勒和西奇威克,首先應該了解19世紀英國燈塔制度的一些情況和它的演變方式。然而,研究英國燈塔制度的歷史不僅有助於我們理解穆勒和西奇威克,而且能夠幫助我們開闊眼界,了解提供燈塔服務的各種可資利用的制度安排。在討論英國燈塔服務的歷史時,我僅限於英格蘭和威爾士,因為這兩地的燈塔制度是穆勒和西奇威克最為熟悉的。
英格蘭和威爾士主要的燈塔機構是領港公會。它也是英國最主要的領港機構。它經營療養院,為海員及其妻子、寡婦、孤兒管理慈善基金。它還負有許多職責,例如,檢修“地方性的燈塔”,為法庭的海事案例聽證會提供海事顧問和領港船長。它是包括倫敦港務局在內的港口委員會的成員。領港公會的成員在許多委員會 (包括政府委員會)中供職,處理海運事務。
領港公會是一種古老的制度。它大概是從中世紀經海員行會演變而來的。1513年,一份要求成立行會的請願書提交給亨利八世,1514年頒發了許可證書。證書賦予領港公會以領港管理權。這一權力和慈善事業在許多年中一直是領港公會最主要的工作。直到很久以後,它才考慮到燈塔本身。
17世紀以前,英國幾乎沒有燈塔,即使到18世紀燈塔也並不多見。然而,確實存在各式各樣的航標。大多數標誌設在岸上,並非特意用於導航的。這些標誌包括教堂和尖塔、房屋和樹叢等。浮標和信標也作導航之用。哈里斯解釋說,信標並不是燈塔,而是“立在岸邊或海灘上,或許是頂端裝有老式籠的柱子”。16世紀初,航標的管理和信標的提供由海軍大臣負責。為了提供浮標和信標,他指派代表向受益於這些航標的船隻收費。1566年,領港公會被賦予提供和管理航標的權力。它們也負責監督私人航標的管理。例如,一個不經允許就砍伐作為航標的樹叢的人將被責以“假公濟私”的罪名,“並將被處以100英鎊的罰款(罰款收入由國王和領港公會平分)。1566年的法令在是否給予領港公會在水面上設置航標的權力的問題上似乎還存有疑慮。這一疑慮在1594年被消除了,當時,海軍大臣將浮標和信標的管理權轉給港領公會。這些工作實際上是如何進行的並不清楚,因為1594年以後海軍大臣繼續負責管理浮標和信標,但後來領港公會在這些領域內的權威似乎被承認了。
17世紀初,領港公會在卡斯特和洛威斯托夫特設置了燈塔。但是直到該世經末,它才建造了另一座燈塔。同時,私人也在建造燈塔。哈里斯寫道:“伊麗莎白社會的一個基本特徵就是,那些公共工程的擁護者表面上是為了公共福利,但實際上卻是為了謀私利。燈塔也沒有逃脫他們的注意。”後來他寫道:“洛威斯托夫特的燈塔完工之後,領港公會的會員就心滿意足不再幹了……。1614年2月,300名船長、船主和漁民請求他們在溫特托立一座燈塔,他們好像什麼也沒幹。對這類請求充耳不聞,不僅動搖了行會的信心,而且既然存在著贏利的前景,所以這等於邀請私人投機者插手。不久他們就這樣做了。”1610—1675年間,領港公會沒有建造一座燈塔,而私人建造的至少有10座。當然,私人建造燈塔的要求使領港公會很為難。一方面,領港公會希望自己成為建造燈塔的唯一的權威機構;另一方面,它又不願意用自己的錢建造燈塔。因此,它反對私人建造燈塔的努力。但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它沒有成功。哈里斯評論道:“燈塔建造者是這一時期投機者的典型代表。他們主要不是出於公共服務的動機。……愛德華·科克爵士1621年在國會上的演講對此提供了有力的依據:‘像船工一類的工程建設者表面一套,實際另一套:他們聲稱是為了公共福利,其實是為了個人。’”困難之處在於,出於公共服務動機的人沒有建造一座燈塔。正如哈里斯後來寫到的:“應該承認,燈塔建造者的最初動機是個人利益,但至少他們能完成建造燈塔的任務。”
私人避免侵犯領港公會法定權力的辦法是從國王那裡獲得專利權。國王允許他們建造燈塔和向受益於燈塔的船隻收取使用費。具體的做法是由船主和貨運主遞交一份請願書,聲稱他們將從燈塔獲得極大的好處並願意支付使用費。我認為,簽名是通過正常渠道徵集的,而且毫無疑問,它們代表了人們的心裡話。國王有時可能授權他們使用專利權以作為他們為他效勞的回報。後來,經營燈塔和徵收使用費的權力由國會通過法令授予個人。
燈塔使用費由所在港口的代理者(它可能代理幾座燈塔)收取,這種代理者可以是個人,但通常是海關官員。每座燈塔的使用費是不同的。船隻每經過一座燈塔,就根據船隻的大小繳納使用費。每個航次每噸收費比率有一個通常的標準(如1/4或1/2便士)。後來,刊載有不同航程所要經過的燈塔相應收費標準的名冊發行了。
同時,領港公會實行了一項既能保住權力又能保住錢財(甚至可能博研聯盟)的政策。領港公會申請經營燈塔的專利權,後向那些願意自己出資建造燈塔的私人出租,並收取租金。私人租借的先決條件是保證進行合作而不與領港公會作對。
這樣的一個例子就是建造和重建坐落在普利第斯海岸14英里礁石上的或許是英國最著名的伊迪斯通燈塔。D·阿蘭·史蒂文森評論道:“1759年在燈塔史上寫下了最富戲劇性的一章:為了抵禦海浪的衝擊,建造者們表現了高度的事業心、才幹和勇氣。”1665年,英國海軍大臣收到一份要求在伊迪斯通礁石上建造燈塔的請願書。領港公會評論道:這雖然值得,“但幾乎是不可能的”。私人企業編年史作者塞紹爾·斯邁爾斯寫道:“……以前,任何一個膽大包天的私人冒險家都不在伊迪斯通礁石上建造燈塔,那裡的海面上連石頭影子都看不到,連一小塊可以站立的地方都沒有。”1692年,沃爾特·懷特菲爾德提出一項建議,領港公會和他達成一項協議。協議規定:他建造燈塔,領港公會分享一半利潤。然而,懷特菲爾德卻沒有著手這項工程。他將他的權利轉讓給亨利·溫斯坦利,後者在1696年與領港公會談判后達成一項協議。協議規定:他得頭五年的利潤,以後50年領港公會分享一半利潤。溫斯坦利造了一座燈塔,後來又造了一座來代替它。燈塔於1699年完工。然而,1703年的一場大風暴把燈塔沖走了。溫斯坦利、燈塔管理員和他手下的一些工作人員都送了命。那時這座燈塔的總造價為 8000英鎊(全部由溫斯坦利負擔),收入為4000英鎊。政府給予溫斯坦利的遺孀200英鎊的撫恤金和每年100英鎊的養老金。如果燈塔必須由具有公益心的人來建造,那麼在伊迪斯通礁石上將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燈塔。但是,私人利益又一次佔了上風。有兩個人,洛維特和拉迪亞德決定再造一座。領港公會援引國會法令賦予的重建和收費的權力,同意向新的建造者出租這一權力,而且條件比溫斯坦利優惠——租期為99年,每年租金為100英鎊,全部利潤歸建造者。燈塔於1709年竣工,它一直工作到1755年才毀於一場大火。租約還有50年才到期。燈塔的權利轉入他人之手。新的所有者們決定進行重建,他們邀請了當時最偉大的工程師約翰·斯米頓。他決定全部用石頭建造,而以前的燈塔是木結構的。燈塔於1759年建成。它一直工作到1882年才被一座領港公會新建的燈塔所代替。
如果我們考察一下19世紀初的情況,就可以理解私人和私人組織在英國的燈塔建設中所起的重要作用。1843年燈塔委員會在它的報告中聲稱,在英格蘭和威爾士有42座燈塔(包括浮動燈塔)屬於領港公會;3座燈塔由領港公會出租給個人;7座燈塔由國王出租給個人;有4座燈塔是起初根據專利權後來根據國會法令屬於私人業主。也就是說,在總共56座燈塔中,有14座由私人或私人組織經營。在1820一1834年間,領港公會建造了9座新的燈塔,購買了5個租給個人的燈塔(除了那9座新建的燈塔之外,又在伯恩漢新建了2座燈塔以替代1座買回的燈塔),購買了3座屬格林威治醫院所有的燈塔(它們是約翰·梅爾德倫爵士在1634年左右建造的,后根據他1719年的遺囑贈送給格林威治醫院)。1820年的情況是,24座燈塔由領港公會經營,22座由私人或私人組織經營。但領港公會的許多燈塔原先不是由他們建造的,而是通過購買或租約到期而得到的(伊迪斯通燈塔就是一個例子,租約於1840年到期)。1820年24座由領港公會經營的燈塔中,12座燈塔是租約到期的結果,1座是1816年由切斯特理事會轉讓的。所以,1820年46座燈塔中只有11座是領港公會建造的,而34座是由私人建造。
由於領港公會的主要建塔活動開始於18世紀末,因此在早期,私人燈塔的地位甚至更為重要。關於1786年的情形,D.A.史蒂文森寫道:“很難評價領港公會對當時英國海岸燈塔的態度。根據它的行動而不是它的主張來判斷,行會建造燈塔的決心從來都不是很堅決的:1806年以前,只要有可能,它就把建造燈塔的權利租讓給承租人。在1786年,它控制著四個地方的燈塔:卡斯特和洛威斯托夫特(這兩處用地方性的浮標使用稅來管理),溫特森和西西里(行會在這兩處立塔是為了阻止個人利用國王專利權收取使用費謀利”)。
然而,至1834年,正如我們所見,領港公會經營著總共56座燈塔中的42座。那時,議會強烈支持領港公會購買私人燈塔的建議。這項建議由下議院小型特別委員會於1822年提出。不久,領港公會開始購買某些私人燈塔。1836年,議會的法令把英國所有的燈塔授予領港公會,領港公會有權購買剩留在私人手中的燈塔。這一工作到1842年完成。從那以後,除“地方性的燈塔”外,在英國不再有屬於私人所有的燈塔了。
1823—1832年間,領港公會花費了74,000英鎊購買了向弗拉索爾姆、費爾思斯、伯恩漢、北福雷蘭茲和南福雷蘭茲地方出租的燈塔。1836年法令公布之後,購買剩餘的私人燈塔花費了近1,200,000英鎊,其中大筆費用是用來購買斯莫爾斯燈塔(租約還有41年到期)和其他三座燈塔:蒂瑪茅斯、斯伯思和斯克略斯(根據議會法令,它的租約還沒有到期)。購買這4座燈塔的費用為:斯莫爾斯,170,000英鎊;蒂瑪茅斯,125,000英鎊;斯伯恩,330,000英鎊;斯克略斯,445,000英鎊。這些費用的數目極大:購買斯克略斯的445,000英鎊等於(根據權威機構的估計)今天的 700—1000萬美元,而它可能產生的收益比今天要高得多(因為稅收水平較低)。因此,我們發現這些人不僅——用薩繆爾森的話來說——“靠經營燈塔而發了一筆大財”,而且確實很成功。
從《下議院小型特別委員會1834年報告》中可以了解到支持領港公會集中管理一切燈塔的理由:
本委員會吃驚地獲悉,燈塔建造在英國各地屬於完全不同的系統。管理機構不同,燈塔稅率和稅額不同,徵收的原則也不同。本委員會發現,燈塔建造這項對英國海軍和商業至關重要的事業,不是在政府的直接監督下進行,由統一部門領導,由富有責任心和遠見卓識、並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和最節約的計劃保證航運安全的人民公僕管理,而是放任自流,那燈塔只能在海難之後,應地方的要求,慢吞吞地建造起來。所有這些或許可以看作是我們偉大國家的恥辱。過去以至現在,燈塔的建造在很大程度上是作為向國家貿易徵稅的手段,為了少數幾個人的利益,他們正享受著國家給他們的這種特權。
本委員會認為,在任何時候,不必要地向我國的任何產業部門徵稅都是不合理的。向航運業徵稅尤其不合理,因為這使它和其他國家的航運業進行不平等競爭時處於很不利的地位。本委員會議為,航運業應免掉向其公開徵收的不必要的每種地方稅和不公平稅。
因此,本委員會強烈建議,在任何情況下,燈塔稅應該降到與管理現有的燈塔和浮動燈塔,或建造和管理國家商業和航運所必需的新燈塔相適應的最低限度。
管理當局無視各獨立機構持續不斷地攫取大量收入(與上述的原則相反);他們名義上是收取燈塔稅,支付管理燈塔的費用,實際上是為少數幾個人謀私利,以達到那些在建造燈塔時不曾考慮到的目的。對此,本委員會不得不表示遺憾。本委員會特別反對重訂出租某些燈塔契約的做法。12年來,下議院小型特別委員會一直呼籲議院對這一問題加以注意……
雖然這一報告特彆強調現有管理的不合理之處,認為某些私人燈塔管理不善,但是可以肯定,堅持將燈塔統一由領港公會管理的主要理由是認為這樣做會降低燈塔稅。當然,這種建議認為燈塔的開支應由國庫支出,這將導致廢除燈塔稅。但這辦不到。在這裡,我們對此不作討論。
令人費解的是,為什麼由領港公會統一管理燈塔就能降低燈塔稅。這種觀點可以在互補壟斷理論中找到某些依據,然而古諾到1838年才發表他的分析著作,所以它不會影響這些關心英國燈塔的人們的觀點,儘管他們比經濟學家更快地認識到古諾的分析著作的重要性。沒有任何理由認為統一管理能使燈塔稅有任何下降。因為要向燈塔的前所有者提供補償,就需要一筆和以前同樣數目的款項。正如領港公會所指出的,由於“作為借款償還的擔保,燈塔稅就被抵押了出去,……在債務還清之前,燈塔稅不能廢除”。實際上,在1848年貸款清償之後,燈塔稅也沒有降低。
另一個降低燈塔稅的方法是領港公會放棄經營自己所有的燈塔所得的凈收入。這筆錢當然用於慈善事業,主要用來資助退休的海員、他們的寡婦和孤兒。燈塔稅的這種用途在1822年和1834年受到議會委員會的反對。1834年委員會特別提到救濟院扶養著142人。有8431個男人、女人和小孩領到年金36先令至30英鎊的資助。它建議正在接受養老金的人繼續接受,直到去世為止,但不增加新的名額,然而實際上卻沒有這樣做。
1853年,政府提議燈塔稅不要再用於慈善事業,領港公會在向國王提交的報告中聲稱,這項收益是它的財產,這和私人業主的燈塔的情況是一樣的(而私人業主由此得到了補償):
國王和立法機構過去一直通過特許狀把燈塔的管理權委託給領港公會。特許狀沒有在任何方面改變作為私人行會的法人團體的法律地位,除了它必須管理燈塔作為獲此特權的條件。行會的法律地位在國王和公眾看來與燈塔稅和其他特權(例如市場、港口和集市等)授予個人的法律地位沒有差別。認為行會負有把燈塔稅降低到管理費用——包括或不包括建造的成本——的永久的法律責任而無用於其他用途的觀點,是完全沒有根據的,而且是不合法律的。如果在頒布特許狀時燈塔稅是合理的,那麼它將繼續有效,儘管由於船運的增加,燈塔稅將產生利潤。特許狀仍是有效的。在這裡,國王是為了大眾的利益,如果那時是合理的,以後則不可撤回。……行會對它們所建造燈塔的所有權與私人業主的所有權同樣有效……而且,將收益的一部分用於慈善事業,使行會的權利至少與私人的權利同樣值得考慮。……屬於領港公會的燈塔和燈塔稅,就行會的目的而言,在嚴格的意義上,是它們用於這些目的的財產。……政府的建議似乎主張這一大筆財產應該給船主,除管理燈塔的開支外其他一概不收。它看似行會的慈善之舉,其實卻是財產的轉讓,而這財產是為了死去的船長和海員的利益,為了他們的家庭,對船主們來說是財產的遺贈品。
這份報告提交給貿易委員會,貿易委員會嚴厲地批評了領港公會的意見:
上議院議員們絲毫不懷疑領港公會聲稱屬於它所有的財產的權利。但是,……行會的情況與個人的情況存在著這樣一個差別:行會擁有財產必須,至少就燈塔稅而言,是為了大眾的利益。因此必須考慮到公共政策的實際情況。議員們不認為為了公共目的的減稅違反財產原則,其中沒有任何既得利益者分享稅收收入。它向國王陛下某一階層的臣民徵稅,而這個階層卻沒有得到任何適當好處作為回報(任何超過管理燈塔的必要支出的燈塔稅就屬於這種稅)。這種減稅不僅沒有違反財產原則,而且是最公正、最有益的。議員們不認為用燈塔的剩餘收入資助窮海員和他們的家屬有任何既得利益的動機,因為個人特權得以保全的既得利益的本質是大家和法律所熟知的。議員們真誠地對已經發放的養老金或其他福利工作不進行絲毫干涉。他們認為不把現在任何人都無權得到的權利給予新的個人,根據公共政策的理由,並不是公正的……議員們認為,燈塔管理費應由燈塔使用費支付。用前一代人為了保護船隻避免觸礁而繳納的收入建造的燈塔應該是今天在英國海岸航行的人們的自然而公正的遺產。他們應該自由地享有環境所能允許的儘可能低的收費標準,其他的任何考慮都不應該成為問題。
燈塔稅用於慈善事業的做法於1853年停止。結果,這使燈塔稅的降低成為可能,價格更接近邊際成本,而且無數默默無聞的海員和他們的家屬的待遇變得更糟。而我們發現,由領港公會統一管理所有的燈塔並不一定會帶來這一後果。
這種變化是1853年調整的一部分,這一調整就是設立商業海洋基金。燈塔稅(和一定數量的其他款項)提供給該基金,該基金用於經營燈塔的支出和其他涉及航運的開支。1898年,這一制度又有所變化,即取消了商業海洋基金,設立通用燈塔基金。這項基金全部由燈塔稅提供,它僅用於燈塔服務的管理。同時,計算燈塔稅的制度也簡化了。每個航次的納稅不再像以前那樣根據船隻經過能夠獲益的燈塔的數目而定。1898年所確定的基本上就是第二節中描述的籌資和管理制度。當然,細節上稍有變動,但制度的基本特徵自1898年以來一直保留了下來。
結論
英國燈塔制度的概況及其演變表明,從穆勒、西奇威克和庇古的論述中所得到的結論有很大的局限性。穆勒似乎認為,假如類似英國燈塔的籌資和管理制度這類事物沒有建立起來,那麼燈塔的私人管理是不可能的(大多數現代讀者可能並不是這樣理解他的)。西奇威克和庇古認為,假如存在受益於燈塔而卻不能向其收費的船隻,那麼政府就必須加以干預。然而,受益於英國燈塔卻沒有繳納使用費的船隻主要是那些不在英國港口停靠而由外國船主管理的船隻。在這種情況下,不清楚所需要的政府行動的性質是什麼,也不清楚政府應該如何行動。例如,儘管俄國、挪威、德國和法國政府的船隻並沒有在英國停泊,這些政府是否必須繳納使用費?或者是否必須支付給英國通用燈塔基金一筆稅款?或者還是由英國政府拿出部分稅收支付給燈塔基金以彌補外國政府沒能繳納的缺額?
文中有關英國燈塔制度的論述只是揭示了某種可能性。早期的歷史表明,與許多經濟學家的信念相反,燈塔的服務可以由私人提供。那時,船主和貨運主可以向國王申請允許私人建造燈塔並向受益的船隻收取(規定的)使用費。燈塔由私人建造、管理、籌資和所有。他們可以立遺囑出賣和處置燈塔。政府的作用局限於燈塔的產權的確定與行使方面。使用費由燈塔的代理人收取。產權執行問題對他們與對向船主提供貨物和勞務的供給者並無二致。產權只有在其調節使用費價格這一點上起著異乎尋常的作用。
後來,英格蘭和威爾士的燈塔委託給領港公會,一個對公眾負責的私人組織,但費用繼續由船隻的燈塔使用費支付。薩繆爾森所熱衷的制度——由政府從普通稅中籌措資金,從來沒有在英國實行過。這種政府籌資的制度並不一定要排除私人企業建造和管理燈塔,但它似乎不允許私人擁有燈塔(除非是很小的形式),這與持續到19世紀30年代末的英國的體制有很大的出入。
燈塔是經濟學中常用的一個例子。不同的經濟學家以燈塔為例來說明自己的某種經濟理論。所以,“燈塔經濟學”並不是象“發展經濟學”或者其他經濟學一樣的經濟學分支,而是圍繞燈塔所提出的各種經濟理論。
公有產權的必要性
二十世紀英國劍橋學派最後一名代表人物A·C·庇古以燈塔為例說明了市場的失靈,以及政府干預的必要性。無論庇古本人的原意是什麼,從庇古的燈塔中得出的推論就是:公有產權是必要的。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要消費兩類不同性質的物品:私人物品與公共物品。
私人物品是那些由私人企業生產並出售的產品,它的特點在於消費中的排他性。例如,一雙鞋子不能同時供兩個人穿,某人吃了一隻蘋果,其他人就不能吃。要消費這種物品就必須支付貨幣以換取其所有權與消費權。因此,這種物品就可以由私人企業來生產,並通過市場定價進行交換。市場調節機制對這類物品是適用的。公共物品的特點則在於消費中的非排他性。這就是說,這種物品一旦生產出來就無法排斥那些不為此物付費的人進行消費。正因為如此,有些經濟學家把公共物品定義為“一旦被生產出來,生產者就無法決定誰來得到”的物品。燈塔就是典型的公共物品,無論誰建造了燈塔,任何人都可以免費地利用。這種免費利用公共物品的現象被經濟學家們稱為“搭便車”。公共物品的這種特點決定了私人企業不願意進行生產,也無從定價和收費。這樣,市場調節的機制也就不適用於公共物品。這種情況被庇古稱為“市場失靈”。
但是,象燈塔這樣的公共物品卻是經濟中所不可缺少的。這樣,就必須由政府來出面建造燈塔,生產公共物品。英國古典經濟學家J·S·穆勒早在一八四八年就指出“雖然海中的船隻可以從燈塔的指引而得益,但若要向他們收取費用,就辦不到。除非政府用強迫抽稅的方法,否則燈塔就會因無利可圖,以致無人建造”。
庇古則以燈塔來支持他關於政府干預的觀點。他認為,由於燈塔難以收益,所以,如果由私人生產,則是私人收益低於社會成本。在這種情況下,以利潤最大化為目的的私人企業必然不願意生產,這就要由政府出面來建造並經營燈塔。
順著這一邏輯思路進一步分析,我們就會提出這樣一個問題:這種由政府所建造的燈塔由誰擁有產權呢?產權應該屬於出資興建燈塔的人。政府建造燈塔的資金來自人民的稅收,因此,燈塔這類公共物品的產權應該屬於作為納稅人的全體人民,也就是說,燈塔在理論上是屬於全民所有制的(當然,如果由當地政府收稅並建造,也可以說是屬於集體所有制的)。政府作為社會的代表建造並擁有燈塔,因此,燈塔在實際上是由國家所有的。公有產權一般都採用了國家所有的形式。這就是說,公共物品的存在還證明了公共產權的必要性。儘管庇古並沒有進一步論證這些問題,但由公共物品引出公有產權的必要性是一個合乎邏輯的結論。私有產權的存在並不排斥公有產權,這也是在以私有製為主體的西方國家中存在相當大國有經濟與公有產權的原因之一。黑格爾有一句名言:凡是存在的必是合理的。公有產權的存在也是合理的。
但是,對這種看法並不是沒有不同意見。一些經濟學家提出,公有產權的缺陷在於缺乏利己動機的刺激,政府建造的燈塔往往經營管理不善。而且,更重要的是,大家都來搭便車,如何來建造更多的車呢?或者換個比喻,大家都來吃免費供應的午餐,這種午餐能支持多久呢?對公有產權的這種質疑正是現代產權理論產生的原因。
公有產權私有化可能性
著名的美國經濟學家羅納德·科思是現代產權理論的奠基者。科思的產權理論以交易費用理論為基礎證明了私有產權的必然性與合理性,被認為是戰後微觀經濟學的重大突破之一。正由於這一貢獻,科思被授予一九九一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在這裡我們並不準備全面討論產權理論,只想介紹科思就燈塔問題有關產權理論的觀點。
以上所介紹的庇古的燈塔之所以引出公有產權,是由於燈塔這種公共物品收費的困難。科思正是要說明燈塔收費的可能性,從而證明私有產權對於經濟而言不僅必要,而且也是可能的。
科思在1974年發表了《經濟學上的燈塔》一文。在這篇文章中,科斯根據對英國早期燈塔制度的研究反駁了一般經濟學家關於私營燈塔無法收費或無利可圖的觀點,證明即使是燈塔這樣的公共物品,私有化也是可能的。科思的這一觀點由其弟子、香港大學教授張五常在《科思的燈塔》一文中進行了介紹與發展。
科思根據事實說明了,早期英國的燈塔是由私人建造並經營的,這些私人根據船的大小、所經過燈塔的數量,成功地對私人船主收費,並從中獲利。以後,燈塔的國營化並不是私人無法收費,而是收費過高。張五常進一步把燈塔收費的困難分為二類,一種是偷看燈塔而不認帳,拒絕交費,另一種是“搭便車”,承認看了燈塔但就是不交費。前一種情況,並不重要,后一種情況則可以通過政府賦予私人燈塔的“專賣權”來解決。因此,結論就是,對燈塔這類公共物品收費是可能的,並不能由燈塔收費的困難引申出必須由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結論。就產權問題而言,也就是公有產權的存在並不必要,對公有產權實現私有化是完全可能的。而且,由於私有產權下效率更高,所以,私有化就是克服公有產權下效率低下的必由之路。科思的產權理論無疑為七十年來以後西方國家國有企業私有化的政策提供了理論依據。也許這正是七十年代之後,產權理論盛行於西方經濟學界,以及科思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也並不是所有的經濟學家都接受這一觀點。首先,公共物品的收費問題並沒有徹底解決。公共物品消費的非排他性是客觀存在的,這就是收費即使不是不可能,也十分困難的原因。以燈塔為例,要使那些不承認利用燈塔,或搭便車者交費,就要有必要的監督設備和人員,這些監督能否起到有效的作用,費用需要多少 (例如,以現代計算機系統來進行監督則費用甚高),所收費用是否足以抵銷成本或有利潤,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如果收費十分困難或贏利甚少,能有私人願意經營燈塔嗎?再者,如果以利潤為導向吸引私人修建燈塔還會造成資源配置不合理或浪費。一個類似的例子是,當實行私有產權時,一個四戶共享的廚房就要安裝四盞電燈,如果實行公有產權,則一盞就夠了。
庇古的燈塔得出公有產權必要的結論,科思的燈塔則否認了公有產權的必要性。在現實中,公有產權確有其種種缺點,而私有化也並不是克服這些缺點的最優途徑。矛盾重重,出路何在?
俱樂部理論與社團產權
美國經濟學家詹姆斯·布坎南曾提出了著名的“公共選擇理論”,並為此而獲得了198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布坎南並沒有就燈塔問題提出什麼理論,但他的俱樂部理論與解決燈塔問題的產權理論相關。因此把俱樂部理論作為燈塔經濟學的一個部分,並冠之以“布坎南的燈塔”。
有些物品既不同於由個人消費的純粹私人物品,又不同於毫無排他性的公共物品,它們的消費容量是有限的,而消費者是無限的。這種物品介於私人物品與公共物品之間,被稱為俱樂部物品。這種物品具有排他性,即它由屬於某俱樂部的成員所共同消費,對此外的其他成員是具有排他性的。但在俱樂部內,各成員間沒有對抗性,即大家可以共同享受而沒有矛盾。例如,某些團體所有的游泳池就屬於這種俱樂部物品。
這種俱樂部物品的產權,既不是私有的,又不是完全公有的,而是一種社團所有制(類似於集體所有制)。這種產權的特點在於社團成員共同佔有,共同享受。布坎南強調指出,俱樂部理論的產權形式僅僅適用於那些可以具有排他性的產品,對以非排他性為基本特徵的公共物品並不完全適用。
但是,如果考慮到產權的變更,把象燈塔這樣的公共物品變為象游泳池這樣的俱樂部物品,也就可以使公有產權變為社團產權。就燈塔的例子而言,布坎南指出,其產權的變更能夠阻止那些沒有“使用燈塔執照”的船隻靠近或通過燈塔照耀下的海峽。遺憾的是,布坎南並沒有進一步說明如何用變更產權的方法來解決燈塔這類公共物品的搭便車問題。他的俱樂部理論對我們解決燈塔產權問題的啟示是,需要一種可塑性的產權結構,並在公共物品中引入排他性裝置。例如,英國運用監視系統使電視廣播這種公共物品變為收費的俱樂部物品,從而也就實現了從公有產權向社團產權的轉變。
在這種社團產權中,俱樂部成員共同承擔費用,共同享受。利益與責任的直接性激勵了所有成員的積極性,從而提高了效率。一旦有成員對該俱樂部不滿意,就可以離開(這種作法被稱為“用腳表決”)。比起私有產權來,它更適於某些共同消費的產品,比起公有產權來,它更加直接,更有效率。正因為如此,這種社團所有制存在相當廣泛,而且,一些原來的社會主義國家(例如,南斯拉夫)在改革公有產權時也採取了這種形式。但是,把公有產權變為社團產權並不是產權變更的唯一形式,也不是產權變更的最好形式。應該採取什麼樣的產權,仍然是經濟學家所關心的問題,也是社會主義經濟改革的熱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