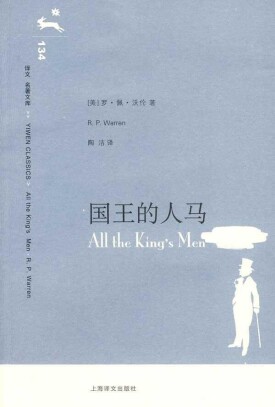國王的人馬
1946年美國出版的長篇小說
《國王的人馬》是由現代美國作家羅伯特·佩恩·沃倫所寫的長篇小說,是他的代表作,曾獲普利策文學獎。
作品以20世紀30年代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的州長休伊·斯的生平為基礎,儘管作者聲稱無意創作政治小說,但是因其對美國社會種種不公正現象的無情揭露,對美國腐敗政治的有力抨擊,《國王的人馬》仍然成為一部寓意深遠的政治小說和能夠準確反映當時美國現實的社會小說。
作品描寫主人公威利·斯塔克,一個原本默默無聞的農家子弟,依靠自己的勤奮努力,懷著改革政治,造福於民的美好願望,一步步走上州長的位子。但此後卻大搞獨裁政治,拉幫結派,黨同伐異,在貪污腐敗的泥坑裡越陷越深,最後遭到一個醫生莫名其妙的槍殺,傑克對塵俗世事完全淡漠了。但他又覺得“歷史是盲目的,人卻不是盲目的”如果不承受過去留下的重擔,也就不可能創造未來。於是他與安妮結合,開始了新的生活。
《國王的人馬》是以30年代美國路易安那州州長休伊·朗的生平為基礎的。郎本是默默無聞農家子弟,從未上過大學。但他通過刻苦自學,8個月修完了大學法學院兩年的課程,通過考試,21歲便當上了律師。3年後,郎進入政界,擔任鐵路專員。1924年,休伊·朗競選州長,但因對三K黨的態度不明而落選。四年以後,朗重整旗鼓,終於因爭取到農民的支持而以微弱的多數當選州長。朗執政后,一面大修土木,另一方面,他拉幫結派,排斥異己,安插親信,大搞獨裁政治。朗採取了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高壓政策,甚至還辦了一份報紙,詆毀攻擊反對派,為自己更功頌德,大造輿論。朗用強權政治鞏固了在路易安娜的絕對統治之後,便向華盛頓進軍,於1923年當上了美國國會參議院。然而1935年正當朗飛揚跋扈、不可一世的時候,被一位醫生莫名其妙的槍殺了。1937年沃倫去路易安娜州立大學任教,聽說了有關休伊·郎的故事,深為觸動,以此素材於1939年寫成詩劇《傷疤》。但他並不滿意,從1943年開始不斷修改這部詩劇,最終拓展成小說《國王的人馬》。
《國王的人馬》這個標題點明了主題思想,他因此在英美廣泛流傳的一首兒童歌謠,亨普蒂·鄧普蒂是個擬人化的雞蛋,歌詞是:
“亨普蒂·鄧普蒂坐在牆上頭,
亨普蒂·鄧普蒂摔了個大跟頭。
國王所有的馬,國王所有的人,
都不能夠把它重新來拼湊。”
沃倫借用童謠表明,威利狂妄自大,否認人的局限性,自以為是人民的救世主,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利,因此受到上帝的懲罰。他進入政界長大權時坐上了牆頭,但他權力腐敗,反而摔了個大跟頭。
傑克
在傑克講故事的過程中我們明顯感到美國南方文化傳統與現代思想的碰撞,體現最明顯的一件事就是傑克可不可以當斯塔克的秘書。鑒於傑克很早以前就認識斯塔克,並且還做過新聞記者,所以當斯塔克當選上州長后,感覺傑克對他會有很大的幫助,就想邀請他做秘書助理。而當傑克回到他往昔生活的伯登碼頭后,他所有的親戚和朋友都對他的這份工作感到不可思議。“你怎麼變成這個樣子?…… 都 是 那 些 人——你 干 的 工作——你為什麼不成個家——找個像樣的工作——”他們這些人感覺自己都是南方貴族的後裔,都有優良的血統,接受過良好的教育,具有無比的優越性,根本就瞧不起斯塔克,因為他沒有貴族血統,沒有顯赫的出身,他的祖祖輩輩也並不是穿長筒靴的紳士。傑克剛開始為他工作的時候,對他也有些不屑和鄙夷,但後來漸漸被他的人格力量所吸引,對其評價逐漸改變。生活在伯登碼頭的這些人都深受南方傳統思想的影響,他們的心中瀰漫著神話般的過去,無法忘卻過去的好時光,他們就像福克納筆下的昆丁和艾米麗小姐,深陷在南方美好的過去,不理解現在,同時又看不到未來。
威利·斯塔克
威利是一個充滿活躍的實幹家,上台以後確實大刀闊斧地進行了一些改革,也作出了一番事業。可惜,他的成就往往是通過骯髒的政治交易獲得的。威利並不是純粹的實利主義者,他也不像泰尼·達非等謀私利、飽私囊的政客上台以前說盡好話,上台以後便把選民的利益拋到九霄雲外,以貪贓枉法、營私舞弊為唯一目的。威利有責任感,心靈深處還是個理想主義者,一心改革世界,挽救人民免於苦難。因此,它能滿足人們的各種要求。私人秘書傑克在他身上找到自己所欠缺的目標、方向、權威和意志力。醫院院長亞當發現威利可以實現自己為之獻身的理想主義的真善美。老百姓更認為威利是正義的化身,人民的救星。威力的悲劇在於過於自負,相信惡一定能創造善,結果乾了很多壞事。他還有一個自私自利的動機:追求絕對的權力,樹立絕對的權威,報復曾經愚弄過他的政界。威利是個悲劇人物還因為他內心深處有一種犯罪感。為了能彌補罪孽,他決心修建一所能造福子孫後代,不為腐敗政治所玷污的醫院。但是威利在政治的泥潭裡陷得太深,無法自拔。泰尼·達非聽說威利要撕毀承包合同,眼看到手的肥肉就要失去,便借刀殺人,挑撥他和院長亞當的關係。結果亞當聽信讒言,以為自己當上院長,是由於妹妹安妮是威利的情人的緣故。亞當一怒之下開槍行刺,結果和威利同歸於盡。
歐文法官
小說里具有南方神話中騎士般形象的人物就是歐文法官。在傑克的心目中法官是一個特別英勇、正直廉潔和有榮譽感的人,是標準的南方紳士。小時的傑克總是以仰慕的眼光看著他,因為他在戰爭中曾經立過戰功,哪怕面對歹徒用槍指著他,他也敢大步向前,把這個歹徒嚇跑。他就是在南方神話中人們所塑造的忠誠的守衛家園的戰士形象,深得人們的敬重。哪怕當他出任法官期間,他也是勤政廉潔,深得人們的尊重和愛戴。除此之外,傑克對法官還有一種特殊的感情,就是在他童年缺少父愛的時候,歐文法官總是扮演著父親的角色,帶他一起制弓弩之類的玩具,給他讀書講故事,傑克感覺到有了法官在,外面再大的風雨他也不怕,可以說法官部分填補了他幼小心靈所受的被父親遺棄的傷害,也讓他感到有了心靈的依靠。可是有一件小事讓傑克不安,就是當傑克去法官家做客時,法官故意把他們多年前做的石弩拿出來演示它的衝力還很大雖然年代已久,可是傑克觀察后發現上面的繩索並不是當年裝上去的的那兩根,歐文法官已經把它換過了,所以傑克感到傷心、困窘,甚至有點上當受騙的感覺。法官對客人小小的欺騙暗示著他在以前的生活中可能存在著更大的欺騙,傑克的失望也預示著將會遭受更大的失望。當 威利·斯塔克為了獲得法官的支持,試圖恐嚇法官時,傑克絕不相信法官是一個輕易被嚇住的人。用他的話說“要是他害怕了,那對我來說是莫大的失望”。傑克奉命調查法官的歷史時,怎麼也不會相信法官是有污點的人,調查也不是為了找到他的污點,而是證明他的清白。然而調查的結果讓傑克大為震驚,法官年輕時確實接受過賄賂,利用職權出賣本州人們的利益給一電力公司而謀個人的私利。該電力公司讓他買股票掙了錢,而且還給他提供會計的職位,迫使原來的會計辭職,揭發無用,該人走上絕路,最終自殺身亡。這個發現摧毀了傑克心中的偶像 形象,使他不得不放棄對南方貴族傳統的盲目信從,伯登埠頭所代表的南方傳統已不適應現實的社會,傑克也不得不接受威利·斯塔克的人是罪惡的結晶,都干過壞事的論點。
亞當·斯坦頓
另一位具有南方紳士形象的人物就是亞當·斯坦頓。作為傑克的童年夥伴,亞當是一名醫術精湛的外科醫生,一心只想著治病救人,對當前的政治根本不感興趣甚至厭惡威利領導的政府。在他看來應該由那些祖祖輩輩都穿著高筒靴的高尚紳士來統治,不能容許一絲的腐敗和墮落。在他的心目中歐文法官和自己的父親斯坦頓州長就是清正廉潔的的化身,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形象。可是隨著傑克調查的深入,得知自己的父親當年在擔任州長時曾經袒護了歐文法官,致使一人含冤而死,雖然明明知道他受賄的事實。這個事實對亞當的打擊實在太大了,他的精神世界幾乎一下崩潰了,感覺自己信仰多年的東西突然沒有了,整個人像失去了支撐。鑒於這件事,亞當答應出任威利·斯塔克創辦的醫院院長。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亞當又接到一個秘密電話被告知他的妹妹安妮成了威利·斯塔克州長的情婦,他再也無法忍受自己的憤怒,隨即找到了州長並擊斃了他,而他也被州長的司機所擊斃。亞當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的眼睛里容不得半點沙子,他無法屈服於目前的社會,最後選擇和他痛恨的人同歸於盡。亞當的悲劇結局是緣於他心目中強烈的南方貴族的榮譽感被一點點地踐踏,才最終同代表現實的威利·斯塔克一起毀滅。
女性人物
小說中還有一些女性形象,如傑克的母親和安妮,他們顛覆了南方人心目中的貴婦人和淑女形象。南方神話中的南方淑女是純潔、優雅、神聖的,是道德聖壇的標誌,是南方文化最好最精美的典範。女人本應忠於自己的丈夫,維護家庭的榮譽,而傑克的母親結了婚後,卻懷上了別人的孩子。這也是傑克在調查歐文法官的歷史時發現的,自己親生父親是歐文法官,而不是那個戴綠帽子而離家出走的父親。也就是說,母親是和自己丈夫的好朋友生了孩子,養父無法忍受才離開,這也是母親對婚姻的極大背叛。在丈夫走後,母親不斷地更換丈夫,大實業家、伯爵、年輕的經理都在他們家生活過。傑克感覺母親總是喜歡自己身邊有男人,並且喜歡男人都圍著她轉。每次回家,感覺傢具變了,人也變了。不過,當母親聽到歐文法官開槍自殺的消息,從她撕心裂肺的哭喊中,傑克了解到她還是深愛著他的,她的心中還是有愛的,多少改變了一些對母親的看法。另一個與傑克關係的是青梅竹馬的女友安妮。她是純潔的化身,對人充滿愛心,做著對 孤兒、白痴、窮人的慈善事業。按照傳統的期望,她本應嫁給與她家門當戶對的傑克,可是由於傑克當時沒有自己的事業,生活漫無目的,他們之間的關係一直若影若離。令大家意想不到的是,安妮一步步淪為威利·斯塔克的情人。這個打擊對傑克的打擊實在太大了,他賴以生存的形象倒塌了。他們這些女性形象暴露了南方傳統中對女性的觀念已經不合時宜了。
主題
發表於1946年的《國王的人馬》實質上卻是一部嚴肅的政治小說,涉及到美國社會和政壇的各個方面。沃倫不愧是一位文學大師,為了不寫成平鋪直敘的自然主義小說,他起用了一位講述人——新聞記者傑克,以第一人稱的手法將整個故事有層次,有條理地呈現出來。這樣做,不僅避免了一般的政治小說常有的枯燥乏味,使故事起伏跌宕,富有情趣,更重要的是把小說提到一個新的高度,即從社會的角度來探求人的本質。
沃倫作為美國南方“重農學派”的成員之一,在1930年和其他十一位學者聯名發表 《我要表明我的態度》 為題的專題 論 文集,反對北方的科學技術和工業文明對南方的侵蝕,留戀農業社會、往昔的田園生活和古老的傳統美德。但是儘管如此,也阻止不了北方的工業和科技對南方生活方式及傳統思想的衝擊,南方神話的傳統在現實社會中已不適時宜。要想成為一個完整的人,不能像亞當和歐文法官一樣只留戀過去的美好,而要像傑克一樣承認自己的過去,才能面對現在和未來,這也是沃倫在其 《民主與詩》 中論證的觀點。
西方文化中對人的主體性的重視可以上溯到古希臘哲學,乃至後來的文藝復興和啟蒙主義思想,尤其是二十世紀科學技術的高速發展使得人的主體意識得到了空前高漲,人開始意識到自我力量的強大,認為“我”可以戰勝一切外在力量,人開始排斥走入他人的世界,認為“他人即是地獄”。人對自我主體性的過分重視就會導致個人主義,每個人都有一個他人不能進入的封閉空間,人和人之間的隔閡越來越大,產生了人與人的二元對立。人與人的二元對立在《國王的人馬》中主要表現為理想主義者與實用主義者、奉獻者和索取者之間的兩相對壘和格格不入。
亞當·斯坦頓完全是理想主義者的化身,他生為前任州長的兒子且家境優越,相比起白手起家的威利,他不用太努力奮鬥就可以得到良好的教育和生活環境。亞當生活在自己理想的生活當中,“心中有一幅關於世界的美好的圖畫,如果這個世界與他心目中的圖畫不相符,他就要拋棄這個世界,即使這種做法意味著不分好壞地把洗澡水連著孩子都一起倒掉。 ”這在情節發展上預言了亞當的結局,他誤以為自己能當上醫院院長是妹妹成為威利的情婦所致,因此當現實違背了他心中對於事業和生活的理想時,他不顧遭致殺身之禍地選擇了槍殺威利的激進手段。被亞當殺害的政客威利·斯塔克卻是個與之截然不同的實用主義者。生於南方農村的威利未上過大學,只能自修法律來通過考試謀得律師一職,為百姓權益伸張正義而得其擁護登上政壇。可是政壇複雜,威利一面為保住職權,網羅親信、排除異己,甚至採取行賄、威脅等不當手段來達到預期目的;另一方面為人民做實事,為建一所窮人能看起病的醫院而親自出面請與自己不相容的亞當來當院長,而此事卻遭到亞當的誤會,而導致了威 利悲劇的發生。理想主義者亞當與實用主義者威利都各持己見,未能看到自己的另一面,最終導致了悲劇。對於現實的態度“亞當·斯坦頓採取的是完全拒絕,威利·斯塔克的是全然接受,而超越二者的二元對立的是傑克·伯登的道德進化。 ”傑克·伯登正是從剛開始的理想主義逐漸過渡到能接受現實的實用主義的存在,實現了二元的消解融合才得以重生,開始了新的生活。
在《國王的人馬》中,傑克就是作為一個具有高度自覺意識的形象出現的。隨著故事情節的推進,傑克每時每刻都在進行自我反思並不斷加深對外物的認識。他既是被束縛在庸俗世界里的小人物之一,又是站在另外一個維度的觀察者。這也就自然而然地把小說背後更深層次的思想內涵引入了小說本身,也就使得作品不附庸於普通的政治小說。沃倫曾經否認這部作品是一種純粹意義上的政治題材小說。政治只是這部小說的一個依託架構,作者的真正目的在於透過政治生活這個極容易產生陰暗面的角度深入探討人性本身的特質並表述其對於歷史的獨特認識。作為一位南方作家,沃倫對南北戰爭的歷史有著廣博的研究和精闢的見解。他認為,南方人只有從南北戰爭的陰影中走出來,才能正確認識自己。在《國王的人馬》中,作者以“故事中的故事”的方法,通過介紹凱斯·馬斯頓這個人物表述了這一想法。
小說在第四章用一整章的篇幅插入了凱斯·馬斯敦和吉爾伯特·馬斯敦的故事。這個距敘述者傑克·伯登已有百餘年歷史的故事並非像看上去的那樣與主題無關,恰恰相反,它反而深化了小說的主題。馬斯敦兄弟都出生在田納西的紅土山上,吉爾伯特·馬斯敦很早就離家出走,憑藉自己的“經驗、狡詐和鐵石心腸”發了一筆又一筆的大財,可凱斯·馬斯敦即使在哥哥吉爾伯特的幫助下有了自己的大種植園,卻一直為情婦報復傭人菲比將其賣身為奴而對黑奴產生愧疚感,始終未使用黑奴幹活,使種植園淪為荒廢。儘管凱斯希望解放黑奴,可是卻不希望解放黑奴的戰爭來臨,仍在一味祈求和平,可是吉爾伯特卻看到了“北方佬要打仗而且還會打好”的 現實。在戰爭中,吉爾伯特成了騎兵上校,可是凱斯卻在密西西比州步槍隊當士兵,不幸在亞特蘭大城外中槍致死。太過理想主義的凱斯和追求實用主義的吉爾伯特儘管都在自己的世界中到達了理想的彼岸,可是他們就像凱斯蛛網理論中被蜘蛛的毒汁所觸及的受害者,“無論你是否有意碰蜘蛛網,結果總是一樣。”凱斯和吉爾伯特都成了歷史過客,可其故事卻使傑克在調查研究中開始理解和接受了人生的深意所在,催發了傑克人生觀的重建使其得到了新生。
沃倫是一位不斷探索人生價值和社會意義的大師,他很注意利用生活中的悲劇來挖掘其潛含的道德含義和自我本質。沃倫曾借傑克之口描述了他所處的那個世界:“它就象一張巨大的蜘蛛網,如果你觸動其中的任何一點,哪怕只是輕輕的一碰,振動也會波及最遠的邊緣。昏睡的蜘蛛受到震動會立即跳起來,吐出蛛絲,將你包圍,並在你皮下注入黑色而使人麻木的毒液”。從作者這段充滿了恐懼的描述中,我們深刻地意識到美國社會的黑暗和官場的險惡,置身於這樣可怕的“黑網”中,人的悲劇性命運,當然是不可避免的了。
在美國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普遍罪惡中,任何人都要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哪怕他最初有著較好的願望,到頭來也是事與願違,必然成為“惡”的工具。譬如威利始終認定自己掌握權力的目的是造福人民,但在實現這一目的過程中卻親手玷污了自己的目的,虛無的理想主義畢竟沒有戰勝現實的權力欲。儘管他有那麼高的威望,手下有那麼多忠臣鋪佐,最終還是難逃身敗名裂的下場,——小說的題意也就在這裡。“國王的人馬”源於美國早期的一首童謠:“爬得高,摔得重,國王的全班人馬,也難讓破鏡重圓”。從中可以看出,作者對改造美國社會,凈化人們被毒化的心靈,似乎不抱多大的期望。除了威利,小說中其他人物的處境也不美妙。傑克秉承威利的旨意,費盡心機地找到歐文法官的“隱私”材料,既造成了歐文自殺,同時又背叛了自己的過去——因為歐文不是別人,正是他的生身父親。亞當醫生的遭遇更令人同情。這位剛正不阿的外科醫生素來對威利的所作所為深惡痛絕。可他有一個致命的弱點——看到別人生病就不忍要去醫治,威利就利用了這一點,迫他就範。
而每當傑克遇到自己無法理解或者無法接受的事情時,他總會選擇一種方式——“大睡眠”來解決。這很明顯是一種逃避。事實上,我們每個人都在用不同的方式逃避,只是都不願意談及自己不願面對某些事情這一事實。逃避,不僅是對個人而言,對於歷史也是一種面對方式。無疑,沃倫更傾向於選擇勇敢的面對和冷靜的思考,在思考中重新認識,也就獲得了能夠站在更高角度看待問題的能力。沃倫對人性的認識無疑對每個人如何看待自己以及自己的人生都是大有裨益的,從某種意義上說,沃倫的作品可以作為人類對於自身心靈認識的一座里程碑。熟悉羅伯特·沃倫的評論家都願意把他作為一位“歷史作家”來解讀。一方面是因為他很多作品的主人公都取材於歷史中的人物,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沃倫獨具特色的歷史觀。《國王的人馬》取景於20世紀40年代的美國地方政治,並以此為切入點清晰深刻地闡明了沃倫的人生觀和歷史觀: 於憧憬中迷失,在自我救贖中完成人性的回歸。這種探索雖然簡樸,卻更加襯托出了其本質的光輝。
作者用相當的篇幅敘述了一位戲劇性人物的人生。從結構上看,這似乎是與主線關係不大的一條支線,但事實上,作者在暗中巧妙地鋪設了聯想的跳板,使人不由自主地拿理想主義的他與實用主義的威利相互對照,進而得出完全一致的結論。在物慾橫流,精神空虛的金錢社會,喪失信仰的實用主義與抽象的道德理想同樣是行不通的。另外,小說還深刻剖析了美國所謂民主競選的虛偽。儘管,從選民到競選人似乎都在按照一種嚴格的程序辦事,其實在幕後操縱競選的還是腰纏萬貫的財閥和手握權柄的黨棍,其間的陰謀陷害和造謠中傷不勝枚舉,以“正直”起家的威利也是靠這樣的競選“策略”才得以當上州長的。
沃倫在《國王的人馬》中通過對人物關係設置和情節內容的發展展現了一個人與社會、人與人、人自身的二元對立現象及其引發失去、死亡的悲劇。 “任何有生命的主體,都是需要他者的主體,既然需要他者,也就決定著任何個體意 義上的主體都是不完整的主體。 ”只有消解了個體內在的二元對立和矛盾衝突,才能實現人與人之間對立的消解從而避免悲劇的發生,最終達到社會的平衡與和諧。和諧個體的構建是創造和諧社會關係的必要前提。在經濟大蕭條后的消沉時期,沃倫用文學的方式預見了重建和諧的可行性和必然性,同時在扉頁上引用《神曲:煉獄》第三章的“只要希望還有一絲兒綠意”以告誡人們在重建中持有樂觀和堅韌的精神的必要性,這與彼時在應用數學界興起的博弈論不謀而合,可見對立走向消解既是歷史的需要也是歷史的必然。
手法
敘事
沃倫在 《國王的人馬》 中採用了網狀的敘事結構,用四個層層嵌入的故事形成了嵌套式敘事,將傑克·伯登的故事、威利·斯塔克的故事、歐文法官的故事以及凱斯·馬斯敦的故事這四個各自相對完整的部分交織起來,共同構成一個完整的故事。《國王的人馬》的表層敘事只為小說提供了一個框架結構,而其主要意圖卻被掩蓋於幾個錯落交織的敘事結構之中。表層敘事是傑克·伯登從敘事者的角度講述自己從一個逃避主義者成長為一個勇於面對社會現實的人的過程。雖然小說是圍繞傑克·伯登展開,但他卻並未像傳統小說中的主人公那樣佔據絕對的核心位置,而是時而作為敘述者,時而作為故事中的人物交錯地出現。小說共十章,其中第三、七、八、十章是在大篇幅地講述傑克·伯登自己的故事,而其他章節中的傑克·伯登大都成了為情節展開而設置的“故事的鑒證者和敘述者”。但也恰恰是這種旁觀者的角色使得他在複雜的現實生活中得以快速地成長,並最終形成了對社會和人生完整的理解和感悟。
第二層敘事是傑克·伯登作為鑒證者所看到的威利·斯塔克的政壇浮沉經歷。在小說的第一、二、六、九章,傑克·伯登回憶了威利·斯塔克從一個土生土長的鄉下人經過堅持不懈的努力而成為州長但又被迫隕落政壇的過程。傑克·伯登目睹威利·斯塔克從發跡到被槍殺致死是其成長的三個重要因素之一。另外兩個因素也都是在威利·斯塔克的直接或間接作用下生成的,即第三層敘事和第四層敘事。
第三層敘事是歐文法官貪污受賄多年之後,因被翻查而愧疚自殺的故事。傑克·伯登雖和歐文法官有著深厚的感情,可是身為州長秘書又不得不聽從州長威利·斯塔克的安排和命令,去調查州長對手麥克·墨菲的幕後支持者歐文法官。第五章一整章都是敘述者傑克·伯登在回憶“對正直法官的調查案”的大獲全勝過程,正是這次翻查歐文法官的歷史使得傑克又憶起了多年前的“第一次探索往昔美景的旅程”,由此引發了小說中的第四層敘事。
第四層敘事是傑克·伯登對自己的歷史學博士論文的回憶,即關於美國內戰時期的凱斯·馬斯敦和吉爾伯特·馬斯敦兩兄弟的故事。作家沃倫用了整個第四章來講述馬斯敦兩兄弟的原委,也正是這個與主題看似無直接關聯的故事道出了網狀敘事結構的內涵和意義,“倒不是因為第一次探索和威利·斯塔克的故事有什麼直接的關係,而是因為它和傑克·伯登的故事有極大的關係,而威利·斯塔克的故事和傑克·伯登的故事,在某種意義上是同一個故事”。這不僅使得傑克·伯登和威利·斯塔克的故事產生了關聯,也把歐文法官的故事和馬斯敦兄弟的故事一同拉進織好的第二層敘事和第一層敘事的框架,使得各層敘事之間相互關聯又層層相疊。
嵌套式的敘事結構形成了一個蛛網的結構,實現了用小說的外在結構形象化地構建出其內在的抽象理論。四個層層嵌入的故事把三代美國人經歷的一百多年的美國歷史織成了一個蛛網,彰顯出沃倫在小說文本中就已道出的“蛛網理論”——“世界就像一個巨大的蜘蛛網,不管你碰到哪裡,不管你如何小心翼翼地輕輕地碰一下,蜘蛛網的震動都會傳播到最遙遠的邊沿,而昏昏欲睡的蜘蛛不再打瞌睡了,它會馬上跳下來,拋出遊絲纏繞碰過蜘蛛網的你,然後把黑色的令人麻木的毒素注入你的皮下。無論你是否有意碰蜘蛛網,結果總是一樣”。小說正是利用四個各自成體而又彼此相連的故事形成了蛛網般的敘事結構,用小說的外在結構體現著沃倫的蛛網哲學觀,既消解了傳統文學中的線性敘事模式,又用新時代中的小人物傑克·伯登的現實生活感悟對已落入歷史的宏大敘事進行了新歷史的闡釋。
時空安排
小說的時空安排也是展現小說情節描繪意義和認識意義的重要部分,正如巴赫金在《小說的時間形式與時空體形式》中所言:“在文學中的藝術時空體里,空間和時間標誌融合在一個被認識了的具體的整體中。時間在這裡濃縮、凝聚,變成藝術上可見的東西;空間則趨向緊張,被捲入時間、情節、歷史的運動之中。時間的標誌展現在空間里,而空間則要通過時間來理解和衡量。 ”在後現代敘事策略中,時間更是變成了空間化了的時間,空間也成了時間化了的空間,而且二者不是單一的、線性的排列,而是破碎地交錯、融合在一起,以呈現現實生活的破碎感和真實感及處於其中的人們的內心的虛無感。
現代派手法
沃倫還採用了大量的典故、隱喻、象徵和意識流等手法。創造了一個內容生動,情節曲折的故事。這種把現代派手法和傳統的故事情節巧妙結合高度統一的做法,使《國王的人馬》及寓意深刻由具有趣味性。
《國王的人馬》在1946年出版,1947年獲得美國文學最高獎普利策文學獎。20世紀末,蘭登書屋在讀者中進行“20世紀最佳100本小說”的調查,該書排名在前四十名之內。主人公威利還是20世紀100個最佳虛構人物之一。
小說在1949年被改編成電影《一代奸雄》,獲得奧斯卡最佳影片和最佳男女主角三項大獎。

國王的人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