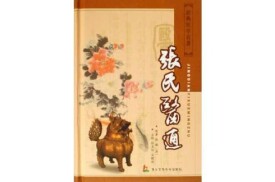張氏醫通
張氏醫通
《張氏醫通》,清·張璐撰,十六卷,刊於1695年(清康熙三十四年)。系一部以雜病為主的綜合性醫著,初名《醫歸》,為反映張氏學術思想的代表著作。體例仿王肯堂《證治準繩》,分內、外、婦、兒、五官各科疾病證治,並附驗案。卷一至卷七為內科部分;卷八為五官科;卷九為外科;卷十至卷十一為婦科;卷十二為小兒疾病;卷十三至十六為方劑。以病集方,方有方解,辨析配伍。本書內容豐富,刊行以後流傳頗廣,人稱“誠醫學正宗也。”
張氏撰寫此書,曾參考歷代醫籍近130種,並向當時醫家尤乘、李用粹、馬元儀等40餘人徵詢意見,歷時50年,易稿10次。《張氏醫通》之體例與證類,主要依照王肯堂之《證治準繩》,主治方葯多參薛己醫案與張介賓《景岳全書》,對前人醫論薈萃綜合,考古驗今,結合本人心得予以潤色闡發。
1705年,康熙皇帝南巡,張璐之子張以柔將《張氏醫通》《診宗三昧》《傷寒緒論》等書進呈康熙,三年後又上奏,康熙御批:“是即發裕德堂,另為裝訂備覽,欽此。”其後上述諸書又被編入《四庫全書》中。現存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刻本及多種清刊本以及日本刻本等,1949年後有排印本。
張璐(1617~1698),字路玉,號石頑老人,吳江(今屬江蘇吳縣)人(《清史稿》載江南長洲人)。祖父張少峰曾在明代為官。張璐少年時攻舉子業,后因明亡清兵南下,避戰亂於太湖“洞庭山中十餘年”(《清史稿·卷五零二》),因此棄絕科舉而專心於醫藥學,至1659年(順治己亥)返回故里行醫與著述。
張璐將《傷寒論》體例重加酌定,參考喻昌《尚論篇》、方有執《傷寒論條辨》及各家對《傷寒論》之註釋與論述,結合本人心得,於公元1667年編撰成《傷寒纘論》與《傷寒緒論》各二卷。“纘者,祖仲景之文;緒者,理諸家之紛紜而清出之,以翼仲景之法”(《清史稿》)。
張氏對脈學很有研究並富有經驗,認為“入門宗派不慎,未免流於異端”,懷著“吾當以三昧水滌除塵見”之宗旨,於公元1689年撰成《診宗三昧》(又名《石頑老人診宗三昧》)一卷。刊行后曾多次再版,其內容被後世一些醫家所引用。周中孚在《鄭堂讀書記·醫家類》中評價此書為“與李氏《瀕湖脈學》同一精密之作”。
張氏的醫著中影響最大者為《張氏醫通》,據作者自序說,從甲申(1644)開始撰寫,至己亥(1659)完成初稿,取名《醫歸》,但“自惴多所未愜,難以示人”,復因其中一部分書稿散佚,因此經多年進行補充修改,令其子張以倬重修《目科治例》、張以柔重輯《痘疹心傳》,至康熙乙亥(1695)才最後定稿,后以《張氏醫通》書名刻印刊行。張氏寫作此書,曾參考歷代醫籍近130種,並向當時醫家尤乘、李用粹、馬元儀等40餘人徵詢意見,歷時50年,易稿10次,可見寫作之認真。
張氏參考《本草綱目》寫作方法,於康熙乙亥(1695)撰成《本經逢原》四卷,分為32部,載葯700餘種,記述藥名、產地、性味、炮製、《本草經》原文、發明、治法等,論述中有不少是作者本人見解。
此外,張氏於康熙戊寅(1698)撰成刊行《千金方衍義》,對《千金方》各種版本進行校勘考訂,並對其中方劑註釋發揮。
自序
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道之興廢,靡不由風俗之變通。非達道人,不能達權通變,以挽風俗之弊也。今夫醫道之變至再至三,豈特一而已哉。餘生萬曆丁巳,於時風俗雖漓,古道未泯。業是道者,各擅專科,未嘗混廁而治也。甲申世變,黎庶奔亡,流離困苦中病不擇醫,醫隨應請,道之一變,自此而始。當是時也,兵火孑遺,托跡靈威丈人之故墟,賴有醫藥種樹之書消磨歲月。因循十有餘載,身同匏繫,聊以著書自娛。歲己亥賦歸故園,篋中輯得方書一通,因名《醫歸》。大都吻合準繩,其間彙集往古傳習諸篇,多有不能暢發其義者,次第以近代名言易之。草創甫成,同人速予授梓。自揣多所未愜,難以示人,僅以傷寒纘緒二論先行問世,頗蒙宇內頷之。壬寅已來,儒林上達,每多降志於醫,醫林好尚之士,日漸聲氣交通,便得名噪一時。於是醫風大振,比戶皆醫,此道之再變也。嗟予固陋,不能與世推移,應機接物而外。時與先聖晤對一堂,無異手提面命。遞年已來,穎禿半床,稿凡十易,惜乎數奇不偶。曩因趨赴孝伯耿公之招,攜至 川公署,失去目科一門。先是內侄顧惠吉,持去痘疹一冊,久假不歸,竟成烏有。知機不偶,已將殘編置之高閣,無復行世之心矣。近聞懸壺之士,與垂簾之侶,互參恆德之術。聖門之教無違,炎黃之德不顯,道之三變,匪特自今。吾於志學之年,留心是道,迄今桑榆入望,歷世頗多。每思物壯則老,時盛必衰,欲挽風俗之弊,寧辭筆削之罪知。因是仍將宿昔所述之言,從頭檢點,爰命倬兒補輯目科治例,柔兒參入痘疹心傳,足成全編,易以通名,標諸簽額。書未竟,適逢客至,隨手開函而語予曰,在昔《韓氏醫通》名世已久,今子亦以是名,得無名實相混之慮乎?予謂不然,吾聞元氏集名長慶,白氏之集亦名長慶,二集並驅。後世未嘗因名混實,奚必拘拘於是耶。客莞然而退,遂以醫通定名。迨夫三變之術,法外之法,非可言語形容也。
康熙乙亥季夏石頑張璐時年七十有九
卷一 中風門
卷二 諸傷門
卷三 寒熱門
諸氣門上
卷四 諸氣門下
諸嘔逆門
卷五 諸血門
諸痛門
卷六 痿痹門
諸風門
神志門
卷七 大小府門
卷八 氣竅門上
七竅門下
卷九 瘡瘍門
雜門
卷十 婦人門上
卷十一 婦人門下
嬰兒門上
嬰兒門下
卷十三 專方
卷十四 專方
卷十五 專方
卷十六 祖方
附張介賓八略總論
《張氏醫通》十六卷,內容包括內、婦、兒、外及五官各科。此書所引的醫學文獻,上自《靈》《素》下迄清初,達一百三十種之多,並還參入了作者的畢生學驗。究其宗旨,務在廣搜歷覽,由博反約,將“千古名賢至論,統敘一堂,八方風氣之疾,匯通一脈。”
《醫通》在各科病症之前,首列《內經》病機、《金匱》治例,但因其文辭質奧,所以詳加釋義,以明其旨,其間不乏真灼之見,如解《素問·咳論》“五藏六府皆令人咳”,以為:“雖言五藏六腑皆令人咳,其所重全在肺胃,而尤重在‘外內合邪’四字,人身有外邪,有內邪,有外內合邪,此雲五藏之久咳乃移於六府,是指內邪郁發而言,若外邪入傷肺合而咳,原無藏府相移之例也。”其所論述,是發人深省的。又解“少火”“壯火”,以為“火在丹田之下者是為少火,離丹田而上者是為壯火,少火亢極則為壯火。”他將少火指為真火,壯火指為邪火,也頗有見地。它如《素問·陰陽應象大論》“陽之氣,以天地之疾風名之”一句,張璐認為“即此一語,可證風從內發”,確實見解不凡。後來葉桂所謂“陽化內風”,不離此意。
《醫通》還保存了一些罕見的醫學文獻,如《潔古要略》、《製藥秘旨》、《黃安道讀宣明論說》、《丹溪或問》、邵元偉《醫學綱目》、盛啟東《醫林黃冶》、陸麗京《醫林新論》、劉默生《治驗》等等。《醫通》所引,多屬精采之論,如劉默生論吐血有血絡隔膜傷破說,以為:吐血一證,人惟知氣逆血溢、火升血泛,不知血絡膈膜之傷破。已傷之膜復有損傷,其吐必多,隔膜傷處有瘀血凝定,血來則緩。若陰火驟衝破瘀積之血,則血如潮湧,面赤如醉,脈亦急疾。少頃火退神清,面白氣平,血亦漸止,用藥須乘此時。瘀積盪盡,緩緩清理,徐徐調補,然不可驟壅,亦不可用耗氣之葯。悉知此義,治血有本矣。又如陸麗京《醫林新論》論內傷有三:一為勞役傷脾,二為饑飽傷胃,三為負重傷血,指出血傷在胃口則咳嘔血腥,痞滿少食,隔間隱隱刺痛,脈必氣口見弦,飽食賓士人多有此。主張用犀角地黃加酒大黃,以奪其勢,然後因病制宜用藥。凡此等等,多能開人眼界,益人心智。
張璐對病證的認識絕不偏執一說,他曾說:“讀古人書須要究其綱旨,以意逆之,是謂得之;若膠執其語,反成窒礙。”如昔人有“西北為真中風,東南為類中風”之說,張氏以為此說只為後人開一“辨別方宜”之大綱。告訴人們東南水土孱弱,卒倒昏迷,多屬元氣疏豁,虛風所襲,不可峻用祛風猛劑,而並不是說西北之人絕無真氣虛而中風者。只是西北資稟剛暴,風火素盛,加以外風猛厲易襲,故西北中風倍劇於東南。據其經驗,五十年來歷診西北之人中風不少,驗其瘖痱遺尿,亦屬下元虛憊;喎辟不遂,總是血脈之廢。反之,東南之人類中也有六經形證見乎外、便溺阻隔見乎內,而宜用續命湯、三化湯者。然而大體言之,張氏認為中風多“外似有餘,中實不足”,尤其以腎虛為主,他曾說:“中風之脈皆真氣內虧,風邪得以斬關直入。即南方類中卒倒,雖當分屬氣屬火屬痰,總由腎氣衰微,不能主持。”在這一思想指導下,張氏治腎氣虛虧的中風,多用地黃飲子加竹瀝、薑汁等取效。
對於疾病的診療,張璐強調“須隨所稟形色之偏勝、病氣之盛衰而為調適,全在機用靈活,不可專守成則。”這在其臨床實踐中亦有所反映,如治濕熱證,認為蒼黑肥盛之人及酒客皆多濕熱,主張在無病之時即宜常服調氣利濕之葯,如六君子加黃連、澤瀉之類,使濕熱之邪日漸消弭。若五旬內外氣血向衰,漸至食少體倦,或胸腹痞滿,或肢體煩疼,不時舉發;或偶有所觸而發,忽然胸高喘脹,煩悶嘔逆,甚至上下不通。主張乘初起元氣未衰,急投控涎丹十餘粒,如不下,少頃再服。控涎丹是專攻濕熱痰涎之葯。另若瘧疾的治療,時醫必先禁止飲食,概用疏風發散,兼消克痰食、寬膈破氣之劑,以至胃氣愈傷,濁邪愈逆。張璐治久瘧壞證,每令續進稠飲,繼與稀糜,使胃氣輸運,可行藥力,然後施治。《醫通》中說:“如此挽回者未遑枚舉。”
據《醫通》可知,張璐善用《內經》及仲景方葯,以之取效於臨床。如陶氏子勞傷咳血,勢若湧泉,服生地汁、墨汁不止。張氏門人投以熱童便暫止。璐診其脈象弦大而虛,自汗喘乏,入夜煩擾。遂於當歸補血湯而熱除。患者時覺左脅刺痛有聲,乃少年時喜酒負氣,毆鬥所致。與澤術麇銜湯加生藕汁調服,大便即下累累紫黑塊,數日未盡。后與四烏賊骨一藘茹為末,入黃雌雞中煮食,留葯蜜丸,盡劑而廖。澤術麇銜湯及四烏賊骨一藘茹丸為《內經》方,前者治酒風,後者治血枯,移用於此,愈見其妙。又顏女患虛羸寒熱,腹痛里急,自汗,喘嗽吐血,脈左微弦,右虛澀不調。張璐投以黃芪建中加當歸、細辛。其處方宗《金匱》黃芪建中之法,更兼《千金》內補建中湯之制。張氏指出,方中“加當歸以和營血,細辛以利肺氣,毋慮辛燥傷血也。,葯后血止,即用桂枝人蔘湯除腹痛、寒熱,后以六味丸將棗仁易萸肉,並間進保元湯、異功散等調理而安。《醫通》記載,張璐治虛損,認為“審系陰虧,則壯水以制陽;陽虛,則培土以厚載。”在臨床上每以“扶脾益肝建功”,則實得力於仲景。此外,張氏還認為仲景瀉心湯諸法,為“濕熱治本之方”,在於祛逆上之濕熱。觀其醫案,所治者獲效良多。
張氏在《醫通》中,對疾病的論治頗多創見。書中立痰火一門,為方書所罕載,在其前雖有梁仁甫《國醫宗旨》論之,然皆泛引膚辭,方葯亦難切於病。張氏於此,不僅發明其義,而且專制方葯,以資運用。他說:“夫所謂痰火者,精髓枯涸於下,痰火憑臨於上,有形之痰、無形之火交固其中。”病因勞思傷神,嗜欲傷精,加以飲食不節,血肉之味蘊釀為痰為火,變動為咳為喘。然此症雖外顯哮喘之狀,而內實有類於消中,總由外內合邪,兩難分解,故溫之燥之,升之攝之,皆非所宜。張氏玉竹飲子為治療痰火之專方(玉竹、茯苓、甘草、桔梗、橘皮、紫菀、川貝母、生薑、白蜜。氣虛加人蔘,虛火加肉桂,客邪加細辛、香豉,咽喉不利唾膿血加阿膠、藕汁,頭額痛加蔥白,便溏用伏龍肝,氣塞磨沉香汁。)此方有滋養肺胃之陰的作用,如其所說:“須知治痰先治火,治火先養陰,此為治痰治火之的訣。”願勿嫌其輕淡而忽之。
《醫通》所載有不少關於急症的治療,單就張璐本人的急症治驗而言,也是很有指導意義的,茲舉數例:韓晉度患腹痛泄瀉下血,服香連丸后飲食艱少,少腹急結,小便癃閉,晝夜去血五十餘度,瘀晦如莧汁。張璐投以理中湯加肉桂二錢,一劑溺通,再劑血減,四劑而瀉止。后與補中益氣加炮姜調理而痊。楊松齡夏月感冒,服發散葯后大小便俱閉濇不通,復服硝、黃,致膀胱不化,溺積不通,法在不救。張璐審其形神未槁,胃氣尚存,即用濟生腎氣湯大劑灌之,服后探吐,小便即時如注,更用十全大補調理而安。在昔丹溪治癃閉多用吐法,或用補中益氣湯,今張氏以濟生腎氣湯灌吐,又補充了一種急救的方術。
另王庸若嘔逆水腫,溲便涓滴不通,醫或用五等、八正不應,六脈沉細如絲。張氏與金液丹五十丸,服后溺如湧泉,其勢頓平,后以濟生腎氣培養而愈。總之,張氏救治急症,療效卓著,這在《醫通》中時有所見。
張氏學驗不勝枚舉,治血證心得尤多,《醫通》載:《千金翼》治吐血,用生地汁半升,煎之兩沸,調生大黃末一方寸匙,分三服,治熱毒吐血有效。又認為:脫血,用大劑人蔘益氣以固血,惟血色鮮明或兼紫塊者宜之,若見晦淡者,為血寒而不得歸經,須兼炮黑乾薑,或大劑理中溫之。同時還指出:失血後頭暈發熱,往往有之,此是虛火上炎外擾之故,不可誤認外感而用風葯。
另若瘀血的診治,《醫通》有不少警語,如說:“蓄血成脹,腹上青紫筋起,或手足有紅縷赤痕,小水利,大便黑……或有產崩血虛,或瘀血不散,亦成腫脹,其人必脈澀、面黑,不可作水濕治之。”又說:“瘦弱人陰虛發熱,脅下痛,多怒,必有瘀血”;“虛人雖有瘀血,其脈必芤,必有一部帶弦。宜兼補以去其血”;“前後心脹,喉中有血腥氣,氣口脈澀,此膈間有瘀血也。”張璐還記載了膈間或胃脘瘀血的一種診斷法,“試法:呷熱薑湯作呃者,瘀血也”,可作參考。凡此論說,多屬經驗之談,對臨床家是大有裨益的,不可等閑觀之。
在《醫通》中尚有目科一門,其原稿佚後由璐子飛疇補寫。篇中有《金針開內障論》、《造金針法》等敘述頗詳。醫案七例,是張璐用金針撥治內障的真實紀錄,案中涉及患者十餘人,大多收“一撥即明”之效,並雲針后眼痛作嘔,服烏梅可止。於此足見,張氏的眼科手術是極其高超的,甚至在歷代醫家中也不可多得,可稱佼佼者。
《醫通》的各門論治中,還載有不少丹方,包括許多食療劑。其13至16卷,載專方、祖方,共千餘首。諸家方葯琳琅滿目,作者的議論卓識紛披,業醫者若能手置一編,含咀而決擇之,必將有不少可喜的收穫。
《鄭堂讀書記》評價說:“其選擇方論,於文氣有不續處,略加片語以貫之;辭氣有不達處,聊易數字以暢之。一切晦滯難明者,雖出名賢,概不置錄。務在廣收歷覽,由博返約,俾後世修岐黃之學者,昭然其由,可謂用心切而為力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