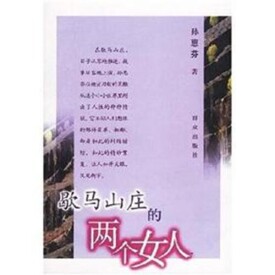歇馬山莊的兩個女人
孫惠芬創作的中篇小說
精彩片段:李平結婚這天,潘桃遠遠地站在自家門外看光景。潘桃穿著乳白色羽絨大衣,臉上帶著淺淺的笑。潘桃也是歇馬山莊新媳婦,昨天才從城裡旅行結婚回來。潘桃最不喜歡結婚大操大辦,穿著大紅大紫的衣服,身前身後被人圍著,好像展覽自己。關鍵是,潘桃不喜歡火爆,什麼事情搞到最火爆,就意味已經到了頂峰,而結婚,只不過是女孩子人生道路上的一個轉折,哪裡是什麼頂峰?再說,有頂峰就有低谷,多少鄉下女孩子,結婚那天又吹又打披紅掛綠,儼然是個公主、皇后、貴婦人,可是沒幾天,不等身上的衣服和臉上的胭脂褪了色,就水落石出地過起窮日子。潘桃絕不想在一時的火爆過去之後,用她的一生,來走她心情的下坡路……
| 第一部分 | 第二部分 | 第三部分 | 第四部分 |
|---|---|---|---|
| 歇馬山莊的兩個女人 | 歇馬山莊的兩個男人 | 給我漱口盂兒 | 民工 |
孫惠芬是一位從遼南農村走出來的作家,農村已經融進了她的血液,一輩子都難以釋懷。正是因為這種農村情結,孫惠芬連續創作了一系列反映民工的小說,《歇馬山莊的兩個女人》便是其中之一。
《歇馬山莊的兩個女人》寫於2001年夏天,那時候孫惠芬剛寫完小說《民工》,講述的是一對父子在城裡打工的故事,寫完后就想,男人們在城裡打工,那麼他們身後的女人們呢,於是就構思了兩個女人的故事。整個寫作非常順利,只用了十幾天。小說最初題目叫《兩個人》,投到《人民文學》,很快收到回信,當時做副主編的李敬澤先生給予小說很高的評價,可他覺得《兩個人》這個題目不是很好,要孫惠芬改成《歇馬山莊的兩個女人》,她堅持過,但最終還是被李敬澤說服。
潘桃
潘桃是一個追求自我,優雅的女性,和李平初次見面是在李平的婚禮上,她認為結婚不應大操大辦,所以她選擇一種自己認為既能彰顯自我又實惠的婚禮模式。但她沒想到的是,一個精心打扮的新娘居然提前下車與未婚夫挽手走過她家門前。突如其來的反差和衝擊毀掉了她的優勝心理,只留給她一陣猝不及防的疼痛感和危機感。潘桃和李平關係發生巨大轉折是在民工離家后,面對空虛寂寞的生活,潘桃需要找到可以傾訴的對象,這時也只有李平可以理解潘桃。面對李平丈夫的回歸,潘桃卻煎熬地等待著沒有回來的丈夫玉柱。此時的潘桃無法忍受李平再次超越和壓倒她,就連婆婆在強調李平風流的時候她的心也會瞬間疼一下,哪怕是“風流”。所以,封建傳統思想成了她最後必勝的武器:“她做過三陪,跟過很多男人。”這句被傳統觀念截然抵制的話毀掉了李平。
李平
李平是一個新婚不久即承擔繁重勞動任務的農村新媳婦,當她知道自己的婚禮打敗潘桃這個歇馬山莊獨佔鰲頭的女人時,她們間的“攀嫉”就被眾人推上了“擂台”。潘桃已經把生活中的點點滴滴都當成與李平的對決,而讓李平格外上心的不是如何過日子,而是一個叫潘桃的女子。儘管李平決定告別過去,踏實地過平常日子。但是,面對那些羨慕和嚮往“城市氣”的女人們,她還是決定用“城市氣”來穩固自己在歇馬山莊的地位,所以她穿上了那件在城裡買的黑白花邊外套毛衣。李平的丈夫和潘桃的丈夫外出打工后,在沒有男性的世界里,同病相憐和空虛寂寞使她們暫時接納了對方。但實際上,她們並未真正放棄“攀嫉”。李平在潘桃家出於禮貌與潘桃的婆婆說了幾十分鐘的話,冷落了潘桃,潘桃就認為李平為人處世比較圓滑。丈夫成子的回家填充了李平的空白,但也喚起了潘桃心底的“攀嫉”,潘桃向婆婆透露了李平曾做過三陪的秘密,李平因此受到傳統道德觀念的“懲罰”,最終離開了歇馬山莊。
在《歌馬山莊的兩個女人》中,孫惠芬以對人的“心靈歷史”一貫的熱切關注,圍繞兩個農村新媳婦由親常到疏遠的感情糾葛,站在城市文明與鄉村文明交匯撞的時代旋渦中,借女性心理的流動與情感的糾葛認真地審視、思考著在傳統與現代、理想與現實的矛盾衝突下鄉村女性的生存境遇。通過描寫主人公們對世俗的困惑、希扎與抗爭,以及對農村女對“城”的渴望,對“鄉土”的回歸,觸及到鄉土中國“農村現代化”和“鄉村女性意識覺醒”發的艱難歷程,從而使其作品在單純的故事情節中包含著豐富的內容,在潺潺溪水一樣清澈透明的敘述背後隱含著深邃的人生哲理和社會文化意蘊。
小說中的歇馬山莊作為歷史轉型期的鄉村,是一個不再執著於腳下的土地,對城市充滿嚮往,又固守著自身的冒昧與傳統的一個空間。在這個傳統文化空間里,女性的貞潔比生命重要。男人因羨慕城市而缺席,可傳統男權文化的影響卻又無處不在影響著婦女的思維方式和審美標準並內化為女性自身的行動準則。潘桃一方面向傳統挑戰,來顯示自己的出類拔萃,另一方面,又利用這種傳統來發泄心中的嫉恨與失落,從而直接導致了李平的不幸,也直接扼殺了她們的友誼。
從作品表層看,《歇馬山莊的兩個女人》在內容上圍繞兩個農村新媳婦由親密到疏遠的感情糾葛,展開綿密的心理描寫。難能可貴的是,作者並沒有困囿於語言技巧的自我歡娛和心理描寫的自我把玩,而是借女性心理的流動與情感的糾葛表現主人公們對世俗的困惑、掙扎與抗爭;通過農村女性對“城”的渴望與“離土”意識的刻畫,觸及到鄉土中國“農村現代化”的艱難歷程,作品蘊涵了相當深刻的社會文化意義,並通過對“離土”'思想與對城市文明嚮往的描寫,孫惠芬揭示了農民精神現代性的覺醒與突圍。雖然客觀地講,《歇馬山莊的兩個女人》是一個“離土”的主題,但並沒有超越新時期鄉土小說的思想高度,無力完成太多的理論超越。
敘事角度
《歇馬山莊的兩個女人》表現了作家精湛的敘事藝術。首先,是第三人稱全知視角的選取。這一極其靈活多變而又神通廣大的敘事視角,賦予作家一雙上帝的眼睛,使他卓然獨立於小說里所有人物之上,無所不在,無所不知。從全景式的鳥瞰,到男女歡愛床第前的窺視,從人物的外表儀態、言行舉止和微妙情感變化,到人物隱含不露、無人知曉的複雜內心世界,敘述者都暢行無阻,從而把讀者引入作家依次展開的生活畫卷中。就本文而言,作者要全景式地展示兩位新媳婦的情感遇合過程,纖毫畢現地鏤示出各自複雜微妙的內心隱秘和情感脈動,如果不是採用了這一全知全能的敘事視角,而是把視角限制在作品中某一人物身上或某一人物的內心世界里,那麼能否達到這樣圓滿的效果,怕要打個很大的問號。事實上,作者正是充分發揮了這一敘述視角的優長,得心應手、遊刃有餘地出入於人物的內心世界,洞燭幽微,寫照傳神,才使她們得到了全方位、多層面、立體化的展示,成為形神兼備、血肉豐滿、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典型形象,使之雙峰並峙、各領風騷、相映生輝、相得益彰。而讀者也得以成為名副其實的“觀眾”,情不自禁地進入這一視角造成的“閱讀幻覺”中,高度投入地觀賞了這出精彩動人的情感和性格的悲劇。在獲得極大心理滿足的同時,去深思和領悟故事的哲理蘊涵,去揣摩作者對生活、人生和人性的深刻反思。
其次是作品勻稱規整的敘事格局。作者從題材本身的特點出發,立足於我國讀者傳統的審美心理和審美習慣,不僅使故事具有高度完整性,而且在敘事過程中多採用“花開兩朵,各表一枝”,有分有合、齊頭並進的布局,使情節的運行有板有眼、井然有序,顯得開合有致、張弛有度,極具節奏感,顯示了純正地道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故事敘述的全過程中,作者如同一位技藝高超的鋼琴演奏家,只見其雙手在琴鍵上靈活自如地彈擊遊走,傳出的曲調時而平靜舒緩,時而低沉壓抑,時而歡快流暢,時而纏綿柔和,時而雷電交加,時而惆悵感傷。異彩紛呈,風光無限,跌宕起伏,引人入勝。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作品首尾照應的寫法,不僅增強了故事的完整性,而且造成了迴環往複的旋律美感。開頭是結婚那天李平和成子從潘桃家門前經過,只見他們並肩“挽手走過”,李平“簡直就是電影里的空姐”,漂亮、迷人、洋氣、城市;結尾仍是他們從這兒經過,卻是“一前一後”,“李平臉色相當蒼白,眼窩深陷著,原來的光彩絲毫不見”。兩相對照,真令人心痛不已,感慨萬千。而最末一筆說二人斷交后,李平家常去的是她的姑婆婆;“潘桃已經懷孕,每天握著婆婆的手,大口大口地嘔吐,想說話。婆婆聽著,看著,目光里流露出無限的幸福與喜悅”。這一筆更像在讀者的心口上灑了一把鹽,其強烈的反諷意味催人沉痛反思。這兩個主人公終於從此告別浪漫,回歸山莊女人最現實的生活軌道。作品的情節營構無疑是獨具匠心的。
最後,是詩意濃郁的敘事筆調。《歇馬山莊的兩個女人》是一篇小說,又具有詩的格調和品位。作家是用詩的筆調歌詠這個情感和心靈的故事的,它的語言像詩那樣明朗動聽又純凈洗鍊,精美典雅,韻味天成,處處散發出詩的芬芳。從敘述方式看,作者善於把“講述”“顯示”和“議論”有機交融在一起,做到情動辭發,情濡其中,使筆下的生活內容境界全出,情味十足,充滿詩情畫意。
修辭角度
從修辭角度看,作者特別善於切合情境氛圍,運用新鮮別緻的巧譬妙喻,溝通抽象與具象、無形與有形、情與景、心與物的聯繫,做到傳情寫照,妙合無垠,筆觸所至,觸著生輝;與此同時,作者又把巧譬妙喻與反覆、排比等修辭手段緊密結合在一起,只見妙語連珠,一氣貫注,文采飛動,氣象萬千,令人目不暇接、美不勝收。作品第二部分寫潘桃婚後尚未從少女時代的浪漫遐想中走進現實的精神狀態時,先用三個“在這樣的春天裡”領起的排句,從“屋子、院子、地壟”三個方面展示農家在這一季節的應有之景,然後反覆運用“沒結婚時”和“結了婚”的對比表現潘桃無法擺脫這一切的心理感受,把潘桃的失望和無奈,她的空虛感、失落感和壓抑感表現得淋漓盡致而又真切可感。
2005年4月24日,根據孫惠芬《歇馬山莊的兩個女人》和《民工》兩部小說改編的電視劇《民工》在中央電視台綜合頻道播出。
2004年,《歇馬山莊的兩個女人》獲得第三屆魯迅文學獎優秀中篇小說獎。
在歇馬山莊,日子從容地推進,故事從容地上演。孫惠芬以她尖刀般的筆觸從這個小小世界里剮出了人性的種種情狀。它不似人們想像的那樣簡單、粗鄙,卻是如此的糾結錯綜,如此的精妙繁複,讓人如開天眼,又見新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