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找到2條詞條名為大伯的結果 展開
- 大伯
- 大爸
大伯
大伯
大伯,常見的主要有兩種意思:一種指大哥,而另一種是指尊稱年長的男人。*註:兒子稱爸爸的哥哥為大伯。
大伯dà bó,詞語解釋為老年男子或父親的長兄。在魯迅的《吶喊·故鄉》中:“大伯!我們什麼時候回來?”這裡的大伯指父親的長兄。
大伯,一般指大哥。而 大伯(大伯),一般指爸爸的兄弟姐妹家中年齡最大的親哥哥(或者爸爸的兄弟姐妹家中唯一的親哥哥)。大伯公(大伯爺),一般指爺爺的大哥哥。
目前比較常見使用地區:兩廣、港澳以及海外粵語覆蓋地區使用。港劇比較常見,如 公主嫁到電視劇的第22集15:23秒有提到。
*對於年長的男人,在粵語里,一般尊稱為“阿伯”、大叔、阿叔等名稱。所以,粵語里 大伯和 阿伯的稱呼是有很明顯區別的。
大伯在家族中的地位很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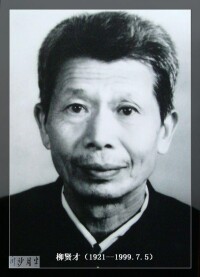
大伯
他躺在漆成黑底色、畫著鮮艷的龍的圖案的柏木壽棺內,被十六個精裝的漢子抬著,緩緩地走在瀰漫著哀傷的街道上。前面,他的子孫後代穿著孝衣、打著幡兒、舉著花圈在慟哭;再前面,是吹吹打打的民間藝人。間或,是噼里啪啦的鞭炮聲在空氣中震蕩著,似乎是在昭告,一個善良本分的老人,在一個陽光混濁、偶有樹葉飄落的晚秋午間,離開了他生活了75年的這個小山村。
大伯命運不濟,一生坎坷,並沒有過過多少好日子。他生於1931年,當時還是民國的戰亂時期。生不逢時的他,在成為剛剛懂些事情的孩童時,又不幸地趕上了日本全面入侵中國。由於當時國民黨政府的華北不抵抗政策,大伯所在的這個位於冀南華北平原西部邊緣的只百餘口人的小山村,很快便淪為敵占區。這裡是丘陵地帶,滿眼都是望天收的山崗坡地,並不盛產糧食,但日本人卻格外的“青睞”,是因為這個地區蘊藏著豐富的煤炭資源,佔領者自然不會放過,於是,便在這裡修築了鐵路,開挖了礦井,構築了碉堡、炮樓等軍事要塞,並蹲踞了重兵進行把守。據村子里的老人們講,僅我們村周圍的小山上,就有三四個炮樓,解放后被老百姓拆掉了,在那些遺址上至今還能看到一些破碎的藍色磚塊和白灰渣子。出於對煤炭資源的掠奪的需要,佔領者實行的是高壓政策,把這裡打造成鐵皮一塊。村子里,不時地有全副武裝的日本軍隊經過,將不寬的街道踩得嘩啦嘩啦之響。村人們便趕忙拉起自己的孩子躲進自家低矮的石屋內,瑟瑟發抖,連大氣都不敢出。日本人在這裡侵佔了8年,大伯的整個的童年,便是在日軍的令人驚悸的鐵蹄聲和刺刀的寒光中度過的。
日本投降后,我們這裡成為較早的被解放的地區之一。很快,土改運動開始了。據大伯講,我們的家族當時在村子里算是相對富裕的。這樣的富裕,也只不過是比一般的人家多置了幾畝的薄田,而且,這些田地是依靠自己的勤勞從一些變賣土地吸大煙的人手裡買來的,在劃定的家庭成分時,便被定成了富農。在那個沒有法制近乎蒙昧的時代,土改過了火,這樣簡單樸素的相對富裕,於是,就被一些人理所應當地認作是大大的罪過,一夜之間,家裡的老老小小都因此成了“罪人”。帶來的災難,便是家裡不但喪失了所有的財產,還搭上了正值壯年的爺爺的性命。那一年,大伯16歲,他的妹妹就是我的姑姑6歲,他的弟弟、我的父親剛剛滿周歲。
爺爺的一條命,並沒有換來一家人的平安和免責,而只是災難歲月的開始。“土改過火”使得一些人徹底紅了眼,兇殘暴戾到了極致,叫囂著要“株連九族、斬草除根”,對村子里的“異己份子”要趕盡殺絕。迫不得已,一家人的逃難生活開始了。剛剛三十齣頭裹著小腳的奶奶,只是個不曾見過世面的農家婦女,應對這樣突如其來的橫禍顯然是一件殘酷的事情。為了生存下去,一家人被迫分散了。奶奶帶著姑姑和父親在幾個親戚家裡東躲西藏,四處尋找避難場所。而大伯則在族人的幫助下跑到了城裡,在本家的一個爺爺開的一個馬車店裡當了小夥計。在近十年裡,殘缺不全的這一家人像乞討般地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這期間,姑姑長大了,出落成了一個大姑娘,再跟著奶奶四處躲藏也不方便了,便草草地嫁了人。像姑姑這樣的情況,一般的出身好的人家是不敢娶的。所以,所嫁的人家出身成分在那個村子里也是比較高的。好在,那家人很善良,對姑姑不錯。尤其是姑父,身材魁梧,是個很能幹的莊稼漢。婚後的日子清苦但平和,姑姑算是有了一個不錯的落腳。
這樣的日子一直持續到了上世紀五十年代的中後期。當時,建國已經有幾年了,局勢比較穩定,農村成立生產合作社,需要補充勞動力,逃亡了多年的奶奶與她的兩個兒子才得到了“特赦”,被獲准回家參加勞動,並在村子里的那條溝邊分到了幾間破房安身。大伯原本一直想在城裡做下去的,但趕上了公私合營,那間馬車店收歸了國有。大伯的出身不好,不能被錄用為正式職工,被辭退了,不得已,也回到了村子里。
此後的很多年,一家人雖沒有了性命之虞,但飽受了長期的受壓制和歧視,忍氣吞聲地過著低人一等的凄然生活。村子里的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抑或說是一些靠“運動”走紅的投機分子,還不斷對奶奶以及大伯、父親恣意地進行攻擊謾罵。好在,這一家人家族傳襲的為人的善良與厚道,是三鄉五里的老百姓們所公認的,很多人在私下裡對他們偷偷地接濟和照顧。在一些好心人的張羅下,大伯與大娘成了家。後來,公社裡開辦了自己的煤礦,要招錄一批挖煤的人。那個年代,生產技術還相當落後,下井採煤是很危險的職業,沒有人想去做。出身好的人命值錢,且頗有優越感,自然不必去冒險;出身不好的命賤,死不足惜,於是,大伯便成了公社煤礦的一個採煤工。雖是在礦上幹活,但並不發工資,勞動報酬是依然在村子里算工分。大伯人好命大,雖然煤礦時不時有礦難事故發生,也死了不少的人,但大伯每次都能倖免於難。
之後的二十多年裡,中國又有很多“運動”,如“四清”、“反右”、“文革”等。每次大的“運動”來了,村子里的像我們家這樣的出身不好的人,都會首當其衝地受到衝擊,被按上一些莫名其妙的罪名挨批鬥、遊街,都成了家常便飯。有的時候,社員們在地里集體勞動。中間休息的時候,大家原本是圍坐在一起隨便拉拉家常的。生產隊長如變態般的突然心血來潮,不懷好意地讓隊里的那些“四類分子”站在人群中央,進行批鬥,以顯示自己的威風和地位。這樣的次數多了,那些樸實的社員們也並不往心裡去了,只是機械地跟著喊口號而已。也是因為這樣特別的遭遇和經歷,造就了大伯和父親他們都有很強的心理承受能力,也磨礪了他們的意志。後來,大伯到礦上去上班了,依靠自己的勤勞和智慧,他成了礦上的骨幹,也靠自己的忠厚和誠實,贏得了大家在人格上的尊重。所以,當“運動”來的時候,礦上的領導和工友們都會以“工作忙”等理由,不開他的批鬥會。實在頂不過去了,就走走過場,做做樣子,算是有個交待。我想,在那十多年裡,大伯雖然每時每刻冒著生命危險在礦井下採煤,但他在心理上應當是相對輕鬆的。在這個時期,他心裡最大的壓抑和痛苦,並不是他自己的處境,而是自己已快到了古稀之年的年邁的母親依然在挨批鬥、自己的兒女因為出身問題不能上學甚至連婚姻都受影響的無奈。
時光荏苒,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隨著國家的撥亂反正和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年已半百的大伯和自己的家人一道,徹底“摘帽”了,被平了反,像去除了常年壓在身上的巨石一般,終於可以直起腰桿長長地吐一口氣,堂堂正正地成了這個村子里正常的一員。他們第一次享受到了“村民”待遇,和村子里的其他人平起平坐,平等地分到了責任田,也第一次讓一家老小吃上了飽飯。可惜,剛剛過上好日子沒兩年,飽受了戰亂和動蕩、守寡半生、沉默寡言的奶奶,耗盡了生命最後的能量,在一個秋天去世了。那一年,我剛好上高中。奶奶下葬的時候,大伯和父親傾盡所能,為奶奶辦了一個風風光光的葬禮。出殯時,大伯和父親都哭得很傷心。
又過了兩年,大伯的唯一的女兒、我的堂姐出嫁了。男方是本村的,而且是村子里的一個大戶人家,家庭條件比較好。這樣的婚事如果要擱在過去,門不當戶不對,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堂姐出嫁那天,大伯非常高興,不善飲酒的他喝了不少,也很激動。在酒桌上,當著一家老小的面,他眼裡含著淚水,在平靜地訴說了關於家族的過去之後,不停地念叨著“感謝好政策,真想不到現在能過成這樣好。”這樣的感恩的話語,在這以後的很多年裡,他時常掛在嘴邊。畢竟,過去與現在,對於他這樣的飽經滄桑的人來說,感覺簡直就是兩重天地。他的這樣的感嘆,是發自內心的,也是由衷的。對於家族過去所遭遇的不平,他並沒有怨天憂人,相反,他只教育自己的子女,要與人為善,向前看,走好以後的路。大伯的這種寬宏和大度,也是他看透了人世間的善惡美醜所悟出的真諦吧。
此後,上了年紀的大伯辭去了原來的公社煤礦上的工作,回到了村裡。這個時候,國家為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推行的政策是“有水快流”,村子里的一些人也紛紛開始興辦自己的小煤礦。像大伯這樣的多年來是一窮二白的家庭,剛剛翻身吃上了飽飯,是根本沒有任何積蓄的,搞投資是不大可能的。因為大伯常年在煤礦工作,有經驗也有技術,便受雇於一家私人礦主,做起了窯工的工作,相當於煤礦的總工程師的位置。在接下來的幾年,大伯上班掙了一些錢,手頭寬裕了。
1991年的春天,我已在省城參加了工作。一天,我正在自己的單身宿舍內看書,聽到了有人敲門。開門后,一個穿一身老式藍色中山裝、中等身材、謝頂、清瘦、有些佝僂的老人出現在門口。他,就是我的大伯。由於多年的生活艱辛,看上去,他比自己的實際年齡要老一些。他的身後,是他的正在上中學的最小的兒子,我的堂弟。
等我把他們讓進來坐下,大伯向我說起了來這裡的緣由。原來,本來歡蹦亂跳的堂弟,忽然一天腰疼起來,甚至到了不能直腰的地步。花甲之年的大伯,領著他在當地四處求醫問葯,幾個月間跑遍了大大小小的醫院,也沒有診斷出個所以然來。最後,抱著一線希望,大伯帶著堂弟坐火車來省城找我。臨末了,大伯歉意地笑笑,不好意思地說給我添麻煩了。我慌忙制止他這樣說,說都是自己一家人沒必要客氣什麼。
在單位外面的一個小飯館簡單吃了點飯後,我便領著他們去了鄰近的省醫院,找了一個熟人,很快就找到了病根,確診為先天性椎管狹窄。先後經過兩次手術,堂弟的病基本上治癒了。出院回家的時候,大伯的神情和來時大不一樣了,露出了歡愉和輕鬆。他搔著頭上稀稀疏疏的頭髮,忙不迭地向醫生表示感謝。他還要向我表示謝意,我趕忙拒絕了。
治好了堂弟的病,大伯並沒有完全輕鬆下來,他要完成最後一項大任務,為兒子蓋新房、娶媳婦。當這一切到變成現實后,他幾乎花完了自己的積蓄連同以後幾年的收入。所以,當他年近七旬終於放棄了在礦上上班的時候,已基本上沒有什麼錢財了。好在,已經過慣了苦日子,大伯並沒有特別在意。
即便是這樣的高齡,且兒成女就了,大伯依然閑不下來,不肯享清福。每天,他都要和大娘一起下地去勞作。打下來的糧食,除了老兩口自己食用,剩下的都給了在外面做事情的孩子們。一直到他去世的這年的春天,他還在地里做農活。
在生活上,大伯是個節儉的人,也不講究。他和大娘兩個人都很少置辦新衣服,但身上的衣服永遠是乾乾淨淨的。在飯食上,一直都是粗茶淡飯。他們很少買菜,鹹菜稀飯是家常便飯,有時候還蒸一些窩頭吃。孩子們為了表示孝心,給他買來雞鴨魚肉什麼的,他都拒收。實在拒絕不了留下來的,便保存下來,等孫子孫女們來了再吃。這樣的情形我也是知道的,因為,每次回老家去看望大伯,所帶的一些營養品,他都要推推桑桑好半天才勉強留下來。只是,因為工作忙了,也有了自己的家,我回家看望大伯的次數並不多,每年只有兩三次。到了大伯家,他都會很開心,忙著給我拿煙、沏茶,然後問一些我的工作和生活情況,也嘮叨一些家務事,最後還囑我做人做事的一些注意事項。就是在這樣的間隔的看望中,我看到大伯慢慢變老了。他變得越發的清瘦,臉上的光澤在漸漸褪去,牙齒徹底脫落了,連抽了大半輩子的煙也戒了。他的耳朵也失了聰,只能藉助助聽器。到了後來的幾次再去,就連助聽器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了,而且飯量也大不如從前了。
最後的一次去看望大伯,是在今年的國慶放假期間。我回到老家后,父親對我說,去看看你大伯吧,他病得很嚴重了。我有些吃驚,忙問是什麼病。父親嘆口氣,說是老了。
午飯後,我是和父母一起去看望大伯的。他剛輸完液,在客廳的躺椅上休息,幾個兒子守在身邊。看到我們來,大伯似乎想起身,但身上力氣不夠已經起不來了。他向我打了聲招呼“你來了!”我湊到他跟前和他說話時,他搖搖頭,說聽不到了。我又和堂哥說了幾分鐘的話,問問情況,才知道大伯已經幾乎不能進食了,主要是靠輸液維持生命,醫生說大約還有兩三個月的壽限。這時,大伯在躺椅上說自己累了,要躺一會兒。我趕忙攙扶他起來,讓他躺在床上。當我抓著他時,感覺他的胳膊已經很細了,似乎只剩下了骨骼。
臨走時,大伯對我說“你回去上班吧,不要惦記我,我沒事”,我諾諾地點點頭,心情沉重地出了房門。半個月後的一個晚上,我接到了父親的電話,說大伯不在了。
趕回去弔孝時,看到大伯已經穿好了壽衣躺在一張單床上。床邊擺放著香燭和祭品,兒子兒媳在地下的乾草上守靈。我跪趴在地上,哭了一通。然後,堂哥揭開蒙在大伯臉上的毛巾,讓我看大伯的遺容。他雙眼緊閉,嘴裡含著元寶,似睡熟了一樣的安詳。他的臉色焦黃,徹底失去了光澤。由於過度的瘦弱,他的兩腮凹陷進去,變成了兩個大坑……
按大伯的遺願,他去世三天後被火化了,一家人哭得一塌糊塗。找陰陽先生看過了,排了七,按傳統的儀式安排的葬禮。據家人的推算,按農曆,如果沒有今年的閏月,大伯去世的那個日子,和奶奶是同一天。時隔二十二年後,他們這對曾經飽受磨難、相依為命的母子,終於可以在九泉之下相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