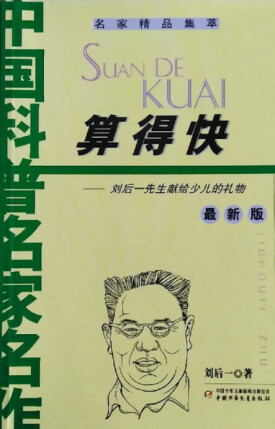算得快
算得快
徠劉后一先生是我國著名科普作家。他從1940年代就開始從事科普創作。《算得快》是他在1960年代初寫的。我們仍要學習速算,更重要的作用是為了理解這樣一種思維方法,那就是世界上有很多複雜的事情,並非不可以用更為簡單的方法來解決和完成。而正是《算得快》這本書,第一次向我展示出這樣一個道理。
讀完了這本書以後,你也許會問:是不是所有的速演演算法,這本書全講到了?這時候請你記住:知識是沒有窮盡的。你只要懂了道理,就可以自己創造出許多新的方法來。還有,當你看這本書的時候,碰到有什麼不懂的地方,希望你多多思考,多多和同學們討論,問問老師和家長。
學每一種速算方法的時候,你也許覺得有點麻煩,還不如照一般的方法按部就班地算來得快哩。這時候,請你記住古人的兩句詩: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每克服了學習上的一個困難,你就會得到無窮的樂趣。才學會一種速算方法的時候,你計算起來一定並不快,還可能會弄錯。這時候請你記住“熟能生巧”這句話。你還不熟練,就需要多做練習,隨時隨地,自己尋找習題練習。這本書每節都有習題,書末附有答數。
此情可待成追憶——優秀暢銷書《算得快》背後的故事/尹傳紅
這是一本內頁微微泛黃、兩角起了褶子的舊書,版權頁上印著:1963年5月北京第1版 1978年2月北京第2版 1978年2月北京第6次印刷。
這是一位跨越了漫漫路途、播撒了數學種子的“園外園丁”,在“科學的春天”到來之時及隨後的歲月里,它輾轉走過了3個家庭、哺育了7個孩子。
這是一份飽含真摯情意、充盈時代氣息的記錄,它寄寓了一位老科普作家的理想、志趣和追求,也熔鑄了他行進在科普創作道路上的艱難和辛酸。
我是那7個孩子當中的一個。當初哪裡想得到,在幸會《算得快》20多年後,又會與它重逢,並與它的作者一家和新、舊兩個版本的編輯結下了不解之緣!?
知識接力
還是先從兩年前說起吧。
2002年2月,我回故鄉柳州過年。到姑母家做客時,我在表弟的書櫃里意外地發現了我那久違了的朋友——《算得快》,不由得驚喜地叫出聲來:“哇噻,我的第一本數學課外書!”
已經闊別20年了,眼前這本黃乎乎的小薄冊泛著一股陳味,又舊又臟。可我捧著它一頁一頁地翻看,卻感到十分親切、溫馨。只是在一瞬間,書中那4位傾心速算、個性鮮明的小主人公——高商、李月珍、杜小甫和王星海,又在我的記憶中活躍起來……
瞧,這書的封面上寫下了2種姓氏5個孩子的名字,還蓋了一個印章,這是怎麼回事?
最清楚個中緣由的是我的父親尹遠源。我跟他提起《算得快》,他仍還記得書的封面鋪黃底,上邊印著小數學迷(高商)的大腦袋瓜兒。前兩天,就這本書的來歷我再次打電話向父親問詢,他講了幾句后便感慨道:“這是當年你們幾個孩子間的知識接力啊!”
大約是在1978年底,父親從報上得知,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新出的一本數學科普書《算得快》,很受歡迎和好評。一直懷才不遇、望子成龍心切的父親,隨即跑到城裡的幾家書店尋覓,但都一無所獲。於是,他便寫信向北京的親戚求助。
我的表伯趙一丁很快就把書寄來了,可並不是新的——在書的左上角,還寫著我的表哥和表姐的名字(趙平、趙楠)。原來,《算得快》一面世就成了“搶得快”、“銷得快”,北京城裡竟然也脫銷了——後來我聽說,《算得快》早年的每次發行,兩三天內便被搶購一空。
這本從北京“遷”往柳州的數學啟蒙讀物,一度成了我課外形影不離的“寶貝”。正是在閱讀《算得快》的過程中,我對數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且說那一陣我跟大妹妹關係不好,老想“吃獨食”,所以在書皮上就只寫下我一個人的名字;還學表哥表姐註上拼音,又蓋上了自個兒的印章。而大妹妹的名字(尹傳劍),顯然是由“主持公道”的父親特意添上去的。我還記得,因為大妹妹用紅筆在書中的插圖上塗抹描畫,我憤怒地訓斥了她,我們的關係由此而變得更“緊張”了……
後來,小妹妹也長大了,於是在書皮上她姐姐的名字下方,用鉛筆寫下了自己的尊姓大名(尹傳志)——我真搞不懂那時她為什麼會那麼“謙虛”。
再後來,這本書又“傳”給了我的兩個表弟黃璟和黃瑞。不過,他倆並沒有在書皮上留下“墨寶”。順便說一句,這哥倆對數學很感興趣,且都考上了名牌大學;老大還獲得過全國中學生數學競賽廣西賽區第一名,德國工作……
吃了一驚
《算得快》讓我記住了作者“劉后一”這個名字。
在我當年的想像中,他肯定是一位知識淵博、戴著眼鏡的老爺爺,興許還在科學院的數學研究所跟陳景潤做同事哩。但沒過多久我就給弄糊塗了,因為父親陸續買來的幾本課外讀物:《“北京人”的故事》、《山頂洞人的故事》和《半坡人的故事》,作者都是劉后一,可這幾本書跟數學一點也不搭界呀?
直覺告訴我,這些書都是同一個劉后一寫的,因為它們具有一些共同的特點:都是用故事體裁普及科學知識;故事鋪陳中的人物都有比較鮮明的性格特徵;再有就是語言活潑、通俗、流暢,讀起來非常輕鬆。
一晃十多年過去了。大學畢業后我來到北京工作,在《科技日報》做編輯。1993年夏的一天,一個同事指了指靠窗邊坐著的一位文靜的女士,悄聲對我說道:“知道嗎?她叫劉碧瑪,她爸爸就是寫《算得快》的劉后一。”這著實讓我吃了一驚,我說我可是劉老爺子的忠實讀者,前幾天還在報上看到周文斌寫他的一篇文章呢(《劉后一和少兒科普》。
碧瑪極易相處,漸漸地我們就成了彼此熟識的朋友。她跟我講了好些她父親的故事。我在20多年前的那個猜測,總算得到了證實。
緣分還不止於此。想不到我先後竟然又在不同的場合結識了老版(1978年版)《算得快》的編輯鄭延慧、新版《算得快》的策劃編輯薛曉哲,以及早在70年代末就報道過劉后一科普創作成果的記者周文斌。人生可真是奇妙啊,與《算得快》相關聯的這些“巧”,怎麼都讓我給碰上啦?
從那以後,我想拜會劉老先生的願望,變得越來越強烈了。
留下遺憾
1996年夏秋之間,我聽說劉后一先生病了,便再次向碧瑪提出去看看他老人家。第二天老先生讓女兒捎來話說,謝謝我的好意,他很願意見我,只是這一陣卧病在床,家裡亂得很,過一段時間再說吧。
然而,此後不到半年便傳來噩耗:老先生在參加科協組織的一次活動時,因腦溢血突發而匆匆離去。這一天是1997年1月24日。
未能見到“活生生”的后一先生令我痛悔不已。我想,那我就去為他送行,作一下彌補吧。豈料,1月31日那天上午,當我在10點20分從郊區匆匆趕到八寶山時,追悼會因故已提前半個多小時舉行,沒讓我趕上。這樣,陰差陽錯,我再也見不到他老人家了!
不過,在後一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際,我策劃、編髮了有關他的大半個版的紀念文章,發表在1998年1月27日的《科技日報》上,這多少讓我得到了一些寬慰。也正是在做這項工作的過程中,我對后一先生的品格、學識和涵養,以及多年來他從事科普創作所付出的辛勞和代價,所承受的艱難和重壓,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
鄭延慧女士告訴我,70年代初她接手編輯需修改再版的《算得快》時,曾到劉后一家去過幾次,發現身為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人員的他處境十分窘迫。當時他一家5口,擠在兩間大約8平方米的房子里,“除了床鋪,難找別的空間。他常常只能在辦公室里寫作到深夜,而後就睡在辦公室……一家人全靠他一個人微薄的工資生活” 。誰能想到,《算得快》這部累計行銷逾1000萬冊,並被譯成多種文字的暢銷書,以及同樣也很受歡迎的《“北京人”的故事》等科普佳作,竟然是在這樣一種環境下寫成的呢?
在徠女兒劉碧瑪眼中,父親劉后一是一個胸懷大志、勤奮好學而又十分“正統”的人。他父母早逝、家境貧寒,有時連課本和練習本也買不起。寒暑假一到,他就去做商店學徒、修路工、制傘小工、家庭教師等,過著半工半讀的生活……他之所以獲得淵博的知識和後來寫出大量的科普作品,大多靠的是刻苦自學。“父親也並非‘完人’。雖然他在科普創作的天地中馳騁自如,但在現實的人際關係中卻城府不深,缺乏圓滑的應變能力,這使得他與許多像入黨啊、晉職啊等等好事失之交臂。”
與劉后一相交多年的周文斌先生,以十分讚賞的口吻稱道他的這位老朋友“淡泊名利”,“有一種與世無爭的超脫”,但同時又直率地指出:“我覺得這些優點的另一面即是他的弱點,那就是委曲求全,不敢據理力爭,不敢當仁不讓。他做了幾十年的科研、學報編委和科普雜誌(〈化石〉)主編的工作,寫下了數十部總計200多萬字的著作,可直到退休仍還是一個副編審。這一點,我感到不公,他的其他朋友也認為不公,而劉后一本人卻忍了。這是我所深為遺憾的。”
在周文斌看來,這一遺憾的背後還有著一個更大的遺憾,那就是科普創作的被輕視。在科技界,有些人雖然對寫科普作品不知從何下筆,更不了解科普創作的艱辛,可卻對科普作家表現出不屑一顧的狂妄。他們視科普創作為“小兒科”,對科學普及的意義更是一知半解,可卻自恃高明、自以為是。這正是我們科普事業的悲哀!“真願意我們的科普界多一些像劉后一這樣的‘副編審’,也真願意我們的科普界不再有像劉后一這樣的‘副編審’。”
園外園丁
“你寫了那麼暢銷的書,若是在我們那兒,有一本就夠吃一輩子的了。”80年代中期,有一位來訪的外國朋友曾這樣對劉后一說。回到家后,他苦笑著跟女兒提起過這事兒,但沒說他是如何作答的。他真的會在乎他吃的“虧”嗎?
女兒說,父親長期業餘從事科普創作,耗費了巨大的精力,然而所得到的稿酬並不多,甚至“不成比例”。儘管如此,他經常拿出稿酬買書贈給渴求知識的青少年,還曾資助了8個“希望工程”的小學生背起書包走入學堂,並將《算得快》等書的重印稿酬全部捐贈給中國青少年基金會編輯出版的大型叢書“希望書庫”。
他其實是一個豁達大度的人。在他的心目中,身外之物遠遠不及他所鍾情的科普創作重要,因此,在種種不公正的待遇乃至刁難面前,他都能夠泰然處之,而不是斤斤計較、患得患失。他曾寫道:“有的人情願窮聊閑逛、‘打百分’,卻看不慣別人業餘給孩子寫東西……有的人以己度人,認為你寫些科普作品,無非是為了出名,得稿費而已。甚至造謠污衊,打擊陷害。在我看來,我上過師範,學過教育學,為孩子們寫作,使他們成為國家的棟樑、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也是我的正業。作為國家幹部,同時又是園外園丁,有何不可,有何不妥?”
在這篇題為《園外園丁》的文章中,他還戲稱自己當年挑燈夜戰的辦公室,是他“耕耘筆墨的桃花源”。字裡行間也透著歡快的筆調:“《算得快》出版了,書店裡,很多小學生特意來買這本書。公園裡,有的孩子聚精會神地看這本書。我開始感到一種從未有過的幸福與快樂,因為我雖然離開了教師崗位,但還是可以為孩子們服務。不是園丁,也是園丁,算得上是一個園外園丁么?我這樣反問自己。”當年,正是了解到一些孩子對算術學習感到費勁,他才決定寫一本學習速算的書,以誘發孩子們對算術的興趣。而這,跟他的生物學專業壓根就不沾邊。
他的風骨著實令人敬重,那就是“君子修道立德,不為窘困而改節”。他跟女兒說過這樣一段話:我們搞古生物研究的人應該胸襟寬廣、達觀,因為宇宙無窮大,個人一生實在太渺小了,何必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神,而況思其智之所不及,憂其力之所不能也!(大意如此。)
曾幾何時,社會上有過這樣一種論點,認為人才有“潛”、“顯”之分。“潛人才”對社會的奉獻遠遠大於從社會中獲得的回報,而“顯人才”則恰恰相反。一切客觀公正的人都會承認,“潛人才”這一稱謂於劉后一當之無愧!
在劉后一先生七周年忌日將至的2003年12月,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推出《算得快》的最新版,開機便印15000冊。半年時間不到,就在我寫下這篇文字的時候,欣聞新版《算得快》銷售形勢看好,又加印了11000冊……
后一先生,我想您沒有什麼可遺憾的了!
不久前,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的薛曉哲編輯送我一本新版《算得快》,勾起了我對往事的回憶。
作為一名科幻作家,我對數學一直迷戀有加。高中時我曾整宿整宿地求解一些艱深的數學問題,其精力之旺盛甚至超過我通宵打電腦遊戲的精神;而當那些難題的面紗雲開霧散時,我的喜悅和興奮真的難以用語言來形容。雖然我後來沒能真的去搞數學專業,但還是閱讀了大量專業和半專業數學書籍,每當我站在圖書館數學部分前,都會有一種拋棄現有的一切重新去學數學的衝動。
凡事都有源頭,檢點我的藏書,《算得快》幾乎是我最早讀到的數學科普書之一。平心而論,那時我還太小了,所以不敢說就是這本書讓我走上了喜愛數學之路,因為我在閱讀它時,學會的也許只是運算上的技巧;但這的確成為在我眼前打開數學之門的一把鑰匙,我相信它對我後來的數學情結和驚人的記憶力有不可忽視的影響。
讓少年讀者一開始能夠迅速融入的自然是精彩的故事,但在閱讀故事的同時,那些速算方法便被潛移默化地注入到我的腦海:在售貨員的故事裡我知道了在加法算式里可以有選擇地先加某些數,在高斯的故事裡我第一次了解到那個從1加到100的主人公原來就是這位數學家(這恐怕是我認識的第一位外國數學家),在加工木板的故事裡我明白了工程中應該嚴格遵循設計先於施工的道理,在古代人計算兩位數乘法的故事裡我驚奇地目睹了阿拉伯人的“鋪地錦”和印度人的“交叉乘法”……及至迅速通讀完全書,那些速算方法便囫圇吞棗般地被塞進了腦子;但也有很多不明白、不清楚、不準確的地方,於是再讀,再學,再算…… 按理說小孩子在讀書時對正文後所附的習題往往會有所抵觸,但由於這本書的引人入勝,使我居然認真地跟隨書中人物一步步尋找速算的方法。
速算的意義,在信息時代里,似乎顯不出什麼更多的作用。我們擁有眾多的計算機器和記憶機器,我們藉助各種裝置來“照顧”我們的大腦;我快捷的運算能力和記憶能力,往往只能勉強與那些由電池供電的裝置打個平手……有人曾對我說過:技術的進步往往會使一些原本屬於人的本領喪失甚至變得無用——這一論述給我留下了相當深刻的印象。我還算不錯的速算本領,似乎大多用於在商店結賬或者在餐廳買單時能很快地複核正誤,儘管在這點上我仍會經常讓朋友們驚訝。在這裡我不想假設這樣的情景:身陷深山,遠離文明,手邊沒有計算器而急需獲得某個數據……這種假設沒有意義,因為在我們的生活中這畢竟屬於非常規情形。
寫在前面
“一口清”的故事
這個辦法真好
高斯的故事
一隻青蛙一張嘴
杜小甫向高商挑戰
當了一回小木匠
五一倍作二
由淺入深
奇妙的七
愉快的春遊
你最喜歡哪個數
掐指一算
打破砂鍋問到底
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
速算高手張叔銘
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世上無難事
溫故如新
觸類旁通
融會貫通
重要的是思維訓練
習題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