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紅一
胡紅一
胡紅一,河南駐馬店人。做過鄉村體育老師、縣委宣傳部宣傳幹事、省電視台文藝編導、《南國早報》文娛主編、首席記者、《健報》(廣西日報主辦)副總編輯。現為廣西藝術創作中心副主任。
中短篇小說《麥子黃了》、《段子》、《紅雨傘》、《小小》、《第一次飛》等數十萬字,散見於全國各地文學刊物。出版過電影小說《真情三人行》、個人文集《廣西當代作家叢書——胡紅一卷》、城市傳記《龍城密碼》、人物傳記《中國式山水狂想》、劇作集《山歌牽出月亮來》等。
除文學創作之外,還廣泛涉獵於新聞、音樂、影視劇、大型歌舞晚會等多個領域的策劃和創作。采寫過《兩個人的學校》、《感天動地父子情》、《四代人和一群白鷺》等新聞特寫、報告文學,並將其改編成電影、電視劇、廣播劇及舞台劇。
擔任作詞的歌曲有《人民公僕》、《大地之約》、《山歌牽出月亮來》、《尖尖謠》、《站在這坡望那坡》、《為生命歌唱》、《錦繡壯鄉》、《留客歌》、《不會忘記》、《幸福路上》、《忠誠》等百餘首,先後參加南寧國際民歌藝術節《大地飛歌》開幕式晚會、中央電視“中韓歌會”、公安部春節聯歡晚會、廣西壯族自治區成立50周年《山歌好比春江水》文藝晚會、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綜藝晚會《祖國萬歲》等100多台大型演出,由陳明、毛阿敏、曲比阿烏、雷佳、呂繼宏、魏松、阿魯阿卓、湯燦、屠洪剛、焦點樂隊等歌星樂隊演唱。

胡紅一
廣西十百千人才、優秀專家。
專著:電影小說《真情三人行》(廣西民族出版社)、《廣西當代作家叢書——胡紅一卷》(灕江出版社)、城市傳記《龍城密碼》(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人物傳記《中國式山水狂想》(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劇作集《山歌牽出月亮來》(中國戲劇出版社)等;
歌曲:《人民公僕》、《山歌牽出月亮來》、《大地之約》、《尖尖謠》、《幸福路上》、《忠誠》等;
廣播劇:《山外有個世界》、《諾言》、《紅帆船》、《我要飛》等;
電影:《那年秋天》、《真情三人行》、《海邊的紅樹林》、《蓋帽》等;
戲劇:歌劇《壯錦》、壯劇《趕山》、彩調劇《山歌牽出月亮來》、音樂劇《龍船調》《過橋風吹》、實景演出《天驕-成吉思汗》、歌舞秀《錦-宴》《風-雅-宋》等。
獲獎情況
電影《真情三人行》獲開羅國際電影節長故事片大獎、第九屆全國“五個一工程獎”、第十 屆“中國人口文化獎”編劇一等獎、中國電影“童牛獎”及優秀兒童演員獎;
廣播劇《山外有個世界》、《諾言》獲全國第七屆“五個一工程“獎、中國廣播劇獎;
新聞報道《兩個人的學校》獲“廣西新聞獎一等獎”、“全國省級晚報新聞一等獎”;
歌曲《人民公僕》、《山歌牽出月亮來》、《忠誠》等被拍攝成音樂電視,在央視及全國各地電視台播出,並榮獲全國“五個一工程”入選作品獎、中國首屆原創歌曲大賽“十大金曲”獎、首屆全國公益歌曲大賽詞曲金獎、全國“廣播新歌”銀獎、廣西文藝創作“銅鼓獎”等;
歌劇《壯錦》獲第11屆中國戲劇節“中國戲劇獎 - 劇目獎”、第9屆中國藝術節“文華優秀劇目獎”;壯劇《趕山》入選“2011-2012年度國家舞台藝術精品工程資助劇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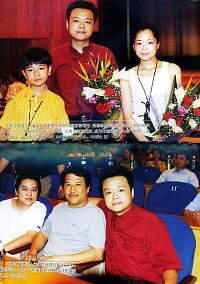
胡紅一
人物特寫:說說東西(節選)
文:胡紅一
從知道東西(廣西作家,廣西文壇三劍客之一)到認識東西,中間隔了好幾年。最初是看他的小說,有時寫的啥都記不囫圇了,名字卻刀刻般閃亮在印象里。心想這傢伙是誰啊?敢起這麼高難度的名字,也不怕別人拿這說事作賤他。
後來去坐落於古都西安的西北大學讀中文系作家班,發現東西的名字雖在花名冊里,卻是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他的遲遲不來報到,並不妨礙教授們每天點他的名,更不影響我趁機霸佔他的床位放雜物。就這麼著,一直“曠課”到我們畢業,東西也沒露過一次面。後來聽說他和余華、韓東、陳染等一起被廣東青年文學院客聘為專業作家,才知道他不來上學的真正原因。
1996年秋,我鬼使神差地成了廣西日報社所屬子報的記者。從遼闊中原一下子來到南寧,飲食氣候語言都無法適應,正舉目無親憋屈鬱悶時,突然得知東西也在同幢大樓上班,心裡頓時生長出幾分親切。在去拜這位名義同學的碼頭之前,我特意重讀了他的部分小說,以便跟他去套近乎。記得那天陽光不錯,推開廣西日報副刊部的門,我就大喊大叫誰是東西?弄得滿屋子人都抬頭看我。一個戴眼鏡的小個子慌忙起身,底氣不足地認領我的詢問,小聲說“我是我是”,表情頗有些緊張失措。如同被打散的紅軍突然尋到組織,我一把攥住他那並不寬厚的手,使勁搖晃自報家門,東西這才把對待一般作者登門投稿的表情,慢慢調整成分寸適當的客氣微笑。當我楞頭楞腦地誇他小說厲害時,東西明顯變得神情緊張起來,故意差開話題大聲介紹同事,很隆重地說這是什麼主任,那是什麼協會會員,極力將一間小小陋室,渲染得不同凡響卧虎藏龍……
自述:為啥寫作(節選)
大約是12歲那年,我的身高一夜之間躥到1·75米,早晨起來胳膊腿兒鑽進前一天脫下的衣服里,才發現袖口和褲腳短了一大截子,還以為是布料縮水了,也沒太在意。背著書包到學校,站在同齡孩子們中間升國旗唱國歌時,才感到高人一頭乍人一膀地不自然,就像羊群里突然跑來一頭驢。坐前面第一排聽課時,後面的學生只見我的後背後腦勺,根本看不清黑板上寫的是什麼,當天就被那個眼睛很好看的女班主任,將我調到最後一排。
在那段日子真是奇怪極了,我的飯量一個勁兒地噌噌往上長,吃得比家裡那頭帶7個崽兒的老母豬還要多,晚上睡覺時骨頭就像剛澆過水的紅高粱,能聽見嘎吧嘎吧的拔節聲……這種一日千里的成長形勢,弄得我又是興奮又是害怕,多年以後回想起來仍歷歷在目:一會兒像個快樂的耗子,一會兒像個憂慮的傻瓜。那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期,中原大地家家戶戶分田分地,剛剛砸爛吃了很久的大鍋飯,自食其力地過上幾天舒心日子,父老鄉親們一天到晚忙著從土地里挖金淘銀,恨不得把吃奶娃娃也當成勞動力使喚。父親是鄉村醫生忙著治病救人,母親一個人忙完地忙家裡,實在忙不過來時,難免會指使我幹些力所能及的農活。說實話,我是個天生不愛勞動的人,就像聖人孔老二說的那樣,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用我娘的話說,叫做伸手不拿四兩重。最喜歡乾的事情就是埋頭睡覺,可以不吃飯睡,可以不分天明地黑地睡,可以拾麥穗時躺在兩座凸起的墳墓之間睡……為了逃避體力勞動,為了能有時間睡大頭覺,我想近一切辦法又被母親一一識破。一天,我突發靈感地搬出桌凳鋪開紙筆,拉起將要寫作的隆重架式,卻有意輕描淡寫地對母親說:“俺要寫書當作家哩!”
這一招不僅把母親嚇愣了,還把整個家族給震驚了。因為,翻遍家譜查遍親人,方圓幾十里姓胡的人家,也沒出過一個能寫會畫的秀才。打這以後,只要我做出寫作狀,就算家裡人正忙著降龍縛虎,也沒人敢指使我干這個干那個,再苦再累,也心甘情願地用崇拜眼光看我。倒是那些鄰居們建立不起“作家”概念,往往把“寫書”當成了“說書”,腦子裡立馬電光石火地浮現出一個場景和一人人物,那就是趁著一年四季農閑時分,竹桿探路走村竄巷的鼓書藝人——瞎子張浩,說這不是學那“瞎浩”巧要飯嗎?見母親聽了臉色不好看,就馬上改口說,我看行得通,說好了也能吃飽飯混個肚子圓。
不管外人怎麼看,我倒是自得其樂,不但落了清閑還被家人重視。有人關注時,就拉開一付不寫出名著不罷休的架式。沒人注意時,索性就蒙頭呼呼睡大覺。時間一長就養成了習慣,哪怕睡得再死再沉,只要聽到家人從外面幹活回來的腳步聲,我都會一躍而起咬著筆桿兒做嘔心瀝血推敲狀。看到這幅畫面,家人往往很高興,彷彿我就是他們那塊長勢最喜人的莊稼地。
拿來寫作當借口,我漸漸有些養尊處優了,皮膚細膩四肢修長,看見油瓶子倒下也懶得去扶。由於生就跟年齡極不相符的大高個兒,放學回家的路上,常被一些走村竄戶的媒婆盯梢尾隨,當她們看到我家那座在當時農村不多見的紅磚青瓦房時,更加堅定了“吃鯉魚”(按照家鄉風俗,結婚新人要逢年過節給媒人送大鯉魚)的信念,就找母親套近乎拉家常,掏出一個又一個漂亮大姑娘的照片,讓母親隨便跳隨便選。這時候,母親往往拍著大腿笑出眼淚來,說俺兒還小隻有十二歲哩,小學生哪能娶媳婦?媒婆橫豎不相信母親的話,拿著那些好看的照片晃過來晃過去,說別哄人啦小學生咋會長那麼高哩,說少要點彩禮行不行啊,說不要彩禮倒貼總可以了吧?可是母親仍一個勁兒地搖頭,說兒子將來不會在農村尋媳婦,說兒子長大要當那啥作家哩!媒婆頓時非常失望,一旁的父親倒是捧著照片愛不釋手,說兒子真是太小了,這麼多好閨女推掉也怪可惜,乾脆說給他老子算咧!母親不笑了,銳利的目光像把錐子,剜得父親直打肉顫。後來在外地輾轉謀生,人近30歲也沒有成家的意思,遠在河南農村的母親就常常嘆息,說早知道這樣,十二歲那年就讓你在農村成親了,方圓幾十里的大姑娘隨便挑隨便選,俺早抱孫子啦。
就這樣,我先裝模作樣“假唱”好幾年,最高成績就是常被作文老師當眾表揚而已。直到18歲參加工作那一天,突然讀懂了父母的期待目光,就知道“事情鬧大了”,不得不硬著頭皮“真唱”,20歲那年第一篇散文在《河南日報》副刊正式發表后,父母這才算是得到了真正的報答,捧著念著跟遠親近鄰炫耀著,高興得像個孩子似的。
生來不大孝順的我,為了讓父母繼續高興,便一路仄歪硬撐著上了“賊船”。也許當年睡過頭了,也許確實不是那塊材料兒,現如今經常一宿接一宿地失眠,把自己整個熬煎得面如菜色,仍然比山西老陳醋還要酸誇獎自己:啊!文學讓我如此“藥渣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