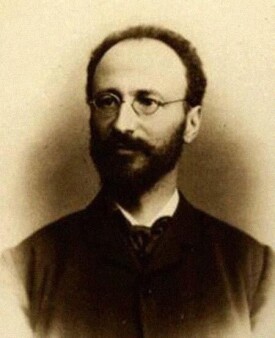共找到7條詞條名為送行的結果 展開
- 梁實秋創作散文
- 詞語概念
- 袁哲生創作的作品結集
- 翁立友主唱
- 馬克斯·比爾博姆《送行》
- 鍾立風演唱歌曲
- 日本2018年高島禮子主演電影
送行
馬克斯·比爾博姆《送行》
《送行》,馬克斯·比爾博姆所著散文。
馬克斯·比爾博姆(1872-1956),英國散文家,劇評家,漫畫家,曾僑居義大利二十年左右。有《馬克斯·比爾博姆文集》傳世。
比爾博姆依靠自己的能耐,很快以獨特的個性而為眾人所熟識。他的才幹為他贏得了進入《黃皮書》第一系列的榮耀,而當時的他還只是個本科生,年僅二十二歲。
1. 作者為什麼要寫這篇文章?寫這篇文章意在表達什麼?
2. 《送行》中作者抒發了什麼感情?
第1部分
1. 內容把握
提問:第一部分寫了什麼?
講解:第一部分(第1-3段),寫送行活動中虛應故事的尷尬。
提問:文章一開始就說“扮好送行的角色似乎是世界上最難的事情了”。送行本是親友之間增強友情,溝通思想的好機會,為什麼作者會認為“最難”呢?
講解:作者舉例說明問題。但是在這裡“我們”犯了一個小錯誤:“朋友越親,路程越遠,分別越久,我們就到得越早,送行也必定越笨拙得可憐”,作者得出結論--無能與場合隆重、感情深度成正比。第2段仍舊沒有說出“難”在何處,只是提到了送行過程中送行人所表現出的笨拙與無能,什麼是笨拙與無能,並沒有說出來。
提問:作者如何寫出送行的為難?
講解:第3段把在家中送客與車站送客作比較。在家門口送客,“親切、自然”,“臉上會流露出心中所感到的真誠的憂傷,話語也很得體,雙方都沒有拘謹,不覺得尷尬”;可是雙方都不敢到此為止,一定要到車站再告別一次。在車站的告別大相徑庭,主客雙方之間像是有了“一道深淵”,話也不會說了,恨不得早早分手,結束這種尷尬。其實,送行的一方與被送的一方都預知會有這種後果,但是所有的人似乎都不敢破壞這種習慣。這種經歷許多人都有過,但是作者把這種場面寫得很“透”。為什麼在家中送客自然自如,而到車站送客會不自在呢?這是因為:在車站送行,不僅場合變了,真正分手告別的時間也不由自己掌握了。
提問:這樣寫有什麼好處?
講解:這一部分用了較多的筆墨,是為下文寫勒羅的真情送行作鋪墊。
第2部分
1. 內容把握
提問:第二部分寫了什麼?怎麼寫的?
講解:第二部分(第4段到結束),寫勒羅作為送行人的精彩演出。這一部分可以分為兩層。
第一層(第4-6段),細緻描寫送行人的尷尬。第二層,寫車站遇勒羅。
提問:第一層寫的內容是什麼?有什麼作用?
第一層(第4-6段),細緻描寫送行人的尷尬。不過,這裡是具體的描寫。第5段寫餞行,是一次“完美的送別”,主人感謝客人的光臨,惋惜他的即將離去,依依惜別。照應前面的觀點,完全可以“到此為止”,可是不能免俗,第二天,還是要到車站送行。“明知要尷尬,不能不尷尬”,過於講究禮節,也會讓人不自在,可是人情守舊,莫不如此。對這種尷尬局面,作者風趣幽默地作了介紹。朋友上了火車,他的臉竟然成了一張“巴望討好、哀哀求助的、笨拙的”“陌生人的臉”,而接下去送行人問的話全是沒話找話,而被送者幾乎變成了不會說話的白痴;往下送行者強作笑顏,點頭、咳嗽,越來越不自在。這一段對場面的具體描寫形象地道出了送行的尷尬,全是為下文作鋪墊。
提問:第二層寫了什麼?這樣寫有什麼好處?
講解:第二層寫車站遇勒羅。
在層層鋪墊之後,“送行”在我們看來,已經成了尷尬無比的事,在這時候,勒羅出現了。
勒羅出現時,他的表現與我們一行的尷尬形成鮮明的對比。雖然同樣是送行,雖然同樣的是一個在車內,一個在月台,他的“演出”熾熱動人。他“正與車廂里一位年輕的小姐熱切地說著什麼”,他有“感人的表情”,“他眼神里深摯的慈愛實在動人”,“臨別贈言從他口中一瀉而出,使他那麼吸引人”,我們這些旁觀者也感受了他的“魅力”
“這魅力我也似曾相識”一句引出插敘,“我”記起這個人是原優秀演員勒羅。對勒羅曾經的交代是為了映襯他如今的生活。因為這個優秀的演員竟然被解聘,還不得不向別人借錢,漂泊他鄉。而如今他有何等精神!衣著華貴高雅,神采奕奕,氣度像個銀行家,“任何人有他來送行,都會感到榮幸的”。在這裡,我已經忘了寫自己的尷尬,全神貫注于勒羅的送別。勒羅完全沒有“我們”的那種尷尬,他的動作傾注了真情,一點也看不出是他的“演出”,看不出任何“職業”成分,而且“確實淚水盈眶”,“注視著列車駛去,直到看不見時才轉過身來”。
“我”和勒羅的交談交代了事情的真相。作為“英美社交處”的僱員,勒羅的任務是受雇為孤獨的在英國沒有朋友的美國旅客送行。“我”對勒羅的工作不理解,認為這些美國人這樣僱人送行沒有必要,因為車站送別是一件很尷尬的事,自己的體會太深了。勒羅的看法不同,並不完全是出於“職業”因素,因為他犯不著在老朋友面前說謊。勒羅認為這樣的送行能給孤獨者免去孤獨感,同時給他們帶去巨大的快樂,他做這件事時是全身心投入的。在他看來,送行需要感情,“我並不試圖演戲。我的確有感情!”“你沒瞧見我眼中的淚水?它們不是我硬擠出來的。告訴你,我真的感動了!”--仔細回顧勒羅的送別,的確沒有虛應故事的成分。把他的送別與“我們”一行人在車站上的表現作比較,可以看出,這個假戲真做的勒羅十分真誠,他已經完全忘記了自己是受雇於人的,否則他為什麼要“注視著列車駛去,直到看不見時才轉過身來”?
更能說明問題的是“我”--一個戲劇評論家被勒羅說服,看到勒羅車站送別的效果,想到自己送別朋友時的尷尬,“我”從這裡,似乎認識到了人們的情感需求。“‘教教我吧!’我叫了起來。”勒羅不但成功地以車站送行為職業,而且征服了傳統觀念,為車站送行注入了情感。
[文章內容總結]
不可否認,這篇散文有喜劇成分,真正送行者反而尷尬,扮演的送行者卻能動真情,真的東西不一定有價值,假的東西不一定沒有價值。作者以幽默的筆法調侃生活中的窘事,對生活中虛應故事的繁瑣禮節暗含針砭。
這篇幽默散文蘊含著對生活的深刻思考。在生活中,人們往往有感情而不懂得如何表達,所以常常是事與願違,會在一些場合出現尷尬,而勒羅受雇扮演“送行者”卻表現出令人感動的真情。這種看似不可思議的故事,通過幽默傳達了人與人渴望真實情感的願望。
一、文章在故事發展中刻畫人物。
文章描寫勒羅,手法藝術,先寫勒羅送別的場面,接著插敘勒羅的經歷,然後寫勒羅的談話。刻畫勒羅的形象,一是通過車站送行的動作神態的描寫,此時“我”並不知道勒羅是受雇送客,因而完全被他的形象所感動。勒羅真誠而慈愛,充滿感情,幾乎像那位美國小姐的父親;勒羅極有風度,穿著得體大方,像個銀行家;勒羅是有教養的,他見到“我”之後的舉止溫文爾雅。在他和“我”的交談中,讀者可以對勒羅有進一步的了解。勒羅是聰明的,他選擇了這樣一個職業;勒羅是敬業的,他出色而認真地完成每一次送行;勒羅是有自己主見的,他並不認為送行是純粹的演戲;勒羅也是精明的,他知道自己已經是送行人中的行家裡手,可以藉助這方面的技巧來賺錢。除了勒羅送行的動作神態描寫以外,還有幾個細節值得注意。如他還記得在七八年以前借過別人微不足道的“半克朗錢”,說明他是一個誠實的人;當“我”提出要學習送行時,“他翻了翻一本精美的記事本又說道”,讓人感到他是一個認真的人。
二、“不動聲色”的幽默手法。
文章作者把一件幾乎是不可思議的事寫得一本正經,甚至理直氣壯,讓人感到了幽默的魅力。文章寫送行的尷尬,說“互相注視著就像不會開口的動作瞧著人一樣”,“只盼著車警吹哨開車來結束這一出滑稽戲”;被送者出現在列車上時,“已像是一張陌生人的臉--一個巴望討好、哀哀求助的、笨拙的陌生人”,把他的尷尬寫得惟妙惟肖。寫勒羅在車站與美國小姐告別假戲真做的動作神態,出神入化;而勒羅的教養風度,則又反襯出“我”這樣的知識分子的沒有見識。這種幽默的寫法使文章產生了戲劇性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