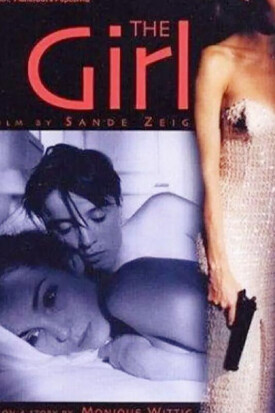共找到20條詞條名為女孩的結果 展開
女孩
2000年美國、法國聯合拍攝影片
兩個同性戀女孩,一個死了,一個追憶當時的情緣,或者把這個故事理解為一個有著同性戀傾向的女孩的性幻想也可。這是一個關於女孩、情人的故事,這兩個概念在影片中又時常混淆。
她,是一個女人,作為一個歌手,她在酒吧里唱歌。
“他”,也是一個女人,作為一個畫者,她在畫室里作畫。
她們本沒有交集,但僅僅是一次神奇的邂逅,造就了一場致命的愛情……
我不喜歡男人,我只會喜歡女人,我喜歡保護她們,當她們蜷縮在我的臂彎中,我的內心會湧起一種想要憐愛她們的感覺。我覺得我比任何男人都樂於讓女人幸福,所以我只欣賞女人,也只愛女人。
她是我一生中的至愛,而我也是她一生中惟一的“他”,但是我真的是不折不扣的女人!
她一個人住在酒店裡,無父無母,也沒有兄弟姐妹。每天她都要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然後風姿搖曳地出現在酒吧中,唱自己喜歡的或是不喜歡的歌。
那天深夜,我一個人在街上遊盪,我喜歡這種無拘無束、自由自在的感覺。當我在一家酒店門前點燃了一支煙的時候,我還不知道這將會對我的人生產生多大的影響。
我深吸了一口煙,任藍色的煙霧在四周升起,於是,感覺自己隨著這煙霧飛升……就在這時,我聽到了仙樂飄飄,那是一種很柔軟、很有磁性的聲音……帶著一種旖旎的風情,會很輕易地撩撥起你的慾望,是沒有絲毫猥褻卻十分想要的那種。
於是我放任自己的腳步,走進了那間酒吧。我看到了隨意地站在舞台上的她,穿著一襲寶石藍珠光夜禮服,配著她的歌聲,讓人迷醉。唱完后,她走向吧台,背對著我坐下,將褐栗色的長發輕輕撩起,再鬆散地放下,隱隱地透漏出一許誘惑,只有我收到了。在我的注視下,她驀然回頭,對上了我凝視的眼睛,於是她的嘴角上揚起一道優美的弧線。
我喜歡看她那碧青色的眼睛,像深邃的潭水,有著無窮的吸力,我承認我是捲入了漩渦之中。
她沒問我的名字,只是第一次就將我帶進了她住的旅館。我親昵地叫她寶貝,寶貝,她帶走了我的世界,從那一夜起。激情過後,我們互相依偎在一起,氣氛柔和而美妙……我們一起抽煙,一起喝香檳,一起吻著彼此充滿柔情的嘴唇。
她的聲音在我的耳邊纏繞:“我不喜歡和女人做這個,但是你與眾不同,你看上去簡直就是一個帥哥……”我知道我自己是一個帥哥,我時常穿著一套深色的西裝,修長的身材讓我看上去比較俊挺,而我的外貌,則更像一個帥氣的男孩。
她吻了吻我的耳垂,接著說:“但是我們只能過一夜,以後就不會再有了。”於是,我們又開始輕柔地彼此摩挲著,皮膚擦出微微的火花,燃燒了我們倆,也迷醉了我們倆。
這一夜餘下的時光,我都走在街上,我沿著河岸走,青石板奏出午夜后的寂寞,我在等待黑夜的結束。沒有了她的陪伴,夜好空。只有嘩嘩的流水,綿綿不絕,而我的思念就像這河水一樣蔓延。也或許那夜我什麼都沒想,只是微笑著,等待著第一縷陽光照在起伏不停的河水上。
我依舊到酒吧去,卻沒有和她說話,她有時瞟我幾眼,有時站起來唱歌,我只是靜靜地坐在那裡,喝著酒,想著不著邊際的事情。有時我會在她的窗下,站著觀察她,看她投注在窗帘上的影子。
那天,我看到她和一個男人親密地摟抱著離去。在之後的無數個日子裡,我從來沒有問過她那天的那個男人,她也從來不說,或許我們有一種相知相惜的感應。但是他卻在我們的生活中掀起了軒然大波。
每到她綿軟的歌聲響起,我就坐到離她最近的地方去,微笑地看著她。直到那一天,她也用深情的目光注視著我,彷彿整首歌就是為我而唱的。
於是幾天的努力化為灰燼,我們的激情再一次燃起。或許是因為那刻意的壓制,我們反而有了更為強烈的爆發。
我們飛快地奔回酒店,她迅速地把自己脫光。雖然我還穿著衣服,但是我們已經緊緊地貼在了一起,我感到火焰在她柔滑的皮膚上迅速地燃起,我也在她愛的低語中失去了控制,在這樣的漩渦中誰還需要控制?!我們都忘記了曾經信守的諾言。
在溫馨過後,我坐在椅子上,給她畫素描,她則點燃了一支煙,斜倚在枕頭上,向我輕聲地訴說:“我正想找一個藝術家,和他在一起……可以躺在床上,自由地呼吸,然後穿上衣服,畫好妝……”說著,她翻身下床,走出卧室。
我跟隨她,來到梳妝台前,依舊擺弄手中的素描。她吹出口中的煙,隨便和我聊些什麼。突然,她站起身,平靜地說:“好了,你該走了。”
“可是,我以為你是要將我留下來呢。”我不置可否地說。
她站起來,很堅決地打開門,近乎草率地說“我愛你”。我只得站起來,走到門口,在很倉促地告別吻后,我就被推了出來。門啪地一聲,在我的身後,很響亮地關上了。我只得對著門板搖了搖頭,再次敲門,對她說:“你還不了解我。”在我下樓的時候,那個男人和我走了個迎面,我知道他是去找她的。
我們擁抱著跳舞,她叫我Lover(愛人),我喜歡這名字,從她的口中說出,輕柔而有動感。
我知道她是一支開在夜色中的玫瑰,她嬌艷而赤裸,脆弱而寂寞,她會對著我發出深情的呼喚:“吻我的肌膚,輕輕地,Lover”,我無法抗拒也不想抗拒。我要讓她在我的愛撫中綻放,她時而熱情如火,時而輕柔似水……所以,我要吻遍她的每一寸肌膚,讓她在其中戰慄、呻吟,讓她在我的愛中美麗……
我喜歡她不顧一切地吻我,喜歡她揉亂我的頭髮,喜歡她在最激動的一刻高聲地大喊:“Lover”,我喜歡她對我做的一切……我就在這一片愛欲中淪陷了。她從不問及我的生活,她也一點都不了解我,而我卻簡直不能沒有她。不管我是不是畫家,只要她喜歡就行,誰在乎呢,這就是我們的生活。
回到畫室,我的模特兼密友布薩維正在床上等著我,我對她說:“我放縱我的愛。”布薩維是我生命中另一個重要的女人,她是一個隨心所欲地寫歌的人,我喜歡她的個性。她具有光滑而黝黑的皮膚,沙啞而低沉的嗓音和明亮而簡單的眼神以及一顆愛我的心。我時常會撫摸著她的肌膚,體會由她的身體中實在地迸發出的我的靈感。
她很了解我,對我說:“柔和的陽光,激情的溫床……”
我們互相理解地笑了,然後我們熱吻,做愛。那是我們的第一次,但是我們都明了那絕對不會是最後一次。
我還是瘋狂地想見她,我在她的房子下徘徊,猶豫該不該進去。她突然從我的背後抱住我,告訴我,從窗子里看見我,就下來找我。於是,我們迅速向樓上跑去,她在我的前面,邊跑邊脫下了高跟鞋、胸衣……,最後,她光潔地站在房門口,快樂地對我說:“鎖上門,進來洗澡……”
當我拾起了她丟在地上的衣物,進入浴室時,她已經愉悅地躺在浴缸中了。她對我說:“習俗要求人們穿衣服,但是人們都想脫掉它。”
我的寶貝,我的女王,接著溫柔地向我下命令:“脫衣服吧。”於是我們就相擁在狹小的浴缸中了。我們更像是初生的嬰兒,沒有一切束縛,只是那麼簡單地擠著,感覺我們前生就已經註定要在一起了。
當我們再次穿戴整齊時,我躺在床上給她畫速寫,她則站在餘暉中擺姿勢。她很平靜地對我說:“我和許多人上過床,因為他們對我的事業有幫助,生活就是這樣子。”她還說,和男人上床就像和他們上酒吧一樣。我反問她:“生活就是這樣子?”
她微笑著肯定:“是的。”我們相視無言,只是笑笑。是什麼奪去了她應有的歡樂,是什麼讓她如此現實,我知道,只是意識到這一點未免有些殘忍。
一天,我和布薩維親昵地躺在床上,我們談起了她。我對布薩維說:“她不適合我。”
“有人會和自己不喜歡的女人瘋狂地做愛嗎?”
我不假思索:“我們只是出於本能。”
“狗才出於本能。找到這樣的一個女人一定非常刺激……”
我知道布薩維是在啟發我,可是連我自己都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了。我瘋狂地迷戀她,卻無法喜歡那麼現實的她;她很喜歡我,卻不願意真正地去了解我。
我和她在舞池中相擁而舞,悠揚的薩克斯將我們的舞步吹的緩慢而凌亂,於是我們熱吻。她低聲告訴我,她喜歡和我跳舞,非常非常喜歡。不經意間,她抬起頭,看見了在一邊用凌厲的眼神看著我們的那個男人。她立即緊張起來,鬆開我的手走了出去。我也沒有抓住她,只是跟在她的身後,看著她回家,她的步伐匆忙而散亂。
在快到旅店門口的時候,她突然轉過身,大聲地對我吼:“你為什麼要跟著我?我每天都要和這個男人周旋,我不想連累你。”
她轉身走了,但馬上又轉過頭:“聽著,不要跟著我回家,我不想見到你!你要小心點,知道嗎?”語氣依舊不見和緩。
我在街上漫無目的地走,還是不知不覺地走到了酒吧前。我看到那個男人推搡著,將她弄上了車。我知道自己對她的命運無能為力,所以我只能站在那裡,彷彿只是一個過客……她可能是更早地意識到了這一點,但是我也沒有她想像的那樣懦弱,畢竟我不止長相上像男人,而且我要呵護女人。
可是在我的記憶中這次經歷卻是這樣的:那是一天下午,天空湛藍,陽光和河水讓她的房子前充滿了銀色,樹葉於是斑駁地閃亮,我和她就是那樣簡單地走出房子,然後分手,回到各自的空間里。我知道這只是我的美好的記憶,可惜美好有時只能是憑空想像出來的。
接下來的時光,我陷入了低谷。布薩維也有好長時間不見了,什麼也沒說就走了;而寶貝的聲音就像一個魔咒,已經沁入我的身心,當我坐在地上畫素描,耳朵里就會充溢著她的聲音,然後筆下就全是她零零碎碎的影子,然而卻總是不能叫人滿意。於是,我畫一張,就扯去一張,再畫,再扯……她是我的福音,此刻卻成了我的夢魘,我知道我逃不脫的。
於是,我就又出現在酒吧里。聽她唱歌,真是令人著迷。我知道她在向調酒師打聽我,好像她不說話,我也能聽到她的聲音。果然,她向我走來,高挑的我在她碧青的眼睛中放出異樣的光彩。我們相互望著,好像是為了補償這許久的未見,她將我的手拉向她,然後放在她柔軟的腰肢上,貼近我,再近些,於是我們緊緊地擁吻……
我為她斟了一杯酒,同時也感受到斜前方傳來的冰冷。他坐在那裡,不帶一絲感情地看著我們,卻分明讓人感受到壓力。可是我們都沒有理會他,讓他的壓力見鬼去吧。
她微笑著說:“我知道我的脾氣不好,我不好,我自以為是,不過,你好像理解我。”她伸出手溫柔地撫摸我的面頰,整理我的髮絲。
激情,無邊無盡的激情讓我們遺忘了世界……閑適的一夜過去了,喧囂遠離我們,白光透過窗子,照在我們激情燃燒后的身體上,一種幸福在蔓延,床上彌散著她誘人的香水味。我和她又神奇地和好了,我們每天都在一起,因為我們彼此喜歡。
終於,我在街上又遇到了布薩維,她的衣著都沒有變,只是她身邊的人變了——在她身邊的是一個很不羈的黑人男子。她居然假裝不認識我,只是說我讓她想起了一個人。我們說著彼此才會懂的暗示,但也只能匆匆別過。我的心裡說不出是什麼滋味。
回到家裡,我看到牆上的小黑板上以前我寫的“In my heart,I am a gentleman(在我的內心,我是一個紳士)”,失神地笑了笑,走到畫架前,將剛具雛形的布薩維的畫像塗花了,畫布上就只是一片蒼茫的白色。有時候就是這樣,什麼也不必說,只要按自己的心情去做就好,而這畫布就是我的心情。
她終於告訴我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我們在排練間里,看到他正在為模特擺造型,但同時他也會拂拂這個的髮絲,摸摸那個的臉蛋,雖然很猥瑣,但是沒有哪個女孩站出來反對。她告訴我,他在監視她們,他監視這裡的每一個人,甚至於我。他是個很危險,也很狡猾的人,她讓我認清他,不要再陷進去了,太危險了。
她的神色轉為憂鬱,原來,他一直在壓迫著她,還不僅僅是監視這麼簡單。她擔憂地
搖了搖頭,說:“你是鬥不過他的,再下去就危險了。”
我學著她的語氣,微笑著說:“誰在乎呢?”
她卻很認真地望著我,鄭重地說:“我在乎!”
雖然我們的關係又近了一層,可是我的狀況卻越來越差了,我甚至根本就沒有作品。還好布薩維回來了,坐在鋼琴前,為我彈了一首她的新作品,是一首深沉中不乏亢奮和震蕩的曲子。我對她說:“這是你的作品?那你的風格變了。”
“喜歡嗎?”
“非常喜歡。”
接著我就向她訴說了我的狀態,然後我長長地嘆了口氣,真不知這樣的狀態會持續多久。
她溫和地鼓勵我:“努力吧!”
我報以微笑,望著她的眼睛說:“我會的。”
可是人生常常會事與願違,我發現時常會有人跟蹤我,好像預示著危險就要來到了。而且她也開始不理睬他了,好像我們要力圖擺脫他的束縛。
在浴室里,她端著杯酒,彷彿若有所思:“他就是喜歡控制女人,算是我遇上的最倒霉的事情了。我知道他們是不會放棄我的,所以我會拒絕他們……但是我知道他們還會再來的,我知道的……”她自顧自地點著頭,喝盡了杯子里的酒。我站在離她不近的地方,看著她,有些懷疑她是醉了。
我取出浴巾,將赤裸裸的她包起來,然後抱著她走進卧室。她在我的懷中發出呵呵嗚嗚的含混不清的聲音,像個孩子。我將她輕輕放在床上,然後就走了。我知道今夜她需要安然入睡,而不是我的陪伴。
黑夜遲遲不肯降臨,可我們卻只是黑暗中的精靈。
我已經好久不去上課了,畫筆也好久不拿了,我只是還會去上早上的課,可是依舊是沒有精神。我也不常去酒吧了,她叫我遠離是非之地,不過我還會時常地站在酒吧門口,遠遠地看著她,看著她被一個個男人接走。
有時我們見面,感覺也會不好。
那天我站在她的化妝間門口,看著她煩躁地點煙,在房間里走來走去,“真是糟透了,鋼琴師不能來了……今晚可是要來大人物。”
“你就是大人物。”
“那只是你這樣看。”
“你不必總是看男人的臉色。”
她吐出長長的煙圈,從鏡子里看著我。突然,她撲到我身上,我們立即粘在一起。她興奮地說:“和愛人做愛真他媽的爽!”她把雙手插進我的指縫間,然後向上舉起,我們就是那樣的親密無間。
她接著說:“但是激情不能持久,沒有激情,就沒有愛人,不管你的態度如何……你可真是個性感尤物。我一點都不好,配不上你,你還是離開我吧。”她放下了我的手,親吻我的嘴唇,她的小腹在我的身上摩擦著,熱度升起。
“我配不上你,我只能配的上他們。”說著,她的身體再次貼近,“我們以前就是這樣做愛的。Lover,你喜歡嗎?”
她的身體像一條舞動的蛇,在我的身上游移,帶來熾熱的溫度。她喃喃地說:“我來高潮了,來呀,Lover,來呀……”於是,我們再度爆發。
之後,她背對著我,好像從袖子里拿出了什麼。我愛撫著她的後背,為她理著髮絲,問她:“那是什麼?”她好像並不願意告訴我,在我的催問下,她打開那張紙,讀了起來:“離開她,否則就會有人……”。
她的聲音黯淡起來:“你知道的,一直有人逼我做某些事情……”
我打斷她:“但是你沒有做。”
她低著頭,看著地面:“是的,我沒有做。所以,我要和你在一起,不管代價如何。”她向後仰,靠在我的膝上,臉上有些微的笑容:“現在我們很幸福。”她滿足地對著我笑了,那一刻我真的感到很幸福,知道這世上還會有一個人為了和你在一起,願意付出任何代價,會有比這更令人感到幸福的事情嗎?
我知道我遇上麻煩了,只有去找布薩維。她果然是我的知己,我還沒有說究竟是遇到了什麼麻煩,她就果斷地說:“我來幫助你排憂解難。你知道我可以的。”
她用堅定的目光告訴我,什麼事情都不值得煩惱,一切有她。於是,我笑了,調皮地問她:“可以多久?”
“你想多久都可以。”她伸出手,放在我的膝蓋上,很有力度,好像要把身上的力量傳給我。我們互相對視著,笑了。
我跟著他進了一家小酒館,向酒保要了一杯酒。然後又為他要了一杯,他喝乾了酒杯里原來的酒,卻故意放倒了酒杯,把我給他要的酒灑在桌面上。然後不屑地看著我,又伸出一隻手指,沾了一點酒,用舌尖舔了舔。他在挑釁,我知道,我們就那樣懷著敵意,彼此對視著。我要告訴他,我並不怕他!
他的出現還是會讓她害怕,雖然她會大聲地讓他滾開,可是趕走了他,她就會更緊地摟住我,更瘋狂地和我做愛,好像世界末日就要到了。她說她不能沒有我,而我在內心告訴自己,她是我的,沒人能搶走她。
我去老地方找布薩維,我們一起打了他的來找茬的保鏢,可是這不能解決什麼問題。
那一夜他還是帶著保鏢找上門來,男人畢竟還是強勢的動物,他們以暴力搶走了她的金飾,砸亂了屋子裡的擺設,也弄壞了我們的心情。她憤怒地說:“他控制不了我!”,但是我們都知道,擺脫這種束縛要付出多大的代價。
接下來的日子,我們的生活被塗上了灰色。我們躺在床上,她背對著我,想著心事。後來她說她認為她就是那個該受到報應的人,她怎麼會有這種想法呢?我要讓她重新快樂起來。
於是一夜又一夜,一個酒吧又一個酒吧,我跟蹤著他。我像一個獵手,在等待對猛獸的致命一擊。為此,我充滿了自信和冷靜,我要保護我最心愛的女人。我向布薩維要了一隻手槍,我想把它送給我的寶貝,讓她防身。
然而她卻在這座城裡消失了,我到處找她,卻不見她的蹤影。可是我卻從調酒師的口中得知,原來他是這裡的老闆,這裡的東西都是他的,這裡的人也都是他的。我終於知道我
是在和誰斗,可是這又有什麼關係呢?我要保護她的決心不會改變。
晚上,我走在街上,讓他的保鏢給打了好多拳。
白天,我坐在她的化妝間,聞著她的香水,想著她的味道,她的身體,她的一切……
我在酒吧里等她,還是不見她,可是他卻進來了,得意洋洋地向我大笑,彷彿在宣告他的勝利。於是我氣憤地回到畫室,拿出抽屜里的槍。黑板上的“I am a gengtleman”,已經消失,我拿起粉筆,決絕地寫上:“I took the gun”,我知道一旦獵人拿起了槍,獵手或是野獸,總有一方會以血來祭奠的。
終於在旅店裡,我看到了她。她穿著一身飾以銀色亮片的白色晚禮服,打開門后,我們親密地接吻,她讓我看她,高興地問我喜歡嗎。我拿出了手槍,遞給她:“給你,你會用得著的。”
她放下了槍,低聲說:“你不知道我經歷了什麼……”她搖了搖頭:“算了,為什麼要你知道呢,都過去了。”我知道她一定是受了很多苦,就像我不會將我的遭遇告訴她一樣,她也沒有告訴我,但是我們是那麼彼此深深地記掛著對方。
我到酒吧里去找他,我要和他決鬥。於是,他帶著我來到地下室,我先是給了他幾拳,但是他一有機會喘息,就使出了渾身解數,將我打倒在地。我真的是打不過他!耳邊傳來她急促而溫婉的歌聲,難道我真的保護不了她?我的心裡充滿了苦澀……
我只好回家。洗完澡,我躺在床上,彷彿所有的意識都被抽空了,我只能獃獃地看著天花板。不知什麼時候,布薩維進來了,她側卧在我的身旁,握住我的手:“要我做些什麼嗎?”
“留下來陪我。”我真的是覺得屋子裡好空、好靜,此時我感到自己的虛弱,好像只有布薩維能安慰我。
第二天,我從睡夢中醒來,布薩維已經走了。我看到她在小黑板上留的字:“I’m with you whatever you do(無論你做什麼,我都支持你)”,於是我又有了力量,我也必須有力量,我的寶貝還在等著我。
我去找她,她告訴我買瓶香檳,然後在窗子下面等她。我買好了香檳,在樓下來回地踱著步子,只見她的身影在窗帘上投出大大小小的影子,就是不見她叫我上去。
於是,我決定自己上去。推開門,我看到赤裸的他,躺在她的床上,熟睡著。我看了她一眼,臉上的微笑消失了,放下香檳,然後走出房間。
沮喪、傷心、無奈、憐惜、痛苦……很多種感受在我的腦袋裡膨脹,就要炸裂開了……我搖擺,我晃動,我要自己完全地沒有意識。可是我真的做不到。
但是,我還是情不自禁地想見她。於是,我和往常一樣去她那裡,我沒有問什麼,也沒有說那天的事。她微笑著問我,是要葡萄酒還是要伏特加。今天的她很高興,開心地對我說,她要帶我去出海,去很遠很遠的地方。她看著並不開心的我問:“怎麼了,Lover?”
我好像是突然下的決定:“我要走了。”
她的笑容凝結在臉上,讓人看上去很難受。她走過來,柔聲地說:“Lover,抱著我嘛。”她的眼神轉為悲哀,“和我說話呀。”
她摟緊我,可是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麼了,居然會那麼狠心地對她說:“我不得不走了。”然後沒有一個告別吻,沒有一聲再見,我就跑下樓去。其實我是怕自己狠不下心,半途而廢,我們的愛情已經傷害了彼此,既然我已經保護不了她,為何還要繼續下去呢?
在樓下,我的步子又猶豫了,或許她會難過,或許她會……我終於轉身,可是我沒有上樓,因為他的保鏢擋住了我,我只有走掉,不管心裡有多麼惦記她。
我就那樣走呀走呀,不知走過了多少天,反正好像是很多天。沒有小鳥,也沒有太陽,沒有光線,也沒有人群……一切在我眼裡都是簡單的鉛色的線條。
我的腦袋裡浮現的都是她,她的房間,她的演出,她的男人……樹在晃動,河水在顫動,我聽見她的呻吟聲,她對我的呼喚。於是我就畫她的裸像,我用紅色和藏青色勾勒她的線條,紅色是她的火熱,青色是她不幸的生活。她應該是紅色的,可是藏青卻成了她必不可少的顏色。這兩種顏色混合,混合……混合成一個美妙而極富動感的她。
我實在受不了這種日夜想念的狀態,決定去找她。在樓梯上,就聽到兩聲槍響,於是我快步走上去,輕聲地呼喚:“寶貝,寶貝……”
我走進卧室,看到了躺在地上的他,他死了。她躺在床上,襯衫敞開著,右肋處沁出一圈殷紅,槍就在她的身側。這就是我的寶貝嗎,此刻她已經奄奄一息。她微笑著看著我,用她好有磁性的嗓音對我說:“你聽到了嗎,兩聲槍響,Lover?”這是她最後這樣叫我了,我知道。
我愛撫著她的頭髮,看著她慢慢地閉上眼睛睡去,這是我最後一次看她,愛撫她,我知道……

女孩
演員表
| 角色名 | 演員名 | 配音 | 備註 |
|---|---|---|---|
| 阿納斯蒂 | 克萊爾·凱姆 | ||
| 女畫家 | 阿加特·德拉 |
職員表
| 總導演 | Sande Zeig |
|---|---|
| 編劇 | Monique Wittig Monique Wittig |
| 配樂 | 理查德·羅賓斯 |
| 剪輯 | 傑拉丁·佩羅尼 |
《女孩》很像一出四幕戲劇。河邊、酒吧、畫室、卧室等四個場景都很像提純后的戲劇布景;主要角色只有兩個。三個配角:夜總會老闆巴斯克、保鏢、黑人女模特的對話極少。這種有意的精練主要是為了給兩個主角的情感、心理創造足夠的空間,以集中表現那種瀰漫於現實時空和心理時空的精神追尋。視覺和心理的提純使得影片寧靜純粹的畫面與內斂的表演、“經濟”的音樂融匯在一起,形成一種“間離”,構造著影片的冥思風格。
男子氣是一種具有保護性、因而也有專制性的東西。阿納斯蒂的生活中有男性,然而她仍然在尋覓男子氣,從男性化的女性身上尋覓。我們只能理解為她不是在尋覓男性,而是面對孤獨、寂寞時對男性氣質的一種填充。當情慾、犧牲都無法撫平寂寞的心靈時,剩下的就只有絕望。
女畫家對阿納斯蒂的愛、對男性的挑戰則是以肉體的實在印證精神的存在。
阿納斯蒂尋覓的結果是絕望;女畫家尋覓的結果是超越肉體的精神而不是肉體實在本身。所以阿納斯蒂只能以自殺結束,女畫家只能在記憶中繼續“情人”的惘然。
桑德·澤格把這個“簡單”故事拍得凄美、纏綿,韻味雋永。
影片窮盡著視覺表現的同時,也在窮盡著人性的追問。
影片第一個鏡頭:一個女孩美麗的足踝由銀幕右側入畫,女主角走在幽深的石板路上,走向鏡頭遠景。景別由開始的近景變為全景。本片另一個女主角——一個沒有露面的女畫家的畫外音娓娓道來,告訴我們女孩是孤兒,遠離故鄉,獨自一人住旅館,在夜總會做歌手……
一個鏡頭一個段落,光影、環境都近於黑白片,女孩的背影漸行漸遠。畫外音和畫面共同傳遞著一個信息——孤獨。孤獨的女孩才會撥動另一顆孤獨女孩的心。
桑德·澤格經常以這種由身體局部引出全景段落的敘述方式,規定你的視角、確定審美取向,不斷地以實在的肉體形象與精神空間形成對照。
兩個孤獨的女孩在夜總會第一次相會。她——那個女畫家覺得唱歌的女孩——阿納斯蒂“把世界上的一切都比下去了”。也許我們會懷疑世界上是否真的存在可以把一切都比下去的女孩,然而人的內心在特定時刻的確需要一個實在的象徵物,如果沒有,人也會本能地要填充一個。
他們在相會的第一個夜晚就相愛了,愛得酣暢淋漓,纏綿熱烈,小鳥依人的阿納斯蒂當然是“女性”角色,女畫家充當男性角色。桑德·澤格沒有交代倆人走到一起的原因,影片經常這樣,不說過程只表現結果。也許阿納斯蒂為女畫家那種職業性的觀察所懾服?也許女畫家的職業使她更中性?也許兩顆孤獨的心不需要說緣由?纏綿之後阿納斯蒂曾對女畫家說:“感覺你就像一個帥氣的小伙,可惜只有一夜。”這樣的表白也只是顯露著她們在纏綿和熱烈掩蓋下的心靈孤寂,並非交代緣由。
這種有意不交代反而為我們留下更大的想像空間,使我們更關注影像本身,使影片更視覺化。
桑德·澤格幾乎在每一個重要的段落都會表現女畫家在同一條河岸的徘徊、等待。你不知道她在等待什麼,但是你會感覺人生總是伴隨著等待。5歲的孩子會等待,50歲的成人會等待,150歲——假如人可以活得那麼久,也在等待,歲月就在等待中流逝,人卻又說不清到底等待什麼,也許只在等待樹上無意飄零的花瓣,也許只在等待樓頭轉瞬即逝的燈光,也許只在等待天涯孤旅中恣意揮灑的淚痕……其實,最終等來的大概只是無法捉摸的永生惆悵。
第一次做愛后女畫家也在河邊、樓下重複著這種等待。桑德·澤格通過鏡頭組接既表現了現實的等待,也表現了心理的等待。表現夜與晝的變化時,她用了一個白閃的技巧。表現空間變化時,她用了一系列的主觀鏡頭:夜色中的花兒,燈火明滅的窗,房子,還有阿納斯蒂與一個青年男人的神秘離去都是女畫家的心理物像,是心靈的渴望與孤獨的物質呈現。而影片那種很少出現,因而顯得很經濟、舒緩而又不安的音樂更是對心理空間的另一種擴展。
《女孩》是一部非常視覺化的影片。
又一次做愛后,女畫家為阿納斯蒂畫像,阿納斯蒂卻莫名其妙地驅逐女畫家,女畫家回到畫室,對照草圖開始為阿納斯蒂作畫,影片最後也以女畫家完成畫作為結。始於繪畫,終於繪畫,桑德·澤格的結構精緻、完整。
女畫家發現阿納斯蒂身邊出現一個男人,阿納斯蒂必然顧此失彼,桑德·澤格用一個意味深長的俯拍全景鏡頭表現這一對同性戀人心理的微妙:倆人在夜色中擦肩而過,沒有對話,卻讓我們感覺出,“他”無所謂,“她”則品味著“他”的無所謂……
第三次幽會時,她為“他”起名——“情人。”“他”說夜晚是“他”的;城市是她的。他們把實在的美好和他們的情感連在一起,使他們的情愛實在而又迷離。
在倆人的情感空間之外桑德·澤格還表現了另外兩個空間,一個等待阿納斯蒂的男人,一個與女畫家十分親密的黑人女孩。女畫家在自己的畫室,在塗滿整面牆的紅色、以及紅色一角,她的白色背影畫像前與黑人女孩親熱,爾後她在旅館門前目睹那個男人強迫阿納斯蒂……
桑德·澤格把實在的肉體之美與形而上的精神追問結合在一起。“情人”曾經與阿納斯蒂共浴,桑德·澤格把兩個女人體拍得猶如美人魚,光潔、細膩、柔美、誘惑,清晰、真切得似乎觸手可及。誘惑時刻卻總是充滿一種幻滅感:“每次和你在一起,都是最後一次。”越是美麗,越是真切,幻滅感越強烈。“我不想這是最後一次,我是你的。”“我喜歡男性化的女孩,尤其在床上。”桑德·澤格總是讓阿納斯蒂在兩情相悅時流露出莫名的幻滅,總是讓視覺感受和人物心理形成一種反差,創造痴迷的極致,暗示幻滅的前景。
“情人”終於見到了那個糾纏阿納斯蒂的男人——夜總會老闆巴斯克。阿納斯蒂告訴“情人”:有人總是逼我做事,我不願意……
“情人”試圖與巴斯克像平等的情人那樣相識,遭拒絕。
巴斯克更頻繁地糾纏阿納斯蒂,“情人”不得不負起保衛的責任。她和女黑人一起在街頭酒吧與巴斯克的保鏢交鋒,這樣的交鋒或者說決鬥後來進行過幾次,最終失敗的當然是“情人”,無論多麼英勇,多麼不屈,畢竟只是有男子氣的“女人”。女人無力挑戰一個傳統社會。
“情人”把挑戰的犧牲視為一種必然:“我要得到,也要付出。”
巴斯克終於把阿納斯蒂劫持。孤獨的“情人”持槍四處搜尋阿納斯蒂,與巴斯克的保鏢決鬥。當“情人”終於找到阿納斯蒂時她沒有解釋失蹤的原因。“情人”把槍給了她:你會用得著的。
影片最後一次由阿納斯蒂的局部美麗肢體開始夜總會段落。演唱結束,她婉拒“情人”上樓的慾望,原來巴斯克躺在她的床上。顯然失蹤期間阿納斯蒂與巴斯克有了“情人”無法弄清的約定。
“情人”第一次獨自跳舞,鏡頭隨著她的舞姿向下搖動,呈現出她舞動的倒影——一切都顛倒了,她們的情感,她們的心態。“情人”第一次拒絕與阿納斯蒂親熱,然後在河邊長時間徘徊,桑德·澤格用快速切換表現“情人”的心理空間:黑白繪畫、此前曾經出現過的生活場景,變形的影像和兩個女人的放大的喘息……
然後桑德·澤格又用長達3分鐘的段落表現“情人”完成阿納斯蒂的大幅畫像,以分切得很細的局部表現她為阿納斯蒂的迷人軀幹著色。完成後的畫像是“情人”對阿納斯蒂的全部美好印象——生理的、心理的美的總和與升華。畫像有著躍動的線條,厚重的色彩,沒有臉的細部——也許她總算找到了阿納斯蒂心靈的印象時刻?
完成畫像的“情人”找到阿納斯蒂,她無助地躺在床頭,腹部有一個流血的彈孔;巴斯克俯在地下,已經死了。她用“他”的槍結束了一切。
她抬頭望著“他”:你傷心嗎,情人?
這既是對“他”的追問,也是對一切情人的追問。
桑德·澤格在本片體現出的主要風格元素:
1.對現代人孤寂心態的關注。
2.內心獨白和視覺語言結合。
3.對話少而精練,幾乎都不是直接的敘事,而是內心的傾訴。
4.由諸多結果累積絕望情緒。
5.以人體局部代替全體,常常由局部引出新的段落。
6.音樂不多,但與情緒直接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