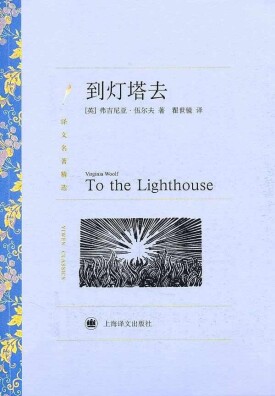共找到2條詞條名為到燈塔去的結果 展開
- 英國弗吉尼亞·伍爾芙創作的長篇小說
- 2019年敏感詞出版的圖書
到燈塔去
英國弗吉尼亞·伍爾芙創作的長篇小說
小說以到燈塔去為貫穿全書的中心線索,寫了拉姆齊一家人和幾位客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的片段生活經歷。拉姆齊先生的幼子詹姆斯想去燈塔,但卻由於天氣不好而未能如願。后大戰爆發,拉姆齊一家歷經滄桑。戰後,拉姆齊先生攜帶一雙兒女乘舟出海,終於到達燈塔。而坐在岸邊畫畫的莉麗・布里斯科也正好在拉姆齊一家到達燈塔的時候,在瞬間的感悟中,向畫幅中央落下一筆,終於畫出了多年縈迴心頭的幻象,從而超越自己,成為一名真正的藝術家。
伍爾芙的母親在她十三歲時去世,她對於母親形象的描述一直停留在她腦海中,母親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她的愛好,她的生活習慣,都在伍爾芙腦中揮之不去,給她留下了深刻的記憶。在伍爾芙二十二歲時,父親去世,父親的形象也永遠地停留在她的腦海中。正是這種深刻的形象令她十分糾結,並一直困擾著她,於是,為了能夠將父親與母親的形象以及與她的情感真正的抒理清晰,她決定寫一部小說。《到燈塔去》中所塑的兩個主要人物拉姆齊夫人與拉姆齊先生的原型正是伍爾芙的父母親。伍爾芙在寫這部小說時,身體逐漸恢復了健康。在她的創作過程中,她盡情地抒發著自己的情感,將自己腦海中多年來儲存的記憶全部揮灑出來,並以最快的速度進行著創作,這種創作是無法歡暢的,是以往的創作所無法比擬的。在《到燈塔去》中,塑造了許許多多不同的人物形象,除了拉姆齊夫人與拉姆齊先生外,還有莉莉、詹姆斯、凱姆、羅傑、等等,這些不同的人物在伍爾芙的生活中都曾出現過,並與她有著各色的聯繫與交集。
小說中的拉姆齊先生正是伍爾芙父親的原型,二人有著極多的相似之處。都是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分子,在家庭中有著絕對的權力和地位。拉姆齊先生是一位現實、嚴謹的哲學家。他崇尚理性思考,痛恨幻想誇張。伍爾芙用二十六個英文字母和鋼琴的鍵盤來象徵拉姆齊先生那種直線型的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模式使他難以看到事物的整體,結果導致他身陷智慧的泥沼,無法將事業開拓推進。在妻子看來,拉姆奇先生“對於平凡的瑣事,生來就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不置一詞;但對於不平凡的事情,他的目光像兀鷹一般敏銳。”“他的目光並不去注視他的妻子正在仔細察看的花朵,”當他舉目注視時,他看到的只是紅色或褐色的某個東西。他在窗外平台上來回踱步的形象表現了他對自己在學術上停滯不前感到焦慮不安。小說中幾次出現“貧瘠、光禿”“黃銅的鳥嘴”“渴血的彎刀”等意象來象徵拉姆奇先生強烈的自我意識與他自私的個性。
拉姆齊先生試圖憑藉理性與邏輯來解釋和處理世上的一切。他在現實生活中,對任何事實都頂禮膜拜,從不肯為讓他人感到愉快而改變一句不中聽的話。拉姆齊先生教育子女們,同樣堅持現實與真理。他教育孩子們的指導思想是:“他們……必須從小認識到人生是艱辛的,事實是不會讓步的,……一個人所需要的最重要的品質是勇氣、真實和毅力。”但在客觀真理和現實生活之前,充滿著童稚與幻想的幼小心靈常常會受到傷害和打擊。小兒子詹姆斯就是受不了父親堅持客觀真相時的嘲諷和挖苦。詹姆斯想在第二天駕船到小島上去看燈塔,拉姆齊先生卻全然不顧兒子的熱情和願望,斷言明天的天氣不會好,不能去燈塔,甚至因拉姆齊太太對兒子“也許明天天氣好”的安慰而頗為氣憤。
拉姆齊夫人美麗賢惠,善於持家,喜歡幻想,注重感性,是感性世界中的完美女性,拉姆齊夫人竭力使孩子幼小的心靈不受到客觀真理的傷害。當凱姆害怕野獸頭骨和詹姆斯喜歡時,她沒有粗暴地拿走,也沒有置之不理,而是用自己的頭巾將它巧妙地遮掩起來。象徵著殘酷事實的野獸頭骨頓時使客觀真理的突兀之處變得柔和了許多,於是凱姆認識到殘酷的事實是客觀存在的,而詹姆斯則意識到了真理以外感性的力量。現實是冷酷和麻木不仁的,令人不安和焦慮,那麼怎樣和與它抗爭,從而達到內心的和諧安寧,一切井然有序呢?拉姆齊夫人的法寶是博愛眾生,用她女性的感性和關愛,使周圍的人快樂滿足,從而抵禦那個不盡如人意的現實世界。
與刻板、理性的丈夫相比,拉姆齊夫人則顯得充滿了幻想。她熱愛自然的、美的事物。她把自己與燈塔發出的第三束光等同起來,將其視為自己的精神之光;當看到無生命的東西、樹木、花朵、河流,拉姆齊夫人感覺它們變成了同一個事物,在表達同一個聲音。在某種意義上,這些事物和她自己就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拉姆齊夫人對事物認識的經驗往往是個人的直覺或頓悟。在千變萬化的瞬間,她總能看到和諧一致、穩定永恆的因素,從而在混亂無序中找到平衡點,保持超然平和的心態。當忙碌完一天的家務,一切平靜下來,拉姆齊夫人便陶醉在無限的遐想之中。在那片《楔形的黑暗內核》里,她讓意識隨意馳騁,盡情放縱著自我,充分享受著精神上的自由。畫家莉麗同樣意識到在混亂中存在著秩序與平靜,在瞬息飛逝的變化中存在著永恆與安定。她和拉姆齊夫人一樣,是統一和諧、安祥平靜的使者。
在這部小說中,伍爾芙除了刻畫代表理性的拉姆齊先生和代表感性的拉姆齊夫人外,還描寫了另一位融合理性與感性的藝術家莉麗·布里斯科,莉麗是一個具有顛覆力量的女性角色。莉麗獻身藝術,想用手中的畫筆來描繪現實與藝術之間的一道橋樑,但是她發現消極的躲避與推脫是難以完成這一任務的。只有在夫人死後,脫離了夫人的庇護,她才有機會與她身邊的男性正面交往,從而直接體會到男性代表的理性的力量,正視自己作為女性的體驗與情感,同時也了解發生了轉變的拉姆齊先生的偉大之處:勇敢、自信、實際。這時的莉麗與男性達成了某種程度的和解,融合了理性與感性,所以她才滿意地完成了她的畫。諳熟理性的創作手法的莉麗,在創作中尊重色彩猶如拉姆齊先生尊重事實一樣,但一直無法完成作品。只有最後融合了理性與感性,才頓悟了永恆藝術的瞬間,在畫布上劃下了那關鍵性的一筆。一味追求理性只會限於理性的漩渦中停滯向前,無法創作出的優秀的藝術作品,只有理性融合了感性,才能重新締造中和諧有序的生活,創造出優秀的作品。伍爾芙創作中要堅持理性的思想,表現出一名藝術家對於藝術創作持有的理性思考。不僅如此,在伍爾芙看來,理性必須與感性結合,也就是說,作家必須具備一種理性的情感藝術觀,才能創作出經久不衰的作品。
在伍爾芙的女性主義主張中,莉麗正是她自己的化身。她從一個新的角度來審視家庭中的每一個成員,她欣賞拉姆齊夫人的溫柔優雅,在她去世后很久仍然非常懷念她,她熱愛藝術,能夠為藝術傾注所有的心血。她具有成熟的女性思想及獨立的精神,勇於拒絕婚姻,她依靠畫畫來展現自己的思想。她與拉姆齊夫人有著本質的不同,她把生活的希望都寄手在自己身上,寄托在藝術身上,所以,她不會擔心這一切支柱的消失。於是,她在藝術創作中盡情地展現自己的意念。在小說的最後,當莉莉看到一家人向燈塔駛去時,她對人生也有了更多的感悟,感受到了生命的真諦。
伍爾芙敏銳地把握住人們對理性與感性的困惑,把“二元對立”引用到小說創作中,力求表現複雜矛盾的內心世界。《到燈塔去》這部小說包含了生活中的許多矛盾、對立和不和諧,小說人物自身性格中的矛盾對立也被刻畫得入木三分。當然呈現生活中的矛盾對立並非伍爾芙的最終目的,尋求擺脫困境的途徑,以達到生活中的最終和諧,才是伍爾芙追求小說內容構思上和諧的初衷。伍爾芙的思想超越了傳統的二元論,她摒棄了二元絕對對立的思想,認為二元雙方既相互對立又互為補充,應該和諧共存於一種動態平衡之中。這種思想始終貫穿於伍爾芙創作中。《到燈塔去》這部小說集中體現了伍爾芙對理性與感性二元和諧的不懈追求。
在《到燈塔去》中,伍爾芙並不是要強調兩性差異,而是希望可以以燈塔作為一種對於美好生活的嚮往。小說中的拉姆齊夫婦為我們展現了生活中單一的色彩,但是生活這幅圖畫是由不同的色彩組成的。拉姆齊先生有男性的缺點與弱點,但是當他帶孩子重新走向燈塔時,他的生命也有了新的思考。他的自省也使小兒子原諒了他,二人終於和解。拉姆齊夫人卻如燈塔一般永遠守護著他,而小兒子詹姆斯身上也彰顯出了父母親所特有的氣質。
小說的第三部分“燈塔”展示了對立衝突的結束,也代表了男性和女性的二元對立徹底消除。拉姆齊夫婦的性格都是偏狹的、有缺陷的,夫人太過感性,過於女性化,而拉姆齊先生則走向另一極端,他們都不是作者心目中完美人格的體現。伍爾芙追求一種合理的兩性關係,拋開狹隘的性別主義偏見,在承認兩性差異的基礎上,把兩性差異進行完美整合,從而實現一種和諧的兩性關係。
小說中拉姆齊先生人格的整合,最終是通過拉姆齊先生克服片面的男性氣質,吸納拉姆齊夫人的心靈、情感、本能、直覺的女性氣質實現的。拉姆齊夫人死後,拉姆齊先生生活在一種孤獨和莫名的空虛之中,他開始對純粹的男性氣質產生了懷疑,他開始接受和欣賞夫人的女性的直覺思維方式。拉姆齊先生因失去了情感的慰藉而轉向莉麗習慣性地乞求同情和憐憫。莉麗雖然沒有向拉姆齊先生表達同情,也沒有斷然回絕。尷尬中莉麗稱讚起他的皮鞋來,把他的注意力從自怨自艾轉向腳下的皮鞋。對皮鞋的讚揚符合雙方的需要,是雙方都可以接受的。因為它既維護了莉麗獨立的自主性地位,也肯定了拉姆齊先生的自尊,從而讓他獲得某種程度的滿足,只是表達方式不同於拉姆齊夫人罷了。拉姆齊先生非但沒有生氣,反而笑了,雙方都得以解脫。看著拉姆齊先生露出笑容,莉麗在負疚中注視這一刻的效果,“她感到他們彷彿到達了一個陽光燦爛的島嶼,和平降臨了,理智戰勝了衝動,陽光永遠照耀,這是可愛的皮鞋帶來的幸福之島。她心頭一軟,湧起了對他的好感”。這也體現了莉麗個體身上的女性氣質和男性氣質從失衡到融合的過程。
在小說的第一部分,莉麗身上的兩性氣質並不平衡,表現在男性氣質佔優勢,如她反對篡改色調,堅持以理性的態度對待繪畫創作。同時,女性氣質的缺乏使她在人際交往中屢屢受阻。她也無法協調體現在拉姆齊夫婦身上的男女兩性原則,對於拉姆齊夫人她持否定態度,認為她對異性過於關切,過分強調婚姻的必要,認為“最糟的就是男人和女人之間的關係”,這種關係也是“極端虛偽的”。偏激的想法使她無法與異性建立有效的溝通,對婚姻的偏見使她人到中年仍孤身一人。雖然她對繪畫熱愛並孜孜不倦地繪畫,但成就微小。女性氣質的喪失就意味著敏感的喪失和藝術感官的鈍化。莉麗花費了10年時間,仍然沒法完成畫作。她不知道該如何安排她畫布上的“空白處”,她無法找到一種方式來平衡畫面上的空間。
10年後重返別墅的莉麗對於拉姆齊夫婦有了新的認識,她不僅發現拉姆齊先生開始對人熱情、關切,而且在對夫人進行追憶時,認識到她身上所具有的女性的包容、關切。對於生活和兩性原則的重新感悟和調和,使莉麗的內心不再偏激和不平衡,達到了理性與感性、客觀世界與主觀世界融合的完美境界。最後,莉麗終於在拉姆齊一家到達燈塔的時候,獲得了新的創作靈感,一舉完成了多年前一直不能完成的繪畫,畫出了在她心頭縈繞多年的幻景,實現了雙性同體在藝術上的完善。
綜上所述,在伍爾芙的《到燈塔去》中,她始終堅信男女之間雖然有著各自不同的特質,但是最終仍然走到一起,達到力量的平衡。藝術的完美體現正是兩性的完美交融。正如小說中的燈塔一般,女性主義的奮鬥目標最終都會實現。
象徵意象
小說中的象徵意象豐富多樣,從燈塔,窗口,莉麗的畫,到燈塔去的航行,到大海,岩石,籬笆,以及拉姆齊先生吟詠的詩句,都是對作品意義的建立有著重要作用的意象。
《到燈塔去》中燈塔本身就暗示著諸多意義。作為一種象徵意象,燈塔是集合了時間與永恆的重要的複合體,一個拉姆齊夫人主觀意識的客觀對應物。在拉姆齊夫人辭世后,燈塔象徵著她身前的生存意義。對於拉姆奇夫婦的小兒子詹姆斯來說,燈塔在他童年時期是“一座銀灰色的、神秘的白塔,長著一隻黃色的眼睛,到了黃昏時分,那眼睛就突然溫柔地睜開。”神秘的燈塔成了小詹姆斯日夜的期盼。但當他長大以後,真地駕船駛進燈塔時,卻發現那只是一座“僵硬筆直屹立著的燈塔,”上面還有幾扇窗戶和晾曬的衣物。詹姆斯疑惑了,“這就是那座朝思暮想的燈塔了,對嗎?”“不,那另外一座也是燈塔。因為,沒有任何事物簡簡單單的就是一件東西。”燈塔使小說中的人物和讀者聯想到生活中似乎遠不可及可又近在眼前的事物。雖然它僅是一座人造的建築物,但卻擁有永恆的本質,因為它是在時間的流逝中創建出來,引導人們去控制、抗擊那些毀滅性的力量。封於燈塔內部的是人類的傳統及其價值,它通過自己的光輝講述著人類的統一和延續。孤島上燈塔的光亮越過黑暗的海水射向對岸,照亮了人的心靈。只是這種光與心靈之間的對話由人來決定。拉姆齊夫人將塔光與自己的個性統一起來,認為這光就是自己的真理之光,它美麗、嚴峻、善於探索;同時她也覺得這塔光是無情不變的,因為它總能夠以某種方式去照亮和凈化人的本質。
雖然許多評論家注意到了燈塔與拉姆齊夫人之間的獨特關係,但也不乏將燈塔視為拉姆齊夫婦整體代表的讀者。當詹姆斯駛船靠近燈塔時,童年時燈塔的印象油然浮現在眼前: 朦朧、神秘、溫柔,使人充滿幻想; 而現實中的燈塔卻面目全非:僵硬、挺拔、孤單。孩提時詹姆斯印象中的燈塔和他實際看到的燈塔無疑是他母親與父親性格的象徵。對燈塔溫柔與嚴苛兩面性的描繪表現出弗吉尼亞·伍爾芙相信世間存在著男、女兩種基本生活原則。這兩種原則的對立對於男、女兩性具有重要的價值,因為正是兩者鮮明的差異使男女兩性之間形成一種制約、互補關係,進而保證了兩性關係的和諧、統一。由此,燈塔成為一個“雌雄同體”的象徵,當然,這只是伍爾芙對兩性關係所寄予的烏托邦式的理想而已。但至少她向我們提出一種思想:“在我們之中每個人都由兩個力量支配一切,一個男性的力量,一個女性的力量。......最正常,最適宜的境況就是在這兩個力量一起和諧地生活、精誠合作的時候”。這一觀點在一定程度上同傳統的以男性為中心的批評觀點和由男性控制、支配女性的政治策略形成鮮明對照,也可以看作是對性別二元對立進行解構的一種最初嘗試。
性愛及母性問題是伍爾芙圍繞燈塔重點探討的問題之一。拉姆齊夫人、畫家莉麗、時時凝望著燈塔,提出這樣那樣的疑慮和想象。弗吉尼亞伍爾芙利用自己的女性人物亦提出諸如“女人需要的是什麼?” “女人必須扮演妻子和母親的角色嗎?”等問題。燈塔折射出的多元的意義從不同層面為這些問題提供了答案。但另一方面,燈塔多棱的光輝又使這些答案顯得撲朔迷離。其實,小說中的不確定性不僅僅反映了伍爾芙的創作風格,而且折射出她對社會、世界的理解與認識。伍爾芙曾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我們處在一個對一切都無法做出結論的世界里。”那麼,對於一部作品來說,它之所以讓人難以做出結論,是因為它的意義是通過讀者來實現的; 不同的讀者從各自的認識和經驗出發,自然會對同一部作品做出不同的理解和詮釋。伍爾芙用她流水般詩情畫意的象徵性語言為讀者創造出的不只是一個空靈、多彩的世界,而且也給讀者提供了同作品、同作者對話的空間。
除了燈塔,“窗”也是小說中一個具有中心意義的象徵物。傍晚時分,拉姆齊先生常在窗外的平台上踱步,思考、討論他的學術問題。拉姆齊夫人及其幼子詹姆斯則坐在窗邊觀望著外面的景色和拉姆齊先生的一舉一動。作為小說第一部分標題的《窗》將客觀世界與拉姆齊夫人那不易被人覺察的主觀意識分隔開來,同時也為夫人提供了一個將自我和現實融為一體的機會。通過窗,拉姆齊夫人觀察著世界,審視著自我與生活。常常在一瞬間,窗內外的景色和靈光使她獲得真諦,實現了個人對主、客觀世界的整合。
《到燈塔去》中的“窗”就是一個意象。通常人們把窗戶當作一種與外界交流的通道。在《到燈塔去》中,“窗”不僅僅是小說第一部分的標題,還是整部作品中的一個重要意象。和窗的傳統內涵不同的是,窗在《到燈塔去》中的逆變意象體現在它不僅象徵著內部世界和外部世界溝通,同時還象徵著這種溝通的局限性和不完整性。
和所有窗口的作用一樣,拉姆齊一家在海濱別墅的窗口是溝通窗戶內外世界的一個框架。窗內的人認識窗外發生的一切,窗外的人也通過窗口觀察窗內的動靜。坐在窗內的拉姆齊夫人任何聲音都極其敏感。“正當她翻著書頁尋找千草耙或刈草機圖片的時候,她被突然打斷了。窗外粗噶的低語聲,… 雖然她聽不見他們在談些什麼,那低語聲使她能夠肯定男人們正在平台上暢談,這談話聲已持續了半個小時…”拉姆齊夫人常常在窗口看見丈夫和塔斯萊談論文學,探討時政,辯駁學術。她不了解男人們為何對這些爭執不休。每當她抬起頭,外面的世界便通過窗口投射到她的眼裡,接著又引起她腦中不斷涌動的思緒,使她時時陷入沉思。夫人通過窗口觀察拉姆齊夫人,觀察著賓客,觀察著正在作畫的莉麗。當她望見威廉·班克斯和莉麗經過窗前時,“她嫣然微笑,因為這時在她腦袋裡閃過的可是個好主意———威廉和莉麗應該結婚”。拉姆齊夫人的熱心善良和感性由她在透過窗戶觀察世界的舉動以及投射在她心中的意識描寫顯現出來。
當然,窗也象徵人們對事物認識的不完整性。莉麗十年前在畫布上勾勒出她從窗口觀察到的夫人的形象,但總不夠清晰明朗。雖然莉麗覺得夫人像女神一樣美麗、嫻雅,富有活力,充滿同情心,她還是隱隱感到夫人身上存在著某種不和諧的東西。她知道要真正地了解夫人,就必須尋求夫人胸中隱藏的秘密。可是夫人心靈密室的大門一直緊鎖著,直至十年後,莉麗重返舊地,還是不能如願以償,此時,夫人已仙逝遠去。共同養育了八個孩子的拉姆齊夫婦感情深篤,但他們並不完全了解對方的思想。坐在窗口的拉姆齊夫人望著窗外丈夫的身影,為他卓越的頭腦感到驕傲; 不過有時她又覺得丈夫的行為顯得那樣奇怪、那樣不同。為什麼他總沉溺在抽象的思維中看不到身邊一切美的事物呢?拉姆齊先生從遠處看到獨自坐在窗前沉思的妻子時,雖覺得“她姿容絕世,”但“在精神上和他距離很遙遠。”拉姆奇夫婦精神上的疏離感源自雙方認識上的差異。拉姆齊夫人對事物的認識往往是感性的,因此她敏感、誇張、愛幻想; 拉姆奇先生從理性的角度對待問題,所以他嚴謹、苛刻、不易變通。顯然,窗的意象折射出人類主觀意識與客觀現實之間的矛盾,以及人意識上的差異性。
在《到燈塔去》中,伍爾芙沒有採取直接內心獨白的方案,而是藉助間接內心獨白來反映人物的思想,行為和性格。在敘述中,利用第三人稱他者來講述,人物角色的心理活動也通過作者的加工和重組后再間接呈現,使褥人物角色的言行都具有了連貫性和邏輯性。作者在這裡的作用是領讀者,導航人,來帶領普通讀者充分理解人物的言行與思維。在第一部分的第一章中有這樣的一段話:
爭吵、分歧、意見不和、各種偏見文織在人生的每一絲纖維當中:啊,為什麼孩子們小小年紀就已經開始爭論不休?拉姆齊夫人不僅為之嘆息。他們太喜歡品頭論足了,她的孩子們。他們簡直胡說八道,荒唐透頂。她拉著詹姆斯的手,離開了餐室。
這段話反映了拉姆齊夫人對於她的孩子們都對坦斯利存有偏見而感到反感。除了拉姆齊夫人的思考之外,還包括作者對讀者的引導一一“拉姆齊夫人不僅為之嘆息” ,以及全知視角的轉換——她拉粉詹姆斯的手。離開了拐室。這種解讀對於讀者把握拉姆齊夫人這個中心人物是很有必要的。接下來是第三部分中到燈塔的旅途中,女兒凱姆的有一段內心獨白:
凱姆又把她的手指漫在波濤里,她想,原來他們居住的這座島嶼就是這般模樣。她開始給自己編造一個從沉船上死裡逃生的故事。她想,我們就這樣乘上了一葉輕舟。她心裡在想:為了她不懂得羅盤的方位,她父親是多麼的生氣;
三次插入了“她想”,對於理解凱姆的個性和父女關係是很重要的。凱姆自幼就桀驁不馴,容歡奔跑和粗每的舉止,而且腸遭父親的痛斥,這些都造成了凱姆對干父親的感受和自我的放逐。另外作者還用到了插入語來對發生的對話,情節進行安排和解釋。在第一部分中莉麗甘對班克斯有這樣一段內心獨白:
我尊敬您,她在內心默默地對他說,在各方面完全尊敬您;您沒有妻室兒女,她渴望著要去撫慰他孤獨的心員,但是不帶任何性感;您為科學而生存,不由自主地,在她眼前浮現出了一片片馬鈴署的標本;讚揚對您來說是一種侮辱;你真是個寬宏大量,心地純潔,英勇無畏的人啊!在這裡,“她在內心獻獄地對他說” ,“她渴望,要去撫慰他孤獨的心員,但是不帶任何性感”。“不由自主地,在她面前浮現出一片片馬鈴署標本”就是作者對莉麗內心獨白的解釋和說明,以便使讀者更進一步地了解兩個人之間的情愫。
《到燈塔去》整個故事像這樣的實例還有很多,就是因為伍爾芙嫻熟的運用了間接內心獨白的方法,才使得整個故事接近完整,脈絡清晰。
伍爾芙利用了大量的意識流的寫法,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自由聯想。自由聯想往往沒有固定的模式一般是角色在面對一件事情的時候,突然聯想到其他的人或是事情,也不受時間空間的影響,因此也變成了讀者在解讀文本是最困惑的地方。
《到燈塔去》第一部分的第五章中,伍爾芙描述的客觀事實很清楚. 就是給兒子詹姆斯的襪子,以便給燈塔看守人的男孩織襪子時不會有太大的出入,這樣簡單的動作一兩分鐘就可以結束,卻用了作者四頁半去描述,其間的文字大多是自由聯想。拉姆齊夫人從窗口姍到班克斯先生和莉麗經過,就想粉他們要結婚;抬頭看到自己的丈夫和他的學生,仰慕者們誇誇其談;她替告詹姆斯要小心,安靜一點,等等。都是插在一個簡單動作中的自由聯想。這些聯想彷彿是沒有章法的,但是通讀全文後卻會發現他們的內在聯繫還是很緊密地,也對以後事態的發展打下了伏筆。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個小事件中作者還用到了空間蒙太奇的用法。三組人物:拉姆齊夫人和詹姆斯,班克斯先生和莉麗。拉姆齊先生和他的志同道合者,它們之間也是對彼此都有自由聯想。自由聯想通常與人的文化背景也有很大的關係,這也是解釋為什麼對拉姆齊夫人和莉麗的文字描述多用到自由聯想的方法,因為他們兩個人都不在憊外部的自然規律,而且都有豐宮的想象力和深刻的同情心,在她們的心中,生活是雜亂無章而又相得益彰的。
《到燈塔去》是伍爾芙最完美的一部作品,它對文學史的貢獻是卓越而深遠的。小說無論是創作視角還是心理描寫,亦或是意識流手法,都極具藝術色彩,尤其是伍爾芙對於女性氣質的理解以及對性別意識的見解,也成為她創作的思想內核。小說通過對代表女性氣質的拉姆齊夫人和代表男性氣質的哲學家拉姆齊先生對立的性格刻畫,旨在展現男女兩性氣質二元對立的現狀,並試圖為他們所代表的兩種不同的生活原則尋找一條和諧與統一的途徑。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