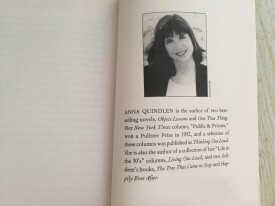安娜·昆德蘭
安娜·昆德蘭
安娜·昆德蘭(Anna Quindlen),女,美國著名作家,出生於賓夕法尼亞州的費城。父親是愛爾蘭人,母親則是義大利人。作品有《主題課程》(Object Lessons)《親情無價》(One True Thing)(曾改編為電影)以及《黑與藍》(Black and Blue)等。
美國專欄作家、書籍作者。歷史上第三個為紐約時報撰寫社論對頁專欄的女性。普利策評論獎得主。
18歲,她以抄寫員的身份加入《紐約郵報》,從此開始了在新聞行業的職業生涯
19歲,母親因為卵巢癌而去世,因此涉及到個人的寫作時,大多聚焦於她死去的母親
1977年,昆德蘭作為普通助理記者加入《紐約時報》。
1983年,她被任命為都市版主編。從1981年到1983年間,她一直撰寫“有關紐約”的專欄。
1985年,因為生育,昆德蘭離開《紐約時報》賦閑在家養育自己兩個年幼的兒子,同時寫作小說。
1986年晚期,她重返該報的工作,開始寫作“三十多歲的生活”專欄。兩年之內,這個專欄開始在全國超過六十家報紙上刊登。
1988年,她女兒的出生讓她再次辭職。
1989年,重新回到《紐約時報》。這一次,她開始寫作《紐約時報》社論對頁赫赫有名的專欄—— “公共與私人”。此時,她已經成為了該報歷史上第三位享此殊榮的女性。1993年時,這些專欄文章的集結《大聲的想》由蘭登書屋出版,隨後在三個月之中一直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
1992年,因為這個專欄,昆德蘭獲得了普利策評論獎。
1999年,重新回到新聞界的昆德蘭選擇了以《新聞周刊》作為舞台。而為了迎接這位新專欄作者的到來,《新聞周刊》在位於曼哈頓的四季酒店舉辦了一次雞尾酒會。
在主持專欄“最後的話”接近9年之後,2009年5月18日,她辭去了這一職務。
暢銷小說:《主題課程》(Object Lessons)《親情無價》(One True Thing)(曾改編為電影)以及《黑與藍》(Black and Blue)《有種感覺叫快樂》。
她在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上開闢的「公評與私情」(Public and Private)專欄贏得了1992年普利茲獎(Pulitzer Prize),後來又集結為《大聲地想》(Thinking Out Loud)。
另有介紹當代思想的《閱讀如何改變了我的生活》(How Reading Changed My Life),以及兩本童書:《大樹留下來》(The Tree That Came to Stay)與《永遠幸福快樂》(Happy Ever After)。
目前她在新聞周刊(Newsweek)上有一個隔周刊登的專欄。
《真情無價》(1998年的時候改編成了電影,由梅瑞爾.斯特里普主演)處理的題材,是一個人死亡的權利。有關於自己母親的死亡,昆德蘭說,“它從未遠離過我的腦海。”“我把自己的時間投注到那些身體正在隕滅的人的身上,他們正在疾病和死亡之間搖擺。我討厭在治癒或者說讓人感到舒適已經沒有希望的前提下,醫生們還覺得自己應該繼續去捅、去測試、去治療。對於人,你就必須去做所有的事情。對於動物的話,你就能夠有隻去做那些正確的事情的奢侈的權利。”
論在紐約作為一個女性:
“我認為,一件並沒有經常被提到的事情是:這裡是作為一個女性的很好的地方。我的意思是說,這裡是事業性女孩的家。這裡經常是一個非常不一樣的地方,對於那些敢於從全世界的其他地方來到紐約城的女孩們來說。在很多方面來說,紐約是個如此另類的地方。你能夠變成一個投票領導人,一個工會組織者或者一個政治力量或者每天外出工作的女孩。在這種意義上來說,我認為這個城市對於女性來說尤為友好。這裡擁有為你自己的未來設計航向的可能性,沒有人會注意到或者說是過分的大驚小怪。這是對於一整個性別的巨大的解放,之前在她們的運動中圍繞的是小心的觀察和設限。因此,我認為,這裡有一種充滿機遇的感覺,在紐約,匿名性已經歷史性地被給予了女性,在很多方式上來說,這跟給與男性的不同。而且,這裡也給與了女性很多的機會,在其他的地方,我們可能都沒有辦法得到。”
論是什麼造就了一個優秀的紐約政客:
“因為紐約客們是一種非常理想主義的人,所以,在紐約政界中有很大的空間能夠給與理想主義。在這個城市中,理想主義跟其他的任何事情都一樣重要。它的理想是作為一個大熔爐,作為一個把迥然有別的事物匯聚在一起,作為一個富人和窮人共同的理想。所以,這裡能夠擁有那種理想主義的政客。但是,在一種現實的水平線上,你們必須讓地鐵們及時的工作。”
“擁有生活”
“擁有生活。一種真正的生活,而不是焦躁不安地想要獲得下一次的升職、更大數額的支票、更大的房子。假如,有一天下午,你發現自己得了動脈瘤,或者是在乳房上發現陰影的話,你真的還認為自己對於這些事情會如此關心嗎?”
關於自己母親的死亡
“它從未遠離過我的腦海。”“我把自己的時間投注到那些身體正在隕滅的人的身上,他們正在疾病和死亡之間搖擺。我討厭在治癒或者說讓人感到舒適已經沒有希望的前提下,醫生們還覺得自己應該繼續去捅、去測試、去治療。對於人,你就必須去做所有的事情。對於動物的話,你就能夠有隻去做那些正確的事情的奢侈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