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納河上的橋
德里納河上的橋
徠《德里納河上的橋》是南斯拉夫現代作家伊沃·安德里奇創作的長篇小說。
《德里納河上的橋》這部表現形式新穎別緻的小說,僅用20多萬字的篇幅就概括了一個國家450年的歷史。它既準確地描述了幾今世紀以來維合格勒城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也細緻地勾畫出一幅幅情趣盎然的生活場景,成功地塑造了幾十個不同歷史時期的典型人物,小說涉及的歷史事件如此之治繁,描寫的人物又是如此之眾多,但並沒有給讀者留下支離破碎,東拼西湊的印象,相反,讀過之後卻覺得作品前後渾然一體,互為關聯,這部小說之所以能得到這樣完美的藝術效果,關鍵在於作者新奇巧妙的藝術構思。德里納河上的橋即是作者構思的焦點,幾乎成了小說主人公的化身。它在地理上連結著東方和西方,在時間上聯結著過去和現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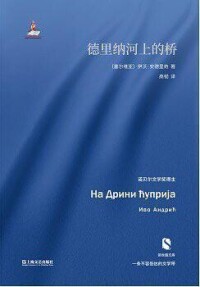
德里納河上的橋
《德里納河上的橋》這部表現形式新穎別緻的小說,僅用20多萬字的篇幅就概括了一個國家450年的歷史。它既準確地描述了幾今世紀以來維合格勒城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也細緻地勾畫出一幅幅情趣盎然的生活場景,成功地塑造了幾十個不同歷史時期的典型人物,小說涉及的歷史事件如此之治繁,描寫的人物又是如此之眾多,但井沒有給讀者留下支離破碎,東拼西湊的印象,相反,讀過之後卻覺得作品前後渾然一體,互為關聯,這部小說之所以能得到這樣完美的藝術效果,關鍵在於作者新奇巧妙的藝術構思。德里納河上的橋即是作者構思的焦點,幾乎成了小說主人公的化身。它在地理上連結著東方和西方,在時間上聯結著過去和現在。它更象人民苦難的目擊者,親眼看到波斯尼亞兒童像羔羊一樣被土耳其侵略者送往異地充當“血貢”;親眼看到成千上萬的鄉民像小雞一樣被抓到工地上服苦役,還親眼看到勇敢無畏的維舍格勒人怎樣組織起來,用自己的熱血和生命譜寫了一曲曲鬥爭的頌歌。總之,這座大橋好似反映波斯尼亞歷史的萬花筒或多稜鏡。有了這樣一個萬花筒或多稜鏡,作者便可以在浩如煙海的歷史事件中隨心取捨,自由馳騁。不管任何人物與事件,只要能和大橋聯繫起來,便可納入作者構思的網路。這就使得小說的跨度異常浩大,頭緒極為繁多。然而,它並不是一部謹嚴的歷史著作,而是一部塑造眾多具體生動的藝術形象的小說。譬如鄉民拉底斯拉夫在小說中出場的場面並不是很多,但是通過對其在橋頭所受樁刑的具體描繪,他的高大形象在讀者心中即深深紮下了根。一如作品中所說,“他已超凡人聖,割斷了塵緣,本身自成體系,不受人間任何羈絆,無憂無慮。誰也不再能把他怎樣,刀槍,讒言惡語乃至土耳其人的淫威都對他無可奈何了。”同樣,羅蒂卡的精明強幹和樂善好施,作者也是通過與酒鬼周旋和救濟乞丐、病人這樣一些具體場面來加以體現的。至於為了更深刻他說明阿里霍扎對大橋的摯愛以及大橋在其生活中的重要位置,作者索性在小說的結尾安排他與大橋同歸於盡。雖然,大橋和他的生命都不存在了,但是他的靈魂則得到了真正的升華。另外,《德里納河上的橋》還創造了長篇小說的新形態,可以說它是用小說形式寫成的有關波斯尼亞人民的苦難和抗爭的莊嚴史詩。安德里奇以大橋為媒介,輔之以民間文學的多種表現手法及各式民間故事傳說,大大增強了小說的傳奇色彩,讀來格外引人入勝,這是小說另一個顯著的藝術特色。首先,小說的題目《德里納河上的橋》就來源於歐洲的一首民歌。開頭幾章有關大橋的種種傳說,往橋墩里活活埋葬一對正在吃奶的攣生耍兒的故事,都是作者從民間文學中吸取的營養。書中對波斯尼亞、塞爾維亞中世紀和上一個世紀的一些民歌也運用得恰到好處。民歌和傳奇故事使小說不同於一般的作品,具有濃郁的鄉土氣息和鮮明的民族特色。所以,《德納河上的橋》在南斯拉夫曾有“巴爾幹人民的史詩”之稱。評論家說它兼有“托爾斯泰的紀念碑式的風格”和“屠格涅夫的抒情情調”,而於1961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並被澤成許多國家的文字。這部作品的不足之處,是在描寫人民大眾的反抗鬥爭時,沒有充分揭示它的階級牛凈實質,有時反而被宗教鬥爭所掩蓋,而人民大眾波瀾壯闊的武裝起義在有些故事中也只是一筆帶過,沒有得到充分的反映。
安德里奇(1892—1975)南斯拉夫作家。1892年10月9日生於特拉天尼克附近的多拉茨村。兩歲喪父,跟母親一齊到了姑母家,在維舍格勒讀小學。架設古城郊德里納河上的11孔大石橋給予幼小的安德里奇以豐富的精神營養,幾個世紀以來關於此橋的種種傳說和故事在他心靈深處播下了良好的文學種子,對他後來的文學創作有非常重要的影響。安德里奇在薩拉熱窩讀完中學,並積極參加愛國學生運動,1914年被奧地利當局逮捕入獄,1917年獲釋。1918年,《南方文學》雜誌創刊,安德里奇即是該刊的創始人之一。以後,他以《南方文學》為陣地,發表了一系列充滿愛國主義激情的詩歌,散文詩和文學評論,積極獻身於民族解放事業。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安德里奇隱居在貝爾格菜德,拒絕同法西斯合作,埋頭文學創作作。寫出了《特拉夫尼克記事》(1945)、《德里納河上的橋》(1945)、《女士》(1945)部長篇小說。它們取材子波斯尼亞歷史、採用記事體,注重歷史事實的準確性,並大量運用民間傳說和神話故事。《特拉夫尼克記事》寫法國駐波斯尼亞領事達維爾尋求正確的人生道路及其理想的幻滅。《女士》則記述了拉伊卡·拉達科維奇的一生。而《德里納河上的橋》以一座大橋的興廢,追述了16世紀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期間波斯尼亞在奧斯曼帝國和奧匈帝國的佔領下所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反映了波斯尼亞人民為爭取民族獨立所進行的英勇鬥爭。此外,安德里奇還著有《澤科》(1950),《萬惡的庭院》(1954)等作品,他於1961年獲諾貝爾文學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