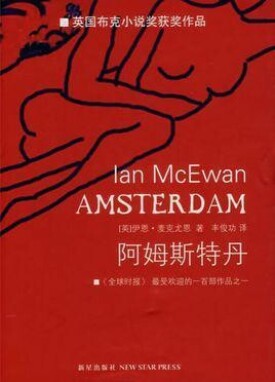共找到9條詞條名為阿姆斯特丹的結果 展開
阿姆斯特丹
作家伊恩·麥克尤恩所著小說
《阿姆斯特丹》是英國作家伊恩·麥克尤恩創作的長篇小說。《阿姆斯特丹》講述了作曲家克利夫·林雷與報社編輯弗農各自逃避死亡卻又走向死亡的故事,通過平行發展的故事線索,將死亡與瘋癲巧妙地嵌入鮮明的後現代敘述。精神之死與肉體的消亡無處不在:死亡解構了音樂家所謂的偉大創意與編輯的至高權力,造成兩人的生活空洞、毫無尊嚴,每日上演儼然小丑般的滑稽表演。該小說中的其他角色也都陷入精神萎縮與肉體病變相互交織成的巨網中,默默等待死亡的緊急迫降。
《阿姆斯特丹》於1998年獲得英國布克文學獎。
在專欄女作家莫利·萊恩的葬禮上,引出兩個主要人物:克利夫·林雷和弗農·哈利戴。二人同為莫利的舊情人,前者是享有一定聲望、被委以創作千禧年交響樂重任的音樂家,後者是一家頗具影響力的報紙的主編。克利夫·林雷和弗農從大學時代就是朋友,先後成為莫利情人的事實並沒有傷及他們的友情;相反,這個事實使他們結成了一個鄙視莫利丈夫的同盟,關係似乎更近一步。莫利的死使克利夫·林雷和弗農深感世事無常,而莫利死前因身體功能失控所承受的屈辱與尊嚴的喪失也使他們觸目驚心,二人遂定下一個君子協定:如果二者中的一方看到對方不能有尊嚴地活著,則有義務幫助對方結束生命。為了逃避法律責任,可以選擇允許“安樂死”的阿姆斯特丹進行。
隨著情節的推進,克利夫·林雷和弗農都面臨了自己事業的危機與挑戰,做出了令對方齒冷的選擇:克利夫·林雷為了自己的音樂創作而對發生在身邊不遠處的一起強姦案置若罔聞,弗農則背棄了自己曾經作為反主流文化鬥士的自由理想、為了提升自己主編的報紙的銷量刊登了外交部長加莫尼的異性裝扮照。加莫尼是莫利的另一位舊情人,這些照片正是莫利的作品,是莫利追求個性解放、蔑視傳統價值的精神寫照。克萊夫和弗農對照片是否刊出觀點截然相反,導致二人的爭執與決裂。最後,兩人都認為對方已經道德淪喪、失去了基本的人性尊嚴,他們不約而同來到阿姆斯特丹,結束了對方的生命。
阿姆斯特丹是一個容許人們選擇安樂死的城市。備受病痛折磨的人可以在這個城市對自己生命存續自由地行使自己的權利。麥克尤恩和他的遠足同伴達成了一個有趣的協議:如果二人之中,有人開始罹患類似“老年痴獃”的病症,那麼為了避免對方陷入屈辱不堪的境地,另一方就要把他帶到阿姆斯特丹,以接受合法的安樂死。結果,一旦哪個人忘記帶上了必備的遠足設備或是記錯了某個日期,對方就會戲謔地調侃:“嗨,你該去阿姆斯特丹了。”然而,這個小玩笑卻促成了麥克尤恩的一個創作念頭:如果把兩位達成協議的人物放在小說里,讓他們反目成仇,之後不約而同地引誘對方來到阿姆斯特丹,又同時謀害了對方的性命,這將是一個不錯的故事。於是,《阿姆斯特丹》長篇小說被便漸漸創作出來。
在《阿姆斯特丹》作品中,藝術大師克萊夫,是一個蹩足的音樂家。在該小說中,威廉·莎士比亞等巨匠反覆出現與蹩足音樂家克萊夫之間形成了強烈的反差,這種反差投射出的是創造性生存的理想和缺失,暗示了當代藝術創造和自然科學領域人才的匱乏,揭示了作者對創造性生存理想的極度渴求。
麥克尤恩崇尚自然科學,但也看重人文精神對現實的引導和救贖,他深信“作家能夠觸到科學所能企及的一切領域,卻絕不會被科學所替代。這是因為作家探究的是人的本性、現狀及特定環境里的表現”。
莫利
莫利,美食評論家、攝影師。莫利的美麗與才華一直為人津津樂道,而她不檢點的私生活卻並未受到批評。她除了對工作的熱情投入之外,還對音樂、政治等方面表現出了非凡的鑒賞力和積極的參與性。她和克利夫·林雷談音樂,談巴赫;和弗農談美食;和加莫尼在一起時,就自由、平等等話題做過深入的探討。
莫利從不打掃她的套間,從不洗盤子,這是一個從來都沒有想過要局限於家庭生活的職業女性,事業才是她生活的動力。莫利是一位經濟獨立、個性獨特的新時代女性,她很顯然是女性性解放思想的踐行者,從不掩飾她對於性的渴望和獵奇心理。莫利跟丈夫喬治分床而眠,她的房間甚至有單獨通向外面的出口。
克利夫·林雷
克利夫·林雷,莫利的老情人。克利夫自詡天才的作曲家卻不得不靠抄襲古人來完成創作。作曲家克利夫因代表作《美之憶》而名聲大噪。1996年初,步入中年的他被政府委以重任,為4年後的千禧年創作一部交響曲,但進展緩慢,三番四次地催稿下才勉強完成。
弗農·哈利戴
弗農·哈利戴是英國《大法官報》的主編,莫利的老情人。弗農其實才華平庸,他是個沒什麼稜角的人,既沒什麼缺點,也沒什麼美德,在大家眼裡是個可有可無的主兒。由於趕上報社所有權利益的重新調整,他僥倖當上了主編。
喬治·萊恩
喬治·萊恩是富可敵國的出版商。喬治是莫利的丈夫。喬治屢次被妻子戴上綠帽子。
朱利安·加莫尼
朱利安·加莫尼是現任外交大臣,莫利的老情人。代表國家立場的外相加莫尼竟然私下裡有“異裝癖”。
《阿姆斯特丹》主題思想:有尊嚴地死去,比無尊嚴地活著更有意義
《阿姆斯特丹》以風流迷人、令無數男性為之傾倒的莫利之死開始。在莫利的葬禮上,死亡與存在的巨大反差成為重大命題,曾與莫利相關的三個男人被圈入了同一幅畫面:新老情人一面在公眾面前握手言歡,一面用最惡毒的語言互相抨擊對方的弱點;被戴了綠帽子的丈夫如釋重負,在扮演受害者的同時積極思考如何展開報復。死者變成了生者口裡的談資,死亡變成了活著的消耗品,本應沉重的場面變得荒唐而滑稽。
如果說莫利死前遭受的病痛是對她行為不檢點的懲罰的話,該小說的大部分章節將揭示其他生者如何在漫長的、生不如死的狀態中忍受更多的折磨。
克利夫:被異化的個人主義者
該小說開頭,克利夫·林雷參加老情人莫利的葬禮時,與死亡第一次近距離接觸。事實上,他是葬禮上唯一感受到死亡的巨大威脅的人——只有他對莫利的死表達出了由衷的感嘆。他之所以能對莫利的死感同身受,不僅僅是由於往日的溫存,更是因為克利夫已然在他自己的肉體上、靈魂里感受到了死亡的存在——首先表現為肢體的麻木與疼痛(與莫利患病初期身體機能的逐步喪失巧合),其次是個人生活中的混亂與無意義。克利夫從他者的死亡中體會到強烈的死亡衝動;死亡巨大的破壞性讓原本孤立的個體感到更加孤獨與無助,從而轉向有意地生產與創造,即生之本能,希望能夠擺脫死亡的陰霾。
殊不知,死亡的本能早已脫離了主體,被潛意識強調,在行為中反覆出現。比如,克利夫與弗農約定殺死彼此,就是潛意識中的死亡本能在作祟。另外,死亡的衝動在暫時得不到釋放的情況下,常常轉化為對自我及他人的否定與厭惡:在克利夫看來,葬禮上的面孔“看起來可真是恐怖,活像是殭屍直立起來歡迎剛死的新鬼”,而情敵兼政敵的外交官加莫尼“臉色是可怕的死魚肚的白”,連德高望重的詩人也像“一隻皺縮的小蜥蜴”。更讓克利夫鬱悶的是,所到之處的芸芸眾生似乎都缺乏對音樂的起碼素養,大眾對自己的創造與才華視而不見;而克利夫他自己視為經典的作品只不過是小朋友練習的樂曲。
克利夫自詡天之驕子,習慣了在公共場合享受尊崇和榮譽。只有獨處時,克利夫才能卸掉諸多假面,暴露出寂寞、無助的真實一面;並承認他自己正在苦苦思索的新樂章不過是“已死世紀的輓歌”。情人的故去激起了他強烈的生存慾望,帶來的卻是在現實與理想中苦苦掙扎的焦灼。原來,名聲赫赫的大作曲家竟也如庸人一般懼怕死亡。工作上遇到的瓶頸狀態與肢體的病變合二為一,凝聚成更強大的死亡威脅,“對工作的焦慮轉變成為更加原始的、對於夜晚的單純恐懼”,無法想象自己變成“一身尿騷味、口涎直流的糟老頭子”,想象中的自己與死前患病的莫利的形象重疊相交。就像克利夫幻想殺死莫利一樣,克利夫無法面對死亡,幻想自己可以自主選擇死亡的方式——自我了結,而非被動地、毫無尊嚴地被死神帶走。這與該小說結尾克利夫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尊嚴掃地地被殺死的現實形成了極大的反差。
自從參加莫利的葬禮后,死亡的氣息似乎無處不在。克利夫沒有意識到的是,死亡解構了生存,一系列的負面能量被相繼釋放:這種分裂、解體、“背叛”的力量意味著徹底的反目的性,其形式是一種向先前的、無機狀態的退化。
被死亡本能主宰的克利夫強烈地希望以藝術上的完美形式來延緩死亡的腳步,但這樣的努力是虛弱的。這個以自我為中心、無力維持正常的家庭關係的“成功人士”嘗試拷問靈魂、探尋真相,然而他固步自封,雖渴望尊重和愛,卻無法走出個人主義的苑囿。更嚴重的是,他對自己內心的惡採用視而不見的態度,反而將其投射到外物與他人身上。克利夫渴望獨處、厭惡他人的態度本質上來源於他對自身缺陷的了解。
當克利夫身處懸崖上,看到下面的海邊發生的醜惡一幕時,他根本沒有想到加以制止。儘管腦海中的音符已經因為干擾而消逝,克利夫仍不打算阻止罪惡的進行,“假裝他沒有到過那兒”,假裝自己與他人的命運“根本就沒有交集”。他自以為馬上就要實現的人生制高點,不過是懸崖上岌岌可危的臨時落腳點;當他選擇對他人的罪行視而不見、帶著他“偉大的”靈感回到樂章的譜寫中,不分晝夜地將其偉大的藝術創作進行到底時,他的人生也即將面臨戲劇化的跌落,迅速接近終點。
弗農:被虛無吞噬的空心人
作為克利夫的朋友、小說的另一位主人公,弗農的存在本身也是荒唐的、毫無意義的。他“在大家眼裡是個可有可無的主兒,因為他的無足輕重而受到推崇”。換而言之,弗農已經體會到他自己具有“空心人”的狀態——無以依附、無所信仰,生存的意義已被抽空,僅剩空虛。同克利夫極為相似的是,這種焦慮感自從莫利的葬禮之後就愈演愈烈,“這種感覺已經侵蝕入他體內,必須得摸著自己的臉才能讓自己放心,他仍舊還是個有形的實體”。可悲的是,弗農無法將自己的真實感受與妻子分享,更不可能與其他高級職員推心置腹——隔閡無處不在,無論是婚姻中的夫妻雙方,還是工作中的夥伴;長期的缺乏交流的狀態讓個人與他人的距離越發遙遠,溫情、關懷與體恤幾乎都是奢侈的期望。而克利夫,以前唯一可以交心的就是莫利,而現在後者已化為細碎的骨灰被喬治收藏。荒唐的是,儘管權力給弗農帶來的不過是異化與空虛,權力仍是“空心人”弗農唯一能抓住的救命稻草,並且抓住一切機會將其行使到最大化。當身為股東的喬治從莫利的遺物中發現了外相加莫尼男扮女裝的照片,立刻召來弗農,而當弗農壓抑住對喬治的厭惡審視照片后,“先是吃驚非小,緊接著的就是發自內心的狂喜。他體會到的是一種沉重的責任感。也許弗農現在就能改變國家的未來,使之變得更加美好”。
這樣的想法也許不是錯覺:數家報社都參與了競標,以獲取照片的轉載權,而這一切都在弗農的運籌帷幄之中,讓他不禁有點懷疑“不久前竟然還曾經深受頭皮麻木和非存在感的折磨,甚至於身陷瘋癲和死亡的恐懼”實在是杞人憂天。正是這種權力帶來的錯覺讓弗農否定了克利夫的建議,堅持刊登加莫尼的照片。正如克利夫所說,弗農的行為無疑是對莫利的背叛;而弗農的一意孤行不僅偏離了莫利的初衷,也導致了其與克利夫關係的惡化。弗農原本打算讓外相的隱私曝光於眾,憑藉這一轟動新聞擴大報紙的發行量、挽救自己岌岌可危的職位。弗農出於完完全全的私慾,企圖藉助工作之便解決個人恩怨,而這樣的狹隘與偏執給他帶來了致命的後果——弗農意想不到的是,照片曝光后,加莫尼的妻子挺身而出,讓加莫尼的公眾形象得以保全。更讓弗農始料不及的是,他自己非但沒能保全自身,反而被勒令停職。最為荒唐的是,當時他與克利夫二人通過紙條互相承諾,尊重彼此的選擇,願意幫助彼此提前結束痛苦;此時恰恰又是通過紙條和紙條上一時衝動的語言,二人坦白了對彼此的不滿與厭惡:克利夫衝動地表達了弗農被辭退是罪有應得的想法,而弗農將其理解成了惡毒的攻擊與幸災樂禍。失業與友情破裂夾雜在一起,讓受到雙重打擊的弗農得出了如下結論:“就在他的生活已經一敗塗地的時候,給了他最致命一擊的竟然是他的老朋友,這是絕對不能饒恕的——是喪心病狂。”
被死亡肢解的個體與慾望
弗農與克利夫的友情經歷了發展與分裂、從好友到敵人的戲劇化轉變。兩人在其間相互滋生的厭惡、恐懼和蔑視,正是瘋癲的個體異化、分裂的最佳表現。弗農與克利夫彷彿互為分身——克利夫與弗農唯一真正愛過的女性都是莫利,並都因後者的過世受到莫大的震動;兩人都覺察到身體方面的退化;兩人都無法與他人建立長期的、穩定的關係,更談不上交心和信任;兩人都是道貌岸然的偽君子,都對自己身處的環境十分不滿卻無力改變;兩人都不同程度地參與了“惡”——克利夫有能力阻止罪行卻無動於衷,弗農則將他人的弱點放大並展示在公眾面前以求自保;兩人都不同程度地察覺到了自身行屍走肉般的生存狀態,潛意識裡都想以死亡求得解脫。兩人都是不折不扣的利己主義者,也都是被空虛吞噬的空心人。兩人都代表了現代文明中個人空間被社會定位鯨吞、個人尊嚴消失殆盡的尷尬境地——克利夫聊以自慰的僅有世人對自己的關注,無論與自己相處還是與他人相處都無法怡然自得;弗農唯一關注的無非是報紙的銷量與自己的職位,一旦後者被剝奪,他作為個人的存在立刻塌陷。二人似乎都沒有信仰,與他人的交集多半出於功利而非真情,無以維繫靈魂。
瘋癲是克利夫與弗農死前的狂歡,是兩人命運交錯的聚點,卻使得最後的團圓同時成為了終點。作者對他們的諷刺集中體現在小說最後的歡宴:兩人放肆的言行彷彿是死前的狂歡,而陰差陽錯的誤殺行為似乎也為兩人相互承諾的安樂死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點。這兩個積極籌劃自覺死亡的可憐蟲最終也沒能主動選擇死亡的方式與時間。他們被昔日的好友、今日的敵人殺死,死於自我蒙蔽,並不是為愛、為美、為崇高的理想獻身。這樣的死亡方式截然不同於古典悲劇英雄式的死亡——死亡的場景毫無儀式感,死亡也無法贏得旁人的同情或哀嘆。克利夫與弗農都是這個已死時代里的小丑,是整個社會環境喪失靈魂、停滯不前的縮影;他們試圖將有限的生存與未知的死亡之間的距離無限拉長,然而這一段無形的距離彷彿一根皮筋,其張力隨著長度的增加而變大。兩人都意識到了自己生存狀態的荒誕,試圖用“荒誕的反抗避免讓生命消失於這樣的存在之中”。
無論是以文明的名義進行自我崇拜,還是借權力之便將他人野蠻化,該小說里的大部分主人公都是瘋癲的、分裂的。背離死亡的逃逸行為是無益的,它勢必以更大的力量將試圖逃離的個人拉近死亡。以克利夫與弗農為首的城市空心人,在不斷追逐慾望的同時離贖罪的路口越來越遠;而“死亡的反面就是慾望”,只有死亡才能帶來慾望的終止,即終極滿足。
在個體特徵被抹殺,原始人對死亡的恐懼逐步被工業化文明、消費型社會取代的同時,死亡及其巨大的陰影並沒有遠離現代人的意識,而是以憂慮、疾病、異化等各種形式潛伏徘徊。克利夫對靈感的焦慮和弗農對職位的憂慮都是死亡內在化的隱喻。更糟的是,由於現代人與自我、與他人、與自然的種種隔離與斷裂,死亡不再被分享、不能被訴說,而是成為個人狹小空間內的另一個夢魘。小說中克利夫與弗農一開始約定彼此終止生命,即“分享死亡”;但兩人都拚命地追逐有生之年的名與利,即“分離生命與死亡”。
克利夫藉以逃避死亡的音樂是純粹精神的,而這個音符的世界單薄無力、經不起推敲。和克利夫相比,弗農追逐更現實的利益,其本身也是虛無的、異化的。如榮格所言:“曾經作為人的個性的東西被淹沒了,某種社會化的優勢功能吞噬了他們。”
克利夫與弗農的悲劇不僅是個人的,也是社會性的。在儼然全景式監獄的社會中,個體不得不屈服於強大的社會機制,個體意志得不到自由施展,始終處於壓抑狀態。當個體逐漸認同外界機制的非人性意志,個體與自身的分裂就到達極限,並進一步表現為個體與自然界、個體與他者之間的疏離與斷裂。社會屬性並沒有給予個體真實的存在感,也不足以讓個體實現自我價值,反而運用權力機制將個體紛紛對立起來,使得個體的生存空間進一步變得狹窄、惡劣。個體雖然試圖對社會施與的限制進行反抗,卻在人性共有的弱點前被自我擊敗。
個體異化導致個體意識的扭曲,慾望也變得妖魔化,成為了被他人意志和強權意志扭曲的偽慾望。連真實的自我慾望都喪失的個體無力進行自我拯救,無意識中的死之本能最終戰勝了快樂原則。《阿姆斯特丹》中的倫敦充斥著謊言與虛妄、被架空的個體意志與被放大的瘋癲。主體的整體性一直無法得以實現,缺失代替完整成為了永恆的狀態。主體慾望的缺失導致揮之不去的空虛與絕望,這些都驅使著主體尋找下一個慾望的替代品。在一系列追求慾望的過程中,個體被慾望奴役,主體被他者化,陷入西西弗式的怪圈:追求——實現(無法實現)——空虛——追求。能夠終止這一怪圈的不是主體本身,只有死亡。作者將深切的憂患隱藏在荒誕的死亡陰影下,該小說中無處不在的死亡與瘋癲的隱喻是對現代都市生活中精神荒蕪、道德淪喪狀態的絕佳諷刺。
互文性
《阿姆斯特丹》開篇第一句話就把讀者帶入了一個文本互相指涉的世界:“莫利以前的兩位情人,在火葬場的小教堂外面站著等候,二月份的寒氣襲擊著他們的後背”。
“莫利”,是作家喬伊斯創作的《尤利西斯》作品中的故事人物。莫利曾擁有數目諸多的情人。麥克尤恩通過借用“莫利”這一人物形象,在文本中喚醒了文學經典《尤利西斯》。在此,麥克尤恩運用互文手法的敘事技巧,即引用意指“一段話語在另一段話語中的重複”,表示通過將原文中的表述引入受文實現文本的再造。原文的存在為解讀受文的意義、主題提供潛在的認知範式,而受文除了實現一定的文化傳承之外,還會對所借鑒元素進行重新地闡發以改造原文的文化意義。
從這個角度來看,莫利是《阿姆斯特丹》為喬伊斯的意識流經典文本招魂的文本基礎。兩個文本中的莫利,除了共用一個名字之外,同時具備一些共同特點:同是已婚婦女,婚前婚後都擁有為數眾多的情人,性感,激情洋溢,對男性富有吸引力。然而,正如互文性引用不是對原文本元素的原樣照抄,麥克尤恩筆下的莫利絕非是她文本前輩的鏡像反映。
麥克尤恩對莫利的再現顯得更加匠心獨具。《阿姆斯特丹》小說開始,便得到了“莫利已死”的訊息。然而,葬禮並非莫利的告別儀式。恰恰相反,葬禮之後,莫利的形象開始出現在所有主要人物的回憶中,在文本中,逐漸看到了那個有才有貌、血肉豐滿的莫利。雖然麥克尤恩沒有從正面描寫莫利,但這並不能說明麥克尤恩的莫利形象在喬伊斯的莫利面前相形見絀。在20世紀初期《尤利西斯》剛剛問世之際,莫利是一個備受爭議的人物形象,不少評論家對莫利在獨白中大談自己的風流韻事、不加掩飾地表達自己的情慾這一事實難以接受,甚至因此將《尤利西斯》標記為淫穢文學。隨著女權運動的發展和性解放大潮的推進,莫利的形象才逐漸被接受並成為女性性解放的代言人。
在小說《阿姆斯特丹》中,莫利互文性與反諷的形象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道德高度。雖然她擁有不計其數的情人,但從這些男性對她的回憶來看,莫利是一個美貌風趣、富有才華、率性真誠的女性,同時兼具了男性的精神導師的身份。在那些沉迷名利、虛偽自負又有各自致命弱點的男性面前,莫利的形象高大起來,成為作品的道德核心。
互文性的運用使原文本為受文的理解闡釋提供了一個潛在的認知範式,而受文對原文則實現了改造性傳承。既然《阿姆斯特丹》中的莫利形象呼喚了《尤利西斯》文本的出現,以《尤利西斯》為模本對《阿姆斯特丹》進行解讀就具有合理性。
《阿姆斯特丹》是一個包含了雙重意義的旅程故事:從直觀的地理意義上講,整個故事記錄了克萊夫和弗農從倫敦到阿姆斯特丹的旅程;而根據情節發展,《阿姆斯特丹》小說以莫利的葬禮開頭,以克利夫·林雷和弗農的死亡結束,實質上是一個“死亡之旅”。
《尤利西斯》再現了一個現代生活中的小寫的“人”,《阿姆斯特丹》則逐漸抹殺了“人”跡,是一個從葬禮到死亡的故事。
在《阿姆斯特丹》中,麥克尤恩講述了兩個舊情人在“后莫利時代”的急速墮落乃至毀滅,從延續性來看,《阿姆斯特丹》似乎是接著《尤利西斯》結尾處莫利的內心獨白寫作的一個後續作品,交代了在《尤利西斯》中沒有給予足夠篇幅的莫利的情人們的生活。麥克尤恩的文本中,雖然莫利從開篇即是死者,但正是這個“死者”不停地出現在各個角色的腦海中,成為他們敘述的對象,直至小說的結尾。
在《阿姆斯特丹》中,莫利不僅佔據了敘事的中心地位,她也統治著這些男性的精神世界:莫利就是核心。
言語反諷
《阿姆斯特丹》中一個典型的言語反諷就是“可憐的莫利”這句話。在莫利的葬禮上,克利夫·林雷和弗農不止一次地說道:“可憐的莫利”。此後,他們兩人一起聊天或者獨處的時候,“可憐的莫利”也多次出現。莫利因患了身體官能失控症而最終腦死亡,這本值得同情。但在莫利死後,該小說中的四位男性——莫利的丈夫喬治、莫利的三位舊情人克利夫·林雷、弗農和加莫尼不斷地回憶他們和莫利一起度過的時光以及莫利對他們的“教導”,反映了莫利對他們巨大的影響力。可以說,無論生前還是死後,莫利都是這些男性頭腦中揮之不去的永恆印象,是一種強大的精神力量。
失去莫利之後,克利夫·林雷和弗農這兩個舊情人似乎失去了道德指引,在各自的職業生涯中犯了致命的錯誤並走上不歸路。雖然莫利死時失去了控制身體的能力,也沒有了意識,但她的死令人同情、值得紀念。克利夫·林雷和弗農則是看到了對方的道德墮落超出底線之後互相謀殺,這樣的死使他們身為音樂家和報紙主編的尊嚴蕩然無存,揭開了二人虛偽的面具,同時也成為醫學界、音樂界、傳媒界甚至是政界的醜聞、笑料。在他們生命的最後一刻,二人的腦海中出現的還是莫利的形象。原來,“可憐的莫利”從來都不是可憐的,而是“強大的”,這是一個絕妙的言語諷刺。
情境反諷
情境反諷貫穿《阿姆斯特丹》小說的始終,從結構的層面上平添了小說的諷刺意味。該小說的標題“阿姆斯特丹”是一個反諷意味濃烈的情境設置。作為《阿姆斯特丹》小說的標題,“阿姆斯特丹”可以被看作一個滿載信息的副文本。一方面,阿姆斯特丹這個城市是該旅程小說的方向與目的地,文本中的主人公進行了一次朝向地理學意義上的阿姆斯特丹之旅;另一方面,阿姆斯特丹是《阿姆斯特丹》小說文本的結局,整個作品則是敘述者積累敘事能量、為在阿姆斯特丹發生的情節互文性與反諷做鋪墊的敘事過程。同時,阿姆斯特丹是該小說中一個結構性的隱喻:明指默許“安樂死”醫學實踐的丹麥城市,暗指如“安樂死”一樣充滿矛盾、爭議、不確定性的現代人的道德狀態。“阿姆斯特丹”是全書的起點,也是人物活動指向的目的地,更是主人公生命終結的終點。如果從倫理的角度審視《阿姆斯特丹》這部作品,整本小說即是對當代人物生存狀態、道德尺度進行審視的場域,是一個爭議發生的“阿姆斯特丹”。
空間敘事
《阿姆斯特丹》融入了更為廣闊的歐洲社會政治視野。《阿姆斯特丹》的故事設定在1996年。小說以主人公克利夫·林雷、弗農和加莫尼齊聚共同情人莫莉的葬禮為開頭場景,以克萊夫受命創作千禧年交響曲和弗農千方百計促銷自己的報刊為核心事件,與核心事件有關的故事空間——喬治的府邸、首相加莫尼府邸和報社等處所——構成小說的主體,多層次、多角度地反映英國斑駁的社會現實,對當代英國的道德、政治、傳媒生活方式進行了探討。在故事的結尾,該小說空間轉換到阿姆斯特丹。克利夫·林雷前往阿姆斯特丹參加千禧年交響樂排練,在招待會上,他與弗農相互準備了放有毒藥的酒,結束了對方的性命。阿姆斯特丹“是一個非理性行為的避難所,因為它視賣淫、安樂死等行為合法,因而吸引了那些有毀滅和自我毀滅傾向的人,濫用這個城市自由的名聲”。
可見,阿姆斯特丹作為小說的標題和主要人物最後活動和命運終結的歸屬地是作家謀划空間敘事的一個顯例。該小說中的空間場景是特定的意識形態寓意和社會文化心理的表徵,其空間敘事放大了個體在特定歷史時刻生存的狀態。
《阿姆斯特丹》小說缺乏嚴肅性。
——約翰·厄普代克(美國作家)
《阿姆斯特丹》從人際關係、媒體影響等方面揭示了“文明生活的本質”,該作品流露出對當今英國社會流行價值的辛辣諷刺。
——陸建德(中國社科院文學所所長)

伊恩·麥克尤恩
麥克尤恩擅長以細膩、犀利而又疏冷的文筆勾繪現代人內在的種種不安和恐懼,探討暴力、死亡、愛欲和善惡的問題。代表作品:《最初的愛情,最後的儀式》、《水泥花園》、《只愛陌生人》、《時間中的孩子》、《黑犬》、《夢想家彼得》、《阿姆斯特丹》、《星期六》、《追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