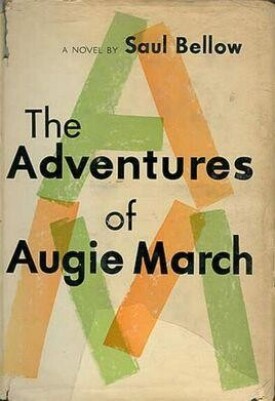奧吉·馬奇歷險記
美國作家索爾·貝婁的成名作
《奧吉·馬奇歷險記》是美國作家索爾·貝婁的第三部長篇小說,也是他的成名作。主人公馬奇是來自貧民窟的猶太少年,自小起周圍的各色人等都想支配他的命運,而馬奇則持有一種強烈反抗態度。因為貧困,他從事過許多職業,但只要發現有被控制的危險,他便立即抽身走開。他雖然沒有失去“自由”,但也找不到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園。他曾想到美麗的大自然中辦一所孤兒院,把愛播向人間,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小說結束時,他成了倒賣戰爭剩餘物資的掮客。
《奧吉·馬奇歷險記》里利用存在主義理論分析了主人公奧吉·馬奇的歷險旅程,試圖回答有關人類存在的問題。該作品著墨於自我意識和社會荒誕性,反映自我和現實的矛盾,關注人的生存狀態和生存心理,從而揭示了奧吉的歷險經歷在本質上是他在荒誕的世界里進行自由選擇,通過自己的行動創造自我本質,從而達到真實存在的過程。它呈現的不僅是某個個體的遭際或民族的命運,而是現代人類艱難地進行個體選擇、尋找自我位置、解決歸屬感等進退維谷的普遍窘境。《奧吉·馬奇歷險記》對物質生活富裕而精神存在危機的現代人具有現實意義。 《奧吉·馬奇歷險記》共12章。
《奧吉·馬奇歷險記》講述了主人公奧吉從20世紀20年代到40年代的人生道路。從小時候起,勞希奶奶、艾洪、西蒙、倫林太太、女友西亞等周圍各種人物就千方百計企圖主宰奧吉的命運。為擺脫外界的控制,他經歷了人世間的種種滄桑:他當過報童,做過雜役,參過軍,在商船上做過水手,去墨西哥尋找機會甚至做過小偷,在不斷漂泊的歲月里,他投身到一個又一個新行當之下,承受種種非禮的待遇。奧吉逐漸長大成年,他漸漸發現對於他這樣的小人物來說,社會就像一張紛亂喧囂的網,從觀念到現實都荒謬且不合情理。他覺得自己處於一個隱隱約約的含有敵意的世界中,到處都是束縛他、制約他的各種因素,想要影響他、改變他的人們一直圍繞在他周圍,他們都試圖把奧吉塑造成他們所希望的樣子。
奧吉隨同女友西亞踏上了通往墨西哥的旅程,然而馴鷹的失敗、身體的重創和女友的背叛使他的夢想變成了泡影。墨西哥之行不僅使奧吉身體受了重傷,而且使他的精神陷入了無法癒合的痛苦之中。在情感上,奧吉成了一個孤獨者,生活在一個與自己對立的、失望的世界之中。所有這一切,使得他似乎成了一個被隨機地“拋”到這個世界上來的“邊緣人”,被遺棄而且孤立無援。此時,世界對他來說是一片虛無。
社會背景
《奧吉· 馬奇歷險記》發生在20世紀30年代世界經濟大蕭條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這一個時期,資本主義得到迅猛的發展,物質財富的積累並沒有給精神世界帶來多大的助力反而出現了個人的精神危機。信仰的缺失,表面的繁榮難以掩飾內心的不安,資本主義的各種弊病暴露無遺。即使這樣,作者仍然對人類精神前途保持這信心。作者藉助奧吉對自己想要的命運的探索來告訴人們:“儘管一個人無法決定自己的命運,至少他能夠把握自己面對命運的方式,有足夠的力量來戰勝醜惡的行為,並使自己的生活完滿。”
人文背景
哲學背景
存在主義產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是20世紀上半葉最具代表性的西方哲學思潮。存在主義自稱以人為中心,是一種研究人的本質、人的選擇以及人的自由等問題的哲學。其代表人物讓·保羅·薩特的哲學思想大體可以總結為以下三點:一是世界是偶然的。世界上沒有任何預先定義的規則,也沒有任何根據某種觀點、思想或精神而演繹出來的預先設定的意義。所以,存在是不確定的、偶然的。面對不確定的客觀外界,人會感到荒誕、混亂,處處受到限制和阻礙。二是自由選擇是人的本質。人在這個世界上是自由的,人的行動選擇也是自由的,自由等於人的真正存在。人是自己行動的唯一指令者,人要認識自由選擇的重要性,並按照自己的選擇去行動和承擔生活的責任。三是存在先於本質。人來到這個世界時沒有任何本質可言。人的本質是通過自己的選擇而創造的,而不是被給定的。要想確立自己的本質必須通過自己的行動,即存在來證明。人是在存在的過程中創造了自己。人不是別的,僅僅是他自己行動的結果。
工業社會物質文明在高速發展的同時,也給人們帶來嚴重的精神危機,這就是異化;異化已然成為工業社會一種重要的現代現象。社會物質化了,人成了物的奴隸,人與物質社會的關係發生異化。高科技產生的自動化加強了勞動分化,造成人與人之間的隔膜、疏離、陌生感,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發生了異化。文明機器的運轉將人格撕裂,人無法在對象上看到自己、承認自己,精神失去了依託,最終導致人與自我關係的異化。貝婁在小說中充分而深刻地展示了現代物質社會中人與物、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及人與自我的異化困境。
生態批評
20世紀60年代以來,在世界範圍內愈演愈烈的生態危機迫使文學家們自主地將生態責任感與人類終極關懷相結合,生態文學乃至生態思潮應運而生。隨著生態批評走向更深入、更廣闊的領域,生態批評家們普遍認為生態批評並非是生態學與文學的簡單相加,也不是套用自然科學術語的批評,而是“吸取生態學的基本思想——主要是整體觀、聯繫觀、和諧觀等”,“生態批評是在生態哲學思想指導下的文學批評。”它把文學批評放在地球生物圈這個廣闊的語境下,立足生態哲學整體與聯繫的觀點,以生態整體主義為基本指導思想,反對長期佔據統治地位的“人類中心主義”,關注文本中體現的生態關懷,結合切實的生態問題和文學文本來探討人與自然的關係問題,“揭示生態危機之思想文化根源,同時也要探索文學的生態審美及其藝術表現”,喚醒人們的生態保護意識,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
創作來源
人物經歷
貝婁於20世紀初期出生於加拿大,上中學前跟隨父母遷至美國芝加哥,成為猶太裔美國人,正是因為這種特殊的身份,才給予了貝婁創作《奧吉·馬奇歷險記》的靈感,他憑藉對猶太移民後代和美國現實社會的雙層了解來塑造人物形象,主人公奧吉·馬奇具有猶太民族的典型特徵和性格,渴望成就美國夢,卻一直過著壓抑的生活,但卻從未忘記過烙印在心的猶太民族身份,在現實社會和生活中不斷成長和領悟。
人物思考
存在主義是索爾·貝婁創作思想的一個重要方面,它來自貝婁對那個時代現實的深邃洞察和冷峻思索。貝婁受到了許多存在主義哲學家和文學家深刻影響,所以他在刻畫奧吉·馬奇這個人物時,充分體現了主人公對自由的追求以及不斷碰壁后的困惑和迷茫、對自我價值和人生意義的思考,強調了“人”在荒誕的世界里的自由選擇和真實存在。
創作取材
《奧吉·馬奇歷險記》取材於美國現代社會生活,主人公在小說開篇時說的第一句話就是:“我是個美國人,出生在芝加哥”。美國元素成了該小說發展的不可或缺的元素,芝加哥更成了故事發展的大舞台。但馬奇又作為一名猶太人,不可避免地承襲了某些猶太文化特性,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存有一種內在的猶太文化情感積澱,所以在其遊歷和歷險中,他顯得如此的與眾不同。
奧吉·馬奇——“我”
主人公奧吉·馬奇是一位出生在芝加哥的猶太孩子。奧吉·馬奇三兄弟自小遭受父親遺棄,由性格軟弱的母親撫養。熱愛生活、內心純潔且崇尚自由的奧吉在當代城市生活中苦苦追尋人生的意義,但卻深陷自我與現實、個人與社會的矛盾之中,遭遇著現代人的精神危機。最後奧吉在不斷流浪的生活中發現了一條生命的軸線,這就是“真理、愛情、和平、慷慨、有益、和諧”。
勞希奶奶教導奧吉:“想在這個世界上存活,就要狠心使用任何手段,包括撒謊和偷竊,那都不算什麼。”奧吉從小就被這種“畸形”教育所渲染和壓迫著,他感覺到自己無論是物質還是精神,都處於“寄人籬下”的狀態。
勞西
勞西奶奶是一個明顯被社會所異化的人物。她奉行“人性惡”的信條,把社會關係當成為人處世最重要的基點,一切利益至上。到了晚年,勞希奶奶的兒子們雖各個成才與發跡,卻無人願意看望與照顧她,最後她被送進了養老院。當她拿出五角錢給奧吉當作送她到養老院的車費時,演繹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異化所造成的悲劇。可悲可嘆的是,人類最珍貴的親情也沒有例外。
奧吉的父母辛苦賺取的房產卻由寄膳房客勞希奶奶掌管,一家人都要聽命於她並為其提供服務,奧吉曾講述過:“自從勞希奶奶到家后媽媽就變成了十足的傭人,全部權利都交付於她,媽媽辛苦操勞的結果都由她來享受,而‘我’和哥哥也得服從勞希奶奶的決定。”造成這種局面的真正原因是勞希奶奶美國白人(WASP)的身份,而奧吉一家為了融入美國社會不得不忍辱吞聲。
艾洪
艾洪是個殘疾人,他是一家地產公司的老闆。奧吉在地產公司打工並寄宿在老闆家。艾洪嫖妓的時候都會要求奧吉幫忙,他對奧吉的教育不同於勞希奶奶,總是用足夠的利益來誘惑和教導奧吉為人處事的道理,而這並未讓奧吉感到尊重。艾洪夫婦經常算計著一切,任何行為都會刻意提醒奧吉要注意自己猶太移民的低等位置。
西蒙
西蒙是主人公奧吉·馬奇的哥哥。西蒙一直是奧吉的偶像,無論是學習,還是工作,西蒙都用行動來證明著美國夢是光鮮的,他工作回來總會談論到自己遇到的名流,並誇誇其談功利社會所帶來的巨大機遇。
主題思想
《奧吉·馬奇歷險記》主題思想:在荒謬、不確定的現實世界中,探索人類存在的價值並追求自由。
《奧吉·馬奇歷險記》展現了美國現代人精神與靈魂的斑駁陸離,對美國社會狀況和時代風貌進行了淋漓盡致的藝術再現。在荒誕的社會裡,所有的一切均與奧吉的願望大相徑庭——作為個體的“人”被忽略,人的慾望被壓制,人的生命在貶值。但是奧吉不願受制於人,拒絕做出改變。因此,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以逃避來與強大的現實對抗,一次又一次地獨自面對這個無意義的世界,荒謬且沒有盡頭。
奧吉·馬奇的自由選擇
奧吉有著一套自己對生活的理解,他反對別的人物或事件掌控他的命運,對生活進行著不受他人干涉的自由追求。自兒時起,奧吉一直在面對想要影響、改變他的頑固人物和難以理喻的荒謬事件,正是這些人物和事件幫助奧吉認識了世界的荒謬和混亂。周圍的各色人等都想支配他的命運,而他則持有一種強烈的反抗態度。當他周圍的人試圖把他塑造成他們所希望的樣子時,奧吉堅定地對想要塑造、改變他的人說“不”,不斷地堅持自我選擇,努力地把握自己的命運。在此過程中,他從事過許多職業,但只要發現有被支配或控制的可能,他便立即抽身走開。他寧願像個流浪漢一樣不斷地去漂泊、做各種苦工,甚至參與犯罪活動,也不願屈服於現實的壓力,受社會環境的限制和人與事的束縛。奧吉在追求個人自由、漂泊歷險的同時,也在進行著精神探索,尋找他可以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園。在這個風雨飄搖的世界里漫遊,奧吉與荒謬的生存環境搏鬥著,抗拒著壓抑自己的外部力量,試圖找到一個他可以賴以生存的立足之地。同時,他也在執著地忠實於自己的內心真實需求和渴望,尋找自己的位置與歸屬,尋找自身存在的意義,並在此過程中實現對自身價值的追求和對人生意義的探索,達到他所希冀的理想境界。
儘管奧吉沒有失去“自由”,儘管一路遭遇的重重挫折和失敗使他孤獨失落、困惑迷茫,但是奧吉對自由的選擇、對自我的追尋如此強烈,以至於任何“阻逆”因素都無法阻擋他的腳步。
在到達死亡的終止線之前,人生是一個無盡的探索過程。只要人的生命沒有走到盡頭,其本質的積累就不會完成,精神求索的旅程就不會結束,自由選擇的過程也就會依然繼續下去。奧吉所經歷的身體上和精神上的雙重旅程、竭力對生命本質與意義的追尋,都強調了人類的自由選擇。這正體現了存在主義哲學的精華:人在這個世界上是自由的,人的行動選擇也是自由的。這種自由賦予人面對荒誕世界進行選擇和行為的權利。所以,人要認識自由選擇的重要性,敢於進行自由選擇,通過行動創造自我本質。
奧吉·馬奇的真實存在
存在主義認為存在先於本質。人剛一出生時,沒有任何本質可言,人的本質是後天通過人的意識自由選擇而形成的。孤立的個人的非理性意識活動才是最真實的存在。人不是別的東西,而僅僅是他自己行動的結果。人在無意義的宇宙中生活,沒有任何本質可言。所以說人的本質是通過自己的選擇而創造,通過自己的行動來證明。奧吉的漂泊旅程實際上是一個尋找的過程——他所尋找的是一個證實自己真實存在的過程。雖然這個探索的過程充滿困惑和無奈,同時他也被自己內心無限的不安與焦慮所折磨、糾纏,但他始終是一個堅定的靈魂安頓的追尋者,堅持通過自己的行動來證明自己真實存在於這個世界中,為追尋真實存在而不停地探索。從童年到中年,奧吉一直努力地抗拒外界干擾,對自我價值和人生意義進行著思考。
身處世界的荒謬混亂之中,理想和現實之間的巨大的差距使得奧吉不能停止流浪和四處漂泊,完成根據自己的意志進行自由選擇以獲得本質的過程。此時,他內心充斥著一種對自我身份、對現實和未來命運的不確定。所以說奧吉所經歷的與其說是身體上的流浪,還不如說是意識上的流浪——他在追尋自己內心的渴望,安頓自己失落的靈魂。只有藉不斷的歷險和探索來實現真正的自我,他才能確定自己是真實地存在於這個世界上,因為人必須通過自己的選擇來決定自己的存在方式,人對自己的存在是負有責任的。所有這些都在奧吉尋找自我本質的過程中得到反映和體現。
在現實生活中,人的思想和行動不能不受外部世界的約束,絕對的真正的存在是不可能實現的。所以,奧吉在追尋內心世界的過程中,對外部世界也在逐漸包容和接納並與之日趨和諧,他逐步地學會了如何處理個體與外部環境之間的關係,如何適應外部世界而不是試圖逃離它。如何處理個體與外部環境之間的關係,如何適應外部世界而不是試圖逃離它。
《奧吉·馬奇歷險記》是索爾·貝婁從存在主義出發,對人類外部世界與內心意識之間衝突的洞察,它著墨於自我意識和社會荒誕性,關心人的生存狀態和生存心理,闡釋了自我本質與生存環境之間的矛盾這一美國當代小說的重要主題。
貝婁通過分析美國底層小人物在現代社會中的生存狀態來探索人類存在的價值及意義。在奧吉對充滿偶然性的世界的探索過程中,雖然現實的荒謬使得他不可抗拒地感到疑惑、失落和疏離,但是奧吉仍然不斷探索著存在的意義和生命的價值。對於奧吉而言,他在進行艱難的個體選擇,在尋找自己的位置,解決歸屬的困惑。所以,該小說給人們的啟示已由外界轉到內心,由物理轉到心理,由現象轉到哲學。通過奧吉的歷險和探索,讀者看到的不僅是某個個體的遭際或民族的命運,而是現代人類的進退維谷的普遍窘境,從而得以在形而上的探究中保持對現實的關注和批判、對人類的剖析和悲憫,這對物質生活富裕而精神存在危機的現代人來說具有現實意義。
《奧吉馬奇歷險記》的主旨是不確定的,貝婁故意不做武斷的結論,讓其沒有肯定的結局,既沒有表現出顯而易見的樂觀,也沒有對生活失去了信心。從某種意義上講,《奧吉馬奇歷險記》又是開放性的,留給讀者更多的遐想餘地。這種凌亂、不確定正是奧吉馬奇真實生活乃至人類生存現實的完美再現,也是貝婁對當代世界及人的獨特理解。也這正是這種模糊和不確定,更接近人和世界的本質,更接近真實。
敘事藝術
貝婁風格
《奧吉·馬奇歷險記》是貝婁的成名代表作。在《奧吉·馬奇歷險記》的創作中,貝婁找到了自己的聲音,一種能夠用最通俗、精緻的語言生動地描繪出當代社會,清楚地道出自己人生哲理的聲音。
1、語言特點:“口語化的街道風格”與“精妙的哲理性分析”相結合語言表達上,《奧吉·馬奇歷險記》使貝婁創立了自己的風格,文體既口語化,又高雅精緻,語言機智風趣又富於哲理,使作品能夠雅俗共賞。
開篇奧吉·馬奇自述伊始,貝婁便借奧吉之口向讀者交待:
“我這人處事待人一向按自己學的一套,自行其是;寫自己的經歷時,我也離不開自己的方式:先敲門,先讓進。”
也就是說,作品有什麼說什麼,娓娓道來,直言不諱。“先敲門,先讓進”,自然流露,不做刻意修飾。市井俚語與辛辣的言辭,真切地反映生活現實。
口語化的表達在小說中隨處可見,比如奧吉和西蒙見面的場景。措辭直白,辛辣尖銳,充滿諷刺的意味。不過,現在他想知道我所經歷的坎坷,可我不想告訴他。我去墨西哥幹什麼?
“‘我’愛上了一個姑娘。”
“哦,是嗎?別的呢?”
‘我’對‘我’的種種失敗和教訓,隻字未提。其中,“去墨西哥幹什麼”,用的是“stay put”,意思是呆在一個地方;“愛上了一個姑娘”,用的是“girl”一詞的俚語形式“bird”;“失敗和教訓”用的是“busted down”而不是“failure”。不說做了什麼事情,而說呆在什麼地方,彷彿西蒙早就料到奧吉會不務正業、遊手好閒。西蒙怕奧吉因為他有錢就看不起他,而奧吉想要得到更好的命運,但又不想把自己碰壁的經歷告訴西蒙。兄弟倆內心的細微變化表達得淋漓盡致。
作品中還時時滲透著閃爍哲理之光的警句,發人深省。奧吉認為,人生道路上最危險的就是這些一心想要操縱他個人命運的人。於是,他警告自己:
“當心,啊,你只不過是粒撒在磁場周圍的鐵屑,全已俯首聽命,那為什麼還要尋求失去更多的自由呢? 那股巨大的阻力威脅著要戳穿你的肋骨,擦破你的臉,折斷你的牙齒,離開。獨自努力地爬著、騎著、乘著、跑著、走著,朝著個人的目標,留心世上那些有權有勢的可畏人物。”
奧吉把他自己比喻成磁場周圍的鐵屑,形象地說明個人已經全然俯首聽命,失去自我。他不禁要問:為什麼還要尋找更多的自由?一個比喻說明了原因。具體生動的事例說明了抽象玄奧的道理:不要淪陷到失去自我的洪流中,要用盡各種辦法,遠離這般樂於操縱他人命運的人。這段話用語輕鬆自然,似乎全然是心中自言自語的摘錄,不作任何文學裝飾,顯得既符合實際,又富哲理,粗俗中又有淡雅的格調,辛辣的措辭中孕育哲人的透徹和深邃。
2、表現手法:“現代主義”與“現實主義”相結合
表現手法上,貝婁既吸收現實主義的某些長處,又運用現代主義的某些手法,把現實描繪和歷史回憶、內心活動和外在世界巧妙地交織在一起,使我們得以同時看到人物的內心和現實世界、現狀和他的歷史或未來。
以小說第一章為例,開篇奧吉回憶母親,是歷史回憶。喬治、勞希奶奶及勞希奶奶教奧吉撒謊,這些都是真實場景的描繪。而奧吉的心裡活動,則是從現在的視角去回憶和總結:媽,有一副圓眼鏡,那一次,事先經過勞希奶奶調教,我才去診所撒了一通謊。現在看來,並非定要撒謊不可。
貝婁把場景再現與從現在視角回憶當時情形相結合,突破了時空的限制,使讀者更好地理解當時勞希奶奶太上皇的地位,以及奧吉兒時與現在不同時期的心理狀態。
倫林太太勸說收養奧吉的一段描寫,也展示出貝婁高超的表現手法。倫林太太的話語描述,奧吉的心理描寫,穿插著從現在時間回憶當時的情形,三者相互交織:
“女人任你挑,就連西亞·芬徹爾那樣的姑娘也行。”她提到芬徹爾家,這使我怦然心動,後來,當我對自己完全說實話時,我不得不承認,我是毫無希望的。
倫林太太的話,是現實的描寫。“她提到”一句是奧吉的心理描寫。“後來”一句使用過去將來完成時態。如此,讀者了解到事情的將來時間裡,奧吉的心理狀態。這便是貝婁獨特的敘事方式和表現手法。
這種“東一拳,西一腳”的寫作風格,給人的感覺是雜亂無章的,但是正是貝婁似乎信手拈來,自然流露的筆觸,心理活動與外在環境的交織,時空的相互轉換和交替,讓讀者全面細緻地了解人物,對當代文化做出精妙的分析。
舉例,第十章,當奧吉拒絕了倫林夫婦的收養,和喬·戈曼一起偷渡加拿大移民被捕后回到芝加哥之時,文中是這樣描述的:
“芝加哥張開它那噴著火焰和濃煙的大嘴吞噬著我們。我心裡明白,我回來不會有安寧和好日子過,首先是那位波蘭女管家,其次是我媽,還有西蒙。”
先是進行景物描寫,用抽象化的火焰和濃煙指代工業化的標誌工廠和汽車,用具體化的大嘴來指代芝加哥這座城市。接著是奧吉的心裡活動。貝婁讓我們看到奧吉置身的外在環境,同時看到奧吉的心理活動;看到工業化大背景,同時看到在物質化面前個人惶惶終日的心理狀態。貝婁引導讀者隨奧吉一同思考,使作品更具普適性,深刻地揭示全人類共同的困境。
3、喜劇風格:“自嘲—幽默”
貝婁的喜劇風格主要是通過“自嘲—幽默”的手法來表現的。這種“自嘲—幽默”的背後蘊含著無可奈何的心情。這是一種以喜寫憂的手法。在貝婁看來,敢於自嘲的人實際上也是一種清醒的表現。
奧吉自嘲的描寫有很多,比如:奧吉苦苦求索,一生都想有個較好的命運,然而卻四處碰壁。當別人問他:“你那場追求有意義的命運的戰鬥進行得怎麼樣”時,奧吉只好自省自嘲地說:“‘我’只是想做正當的事,而‘我’卻碰得頭破血流,牙齒掉了,心靈受到創傷,十足是個糟糕透頂的戰士。”
又比如奧吉和西蒙見面的場景,對話之前穿插了一段奧吉的心理活動描寫:
“我並沒有感到自己比西蒙強,一點也不。如果我真的輕鬆愉快,悠然自得,他也許會羨慕我的。可就我這般光景,還有什麼值得羨慕的呢?”
奧吉的這般自嘲似乎正是西蒙心中所想:是啊,這般光景有什麼值得羨慕的呢?但是奧吉心理想的,並且時時追尋的並沒有說出口,那就是“我得有個夠好的命運,而這是首要的”。當西蒙神氣不可一世地開著汽車在街道上馳騁,奧吉不無諷刺地對自己說:
“在機械王國里稱雄的人又有什麼不好呢,相信我,‘我’並沒有為自己,為堅持有一個‘高級的’、獨立的命運而自豪,‘我’所能說明的一點就是,儘管‘我’渴望獨立自主的命運,然而這並不僅僅為了‘我’自己。啊,何必太認真呢?認真只是為少數人所有,只有少數得天獨厚的人才能說得清楚。”
這樣看來,奧吉似乎覺得在物質至上的現實社會中,稱雄的人並沒有什麼不好。但是奧吉這樣說,並不說明他放棄了自己的尊嚴,放棄了追尋更好的命運。他渴望獨立自主的命運,而且深知這不僅僅是為了他自己。奧吉是如此堅定,但在別人眼中,自己真的沒有什麼值得誇耀,這種情形讓奧吉如何自處呢?反觀在機械世界里稱雄的人,他們真的幸福快樂嗎?如果真的如此,人們為什麼整天悶悶不樂,西蒙又為什麼會有自殺的想法?一切沒有人能說得清,奧吉只能時常“自嘲”,才會得到短暫的心理平衡。這樣的“自嘲”,一方面讓讀者看到人物的執著追求,另一方面也說明,貝婁認為追求自我本質的人,註定會在物質社會中面臨失敗和挫折,聊以自慰的方式也許只能是自嘲。然而,有勇氣自嘲的人,也是清醒的,沒有被淹沒在迷失自我的洪流中。
本文從語言特點、表現手法、喜劇風格三個方面分析了小說《奧吉·馬奇歷險記》獨特的“貝婁風格”。可以清晰地看到貝婁對傳統敘事藝術的超越和發展。貝婁對於異化的環境與個人尊嚴的關係這一主題的探索,對當代人極具啟發作用。正如奧吉所領悟的:“人生的軸線必須是直的,這些軸線忽然一下子筆直貫穿‘我’的全身。真理、愛情、和平、慷慨、有益、和諧,‘我’想我只能從低微處、簡單處做起。”
奧吉決定從最低微處做起,有自己的地盤,從福利院接來孩子,從南方接回媽媽和弟弟喬治,在一方凈土上,實現自己對自由的追求,不再受制於其他任何人。他這個小小的願望因為戰爭爆發最終沒能實現,但是他留給現代人的啟迪遠不止於此。貝婁以他獨特的方式不知不覺中將讀者帶入對生活哲理性的思考。這種對人性和生活的思考超越國度和時代,道明了生活的真諦:從細微處做起,做一個善良的人,追求純真的自我,實現一個有價值、有尊嚴的人生。
該作品無論人物設置、故事情節,還是敘事風格、文化內涵,都極具特色,成為美國猶太文學的經典之作。小說的主人公奧吉·馬奇是第二代猶太移民的典型代表,他跟隨上輩來到美國奮鬥、拼搏,過著寄人籬下的底層生活,奧吉深受“美國夢”的誘惑和影響,從未放棄過追求幸福生活的權利,在接受了現實和夢想的重重打擊后,奧吉開始了尋覓猶太民族身份之路,輾轉多國后又回到了美國芝加哥,他身上既具備著猶太人與生俱來的頑強品質,也承擔著融入美國主流社會的艱巨任務,鑄就了主人公成長的“三部曲”。貝婁試圖勾勒屬於主人公奧吉·馬奇的坎坷人生,為讀者呈現美國猶太移民的真實生存狀態,奧吉的成長旅程無疑也是整個猶太民族的壯大之路,作者藉助文學的力量來引導“美國夢”追尋者憑藉實力來紮根美國本土,獲得屬於自我民族的身份和地位。
——閻爽(中央司法警官學院副教授)
《奧吉·馬奇歷險記》常常被稱為當代的《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同是歷險記題材,“無論從形式上還是從體裁上來說《奧吉·馬奇歷險記》都是對《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的直接繼承”。而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奧吉·馬奇歷險記》的主人公奧吉與他的前輩哈克也有相似之處。兩位主人公的性格都具有反抗性——哈克與所謂的“社會文明”格格不入,而奧吉對周遭的人具有強烈的說“不”的願望。於是,出走冒險是他們選擇的逃脫束縛、反抗現實的方式。然而在不同的時代與社會文化背景下,身世、性格與經歷相似的兩個人物形象卻具有不同的典型意義:哈克是資本主義上升時期廢奴運動的產物,是追求自由與新文化的象徵,而奧吉是異化世界的犧牲品、是“反英雄”的典型。
——韓山師範學院大學英語教研部

索爾·貝婁
主要作品有:《兩個早晨的獨白》、《奧吉·馬奇歷險記》、《雨王漢德森》、《賽姆勒先生的行星》、《洪堡的禮物》等。1976年,他以“對當代文化富於人性的理解和精妙的分析”獲得諾貝爾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