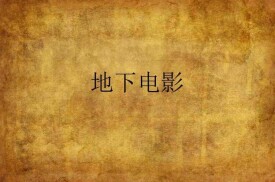地下電影
地下電影
地下電影(underground film)是五十年代末出現在美國的一個秘密放映個人製作的實驗性影片的運動。不久后,這個詞就被用來指稱美國和西歐的一切實驗電影。
由此,這類實驗影片的製作和放映活動便愈來愈轉入地下,因而得名,地下電影具有先鋒性,不同時期的地下電影對於核心主題有著不同的追求。
從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美國紐約市警察局多次對一個專門放映實驗電影的電影資料館進行干預,因為那裡放映出的內容淫穢,放肆地描寫性愛、同性戀、易裝癖、色情舞會和頹虛生活方式等一切違禁題材的短片。有一次還逮捕了這种放映會的組者. "美國新電影集團"的首領約·梅卡斯。由此,這類實驗影片的製作和放映活動便愈來愈轉入地下,因而得名。
地下電影運動的初期代表人物是傑克·新密士(《燃燒的生*物》,1963,等)和安第·瓦霍爾(《吻》,1963,等).在他們的影片里,引人注目的是赤裸裸的性描寫和毫不掩飾的虛無主義思想,而不是表現技巧上的創新。誠如約納斯-梅卡斯在1967年發表的《我們在哪裡--地下?--"美國新電影"》一文中宣稱: "我們對自己說:我們不知道什麼是人,我們不知道什麼是電影。因此我們要完全開放。我們將朝任何方向行動……我們就是一切事物的準則。"從六十年代中期開始,愈來愈多的具有不同創作傾向的實驗電影導演加入了地下電影的行列,並明確提出要使電影成為一種現代派的藝術,儘管這些個人影片製作者風格迥異,競相標新立異,但有兩個共同的特徵:一是無例外地使用18毫米膠片,以此作為與商業電影相對立的一個標誌:是在題材上繼續趨向於性的表現和鼓吹反傳統道德觀念.如美國影評家帕克·泰勒所指出的: "地下電影的歷史是從這樣一個論斷開始的:電影攝影機的最重要的、不應該被遺忘的功能著之一,就是要深入到那些成為禁忌的領域中去,這些領域對於照相性的再現說來過於隱私,過於令人震驚,過於不合乎道德規範。"
從六十年代中期開始.地下電影運動也出現在西歐各國,特別是西德、義大利、荷蘭和英國。西歐地下電影的主要傾向是拍攝結構主義的抽象影片,主要代表人物有英國的馬爾科姆·勒·格里斯和彼得·吉達爾,西德的成爾納·奈克斯和奧地利的彼得·科佩爾卡等。
由於“地下電影”無法進入正常的發行渠道,一般很難看到。它們在國內的傳播,主要採用三種方式。
一是通過“民間觀影組織”在一些電影酒吧(如原北大東門外的“雕刻時光”、北大西門外的“Everyday雕刻時光酒吧”、清華東門外的“盒子咖啡館”、“燕尾蝶咖啡館”、原電影學院附近的“黃亭子酒吧”等)放映,或者在大學校園內以學術交流的名義進行小範圍的放映。最早出現的觀影組織是成立於1996年10月1日的上海“101工作室”(負責人徐鳶),隨後廣州的“緣影會”成立於1998年(負責人歐寧),北京的“實踐社”成立於2000年4月1日(負責人羊子),南京的“後窗藝術電影觀摩會”成立於2000年6月(負責人衛西諦),瀋陽的“自由電影”成立於2000年,以及武漢的觀影會(組織人Rock)、鄭州邊緣社、重慶M公社、山西漸近線觀影會等等,這些類似於影迷俱樂部的組織,除實踐社由北京電影學院的學生髮起之外,其他的都是業餘電影愛好者自發形成的,基本上都是非營利的。但是,隨著它們影響的增加,活動範圍也不僅僅限於觀影,比如上海“101工作室”的主要負責人成為現任《中國銀幕》雜誌社創作總監或擔任編輯、記者之職,而北京的“實踐社”嘗試舉辦了“第一屆中國獨立映像節”(主辦單位是南方周末、實踐社和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而後“映像節”上的作品開始在全國主要大城市漫遊(如瀋陽、上海、成都、南京、重慶、昆明等),據執行主席羊子打算,“映像節”徵集影片的範圍將擴展到整個華人地區,而且,實踐社與法國克萊蒙費朗短片電影節合作,將在2002年2月的電影節上舉辦“中國新影像展映”的活動。這些來自於民間的觀影群體不僅改變了中國電影的觀影方式,在某種程度上普及了電影文化,並有可能成為中國電影市場分化的基礎。
“地下電影”的第二種方式是通過“盜版” VCD和DVD 。隨著盜版音像事業的蓬勃發展,以前被“電影學院”和“電影資料館”所壟斷的片源正在被打破,如同打口帶一樣,大批電影史中確立的大師級影片以及通過國際電影節呈現出來的藝術電影,受到廣大電影愛好者的歡迎,這不僅為上面提到的觀影組織提供了片源,而且成為影迷觀看電影的主要渠道。據一項關於大學生接觸電影方式的調查顯示:“通過電影錄像或VCD接觸電影的大學生佔80.6%”。如果進一步區分的話,前幾年大量出現的盜版VCD主要是好萊塢大片和港台的通俗電影,藝術電影很少,之所以盜版藝術電影,似乎是出於為已經飽和的盜版市場尋找新的消費群體,但“最近”剛剛興起的盜版DVD則從一開始就傾向於藝術電影。暫且不談“盜版”對於電影工業的損害,其產生的一個直接的結果,就是大量非電影專業的電影Fans的形成,他們藉助網站在一些電影論壇和BBS中自由地討論電影,並有可能成為未來中國藝術電影市場的潛在消費群體。
FTP上傳工具
第三種方式,則是通過提供電影下載的區域網或FTP站點還是“最近”流傳的BT下載等等下載(“今後”寬頻網會更方便地提供影像的傳遞)來觀看“地下電影”,如《蘇州河》、《小武》等,當然,網上的電影也大多是通過盜版VCD和DVD上載到網上的,其影像效果更加粗糙。
通過這三種方式,“地下電影”並沒有真正地被掩埋在“地下”,而是在一定範圍??當然需要指出的是,這些“地下電影”基本上處於封存狀態,有趣的是,從這三種觀影方式也可以看出,喜歡電影的觀眾並不去“電影院”看電影,而這些脫離電影院的電影是否可以叫做真正的電影(不是膠片放映),其盜版和FTP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到這些青年電影愛好者對於電影的認識,似乎也是一個需要討論的問題。
“城市的一代”
2001年 2月23日——3月8日在紐約林肯藝術中心舉辦了名為“The urban generation?Chinese cinema in transformation”(城市的一代:中國電影正在轉變!)的中國電影節,組織者為紐約大學電影系和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化系,共有十個中國青年導演的十一部作品參展,有《巫山雲雨》(章明)、《郵差》(何建軍)、《小武》(賈樟柯)《月蝕》(王安全)、《長大成人》(路學長)、《呼我》(阿年)、《兒子》(張元)、《趙先生》(呂樂)、《民警故事》(寧瀛)、《橫豎橫》(王光麗)和《站台》(賈樟柯),幾乎都是“地下電影”(“沒有機會在中國上映”)/“獨立電影”(“國家電影體制之外的作品”)/第六代導演的片子,這也可以看作是續中國大陸第五代導演之後,“地下電影”獲得國外的認同的一種體現(儘管“地下電影”很早就已在國外流傳,而且上面提到的片子也已打破體制內、外的區別)。
從第六代在國際電影節上獲獎的情況來看,還遠沒法與第五代導演分庭抗爭,雖然獲獎不斷,但很少能在戛納、威尼斯、柏林三大國際主流電影節上獲獎(只是王小帥的《十七歲的單車》獲第51屆柏林電影節評審團大獎銀熊獎)。這種第六代不如(起碼從影響上說)第五代的原因在黃式憲著《“第六代”被“命名”——中國影壇迎接新千禧春訊第一聲》中被解釋為(第六代)“沒有形成令人振奮、眾口皆碑的‘衝擊波’,則顯然是受到了世紀交替之秋,被學術界稱之為一個深度和力度俱被解構的‘後文化時代’的總體語境所給予的制約”(不知道“後文化時代”是不是指一種與第五代相比不再復現的歷史機遇) 。他們的意義還其行為本身以及製作模式突破了建國以來國家壟斷生產電影的體制即獨立製作,“為中國電影開闢出一條嶄新而充滿活力的革命路線” ,當然,獨立電影的製作方式又或多或少地決定了這些第六代導演的片子成為“地下電影”的命運。不過,城市影像的表達也成為他們在電影風格上區別於第五代電影的重要標識。
“地下電影”浮現在90年代
“地下電影”是90年代才開始出現的一種電影事實,而且尤其是這幾年,這些屢禁不止的“地下電影”似乎呈現出一股強大的誘惑力而在國外電影節與國內封殺市場之間遊刃有餘地上演著。有趣的是,“地下電影”紛紛在國外電影節上湧現出來,似乎與“電影國際化”和電影“走向世界”的主流敘述相吻合,可結果卻是被排斥在主流敘述之外(似乎官方通過電影來形塑民族整合或裝點門面的興趣並不大,相比它們的違規行為來說,功不抵過) ,其被禁的原因,來自於這些影片在沒有送交國家電影局審查或者在沒有被通過的情況就送出國外參加比賽,從而不能獲得在國內公映的權力。
對於成為“地下電影”的後果,有的導演似乎已經早有所料,如賈樟柯坦承,他本人在拍《站台》這部片子時,就已經知道《站台》不會獲准在大陸上映,因為他在禁拍期還沒有結束的情況下,《站台》已經拍攝製作完成了,可謂“罪上加罪”。而未經國家電影局審核私自送出國外評獎的情況並非沒有處罰的先例,早在1993年就出現了所謂的“七君子事件” ,既然明知道不會獲得公映的結果,他們為什麼還要頂著違規前行呢?
這些電影人對海外電影市場的興趣,與其說是他們懷抱民族復興而伴隨著一系列“走向世界”的豪情,不如說在90年代隨著國內市場化的深化,“海外藝術電影的製片人與投資者開始矚目於大陸這些生機勃勃的藝術家”的結果。從內部看,隨著中國由計劃經濟全面向市場經濟的轉軌,昔日被國家壟斷的電影工業,已經不可能從國家那裡獲得更多的扶持,在越來越有限的國家電影資本的現實下,國家對於電影生產只能重點支持,而不可能全面承包。相比藝術電影、商業電影,主旋律影片更吸引著國家始終不渝的興趣,再加上主旋律影片在市場面前的脆弱性(無法收回成本),更加強了國家對其投資的力度,似乎90年代??大量生產為意識形態的國家利益服務的主旋律影片的壟斷集團。在這樣一個背景下,本來剛剛復興的民族電影,突然失去國家扶持而成為拋向市場的商業大潮中的“孤兒”。這樣就為海外資本投資大陸電影市場提供了歷史的契機,同時也是一種“內在需要”(作為自負盈虧的製片廠除了完成國家定購的主旋律影片之外,還有大量閑置的時間和精力來自謀生路或創收,顯然也需要資本的注入)。當然,相比昂貴的好萊塢製作,投資中國大陸電影要划算的多:充足的實景、廉價的演員和工作人員等條件,都是吸引歐洲資本、港台資本和少量的大陸民間資本的好選擇。
從這一點上也可以看出,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國資本在中國加入WTO以前已經很順利的進駐中國電影的“生產”市場,因此,瀰漫在國內電影市場上的除了一些主旋律影片之外,另一種似乎司空見慣的現象卻是“合拍片”(合資片)的出現。在一篇《今年(2001年)最值得期待的八部中國電影》 中,羅列的八部電影幾乎全是合拍片。另外,不容忽視的是,相對電影工業“生產”的市場化運作,在消費渠道卻保持計劃經濟的作風。雖然在1995年,中國大陸首次允許每年進口10部好萊塢大片,但卻沒有改革已經成為電影工業不可或缺的影院制度。從體制上來說,中國沒有院線放映的機制,只有一個電影管理總局,下屬十六個合法的電影製片廠,可謂是高度計劃經濟的產物(儘管它已經由國營轉為了國有),電影的放映權以及電影的院線依然成為國家的壟斷。這樣,相比廣闊的海外藝術電影市場,和日漸委瑣的國內市場以及壟斷的營銷策略,呈現在這些體制內的合資片和“外資片”(全資片)面前的,一邊是海外的“陽關道”,另一邊則是國內的“獨木橋”。正是在這种放棄“獨木橋”而闖“陽關道”的選擇,使一些與國內沒有資金關係(利益關係)的“外資片”往往(宿命和理所當然地)走向“地下電影”的命運,這在90年代中國電影圖景中浮現了一幅“獨特”的電影之路。
如前面提到的第五代導演張藝謀、陳凱歌、田壯壯的三部片子無一例外都是海外投資,而且都在當年的重要電影節上獲獎。《藍風箏》有香港和日本資金,以日本影片的名義參加國際電影節,獲得第六屆東京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獎、最佳女演員獎和最佳導演獎;《霸王別姬》是香港湯臣公司出品,獲當年戛納金棕櫚大獎;而《活著》
《活著》
投資方為香港年代公司,影片獲戛納評委會獎,演員葛優也登上戛納影帝的寶座。之後等待它們的就是打入中國著名禁片的行列。這些影片與他們以前的片子有著本質的不同,以前的片子市場始終在國內,而當前由於海外資金的介入,電影市場已經由國內轉向了國外,所以他們不用擔心市場以及是否能在本地上演等問題,進而也不用在乎影片的主題是否照顧禁區,因為影片只要在國外電影節上獲獎,就可以打開海外的藝術電影市場。影像本身似乎與中國的關係並不那麼親密,或許僅僅是一個鏡中的中國影像。雖然他們都是體制內的導演,但也獲得禁片的殊榮,似乎與獨立製片人具有了相同的命運,這至少反映了中國電影人在本土和國際語境的尷尬遭遇。
而對於那些獨立製片人來說,他們沒有如同張藝謀影片擁有一個穩定的海外市場和持久國際的聲譽的優越條件,而需要面對更多的尷尬和特殊境遇。最早進行獨立製作的是張元,然後出現了何建軍、王小帥、賈樟柯等人。一般來說,他們都要冒著背負債務的壓力或在極其拮据的情況下拍攝第一部作品,顯然殘酷的現實似乎不可能允許他們進行多次嘗試。王小帥的《冬春的日子》只花了10萬,資金來自於幾個朋友的拼湊,好像攝影師劉傑、演員劉小東都出了資;何建軍的《郵差》花了70多萬,主要來自於大部分是鹿特丹電影節和香港朋友贊助,並在歐洲完成後期製作的(因為其第一部作品《懸戀》曾在鹿特丹電影節上獲獎);賈樟柯的《小武》花了30多萬,主要來自於香港的投資,他曾因《小山回家》獲1996年香港獨立短片及錄像比賽故事片金獎。然後,這些作品在國際電影節上出現並獲獎,從而他們就可以擁有充分的資金來繼續自己“獨立”製作的藝術生涯。等到王小帥拍攝《十七歲的單車》時就已經可以有300萬的資金,而賈樟柯的《站台》也可以在法國資金和日本北野武事務所的投資下相對寬裕的環境下製作完成。
“地下電影”作為一個特殊時期出現在90年代的中國電影表象當中,可以說它是全球化背景下國外資本滲透和國內市場越來越市場化運作的國家電影工業所壟斷的電影放映市場下的怪胎。我曾粗略地查看了一下《電影審查暫行規定》 ,這個規定並不是嚴格的電影分級制度,而是國家實行電影審查制度的規定,即未經廣播電影電視部的電影審查機構審查通過的電影片不得發行、放映、進口和出口。除確定了電影審查程序,在“第三章審查標準”中規定了電影中被禁止的內容,比如危害國家利益、煽動民族分裂、泄露國家利益、宣傳淫穢暴力等,可是卻往往在具體禁止內容的每一條最後加上一個模糊的條款,比如“第九條電影片禁止載有下列內容”的最後一款是“(九)有國家規定禁止的其它內容的”;“第十條電影片中個別情節、語言或畫面有下列內容的,應當刪剪、修改”的最後一款是“(六)其它應當刪剪、修改的內容”,甚至“第二??廣播電影電視部在特殊情況下可以作出停止放映或者刪剪的決定”。諸如這些“其它、應當、特殊情況”等不具有可操作性的辭彙在電影審查規定中出現,可以說為電影審查籠罩上了濃重的行政命令和家長式管理的意味。而且,從公布的主管電影審查的委員名單 中,可以看出他們絕大部分是廣電部和中宣部的官員,而直接參與電影生產的編劇、導演(如於彥夫、李前寬、楊在葆等也都是拍攝主旋律影片的導演)幾乎沒有,這樣一個完全代表官方意味的“電影審查制度”不過是一種國家意識形態塑造的工具,而且因為其控制著電影放映的權力而成為鉗制中國電影創作的頸瓶。雖然“地下電影”絕大部分不涉及審查規定的禁止內容,但因為其漠視審查程序存在本身已經自毀在國內獲得放映權的前程。
不過,世紀之交,中國電影市場也發生了新的變化。一方面,中國的“藝術院線”已經悄然開始啟動。2001年10月份,北京紫禁城三聯影視發行公司在全國一些大中城市推出了一個叫“Avant Garde電影”(即先鋒、前衛、另類電影)的概念,在這些城市選擇幾個豪華電影院中的小廳(200座左右),放映一些“另類”的電影(第一部是王全安的《月蝕》),這樣對觀眾進行分層的作法,完全是出於市場的考慮,他們將定期舉辦導演、演員與觀眾見面會以及藝術影片展等活動,讓那些平日習慣去VCD超市裡淘片子的觀眾成為這裡的常客;另一方面,中國加入WTO之後將在三年內逐步放開允許外資建設、更新、擁有及經營電影院的所有權,允許有49%的外國股權參與合作經營錄像和錄音帶等視聽產品銷售業。這樣隨著院線制度的建立和進一步市場化,以及國家對於體制外電影的寬容,應該可以說會有更多的“地下電影”進入“地上”,固然不能保證它們曾經被禁演的身份和國外獲得大獎的歷史使其獲得票房的號召力,但至少為它們存在保有一份合法的“地上”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