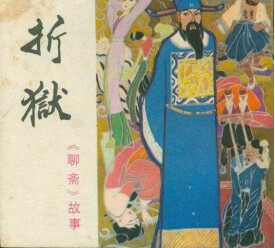共找到2條詞條名為折獄的結果 展開
- 漢語詞語
- 聊齋志異篇目
折獄
聊齋志異篇目
《折獄》是清代小說家蒲松齡創作的文言短篇小說。
邑之西崖庄,有賈某,被人殺於途;隔夜,其妻亦自經死。賈弟鳴於官。時浙江費公禕祉令淄,親詣驗之。見布袱裹銀五錢余,尚在腰中,知非為財也者。拘兩村鄰保,審質一過,殊少端緒,並未搒掠,釋散歸農;但命約地細察,十日一關白而已。逾半年,事漸懈。賈弟怨公仁柔,上堂屢聒。公怒曰:“汝既不能指名,欲我以桎梏加良民耶?”呵逐而出。賈弟無所伸訴,憤葬兄嫂。
一日,以逋賦故,逮數人至。內一人周成,懼責,上言錢糧措辦已足,即於腰中出銀袱,稟公驗視。公驗已,便問:“汝家何里?”答云:“某村。”又問:“去西崖幾里?”答云:“五六里。”“去年被殺賈某,系汝何人?”答云:“不識其人。”公勃然曰:“汝殺之,尚雲不識耶!”周力辨,不聽;嚴梏之,果伏其罪。先是,賈妻王氏,將詣姻家,慚無釵飾,聒夫使假於鄰。夫不肯。妻自假之,頗甚珍重。歸途,卸而裹諸袱,內袖中。既至家,探之已亡。不敢告夫,又無力償鄰,懊惱欲死。是日,周適拾之,知為賈妻所遺,窺賈他出,半夜逾垣,將執以求合。時溽暑,王氏卧庭中,周潛就淫之。王氏覺,大號。周急止之,留袱納釵。事已,婦囑曰:“后勿來,吾家男子惡,犯恐俱死:”周怒曰:“我挾勾欄數宿之資,寧一度可償耶?”婦慰之曰:“我非不願相交,渠常善病,不如從容以待其死。”周乃去,於是殺賈,夜詣婦曰:“今某已被人殺,請如所約。”婦聞大哭,周懼而逃,天明則婦死矣。公廉得情,以周抵罪。共服其神,而不知所以能察之故。公曰:“事無難辦,要在隨處留心耳。初驗屍時,見銀袱刺萬字文;周袱亦然,是出一手也。及詰之,又雲無舊,詞貌詭變,是以確知其真兇也。”
異史氏曰:“世之折獄者,非悠悠置之,則縲係數十人而狼藉之耳。堂上肉鼓吹,喧闐旁午,遂嚬蹙曰:‘我勞心民事也。’雲板三敲,則聲色並進,難決之詞,不復置念;專待升堂時,禍桑樹以烹老龜耳。嗚呼!民情何由得哉!余每曰:”智者不必仁,而仁者則必智。蓋用心苦則機關出也。’‘隨在留心’之言,可以教天下之宰民社者矣。”
邑人胡成,與馮安同里,世有郤。胡父子強,馮屈意交歡,胡終猜之。一日,共飲薄醉,頗頃肝膽。胡大言:“勿憂貧,百金之產不難致也。”馮以其家不豐,故嗤之,胡正色曰:“實相告:昨途遇大商,載厚裝來,我顛越於南山眢井中矣。”馮又笑之。時胡有妹夫鄭倫,托為說合田產,寄數百金於胡家,遂盡出以炫馮。馮信之。既散,陰以狀報邑。公拘胡對勘,胡言其實,問鄭及產主皆不訛。乃共驗諸眢井。一役縋下,則果有無首之屍在焉。胡大駭,莫可置辨,但稱冤苦。公怒,擊喙數十,曰:“確有證據,尚叫屈耶!”以死囚具禁制之。屍戒勿出,惟曉示諸村,使屍主投狀。
逾日,有婦人抱狀,自言為亡者妻,言:“夫何甲,揭數百金作貿易,被胡殺死。”公曰:“井有死人,恐未必即是汝夫。”婦執言甚堅。公乃命出屍於井,視之,果不妄。婦不敢近,卻立而號。公曰:“真犯已得,但骸軀未全。汝暫歸,待得死者首,即招報令其抵償。”遂自獄中喚胡出,呵曰:“明日不將頭至,當械折股!”役押去,終日而返。詰之,但有號泣。乃以梏具置前,作刑勢,卻又不刑,曰,“想汝當夜扛屍忙迫,不知墜落何處,奈何不細尋之?”胡哀祈容急覓。公乃問婦:“子女幾何?”答曰:“無。”問:“甲有何戚屬?”“但有堂叔一人。”慨然曰:“少年喪夫,伶仃如此,其何以為生矣?”婦乃哭,叩求憐憫。公曰:“殺人之罪已定,但得全屍,此案即結;結案后,速醮可也。汝少婦,勿復出入公門。”婦感泣,叩頭而下。公即票示里人,代覓其首。經宿,即有同村王五,報稱已獲。問驗既明,賞以千錢。喚甲叔至,曰:“大案已成;然人命重大,非積歲不能成結。侄既無出,少婦亦難存活,早令適人。此後亦無他務,但有上台檢駁,止須汝應身耳。”甲叔不肯,飛兩簽下;再辯,又一簽下。甲叔懼,應之而出。婦聞,詣謝公恩。公極意慰諭之。又諭:“有買婦者,當堂關白。”既下,即有投婚狀者,蓋即報人頭之王五也。公喚婦上,曰:“殺人之真犯,汝知之乎?”答曰:“胡成。”公曰:“非也。汝與王五乃真犯耳。”二人大駭,力辨冤枉。公曰:“我久知其情,所以遲遲而發者,恐有萬一之屈耳。屍未出井,何以確信為汝夫?蓋先知其死矣。且甲死猶衣敗絮,數百金何所自來?”又謂王五曰:“頭之所在,汝何知之熟也!所以如此其急者,意在速合耳。”兩人驚顏如土,不能強置一詞。並械之,果吐其實。蓋王五與婦私已久,謀殺其夫,而適值胡成之戲也。乃釋胡。馮以誣告,重笞,徒三年。事結,並未妄刑一人。
異史氏曰:“我夫子有仁愛名,即此一事,亦以見仁人之用心苦矣。方宰淄時,松才弱冠,過蒙器許,而駑鈍不才,竟以不舞之鶴為羊公辱。是我夫子有不哲之一事,則某實貽之也。悲夫!”
據《聊齋志異》鑄雪齋抄本
自經:自縊;上吊。
費公禕祉:費禕祉字支嶠,浙江鄞縣人,順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為淄川縣令。
鄰保:猶言鄰居、近鄰。《周禮·地官·遂人》:“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又《周禮·地官·大司徒》:“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
約地:指鄉約、地保之類的鄉中小吏。蒲松齡《代畢仲賀韋玉霄任五村鄉約序》,謂鄉約“脫有關白,則冠帶上公庭”。
仁柔:猶言心慈手軟,不夠果斷。
逋賦:拖欠賦稅。
錢糧:田賦所征錢和糧的合稱。清代則專指田賦稅款,糧食也折錢繳納。
銀袱:包裹銀錢的包袱。
何親:據二十四卷抄本,原作“何物”。
釵飾:婦女的首飾。釵,兩股笄。
留袱納釵:自己留下包袱,把釵飾給了王氏。納,支付。
廉:考察。情:指案情。
無舊:無舊交。
詞貌詭變:言詞搪塞,神態異常。
折獄:斷案。折,判斷。獄,訟案。
悠悠置之:謂長期擱置,不加處理。悠悠,安閑自在,此謂漫不經心。
縲(léi 雷)系:囚禁。狼藉之:把他們折磨得不成樣子。狼藉,折磨、作踐。
內鼓吹:喻拷打犯人的聲響。鼓吹,擊鼓奏樂。后蜀李匡遠為鹽亭令,一天不對犯人施刑,就心中不樂。聞答撻之聲,曰:“此我一部肉鼓吹。”見《外史檮杌》。
喧闐旁午:哄鬧。喧闐,哄鬧聲。旁午,交錯,紛繁。語見《漢書·霍光傳》顏師古注,“一縱一橫為旁午,猶言交橫也。”
嚬蹙:皺眉蹙容!謂裝出一副憂心的樣子。
雲板三敲:此指打點退堂。雲板,報時報事之器,俗謂之“點”。板形刻作雲朵狀,故名。舊時官署或權貴之家皆擊雲板作為報事的信號。
難決之詞:難以判斷的官司。詞,詞訟,訴訟。
禍桑樹以烹老龜:比喻胡亂判案,濫施刑罰使眾多無辜者牽累受害。傳說三國時,吳國永康有人入山捉到一隻大龜,以船載歸,要獻給吳王孫權,夜間系舟於大桑樹。舟人聽見大龜說:我既被捉,將被烹煮,但是燒盡南山之柴,也煮我不爛。桑樹說:諸葛恪見識廣博,假使用我們桑樹去燒你,你怎麼辦呢?孫權得龜,焚柴百車,龜依然如故。諸葛恪獻策,砍桑樹燒煮,果然把龜煮爛。出自《異苑》,見《太平廣記》卷四六八《永康人》。這裡以桑樹與老龜比喻訴訟的兩造。
機關:計謀或計策。此指弄清案情的線索和辦法。
宰民社者:理民的地方官。民社,人民與社稷。
世有郤,世代不和睦。郤,通“隙”,嫌隙。
猜:猜疑;不信任。
大言:說大話。
大商,據二十四卷抄本,原作“大高”。
顛越:隕墜。眢(yuān 淵)井:無水的井;枯井。
對勘:查對核實。
擊喙(huì會):掌嘴,打嘴巴。
死囚具:為死刑囚犯所用的刑具。
有婦人抱狀:有個婦人抱持狀紙,親詣公堂。按清制,婦女不宜出入公門,有訴訟之事,得委派親屬或僕人代替。此婦女抱狀自至,甚為蹊蹺。
招報:公開判決。招,揭示其罪。報,斷獄,判決。
械折(shé舌)股:夾斷你的腿。械,刑具,此指夾棍之類的刑械。
票示,持官牌傳令。票,舊時稱官牌為“票”,見《正字通》。
簽:舊時官吏審案時,公案上置簽筒,用刑時就拔簽擲地,衙役則憑簽施刑。
既下:據二十四卷抄本,原作“即下”。
“異史氏曰”一段:據二十四卷抄本訃,底本闕。
我夫子:指費禕祉。夫子,舊時對老師的專稱。
松:蒲松齡自稱。弱冠:古時男子二十歲成人,初加冠,因體弱未壯,故你”弱冠”;後來也以稱一般少年。
器許:器重和讚許。
競以不舞之鶴為羊公辱:意謂自己無能,辜負了賞識者的厚望。《世說新語·排調》:“昔羊叔子有鶴善舞,嘗向客稱之。客試使驅來,氃氋而不肯舞。”蒲松齡以自己科學受挫,有負責禕祉的器許,故有此喻。
不哲:不明智。
貽:留給。
淄川縣的西崖庄,有一個姓賈的被人殺死在路上。隔了一夜,他的妻子也上吊死了。
賈某的弟弟告到了縣官那裡。當時浙江的費禕祉在淄川做縣令,親自去驗屍。他看到死者布包袱里包著五錢多銀子還在腰中,知道不是圖財害命。傳來兩村的鄰居審問了一遍,沒有什麼頭緒,也沒有責打他們,就把他們釋放回去種地了。只是命鄉約地保仔細偵察,十天向他彙報一次情況。
過了半年,事情漸漸鬆懈下來。賈某的弟弟埋怨費縣令心慈手軟,多次上公堂吵鬧。費縣令生氣地說:“你既然不能指出誰是兇手,想叫我用酷刑拷打良民嗎?”呵斥一頓,把他趕了出去。賈某的弟弟無處伸訴冤情,氣憤地把哥哥嫂子埋葬了。
一天,因為逃稅的緣故,縣裡逮來幾個人。其中有一個叫周成的害怕責打,告訴縣令說錢糧已經籌辦足了。就從腰裡取出銀袱,交給費縣令驗視。費縣令查看完了,便問他:“你家住在哪裡?”回答說:“某村。”又問:“離西崖村幾里路?”回答說:“五六里。”“去年被殺的賈某是你什麼人?”回答說:“我不認識那個人。”費縣令勃然大怒說:“你殺了他,還說不認識?”周成竭力辯解,費縣令不聽,嚴刑拷打,他果然認罪了。
原來,賈某的妻子王氏,要走親戚家,沒有首飾覺得羞愧,鬧著叫丈夫到鄰居家去借。丈夫不肯,妻子自己去借了。她非常珍重,回來的路上,從頭上卸下首飾包在包袱里,塞進袖筒中。等回到家,伸手一摸,首飾沒有了。王氏不敢告訴丈夫,又沒有辦法償還鄰居,懊惱得要死。這天,周成正巧拾到了首飾,知道是賈某的妻子丟的。乘賈某外出以後,周成半夜從牆上爬過去,想以首飾要挾和賈妻苟合。當時正是熱天,王氏睡在院子里,周成悄悄走近她將她強姦。王氏醒覺,大聲喊叫。周成急忙制止,留下包袱把首飾給了她。事情辦完了,王氏囑咐說:“以後不要來了,我家男人很兇,讓他知道了,你我都得死!”周成怒沖沖地說:“我給你的東西夠到妓院嫖好幾宿的!難道只干這一次就能抵償了嗎?”王氏安慰他說:“我並不是不願與你相交,我男人常常鬧病,不如慢慢等他病死就行了。”周成走了,於是就殺了賈某;夜裡又到王氏家說:“現在你男人已經被人殺了,請你按說的辦!”王氏聽了大哭起來。周成害怕驚動鄰居,逃走了。天明后王氏也死了。費縣令查明實情,將周成抵罪。
大家都佩服費縣令斷案神明,但不知所以能察明案情的緣故。費縣令說;“事情並不難辦,只是要隨時隨地留心罷了。當初驗屍的時候,我見包銀子的包袱綉著萬字文,周成的包袱也一樣,是出自一人之手。等審問他時,他又說以前不認識賈某,言詞搪塞。神態異常,所以知道他就是真正的兇手了。”
異史氏說:“世上斷案的官,並非都漫不經心不加處理長期擱置,有的官囚禁了數十人而且把他們折磨得不成樣子。公堂上拷打犯人像擊鼓聲,哄鬧的聲音交錯紛繁,於是皺著眉裝著一副憂心的樣子說:‘我對民間的事太勞心了。等到打了退堂鼓,回去就吃喝玩樂,對難以判斷的官司,不再放在心上;專等升堂時,無論原告被告一律不問青紅皂白各打幾十大板,就像用桑樹煮老龜一樣,兩邊遭了禍罷了。唉!民間怨情誰來管呢!我常常說;‘聰明人不必講仁,而講仁義的人必須聰明;只要是用心良苦那弄清楚案情的線索辦法也就出來了。”隨時留心的話,可以教天下的縣令等官員怎樣治理好百姓管理好國家啊。”
淄川縣有個叫胡成的,與馮安同一個村子,兩家世代不和。胡家父子很霸道,馮安曲意同他交往,胡家卻終不信任他。
一天,他們一塊喝酒,略有醉意時,兩人說了些心裡話。胡成吹噓:“不要憂愁貧窮,百把兩銀子的財產不難弄到手!”馮安認為胡成並不富裕,是在吹牛,故意譏笑他。胡成一本正經地說:“實話告訴你,我昨天在路上遇見一個大商人,車上裝著很多財物,我把他扔進南山的枯井裡了。”馮安又嘲笑他。當時,胡成有個妹夫叫鄭倫,托胡成說合購買田產,在胡成家寄存了好幾百兩銀子。這時胡成就全部拿出來在馮安面前炫耀,馮安相信了。散席以後,馮安偷偷地寫了狀紙告到縣衙。費縣令拘捕了胡成對質審問,胡成說了實情;費縣令又問鄭倫和產主,都說是這樣。於是就一塊去察看南山枯井。一個衙役用繩子吊著下去,竟發現井中果然有一具無頭屍體。胡成大吃一驚,無法辯白,只能大喊冤苦。費縣令生了氣,命人打嘴幾十下,說:“證據確鑿,還叫冤屈!”用死刑犯的刑具將他鎖了起來。卻不讓弄出屍體來,只是告知各村,讓屍主呈報狀子。
過了一天,有個婦人持狀紙來到公堂,聲稱自己是死者的妻子,說:“我丈夫何甲,帶著數百兩銀子出門做買賣,被胡成殺死。”費縣令說:“井中確實有死人,但未必就是你丈夫。”婦人堅持說是。費縣令就命把屍體弄出井來,眾人一看,果然是婦人的丈夫。婦人不敢到跟前,站在遠處號哭。費縣令說:“真正的兇手已經抓住了,但屍體不完整。你暫時回去,等找到死者的頭顱,立即公開判決,讓胡成償命。”接著把胡成從獄中喚出來,呵斥說:“明天不將頭顱交出來,就打斷你的腿!”叫衙役押他出去,找了一天回來,追問他,他只是嚎哭。費縣令讓衙役把刑具扔在他面前,擺出要用刑的樣子,卻又不動刑,說:“想必是你那天夜裡扛著屍體慌忙急迫,不知將頭掉到什麼地方了。怎麼不仔細尋找呢?”胡成哀求縣官准許他再找。縣令問婦人:“你有幾個子女?”回答說:“沒有。”縣令問:“何甲有什麼親屬?”“只有一個堂叔。”縣令感慨地說:“年輕輕就死了丈夫,這樣孤苦憐仃以後怎麼生活呢?”婦人又哭起來,給縣令磕頭請求憐憫。縣令說:“殺人的罪已經定了。只要尋找全屍,此案就完結了。結案后,你趕快改嫁。你是一個年輕少婦,不要再出入公門。”婦人感動得哭了,叩頭下了公堂。縣令立即傳令村裡的人,替官府尋找人頭。過了一宿,就有同村的王五,報稱已經找到了。縣令審問查驗清楚,賞給他一千錢。又把何甲的堂叔傳到公堂,說:“大案已經查清,但是人命重大,不到一年不能結案。你侄兒既然沒有子女,一個年輕輕的寡婦也難以生活,讓她早點嫁人吧。以後也沒有別的事,只有上司來複核時,你須出面應聲。”何甲的堂叔不肯,費公從堂上扔下兩根動刑的簽子;再申辯,又扔下一簽。甲叔害怕了,只好答應後退了下去。婦人聽到這個消息,到公堂謝恩。費縣令極力安慰她,又傳令:“有誰願買這婦人,當堂報告。”婦人下堂后,就有一個來投婚狀的人,原來就是找到人頭的王五。縣令傳喚婦人上堂,說:“真正的殺人兇手,你知道是誰嗎?”婦人回答說:“胡成。”縣令說:“不是。你與王五才是真正的兇犯!”二人大驚,極力辯白,叫喊冤枉。縣令說:“我早已知道其中詳情!之所以一直到現在才說明,是怕萬一屈枉了好人!屍體沒有弄出枯井,你怎麼能確信就是你丈夫?這是因為在此以前你就知道你丈夫死在井裡了!況且何甲死的時候還穿著破爛衣服,數百兩銀子是從什麼地方弄來的?”又對王五說:“人頭在哪裡,你怎麼知道得那樣清楚?你之所以這樣急迫,是打算早點娶到這婦人罷了!”兩人嚇得面如黃土,一句話也說不出來。費縣令用刑拷問二人,果然吐露了真情。原來王五與婦人私通已經很久,兩人合謀殺了她的丈夫。恰巧碰上胡成開玩笑說殺了人,二人才想嫁禍於胡成。費縣令於是釋放了胡成。馮安以誣告罪,打了頓板子,判了三年勞役。直到案子結束,費縣令沒有對一個人亂動刑罰。
異史氏說:“我老師費公有仁愛的美名,僅這一件事,也就可以看出愛民的用心多麼誠摯儘力。他剛到淄川任縣令時,我當時還是個少年,承蒙他器重和讚許,而我愚鈍不才,竟在科舉受挫,辜負了老師的厚望,正如羊叔子有一隻鶴善於跳舞,在客人面前一試,偏偏不跳使羊叔子丟臉一樣。我的科舉不中正是我老師器重我不明智的一方面,看來這正是我留給老師的。真令人悲傷啊!”
蒲松齡(1640-1715),清代文學家,字留仙,一字劍臣,別號柳泉居士,世稱聊齋先生,山東淄川(今山東淄博市)人。蒲松齡一生熱衷功名,醉心科舉,但他除了十九歲時應童子試曾連續考中縣、府、道三個第一,補博士弟子員外,以後屢受挫折,一直鬱郁不得志。他一面教書,一面應考了四十年,到七十一歲時才援例出貢,補了個歲貢生,四年後便死去了。一生中的坎坷遭遇使蒲松齡對當時政治的黑暗和科舉的弊端有了一定的認識;生活的貧困使他對廣大勞動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有了一定的了解和體會。因此,他以自己的切身感受寫了不少著作,今存除《聊齋志異》外,還有《聊齋文集》和《詩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