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特雷弗
威廉·特雷弗
威廉·特雷弗,愛爾蘭文學界元老,當代短篇小說大師,素有“愛爾蘭的契訶夫”之稱。

威廉·特雷弗
他的家庭具有英、愛雙重背景,信仰新教。因父在銀行任職,所以特雷弗有一個遷移不定的童年,先後在13所不同的學校讀書。動蕩的生活,與眾不同的信仰,使他從小時候起就有一個作家的獨特視角。
2004年,76歲的特雷弗為世人呈上了其新作《第三者》,收錄了他最近的十二部短篇小說,並被文壇盛讚為“再度展現大師功力的著作”。
目前他已經出版長篇小說29部,短篇小說集16部,獲重大獎項數十個,對英語文學產生了很大影響。
2016年11月20日,星期天,威廉·特雷弗在英國薩默塞特郡去世,享年88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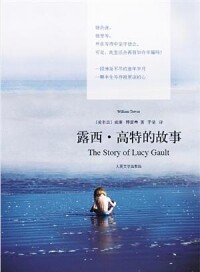
威廉·特雷弗 《露西·高特的故事》
故事構建得幾近完美,堪比契訶夫——兩者間比較是不可避免的——他們總是給讀者留有沉思的空間。
——安妮塔·布魯克納(布克獎得主)
如同倫勃朗,特雷弗總是熱切而仁慈地凝望著他筆下的人物……他對人性的理解是精確的……他的故事無不體現著一種平靜的睿智。
——《泰晤士報》
他的第一部重要作品《老校友》,曾獲1964年霍桑頓獎。一群老校友委員會成員在推選下一任會長過程中勾心鬥角,互相猜忌,並以回憶的形式展現了這群老校友當年在學校時的矛盾和競爭。儘管年事已高,但依然對當年所受的屈辱無法釋懷。既要應付來自外界的壓力,防備別人的進攻,又要面對自己日益衰老的身體和病痛,他們內心極其孤獨和悲涼。小說提出這樣一個主題——人們該如何面對自己的不幸?對於成功和失敗該抱什麼樣的態度?怎樣才能在現代社會中保護自己?
儘管特雷弗的作品中有許多地道的英國人物,然而他偏愛的主題還是愛爾蘭和愛爾蘭人。同喬伊斯一樣,他選擇了一種自我流放,流離於自己的祖國之外進行創作。這對於特雷弗來說,無論從時間上還是距離上,他都能以旁觀者的冷靜審視祖國的文化,揭示種族、階級和宗教等人為的障礙如何影響著人們的教育、愛情、婚姻等方方面面。其中最具有典型意義的作品要數《命運的嘲弄》和《花園的寂靜》。
《命運的嘲弄》是一部探討歷史的重負對愛爾蘭人生活的影響的作品。在恢弘的歷史場面上將幾個不同時期的情節融合在一起。愛爾蘭的昆頓家族同英國伍德庫姆家族長期有聯姻的傳統。19世紀初,安娜·伍德庫姆嫁到昆頓家在科克郡的基爾尼莊園。飢荒席捲愛爾蘭,安娜試圖救濟災民,並警醒家人和英國殖民官員留意民眾的困頓狀況。結果激怒了整個家族,被剝奪了繼承權。基爾尼莊園的以後幾代人仍然沿襲迎娶英國新娘的傳統。小說切換到愛爾蘭歷史上另一個創傷時代——英愛戰爭。威廉·昆頓和他的英國妻子伊芙有著田園詩般的婚姻生活,有三個孩子。他們支持公益事業,並在英愛戰爭中傾向馬克·科林斯,因此在自己的階級圈子、宗教圈子中被孤立起來。他們的政治活動最終導致基爾尼莊園被縱火焚毀。威廉、兩個女兒以及許多仆佣被燒死,伊芙和兒子威利退居科克市的一棟小屋。伊芙無力面對喪夫失女之痛,日漸頹廢,酗酒澆愁。長大后的威利同英國的表親瑪麗安娜之間有了愛情。可是懷了孕的瑪麗安娜來到敗落的基爾尼莊園卻發現威利神秘失蹤。瑪麗安娜在威利的姑姑和一名還俗的神甫幫助下,獨自撫養著女兒伊梅爾達。年老時他們終於破鏡重圓,原來威利因報復而謀殺了下縱火令燒毀基爾尼莊園的傢伙,逃離了愛爾蘭。昆頓家族衰微的過程以伊梅爾達不堪這一代代的精神重負以致神志失常而告終。
特雷弗的歷史觀,不管是個人的還是政治的,都是獨特的。儘管作品中提到了英國政府在其統治期間對愛爾蘭的不聞不問,甚至動用武力,他拒絕將一切歸罪於歷史上英國的不當統治。他一直在探討歷史對生者的折磨,一直暗示人類有義務掙脫回憶的絞索,超越這種不幸,戰勝這種不幸,為自己的下一代塑造一個全新的未來。
《花園的靜寂》某種意義上是《命運的嘲弄》的繼續,仍然以大宅為背景,嘗試在過去與現在之間達成一種妥協。這部作品特彆強調“暴力”那一石千浪的後繼性影響,在控訴愛爾蘭歷史對人民的消極影響方面毫不留情。
在反思愛爾蘭的歷史與文化的同時,他的作品還將注意力放到了女性所面臨的問題上。在《命運的嘲弄》中,描寫受到傷害的女性時——失去繼承權的安娜、酗酒的伊芙、被遺棄的瑪麗安娜、精神錯亂的伊梅爾達——筆觸充滿同情。小說中丈夫們沒有一個比他們的英國妻子更睿智、更堅強,她們都是男性以崇高的名義所作決定的犧牲品。丈夫們要麼不願採取行動,要麼無力採取行動,要麼採取不明智的行動。而《花園的寂靜》中只有女性的形象是有活力,有勇氣而充滿理性的,頑強地抗衡著一個家族無法逆轉的頹勢。在歷史與男性的坐標軸上,特雷弗筆下的女性以平行甚至超越男性的波形線橫穿歷史。
特雷弗很擅長描繪女性生活細節和她們內心的微妙活動。他的早期作品《奧尼爾旅社的埃克道夫太太》、《格梅茲小姐和教友們》、《孤獨的伊麗莎白》都是表現女性題材,刻畫了女性孤獨的心理狀態。《孤獨的伊麗莎白》尤其受到好評。伊麗莎白是一位帶著三個女兒的離婚婦女,住院時結識了其他三位境遇相似的婦女。在交往中伊麗莎白看到了自身可悲的命運,也感受到人生在世徹底的孤獨,誰也無法進入別人複雜的內心世界。在他的短篇小說中女性的形象更多。《浪漫舞廳》、《阿特拉克塔》、《碰運氣》等,女性形象幾乎涵蓋了社會的方方面面,形形色色,但心底那真實的孤獨始終揮之不去。
女性題材只是特雷弗藉以立體反映愛爾蘭社會,傳達其本人人文思想的一個手段,這與其他題材的創作是齊頭並進的,例如宗教題材。在一個宗教可以決定社會安寧以及文化發展的國度,如果從幼年起信仰就非屬於主流宗教,那麼這樣一個作家會如何在作品中體現自己的宗教觀呢?
較近的短篇小說集《山裡的單身漢》中有一篇夢境般的故事《聖母的禮物》。虔誠的邁克一生三次看到聖母的出現,幻覺由此決定了他的人生。18歲時受聖母的指引突然離開父親的農場,進入一家修道院;35歲時受到聖母的指引又突然離開修道院,在高山峭壁下“找到了心靈的寧靜”;幾年後聖母最後一次顯靈,指引他回歸故里。對這一切毫不置疑的邁克徒步穿越愛爾蘭的村村寨寨,就像一條流浪的狗終於在消失幾十年後又回到了故鄉。儘管表面上看小說沒有絲毫的諷刺意味,然而很難相信特雷弗希望讀者與邁克一樣對聖母的顯靈信以為真。邁克是一個完全憑直覺支配而缺少判斷力的人。他的幻覺是真的嗎?這位孤獨的人一生是不是都白費了?超越宗教之外來看,宗教中的降靈與欺騙是不是一回事?特雷弗對此未著一言,轉而描寫兒子失而復得后邁克父母洋溢的快樂。
其他,如本集中的《法衣》里迷惘的新教牧師,感到不僅與天主教的愛爾蘭失去聯繫,而且感到同整個世界失去了聯繫。《死於耶路撒冷》,探討宗教在世俗世界中的地位,對天主教和新教人物予以同樣富有同情心的描寫。從其作品來看,特雷弗似乎沒有明確的宗教觀,也可能有意在作品中隱去自己的觀點。他更多的表現為宗教上的懷疑論者,在他的作品中很少感覺到上帝那種操縱一切的力量。
特雷弗作品中的人物都被賦予自然精確的描寫——具體的時間、具體的地點,似乎每個人的故事就像是一首代代相傳的歌謠,具有某種原型。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他筆下的人物類型之多令人震驚。在特雷弗的短篇中,人物與地點之間有一種神秘的聯繫,似乎一個民族的靈魂是他們所居之上的土地塑造的。尤其在以偏遠的鄉村為背景的小說中,個人似乎完全是他們所出生的狹小世界的產物,甚至失去意志的自由,失去別處謀生的決心。短篇小說集《山裡的單身漢》中的題名故事十分突出地體現了作者的這一思想。
該故事講述的是一個29歲的兒子鮑利,為了取悅寡居的母親,接受了令自己生畏的那一點地產,回到地處偏僻的小農場。現在的愛爾蘭婦女們寧願到加油站或化肥廠打工也不願嫁給他們這樣的單身漢,過令靈魂麻木的艱辛生活。就他這樣的愛爾蘭人來說,對先主們的認知卻又是他們所不能放棄的。鮑利是英雄?是傻瓜?抑或僅僅是溫順的兒子?如果說他代表了愛爾蘭的過去,模稜兩可;如果說他代表愛爾蘭的未來,這絕不可能,單身漢沒有後裔,他們所代表的一切將不再繼續。這樣的前景如同古代愛爾蘭的民謠,內容已經朽去,形式尚且存在,卻不會延續。
受喬伊斯的影響,特雷弗的許多作品注重象徵性細節描寫,放棄戲劇性編排;幽思,懷舊,氛圍十足又往往含而不露,並使用喬伊斯小說中典型的“淡出”式結尾。例如《浪漫舞廳》、《山裡的單身漢》、《家庭罪惡》等。總的說來這種影響是正面有益的,但有時這種結尾給人的感覺是缺少某種活力。
特雷弗還創作其他類型的文學作品。例如《影集里的風光》(劇本)、《茱麗葉的故事》(兒童文學)等。根據《老校友》改編的舞台劇於1971年上演,隨後他又根據自己的短篇小說創作了許多成功的舞台劇和電視劇,幾乎每年都有一部舞台劇或電視劇在倫敦上演或播出。
特雷弗目睹了愛爾蘭近一個世紀的風風雨雨。鄉愁的源頭滋養著80年漂泊的流程,創造了愛爾蘭文學的又一輝煌,他不愧是愛爾蘭文學園中的月桂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