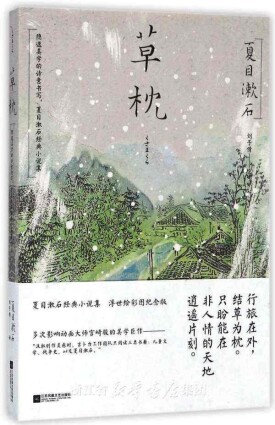草枕
日本夏目漱石創作的散文小說
《草枕》是日本作家夏目漱石創作的中篇散文體小說。作品講述一位青年畫工為逃避現實世界,遠離鬧市隱居山村,追尋“非人情”美感而經歷的一段旅程。
作者把《草枕》的主要舞台設在山中溫泉即那古井溫泉,並把它描繪成脫離塵俗的“非人情”的天地,如繞過好幾道險峻的山道才能抵達的目的地,山道旁邊散開著油菜花、蒲公英、山櫻花,沒有船無法到達的地方等等。這樣的外部格局的設定,如同桃花源與世隔絕的世界,即夏目漱石的“非人情”天地。同時,作者還把“非人情”天地中所有登場人物都塑造成近似於“非人情”的人物形象。譬如,山崖茶館的老太太、女主人公那美、觀海寺的大轍法師、理髮館的師傅等等。作者如此處心積慮地設定與布置,其目的是把畫家的“非人情”之旅描繪成“脫離世俗煩惱的超然心境”(《草枕》)的旅行。夏目漱石為了達到此目的,使用的最主要的手段之一就是引用陶淵明的“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和王維的“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的詩境。
該小說雖然以敘事為主,但意蘊深刻,對於研究日本唯美主義文學特色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草枕》以畫家本人,即以第一人稱的口吻敘述自己的旅行見聞。主人公是一位畫家,他去九洲旅行旅行,他厭倦了充滿私情雜欲、是是非非的現實生活,背起畫具,去山中尋求清新靜謐的理想世界:道路的左前方聳立著一座山峰,像倒扣著的鐵桶。山間煙霧沆盪,依稀難辨。前邊有一座禿山,峭拔凌厲,直逼眉梢。光禿的山脊,像巨人用斧頭劈開來一般,銳利的斷面一直插進谷底。可謂山路險峻,舉步維艱。
在山那方的那古井溫泉勝地,畫家見到了屢有耳聞的脫俗的女子那美,通過那美又進一步接觸到了那古井的山山水水和融於自然山水中的僧侶村人。所見所聞無一不清新超俗,好似淡出世外。房東、姑娘、女傭、男僕,都不知不覺退避了,只剩下畫家一人以及古井溫泉的清新與靜謐。說他們退避,並非退向普通的地方,是退到了紅霞之國,或白雲之國。“紅霞之國”、“白雲之國”,就是與現實世界的“普通地方”相區別的不同之地。
夏目漱石的創作意圖與當時的文壇傾向有關。當時文壇主流文學是自然主義流派。由於受法國左拉的自然主義理論影響,日本逐漸興起自然主義文學思潮。自然主義文學追求的是“真”而排除了“美”、排除空想,最後陷入描寫卑小人物,暴露人性的醜惡心理一面的帶有陰鬱色彩的負面傾向。正是對於這種文學主張的不滿,夏目漱石提出了“非人情”理論,追求超脫世俗的美,創作了《草枕》。
夏目漱石在《我的草枕》中寫道:他只想表達一種感覺,只要在作者心中留下一個美好的感覺就行了。因此,《草枕》這部小說情節簡單,沒有事件的發展過程。該作品可以說是夏目漱石反擊自然主義文學之作。
當時,夏目漱石受到夫妻問題、家族間題、健康問題、經濟問題等諸多問題的困擾,他無法像陶淵明一樣,身處現實世界而忘掉“世俗的煩惱”,渴求憑藉《草枕》這部作品,哪怕是短暫的時間,也要在陶淵明的世界里徘徊。通過《草枕》,他明確表達了自己哪怕是暫時的也要力爭從現實痛苦中擺脫出來的心境。
該小說是根據作者在熊本的一段經歷為題材而創作的。明治30年(1927年)末至第2年正月,他與友人山川信次郎一同暫住過熊本縣玉石郡玉水村的小天溫泉。
夏目漱石的小說《草枕》最初於明治39年(1906年)發表在雜誌《新小說》上。當時他似乎受到俳句雜誌《杜鵑》(夏目漱石几年以前曾在該雜誌上發表過成名作《我是貓》)的影響,所以,《草枕》一發表,就有許多人指出,這是一部俳句性小說。“草枕”一詞在歌中意為“旅行”,所以,漱石以“草枕”為題目,意在描寫主人公的旅行過程。
“我”
“我”,30多歲,是一位畫家。“我”不急於趕路,腳步散漫在彎彎曲曲的羊腸小道上,原本打算到那古井寫生,卻一路悠閑地觀察周邊之景,只是停留在心中思考作畫,並未落筆;並且認為美在“餘裕”,故閑靜的春天、自由自在的海水、安閑的木瓜花、悠閑鳴叫的鴿子等自然之景都是“我”所喜歡的。而像雲雀那樣急促地鳴叫,把周圍的空氣變得難以忍受的“非餘裕”則是“我”想避開的。
那美
那美曾一度離開山中嫁往都市,卻以失敗告終,再度返回山裡。那美戀愛生活中遇到兩個男人,一個是她在京都上學時認識的,另一個是當地城裡的財主。她一心想嫁給那位京都的公子,父母卻硬逼著她嫁給那家財主。這財主是因她長得標緻才看重她,兩人總是合不來,後來那財主的銀行倒閉了,她便離開丈夫回到了娘家。村裡人卻都說她心狠,無情無義。
《草枕》主題思想:以“非人情”的心境去觀察審美對象,思考人世。
作者在作品的第一章節中曾這樣寫道:“誠然,作為人世上的一分子,儘管十分喜愛,也不會長久置身於非人情的環境之中。淵明不可能一年到頭都盯著南山瞧個沒完,王維也不願意在竹林中連蚊帳也不掛一直睡下去。‘我’當然也是如此。”由此可見,作者在《草枕》中所要宣揚的,並不是生活上的避世隱居,而是心靈上的超脫淡薄。
《草枕》的主人公為了忘卻世俗的煩惱來到山中溫泉旅行,因為作者一開始就意識到在這個塵世間並不存在“非人情”的天地,因此,特意來到人煙稀少脫離塵世的山中,避開都市的煩惱和情感糾葛,求得精神上的一時解脫。畫家的旅途就像陶淵明和王維的詩歌里所描繪出來的詩境一樣,切實體現了作者“直接從大自然中吸收,即使是短暫的也要盡情地徘徊在非人情天地的真摯的願望”。
夏目漱石雖然從漢詩創作中積極地尋求“非人情”天地,並迫切地期望要在其中得到精神上的解脫,但即使是在可以寄託自己精神世界的漢詩世界里,也存在因自己不能隨心所欲的痛苦而煩惱的情形。夏目漱石標榜的“非人情”之旅是短暫的、一時的,它不會維持很長時間,最終還是要回到現實世界里去。《草枕》的主人公在小說的結尾部分,與女主人公那美一起乘船下河的場面,就是返回現實世界的場面。不管主人公在山中那古井溫泉的所見所聞以及所經歷的事情多麼的“非人情”,那隻不過是漫長而痛苦的人生旅程中短暫的解脫而已。既然生在煩惱甚多的塵世間,就永遠不可能擺脫掉世俗的煩惱。
現實世界充滿煩悶,難居卻又不可搬遷。此時,藝術之士的使命應運而生,他們創作的詩畫正是為世人排憂解悶、使世界變得嫻靜愉快的途徑。確切地說,作者認為藝術世界是非人情的世界。
“非人情”有兩層涵義:第一,在藝術鑒賞中要站在第三者的立場上細心觀察人世,將自己的利害束之高閣,從而創造或欣賞美。保持這樣的審美心態,還需做到物我合一的境界。第二,“非人情”是相對“人情”而言的。在《草枕》中,漱石對輪船、火車、權利、義務、道德、禮義等感到膩煩,認為西洋詩充斥同情、愛、正義、自由、金錢交易等內容,批判西洋詩這種以吟詠人情為根本的庸俗性質。“非人情”排除人情與道德的煩惱,最終指向自然之美。
在《草枕》中,畫家喜歡呆在寧靜的山村裡,認為“能夠這樣一直呆下去的是幸福的人。在東京要是這般呆著,立即就會被電車軋死。即使不被電車軋死,也會被警察趕走。城市這種地方,總把太平當乞丐,總把賊的頭目和偵探付高薪。”這與其說是對東京的諷刺,不如說是對與20世紀的東京相接的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一種反抗與譴責。用《草枕》中的一句話來總結——“醒悟和迷惘雖然時常爭吵不休,卻又能共處於一室”。這種矛盾對立又共存的道理,就如世界和而不同,亦能呈現精彩與美妙。
作者繼承了日本人傳統的悲劇審美趣味,弘揚了日本民族關於“和”的文化精髓;又在此基礎上有所創新,提出“餘裕”“非人情”“則天去私”等獨樹一幟、頗具個人特色的美學思想,宛如夏夜耀眼的星辰,綻放睿智之光。儘管作者的思想有一些模糊和矛盾之處,從而遭到一些質疑或非議,但正所謂瑕不掩瑜。這些瑕疵不足以掩蓋作者在日本美學史上所作出的貢獻。
藝術特色
非人情美學
“非人情”是一種超越道德或人情的境界,是帶有超脫世俗的出世的境地,也可以理解為一種藝術審美世界。夏目漱石在《草枕》中對“非人情”理論作了具體實踐。該小說的結論在文本最後一段話上。起初女主人公“那美”請畫家給她作畫,當時畫家無法創作。不久,當他們去車站送行時,那美與即將離別的前夫告別,文本中寫到:“那美姑娘茫然地目送著賓士的火車,她那茫然的神情里奇妙地浮現著一種從前未曾見到的憐憫之情。‘有啦,有啦,有了這副表情就能作畫啦!’‘我’拍拍那美姑娘的肩頭小聲說。‘我’胸中的畫面在這一剎那間完成了。”可見,作者將藝術成立的條件小說化了。
通讀《草枕》文本,可以發現作為出場人物的畫家始終沒有實際作出一幅畫來,只是傾注於“觀察”並加之思考。其實從小說開頭部分就可看出畫家坦言自己實際是不畫出畫的畫家,而是用“觀察”代替了實際的繪畫創作。而且,這種觀察具有雙重性。即包括畫家所要描繪的主體,以及畫家所要描繪的意圖,兩者缺一不可。“因此,不論是天然,還是人事,在眾俗辟易而難於接近的地方,藝術家發現了無數的琳琅,認識了無上的寶璐。世俗名之曰美化。其實並不是什麼美化,燦爛的光彩自古赫然存在於現象的世界。”這裡談到的“現象的世界”即畫家所要描繪的主體。
又如文本中敘述到:“倘若由此再進一步,便可將‘我’所感覺的物象,溶進‘我’所感到的情趣,在畫布上淋漓揮灑,使其栩栩如生。此種藝術家的意圖,就是將特別的感興寄寓於自己捕捉的森羅萬象之內。”這裡就強調了具備畫家所要描繪的意圖。
而文本結尾處,畫家正是在女主人公那美臉上找到了“悲憫”,他胸中的那幅畫才得以完成。其實,畫家一直想創作能表達自己的心情的畫。而那美表情中流露出的“悲憫”,不僅是她的感情,而且也應該是畫家自身的心情。即當兩者都融合為一體,具有雙重性時,畫家所要描繪的圖畫就成立了。
作者想創作的圖畫流露出的心境,文中有揭示:“經過反覆考慮,終於想到了,在這多種情緒中忘卻了‘哀憐’二字,‘哀憐’是神所不知而又最接近神的人之常情”。
“善難行,德難施,節操不易守,為義而捨命太可惜。要是決心實行這些事,不管對誰來說,都是痛苦的。要敢於冒犯這種痛苦,內心就必須隱含著戰勝痛苦的歡愉。所謂畫,所謂詩,所謂戲劇,都是蘊蓄於此種悲酸之中的快感的別名,了解其中意趣,方能使吾人之作變得壯烈,變得嫻雅;方能戰勝一切困苦,方能將肉體的苦痛置之度外,無視物質上的不便,驅動勇猛”。這段話中蘊含有深刻的人生哲理以及藝術觀。
《草枕》中,起初畫家是為了追求沒有煩惱的世外桃源開始旅行的,持有出世的心境。例如文本的開頭部分引用了中國古代詩人陶淵明的名句:“採菊東南下,悠然見南山。”以及詩人王維的《竹里館》中的名句“獨坐幽篁里,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展現出一幅幅充滿悠閑心境的田園畫卷。但作者也意識到人一世也是不能恆久保持這種超脫世俗的狀態。於是談到“誠然,作為人世上的一分子,儘管十分喜歡,也不會長久置身於非人情的環境之中。”
那美的人生充滿苦難挫折,她戀愛生活中遇到兩個男人,一個是她在京都上學時認識的,另一個是當地城裡的財主。她一心想嫁給那位京都的公子,父母卻硬逼著她嫁給那家財主。這財主是因她長得標緻才看重她的,兩人總是合不來,後來那財主的銀行倒閉了,她便離開丈夫回到了娘家。村裡人卻都說她心狠,無情無義,議論紛紛。例如理髮店夥計關於那美向畫家這樣介紹,“少爺,那姑娘模樣兒雖好,其實是個瘋子。”“為什麼,少爺,村上的人都管她叫瘋子呢。”,“她是個沒有頭腦的女子,真難辦。”對於這些重重困境,女主人公卻始終保持樂觀表情,文本中多處出現她的笑聲描寫。而且作者也寫到“平素那女子臉上只是充滿著愚弄別人的微笑和那緊蹙抑眉,激進好勝的表情”,對於這一倔強地忍受著人世慘苦的女主人公形象,作者是加以肯定的。而且,她的內心也是痛苦的,否則小說結尾處,當她的丈夫與她分手遠走他鄉時,就不會出現那“悲憫”的表情。
最後在她那一剎那的凄婉表情上,畫家找到了他需要創作的畫,這不僅是藝術,同時也體現了一種人生觀。正如作者闡述到的“要敢於冒犯這種痛苦,內心就必須隱含著戰勝痛苦的歡愉。”是對於人生不畏的處世態度,從藝術角度可以說是一種“美”,達到了“非人情”之境。那美臉上浮現的“哀憐”的表情,應該是源於對於即將趕赴戰場的前夫有可能面臨死亡的厄運的一種擔憂。這種表情也是基於“人情”基礎上的,不脫離於人性的一面,也印證了文中關於“哀憐”的表述:“‘哀憐’是神所不知而又最接近神的人之常情”。可以看出夏目漱石理解的“哀憐”是一種盡量接近神,但屬於人性一面的神所不可了解的一種感情。因此,這種“非人情”並非意味著完全脫離人生痛苦煩惱的極樂世界,而是一種面對世俗的態度,是建立在客觀世界基礎上的超脫心境,從而就體現出一種美,即“非人情美學” 。
餘裕美學
“餘裕”是漱石重要的美學思想之一。所謂有餘裕的小說,顧名思義,是從容不迫的小說。是避開“非常”情況的小說。餘裕是一種對社會現實與人生重大問題無所觸及的境界美,以隨意從容的心境徜徉在自然風光與平凡生活之中。同時,餘裕還是一種“低徊趣味”,體現在小說上,就是一種要求敘述者有充裕的時間佇立一旁細心觀察的趣味。作者在《草枕》中論及“餘裕”,並指出其重要性——“餘裕之於畫,之於詩,乃至於文章,皆為必備的條件。”可以說,《草枕》體現了這一美學思想。
詩詞語句
《草枕》中曾多次引用到漢文典籍中的詩詞語句,尤其以對陶淵明詩歌的引用最為直接和精彩,它們不僅豐富了文章的內容,而且為文章增添了非本土的情趣。除了山水田園詩外,《草枕》中還包含著許多顯而易見的中國元素。
比如文本中第三章描寫旅館房間時這樣寫道:“我仰卧著,偶然睜開眼睛一看,天窗上懸著鑲有朱紅木框的匾額,雖然躺著,卻也清晰地看到寫著這樣一行字:‘竹影拂階塵不動。’”這句“竹影拂階塵不動”來源於中國明末儒者洪應明(字自誠)所著《菜根譚》中的句子:“古德雲;‘竹影拂(掃)階塵不動,月輪穿沼水無痕。’人常持此意,以應事接物,身心何等自在”;之後在論述文學創作客觀性的時候還把藝術家們虛構出來的狹隘的藝術世界稱為“壺中之天地”,這指的是仙境,另一個世界。出自《後漢書·方術列傳·費長房傳》中的典故,即“汝南費長房,在市上遇一賣葯翁,請他一同入葯壺,在一座宮殿里品嘗了美酒佳肴。”
除此之外,文本中還運用到了大量類似“方枘圓鑿”“蜀犬吠日”“吳牛喘月”的成語,並且多次提到出自中國的陳設器物,書法字畫等,這些都是中國元素的具體體現。夏目漱石對這些中國元素巧妙純熟的運用,不僅豐富了作品的內容,更升華了藝術表現力,將他所推崇的“東洋趣味”在作品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日本唯美主義文學對中國造成影響,尤其是夏目漱石的《草枕》這樣的作品,更是對中國的唯美主義文學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中國文學界公認的唯美主義思潮也在此過程中產生。
《草枕》缺乏情節性。
——夏目漱石研究家兼評論家柄谷行人
《草枕》全篇充滿了濃厚的東方禪宗哲學、老莊思想的色彩,其中有對中國的陶淵明、王維的詩的意境的推崇。因此,中國人讀來,自有一種會心之感。也許正是因為這樣,《草枕》在中國評價很高。
——王向東(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
《草枕》所表現的東洋人的情趣在近代資本主義文明的騷動忙亂和“迫切”的生活中,有著特殊的風味。
——謝六逸(翻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