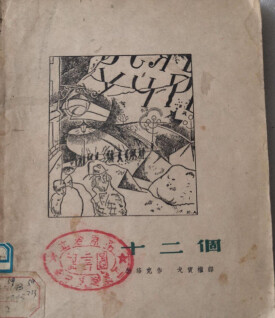十二個
十二個
十二個(俄文:ДВЕНАДЦАТЬ),長詩。前蘇聯作家勃洛克於1918年仿照十二使徒尋找耶穌基督的故事,寫十二個赤衛軍戰士在十月革命后的風雪之夜巡視彼得格勒的大街。那些舊制度的維護者資本家、雄辯士、神父、貴婦人在黑暗中咒罵革命。而代表新世界的十二個戰士則英勇剛強,堅定地向前邁進。長詩《十二今》是詩人獻給偉大十月的藝術傑作,他運用象徵主義方法歌頌革命時代的精神,揭示舊世界滅亡的必然性,預示新生活的廣闊前景。
徠長詩《十二個》,既標誌著勃洛克創作的高峰,也是他獻給十月革命的一份厚禮。
(節選)
第一首:
黑色的夜。
白色的雪。
風呀,風呀!
人的腳都站不住。
風呀,風呀——
吹遍了上帝保佑的全世界!
風卷颳起,
白色的雪。
雪下面——是冰塊。
滑呀,難走呀,
每個行路的人,
都會滑倒——唉,不幸的人!
從這所房子到那所房子,
拉著一根粗繩。
粗繩上-是標語,
“全部政權歸於立憲會議!”
一個老太婆很傷心——哭起來了,
她怎樣都不能理解,這是什麼意思,
為什麼要有這樣一條標語,
為什麼要這麼大的一塊布?
能給小夥子們做多少包腳布呀,
可是每個人——都是裸體,光腳。
老太婆,像一隻老母雞,
好不容易才繞過雪堆。
——哦,我的聖母庇護神呀!
——哦,布爾什維克在把人趕進墳墓!
刮人的風呀!
嚴寒也不讓步!
一個資產階級站在十字街口,
把鼻子藏進了衣領。
啊,那是誰?——披著長頭髮的人。
低聲在講話:
——賣國賊!
——俄羅斯毀滅了!
大概,這是位作家——
雄辯士……
那兒是位穿長袍的——
順著旁邊-走過雪堆……
為什麼現在不快活,
神父同志?
你還記得嗎,從前。
你挺著肚子往前走,
肚子上的十字架,
向老百姓閃著光?
那兒是位穿羔皮大衣的貴太太。
碰到了另一位太太:
——我們已經哭過啦,哭過啦。
腳下滑了一交,
於是——噗通一聲——直躺了下來!
喂,喂!
抓緊呀,爬起來呀!
愉快的風,
又作惡,又快活。
捲起衣裙,
颳倒行人,
撕著、揉著和刮著那條大標語。
“全部政權歸於立憲會議!”
它還帶來了一陣話語
……我們也開過會。
……就在這所房子里。
……我們討論——
我們表決。
短時——十塊錢,通夜——二十五。
……再少——誰的也不收。
……我們去睏覺吧.
深深的夜。
街道空寂。
一個流浪漢躬著肩背,
還有風在唿嘯……唉,不幸的人!
來吧——
讓我們接吻……
麵包!
將來怎麼樣?
走吧!
黑色、黑色的夜空。
惡念,憂鬱的惡念,
在胸中沸騰。
黑色的惡念,神聖的惡念。
同志!要提高警惕!
第二首:
風在散步,雪在飛舞。
十二個人在走著路。
槍上的黑皮帶,
四周圍是——火,火,火。
嘴裡——銜著手卷的紙煙,便帽亂戴著,
背上應該綉上個紅方塊愛司的花樣!
自由,自由,
唉,唉,沒有十字架啦!
特拉一嗒一嗒!
冷呀,同志們,冷呀!
——而凡尼卡和卡季卡——在小酒館里。
——她有“克倫基”藏在襪子里!
——凡紐什卡現在也發財了。
——凡紐什卡從前是我們的人,現在變成大兵啦!
嚷,凡尼卡,你這個狗崽、資產階級,
試一試,你敢和我的情人接吻!
自由,自由,
唉,唉,沒有十字架啦!
卡季卡正和凡尼卡忙著呢——
忙什麼,忙什麼?。
特拉一嗒一嗒!
四周圍是——火,火,火。
槍上的皮帶——背好它。
堅持著革命的步伐吧!
永不休息的敵人不會打目盒睡!
同志,拿住槍,不要膽怯!
我們要用子彈射擊神聖的俄羅斯——
那堅強的,
那農村的,
那大屁股的俄羅斯!
唉,唉,沒有十字架啦!
1.“全部政權歸於立憲會議!”是1918年1月間俄國各資產階級政黨所提出的一個反動口號,來和布爾什維克的“全部政權歸於蘇維埃!”的口號相對立。
2.此字塬文是Вития,即雄辯家,說教者,此處含有諷刺之意。
3.下面的幾句話,都是街頭的妓女講的。
4.紅方塊愛司的花樣,塬文為Вубновыйтуз,是撲克牌中的一種花樣。在十月革命前,這是縫在苦役犯人背上的一塊紅布片。
5.含有無宗教信仰之意。
6.“克倫基”(Керенки)是1917年資產階級臨時政府所發行的一種20及40盧布的紙幣,“克倫基”一名,即從臨時政府的首領社會民主黨員克倫斯基(Керенский)之名而來。
7.凡紐什卡是伊凡及凡尼卡的昵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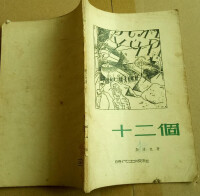
двенадцать
十月革命成為勃洛克詩歌創作中的一個分水嶺。十月革命之前,勃洛克創作了反映“喜悅—痛苦”象徵內涵的詩劇《玫瑰花與十字架》(1913),表現“音樂與光明的旋風”式的愛情組詩《卡門》(1914)和《豎琴與小提琴》(1908—1916),以及思考人之使命的長詩《夜鶯園》(1915)。十月革命后,勃洛克以整個的身心和全部的感情去迎接十月革命,勃洛克創作了後期代表作———長詩《十二個》。
為了創作這首長詩,勃洛克在1918年1月,構思和醞釀了三個星期,最後於27日和28日兩天完成。
勃洛克創作出充滿詩意體驗和象徵意味的長詩《十二個》,形象地揭示了複雜時代與宗教傳統、社會變革與個人體驗的隱蔽關聯。
勃洛克比較客觀如實地描寫人民群眾的代表———十二個赤衛隊員,並沒有將其理想化、片面化和妖魔化。在《十二個》中,十二個赤衛隊員清楚自己是人民群眾力量的表達者和象徵者,意識到自己崇高的革命職責,並隨時隨地用激情和力量履行打破舊世界的職責,捍衛新世界的理想(“保持革命的步伐不甘心的敵人沒有打瞌睡”)。
勃洛克在長詩中描寫猛烈的暴風雪、吹得人站不住腳的驟風、嚴寒的黑夜。他常常給予這些自然現象以特殊的神秘的象徵意義。在寫作《十二個》的過程中,他的日記里不斷出現這樣的記載:“傍晚暴風雪(變革的旅伴)”(1月3日)、“風在喧嘯(又是旋風?)”(1月6日)。他在生理上都能感到舊世界被摧毀的聲音:“近日睜著眼睛躺在黑暗中,聽見轟隆、轟隆,我想地震開始了”(1月9日)。他指出:“革命像驟風,像暴風雪”,它的流發出威嚴和震耳欲聾的轟鳴”,“偉大的轟鳴”。詩人將自己高昂的革命激情,將自己雄渾的詩歌力量融於長詩中飛揚於天地之間的白色的雪的和怒風呼嘯的黑色的夜的旋律之中。
在彼得格勒大街上,從黑夜的暴風雪深處,出現了長詩的主人公—一巡邏隊,十二個赤衛軍戰士。他們是新世界的代表者,是新世界的十二使徒,他們主宰歷史的命運。他們四周是火,火,火。火是革命的象徵。他們要使全世界燃起熊熊大火。詩人把十二個描繪成背上應該綉上紅方塊愛司花樣的人們,他們是被上流社會視為暴徒、罪犯的人們,是來自社會最底層的群眾。然而他們憤怒了,造反了。這種造反表現出強大的人民自發性力量。在造反過程中發生過搶劫、情殺(十二個中唯一有名字的彼特魯哈殺死了他的情人卡奇卡),他們睥睨一切,為所欲為:“自由,自由,沒有十字架啦”。如果連千百年來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都可以拋棄,那麼舊制度、沙皇、貴族、地主、資本家……一定能打倒。
勃洛克將大自然的暴風雪和黑夜、將象徵世界革命的大火,同主人公的白髮性革命激情融匯成一個洶湧澎湃、呼嘯怒號的英雄主義多聲部的悲壯交響曲。
勃洛克以前的詩歌寫的多是主人公個人同社會、個人同環境的對立和鬥爭,而只有在《十二個》中表現了新舊兩個世界的勢不兩立的決戰。
十二個赤衛軍戰士在長詩中從始至終都在暴風雪的黑夜中行進,他們具有極大的概括性和象徵性,我們看不見他們的表情,只能感覺到他們為了革命鬥爭表現出嚴峻、冷漠、堅強,他們帶著上了刺的槍,保持革命的紀律,跟著耶穌基督走向遠方,走向革命的聖地天國。
《十二個》是詩人發自心底的對十月革命和站起來投入鬥爭的人民群眾的一曲激昂的讚歌.
詩作形式精巧,構思巧妙,結構嚴整,構架了三條充滿戲劇性的情節線索:線索之一是,“彼得魯哈—卡奇卡—萬卡”三人因感情糾葛而引發的悲劇故事;線索之二是,十二個赤衛隊員在彼得堡大街上,伴著雄壯的歌聲邁著自豪的前進步伐;線索之三是,老太婆、資產階級、貴太太、神甫、流浪漢等不同階層、不同意識、不同身份的民眾對革命的不同反應。所有這一切,都發生在“黑夜”里恣意橫行的“暴風雪”、“大狂風”等自然背景之中。由此,三條情節線索既彼此獨立,情節完整,又相互交織,對比鮮明,彰顯出革命洪流的勢不可擋,抨擊了沙皇專制統治的保守黑暗。在作者筆下,現實生活中的自然現象具有強烈的隱喻意義和審美的修辭效果:“黑夜”象徵黑暗和腐朽,“暴風”、“驟雪”、“狂風”隱喻著強有力的摧毀力量和運動革命過程中的混亂無序;“白色”象徵光明和純潔,而“癩皮狗”、“餓狗”、“喪家犬”、“無家可歸的狗”則隱喻行將就木、即將毀滅的舊世界。在詩中,舊世界的滅亡和新世界的誕生,直接與人民大眾聯繫在一起,而來自城市底層的十二個赤衛隊員則是人民的代表:
在革命期間彼得格勒街道後面,面對著百廢待興的廢墟,詩人看到一個新世界即將誕生,一個新俄羅斯正在崛起;在巡邏的十二個赤衛隊員的身後,詩人看到奔向未來的人民大眾,一個人民做主的時代正在到來。在“拿著旗子的基督”的帶領下,“他們邁著雄赳赳的腳步走向遠方”———這面旗幟鮮艷而巨大,充滿激情和感召;這個基督雖無跡可尋,但充滿號召力和革命激情;這些腳步堅定而執著,豪邁而有力;這個遠方,雖朦朧卻美好,雖未知卻美妙。這些形象共同體現出詩人對十月革命、人民群眾和未來世界的認知立場和價值訴求———向舊世界報復的“革命風暴”,是滌盪骯髒、消除苦難的暴風雪,是正確而偉大的;跟隨基督前進的“十二個赤衛隊員”是新生活的代表者和捍衛者,是人民自發力量的表達者,同時帶有無政府主義的極端性;而未來新世界則是符合宗教道德的,也是朦朧模糊的。
耐人尋味的是,對長詩的標題“十二個”,對中間若隱若現、結尾處明確出現的基督形象,俄羅斯評論界向來見仁見智,言人人殊,甚至彼此對立,迥然相異。有人認為,基督形象是革命者和社會主義者的象徵,象徵著革命者的共產主義理想,乃是一種宗教式信仰;有人認為,基督形象是符合教規的《福音書》里的人物,基督是美好未來的象徵:有人認為,基督形象是異教的基督,是古老信徒派“燃燒的”基督,是永恆的女性氣質的化身;也有人認為,基督形象是一個超凡脫俗的超人,是一個融合了西方外來思想和俄國民族傳統的藝術家;更有甚者認為,基督形象是一個反基督者,一個敵基督者,是一個充滿革命暴力的基督。可以肯定的是,標題“十二個”具有象徵意義,十二個赤衛隊員很容易讓人聯想到耶穌基督的十二個使徒,長詩在結構上分成12章,這與標題似乎又有著某種形式關聯和內在呼應。而抽象的基督隱喻著:作者寫十二個赤衛隊員和基督形象,將二者並置共存,是一種內在意識的宰制和牽引,它們隱藏在一個“在前面奔跑著的斑點”後面,陷入靈感的迷狂狀態之中,斑點巨大而光亮,“激動著和吸引著我”。至於“拿著旗子的基督”,在勃洛克看來是比較模糊的形象:“‘既是這樣又不是這樣’……當旗子隨風飄動(在雨中或是在雪中,更主要的———是在夜色的黑暗中),就想到在它的下面有某個巨大的人,曾經和他有關的(他不是舉著,不是拿著,怎麼樣呢———但我不會講)。”不僅如此,詩人還曾經在筆記本上寫道,基督形象是一個“女性的幻影”,凡此種種。如此看來,模糊的基督形象具有詮釋的多樣性:既可以理解為對革命的道義上的認可,也可以認為是崇高的道德理想的象徵;既可以理解成對新世界的誕生和精神的改造的期待,也可以認為是一種凌駕於人間之上的抽象力量,更可以認為是一種未來烏托邦世界的認同與召喚。然而,形象的詮釋是有限度的,一如義大利符號學家安伯托·艾柯所言,“說詮釋(‘衍義’的基本特徵)潛在地是無限的並不意味著詮釋沒有一個客觀的對象,並不意味著它可以像水流一樣毫無約束地任意‘蔓延’。說一個文本潛在地沒有結尾並不意味著每一詮釋行為都可能得到一個令人滿意的結果”,因為“在神秘的創作過程與難以駕馭的詮釋過程之間,作品‘文本’的存在無異於一支舒心劑,它使我們的詮釋活動不是漫無目的地到處漂泊,而是有所歸依”。俄羅斯學者圖爾科夫在《勃洛克傳》中認為,“詩人不是占星家,他的詩不是占星圖。在詩中尋找對具體事件的預言,……這是可笑的”,勃洛克雖然看到人民運動的洪流和摧枯拉朽的革命是“生活的開端”,但對究竟誰可以拯救黑暗的舊世界,建立美好的新世界,並不明確和清晰。國內學者鄭體武從詩人身份和詩歌審美角度出發,審視和詮釋革命基督形象,其看法別有一番新意:“從作者本人的解釋可以看出,《十二個》的基督與其說是一個抽象的幻影,不如說是對社會歷史巨變的一種詩意體驗。”綜合各種觀點,大致可以說,詩人通過基督形象給予十月革命和人民群眾一種道德解釋和象徵認知———任何革命和信仰都是在傳統和遺產上建立起來。事實上,蘇維埃政權的建立和蘇聯發展道路的確定,既有來自西歐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引和空想社會主義學說的誘惑,又有俄羅斯集體主義理念傳統的支配和東正教烏托邦意識的滲透。
長詩《十二個》是勃洛克後期創作的代表作,被托洛茨基譽為“個人藝術的天鵝之歌”,集中體現了詩人對人民和革命的看法,具有高度的藝術水準和深刻的思想內涵。
魯迅點評:
能在雜沓的都會裡看見詩者,也將在動搖的革命中看見詩。所以勃洛克做出《十二個》,而且因此“在十月革命的舞台上登場了”。但他的能上革命的舞台,也不只因為他是都會詩人;乃是,如托羅茲基言,因為他“向著我們這邊突進了。突進而受傷了”。
《十二個》於是便成了十月革命的重要作品,還要永久地流傳。
舊的詩人沉默,失措,逃走了,新的詩人還未彈他的奇穎的琴。勃洛克獨在革命的俄國中,傾聽“咆哮獰猛,吐著長太息的破壞的音樂”。他聽到黑夜白雪間的風,老女人的哀怨,教士和富翁和太太的彷徨,會議中的講嫖錢,復仇的歌和槍聲,卡基卡的血。然而他又聽到癩皮狗似的舊世界:他向著革命這邊突進了。
然而他究竟不是新興的革命詩人,於是雖然突進,卻終於受傷,他在十二個之前,看見了戴著白玫瑰花圈的耶穌基督。
但這正是俄國十月革命“時代的最重要的作品”。
詩《十二個》里就可以看見這樣的心:他向前,所以向革命突進了,然而反顧,於是受傷。
這詩的體式在中國很異樣;但我以為很能表現著俄國那時的神情;細看起來,也許會感到那大震撼,大咆哮的氣息。可惜翻譯最不易。
亞歷山大·亞歷山德羅維奇·勃洛克(1880~1921),俄羅斯著名的抒情詩人,俄國象徵主義詩歌的傑出代表。勃洛克出生並受教於貴族知識分子家庭,他的童年與少年時代,最初是在彼得堡的“校長寓所”度過的。他的第一本詩集是《美婦人之詩》。勃洛克早期詩歌受象徵主義的影響,1904年出版第一部詩集《美女詩草》而蜚聲文壇。1905年革命爆發之後,詩人宣布放棄象徵主義,寫下了揭示“可怕的世界”的作品,表達了對生活和未來的嚮往。十月革命后,勃洛克的創作走向巔峰,在動亂中寫成了謎一般的著名長詩《十二個》(1918),確立了勃洛克在俄羅斯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