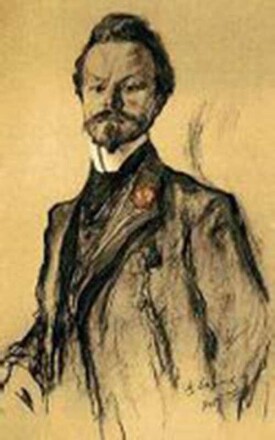巴爾蒙特
巴爾蒙特
巴爾蒙特,康斯坦丁·德米特里耶維奇(Бальмонт Константин Дмитриевич,1867-1942)詩人,評論家,翻譯家。童年時代大量閱讀,尤其對詩歌感興趣,嘗試自己寫詩。
巴爾蒙特在20世紀初的俄國詩壇中佔有重要地位。他一生執著於太陽的崇拜,自稱為“太陽的歌手”,以太陽為題材的作品成為他創作的高峰。巴爾蒙特作為俄國象徵派領袖人物之一,追求音樂性強、辭藻優美、意境深遠的詩風。他的詩歌以鮮明的形象性和獨到的藝術手法得到了世人的讚譽。1890年以後出版了三本詩集:《在北方的天空下》(Под северным небом,1894),《在無窮之中》(В безбрежности,1895),《靜》(Тишина,1898)。它們不僅確立了巴爾蒙特的詩人地位,也是俄羅斯象徵主義的奠基之作。此後詩人筆耕不輟,創作了大量詩篇。1906-1913年居住在法國,多次旅行。巴爾蒙特不接受十月革命,1920年舉家遷往法國,並在國外繼續從事創作。1937年出版了最後一本詩集。
巴爾蒙特的一生充滿動蕩,得到的評價也曾經褒貶不一。1867年,他出生於貴族家庭,后在莫斯科大學法律系就讀,終因參加學潮被開除。他週遊世界,通曉多種語言,把很多外國作品翻譯成俄文介紹到俄國(如:雪萊、波德萊爾等人的作品) ,打開俄國人的眼界。1907年,他為工人們寫了《復仇者之歌》,併到處朗誦,惹惱了沙皇政府,被趕出俄國。二月革命后巴爾蒙特返回祖國,那時俄國的詩壇上已形成各種流派。從象徵主義在俄國一出現時起,他就積極投入到該流派當中,成為了象徵派第一浪潮的代表人物之一。用勃洛克的話說,巴爾蒙特“是俄國象徵主義最偉大的創造者之一”。但後來巴爾蒙特的革命熱情發生轉變,對到來的十月革命表示反對並拒絕參與,因此在那個以政治態度作為評價作家標準的年代,他一度被定性為“頹廢、個人主義、反革命”。他的詩歌也被說成“基調屬於頹廢主義,在藝術上追求過分的誇飾和外表的華麗”長期被打入另冊。1942年,他懷著苦悶和憂鬱凄涼地客死在巴黎。
巴爾蒙特作為太陽的“歌手”,很重視詩歌的音樂性,他為俄國詩壇開創了很多獨特的韻律方式。他說:“我總是在由語言的確定區域向音樂的不確定區域靠近,我竭盡全力追求音樂性。”他在《詩即魔法》一書中寫道,“詩即有節奏的語言表達出來的內在音樂。”而這也是象徵派所追求的藝術境界。巴爾蒙特在自己的詩作中巧妙地使用輔音同音、內韻、復沓、頂針等手法,營造出一詠三嘆的氛圍,使每首詩都成為一首首渾然天成的歌曲。勃留索夫稱讚他的詩歌“在輕盈方面超過了費特,在悅耳方面超過了萊蒙托夫”。
巴爾蒙特還很善於為詩歌營造優美、深遠的意境。他常常使用大膽出奇的象徵、通感、隱喻等修辭手段,使詩語飄逸灑韻韻味悠長巴爾蒙特說:“現實主義者永遠是簡單的觀察者,象徵主義者則永遠是思想家。現實主義者只熱衷於表現具體的生活⋯⋯象徵主義者遠離現實的存在,只在其中看到自己的理想⋯⋯”也許正因為他的這種堅持,正因為他就是一個永遠思考著現實存在背後的象徵主義者,他的詩歌才獲得了如此動人的魅力,他的精神才能永遠追隨太陽的光華。
《為了看看陽光,我來到這世上》
我來到這個世界為的是看太陽,
和蔚藍色的原野。
我來到這個世界為的是看太陽,
和連綿的群山。
我來到這個世界為的是看大海,
和百花盛開的峽谷。
我與世界面對面簽訂了和約。
我是世界的真主。
我戰勝了冷漠無言的山川,
我創造了自己的理想。
我每時每刻都充滿了啟示,
我時時刻刻都在歌唱。
我的理想來自苦難,
但我因此而受人喜愛。
試問天下誰能與我的歌聲媲美?
無人、無人媲美。
我來到這個世界為的是看太陽,
而一旦天光熄滅,
我也仍將歌唱……我要歌頌太陽
直到人生的最後時光!
巴爾蒙特作為世紀之交的一個複雜的文學現象,得到過諸如“俄羅斯詩歌的巴格尼尼”的讚譽,也受到過諸如“充滿反社會的個人主義情緒”的非議。但最重要的是他以自己一生的創作印證了他對生活真諦的思考和“我來到這個世界為的是看太陽”的理想。巴爾蒙特的詩集在俄羅斯受到越來越多讀者的歡迎,還被譯成多國文字介紹到國外。我國著名翻譯家藍英年在《〈塞納河畔〉譯後記》中給以巴爾蒙特這樣的評價:“二十世紀俄國詩歌史可以沒有阿達莫維奇,甚至伊萬諾夫,卻不能沒有巴爾蒙特。”這位堅信“人不能生存,當身體離開太陽,心離開歌”(引自阿赫瑪托娃詩《他說過……》)的“太陽的歌手”也終於像他應該的那樣,穿過拒絕接受他的若干時代的死亡地帶,終於在後世得到復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