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獨憔悴
冰心所著短篇小說
1919年發表。南京學堂學生代表穎銘、穎石兄弟倆參加請願鬥爭,身為軍閥政府官僚的父親停止了他們的學業,將他們關在家中。后兄弟倆當了辦事員,在苦悶中低吟“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的詩句。
冰心(1900-1999),原名謝婉瑩,筆名冰心,福建人。1913年全家遷至北京。1918年進協和女子大學(后併入燕京大學)學醫,后改學文學。從1919年9月起,以冰心為筆名寫了許多小說,如《兩個家庭》、《斯人獨憔悴》等,同時創作散文和詩歌。后結集為《繁星》、《春水》。建國后,曾任中國文聯副主席、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委。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早的女作家之一。

年輕的冰心
短篇小說。冰心作。
本書共選收冰心創作的小說五十三篇,包括《兩個家庭》《斯人獨憔悴》《去國》《最後的安息》《是誰斷送了你》《海上》《愛的實現》《我的母親》《小桔燈》《干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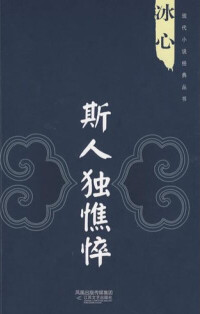
斯人獨憔悴
頭等車上,憑窗立著一個少年。年紀約有十七八歲。學生打扮,眉目很英秀,只是神色非常的沉寂,似乎有重大的憂慮,壓在眉端。他注目望著這一片平原,卻不象是看玩景色,一會兒微微的嘆口氣,猛然將手中拿著的一張印刷品,撕得粉碎,揚在窗外,口中微吟道:“安邦治國平天下,自有周公孔聖人。”
站在背後的劉貴,輕輕的說道:“二少爺,窗口風大,不要盡著站在那裡!”他回頭一看,便坐了下去,臉上仍顯著極其無聊。劉貴遞過一張報紙來,他搖一搖頭,卻仍舊站起來,憑在窗口。
天色漸漸的暗了下來,火車漸漸的走近天津,這二少爺的顏色,也漸漸的沉寂。車到了站,劉貴跟著下了車,走出站外,便有一輛汽車,等著他們。嗚嗚的響聲,又送他們到家了。
家門口停著四五輛汽車,門楣上的電燈,照耀得明如白晝。兩個兵丁,倚著槍站在燈下,看見二少爺來了,趕緊立正。他略一點頭,一直走了進去。
客廳裡邊有打牌說笑的聲音,五六個僕役,出來進去的伺候著。二少爺從門外經過的時候,他們都笑著請了安,他卻皺著眉,搖一搖頭,不叫他們聲響,悄悄的走進里院去。
他姊姊穎貞,正在自己屋裡燈下看書。東廂房裡,也有婦女們打牌喧笑的聲音。
他走進穎貞屋裡,穎貞聽見帘子響,回過頭來,一看,連忙站起來,說:“穎石,你回來了,穎銘呢?”穎石說:“銘哥被我們學校的幹事部留下了,因為他是個重要的人物。”穎貞皺眉道:“你見過父親沒有?”穎石道:“沒有,父親打著牌,我沒敢驚動。”穎貞似乎要說什麼,看著他弟弟的臉,卻又咽住。
這時化卿先生從外面進來,叫道:“穎貞,他們回來了么?”穎貞連忙應道:“石弟回來了,在屋裡呢。”一面把穎石推出去。穎石慌忙走出廊外,迎著父親,請了一個木強不靈的安。化卿看了穎石一眼,問:“你哥哥呢?”穎石吞吞吐吐的答應道:“銘哥病了,不能回來,在醫院裡住著呢。”化卿咄的一聲道:“胡說!你們在南京做了什麼代表了,難道我不曉得!”穎石也不敢做聲,跟著父親進來。化卿一面坐下,一面從懷裡掏出一封信來,擲給穎石道:“你自己看罷!”穎石兩手顫動著,拿起信來。原來是他們校長給他父親的信,說他們兩個都在學生會裡,做什麼代表和幹事,恐怕他們是年幼無知,受人脅誘;請他父親叫他們回來,免得將來懲戒的時候,玉石俱焚,有礙情面,等等的話。穎石看完了,低著頭也不言語。化卿冷笑說:“還有什麼可辯的么?”穎石道:“這是校長他自己誤會,其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情。就是因為近來青島的問題,很是緊急,國民卻仍然沉睡不醒。我們很覺得悲痛,便出去給他們演講,並勸人購買國貨,盼望他們一齊醒悟過來,鼓起民氣,可以做政府的後援。這並不是作姦犯科……”化卿道:“你瞞得過我,卻瞞不過校長,他同我是老朋友,並且你們去的時候,我還托他照應,他自然得告訴我的。我只恨你們不學好,離了我的眼,便將我所囑咐的話,忘在九霄雲外,和那些血氣之徒,連在一起,便想犯上作亂,我真不願意有這樣偉人英雄的兒子!”穎石聽著,急得臉都紅了,眼淚在眼圈裡亂轉,過一會子說:“父親不要誤會!我們的同學,也不是血氣之徒,不過國家危險的時候,我們都是國民一分子,自然都有一分熱腸。並且這愛國運動,絕對沒有一點暴亂的行為,極其光明正大;中外人士,都很讚美的。至於說我們要做英雄偉人,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現在學生們,在外面運動的多著呢,他們的才幹,勝過我們百倍,就是有偉人英雄的頭銜,也輪不到……”這時穎石臉上火熱,眼淚也幹了,目光奕奕的一直說下去。穎貞看見她兄弟熱血噴薄,改了常態,話語漸漸的激烈起來,恐怕要惹父親的盛怒,十分的擔心著急,便對他使個眼色……
忽然一聲桌子響,茶杯花瓶都摔在地下,跌得粉碎。化卿先生臉都氣黃了,站了起來,喝道:“好!好!率性和我辯駁起來了!這樣小小的年紀,便眼裡沒有父親了,這還了得!”穎貞驚呆了。穎石退到屋角,手足都嚇得冰冷。廂房裡的姨娘們,聽見化卿聲色俱厲,都擱下牌,站在廊外,悄悄的聽著。
化卿道:“你們是國民一分子,難道政府裡面,都是外國人?若沒有學生出來愛國,恐怕中國早就滅亡了!照此說來,虧得我有你們兩個愛國的兒子,否則我竟是民國的罪人了!”穎貞看父親氣到這個地步,慢慢的走過來,想解勸一兩句。化卿又說道:“要論到青島的事情,日本從德國手裡奪過的時候,我們中國還是中立國的地位,論理應該歸與他們。況且他們還說和我們共同管理,總算是仁至義盡的了!現在我們政府里一切的用款,哪一項不是和他們借來的?象這樣緩急相通的朋友,難道便可以隨隨便便的得罪了?眼看著這交情便要被你們鬧糟了,日本兵來的時候,橫豎你們也只是後退,仍是政府去承當。你這會兒也不言語了,你自己想一想,你們做的事合理不合理?是不是以怨報德?是不是不顧大局?”穎石低著頭,眼淚又滾了下來。
化卿便一疊連聲叫劉貴,劉貴慌忙答應著,垂著手站在簾外。化卿罵道:“無用的東西!我叫你去接他們,為何只接回一個來?難道他的話可聽,我的話不可聽么?”劉貴也不敢答應。化卿又說:“明天早車你再走一遭,你告訴大少爺說要是再不回來,就永遠不必回家了。”劉貴應了幾聲“是”,慢慢的退了出去。
四姨娘走了進來,笑著說:“二少爺年紀小,老爺也不必和他生氣了,外頭還有客坐著呢。”一面又問穎石說:“少爺穿得這樣單薄,不覺得冷么?”化卿便上下打量了穎石一番,冷笑說:“率性連白鞋白帽,都穿戴起來,這便是‘無父無君’的證據了!”
一個僕人進來說:“王老爺要回去了。”化卿方站起走出,姨娘們也慢慢的自去打牌,屋裡又只剩姊弟二人。
穎貞嘆了一口氣,叫:“張媽,將地下打掃了,再吩咐廚房開一桌飯來,二少爺還沒有吃飯呢。”張媽在外面答應著。穎石搖手說:“不用了。”一面說:“哥哥真箇在醫院裡,這一兩天恐怕還不能回來。”穎貞道:“你剛才不是說被幹事部留下么?”穎石說:“這不過是一半的緣由,上禮拜六他們那一隊出去演講,被軍隊圍住,一定不叫開講。哥哥上去和他們講理,說得慷慨激昂。聽的人愈聚愈多,都大呼拍手。那排長惱羞成怒,拿著槍頭的刺刀,向哥哥的手臂上扎了一下,當下……哥哥……便昏倒了。那時……”穎石說到這裡,已經哭得哽咽難言。穎貞也哭了,便說:“唉,是真……”穎石哭著應道:“可不是真的么?”
明天一清早,劉貴就到里院問道:“張姐,你問問大小姐有什麼話吩咐沒有。我要走了。”張媽進去回了,穎貞隔著玻璃窗說:“你告訴大少爺,千萬快快的回來,也千萬不要穿白帆布鞋子,省得老爺又要動氣。”
兩天以後,穎銘也回來了,穿著白官紗衫,青紗馬褂,腳底下是白襪子,青緞鞋,戴著一頂小帽,更顯得面色慘白。進院的時候,姊姊和弟弟,都坐在廊子上,逗小狗兒玩。穎石看見哥哥這樣打扮著回來,不禁好笑,又覺得十分傷心,含著眼淚,站起來點一點頭。穎銘反微微的慘笑。姊姊也沒說什麼,只往東廂房努一努嘴。穎銘會意,便伸了一伸舌頭,笑了一笑,恭恭敬敬的進去。
化卿正卧在床上吞雲吐霧,四姨娘坐在一旁,陪著說話。穎銘進去了,化卿連正眼也不看,仍舊不住的抽煙。穎銘不敢言語,只垂手站在一旁,等到化卿慢慢的坐起來,方才過去請了安。化卿道:“你也肯回來了么?我以為你是‘國爾忘家’的了!”穎銘紅了臉道:“孩兒實在是病著,不然……”化卿冷笑了幾聲,方要說話。四姨娘正在那裡燒煙,看見化卿顏色又變了,便連忙坐起來,說:“得了!前兩天就為著什麼‘青島’‘白島’的事,和二少爺生氣,把小姐屋裡的東西都摔了,自己還氣得頭痛兩天,今天才好了,又來找事。他兩個都已經回來了,就算了,何必又生這多餘的氣?”一面又回頭對穎銘說:“大少爺,你先出去歇歇罷,我已經吩咐廚房裡,替你預備下飯了。”化卿聽了四姨娘一篇的話,便也不再說什麼,就從四姨娘手裡,接過煙槍來,一面卧下。穎銘看見他父親的怒氣,已經被四姨娘壓了下去,便悄悄的退了出來,徑到穎貞屋裡。
穎貞問道:“銘弟,你的傷好了么?”穎銘望了一望窗外,便捲起袖子來,臂上的繃帶裹得很厚,也隱隱的現出血跡。穎貞滿心的不忍,便道:“快放下來罷!省得招了風要腫起來。”穎石問:“哥哥,現在還痛不痛?”穎銘一面放下袖子,一面笑道:“我要是怕痛,當初也不肯出去了!”穎貞問道:“現在你們幹事部里的情形怎麼樣?你的缺有人替了么?”穎銘道:“劉貴來了,告訴我父親和石弟生氣的光景,以及父親和你吩咐我的話,我哪裡還敢逗留,趕緊收拾了回來。他們原是再三的不肯,我只得將家裡的情形告訴了,他們也只得放我走。至於他們進行的手續,也都和別的學校大同小異的。”穎石道:“你還算僥倖,只可憐我當了先鋒,冒冒失失的正碰在氣頭上。那天晚上的光景,真是……從我有生以來,也沒有挨過這樣的罵!唉,處在這樣黑暗的家庭,還有什麼可說的,中國空生了我這個人了。”說著便滴下淚來。穎貞道:“都是你們校長給送了信,否則也不至於被父親知道。其實我在學校里,也辦了不少的事。不過在父親面前,總是附和他的意見,父親便拿我當做好人,因此也不攔阻我去上學。”說到此處,穎銘不禁好笑。
穎銘的行李到了,化卿便親自出來逐樣的翻檢,看見書籍堆里有好幾束的印刷品,並各種的雜誌;化卿略一過目,便都撕了,登時滿院里紙花亂飛。穎銘穎石在窗內看見,也不敢出來,只急得悄悄的跺腳,低聲對穎貞說:“姊姊!你出去救一救罷!”穎貞便出來,對化卿陪笑說:“不用父親費力了,等我來檢看罷。天都黑了,你老人家眼花,回頭把講義也撕了,豈不可惜。”一面便彎腰去檢點,化卿才慢慢的走開。
他們弟兄二人,仍舊住在當初的小院里,度那百無聊賴的光陰。書房裡雖然也磊著滿滿的書,卻都是制藝、策論和古文、唐詩等等。所看的報紙,也只有《公言報》一種,連消遣的材料都沒有了。至於學校里朋友的交際和通信,是一律在禁止之列。穎石生性本來是活潑的,加以這些日子,在學校內很是自由,忽然關在家內,便覺得非常的不慣,背地裡唉聲嘆氣。悶來便拿起筆亂寫些白話文章,寫完又不敢留著,便又自己撕了,撕了又寫,天天這樣。穎銘是一個沉默的人,也不顯出失意的樣子,每天臨幾張字帖,讀幾遍唐詩,自己在小院子里,澆花種竹,率性連外面的事情,不聞不問起來。有時他們也和幾個姨娘一處打牌,但是他們所最以為快樂的事情,便是和姊姊穎貞,三人在一塊兒,談話解悶。
化卿的氣,也漸漸的平了,看見他們三人,這些日子,倒是很循規蹈矩的,心中便也喜歡;無形中便把限制的條件,鬆了一點。
有一天,穎銘替父親去應酬一個飯局,回來便悄悄的對穎貞說:“姊姊,今天我在道上,遇見我們學校幹事部里的幾個同學,都騎著自行車,帶著幾卷的印刷品,在街上走。我奇怪他們為何都來到天津,想是請願團中也有他們,當下也不及打個招呼,汽車便走過去了。”穎石聽了便說:“他們為什麼不來這裡,告訴我們一點學校里的消息?想是以為我們現在不熱心了,便不理我們了,唉,真是委屈!”說著覺得十分激切。穎貞微笑道:“這事我卻不贊成。”穎石便問道:“為什麼不贊成?”穎貞道:“外交內政的問題,先不必說。看他們請願的條件,哪一條是辦得到的?就是都辦得到,政府也決然不肯應許,恐怕啟學生干政之漸。這樣日久天長的做下去,不過多住幾回警察廳,並且兩方面都用柔軟的辦法,回數多了,也都覺得無意思,不但沒有結果,也不能下台。我勸你們秋季上學以後,還是做一點切實的事情,穎銘,你看怎樣?”穎銘點一點頭,也不說什麼。穎石本來沒有成見,便也贊成兄姊的意思。
一個禮拜以後,南京學堂來了一封公函,報告開學的日期。弟兄二人,都喜歡得吃不下飯去,都催著穎貞去和父親要了學費,便好動身。穎貞去說時,化卿卻道:“不必去了,現在這風潮還沒有平息,將來還要搗亂。我已經把他兩個人都補了辦事員,先做幾年事,定一定性子。求學一節,日後再議罷!”穎貞呆了一呆,便說:“他們的學問和閱歷,都還不夠辦事的資格,倘若……”化卿搖頭道:“不要緊的,哪裡便用得著他們去辦事?就是辦事上有一差二錯,有我在還怕什麼!”穎貞知道難以進言,坐了一會,便出來了。
走到院子里,心中很是游移不決,恐怕他們聽見了,一定要難受。正要轉身進來,只見劉貴在院門口,探了一探頭,便走近前說:“大少爺說,叫我看小姐出來了,便請過那院去。”穎貞只得過來。穎石迎著姊姊,伸手道:“鈔票呢?”穎貞微微的笑了一笑,一面走進屋裡坐下,慢慢的一五一十都告訴了。兄弟二人聽完了,都半天說不出話來,過了一會,穎石忍不住哭倒在床上道:“難道我們連求學的希望都絕了么?”穎銘眼圈也紅了,便站起來,在屋裡走了幾轉,仍舊坐下。穎貞也想不出什麼安慰的話來,坐了半天,便默默的出來,心中非常的難過,只得自己在屋裡彈琴散悶。等到黃昏,還不見他們出來,便悄悄的走到他們院里,從窗外往裡看時,穎石蒙著頭,在床上躺著,想是睡著了。穎銘斜倚在一張藤椅上,手裡拿著一本唐詩“心不在焉”的只管往下吟哦。到了“出門搔白首,若負平生志,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似乎有了感觸,便來回的念了幾遍。穎貞便不進去,自己又悄悄的回來,走到小院的門口,還聽見穎銘低徊欲絕的吟道:“……滿京華,斯人獨憔悴!
冰心是在“五四”精神召喚下最早開始創作活動的一位女作家。冰心說是“‘五四’運動的一聲驚雷把我‘震’上了寫作的道路”。“五四”反帝、反封建的洶湧浪潮和要民主、要進步的時代精神,給冰心巨大的衝擊,激發了她的熱情,陶冶了她的性靈,使她有了初步的民主主義思想。這一同時代與之俱來的進步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是她早期作品思想的重要因素。尤其在她的“問題小說”中體現得更為明顯。
“五四”時期的“問題小說”,是指描寫當時人們所普遍關心的社會問題的小說。冰心的“問題小說”,嚴格說來是指冰心1927年之前寫的小說。這些小說都是冰心參加“五四”運動之後,有所感,有所思,隨手寫下來的。它反映了青年在新舊思想交替時代所遇到的種種苦悶,如報國無門、家庭婚姻、婦女地位,兵士生活等問題。《斯人獨憔悴》便是她的“問題小說”中較有代表性的一篇。
這篇小說通過青年學生穎銘、穎石兄弟與父親化卿的矛盾,揭露了封建專制的野蠻醜惡,表現了人民群眾反帝反封建的心聲。小說寫於1919年10月,所反映的也正是前此不久爆發的震撼人心的“五四”運動。主人公穎銘兄弟的遭遇很快引起了當時眾多青年學生的共鳴,因而小說發表三個月以後,就上演了根據它改編的話劇,這不僅僅是一個初登文壇的女學生的殊榮,更說明了小說反映問題的社會性。
從藝術的角度上看,這篇小說的最大成就是塑造了一個豐滿的藝術形象——化卿。在小說中,化卿完全是以一個封建專制家長的身份出現的,但卻絲毫沒有概念化的痕迹,小說對此人表現得很巧妙。首先,作者採用側面烘托的手法來表現人物。小說開頭寫穎石在回家的列車上憑窗而立,“神色非常的沉寂,似乎有重大的憂慮,壓在眉端”,而且“火車漸漸的走近天津”他的神色“也漸漸的沉寂”,這裡人物神情的描寫一方面表明穎石為國事擔憂,但更主要的是以此說明隨著火車的漸近家園,他內心的壓力便逐漸加重,暗示了穎石之父——化卿在他心中的威勢。穎石來到家門前,小說著意交代“家門口停著四五輛汽車”,門楣上的電燈明如白晝,兵丁倚槍而立,這便告訴讀者化卿的身份和地位之顯赫,而遠遠傳來的房中打牌的喧鬧聲,又可以說明化卿之流在國難當頭之時,仍在過著紙醉金迷的腐化生活。看到穎石,姐姐穎貞的問話和欲言又止的神情暗示了一場風暴即將來臨。這一切交代從多方面烘託了人物形象,為人物的出場做足了準備。
接下來,小說從正面對人物進行刻畫。作者先從人物的語言、動作和神態上直接表現化卿的思想性格。收到校長的來信,他知道兒子參加了愛國運動,對此他先是冷笑,進而稱愛國學生是“血氣之徒”,是“犯上作亂”。當穎石據理分辯,表達自己的愛國熱情時,作者用摔在地上的茶杯花瓶的一聲炸裂,打斷了穎石的剖白;接著寫化卿的“臉都氣黃了”。這種“氣”一是擺老子的威嚴,氣兒子竟“索性和我辯駁起來了”,“眼裡沒有父親了”;更主要的是氣穎石剖白的內容。在他看來,中國的國土被日本從德國手裡奪過是理所應當,日本人既已答應與中國“共同管理”,已經是“仁至義盡了”,因而學生的一番行動便是“以怨報德”。這就將一個“道貌岸然,賣國求榮,寡廉鮮恥”的形象活現了出來。
化卿不僅僅在思想上卑劣無恥,在行動上還是帝國主義和反動的封建統治的幫凶。為使兒子束手就範,規規矩矩,他把他們軟禁在家中,不得與外界接觸,剝奪其行動自由。不僅如此,還禁錮他們的思想,扼殺他們的精神。他親自動手搜查他們的書籍,並撕毀各種雜誌和印刷品,“登時滿院里紙花亂飛”,簡直是一副喪心病狂的架勢。更有甚者,最後竟然實行經濟制裁,南京學堂通知開學,他不給兒子學費,還斷然宣布:“不必去了,現在這風潮還沒有平息,將來還要搗亂……先做幾年事,定一定性子。”
小說通過這一系列情節的描述,塑造出了化卿這一有血有肉的豐滿藝術形象。他仇視新思想,仇視新事物,認賊作父,賣國求榮,竭盡全力維護封建思想和封建專制,將兒子們的愛國行動看成是以怨報德,就是兒子穿一雙白鞋也被認為是“無父無君”的證據。在他眼裡,兒子沒有獨立的人格,只是他的附屬品,對他應該言聽計從。他時刻擺老子的威嚴架勢,對穎石那種凶神惡煞的態度就是明證。對兒子如此,對待下人則更無好臉色,輕則喝斥,重則打罵。
小說中的化卿,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封建統治階級代表人物。在“五四”時期,這類思想頑固,生活腐化的封建衛道者,比比皆是,因而作者塑造這樣的一個形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但冰心不願寫劍拔弩張的激烈場面,因而對化卿的粗暴,專橫表現得仍比較含蓄,體現了冰心小說委婉的特色。
與化卿的耀武揚威相對,小說中的兩位正面主人公則顯得軟弱無力。作者採用對比的方式,一方面突出了化卿的粗暴、專橫,一方面也反襯出穎銘兄弟的怯弱無奈。這兩位兄弟雖懷有一腔愛國熱情,但在封建專制化身的父親面前,則處處表現得被動、軟弱,穎石剛一見到化卿就顯得“木強不靈”,進而在父親摔花瓶的威嚇之下“手足都嚇得冰冷”,退到屋角;穎銘一聽說父親生了氣,也只得放下進步工作,趕緊回到家中;看到父親殘忍地撕毀能給他們一點新鮮空氣的印刷品和雜誌,他們無可奈何,只有搬來姐姐穎貞去救援;對父親的軟禁,他們絲毫不加反抗,而是一個讀唐詩,澆花種竹,“索性連外面的事情,不聞不問起來”,一個也只能唉聲嘆氣地寫些不敢留著的白話文章,發泄心中的鬱悶;最後,當化卿剝奪了他們繼續求學的機會,他們也只有蒙頭大睡或凄惶地低吟“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一任自己“憔悴”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