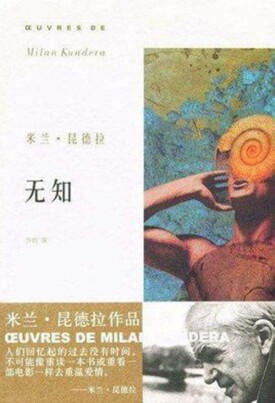共找到4條詞條名為無知的結果 展開
- 漢語詞語
- 米蘭·昆德拉創作中篇小說
- 李肖逸演唱歌曲
- Pino、木子演唱歌曲
無知
米蘭·昆德拉創作中篇小說
《無知》是米蘭·昆德拉創作的中篇小說,與《慢》、《身份》被法國讀書界稱為“遺忘三部曲”。
小說講述流亡二十年的女主人公重返祖國捷克,歸國途中在巴黎機場邂逅舊相識,然而今非昔比,被中斷的故事總難再續,回歸總難踏實。
《無知》以大回歸為背景,透過小說中人物失敗的生活和生活的失敗,昆德拉近乎冷酷地揭示了諸如“返鄉”、“愛情”、“溫暖的家庭”、“友情”等方面所存在的虛假及在現代社會所遭遇的尷尬,顯露出了令人可怕的生存底色,從而揭示了現代人生存的另一困境—人與人之間的疏離與隔膜,進而警示世人關注日益喪失的存在的精神家園。
約瑟夫是在1969年離開捷克去到丹麥的,與伊萊娜在同一時間返回布拉格。哥嫂對他的歸來並不感到高興,相反擔心他回來是為了房產。而約瑟夫並不在意房產,特別想帶走的只是他特別喜愛的一幅畫。雙方互不理解。作品還寫了他和朋友不歡而散的約會,他對昔日日記的銷毀。在和不知姓名的女人(其實就是伊萊娜)約會做愛后,他偷偷地離開了這個女人,離開了布拉格,返回丹麥。
米拉達的故事與伊萊娜、約瑟夫的返鄉故事似乎不甚相干,但她的故事又與前兩人的故事相交織,並在對存在主題的探究上相互呼應,相互闡釋。在直接關係上,她與返鄉的伊萊娜有過約會交談,在間接關係上,她和流亡前的約瑟夫有過戀愛關係,而今只是從伊萊娜嘴裡得知,這個以前和自己有過戀愛關係的男人回到了布拉格,伊萊娜正準備與之約會。米拉達一直保持著一種髮型,保守著左耳的秘密。透過約瑟夫毀掉的日記明白,一場和約瑟夫刻骨銘心的失敗戀愛,使得一個小姑娘悲壯地去殉情,到冰天雪地的山中自殺,結果人沒死,但左耳給凍掉了。從此之後,她再沒有戀愛過,一直獨身生活。
古斯塔夫是瑞典人,他在法國和伊萊娜成了情人。他因為痛恨他出生的城市,發誓不再踏上那片土地。他和妻子的關係很糟糕,所以,他一直在逃避,用所謂的善良作掩護,躲到女人的懷抱中,但他從不把自己的愛無保留地給予他所愛的女人。
1968年,俄國人興兵五十萬,入侵捷克,使捷克陷入了政治恐怖之中,告密、檢舉、大清洗、排斥異己,使眾多的捷克有識之士遭到迫害,普通人的生活也同樣陷入混亂、恐怖之中。於是,迫使許多人如小說的人物伊拉娜、約瑟夫等成了流亡者。流亡者面臨著雙重困境。在新的環境中,他們是異鄉人,是“他者”(異類),是作為被貼了標籤“流亡者”的符號而存在著,被人想象性地同情、把握、存在。周圍的人既不知道他們的過去,也對他們內心的苦悶、痛苦和恐懼一無所知。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他們很難融入新的環境。當他們經過二十年的適應,與新的環境有所融合之後再返鄉,又使家鄉人與他們產生了嚴重的隔膜。家鄉人對他們的流亡生活一無所知,而且也不願意去了解、去理解。殘酷的政治,導致了被迫流亡的孤獨與隔膜,同樣也導致了返鄉的無奈和疏離。這樣的惡果並不只是發生在小說中的人物身上,也不只是發生在捷克人身上,這是一個時代的悲劇、又是歷史上不斷上演的悲劇。
伊萊娜
伊萊娜回歸久別的祖國,正如當年跟隨丈夫馬克遠離祖國一樣,始終處於被動境地。當年為了逃避強勢母親所帶來精神上的壓迫感,無奈之下她選擇自己並不愛的一個男人馬克做丈夫,隨之又踏上了離家之路。生活在異國他鄉,不再有母親的強勢,她感到輕鬆與自在,眷念著巴黎的風景線,祖國漸漸在淡化之中變得模糊起來。但是在朋友眼中她始終是作為一個被祖國遺棄的流亡者身份而被關注與同情,一句“你還在這兒幹什麼”的質問,使得女主人公內心深處隱藏著的祖國之情頓然而起,於是一場“大回歸”便在“一無所知”下拉開了自己的帷幕。小說中,可以看到伊萊娜的大回歸是失敗的,甚至將自己拋進了一次混亂、顛倒與迷失的尷尬處境當中。昆德拉在其中穿插進去了伊萊娜少女時期一段意猶未盡的戀情。回歸途中偶遇昔日戀人約瑟夫,伊萊娜以為這段偶然邂逅便是自己選擇回歸之意義,哪裡知道在自己記憶深處所保留的關好的往事,在約瑟夫那裡卻遭到最徹底的遺忘,誤解由此而來。遭到回歸重創之下,伊萊娜試圖重燃與約瑟夫的舊情來彌補回歸的無意義與內心的孤獨;約瑟夫卻把伊萊娜當作自己回歸后一次記夫的救贖。結果兩個人都無法根除那來自回歸后精神上絕望的孤獨感,致使一個喝得爛醉,另一個只想趕快逃離。
約瑟夫
如果說伊萊娜在對故鄉的恐懼中還有熱切的期望的話,約瑟夫則是完全被動地踏上回鄉路的。離開故鄉是為了逃避(對動蕩的政局的逃避),回到故鄉也是為了逃避(對妻子的過世的逃避)。所有的記憶都在這流亡的路上丟失了。他對於回歸沒有激動,沒有沮喪,甚至連冷漠都沒有。父母、伯父、伯母這些值得留戀的稱呼早已湮沒在不起眼的墓群里,而自己以前用過的東西也早已成了哥嫂的財產。他感到自己是個死而復生的人,只能卑怯地看著這一切。同伊萊娜一樣,他其實也不再屬於這片土地了。
《無知》中主要人物都是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后流亡,接著歷經波折后在1989年後共產黨政權垮台後回到捷克,但是他們發現收留他們的西方社會對他們的同情隨著社會主義的消失而同時消退,而家鄉的人對他們在西方的經歷也幾乎毫無興趣。他們進退維谷。作者對所謂鄉愁,未來,性,愛情,甚至時間本身進行了無情的解剖,最後展示了這樣一個事實即無知取得了勝利而記憶卻以失敗告終。“無知”是憤怒的方式,是悲憫的一聲嘆息,是不可調和的壓抑性沉默;然而,絕不是“難得糊塗”,它帶有濃郁的自傳色彩和去國懷鄉的情緒,是昆德拉現實存在的刻意書寫。作品中的男女主人公約瑟夫和伊萊娜時隔20年後回到祖國捷克,在布拉格機場巧遇,但最終卻無法回歸故土。
因為流亡者和移民者跨越了兩種或多種文化,所以他們不但要面對現實生活中存在的異質文化,同時又不能忽略自己的族裔文化。在此過程中,他們自身既接受了歸化國的文化、社會環境、生活方式等因素的同化,又無法從現實生活和內心世界中與自身的族裔文化進行分離,這種矛盾情結使得他們在思想意識上經歷了困惑。兩種不同的文化相互作用並相互影響,而當二者產生衝突和矛盾時,流亡者就必然要經受某種程度的孤獨和痛苦。當伊萊娜現在的瑞典男友古斯塔夫決定去她的城市—布拉格工作時,她“對此並不開心,反而感到一種隱隱的威脅”,她認為古斯塔夫想要了解並接觸布拉格的想法實在是太瘋狂了。古斯塔夫無法真正地了解伊萊娜,因為對伊萊娜來說,古斯塔夫心中的她的祖國山於她母親的存在反而使自己的心理變得脆弱和不成熟。伊萊娜在自我定位情感上具有分離性,所以當他人與自己對事物的判斷和看法產生分歧時會表不出困惑,甚至產生一種威脅感。
對於流亡者和移民者來說,身份認同危機一直困擾著他們,對身份問題的探尋也從未停比過。而流亡者不論是身處異質文化下的歸化國,還是身處自己的祖國都不能得到歸屬感和認同感。他們跨越不同的文化,卻又不完全屬於任何一種文化,搖擺於不同文化之間使得他們的身份變得模糊、不確定,所以流亡者對於自我身份的追尋始終處於一個矛盾的、動態的、可協商的探索過程。他們努力構建屬於自己的身份認同感,卻始終無法擁有一個恆定不變的身份,內心的矛盾與孤獨、對身份的迷茫與錯亂,始終伴隨著他們的流亡生活。
如果遺忘摧毀的是人類歷史進程中那些美好的東西,而對曾經犯下的錯誤又不反思,帶來的就不只是人與人之間的隔膜,而是精神家園的不可回歸。返回家鄉的伊萊娜、約瑟夫找不到曾經熟悉的故鄉,就是在法國,伊萊娜也曾為那些破敗的行將消失的美景(作為美好的歷史見證)而哭泣。約瑟夫被人遺忘,但他也在遺忘,他忘記了伊萊娜,毀滅了與伊萊娜可能有的美好的愛情,他毀棄掉昔日的日記,徹底毀滅、埋葬了與米拉達那段初戀。勛伯格被人遺忘,真正的音樂被“收音機”這個“細菌”吞噬了。音樂犧牲在音樂的髒水裡。遺忘無處不在,遺忘讓人輕鬆得忘乎所以。但是,人類並沒有因為遺忘,惡行就自行消失,不公不義就退場,悲苦與人禍就不發生。正是遺忘,讓人逐漸失去了反思的能力,失去了質疑、批判的能力,失去了思考的勇氣,失去了自省、自審、自糾、自救的沉重與莊嚴,失去了對真理、正義的堅守與追求,失去了對生活的熱愛和信仰。遺忘細菌的侵擾,損害的不只是個人健康的機體,也損害著人與人正常的人際關係,損害著人類的精神世界,讓人更為孤立、孤獨、無助,無家可歸。
昆德拉是刻薄的,殘忍的。他的殘忍在於無情地剝去真理外面裹著的那些閃亮的、迷人的外衣,把真理赤裸裸地直陳你的眼前,直逼你的心底,刺激著你的神經。他的殘忍更在於他善於調遣各種可能的小說手段,在對位與錯位、變奏與暗示、反諷與反襯中讓虛幻的景象與美麗的記憶精心維繫著,一直持續著,但剎那間,筆鋒一轉,美麗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醜陋;幸福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痛苦。讀者自以為置身於天堂,轉眼間發現自己明明是在地獄。這種一而再,再而三被巧妙地矇騙的感覺,讓讀者在閱讀中平添了一種緊張感,因緊張而不得不放慢閱讀的速度,因害怕被欺騙,而又經常會重讀已經讀過的章節,生怕掉入敘述者設下的陷阱,落下無知、可笑的話柄。
面對法國文學評論界的質疑,針對“語言疲勞”、“形式生硬”、“風格貧乏”等刺耳的批評,昆德拉把書稿交給西班牙,於2000年以西班牙語與讀者見面。首印十萬冊,引起廣泛的關注、強烈的反響和普遍的好評。
作家畢飛宇:這本書可以取許許多多的書名,本真一點可以叫《流亡》,史詩一點可以叫《大回歸》,青春一點可以叫《布拉格的森林》,老氣橫秋一點可以叫《就這麼活了一輩子》,時尚一點可以叫《天還沒黑就分手》,激情一點可以叫《革命,繼續革命》,另類一點可以叫《我用幽把你默死》,下半身一點可以叫《把丈母娘睡了》,但是,昆德拉起了一個不著四六的名字:《無知》。
米蘭·昆德拉,捷克小說家,生於捷克布爾諾市。父親為鋼琴家、音樂藝術學院的教授。20世紀50年代初,他作為詩人登上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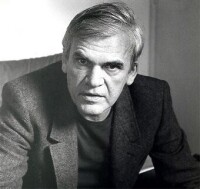
米蘭·昆德拉
1967年,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玩笑》在捷克出版,獲得巨大成功,連出三版,印數驚人,每次都在幾天內售罄。作者在捷克當代文壇上的重要地位從此確定。但好景不長。1968年,蘇聯入侵捷克后,《玩笑》被列為禁書。昆德拉失去了在電影學院的職務。他的文學創作難以進行。在此情形下,他攜妻子於1975年離開捷克,來到法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