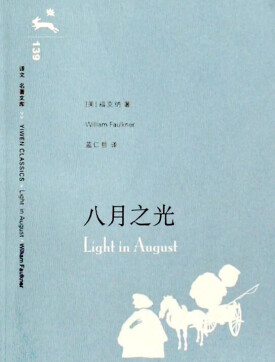共找到2條詞條名為八月之光的結果 展開
- 1932年威廉·福克納所著圖書
- 西渡所作詩歌
八月之光
1932年威廉·福克納所著圖書
《八月之光》是美國作家威廉·福克納創作的長篇小說,也是其代表作之一。在作家營造的“約克納帕塔法世系”中佔有重要位置。
小說通過傑弗生鎮十天的社會生活的描述,揭示了幾個主要人特的一生極其三代家史,體現了人類“心靈深處的亘古至今的真實情感、愛情、同情,自豪、憐憫之心和犧牲精神”,表明了作家反對種族偏見和宗教偏見的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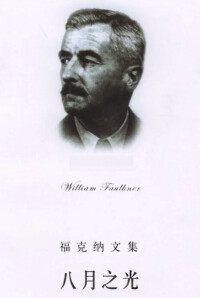
其他版本的《八月之光》
20世紀20年代末,美國南方社會處於新舊交替的歷史時期,即南方文藝復興時期,社會矛盾衝突尤為激烈。這不僅表現為宗教的侄桔與掙扎,還有種族、性別、新興工商主義與傳統價值觀念間等諸多矛盾,以及由此導致的人性的扭曲與異化,和人們對歷史、現實的重新審視、對自我(即主體理性)的尋求。
《喧嘩與騷動》和《我彌留之際》為作者贏得高度讚許之後,《聖殿》卻又不期而然地帶來某些負面影響,福克納創作《八月之光》時便格外警惕,並對新作抱有很高的期望。從現存的《八月之光》手稿上的標註日期看,福克納於1931年8月17日(也許更早一些)開始動筆,直到次年2月19日完稿。創作過程順利,完成後他也很滿意,送給出版社后很快排出了校樣。他在1932年秋看完校樣后致他的朋友兼出版代理人本·華生的信中寫道:”我看不出它有什麼不妥之處。我希望就照現在這樣出版。這部小說是小說而非軼事,也許因此它可能顯得頭重腳輕。”
如果說一則“軼事”往往僅是世間流傳的故事,一部小說則是一個由作家自己虛構的世界。《八月之光》不是由某個傳聞故事衍生出來。它的創作源出於福克納腦海里的一個意象。談到《八月之光》的醞釀,福克納後來回憶說,最初在他頭腦里“只是一個名叫莉娜·格羅夫的年輕姑娘,懷著身孕,決心赤手空拳地去尋找她的情夫”。
莉娜·格魯夫
第一條主線主人公莉娜·格魯夫的姓氏“格魯夫”既有“樹叢、樹林”的意思,也暗含“生命”的意義。莉娜·格魯夫懷著身孕尋夫的歷程,和森林女神的形象不謀而合,也正是福克納想要體現的“大地母親”的形象。可以說,莉娜·格魯夫在福克納的筆下就是大地母親的化身。大地母親是繁衍女神,象徵著生育、繁殖和多產;而莉娜·格魯夫所體現的人物特徵“life(生命力)、peace(平和)、and quaint order(體態健康)”,正是作者試圖傳遞給讀者的一種大地母親的形象特徵。Hlavsa Jmmes認為莉娜就是聖母瑪利亞的象徵,而一直幫助陪伴她的支線人物拜倫·伯奇(Byron Bunch)就是Joseph(約瑟)的象徵。正如聖母瑪利亞一樣,莉娜出現在八月,凱撒·奧古斯都時代和聖母升天節的日子,她穿的是聖母瑪利亞的顏色———藍色,她也拿著一把棕櫚扇……從情節上說,莉娜一路尋夫無果也和聖母瑪利亞無孕而生,受聖靈感應而懷孕,有著相似之處。
莉娜與其說是福克納塑造的一個人物,不如說是他有意運用的一個非人格化的意味雋永的象徵。她從容自在地行進在路上的形象貫穿小說始終,不僅為整個小說構建了一個框架,更暗示了一個以鄉村背景的淳樸人生。她身上閃現的自然淳樸、寬厚仁愛、堅韌不拔、樂觀自在的精神。可以說,她就是“八月之光”的光輝的具體象徵。
喬·克里斯默斯
第二條主線主人公喬·克里斯默斯表面上很顯然是由於出生在聖誕夜,由此被命名為“喬·克里斯默斯(Chrismas)”。而小說中故事情節的發展、人物的命運結局又似乎暗示了一個驚人的相似:喬·克里斯默斯搞不清楚自己的身世,不知自己的生父是誰,一生都在為“我是誰”而糾結。正如耶穌基督的誕生是由聖母瑪利亞無孕而生,而沒有生父。當莉娜·格魯夫的嬰兒在星期一降生時,恰恰是喬·克里斯默斯被殺死的時間。這樣的安排和耶穌基督的受難與復活有著不謀而合的相似,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喬·克里斯默斯就是耶穌基督的化身。喬·克里斯默斯的名字縮寫為“J.C”這又和耶穌基督(Jesus Christ)的名字縮寫一致。因此,很多批評家都在各自的文章中將喬·克里斯默斯比作耶穌。
蓋爾·海托華
第三條主線人物蓋爾·海托華是一個被廢黜的長老會派教會牧師。他自幼生活在祖父(美國內戰時南部同盟軍戰死的騎兵)的陰影里。他對現實世界漠不關心,對教區和會眾也熟視無睹,甚至在佈道壇上夢囈起祖父的光榮和死時的情景。他對妻子的冷漠導致妻子離家出走最終跳樓自殺。凡此種種,蓋爾·海托華最後被教會罷免了牧師的職務,但他拒絕離開傑弗生鎮,過著離群索居、晦暗陰鬱的日子。蓋爾·海托華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一個道德“反射器”,在象徵的含義下,他和莉娜·格魯夫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莉娜總是在行進,蓋爾·海托華總是坐在窗口;莉娜走在灑滿陽光的道路上,蓋爾·海托華住在黑暗的屋子裡;莉娜年輕充滿活力,蓋爾·海托華年老而晦暗;莉娜象徵著生育多產,蓋爾·海托華象徵著貧瘠而無結果。此外,蓋爾·海托華的孤獨與唯我也與莉娜的完整與完美形成了鮮明的象徵對比。但是到了文章末尾,海托華為莉娜接生之後感受到了生命的活力與喜悅,打破了傳統的道德觀念,開始理解拜倫對莉娜的愛,終於從沉睡夢幻之中覺醒而且認識到自己的過錯。
這部小說在福克納創作生涯中的重要代表意義和其思想的深刻性,以及對人類所寄予的希望,作者通過對莉娜·格羅夫、喬·克里斯默斯等人物性格、行為的分析,揭示出福克納對現代異化問題的關注,對主體理性的“回歸式”企求。
在早期的批評文章中,曾有人提出過一種解釋,認為“八月之光”是一個針對莉娜身孕的鄉村俗語,原指懷孕的母牛到八月產仔后體重就變輕了。按照這種解釋,”light”是形容詞“輕”而非名詞“光”的意思。通常,一個作家絕不會選用一個貶低自己作品主人公的鄉村俚語來做標題,這顯然是不能成立的誤解。福克納採用“八月之光”的引喻早見於《喧嘩與騷動》里昆丁講述的一節:“在老家八月底有幾天也是這樣的,空氣稀薄而熱烈,彷彿空氣中有一種悲哀、惹人懷念家鄉而怪熟悉的東西。人無非是其氣候經驗之總和而已,這是父親說的。”這個引喻的涵義也可以從《八月之光》初版時護封標題頁上灑滿陽光的設計圖案得到證實,最新的:1985年改訂本的封面也採用了類似的設計。
傑弗生鎮是《八月之光》的社會背景,克里斯默斯的謀殺轟動了全鎮,而且,整個小說的相當大部分的情節都是從第三者的眼光或民眾反應的角度傳達出來。因此,小說從頭到尾給人一個深刻的印象:傑弗生鎮是一個公眾積極參與、社會輿論強大、相當封閉落後的美國南方社會。很明顯,這個社會的精神支柱是傳統的道德觀念和宗教教義的清規戒律。它要求生活其中的每個人都按它的規範行事,任何偏離其準則的言論舉止都會遭到公眾的議論或譴責。這樣的社會必然保守封閉、對外排斥,成為產生社會偏見和種族歧視的溫床。
當然,人與社會的關係總是兩方面的。人的因素常常是更主要的方面,人對社會採取不同的態度和立場往往會引出不同的結果。克里斯默斯的悲劇有社會對他的不公,種族歧視的壓力,但命運的作對卻是註定不變的。”那條延伸了三十年的街道……已經繞了個圓圈,但他仍然套在裡面。”在他為社會中的“自我”而苦惱而求索的一生中,他對社會和他人採取了不妥協的頑強態度,可是,他自己也忽視了對社會和對自己的了解,甚至“他在這片土地上長大成人……對這片土地的真正形態和感受還一無所知,……對大地也必須遵循的不可更改的法則,他仍然一竅不通。”直到他感到周身虛脫無力,才意識到。生存原來是這麼回事”。(第14章)在海托華和伯頓的情形,可以說伯頓更多的是歷史創傷的受害者,一個被社會扭曲了的人物,而海托華雖生猶死地虛擲了一生,則主要應由他自己負責。對莉娜來說,她是自然的幸運兒。她總是得到各地鄉親的幫助,傑弗生鎮的鄉親對她也是友善的。正像福克納在他的其他小說里所表現的那樣,他對南方社會的描寫是客觀真實的,但對存在的問題和弊端所持的態度,則是相當溫和的。
在福克納筆下,人性之光的顯現,是通過兩條明線而最後達到暗合的一條是痛苦、殉難的線,一條是光明、本真的線。具體地說,喬·克里斯默斯便是前者。三十年的折磨和打擊,三十年心靈的流浪和對“自我”身份的追尋與確認,都以痛苦和絕望告終。正如他的名字所喻示的那樣,他苦難而生,殉難而亡。他是社會種種矛盾尤其是種族主義的祭品,也是一盞警醒愚妄和偏狹的世俗靈魂的長明燈:“他們不會忘記這情景。無論在多麼清幽的山谷,無論在多麼寧靜怡人的古老河邊,也無論在任何孩子純潔如鏡的臉上,他們都將記起舊日的災難,並化生出新的希望。但正如前文所說,他對“人”之本義的理解,對仍在迷茫中、仍被異化之力盲目牽引的人的警示,是以生命為代價的"但克里斯默斯在痛苦、毀滅中明白的道理,原卻只是人本來的存在"這便是小說中的另一條線以莉娜·格羅夫為代表的“自然”美。莉娜是作為光明、美、自然、不折不撓和希望的化身,在小說中出現的她,也是福克納創作生涯中的第一縷亮光,是“比基督文明更為古老”的時代精神的再現,她“從容自在地行進在路上的形象”,猶若“古瓮上的繪畫”,“老在行進卻沒有移動”,那是一幅自古未變也不會變的“靜態美”的圖景,是福克納所讚美的自然的美的人性: 使人類永垂不朽的“勇氣、榮譽、希望、自豪、同情、憐憫之心和犧牲精神,莉娜便是所有這些美德的綜合體。喬·克里斯默斯在生命的最後時刻所顯現的,也正是這些人之所以成為他自身的美德。他手中上了膛的槍,成了人類力量和寬恕的象徵。也正是在這裡,喬·克里斯默斯,福克納筆下的社會異化的犧牲品,經過苦苦求索,驀然回首終於找到的“自我”,與“人類昔日的榮耀”之化身的莉娜·格羅夫所具備的美德,實現完美的暗合"這也暗示了福克納給處於困境中的現代人所指的一條精神出路。
1957年福克納在弗吉尼亞大學講演時,有人問到這個問題,福克納明確地這樣答道:”在密西西比州,八月中旬會有幾天突然出現秋天即至的跡象:天氣涼爽,天空里瀰漫著柔和透明的光線,彷彿它不是來自當天而是從古老的往昔降臨,甚至可能有從希臘、從奧林匹克山某處來的農牧神、森林神和其他神祗。這種天氣只持續一兩天便消失了。但在我生長的縣內每年八月都會出現。這就是那標題的涵義。對我說來,它是一個令人怡悅和喚起遐想的標題,因為它使我回憶起那段時間,領略到那比我們的基督教文明更古老的透明光澤。”
福克納的回答既表明“八月之光”是指他家鄉實有的自然景象,更暗示了它包含的古老深遠的底蘊。因此,這個“喚起遐想的標題”令人聯想到莉娜身上閃現的超越道德準則的異教觀,她那自然純真、超然物外的品性;也可用來寓言般地暗示這部小說超越時空的普遍意義——人世間、人生中總有那麼一段神奇的時光,即使很短暫;小說中幾個主要人物屆時都從中得到了啟迪或拯救:拜倫·邦奇遇到莉娜后一見鍾情,儼然變成了另一個人;喬·克里斯默斯一生追尋自我,最後發現他生活中需要的只是簡單的寧靜;海托華在助產新生命的感悟下,終於掙脫出往昔的惡夢,認識到自己的過錯和人們應當彼此相依的生存事實。推而言之,《八月之光》可以作為《福克納在接受諾貝爾文學獎時的演說》的註釋,象徵著人類將賴以“永垂不朽”的古今延綿的“人類昔日的榮耀”。
在小說藝術形式方面,福克納在《八月之光》里把現代主義的技巧與傳統的藝術手法有機地結合起來。如果說,他此前的小說以多角度的敘事觀點著稱,《八月之光》則以多線索的情節結構聞名。正像《喧嘩與騷動》和《我彌留之際》一次只讓讀者通過一個人物的視角去觀察和理解中心故事,《八月之光》拒絕讀者順著一條連貫的線索去窺知全貌。福克納能夠如此操作所憑藉的控制閥,前者是人物的意識流動,後者則是時間的跳躍交織。
時間的跳躍與交織是《八月之光》這部小說比較有特色的寫作手法之一。作者運用了多種時間手段使得在十多天發生的故事可以追溯到人物的一生甚至是直至其父輩祖輩的三代家史。作者大量運用了預敘、閃回、跳躍、更替、時間流逝等等手段,其中又以閃回為突出。福克納對於小說里時間的掌控與運用可謂得心應手,信手拈來。特別在第二主線人物喬·克里斯默斯的構建中,更是用得淋漓盡致、極盡其所能。
從時間情節上來看,《八月之光》故事發生在八月中旬,大約歷時10天。莉娜·格魯夫在小說開始時行進在路上的時間是星期五,星期六下午她到達傑弗生鎮,這時小說描述了莉娜·格魯夫看到的一個景象:一幢住宅在燃燒,預示著一樁兇殺案發生了。這案子涉及兩個住在現場附近的嫌疑犯——盧卡斯·伯奇和喬·克里斯默斯。兇手喬·克里斯默斯逃跑了;為了獲得賞金,作為兇手朋友的伯奇露面來幫助警方捕捉兇手。喬·克里斯默斯逃跑躲藏一周之後,星期六主動出現在摩茲鎮。莉娜一路來尋找的情夫恰恰就是盧卡斯·伯奇,卻遇見了拜倫·伯奇,此時她已即將生產。在伯奇的幫助下,莉娜住進了喬·克里斯默斯和伯奇先前住過的小木屋;下一周的星期一早上,莉娜·格魯夫由蓋爾·海托華助產,嬰兒誕生了。嬰兒出生這天恰好是兇手喬·克里斯默斯被殺害之日,也在這一天盧卡斯·伯奇去小木屋會見莉娜·格魯夫,可是見面幾分鐘后,盧卡斯·伯奇便又逃離。於是,如同小說開始時那樣,莉娜·格魯夫又上路了。整個故事橫向發生的時間雖然只有十天,然而縱向延伸的過去時間卻涉及幾個人物的一生,甚至涉及了其父輩祖輩的三代家史。福克納筆下的時間在現在與過去之間流動,不斷地前後跳躍相互交叉,形成了一個縱橫交錯、血肉豐滿的故事肌體。
福克納在《八月之光》里試驗著一種高度自由的組合結構。1957年他被問到為什麼把海托華的身世放在倒數第二章,他答道:”除非像驚險故事那樣沿著一條直線發展,否則一本小說只能是一系列斷片。這多半像是裝飾一個展覽櫥窗。要把各種不同的物件擺放得體,相互映襯,需要有相當的眼力和審美情趣。原因就在於此。在我看來,那樣放最合適:克里斯默斯故事的悲劇結局最好以其對立面的悲劇來反襯。”在福克納看來,小說的結構布局,如同干木工活兒,多半憑經驗、憑感覺行事,或者像“裝飾展覽櫥窗”那樣,需要的是以藝術的眼光將不同的物件排列組合,而且正是從物件的自由排列組合中呈現出新穎的構型。因此,小說的形式可以是多元組合結構,而不必是傳統的人工斧削的直線型的單一模式;小說結構所追求的不是整齊勻稱的機械統一體,而應由各斷片以自身的理由呈現出獨特的形狀,千姿百態地組合在一起,形成一片天然成趣的畫面。
從平行線索之間見到它們的聯繫,從看似分裂的排列看出天然渾成的組合,顯然這對讀者更具有挑戰性。在創作過程中,福克納曾一度把第三章的情節放在開頭,後來才改成以莉娜的故事開端,末了再以她的故事結尾。這一首一尾,構成了整個小說的統一框架。莉娜的故事採用傳統的敘事手法,因為這更適應她的故事的主題含義。她的故事在首章運用的是直接描述,末章卻通過一個傢具商販來轉述,兩相對照,一近一遠地呈現出她不斷“行進在路上”的永恆意象。前三章分別引入莉娜、克里斯默斯和海托華的故事,其中包含一個共同之處:描寫他們如何來到傑弗生鎮;最後三章這三人的順序卻顛倒過來,分別描寫他們如何離開(包括死的方式)傑弗生鎮。這樣,前後六章在兩個層面上首尾呼應,遙相對照,使這部看似畸形的小說不失為一個獨特的統一體。在各線索之間,尤其是兩大平行主線之間,表面上兩線從未交叉,莉娜與克里斯默斯從未見過面,但福克納從小說主題、人物遭遇、事件:行動、時間、用品、話語、意象等諸多細節描寫上,巧妙地大量採用了對置、對位、對應、反襯等手法,構成了不同線索之間的契合與張力,維繫了小說的整體結構。比如,莉娜和克里斯默斯都是孤兒,曾被另一家收養,最後都以越窗的方式逃走;在同一個星期五,莉娜搭乘馬車懷著希望去會見情夫,朝傑弗生鎮悠緩地行駛;克里斯默斯卻從早到晚消磨時光,懷著殺人的動機等待夜幕降臨去殺死情人;莉娜來到傑弗生鎮的一周正是克里斯默斯逃離該鎮的時候;莉娜的嬰兒在星期一誕生,克里斯默斯卻在這一天慘遭殺害;兩個人都對自己的姓名十分重視,一個說:“我現在還沒姓伯奇呢,我叫莉娜·格羅夫。”(第1章)另一個聲稱:”我不姓麥克依琴,克里斯默斯才是我的姓。”(第6章)在其他線索之間也大量運用這些手法:海托華和伯頓都是堅持住在傑弗生鎮的不受歡迎的外來者,他們的祖輩父輩都有美國內戰和重建時期的不幸經歷,都有類似的怪癖,對後代留下了沉痛的精神創傷;莉娜和伯頓,一個年輕單純、充滿活力生機,一個空負了年華、以死作為解脫,但兩人大致在同一時候懷上身孕,前者為後者燒毀的莊園帶來新生;星期一下午的同一時候,拜倫-邦奇在野外追趕再次逃離的伯奇,矮小的邦奇甘願被高大的伯奇痛打一頓;而氣盛的珀西·格雷姆則在城裡窮追亡命的克里斯默斯,後者握著手槍卻未向追擊者還擊。……細心閱讀,便會發現層出不窮的這類細節描寫。福克納似乎關心的不是各線索之間的融匯或調和,相反是彼此間的對置、對比或反襯,正是這些匠心獨運的手法,賦予了《八月之光》多線索結構的向心力,使“頭重腳輕”的形態獲得了內在的整體性。邁克爾·米爾格特高度地評價了福克納的探索和取得的成就:“正是在《八月之光》的創作里,福克納首次成功地找到了自己的結構模式:幾條在本質上彼此區別、各自獨立的敘事線索既能同時展開又能不斷地相互影響——每一條線索都在以某種方式持續地默契另外的線索,往往造成相得益彰的甚至是喜劇式的效果。”
1932年10月6日《八月之光》在美國問世,立即引起評論家的關注,就在小說發表的同一周內,美國很有影響的報刊《星期六文學評論》和《紐約時報書評》即載文評論;次年1月,一向對福克納作品並不熱心的英國也相繼有權威的批評家撰文。儘管初期的評論在肯定它的同時不無訾議,但隨著評論的深入,到了1935年8月,《八月之光》作為福克納有特色的重要作品已得到公認。
評論家喬治·奧當尼爾(Goegre O'Dnonen)則說:“總的來看,《八月之光》比福克納所寫的任何一部作品都更為成熟,視界更為寬廣,更接近於最終和真實地揭示出人的潛力。”

威廉·福克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