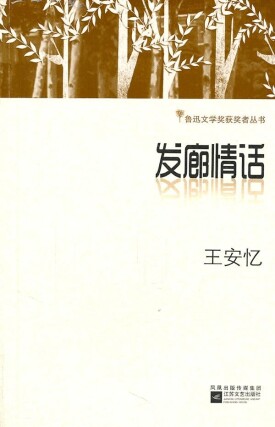髮廊情話
髮廊情話
2003年,王安憶的短篇小說《髮廊情話》發表於其短篇小說集《髮廊情話》。
《髮廊情話》以風塵女子虛實摻夾的情話講述,對世俗人生的一種人情世態作了生動逼真傳神的藝術寫照,但它不僅僅只是“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或者說只是王安憶對上海市民生活眾生相的一種隨意勾勒,更是在於寫實與象徵的結合中所體現出的王安憶認識上的一些東西。語言細膩舒緩、神吹海聊、虛實相生、真假摻夾,生動揭示了上海髮廊的社會意蘊,體現了王安憶小說創作獨特的藝術氣質。
《髮廊情話》的情節並不複雜,在一個蘇北人開的髮廊里,經常有一些閑客,有一天這其中的一個一時技癢,代髮廊的小姐幫客人洗頭,由此開始了自己的人生經歷講述,她在言語之間經常誇耀自己的聰明和氣質,講自己也開過髮廊,賣過百貨、開過餐館,經歷頗為豐富。但她走後,兩個髮廊的小姐在把她的浪漫情話加以重組還原為現實時,卻覺得故事時間與其實際年齡對不上號,正在質疑之時,在故事講述中一言不發靜觀默察的老闆,聲氣言辭極粗暴地吐出一個字“雞”,對女主人公妓女的身份給予揭破,一屋的聒噪戛然而止。
作者曾往白茅嶺的上海勞教農場採訪,翻檢卡片時,發現在好幾個賣淫女的卡片上,都提到同一個人,後來作者從一個女孩子口中得知,那個男人跟她說了一句重要的話:“不要去和年輕的人搞,搞出感情來就麻煩了。”
這句囑咐,包含著情感之道,是在通常認識之外的。好像專針對一些失去愛情的人群,可其實又不止是這人群。這感情處境的複雜性,如此簡約地說出來,確是簡樸的哲學。當然這是市井的哲學,注重現實,而將精神視作無意義的浪費,它多少是苟且的,可是生活不那麼容易,收和支很難平衡,先要保存實力,然後方可再談爭取。
作者一直想為這句話寫一個故事。因這句話畢竟缺乏材料,資源有限,所以這故事不能太重大,但太小了卻又承不住這句話,因這句話的內核還是比較結實的。所以,作者需要一個大小適中的故事,既不能辜負了這門“哲學”,又不能言過其實。而且愛情這個題材很難處理,它很容易滑向傷感劇,所以還輕重適度。
直接促使作者提筆寫這個故事的是因為有一位女作家為了炒作提高自己知名度,為了其妓女文學的系列作品能夠賣得更火,以一副我是妓女我怕誰的氣勢,在報紙、雜誌、網路上對以王安憶為代表的一大批女作家進行連篇累牘的叫罵與喧囂。在做秀炒作的喧囂聲浪尚未絕響之時,王安憶終於以筆為旗,開始了對妓女作家的回擊,以作家的身份和文學的形式來言說文學事端,以她最拿手的小說,以她最熟悉的上海,以她最常描寫的淮海路上的女孩子形象,以《髮廊情話》這篇小說,借“雞插花翎扮鳳凰”的故事,以話語與歷史關係探討構成的象徵隱喻結構,對當前女性文學中存在的問題和一些醜陋現象進行揭示和批判。
從標題上看,很容易將它歸入這些年風靡一時的“打工文學”、“底層文學”的範疇之中。但細讀之後便可發現,《髮廊情話》與有著強烈社會倫理訴求的后兩者大相徑庭。雖然同樣以底層社會的人物為對象,但王安憶關注的並不是這些人物性格、命運以及他們艱難的生存處境,並不想深究深藏其後的社會、倫理意蘊,她醉心的是髮廊里散漫、細碎、近乎原生態的日常生活狀態,髮廊老闆,兩個洗髮的外來妹,一個神秘兮兮的女人,構成了一個狹逼、平淡無奇的小世界。那女人的大段講述構成了小說後半部分的主體,而她滔滔不絕的講述充斥了日常生活的細節,其噯昧的真實身份也只是在結尾處作了暗示。人們可從中覺察到世態人情的變遷,但它難以被化約到社會、政治、歷史的宏大敘事框架之一。
這部小說整體構成了一個巧妙的象徵隱喻系統,其意義和價值不僅止於尺幅興波中反映出的世俗人生,也不僅止於精當獨到的結構安排和語言表達,而在於藉此象徵隱喻表達的言外之旨,話外之音,在於寫實與象徵的結合中所體現出的王安憶認識上的一些東西。它啟示我們跳出故事之外,想到許多用語言粉飾、遮掩、隱瞞真相的人物與舉動,想到那些從字縫裡看出字來的歷史真相的出示者。
綿密的文筆
《髮廊情話》把王安憶綿密的文筆發揮到極致,她對一個髮廊空間的工筆細繪,使整篇小說像是一席浮動的油彩。與此同時,在王安憶的敘述中,體會到的更是一種從容。她幾乎是在不經意間,就把上海一個嘈雜小街上的人心世相講透了。她的文筆是一點點氤氳開來的,似乎是溫吞的,根底卻老辣無比,她甚至只在人物的衣著或一個微小的動作上,就窺視到了他們的各自歷史,他們與這座城市來龍去脈的關係。所以,題目雖是《髮廊情話》,卻彷彿講的是上海市井市民的“風俗史”和“生活史”。在看似隨意的“髮廊閑談”中,令人對這個城市有了精微的了解,似乎看到了那個蘇北的理髮師傅、安徽的洗頭姑娘還有那個有故事的淮海路“氣質”女人。這就是王安憶的小說美學,她不是依賴於爆破性的情節來展示自己敘述的力量,而是通過一種綿密和看似隨意的點染,揮發出一種綿長和耐人尋味的力道和勁道。
這篇小說是作者另一篇小說《小酒館》寫作風格的延續。在這個容量狹小的篇章里,個個人物都受到多角度多層次的精雕細刻,情節跌宕而又柔和,給人嶄新的閱讀感受。
細節的敘述
《髮廊情話》沒有情節,它是由一組組細節所構成的敘事節奏,推動著故事的前進。小說從髮廊的細節寫起,寫到老闆的形象,寫到外來妹的性格,以及理髮的諸種細節,幾乎在小說展開到三分之一以後才出現了一個新的敘述者,這個女人的敘事與作家的敘事幾乎沒有區別,融化一體,以至連標點符號也不引用,一氣呵成。但其所敘述的內容仍然是充分細節化的,而不是情節化,這就是敘述人要在講光頭的故事中途突然轉換話題,插入對老法師的細節敘述,這樣就有效地阻止了情節化的出現。敘述到最後,敘述人與光頭的關係仍然語焉不詳,老闆以過來人的經驗揭穿了敘述者的身份是“雞”,於是才修補起敘述人與兩個男人之間的複雜糾葛。這篇小說當然不是寫一個髮廊女人與兩個男人的故事情節,卻把改革變化中城市下層市民生活信息的場景通過細節歷歷在目地顯示出來。因此也可以說,這是一部關於細節敘述的小說。
從容的敘事
從王安憶的《髮廊情話》,可以看到作者對都市經驗的嫻熟表達,對上海女人的精細觀察,和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上海風”。“髮廊”這種場所,藏在都市的皺褶里,司空見慣,但其人生含量卻也很雜、很豐富,可以品出多種嘴臉、多種活法兒,品出複雜的滋味。王安憶的筆很老到、很從容,最後的“包袱”也抖得妙。一開始,對蘇北老闆的白描就有意思,他雖有鄉下男人的本質,卻又長得有點“艷”,特別是那雙女人樣白和軟的手,“有一種怪異的性感”,是溫水、洗髮精、護髮素、女人的頭髮養護成的。寫髮廊早晨開門前的混濁氣味,也很見描畫的功力。並不理髮的“閑人”們確是一景,那個“女客”遂浮出。全篇幾乎都是那個女客在饒舌,生意經、男女、騙術,還有“老法師”的手段,無所不談,構成一個言語場,跟上網聊天差不多,不妨看作一種奇特的慾望釋放方式。最後隨著對其背影的一個輕蔑的“雞”字,戛然而止,四周清靜下來。也許這作品的缺點是過於流暢,要是能“澀”一點或者更好。
語言藝術
在《髮廊情話》中,王安憶將兩種故事元素混合在一起,一種故事元素是髮廊里這一天的經歷,老闆,兩位小姐,她,還有來來往往的顧客,他們的行為、交流、心態;另一種故事元素是“她”講述的自己曾經開發廊的故事。王安憶侍弄語言到了痴迷的程度,她能捕捉到與生活印象最貼切的詞語、節奏,於是就有了色彩,就有了情調。然而通篇敘述過於冷靜,彷彿有一塊巨大的玻璃窗,將敘述者與敘述對象分隔為兩個世界,敘述者站在玻璃的另一面不動聲色地觀察對方的一言一行,雖然看對象一清二楚,卻感受不到玻璃那邊的情感冷熱。作者把握了“她”在髮廊里的言行的細微末節,從輪廓到色彩都活靈活現地傳達給了讀者,卻無視“她”的內心,所以當小說在“她”是“雞”的判斷中結束時,會令人覺得整篇小說其實是在擺弄“她”的過程,無論“她”是不是“雞”,這樣對待“她”似乎是不妥的。
淮海路的女子的出現與其情話講述,故事的節奏加快,並且敘述的視角聚焦在這個神秘的女子身上,這個女子自我經歷講述的話語和行為構成了故事的主幹。這個自恃資質與智商,淺薄而又極具虛榮心的女子,把妓女的經歷吹噓得如此浪漫和富於傳奇色彩,她的講敘看似無心的隨意閑聊,其實是非常工於心計的,簡短的自述的描繪中會聚了時下暢銷書的多種要素,有女性創業史,有三角戀,有神秘又具個性的人物,有高智商詐騙犯罪。沉迷於故事中的小姐和看客們是難辯真假的,這些都迎合了她們平淡生活中對浪漫傳奇的嚮往,前面描寫的髮廊生活,正是平凡、缺乏激情的,這樣的生活就是為了這種嚮往打下基礎。這種迎合聽眾心理的自傳講述,緊緊地捉住了理髮店裡幾個人,她們被女子精彩的一生吸引,意猶未盡,加入自己的想象,來滿足自己空白的浪漫故事。除了交替出現上述的靜態人物及場景描寫外,就只是對陳舊“事實”的陳述。為了保持這種擺龍門陣似的風格,小說只有描寫和敘述,基本廢除了對話。在髮廊小姐們專心傾聽她的話之時,其中她的話就破綻百出,但是小姐們都很投入在她的故事,她的傳奇的一生,就像小學生聽課,專心致志,然後,都忽略了老闆的反映,她說到緊張之處“老闆在櫃檯里打瞌睡,對她的故事不感興趣的樣子”,這與結尾的老闆的神情,說話互相照應。正是這樣的語言描寫,生動體現了王安憶要寫的目的,講述中一系列的破綻,也為結尾做了鋪墊。
2004年12月27日,第三屆魯迅文學獎頒獎大會在深圳舉行,王安憶的《髮廊情話》被評為短篇小說獎。
《髮廊情話》獲魯迅文學獎時評委的評語:“王安憶的短篇小說重視文體創新,文本意識強烈,是南方語系小說創作的代表之一。《髮廊情話》以白描的手法,自然的風格,看似無法無規的處置,充分表現了作者自由純熟的小說觀念和技巧。作品對底層人群生存現狀的深切關注,體現了作者一貫的人文關懷精神。”
現代哲學學士、編審張啟智:小說以生活的一個斷面為切入點,以“閑人”的閑談為敘述對象,沒有很強的故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