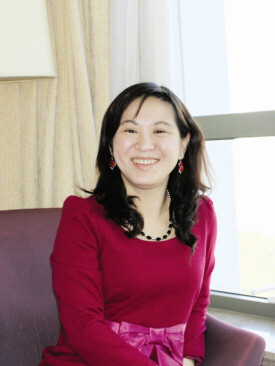葉傾城
中國女作家
葉傾城,原名胡慶雲,作家,1995年開始文學創作,湖北省作家協會會員。國內發行量最大雜誌《讀者》的簽約作家,其作品在諸多的報雜誌中有很高的轉載率。著有《愛是一生的修行》《愛是一種修行》《傾城十年》《情感的第三條道路》《愛與不愛都是事兒》《一杯閑半生愁》等多部散文集,《原配》《心碎之舞》《麒麟夜》等多部長篇小說,獨立編劇的電影《如果愛上我的青春》於2014年上映。“寫作之於我,越來越像一樁宿命,一份天賜的枷鎖,但我願意背負這沉重,直至永遠。”她如是說。為此,她筆耕不輟,期冀有朝一日成為文壇常青樹。
她在自我介紹上說:如果你曾愛過我,你自然知道。如果你不曾,我該如何讓你明白呢。
祖籍湖北黃陂,1972年生於東北小城丹東,長於中南重鎮武漢,長江水浣過發,也濯過足。華中理工大學漢口分院畢業,就職於湖北省政府辦公廳。後來辭去公職,移居北京,先後供職於京華時報、競報、盛大文學。2010年至2011年8月5日任金鷹955子夜車站主持人。
信箱集
《愛或不愛都是事兒》
《一夜傾城》(再版書名為《別糾結,好好愛》)。
長篇小說“傾城之戀系列”
《原配》
《心碎之舞》
《麒麟夜》
散文集
《愛是一生的修行》
《愛是一種修行》
《一杯閑半生愁》
《玲瓏四犯》
《馬不停蹄地錯過》
《玻璃杯里跳舞的天使》
《住在內衣里》
《不要臉要趁早》
《優雅地低於愛情》
《鳳凰於飛》
《煙花雨》
《心靈雞湯中國卷》
《我的百合歲月》
《愛我少一點愛我久一點》
《再多不舍也要勇敢向前》
《孩子,謝謝你選我做媽媽》
長篇散文
《三十八周零四天》
童書
《你好啊,一年級——陶小鯨上學了》
《你好啊,一年級——陶小鯨的笨爸爸》
精選集“傾城十年”系列
《比目思》
《蒼耳心》
《芙蓉錦》
譯作
《誰動了我的乳酪》(兒童版)
《花園裡的沉思》
《走出非洲》
《給媽媽的60張明信片》
編劇
《如果愛上我的青春》

葉傾城
如果,我從不曾向你說過一句又一句沉醉甜蜜的話,你還能不能懂得,我茂林深處一般的心中啊,那湖泊般清澈映落的心事?
如果,你眸中沉默的火我不曾遇見,當我在漆黑的人世間徜徉,會不會知道,你始終在我的身邊,一如日升月落,生生世世?
深冬及其潦草短促的黃昏時分夜色蕭蕭而下,她急著下班,門診卻轉來了病人,是一位白內障的老人,正由老妻攙扶著送來.急切著見那醫院門口佇立等待的男孩,她只草草問幾句,便開出住院通知單,起身:"你跟我去病房。"交待老太太,“到那邊去交費。”
老太太卻不動,只微笑側頭,指指自己的耳朵。老人靜靜開口:“醫生,還是我和她一起去交費吧。我妻子,她聽不見。”她驚愕地抬頭,陡然看見老人一絲不苟的白髮下,面容安詳儒雅,瞳孔卻是灰濛濛的白,黯然無光,彷彿被廢棄的礦坑。他的眼睛,已經死了。他是盲的,而她,是聾的?
消息一如蓮瓣上的風,動蕩的傳遞,病房裡從此多了好奇的眼光。而乍看上去,他們竟如此平常,老人閉目養神,老太太就無聲地忙前忙后,一臉謙和的笑。午後,老太太坐在床沿上,一瓣瓣剝開橘子,細細撕去筋絡,輕輕遞過去,老人總是適時地張開嘴接過。而她,目不轉睛地看著老人咀嚼與吞咽,微笑著,自己也吃一瓣,在將下一瓣橘子喂到老人口裡......
一舉一動間,竟彷彿不是在穿越光明與黑暗、有聲到無聲的崇山峻岭,只如明月山崗,清風大獎,是亘古以來便如此完美契合,不消更動,亦不屑言辭。
而他不能看,她不能聽,要怎樣才能溝通交流,接下命運無窮的招數?一個巨大的謎團,由四隻蒼老的手擁滿,她永遠都猜不透。終有一次她耐不住地問起,老人無光的眼中透出微微笑意:“你以後會明白的。”
那以後,卻也來得太過迅猛,以至於無從反應。一天,她看見老太太提著水瓶從水房蹣跚而出,剛想上前幫忙,卻已有炸裂聲,驚天動地,代替了她自己聽不見的呼喊。老太太僕倒,從此再也不能站起......只無聲地,掙扎著,比劃同一個姿勢:抬起,又萎垂,又抬起,又萎垂,彷彿舞者的謝幕,彷彿瀕死的天鵝,直到越來越虛弱,越來越......沒人懂得手語,卻沒人懂得她的心意:請不要告訴他,請幫我,照顧好他。
而她默默地褪下醫生的白袍,將纖纖素手在水龍頭下洗了又洗,要衝掉所有醫院的氣息。然後靜靜走向老人,坐在她慣坐的位置上,輕輕地,剝開橘子......橘瓣遞到老人唇邊的瞬間,他開口了:"她,我的妻子,怎麼樣了?要不要緊?"忽然地,聽見窗外的綠樹上下不知名的鳥叫得那樣快樂,而老人白色的眼睛痛苦地痙攣著,琥珀融化般流下厚重濁黃的淚。
四十年前,便知道黑暗的不歸路。那年攻關小組幾晝夜的不眠不休后,眼前忽然地一片血紅,隨即死一般漆黑。在醒來雙眼已在繃帶后無人可預期,繃帶拆除后他生命的顏色。他沒有通知鄉下的父母,只獨自躺在小屋裡,從不知黑暗的重量,會這般地,以萬傾之勢壓下,二十二歲的大男孩子,終於,哭了。
突然泛來淡淡的茉莉花香,一雙女性的手,正隔著紗布,輕柔地為他拭淚。他不禁動容,啞聲問:“你是誰?”一無迴音,卻有什麼東西軟軟抵著他的嘴唇,他驚疑地、機械地張開嘴,一瓣染著茉莉花香的橘子甘甜地喂到他嘴裡.....整整七夜,沒有聲音,沒有光,卻有茉莉橘子,日復一日,滋潤他乾枯的喉嚨,是黑暗國度里唯一的安慰與期待。只是,她為什麼從來不對他說一句話呢?
繃帶拆除的剎那,他的雙目渴盼地四處張望,喧嘩的人群里,要到哪裡才能覓到那一瓣清甜的茉莉橘子。
漸漸,連他自己也懷疑不過是一場夢境。卻在無意間,握到了她的手,嗅到她掌心淡淡的茉莉芳香,霎時間,所有的記憶如風雲初起。她只靜靜地抬起頭,深深地與他對視。她是設計院的清潔女工,大地一般寂靜豐美的女子,每天掃地如掃除人生。只是,每天朝夕相處的日子裡,他怎麼從來不知曉她對他的感情?
而原來,從未出口過的愛,彷彿蘊藏在煤里的火焰,以及深埋在地底的河流,是人生的燃燒與奔騰。
她略微悸動。他鬆手,復又緊緊握住,然後拉到自己懷裡,自此,握住一生不變溫柔,不染塵的約誓。
四十年後,老人仍有同樣堅毅的面容,而年輕娟秀的女醫生,肅然起敬。
誰說我的心事必得用言語傾訴,誰說只能用雙眼識出你無雙的容顏?若命運將你我剝奪,如貧瘠沙漠里一棵乾渴的仙人掌,我也會為你盛放一千朵繁花,同時向你綻現,我唯一的美麗。
《安能辨他是雌雄》
今夏在草原。清晨逸馬在希拉穆仁,是我深愛的黑駿馬,微一揚鞭,鞭梢不及馬背,它已飛奔,兩耳聞得風聲颯颯。
靜下來卻走得平穩,偶爾叼一口閑花野草,我與馬倌聊天,“它是公是母?”馬倌答,“都是公的,母馬騎上走不動。”我舉目看看,人家的馬肚下面好大一個話兒,我的馬卻空空如也,莫名便覺不平,“為啥那匹馬有,我的馬沒有?”馬倌笑得金牙在陽光下閃閃放光,“你那匹是閹過的。”
我靠,這臉丟得。
下午陽光酷烈,草原無遮無擋,一望無際盛大的綠。我坐在旗杆下,抱了一頭小白羊,與小孩們聊天。滿懷軟香暖玉,我問,“這羊是公是母呀?”小孩的母親是個中年婦人,聞聲熱情前來,“這不就是俗話說的,要知道你媽是公是母,掀開尾巴一看。”尾巴掀開半晌,我仍不明就裡,婦人幫我指點,“喏,這個是出糞的,這個是出尿的,這是頭小母羊嘛。”我繼續懵懂,“那公羊呢。”婦人駭笑,“公羊的尿從肚子下面走嘛。”大約不信有這種白痴,停停又加一句,“這說得再清楚也沒有了。”此時已笑翻了一地的人。好在日頭毒,人人曬得紅頭赤臉,再加一份緋紅,也看不出。
雌與雄,豈是那麼好辨的?
此行,是經山西去內蒙,到五台山那天正是盂蘭盆節前日,五爺廟外便聽得鼓樂磬鈸,原來是有人還願送戲。舞台一角有個牌子,《潘楊訟》。
在酷日下的園子里,我看向舞台,很吃力地辨認,那描了慘白臉孔,是潘仁美?他們驚他嚇他,而他不過是披髮蒼涼的老人。一個敦實的胖老太太,是佘太君吧?一直掛著一種穩紮穩打、勝算在握的笑容,她驕矜地坐下來,正在八賢王身邊,但輸贏還沒定呢。
自然沒有字幕,我正覺得悶,忽然分花拂柳,上場一個極清俊的小生,劍眉星目,滿面撲粉,腮紅卻紅得柔和,彷彿天然膚色。而盛夏午後的太陽照在我頭上。
我站得那麼近,他的厚底靴,踏踏踏,就在我頭頂上,袍裾微掀,裡面是大紅絲褲。氣宇軒昂,卻線條柔和輕盈。是個女子嗎?我拿不準。
他是誰?楊家將里有這一號?可憐的我,正“楊六郎”、“楊宗保”地亂蒙,皇帝已經喚道,“寇愛卿,”———豈有這麼年輕俊美的寇準。
烈日當頭,幾乎是噴火的龍,毒焰。他們都避到樹蔭下,惟我在舞台的正下方,半痴半迷。寇準在台上忽遇難題,舉重若輕,起了好主意,則眉目一場,嬌憨如好女,又明明有大將之風。我越看越心驚。
山間之戲簡陋著。鬼卒著戲裝就從后場連忙衝出來,大約人有三急,再一刻,已經換了衙役,氣定神閑上場。戲分完了的演員就在不遠處,往臉盆里白花花倒洗衣粉,出那麼多泡沫,七彩妝容浸進去,重手搓出來,一張張樸實憨厚的臉,是一部返璞歸真的戲外戲。
周圍多的是散漫的遊客,亂著拍照,上香,到處閑逛。大家都只是偶爾到此一游吧,想來往後也不大記得五台山,五台山也不大記得我們。我在陽光底下,也是一種暫時的存在。然而我眼中的寇準,那麼美,敷粉胭脂,黑靴紅褲,大義凜然,卻又聰明機巧。他哈哈長笑,我忽然看見酒窩,女子無疑了。
那一刻,我只覺恍惚,彷彿我不是一個遊客,與五台山半日之緣,而是附近鄉野人家的女兒。偶爾趕廟會,燒香許願求一個好人家。在廟裡看了一齣戲,便遇上前生的冤孽。
若他是男子,我會嫁他,洗手作羹,追隨他天涯海角,他是我一生惟一的愛人。若他是女子,我但願與她結拜姐妹,雙棲雙宿直至白首,無論她是否紅顏終改,抑或嫁作平凡人婦,我唯願與她嫁同一個男子……
散戲之後,鄉間有多少不知所蹤的女孩?而所有的美,都是雌雄同體的。
《紙巾上的愛》

葉傾城
一瞬間,她想起了丈夫為她擦淚的紙巾--輕盈而柔軟,淡淡的茉莉清香沁人心脾。
有時,即使是一張紙巾,也可以改變一個人的一生。
婚禮上,她的淚紛紛而下,不只是新娘必有的喜淚。
當初她堅持要舉行的盛大的婚宴,不是沒有一點補償心理的。
他是留美的醫學博士,開一家藥品公司,家財萬貫,學富五車,第一次見面,對她說手術室的笑語,自己笑得“呵呵”地。她也附和地淺笑,可是根本沒聽懂一大堆專業術語。
他對她好。送花,開車送她上下班,帶她去豪華娛樂場所,出資為她出了兩本散文集。但是他自己只翻了幾頁就睡著了。對於他,她始終是高山仰止,敬而遠之。可她周圍所有的人都動了心--這樣的男人不嫁,還要等什麼樣的男人?
她最後還是嫁了,只是淚不由自主往下流。在豪華的賓士車裡,他一路用紙巾細細地為她拭淚,淡淡的茉莉清香籠了她一臉。
安逸的日子裡,她想起了那個男孩。
是在一次筆會上認識那個男孩的。第一個晚上,月光潑潑濺濺得滿山都是。她倚著靠山的欄桿,把自己放在月光里去,聽著遠遠舞會裡的舞曲人聲。這時,聽見他從她身邊走過,停一停,低低吟了一句:“幾處吹茄明月夜。”她驚得直起身來:莫非他聽得見她心裡的聲音?
他們以後就總是這樣:一句話,她說了上半句,他便很自然地接觸了下一半。筆會結束后,他們回到了各自的城市,卻仍舊藉助電話與郵遞員,談詩說文,談天說地,然後談情說愛,終至於--談婚論嫁。
不自覺地將男孩的信揉成了一團,她整個人都愣住了。也許,她一直都知道有這樣的結果,只是……她看見丈夫在電腦前專註的身影,已經開始了中年的微胖--他怎麼辦?
男孩不斷地催問。每次見到男孩,她都下決心回家后立刻對丈夫攤牌。可是,怎麼說出口?他對她,一直是那麼好。
她在時間裡煎熬,思緒紛亂如風起時的槐花:進,或者退?離婚或不離婚?他們再見面的時候,男孩追問的聲音越來越大。她想起自己的諸般委屈,不由得就落了淚。
男孩慌了,翻遍全身才摸出一張紙巾遞給她。
那紙顏色灰濛濛的,紋理粗枝大葉,捏在手裡,堅硬粗糙,一看就知道是自由市場上論斤稱賣的。
她想起他為她拭淚時那帶著淡淡的茉莉清香的紙巾,柔軟細膩而輕盈,仿如他給她的日子:舒適的,溫存的,清潔的。如果不是遇上他,她不可能在兩年內連出兩本書,也不可能至今還保留了一份少女不諳世事的純凈,她想起他的豪華私家車和那些與男孩在寒風凜冽的街頭等末班車的深夜;他的建伍音響和男孩要經常拍一拍才會響得“隨身聽”……男孩給了她愛情,他卻給了她一個女人一生中差不多最為重要的東西:安全感。
不知不覺地,她的淚止住了,她將男孩的紙巾還給了他,靜靜地說:“我自己有。”
她後來還是會常常地想起男孩,可是一次也沒有後悔過自己的選擇:如果,感情和生活的品質,一個是玫瑰,另一個是每天必吃的一把青菜,那麼,她只能選擇後者。
只是,那一天,男孩遞過來的,為什麼會是那麼低劣的一張紙巾呢?
《永不縮回雙手的父親》
幾年前,武漢發生了一起火車汽車相撞的事故。
一輛早班的公共汽車擱淺在一個無人看守的道口,駕駛員下車找水去了。是農曆正月,天寒地凍,十幾名乘客都舒舒服服地呆在還算暖和的車廂里,誰也沒有想到大禍的將臨。
沒人留意到火車是幾時來的,從遠遠的岔道。只能說,是呵氣成霜的車玻璃模糊了眾人的視線,而馬達的轟鳴和緊閉的門窗又隔絕了汽笛的鳴響。當發覺的時候,頃刻間,一切已經停止了。
——一切都停止了,卻突然間爆發出孩子的哭聲。
那是一個大概兩三歲的小孩子,就躺在路基旁邊一點點遠的地方,小小整潔的紅棉襖,一手揉著惺忪的眼睛,還不知發生了什麼事,只一味哭叫:“爸爸,爸爸……”
有旁觀者說,在最後的剎那,有一雙手伸出窗外,把孩子拋了出來……
他的父親,後來找到了。他身體上所有的骨頭都被撞斷了,他的頭顱被擠扁了,他滿是血污與腦漿的衣服看不出顏色與質地……是怎麼認出他的呢?
因為他的雙手,仍對著窗外,做著拋丟的姿勢。
好幾年前的事了,早沒人記得他的名字,只是,在經過這個道口的時候,還會有人指指點點:“曾經,有一個父親……”
還有,那個孩子現在長大了嗎?
很久很久以前,中原一戶農家有個頑劣的子弟,讀書不成,反把老師的鬍子一根都拔下來,種田也不成,一時興起,把家裡的麥田都砍得七零八落。每天只跟著狐朋狗友打架惹事,偷雞摸狗。
他的父親,一位忠厚的庄稼人,忍不住呵斥了他幾句,兒子不服,反而破口大罵,父親不得已,拎起菜刀嚇唬他,沒想到兒子衝過來搶過刀子,一刀揮去。
老人捧著受傷的右手倒在地上,鮮血淋漓,痛苦地呻吟著。而鑄成大禍的兒子,竟連看都不看一眼,揚長而去。
從此生死不知。正是亂世,不知怎的,兒子再回來的時候,是將軍了。起豪宅,置美妾,多少算有身份的人,要講點面子,遂也把老父安置在後院。卻一直冷漠,開口閉口“老狗奴”,自己夜夜笙歌,父親連想要一口水喝,也得自己用殘缺的手掌拎著水桶去井邊。
鄰人都道:“這種逆子,雷怎麼不劈了他?”
許是真有報應這回事吧。一夜,將軍的仇家尋仇而來,直殺入內室,大宅里,那麼多的幕僚、護衛、清客,逃得光光的,眼看將軍就要死在刀光之下。突然,一個老人從後院沖了進來,用唯一的、完好的左手死死地握住了刀刃,他的蒼蒼白髮,他不顧命的悍猛連刺客都驚了一下,他便趁這一刻的間隙大喊:“兒啊,快跑,快跑……”
自此,老人雙手俱廢。
三天後,逃亡的兒子回來了。他徑直走到三天不眠不休、翹首期盼的父親面前,深深地叩下頭去,含淚叫了一聲:“爹——”
一刀為他,另一刀還是為他,只因他是,他的兒子。
《母親的心》
朋友告訴我:她的外婆老年痴獃了。
外婆先是不認識外公,堅決不許這個“陌生男人’上她的床,同床共枕了50年的老伴只好睡到客廳去。然後外婆有一天出了門就不見蹤跡,最後在派出所的幫助下家人才終於將她找回,原來外婆一心一意要找她童年時代的家,怎麼也不肯承認現在的家跟她有任何關係。
哄著騙著,好不容易說服外婆留下來,外婆卻又忘了她從小一手帶大的外孫外孫女們,以為他們是一群野孩子,來搶她的食物,她用拐杖打他們,一手護住自己的飯碗:“走開走開,不許吃我的飯。”弄得全家人都哭笑不得。
幸虧外婆還認得一個人廠--朋友的母親,記得她是自己的女兒。每次看到她,臉上都會露出笑容。叫她:“毛毛,毛毛。”黃昏的時候搬個凳子坐在樓下,嘮叨著:“毛毛怎麼還不放學呢?”--連毛毛的女兒都大學畢業了。
家人吃准了外婆的這一點。以後她再要說回自己的家,就恫嚇她:“再鬧,毛毛就不要你了。”外婆就會立刻安靜下來。
有一年國慶節,來了遠客,朋友的母親親自下廚烹制家宴,招待客人。飯桌上外婆又有了極為怪異的行動。每當一盤菜上桌,外婆都會警覺地向四面窺探,鬼鬼祟祟地,彷彿一個準備偷糖的小孩。終於判斷沒有人注意她,外婆就在眾目睽睽下挾上一大筷子菜,大大方方地放在自己的口袋裡。賓主皆大驚失色,卻又彼此都裝著沒看見,只有外婆自己,彷彿認定自己幹得非常巧妙隱秘,露出歡暢的笑容。那頓飯吃得……實在是有些艱難。
上完最後一個菜,一直忙得腳不沾地的朋友的母親,才從廚房裡出來,一邊問客人“吃好了沒有”,隨手從盤子里揀些剩菜吃。這時,外婆一下子彈了起來,一把抓住女兒的手,用力拽她,女兒莫名其妙,只好跟著她起身。
外婆一路把女兒拉到門口,警惕地用身子擋住眾人的視線,然後就在口袋裡掏啊掏,笑嘻嘻地把剛才藏在裡面的菜捧了出來,往女兒手裡塞:“毛毛,我特意給你留的,你吃呀,你吃呀。”
女兒雙手捧著那一堆各種各樣、混成一團、被擠壓得不成形的菜,好久,才愣愣地抬起頭,看見母親的笑臉,她突然哭了。
疾病切斷了外婆與世界的所有聯繫,讓她遺忘了生命中的一切關聯,一切親愛的人,而唯一不能割斷的,是母女的血緣。她的靈魂已經在疾病的侵蝕下慢慢地死去,然而永遠不肯死去的,是那一顆母親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