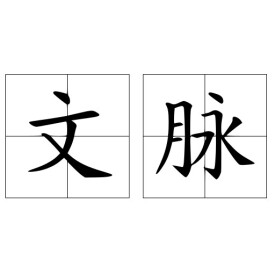文脈
文脈
文脈拼音:wénmài。文章的線索;文脈——城市記憶的延續。
在風水學上,“文脈”為龍脈的一種,是負屓之魂,屬文曲昌興之象。廣義龍脈曰為山川之勢(五峰三脈),狹義龍脈則有文武之別——文魂秦嶺(陝西九龍山)、武德鳳陽(安徽)。伏羲魂化九龍、真身遊歷天下,所遺百峰,皆為龍脈。從廣義上說,只要水、土、光照等幾大要素十足俱全、山勢整形,便可稱為“龍”,但真正具有靈性的,全國只存三條;具有文魂武德的,則僅有此兩處。因為真脈存量過於稀少、無法普及應用,故歷代風水學家普遍認同只要山勢起伏得當,便可算作龍脈的說法。
文脈是指介於各種元素之間的對話與內在聯繫,指局部與整體之間對話的內在聯繫。
另一種“文脈”定義:華夏文明發源的脈絡。此文脈起源於兩河流域,現今“文化龍脈”與“風水文脈”唯一併存完好的區域在陝西戶縣(夏代古國扈氏,今屬西安市),其餘“雙標準”的文脈由於歷史變遷,均已名存實亡(只存文化沿襲的居多,實體脈絡已破壞殆盡)。有許多學者,不斷呼籲暫緩“將一切風水學說視同迷信”的觀點,建議在保存歷史“習俗”的前提下,盡量避免進行毀滅性的大規模現代化開發——僅存的秦嶺九龍山文脈也已被開發為公墓,所幸沒有進行大規模人工改造,而是完全依照原始地表形態建設的風景區級公墓,使“華夏文脈之宗”得以儘可能的保留,當屬不幸中的萬幸。
簡介
一些有意義的傳統生活場景被破壞,城市也因此失去了自己的特色,歷史形成的街道、衚衕、牌坊、宗教聖地等等城市形態作為完整表達建築和城市意象的文脈,被成片、成街、成坊地拆除,威脅到城市形態的相容性和延續性。難道我們的城市發展到只有依靠一張張發黃的老照片去尋找那曾經的記憶不可了嗎?其實,“立新”不必“破舊”,尊重歷史傳統並不等於食古不化、拘泥於傳統。相反,有意識地保留這些傳統文脈,將使得這個城市更富有地方風味。
文脈與城市
文脈(Context)一詞,最早源於語言學範疇。它是一個在特定的空間發展起來的歷史範疇,其上延下伸包含著極其廣泛的內容。從狹義上解釋即“一種文化的脈絡”,美國人類學艾爾弗內德·克羅伯和克萊德·克拉柯亨指出:“文化是包括各種外顯或內隱的行為模式,它借符號之使用而被學到或傳授,並構成人類群體的出色成就;文化的基本核心,包括由歷史衍生及選擇而成的傳統觀念,尤其是價值觀念;文化體系雖可被認為是人類活動的產物,但也可被視為限制人類作進一步活動的因素。”克拉柯亨把“文脈”界定為“歷史上所創造的生存的式樣系統。”
城市是歷史形成的,從認識史的角度考察,城市是社會文化的薈萃,建築精華的鐘集,科學技術的結晶。英國著名“史前”學者戈登·柴爾德認為城市的出現是人類步入文明的里程碑。對於人類文化的研究,莫不以城市建築的出現作為文明時代的具體標誌而與文字、(金屬)工具並列。對於城市建築的探究,無疑需要以文化的脈絡為背景。由於自然條件、經濟技術、社會文化習俗的不同,環境中總會有一些特有的符號和排列方式,形成這個城市所特有的地域文化和建築式樣,也就形成了其獨有的城市形象。
隨著時代的前進,科學技術的進步和文化交流的頻繁,城市的形象可能帶來走向趨同的一面,文脈又讓我們不時從民族、地域中尋找文化的亮點,如果我們對城市歷史建築僅僅處於維持狀態,它仍像一個僵化的軀殼,它的光輝只會逐漸地減損、消失,這種保護也只是維持一種自然的衰敗,實際上我們可以採用一種積極變換角度的思維過程——在歷史環境中注入新的生命,賦予建築以新的內涵,使新老建築協調共生,歷史的記憶得以延續。
文脈與後現代建築
對文脈問題的認識,早已有之,並可以追溯到前工業時代甚至古希臘時期。文脈思想真正被正式提出,還是20世紀60年代以後的事,是隨著後現代建築的出現而出現的。
後現代建築注意到現代主義建築和城市規劃過分強調對象本身,而不注意對象彼此之間的關聯和脈絡,缺乏對城市文脈的理解。建築上表現為:國際式風格千篇一律的方盒子超然於歷史性和地方性之上,只具有技術語義和少量的功能語義,沒有思索回味的餘地,導致了環境的冷漠和乏味,致使工業城市陷於一片混亂之中。為此,後現代建築試圖恢復原有城市的秩序和精神,重建失去的城市結構和文化,從理論到實踐積極探索城市設計和建築設計新的語言模式和新的發展方向。他們主張:從傳統化、地方化、民間化的內容和形式(即文脈)中找到自己的立足點,並從中激活創作靈感,將歷史的片段、傳統的語彙運用於建築創作中,但又不是簡單的復古,而是帶有明顯的“現代意識”,經過擷取、改造、移植等創作手段來實現新的創作過程,使建築的傳統和文化與當代社會有機結合,並為當代人所接受。
在此提到後現代主義,只不過是想從建築語言的角度把後現代主義建築的本質認知引入對城市記憶延續的思考中,借鑒後現代主義思潮背後由時代性和地域性所確定的處理問題的思維方式和具體方法,結合我們身邊以有的成功實例,使它有效地參與當代城市建設的重構中。
文脈的繼承與創新
繼承與創新之間的關係問題多年來一直是設計關注的焦點。其實,從語言學的觀點看,這一矛盾就是語言的穩定性和變易性之間的矛盾。作為設計者在形式設計上的得失成敗取決於所掌握“辭彙”的豐富程度和運用“語法”的熟練程度。設計者要想使自己的作品能夠被他人真正理解,就必須選擇恰當的“詞”並遵守一定的“語法”。但這並不意味著設計者只能墨守成規,毫無個人的建樹。設計者巧妙地運用個別新的符號,或者有意識的改變符號間的一些常規組合關係,創造出新穎動人的作品,這也就是設計上的創新。
擷取
城市要發展,就會有新的建築產生。然而在“辭彙”和“語法”趨於統一的態勢中,文脈可以讓我們不時從傳統化、地方化、民間化的內容和形式中找到自己文化的亮點。一個民族由於自然條件、經濟技術、社會文化習俗的不同,環境中總會有一些特有的符號和排列方式。就像口語中的方言一樣,設計者巧妙地注入這種“鄉音”可以加強環境的歷史連續感和鄉土氣息,增強環境語言的感染力。上海的金茂大廈就是從傳統中提取滿足現代生活的空間結構。金茂大廈塔樓平面雙軸對稱,提煉“塔”的形意,外形柔和的階梯韻律,勾出了剛勁有力的輪廓線。其應用高技術手段來表現的中國古塔的韻律是那麼的惟妙惟肖避開了從形式、空間層面上的具象承傳,而從更深層的文化美學上去尋找交融點,用技術與手法來表現地域文化的精髓。從建築布局和細部處理等多個方面都可以看到一些傳統建築形態語言運用與變異,在現代物質技術條件下擁有了新的活力。在此我們可以將其看成是對傳統文脈的發展。
移植
新建築的產生難道就必須付出舊建築消亡的代價嗎?其實,“立新”不必“破舊”,關鍵在於如何將簡約而又複雜的語義,以傳統而又時尚的語構,運用於現代藝術設計中,從而創造出個性化、人文化的全新設計符號。 “新天地”項目是位於上海市興業路黃陂路、中共一大會址的周邊地區。“會址”對面的南地塊,設計為不高的現代建築,其間點綴一些保留的傳統建築,與“會址”相協調。而“會址”所在的北地塊,則大片地保留了里弄的格局,精心保留和修復了石庫門建築外觀立面、細部和里弄空間的尺度,對建築內部則作了較大的改造,以適應辦公、商業、居住、餐飲和娛樂等現代生活形態。設計師在此只不過象醫生一般將新“的器官”移植給“垂死的軀體”使其獲得新生。其實,在上海這個東西方文化衝擊的大都市裡,傳統的里弄生活形態從來沒有死過,“新天地”給予它的只是合理的變化和延續,留給我們的是更多的思索與啟示。
改造
在人們對習以為常的事物難以引起足夠的注意和興趣情況下,將一些常見的符號變形、分裂,或者把代碼編製順序加以改變,就可以起到引人注目、發人深省,加強環境語言的信息傳遞的作用。符號像文字語言一樣,既根於往昔的經驗,又與飛速發展著的社會相聯繫,新的功能、新的材料、新的技術召喚著新的思想。怎樣使環境既具有歷史的連續性,又適應新時代的要求?粵中造船廠舊址或許可以告訴我們些什麼。在舊造船廠到公園的質變過程里,設計師首先保留了如:多個不同時代的船塢、廠房、水塔、龍門吊、鐵軌、煙囪等歷史的與時間的積澱,然後進行修飾和改造,包括增或減的設計,最後以創造新的語言和形式,更藝術地顯現作為城市記憶的舊船廠近半個世紀的經歷,更充分的滿足了作為公園的新的功能要求。或許當你游弋於中山岐江公園感受到的不僅僅再是設計師對公園的規劃的處心積慮,或許更多的是那段可歌可泣的城市精神的再生。粵中造船廠熱火朝天為革命的場景精神在重現,城市記憶在發展中延續。
簡介
城市記憶的延續,對於設計師來說是建築創作中富有挑戰意義的命題。這項工作不僅僅意味這要探究歷史而且意味著在歷史環境中注入新的生命。形式的模仿是以新的形式的自我消失來獲得協調,但新形式的自我消失並不意味著對歷史的尊重。歷史遺留下來的舊建築的價值在於它距當今時代的時間。形式的模仿只能含糊或抹殺時間,沒有時間差也就無所謂價值得體現。環視一下我們周圍的現狀,不乏“地道式模仿”、“改良式模仿”以及“符號的演義”等眾多作品,這些作品中,新的設計喪失了自身的形式特點,協調被看成創造的目的,而模仿幾乎成為獲取協調的必由之路。面對現實深感我們在傳統建築的保護與更新和在傳統環境中添加新建築設計中應該加強三方面的探討。
首先是對符號的意義和功能的思考
一般來說,在文化活動中人們所受到的限制是符號方面的限制,不是人們駕馭符號,而是符號駕馭人。而所謂精通文化,在符號層面上起碼應該做到嫻熟地操作構成該文化符號系統而不是符號本身,並把新的經驗和見識編織到符號中去。其實符號本身也在發生變化,而有關文化的繼承和革新的奧秘就在這變異之中。
其次是對現代建築語言的深刻認識
現代建築語言是基於建築設計的理論和建築材料及手段為基礎的空間語言。它的形式語言不是符號,而是建構建築形體和空間的手段。成熟的設計行為必定有深厚的理論基礎支持,就新老建築協調而言,首要的任務是剖析歷史,知識是對已定論的建築事實的認知包括歷史文化,因此涉及歷史建築的創作必須是再認識歷史的過程,重新尋求空間、環境、技術概念等不和協因素間可對話的媒介,以本質新與舊的統一作為出發點開拓共生的理念,共生不僅能最大限度地真實地保留舊建築,同時利用新設計中的現代材料及手段的對比,更大限度地用時間差來表現老建築悠久的歷史,城市的文化。
記憶的延續不是依靠某一人或一部分人的努力就得以延續的,還需要靠全民的共同創造,我們需要思考的不僅僅再是建築或城市本身,而是超越建築物質本身的需要,創造能產生共鳴的精神世界——文化,這或許建築設計的最終目的。
現代化是否一定以切斷歷史為代價?徹底地破舊立新是否就是現代化建設的標誌?新的城市建設是否一定不能容忍舊建築的存在?我們在追求現代化的同時是否真的不在需要看到歷史的遺存?人的生命需要相同的血脈得以延續,城市的延續也需要其獨有的“血脈”使其永生。我們的城市在進步的同時已經丟失了太多的東西,我們不能留給後人一個被切斷的歷史。這需要我們投入更多的思考,在歷史文脈中注入新的生命,賦予城市以新的內涵,歷史的記憶得以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