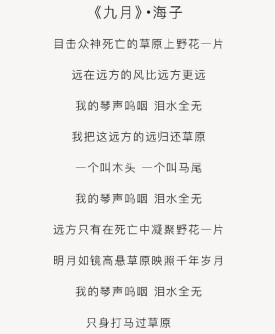共找到21條詞條名為九月的結果 展開
九月
海子寫的詩歌
《九月》是海子寫於一九八六年的一首詩歌,它以充滿神秘色彩、閃爍神性光芒的意象和獨具特色的語言構造,對所述事物進行了詩性的言說與燭照。
目擊眾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
遠在遠方的風比遠方更遠
我的琴聲嗚咽 淚水全無
我把這遠方的遠歸還草原
一個叫馬頭 一個叫馬尾
我的琴聲嗚咽 淚水全無
遠方只有在死亡中凝聚野花一片
明月如鏡高懸草原映照千年歲月
我的琴聲嗚咽 淚水全無
隻身打馬過草原
註:海子原詩為“一個叫馬頭,一個叫馬尾”。而張慧生作曲,周雲蓬演唱的歌曲版本為“一個叫木頭,一個叫馬尾”。(參見“九月”詞條之義項名:“周雲蓬演唱歌曲”)

海子
應該說,此時的海子思想上是相對較成熟的,對於世界、生存、死亡、時間與空間等已經建立了一套屬於自己的認識框架。這首詩就是詩人思考的結果,認識的反映,它以充滿神秘色彩、閃爍神性光芒的意象和獨具特色的語言構造,對上述事物進行了詩性的言說與燭照。海子受存在主義哲學的影響是很深刻的,從存在主義哲學出發自然就可以解開海子詩歌中的重要思想環節。
“目擊眾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詩歌一開頭就將讀者牽引到一個充滿神秘氛圍的情景之中,在這裡,渺遠的時間與曠闊的空間扭結糾纏在一起,生命與死亡在互相詮釋。“目擊”一詞別有意味,它表示了詩人入思的起點,“目擊”的不是“眾神死亡”,而是“野花一片”,是草原上的一派生機,“野花”是草原的此在,作為草原此在之在的“野花”倚靠在“眾神死亡”之上,因此,“野花”的存在是向死之存在,抵達著存在的本質。“眾神死亡”儘管不是詩人“目擊”所見,但它是詩人“以神遇”而不是“以目視”獲得的。從現實的層面上來說,眾神“死亡”是一個並不通順的邏輯搭配,死亡總是與生存相連在一起的,因為眾神從來沒有生存過,所以無從談其死亡。不過,從另外的思路來看,眾神的生存確實發生過,眾神與人類的照面意味著人類已經懂得從現實中超逸出來,思向永遠和終極。這樣,“眾神死亡”在此表明人類歷史之久長,人類與神靈的會晤開始出現中斷。眾神在草原上的“死亡”將草原的遠古與神秘驀然藏匿,草原的深邃歷史遁入無形,草原因此就讓人頓生遙遠之感。
目擊眾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
遠在遠方的風比遠方更遠
“風”是海子喜歡歌詠的事物,在海子眼裡,“風”總是親切而貼近的。在組詩《母親》中,詩人說“風很美”、“風 吹遍草原”;在《黃金草原》中,詩人說“風吹來風吹去”的當兒,女人“如星的名字”或者羊肉的腥香令人沉醉。可是“風”遠在遠方時,為什麼會比遠方更遠呢?很顯然,“遠在遠方”中的“遠方”並不是一個純實在的概念,而是虛實相間,是歷史與現實的交融;也不是一個純空間的指向,而是時空並指。時間和空間都是無邊無際無始無終的,時空的無邊無際無始無終常常令現實生存中的人們感到悵然。作為遠方之處隱隱約約似有似無的事物,“風”的存在更令人難以捉摸。風的漂浮不定,風的來去無蹤,都增加了遠在遠方的空間之空洞感和時間之虛無感。遠方的風因此存在於我們的視線之外,感覺之外,所以顯得比遠方更遠。
我的琴聲嗚咽淚水全無
我把這遠方的遠歸還草原
一個叫木頭一個叫馬尾
我的琴聲嗚咽淚水全無
“我”的出現再次標明了詩人的在場,直接啟用“我”來現身,較之開頭的“目擊”而言,更強調了詩人的主體介入,主體進入事物內部,開始領會和解釋。“作為領會的此在向著可能性籌劃它的存在。”“領會的籌劃活動本身具有使自己成形的可能性。我們把領會使自己成形的活動稱為解釋。”
詩人領會到什麼?他又如何在解釋?詩人的領會其實是一開始就發生了的,當他“目擊”到諸般物象時,他就開始思入世界,開始領悟其間的真髓,開始追尋自我在此間的可能性存在。“我的琴聲嗚咽淚水全無”,這是對領會的傳達,是對自我心靈律動的解釋。且不說“琴”與“情”相諧雙關的慣常表達策略,單這琴聲的“嗚咽”就足以讓人心動不已。“琴聲嗚咽”,將琴聲人格化,人格化了的“琴聲”傾訴著人的情感與情緒,從詞義上分析,“嗚咽”是低低的哭泣,較之“放聲號啕”,它更言說著內心的痛楚以及對這種痛楚的隱忍。“嗚咽”的琴聲已經將詩人的諸般情感一應牽帶而出,詩人情感表達的方式從而變得更含蓄和隱晦,不再有任何錶面的身體語言,所以詩人說“淚水全無”。
“我把這遠方的遠歸還草原”,重新述說了詩人與草原之間的空間關係。在人類生存境域中,時間與空間的經緯交織成人的此在,卡西爾曾經說過:“空間和時間是一切實在與之相關聯的構架。我們只有在空間和時間的條件下才能設想任何真實的事物。”詩人之所以要將遠方之遠“歸還草原”,意在表明自己從草原這個神秘空間的退場,不入住和佔有此間,不與草原發生內在的空間關係,神聖草原因為沒有“我”的侵佔而相對於“我”來說得以完整,“我”因為沒有入住草原並沉迷於神秘之間而將草原的神秘性永遠存放到想象之中。
因為草原的神秘幽遠被保持到想象之中,草原在“我”的視野上從此“缺席”,草原的空闊退隱之後,手中的事物開始鮮明呈現。這鮮明呈現出來的事物是什麼?是“木頭”,是“馬尾”。木頭和馬尾的出場,將草原的歷史帶走又將草原人的歷史帶來,“木頭”和“馬尾”組合成的馬頭琴,是一個民族情感的凝聚、智慧的結晶與生命的象徵。在馬頭琴上的木頭和馬尾不再是原初形態的木頭和馬尾,已經同人類的歷史、人類精神生活聯繫在一起,它們有點像海德格爾描述的那雙破損的鞋具,確實海子讓海明找的那雙馬尾鞋,就等於九月演唱著一樣,開始去卻其作為器具的有用性,直接敞現存在本身。
看看海德格爾對這個破損鞋具的描述吧:“從鞋具磨損的內部那黑洞洞的敞口中,凝聚著勞動步履的艱辛。這硬邦邦、沉甸甸的破舊農鞋裡,聚積著那寒風陡峭中邁進在一望無際的永遠單調的田壟上的步履的堅韌和滯緩。皮製農鞋上粘著濕潤而肥沃的泥土。暮色降臨,這雙鞋在田野小徑上踽踽而行。在這鞋具里,迴響著大地無聲的召喚,顯示著大地對成熟穀物的寧靜的饋贈,表徵著大地在冬閑的荒蕪田野里朦朧的冬眠。這器具浸透著對麵包的穩靠性的無怨無艾的焦慮,以及那戰勝了貧困的無言的喜悅,隱含著分娩陣痛時的哆嗦,死亡逼近時的戰慄。這器具屬於大地,它在農婦的世界里得到保存。”在海德格爾這段富有詩意的描述里,我們看到了鞋具與農人生命的粘連。海子筆下的“木頭”“馬尾”也與那鞋具一樣,同草原人的生活與生命密切粘連在一切,不可分離。在木頭和馬尾交合而成的馬頭琴不斷的傾訴中,草原人的歷史得以留存。
第二節詩人再次凝視遠方,對它作出尋思,“遠方只有在死亡中凝聚野花一片”,這裡涉及到死亡與生存的關係問題。海德格爾指出:“死作為此在的終結乃是此在最本己的、無所關聯的、確知的、而作為其本身則不確定的、不可逾越的可能性。死,作為此在的終結存在,存在在這一存在者向其終結的存在之中。”
海德格爾言說死亡其實就是在言說生存,他強調生存是向死的存在。在這個意義上說,遠方的存在也是面向死亡的存在,而作為遠方在死亡中凝聚的生命形態,這裡的“野花”攜帶的意蘊是豐厚的,它不再只是第一節中那個存在於現實中的具體實在的物象,而是更多的呈現著象徵意味。野花的馥郁馨香與勃勃生機是由死亡賦予的,由遠方廣漠的死亡所凝聚而成的野花是一種精神性的存在,它是不死的。所謂不死的事物是抽空了時間與空間的事物,或者說是時間與空間永遠凝固著的事物。時間與空間在什麼情形下會被抽空呢?或者時間與空間什麼狀態下會永遠凝固呢?只有當一種物質積聚為一種精神,或者沉澱為一種文化時才有可能。因此,這不死的野花就是草原文化的隱喻,或者說就是草原精神的象徵。
遠方只有在死亡中凝聚野花一片
明月如鏡高懸草原映照千年歲月
我的琴聲嗚咽淚水全無
隻身打馬過草原
在詩人對明明如鏡的皓月映照草原和千年歲月的描述中,我們再次被帶入到闊大的空間和悠長的時間之中,而闊大空間與悠長時間的寫照,再度引發詩人無端的愁緒與感嘆,詩人不禁又一次重複地表白了“琴聲嗚咽,淚水全無”的情感態度。詩歌的最後一句實屬神來之筆,“隻身打馬過草原”,看似輕輕的一筆帶過,卻是語重千鈞,蘊意豐富,作為草原上的一個匆匆過客,詩人在這裡領悟到時空的無垠和人生的渺然,感覺到世間蘊藏的宗教意味的高遠和哲理玄思的深邃,面對這一切,他想說什麼呢?他又能說什麼呢?也許一個存在主義者面對世界的最基本態度就是聆聽,因為“本真的言說首先是聆聽”,而且“唯有所領會者能聆聽”,在聆聽和領會之後,詩人才發出了“琴聲嗚咽淚水全無”的深切喟嘆。
在前述中,我們從存在主義哲學的視角出發,對海子《九月》一詩作了詳細的讀解。不過,海子在草原之上寄寓的沉思並非純然是存在主義的,從他對邈遠時間與曠闊空間的無限感慨中,我們似乎讀到了陳子昂似的感時傷逝的古典情懷。當海子“隻身打馬過草原”,發出“目擊眾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明月如鏡高懸草原映照千年歲月”的歌吟時,我們依稀讀到了“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的嘆惋;而面對“琴聲嗚咽淚水全無”的詩句,我們又怎能不聯想到“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的傷感呢?事實上,感時傷逝是中國古代文人騷客的一致之思,從孔夫子的“逝者如斯夫”(《論語·子罕》),到曹子建的“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贈白馬王彪》),到李太白的“生者為過客,死者為歸人。天地一逆旅,同悲萬古塵”(《擬古十二首》之九),再到蘇東坡的“世路無窮,勞生有限,似此區區長鮮歡”(《沁園春》),多少詩人用他們手中的筆撰寫出了關於時光易逝、人生短促的感嘆。海子也加入到這個行列之中,只不過他在傳統詩思中添設了存在主義的哲學意味,他又在存在主義哲學思想中摻雜了中國傳統的詩思,他的詩歌體現出存在主義與傳統詩思的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