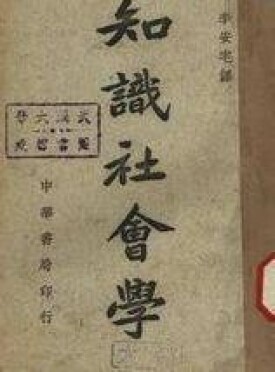知識社會學
知識社會學
研究知識或思想產生、發展與社會文化之間聯繫的一門社會學分支學科。又稱思想社會學。1924年,德國社會學家M.舍勒在《知識社會學的嘗試》一書中首先使用“知識社會學”的名稱。這裡的“知識”一詞的含義包括思想、意識形態、法學觀念、倫理觀念、哲學、藝術、科學和技術等觀念。知識社會學主要是研究思想、意識形態與社會群體、文化制度、歷史情境、時代精神、民族文化心理等社會文化之間的聯繫,或者說是研究這些社會文化因素如何影響思想和意識形態的產生和發展。
(sociology of knowledge)
知識社會學的產生和發展,是社會學本身發展的結果,同時也是社會學轉向研究意識形態的發展與社會文化的聯繫的結果。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失敗后,出現了社會文化、思想、意識形態的危機,一些社會學家轉而研究人類歷史的不同時期、不同種族和民族的思想、意識、精神的發展,研究各種思想、意識形態的發展與社會文化的聯繫。這種研究最初可見於社會學家M.韋伯論宗教與社會現象的關係、W.桑巴特論資本主義發展與社會現象的聯繫。
在《社會學與世界觀》(1923~1924)、《知識社會學的嘗試》、《知識方式與社會》(1926)等著作中,論述了知識或思想與社會生活的關係。他把知識劃分為解脫的、教養的、事業的 3種類型,認為知識或思想都是社會生活的產物,要研究它的產生和發展,就應分析它與社會群體之間的聯繫,說明何種社會群體產生何種思想、某種思想為什麼得以發展。
是繼舍勒之後對知識社會學的研究貢獻最大的人物之一。他著有《意識形態與烏托邦──知識社會學導論》(1929)、《重建時代的人與社會》(1940)、《知識社會學論文集》(1952)等。他強調要研究思想史上各種變動著的觀念、知識對於思想發展的影響和作用。他分析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的官僚保守主義、歷史保守主義、自由民主思想、社會主義、法西斯主義五種政治思潮,認為這些都是在不同社會群體生活實踐中產生的思想或知識,是社會群體歷史經驗的集合。社會群體的生活形式不同,對世界的認識和解釋也不同,但作為知識或思想都有共同的假定。曼海姆認為,知識社會學的任務就是對思想的形成、發展、變化及各種觀念的相互依賴關係進行有控制的經驗研究,找出意識形態與社會群體的聯繫,然後由經驗研究上升到認識論高度,探討思想意識反映社會存在的真實程度,確定思想意識與社會存在的關係及其結構,建立起檢驗知識或思想的正確標準。他所說的社會存在,主要指知識或思想以外的其他社會文化因素,包括階級、社會地位、職業群體、代際關係、生產方式、權力結構、歷史情境、競爭、衝突、流動,以及價值觀、世界觀、社會思潮、時代精神、民族精神、文化心理等。
是知識或思想存在的基礎、知識或思想存在的形態和存在的關係。當代知識社會學的發展,愈來愈走向經驗研究,主要是研究知識的生產、儲存、傳播和應用。當代大規模的知識生產和傳播,造成一種知識密集的社會。社會學愈來愈重視知識在社會發展、變遷中的地位和作用,並涉及知識或思想在社會政策的制定和實施等一系列問題。
÷知識社會學是一門研究知識與社會之關係的科學。它既是社會學中的一支,又是認識論的一部分。作為認識論的一部分,它專門研究知識或思想所受社會條件的制約。就歷史發展的角度說,知識社會學主要是德國思想家的貢獻。如果將德國哲學家、社會學家舍勒1924年出版的《知識社會學問題》、1926年出版的《知識形式與社會》視為該學科的奠基性著作,則知識社會學在西方至少已有近80年的歷史。
最早把西方的知識社會學介紹到中國來的人,據筆者目前掌握的資料,是當時燕京大學教授李安宅(1900—1985)及其老師張東蓀(1886—1973)。李安宅以《孟漢論知識社會學》為題,把德國學者曼海姆的《意識形態與烏托邦——知識社會學引論》一書的第五編,從英文本翻譯成中文,發表在1938年6月燕京大學出版的《社會學界》第十卷上。這篇譯文後來又出了單行本,書名叫《知識社會學》(上海中華書局出版),同時“附錄”張東蓀的《思想言語與文化》。該書不僅認為知識社會學是“包括一種體大思精的系統,代表一個嶄新的領域”,而且在當時就已經意識到“知識社會學的觀點”也許可以作為中國努力建設社會史、社會思想史的“指南針”(《知識社會學》,“譯者弁言”2—3頁)。
張東蓀的文章對知識社會學有介紹,但主要的目標是通過批評“孟漢底體系”而創建中國人自己的第一種“知識社會學”。所以,張東蓀既是知識社會學的引進者,又是中國“知識社會學”的創建者。他的《思想言語與文化》一文,表達的就是一種完整的“知識社會學”。其中心是證明“概念的知識”亦即“解釋的知識”(包括政治思想、社會思想、道德見解、哲學思想、宗教理論、物理學等)是受到文化的左右,跟著文化走的。換言之,思想是受“社會情況”左右的,此“社會情況”既包括社會上無形或有形的勢力,亦包括“很遙遠的社會影響”之“暗中支配”。此種“遙遠的影響”即是所謂“文化”。他以為西方人把自己的知識視為人類普遍的知識加以論究是不對的,因為西方人的知識僅是人類知識之一種。西方人的知識之外,還有其他類型的知識存在。這就是“從社會學的研究知識”所得到的結果。
這是知識社會學在中國的一步重要進展。第二步進展也是張東蓀完成的,就是從知識社會學過渡到獨立知識論,同時承認人類知識所受的三種限制:知識社會學所發現的“社會學的限制”;康德所發現的“生物學的限制”;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所發現的“心理學的限制”。承認三種限制而非一種限制,表明張東蓀已經從知識社會學的觀點中走出來,踏上了獨立知識論的道路。隨著《知識與文化》、《思想與社會》、《理性與民主》三書的出版,張東蓀以建立“獨立知識論”為主要目標的哲學體系最後完成,至此“知識社會學”被融入到“獨立知識論”中。第三步進展表現在應用方面,就是以“知識社會學”為立足點解釋哲學以及哲學家的使命。這一步也是張東蓀完成的。他認為,從社會學的觀點看,有了文化的需要,就會有理論、哲學;理論的產生是基於文化、社會的要求,時代、要求一變,真理也就跟著變了,以前的真理便不再是現在的真理;哲學既是文化的產物,則文化到了不能不變的時候,哲學家就應該站出來做思想領導,“產生新的哲學家”(張東蓀《哲學是什麼?哲學家應該做什麼?》,《時與文》(周刊)第5期,1947年4月11日出版)。1949年以後,知識社會學在中國,在介紹方面有一些進展,但在自創方面進展緩慢。
通過考察知識社會學在中國進展的過程,可以得到三點教訓:第一,就西方哲學史的角度說,知識社會學的產生與興盛是以知識之重要性的日益提升為背景的,所以必須加強知識社會學的研究與自創;第二,就中國哲學史的角度說,知識社會學的介紹與自創是中國現代哲學史的一項重要內容,值得認真研究與總結,這也許會成為打開中國現代哲學之寶庫的一把鑰匙;第三,就現實角度說,中國正逐漸步入“知識經濟”時代,知識開始在社會中佔據中心地位,研究知識與社會的關係正成為中國學者的義務與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