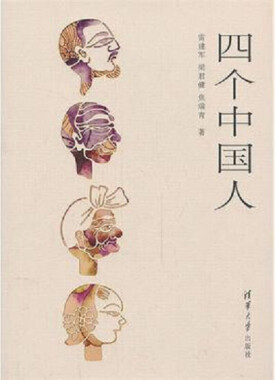四個中國人
四個中國人
《四個中國人》作者雷建軍、梁君健、焦瑞青在這裡給我們展示的不是符號化的中國人,而是用羅中立的油畫《父親》中那樣的筆觸呈現的四個具象的、有血有肉的、凝練一方水土的普通中國人。書中簡單而有趣的微觀生活,可以有宏觀的升華,但還要回到微觀,從四個回到更多人的微觀世界,讓更好的精神生活在微觀、在日常生根發芽。
《四個中國人》以他們四個人的日常生活來呈現本真質樸的“中國人”。
呂崇德
程宵春
高喜業
池素英
後記
“在這種社會中,人們相互之間再沒有種姓、階級、行會、家庭的任何聯繫,他們一心關注的只是自己的個人利益,他們只考慮自己,蜷縮於狹隘的個人主義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在這類社會中,沒有什麼東西是固定不變的,每個人都苦心焦慮,生怕地位下降,並拚命向上爬;金錢已成為區分貴賤尊卑的主要標誌,還具有一種獨特的流動性,它不斷地易手,改變著個人的處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幾乎無人不拚命地攢錢或賺錢。不惜一切代價發財致富的慾望、對商業的嗜好、對物質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為最普遍的感情。”這是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對於革命后的社會的描述,字字句句讓我們想起今天的中國。
對中國而言,過去的一百年隔三岔五就會有革命發生,但所有這些流血的革命似乎只是一場真正革命的前奏和準備。這次革命被稱為改革,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它幾乎徹底改變了中國人的生產方式,進而改變了中國人的生活方式,然後日積月累,到今天我們看到了明顯的中國主流人群心性的變化。面對這樣的變化,不同的階層,不同的人都試圖開出不同的藥方,而我們把目光放在大眾本身,從所謂“原子化的底層”“單向度的人”中尋找微觀的、鮮活的個體,尋找“無力的底層”自己所擁有的力量。
呂崇德、程宵春、高喜業、池素英,從這四個人的故事中,從他們的成長經歷、學藝過程中,從他們當下的生活態度中,我們不僅尋找到了這種力量,而且還發現了這種力量的形成機制,那就是手藝的傳承機制,我們發現這種傳承機制本身就是這種力量的編碼過程。雖然所有的遺產都是傳統文化的編碼器,但只有非物質文化遺產,只有活著的傳承可以讓我們看到編碼的過程,這就是記錄和深描這四個人的重要性,就是研究非物質文化遺產在當代社會的功能的重要性,也是非物質文化遺產對於中國文化重生的重要性。
在這裡,傳承不是概念的而是具體的,它是皮影藝人的“活兒”與操守,它是紙簾藝人的技術與行規,它是說喜藝人的能耐與經驗,它是扇鼓藝人的切磋與自律,它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有明確的目標、具體的細節、經年累月的過程,和滲入到每一個環節的規矩,最重要的是它一對一,口到口,手到手,眼到眼,心到心,中間沒有任何媒介,由人傳給人,而這一切正是當代社會所重度依賴的現代教育體系所逐漸丟失的。不幸的是,今天的社會把太多的教育功能推向了這種體系,指望這種只能培養才的體系來培養人,從而丟掉了最重要的教育領地——家,丟掉了最有效的教育方式一生活,丟掉了最重要的教育工具——人,捨本逐末、緣木求魚。幸運的是,我們在這些非物質文化遺產行將消失以前,看到了它們的編碼過程,並將它們記錄與揭示出來,期望用普通大眾自己的力量來重塑大眾自己的生活。所以,看完這四個人的故事,與其抱怨轉型期的種種社會亂象,不如在你的關係人群中,建設一種可以傳承的“手藝”,有目標,有過程,有細節,有規矩,天長日久、經年累月、潤物無聲。
當然,中國人是一個變化著的複雜概念,任何的判斷都難免有失偏頗,所以我們選擇四個具體的人,選擇長時段的觀察,選擇講故事的方法,試圖讓人們感覺到生活的氣息、觸摸到文明的脈搏。同時我們也看到從四個具體的人升華到一般的中NA,這種抽象過程可能導致的風險。好在,非物質文化遺產可以幫助我們在微觀事實與宏觀結構之問穿梭,幫助我們穿透歷史與現實。
清影工作室
2013年6月
今天,“中國人”,是一個讓人又愛又恨的名字。
網路上的中國人光怪陸離。
電視上的中國人不食人間煙火。
生活中的中國人,要麼經常按著汽車喇叭從你身邊呼嘯而過,不管你是否懷孕,是否有心臟病;要麼在地鐵里漠然或假裝玩著手機,全然不顧身邊抱孩子的女人和白髮蒼蒼的老人。
中國人怎麼了?
我們是否還流著唐詩宋詞中那些有情懷的中國人的血液?我們是否還是辜鴻銘眼裡不需警察與律師而能社會和諧自處的中國人的後裔?我們是否還是黃仁宇筆下對己謙而對人讓的中國文化的繼承者?抑或這些都是我們美好的想象,中國只是一個地名而非文化名稱,因為自從孔子痛心疾首地說禮崩樂壞之後,禮樂再也沒能恢復,如同秦暉教授用盡半輩子實證研究而無奈地笑著說,那種士紳與農民溫情脈脈的鄉土中國從來就沒存在過。
2007年開始,清影工作室一直在進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一邊拍紀錄片一邊做研究。這期間我們在陝西華縣遇見了演皮影的呂崇德,在浙江衢州遇見了打紙簾的程宵春,在陝西榆林遇見了唱紅白的高喜業,在河北贊皇遇見了跳扇鼓的池素英。這四個人隔著千山萬水但都與人為善,為人著想,離開了熟人社會的生活系統,卻依然保持著做人的底線,他們用日常的生活方式維繫著我們心中對“中國人”的幻想。
演皮影的呂師,從地主娃到皮影藝人,一生命運多舛,但彈起月琴,就如泣如訴地講述真正的中國故事,拿起鋤頭就做一個真正的中國農民,城裡塬上兩頭跑,日子緊緊巴巴,但生活有滋有味。
打紙簾的宵春,上班在化肥廠裝尿素,下班回自己家織帘子,傳承千年的宣紙彷彿只在他一個人心中,對工業化的鄙視與屈服都在他的聲聲嘆息與滴滴眼淚之中。手閑了練字,心閑了吹簫,身閑了捉魚,琴棋書畫只是生活中的玩意兒。
唱酸曲的喜業,一生走南闖北,落葉歸根,做起了“下賤人”,在大俗的紅白喜事上靠作踐自己搏名搏利,但在夕陽下放羊時一首首酸曲從心底湧出,那是一個擁有無限溫暖的精神世界,單純而悠遠。
跳扇鼓的素英,在窮山溝里樂活著,一閑下來就打扇鼓。農村人有說不出的美感,吳冠中說,他在鄉間作畫,畫得好的農民便說,這張畫美;畫得不好了,農民們說,這畫很漂亮。農民在心裡知道“漂亮”和“美”的區別,素英也是如此。
是什麼賦予了這四個人,四個普通中國人,當代社會夢寐以求的自律與快樂,讓他們在複雜的社會中保持相對的單純與寧靜?我們試著用鏡頭、用特寫來關注他們,用參與式的觀察來審視他們,用長時段的沉澱來思考他們。
我們發現,傳承可能是塑造他們的機制。皮影戲的師徒傳承、打紙簾的父子傳承、二人台的江湖傳承、扇鼓樂的同伴傳承,總之在一點一滴中,在日常生活中,由於有傳承的目標,戒律被無形中樹立,文化被無形中繼承,人被無形中塑造。這種機制與現行的社會教育體系不同,它沒有批量生產,它沒有急功近利,它沒有錦標競賽,它春風化雨潤物無聲,而這些是以前在社會教育不發達的狀況下,每個中國家庭都有的。
我們發現,“有閑”可能是塑造他們的條件。傳統農村生活中,忙閑有時,忙閑有度,春忙夏種秋收冬閑,大可以玩個盡興。工業生產、商業活動透支了人們的閑暇時間,人們更習慣將碎片化的時間花在媒介上,人們更習慣媒介化的交流而不是真實的生活,殊不知媒介使人焦躁。閑是和慾望成反比的,這四個人都不算富裕,但慾望有限,所以他們都有自己生活中的閑和閑出來的情趣,有情趣則不焦慮。
我們發現,市場化可能是泯滅他們的催化劑。市場對規模的追求,對速度的追求,對成本的追求,歸結成一句話對利潤的追求,可以徹底顛覆一對一的傳承模式,同時也可以用便捷低廉的方式俘獲捲入市場的民眾,所以傳統文化生活先從城市淡去,然後再從農村淡去。這不僅關乎文化,也關乎一代人,幾代人,甚至整個民族的心性,老一代有文化沒知識,而新一代有知識沒文化。這種趨勢也許無法阻擋,也許沒必要阻擋,但我們可以在市場的洪流中,看到多元的存在,向歷史習得更好的精神生活。四個中國人,簡單而有趣的微觀生活,可以有宏觀的升華,但還要回到微觀,從四個回到更多人的微觀世界,讓更好的精神生活在微觀、在日常生根發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