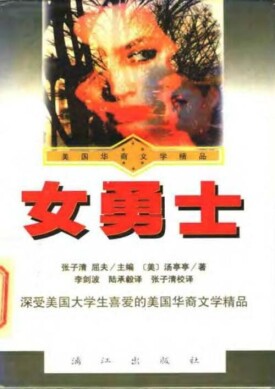共找到2條詞條名為女勇士的結果 展開
- 美國華裔作家湯亭亭所著的小說
- 1948年的香港電影
女勇士
美國華裔作家湯亭亭所著的小說
《女勇士》是美國華裔作家湯亭亭的處女作。作品以中國為背景,通過極富想像力的虛構與簡潔的白描,展示了一個生活在艱難創業的華人圈中的小女孩的童年生活及她周圍的女性的現實生活。作品熔美國華人街受歧視、受壓抑、貧困、不安定的華人生活現實,與中國大陸的神異鬼怪、仙風道骨、自由戰鬥的女英雄故事等於一爐。行筆或細膩委婉、或天馬行空;氣勢酣暢淋漓,給人以甘美的享受。
全書分五個部分:無名女子、白虎山學道、鄉村醫生、西宮門外、羌笛野曲。
第一部分“無名女子”是通過第一人稱敘述者“我”聽母親講家庭的慘劇。姑姑新婚不久,丈夫去美國淘金,幾年後,姑姑懷孕。由於她偷了漢子,違反了封建社會婦女的“三從四德”,全村人為之震怒,在姑姑分娩的當晚,他們砸了她家,姑姑走投無路,被迫在豬圈中生下孩子,然後抱著嬰兒投井自殺。
第二部分“白虎山學道”是根據中國婦孺皆知、膾炙人口的花木蘭女扮男裝殺敵立功的故事改編而成。作者想象自己成為“花木蘭”進白虎山修鍊十五年,然後帶兵打仗報了國恨家仇,回到故鄉成了英雄。
第三部分“巫醫”描述了母親“勇蘭”在中國學醫和行醫的經歷,以及她能捉鬼和招魂的故事。
第四部分“西宮門外”寫的是姨媽月蘭的不幸遭遇。
最後一部分“羌笛野曲”寫的是“我”回憶從幼兒園到成人的成長經歷。
該書所涉及的題材相當廣泛,幾乎包涵了關於移民處境、代溝、青少年的困惑和叛逆、女權主義、邊緣文化、尋根意識、家庭史詩、東方話語、紅色中國、文化衝突、個人經驗與官方話語等使西方學者和讀者深感興趣的種種成分。人們可以從各個角度閱讀它,不同的讀者可從中發現不同的可讀性。
美國華裔文學(總序)
譯序
一 無名女子
二 白虎山學道
三 鄉村醫生
四 西宮門外
五 羌笛野曲
東西方神話的移植和變形——美國當代著名華裔小說家湯亭亭談創作
20世紀,兩場世界大戰對西方人的身體造成巨大的創傷。也給青少年的心理帶來了嚴重的後遺症。與白人青少年相比,華裔青少年在成長的道路上承受得更多,而其中的女孩們則是遭受最多傷害的一群人。當時的華裔青少年是移民到美國的第二代人,華裔的面孔在美國主流社會中標誌著他們是邊緣的一群人,她們在美國社會找不到家的感覺,但也不可能返回到自己父母的祖國。
無名姑姑
無名姑姑是受封建男權壓迫的一個典型案例。她的故事發生在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農村。姑姑的丈夫在度完新婚之夜後去美國淘金。兩年後,姑姑卻懷孕了,被指和他人通姦,並連累一家受到族人和村民的譴責與衝擊。蒙羞的姑姑在生下孩子的當夜懷抱著嬰兒跳進了自家的井中溺水身亡。
勇蘭
母親勇蘭在丈夫去美國淘金后,便隻身一人進城學醫。在助產士學校,勇蘭和五名女學生同住一間宿舍,學習異常發奮,很快便成為“看一眼書就能學會的天生學者”。勇蘭憑藉堅定的意志和不懈的努力完成了學業,成了一名醫生,並打破了只有男性才可以成為學者的封建慣例。畢業之後,勇蘭開始了行醫生涯。作為一名職業女性,她保留了“勇蘭”這一少女時代的名字,而沒有冠以丈夫的姓氏,以免淪為丈夫的附屬品。
幾年之後,勇蘭前往美國與丈夫團聚,卻遇到了種族主義的壓迫。勇蘭在中國以為取得學位便能夠在美國安身立命,然而現實卻是不得不和丈夫一起經營洗衣作坊。勇蘭不怕吃苦的樂觀精神繼續在美國延續,夏天洗衣作坊酷暑難耐,她便講鬼故事給孩子們聽,“讓他們背脊發涼”。在雙重壓迫下,勇蘭像男人一樣努力幹活,為生存而奮鬥,實現了女性從受壓迫者到學者到勇士的轉變。
花木蘭
這個花木蘭的故事不同於民間傳說中的花木蘭,湯亭亭基於母親的敘述和自己的想象,重新詮釋了花木蘭的故事。湯亭亭筆下的花木蘭則不再是替父從軍的盡孝女兒。木蘭想要擺脫為人婦、為人奴的命運,在一隻鳥的引領下進自虎山拜師學藝。學成之後,木蘭返回家鄉,代替老父為村民報仇,穿上了男人的盔甲,像男人一樣打仗,擺脫了傳統女性的地位。誠然,她學習武術是為了抗擊匈奴、保家衛國,讓自己名垂青史,但同時也是為了逃避田間勞作、挖紅薯的命運。所以,木蘭進山學藝是一種自我提升、自我價值的實現,是為了擺脫家務瑣事,而非出於對長輩的孝順。此外,湯亭亭筆下的花木蘭沒有對統治者盡忠,反而在最後砍掉了皇帝的腦袋。皇帝是封建統治的最高象徵,所以木蘭的舉動是對封建社會的徹底否定。同時也是對父權社會的無情鞭笞。
月蘭
月蘭姨媽的身上帶有中國傳統女性的典型特徵:軟弱、膽怯、順從等。她聽從父母之命嫁給了一個比自己小許多歲的男人。丈夫移民美國成為腦科醫生后,重娶了一位華裔太太。月蘭在香港過著棄婦的生活,靠著丈夫寄來的錢毫無怨言地將獨生女撫養成人。她幾乎是自願扮演著封建男權社會對女性所要求的角色。在姐姐勇蘭的鼓勵下,她終於在70歲之前踏上了美國的土地。這場尋夫記在丈夫只同意給她和勇蘭買一碗麵條當午餐的情況下草草收場。月蘭無法適應美國的生活,最後瘋癲病死在加州的一家精神病院里。
“我”
“我”指作者湯亭亭。“我”下定決心,希望可以通過自身努力,成為白虎山上的那個“女勇士”,以此來改善自己處境,幫助父母與身邊的鄉親。但是在殘酷的現實面前,“我”所能做的,就是迫使自己成為地道的美國女性。
儘管從母親那裡聽來的花木蘭和岳飛的故事感染著“我”,儘管無名姑姑的事迹震撼了我,儘管母親的轉變影響了我。“我”還是被目前所處的這個大環境所影響著。與此同時,“我”想參加學校的節目表演,想讓自己的體育成績和文化課成績並駕齊驅,更幻想著能在哪一天肆無忌憚地衝下教學樓的樓梯,放聲大笑。這是一種美國文化帶給她的感受:只要是屬於“我”的權利,“我”就有理由去追求。
“我”朝著成為地道美國人的目標奮進的時候,也對女性主義有了不同的見解:女性想要不依靠男性在社會上立足,唯有樹立堅定的信念,加之努力付出。與此同時,中國傳統文化並非都是糟粕,同樣,正確面對美國文化,二者相結合,並為之所用,這才是作為華裔女性所應堅持的道路。
主題思想
以《女勇士》中“我”為代表的華裔女孩的父母是美國的第一代華人移民,他們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被傳統觀念所束縛。為了在新的土地上生存下去。他們努力學習英語,了解當地的風俗習慣,但在內心深處,無法割捨中國文化,並且向他們的子女講述頭腦中固有的傳統思想。然而第二代移民生長在美國社會、在美國的公立學校接受教育,父母傳達的中國傳統觀念與他們所接受的美國文化價值觀念產生了衝突,讓他們困惑不已;黃種人在白人社會並未被完全接受,他們在兩種文化的夾縫中生活,自己的文化身份無法得到明確,更加重了困惑感。
《女勇士》中的主人公小女孩“我”也為兩種文化困惑。父母的故事裡提到的中國人的生活和日常生活習慣也與子女在美國的生活方式和觀念大相徑庭,有些細節甚至讓子女感到恐懼。在後來經歷了“送葯”事件之後,“我”更是直接、深刻感受到了中國的傳統觀念和美國教育觀念之間的衝突,令“我”無所適從。西藥店把別人的葯誤送到“我”的家裡,母親見到之後認為“送葯”是個不祥之兆,這是從母親骨子裡的中國傳統觀念體現出的。她覺得這算得上是飛來橫禍,會詛咒全家人生病,因此必須要讓西藥店做出一些補救措施,例如送糖果,可以驅趕葯帶來的晦氣。她堅持讓“我”去西藥店,還教“我”怎樣跟藥劑師交涉。其實,從頭到尾,“我”都清楚,藥劑師並沒有像母親認為的那樣理解了“我”的行為,反而認為是在向他乞討。“我”認為這是藥師在對我們施捨,而母親認為“她教會了洋鬼子藥師講禮節”。在這場兩種文化的衝突之中,“我”完全感受到了處於文化邊緣的困惑,雖然母親與藥劑師雙方的想法“我”都了解,但卻沒有辦法來向他們解釋清楚。更沒有辦法解決文化衝突帶來的壓抑感。
《女勇士》中的主人公小女孩最初並不了解兩種性別之間的差異,但是家庭和“我”身處的唐人街一直想讓“我”成為“溫柔”的女子。在此過程中,“我”才漸漸明白了女性地位的低下。作為第一代華人移民,父母給兒子和女兒的不同待遇會讓女兒產生困惑,並且會造成女兒內心的不舒服。弟弟的誕生給“我”帶來了許多關於性別的差異。弟弟出生時,“我”詢問父母是否在我出生時也用雞蛋在“我”臉上滾過,是否也給“我”過滿月,是否也把照片寄給奶奶。隨著年齡的增大,“我”更加清楚地意識到男性與女性之問的不平等,而這種清醒的認識更加深了“我”的成長困惑。“語言在我們的社會中是性別歧視的主要載體”。“女娃好比飯里蛆”“寧養呆鵝不養女仔”“養女好比養牛鸝鳥”“養女等於白填”“女大必為別人妻”,這些常聽到的說法令“我”感到討厭。
語言代表著人與世界的連接,書中美國華裔女孩的沉默代表了她們在主流社會中邊緣化的地位。她們講著美國的語言,有著美國的思維方式,卻長著中國人的面孔,長期在兩種文化的邊緣徘徊,受到封建父權制的壓迫,她們對這種邊緣化的地位感到困惑,於是普遍選擇了失語、沉默。“我”在進入美國的幼兒園的第一年就沉默了。但是沉默的結果卻是被質疑智商有問題,低的智商又會受到社會上更多的歧視。於是,沉默實際上又進一步加大了她們的邊緣化。華裔女孩兒的沉默並不是真的不會說話,她們在唐人街聲如洪鐘,可以在華人學校一起朗讀課文,可以相互打鬧,甚至又喊又叫。由此可見,她們的沉默不是不會說英語,她們是缺乏在主流社會中發出聲音的勇氣與自信,因此只能用沉默來保護本來已處於弱勢地位的自己。作出無力的反抗。
生活在美國的華裔女性在中美兩種不同的文化之問很容易感受到來自文化和性別的雙重困惑與壓力。華裔故意躲開中國文化的影響。急切地想成為真正的美國人,卻又發現融入美國的主流文化並不容易,才開始意識到保持中國傳統的必要性。在美國社會,華人的地位低下,他們經歷了被排擠的悲慘事件;同時,他們在美國出生、成長,在美國的公立學校接受教育,受到美國主流文化和價值觀的教育。因此在一個多元文化的環境里,解決困惑而後覺醒對她們而言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為了找到答案,她們在兩種文化、兩個世界中要學會融合不同的文化。
全書的結尾是“歌詞翻譯得也不錯”,恰好象徵了不同文化之間的融合。“我”的最終願望是全球化,一個擺脫邊緣化的方式,也是華裔美國女性建立自己文化身份的方式。
藝術特色
全書第一、二、三、五章均用第一人稱敘述,而第四章卻轉為使用第三人稱敘述,這給讀者以作者冷靜客觀甚至可以說是“冷眼旁觀”地進行敘述的感覺。如果說前三章中,作者是在以“我”的經歷與感受引領讀者近距離感受並融入所述故事的話;那麼,在第四章中作者則冷靜地抽出身來以旁觀者的身份遠距離地與讀者一起欣賞這部講述月蘭悲慘命運的情景短劇。這樣,作者就以參與者與旁觀者的雙重身份從近距離與遠距離兩個角度向讀者講述了所述故事。
戲仿。湯亭亭筆下的花木蘭雖然保留了中國古典文學中孝敬父母、替父從軍、男扮女裝等內容,但卻把中國古典文學中宣揚的忠君愛國的儒家思想通過戲仿的寫作手法,轉變成了追求自由愛情、達到女性解放、實現個人價值的好萊塢式的女英雄形象。其次,湯亭亭戲仿了岳母刺字的具體情節。刺字者由岳母變成了花木蘭的父親,被刺字者由抗金英雄岳飛變成了巾幗英雄花木蘭,刺的字由“精忠報國”變成了報仇雪恨的誓言。花木蘭背上被刺的字時刻提醒她不要忘記華裔身份,要捍衛自己的種族,銘記自己的歷史。這些字就“像軍隊,像我的軍隊”。
拼貼。湯亭亭高超且巧妙地運用了拼貼這種後現代主義的創作技巧,從中國古典文學、神話傳說、毛澤東領導農民起義、紅色中國的土地改革到個人經歷、移民問題、代溝、女權運動,將中國文化與美國文學,將中國傳統與美國現實融為一體。她筆下的世界是一個多元開放的世界,是一個文化融合的拼盤。除了對花木蘭這個經典形象進行拼貼外,湯亭亭在最後一章《羌笛野曲》中,借用了蔡文姬這一中國歷史人物形象對其進行拼貼式的再創造。在湯亭亭的筆下,蔡文姬不再是東漢末年不幸被擄掠,嫁給匈奴后被重金贖回,又遭受母子分離的悲情女子,而是被塑造成與匈奴丈夫夫妻恩愛,共同抗敵,思念故國的感情豐富的女性形象。湯亭亭借蔡文姬形象的再塑造,體現出作為美國社會邊緣的華裔女性,面對中美文化的碰撞夾擊,面對滾滾而來的女權主義浪潮,不再保持沉默,大膽地發出自己的聲音,積極地尋求自身的身份。
迷宮。湯亭亭在《女勇士》中營造出一種錯綜複雜、令人眼花繚亂的無序結構。在第二章《白虎山》中,“我”作為一名中國女孩,受到花木蘭故事的啟發,決定“必須成為女武士”。緊接著作者筆鋒一轉,“我”變成了花木蘭,女扮男裝征戰沙場。“我”和花木蘭之間沒有任何過渡性的暗示或者提醒,令讀者一頭霧水,難以區分虛構與現實的界限,從而體現出華裔女性在美國社會中所遭受的種族與性別的雙重歧視。在第三章《巫醫》中,“我”講述了母親學生時代在宿舍捉鬼的離奇故事。在母親講完捉鬼故事之後,湯亭亭寫到:“當煙霧散盡,我想我母親是說她和同學們在床腳下找到了一塊滴血的木頭”。讀者剛剛有撥開雲霧見青天之感,卻因為“我”對母親的話的質疑和評論,再次陷入撲朔迷離之中。在小說中既沒有確定的答案,也沒有柳暗花明的轉折,這種有象無意的迷宮式寫作技巧凸顯了小說的不確定性。
零散敘事。《女勇士》第一章的主人公無名氏姑姑在以後的四部分中再沒有出現,取而代之的主人公從幻化成花木蘭的“我”、母親以及姨媽月蘭,到再次幻化成蔡文姬的“我”。這種零散的結構讓讀者有霧裡看花的模糊感。湯亭亭在各章之間沒有採取直線敘事模式,使小說呈跳躍式前進,不同主人公交替出現,沒有共同的敘事背景,顛覆了傳統小說的宏大敘事。她將各種零散的片段串聯在一起,讓小說的主題不言自明,即華裔女性擺脫美國社會邊緣人的地位,融入到美國主流社會中的蛻變過程,刻畫她們的果敢與擔當,描述她們在中美文化夾擊中的艱難處境。
互文性。在《女勇士》中,互文性首先表現在對中國歷史故事中花木蘭和蔡文姬的人物形象的戲仿和拼貼;其次,在故事情節,甚至細節描寫方面,互文性也表現得淋漓盡致。在第二章《白虎山》中,“我”進山修鍊,偶遇“小白兔”。兔子自己主動跳入火堆,變成兔肉,為“我”果腹。“我吃著兔肉,心裡明白兔子是為我做出自我犧牲的”。這不僅讓人想起敦煌壁畫中所描畫的早期佛經中“薩捶那太子捨身喂虎”的情節。在小說中,佛經中“虎”幻化為“我”,佛經中的“薩捶那太子”幻化為“小白兔”。“小白兔”的情節又與西方經典童話《愛麗絲仙境漫遊》不謀而合。這種中西方故事人物和情節的混淆,凸顯出小說互文性的特點,表現出美國華裔已經將中美文化的交織融入到現實生活和文學創作中。
《女勇士》這本小說一經出版就轟動美國文壇,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和積極討論,並於當年獲得美國國家圖書評論界非小說獎,湯亭亭本人也躋身於美國當代主要作家之列。這本小說後來被柯林頓總統褒獎為一部劃時代的巨著,並被選入美國大學華裔文學的閱讀書單。小說開頭的第一句話“You must not tell anyone what I am about to tell you”曾經一度成為美國大學生們的口頭禪。這本小說扭轉了當時美國社會對中國社會的認識,顛覆了美國大眾對中國女性的偏見。
《女勇士》自發表以來,在華裔美國文學中一直受到關注。褒獎該作品的學者以女性主義者居多,而批判的聲音則多來自於華裔男性作家陣營,其中當以趙健秀為代表。趙健秀亦是著名華裔美國作家,曾是湯亭亭的同窗,不過他對湯亭亭作品的批評一點都不留情面。趙建秀在其主編的《大哎咿!華裔與日裔美國文學選集》序文《真真假假的亞裔美國作家們,大家一起來》中痛批湯亭亭的作品《女勇士》篡改亞裔美國歷史和文學;還寫了一篇戲仿《女勇士》的作品Unmanly Warrior。歸根到底,以趙建秀為代表的華裔男性作家普遍認為《女勇士》中的女性故事迎合了白人對東方女性的幻想和對華人男性的貶低。
湯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1940—),祖籍廣東新會,1940年出生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蒙士得頓市。湯亭亭的父母於20世紀30年代移民美國。她自幼愛好文學、散文和詩歌。1958年她獲得獎學金進入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就讀,先念工程學系,後轉念英國文學,於1962年考獲文學學士學位。1962年底她與同班同學厄爾·金斯頓(Earl Kingston)結婚。婚後她曾在加州中學和夏威夷中學擔任英文教師多年。1970年至1977年她曾任夏威夷大學英國文學系教授,后又擔任東部密歇根大學英國文學系教授。她於1990年起擔任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英國文學系教授,並從2001年起還擔任著名文學刊物《加州文學》(The Literature of California)的主編。湯亭亭一生從事英國文學的教學和著述,她的成名作品曾獲多項榮譽。1997年她獲得了美國人文科學金牌獎,1998年獲終生成就獎和文學獎,2001年獲聯邦俱樂部書籍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