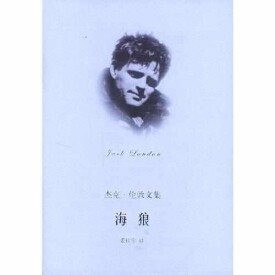共找到14條詞條名為海狼的結果 展開
海狼
美傑克·倫敦著長篇小說
《海狼》是美國作家傑克·倫敦創作的長篇小說。小說描寫了在一艘名為“幽靈號”的以捕獵海豹為生的帆船上發生的一場動人心弦的搏鬥和刻骨銘心的愛情故事。
小說中的“狼”不僅是船長拉森的名字,對作者而言,也是超人的代名詞,作者通過作品帶領讀者進入豪放粗獷荒野,體驗蠻荒生活的冷酷無情,感受人性兇殘的黑暗面和原始生命的光輝;同時也揭露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弊端,表現了對勞動人員頑強意志的歌頌和苦難生活的同情。
《海狼》在直到1999年的八十多年間中,曾十幾次被搬上銀幕,傑克倫敦在1913年的版本中,出演一位水手。
在《海狼》一書中,傑克·倫敦將社會舞台放到了一艘捕海豹的帆船“魔鬼號”上。主人公凡·衛登是一位文學評論者,在與朋友周末度假返程的途中,遭遇大霧,他們的船被撞沉。在冰冷的海水裡垂死掙扎之際,幸運的衛登被“魔鬼號”船長拉森救起。由於船上大副的死亡,拉森不同意將衛登送回舊金山,而是逼他隨船出海,並做各種苦工。在此期間,衛登目睹了拉森的冷酷無情以及他的暴力統治。拉森綽號“海狼”,他比一般的水手強壯,力大無窮。堅信“大吞小,強凌弱”。他為了保住他的一條帆板不被大浪沖走,竟白白搭上一個水手凱利的性命。他不高興時拿廚子托馬斯出氣,讓人抓住他,用繩子將他拴住扔到海里折磨他,結果被鯊魚咬去一隻腳。衛登一不小心將爐灰撤在他身上,
他便對他拳腳相加。最終他的暴力統治激起反抗,幾名水手聯合起來把他和大副扔到海里,大副葬身海底。他卻又爬回船上奪回控制權,之後他借口報復了帶頭反抗的兩名水手,利用海上風暴讓他們葬身大誨。
“魔鬼號”偶然救起了在輪船失事中倖存的莫德。衛登對她一見鍾情。而如惡魔般的拉森則想的是將莫德淪為他的性奴隸。船長海狼強大無比,是一頭猛獸,凡·衛登先生,雖然學富五車,卻如同一頭小羊,力量懸殊不成比例,毫無反抗之力;“美麗的女作家與凡·衛登先生邂逅於苦難之中,共同的遭遇很快把他們連接在一起,但他們充其量不過是兩隻小羊,無法改變其力量對比,儘管他們不甘被奴役,運用其知識和智慧與之周旋,卻很難擺脫其被統治的命運。”衛登為了解救她,終於和莫德找機會逃走,由於偏離了航線,不得不在一個海豹聚集的小島上暫時安頓下來,過了一段艱苦的努力生存的日子。眾叛親離的拉森和“魔鬼號”也撞上了這個小島。船上的水手和獵人不堪拉森的壓迫,又禁不住有人故意的金錢誘惑,全部叛逃“魔鬼號”去為拉森的敵人工作。拉森也不再是那個身體強壯、堅不可催的樣子了,經常的頭痛,可能是頭部的瘤造成了他的迅速衰弱甚至失明。他漸漸出現了偏癱,生命之火慢慢地熄滅了。衛登與莫德安葬了拉森,他們修復“魔鬼號”並揚帆返航,最終弱者終於戰勝了強者,文明終於戰勝了野蠻。
傑克·倫敦生活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這個階段是資本主義瘋狂地向全世界擴張並且逐漸走向鼎盛的時代。美國的疆域已從東海岸通到西海岸,第一批人是探索土地的開路先鋒,然後是從土著人手中野蠻奪取土地的士兵,最後才湧入成千上百萬的定居者。這些定居者大都來自東海岸和歐洲。他們開闢農場和開發土地,他們多是來圓發財夢的冒險家、投機者和躍躍欲試的各方來客。“不穩定的野外生活很容易激發起他們身上的獸性”,這種環境下,弱肉強食的超人哲學、優勝劣汰的達爾文主義開始盛行開來,並且佔有很大的市場。
拉森
由海洋造就的拉森,在與海洋的朝夕相處中,內心時刻處於一種不斷戰鬥的狀態。他出生在一個貧窮的海上漁民家庭,很小就踏上了航船。在船上,他被人們拳打腳踢,惡語相加,無人庇護的他只能學著自己保護自己。水手生活,給拉森打開的關於世界的窗口,這是一個弱肉強食的世界,他逐漸認識到,人只有自身強大才能戰勝別人,由此成為永不停戰的“海狼”拉森。 “人性”和“獸性”在他的身上不斷激戰著,使他成為一個喜怒無常、令人琢磨不透的人。這種琢磨不透也使“海狼”成為海洋文學史上一個富有個性魅力的形象。
凡·衛登
凡·衛登原本是一個有教養的學者,而淵博的學識和良好的教養對他在魔鬼號上的生存沒有裨益,他處於最底層。儘管他努力工作,還備受欺凌。在殘酷的現實中,為了能夠生存下去,免受羞辱、毆打,凡·衛登不得不脫下文明的外衣,放下先前所秉承的教養,靠著暴力為自己贏得一份生存之地。凡·衛登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海狼的人生哲學:強權便是真理,懦弱便是錯誤。
作品主題
生存法則
有人如此評論拉森:“這個人出身貧寒,備受壓迫,因而極度仇恨壓迫者與不勞而獲者,並仇視主流社會;但他一旦佔據了某種統治地位,哪怕只是一艘海船的船長,卻又去變本加厲地壓迫別人,踐踏弱者。他嗜血成性,專制自私,是一個獨裁、魔王。”衛登如此描述他對拉森的第一印象:“他(拉森)並不是外表上像只猩猩,我想說的是,除了他外表的力量之外,這種力量本身就是某種有形物,這種力量使我們很快聯想到原始性、野獸以及我們想象中居住在樹上的猿人。簡而言之,那種力量猶如斬斷頭的蛇一般,蛇雖死,但身體扭動不停,或者說這種力量仍在一塊變形的龜肉里蠕動,用手指一戳,它就會蜷縮、抖動。”但這個原始的野蠻人並不是“力大無腦”。他知識豐富,對天文、地理、文學、科學都能略知一二,可稱是“四肢發達”而又“頭腦豐富”的完美結合體。他用這種超乎凡人的力與智的結合,牢牢控制了船員的生命。在他的生存法則中,強者為王,後者則淪為強者的奴隸。
在“魔鬼號”上,沒有法律秩序,沒有正義與邪惡之分,沒有人性,更沒有人類最真最美的情感。船員的生命對他來說,就像是一隻螞蟻,他想讓誰死,誰就得死。正如拉森自己所說“生命沒有任何價值。它是廉價中最廉價的。”他成了達爾文主義的最忠實的追隨考和最有力的實施者。他在海上招來的船員只是拿著工資的奴隸。海豹獵手就是他的幫凶。他營救出來的遭到海難的人就成了他的廉價勞動力。用來填補減員的空缺。按拉森說法,“生命像是酵母,一種活動的東西……大吞小才可以維持他們的活動,強食弱才能保持他們的力量。”對於前任大副之死,他不僅臭罵,還粗暴地為他舉行海葬,隨便把他扔入大海了事。當新來的水手哈里森不小心被高處桅杆掛住了,隨時面臨生命的危險.拉森竟不許任何人上去幫他,還振振有詞地說;“如果他攤了下來,腦漿像蜂蜜從蜂房裡漏出來一佯流到甲板上,那對世界也不是什麼損失。他對世界毫無價值。”為了填補空缺,他逼迫被他救上船的衛登來為他幹活,不服從便打。在這個暴君的統治及影響下,其他船員也變得粗暴野蠻起來。托馬斯整天磨刀霍霍對著衛登,但衛登並不示弱,也拿來刀在磨石上整天相對,最後贏得勝利。約翰遜因說話冒犯了拉森,被他打得遍體鱗傷,體無完膚,水手裡奇打抱不平對拉森破口大罵,之後又將好事的廚子痛打一頓。在拉森統治的世界里,以暴制暴才是生存法則。
性別政治
包括作家傑克·倫敦在內的很多進步男性知識分子,他們支持和擁護女權主義,表達對社會變革的期待;但根深蒂固的傳統思想又在意識深層進行抵觸,最終常常把他們扼回對傳統權力關係的渴望中。在《海狼》中我們能夠看到某種不和諧:一方來自作家有意識表達的理念,另一方來自深藏於作家無意識的渴望;一種表現為性別政治的原則觀念,另一種是社會生活的實用主義。兩種傾向交織在一起,使小說成為一個矛盾的文本。特里·伊格爾頓認為:“正是在女權主義政治的性質里,符號和形象寫出並且戲劇化了的經驗才具有特殊的意義。”被傑克·倫敦符號化、形象化和戲劇化的認識經驗,的確有其特殊的聞釋意義。《海狼》就是一個說明問題的個案。
《海狼》首先是作為雜誌故事連載發表的,作家將不到全書一半的已寫就書稿,連同總體構思一起寄給《世紀》雜誌進行連載,然後按雜誌的發行日期要求,不斷提供新寫的後續部分。正是在這后一半中,在交稿時限的“催追”下,傑克·倫敦更少顧及設定人物的前後一致性,讓自己的真實意願不自覺地流露到了筆尖。就這樣,在對待女性社會角色問題上,小說前後部分出現了大幅度的轉向:前半部作家有意識地靠近女權思想.而後半部中作家內心的男權思想強烈反彈,讓一位社會上卓有成就的獨立的新女性,最終滑向了傳統的角色。可以在《海狼》這個戲劇化演繹的故事本身和故事背後的潛台詞中,讀到文外的另一個故事。
作家在《海狼》中不再強調“女人可以像男人”,而讓女性顯示自身無法取代的優勢,其中之一是她的精神和道德上的影響力。莫德這位年輕女子的出現,像催化劑一樣給船上的人際關係帶來了變化,不僅使衛登的角色出現了轉化,而且也改交了整個小說的走向。喬納森·奧爾巴赫認為,小說中有兩次重大轉折,一次是莫德登船,另一次是莫德和衛登到達安第弗島,兩個事件“都導致了小說主人公(衛登)象徵性的再生”。衛登在船上開始是個無助的弱者,忍氣吞聲;莫德的到達激發了他內在的能量,他不再逆來順受,開始向反叛者和保護者的角色轉化,與拉森的對立隨之變得公開和激烈。
如果把小說的男女人物歸納一下,就可以發現衛登和莫德兩人構成了正好相反的兩條發展路線。衛登開始出現為一個城市文明的受害者;進入“魔鬼號”男性社會中經受磨鍊;莫德登船后出現突變和轉折,成為保護者;在與海上暴風雨的搏鬥中證明自己男子漢的勇氣和價值;在海島的生存鬥爭中完全成為主宰。莫德一開始出現為一個解放了的新女性,不僅品貌出眾,而且具有不遜於男人的才智和能力;故事發展中很快變得無助,成為被保護者;暴風雨的考驗中在男人的表演舞台上消失,躲進船艙;到了海島上完全成為男人的輔助者,自甘回歸傳統的家庭婦女的角色。就這樣,小說在一個女性人物的設定和發展上,出現了明顯的前後不一致。於是,讀者在閱讀一部男性的成長小說時,也讀到了一部女性的“反成長小說”。
藝術特色
藝術風格
《海狼》這部作品中客觀真實地再現了“魔鬼號”上的生存狀態,讀者從中欣賞到的既有兇險、冷漠的大海,又有性格兇悍的海狼。既有人與自然的對峙,又有人與人之間的殘酷鬥爭。生存競爭和自然選擇成為了人類社會普遍存在的現象。傑克·倫敦很好地將達爾文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理論運用到小說的創作中去,從人物塑造的角度把海狼拉森塑造成彰顯其殘暴和動物生存本能的形象,強調了遺傳和環境的影響;他把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生存競爭觀點用來解釋社會現象和人際關係。提出生存是第一要務,這就使小說帶上了自然主義色彩。同時他也強調了主人公的自主性。
人物形象
為了更好地塑造人物形象,突出人物特徵,傑克·倫敦經常選擇極端的環境作為小說的背景。比如嚴寒、飢餓、驚恐、死亡,突出人在這些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下的反應。只有那些適合環境要求的人才能生存下來,否則只有死亡。《海狼》中的“魔鬼號”,因為在海上漂泊.變成了一個遠離文明世界束縛的獨立世界,法律、道德無法發揮它應有的作用。如果想在這個非道德的世界生存下來,必須符合這個小世界的生存之道,即放棄道德、拋棄幻想、動用一切、捍衛生存。在魔鬼號上,海狼代表最高的權威,憑藉他強有力的力量,統治著整條船,他可以依照自己的意願,為所欲為,甚至視別人的生命為兒戲,恣意妄為。在他的暴政下、水手們的人性漸漸地被扭曲、萎縮、變形。他們不會考慮別人的感受和利益,只是為生存而爭奪、甚至不藉以毀滅他人為代價來滿足自己的生存。小說另一主要人物凡·韋登的成長過程.也體現了小說的適者生存觀。他也是把生存作為第一要務,放棄原有的一切觀念。努力適應新的殘酷的生存環境。如果從更廣闊的角度來看,《海狼》中的“魔鬼號”可看做是人類社會的寫照,生存在上面的各色人物可以看做是人類的代表,反映出人類社會中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景象。毋庸置疑,無論是充滿獸性力量的海狼,還是想征服對方的捕海豹船上的水手們,還是凡·韋登在生存競爭中放棄教養,張揚獸性,都說明了生存成了第一要務,其餘的都得給它讓路。
對於拉森這隻殘暴的狼來說,衛登則是一隻誤入狼穴的羔羊。衛登最滿腹經綸,但是在身體上卻遠遠不是拉森的對手,他被拉森強迫去做廚房雜活,若不從便拳腳相向。他卻無反抗之力,只能順從。“就像落難於荒島的魯濱孫·克曹索一樣,他所面臨的首要問題就是如何生存下去。”衛登比拉森的優勢之處在於,來自文明世界的他,人性並未泯滅,還有人類特有的情感與理智。他與同他有一樣遭遇的莫德小姐一見鍾情,擦出了愛的火花。衛登對拉森的仇恨一是因為拉森對他人的虐待,二是他的奪人之愛,所以很多次,他都產生了幹掉拉森的念頭,但為了成功逃離“魔鬼號”的長遠之計,他剋制住了這種衝動。最終兩個人聯手共同對付拉森。他們運用計謀以及豐富的知識,終於逃脫了拉森的魔掌。他們駕著一葉扁舟漂到了一個海豹聚集的小島上。在發現了漂浮到小島的”魔鬼號”之後,衛登把當學生時所學到的物理知識運用到實踐中去,成功製造出新的桅杆,修復了“魔鬼號”,而這時拉森的身體狀況每況愈下。但衛登與莫德並沒有伺機報復,而是細心照料。當看到拉森雙目失明、頭疼病發作摔倒在甲板上時,衛登與其錫出於同情前去照料他,不想拉森突然死死掐住衛登的咽喉,在緊要關頭,莫德本能地拿起捕海豹的木棍砸開了拉森,這讓衛登讚嘆不已:“她真是我的女人,我的伴侶,伴我而戰,像遠古的穴居人的伴侶—樣,她的全部原始本能都覺醒了,忘卻了她所受的教養,在她從前所過的那種惟一的讓人弱化的文明生活下變得堅強起來。”雖然他們的耐心與關愛並沒有留住拉森的生命,但這給充滿黑暗、暴力的畫面帶來了一絲絲人性的充環。隨著拉森的安葬,他的“叢林法則”隨著他一起安眠於海底。這象徵潛弱者戰勝了強者。
雖然傑克·倫敦傾向於把凡·衛登塑造成正面人物,而把拉森塑造成反面人物。但作者並沒有把拉森刻畫得一無是處,而把衛登描寫得盡善盡美。凡·衛登曾經手無縛雞之力,在“魔鬼號”上當雜役,通過於體力活,肌肉變得發達,性情越來越勇敢,從而得到了全面“鍛煉”。可以說,傑克·倫敦在取拉森之長補凡·衛登之短。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文弱書生”並不是傑克·倫敦的理想人生模式。而以物質利益為第一追求的“霸權主義”式的強者,也不是他所提倡的。賦予強者以人道主義思想,才是傑克·倫敦的理想人生。
《海狼》被譽為是海上題材里的精品之作之一。這個故事,不僅在文學上獲得了很大的成功,而且也被後人搬到了銀幕上,也受到了廣泛的好評。

傑克·倫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