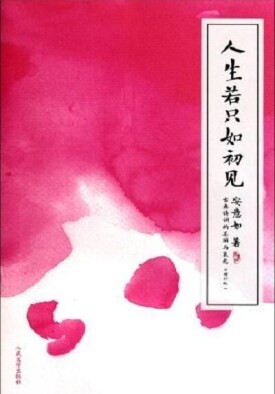共找到16條詞條名為人生若只如初見的結果 展開
人生若只如初見
安意如所作散文集
《人生若只如初見》是安意如的作品,是2006年6月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部綜合性的詩詞鑒賞類散文集。該書多選取古代才子佳人的故事,配合古詩詞內容進行賞析解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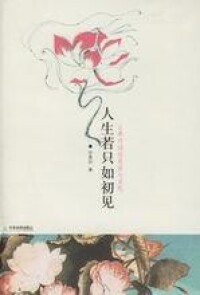
封面
她似在談詩詞,又似在談風月。她不拘泥於對古典詩詞字面的理解,也非傳統意義上的簡單賞析,而是一種風格獨特、感情豐富的散文隨筆。
詩人,詞人,凸現其曠世奇才與至真性情。才子,佳人,似笑非笑的嫣然,執迷不悔的凜然,心照不宣的釋然,讓我們在悲喜交加中恍然……
他們憤世嫉俗的不羈性情,她們旖旎獨特的古典韻致,共同演繹出流傳千古的浪漫往事,為我們留下太多可歌可泣、可感可嘆的愛情回憶。
邂逅一首好詞,如同在春之暮野。邂逅一個人,眼波流轉,微笑蔓延,黯然心動。若,人生若只如初見,多好。
他仍是他的曠世君主,她仍做她的絕代佳人,江山美人兩不侵。
沒有開始,就沒有結束。
| 人生若只如初見 | 1 |
| 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 9 |
| 天地合,乃敢與君絕 | 15 |
| 願得一心人,白首不相離 | 20 |
| 結髮為夫妻,恩愛兩不疑 | 26 |
|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 31 |
| 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 | 36 |
| 潘岳悼亡猶費詞 | 41 |
| 天不絕人願,故使儂見郎 | 50 |
| 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 | 54 |
| 昔日芙蓉花,今成斷根草 | 58 |
| 與君初相識,猶如故人歸 | 62 |
| 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 | 69 |
| 薛濤箋上十離詩 | 74 |
| 至高至明日月,至親至疏夫妻 | 83 |
| 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 | 88 |
| 唯將終夜長開眼,報答平生未展眉 | 93 |
| 從此無心愛良夜,任他明月下西樓 | 96 |
| 星沉海底當窗見,雨過河源隔座看 | 103 |
| 三生杜牧、十里揚州,前事休說 | 107 |
| 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 | 112 |
| 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 | 119 |
| 傷情處、高城望斷,燈火已黃昏 | 124 |
| 江城子 | 130 |
| 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 | 135 |
| 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 | 140 |
| 風住塵香花已盡 | 146 |
| 一杯愁緒,幾年離索 | 151 |
| 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 157 |
| 斷腸詞 | 162 |
| 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 | 172 |
| 斷腸人在天涯 | 179 |
|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 183 |
| 當時只道是尋常 | 189 |
| 後記:功夫應在詩外 | 196 |
(九思寫)
我沒見過安意如。半年前的一天,我在博客上偶然看到她的一篇《桃夭》,初看時文字質樸,以為是個男的,再細看另一篇《妙玉愛玲》,也就是後來錄入《看張》那本書中的一篇,才發現她是個女孩子。起初以為她是張愛玲的崇拜者,因為我已經知道了她的年齡,對她對張愛玲的深刻理解很驚訝。以為不用全力是不能達到的,而用了全力,張的幽暗絕望對她應當是沒有好處的。於是好為人師的指導她不要沉溺於張的小資世界……“所以,當時代很熱鬧之時,如果能敞開心靈迎接世界當是最好的。”但她隨後回復,那只是為了寫作,不沉溺、不膜拜,只是要費些心思罷了。很快她完成了《看張》的工作,並筆耕不輟,更讓我確信了她的筆力。
那一段時間她每天解一兩首《國風》,從《周南》到《召南》,從所選的篇目上,我看到了她的眼光和對詩的具有穿透性的理解力。一般來說,《詩經》名頭之高婦孺皆知,是中國詩歌的源頭,但從漢代以來,就沒有幾個真正能完全懂得的了。讀《詩經》如果沒有註釋,將是寸步難行。大多數說自己喜歡《詩經》的。只能夠喜歡《蒹葭》、《關雎》等少數篇章中的少數句子罷了,真拿了“詩三百”讓他讀,可能只是如葉公好龍束之高閣了。她邊讀邊解,文字如那四言詩一樣,讓人搖旌以夢,於是,油然而生敬佩之情。
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這就是中國詩可抒不平之怨,可達社會之用,可寄山水之情的思想源頭。因為有了詩教,我們可以不求諸宗教的迷狂而自有生命的皈依與安逸。讀詩、誦詩、解詩是我們優秀的傳統。詩歌塑造了我們的詩心。但史詩三千年,多數詩歌都因年代久遠而與我們的生活隔膜起來,除了極少數外,我們讀詩都需要藉助參考書。通過參考書我們了解字義、詞義、背景等等。但參考書紛繁多樣,註釋也常出歧義。除開這些不講,光是訓詁考據也要消耗太多精力,必然破壞讀詩的整體美感,等到弄懂詩文中的字義詞義,再去欣賞,已經沒有更多的心力了。
安意如這本書也是讀詩的參考書,但不是註釋書。“沉吟”,不是朗讀,不是歌唱,而是用心去讀,用心去感應。感應詩歌、感應詩人、感應詩心。安意如還是位二十來歲的女孩子,不是學問家,但她懂詩。因為她懂人,更懂得詩人。詩人都是真性情的自在人,不管是古人還是今人。但對大多數人來說,詩人都是怪人,他們不懂人情世故,癲癇痴狂,常常與人格格不入。可“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安意如就是其中的“知我者”,是可以和古今詩人心靈相通的人。因為她自己同樣擁有一顆詩心,但又不拘泥於詩,她首先著眼於弄懂詩人。她先看詩人的敏銳,再看他們的俯仰沉浮,還看他們的生活交遊。她透過詩文體味詩的境界,掌握詩的典故,了解詩人的生活,然後再從小處著手,以小說家的想象力和詩人的敏銳,寫出了這些既有嚴謹的史實,也有精闢的論述,還有圓通的故事的美麗詩話,讓時代久遠的漢字再現還原了詩情、詩景、詩事、詩史,歷歷在目,玲瓏精緻。
她解曹操的《短歌行》中寫道:“‘青青子衿’二句直用《子衿》的原句,一字不變,意喻卻變得深遠。連境界也由最初的男女之愛變得廣袤高遠。曹操說‘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固然是直接比喻了對賢才的思念;更值得注意的是他所省掉的兩句話:‘從我不住,子寧不嗣音?’他用一種委婉的含蓄的方法來提醒那些‘賢’:‘我縱然求才若渴,然而事實上天下之大,我不可能一個一個地去找你們,就算我沒有去找你們,你們為什麼不主動來投奔我呢?’”經她這樣對比提醒,曹操就不單是簡單的深沉、含蓄,同時他那海納百川的帝王氣概也栩栩如生了。她寫秦觀道:“我心底透出的意象里,少游這個人,應是青衫磊落,煢然獨立於花廊下,抬頭看著樓上的愛人,臉上有陽光陰影的文弱男子,有著暗雅如蘭的憂傷。那青草清輝般的邂逅,應是他的。那時候,我甚至懷疑他眉間的愁緒,是他愛的某個女子也抹不平的。他骨子裡是凄婉的,連思人也是‘倚危亭,恨如芳草。過盡飛鴻字字愁’,比易安的‘滿地黃花堆積,雁過也,正傷心,卻是舊時相識’還要幽邃深長的思意,稀貴而真誠,所以隔了千年看去仍是動人。”有了這樣一個秦觀,我們再去看“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里斜陽暮”,又是怎樣的哀婉悲切呢?她解柳永:“晚年的柳永落魄潦倒,身無分文,但他的死卻是轟轟烈烈、蕩氣迴腸。相傳柳永死時,‘葬資竟無所出’,妓女們集資安葬了他。此後,每逢清明,都有歌妓舞姬載酒於柳永墓前,祭奠他,時人謂之‘吊柳會’,也叫‘上風流冢’。沒有入‘吊柳會’、上‘風流冢’者,不敢到樂游原上踏青。並形成一種習俗,一直持續到朱室南渡。後人有詩題柳永墓云:樂游原上妓如雲,盡上風流柳七墳。可笑紛紛縉紳輩,憐才不及眾紅裙。‘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是他寫出的流傳千古的名句,深情宛然可繪。草色煙光殘照里,我遇上柳七,也會備下清酒佳肴,供他淺斟低飲,不會讓他一人把欄桿拍遍,感嘆無言誰會憑欄意。”這樣被我們常常定格為溺於酒色的柳三變是不是會讓人覺得更加意味深長呢?
我想,安意如的方法定然會讓一些學問家不以為然,但我以為這的確是讀懂詩詞、理解詩人的捷徑,因為詩本身應當是生活中的最真,功夫自然應當是在詩外的,而不僅僅在文字之中。
| 出版年 | 名稱 | 出版社 | ISBN | 頁數 |
| 2011-8 | 人生若只如初見 | 人民文學出版社 | 9787020070008 | 343 |
| 2006-8 | 人生若只如初見 | 天津教育出版社 | 7530945726 | 197 |
安意如,原名張莉,女,雙子座,1984年6月20日出生於安徽績溪,現定居北京。自由寫作者。喜歡旅行,變換不同的城市居住。2002年畢業於安徽某中專院校,做過短時的會計。
2003年 以“如冰戀楓”為名混跡於金庸客棧。
2004年 應書商之約寫第一部長篇小說《要定你,言承旭》,於2005年6月由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當時筆名為粉Q女生)翌年2月赴京參與動畫劇本創作,並寫作《看張·愛玲畫語》,由雲南美術出版社於2005年9月出版。
此後與北京弘文館建立合作關係,創作詩詞評賞“浪漫古典情”系列,2006年8月至10月由天津教育出版社推出其中的《人生若只如初見》、《當時只道是尋常》和《思無邪》。這三本書因大量內容一字不改地複製他人作品引發媒體爭議。2007年6月出版言情小說《惜春紀》(此書因改寫《紅樓夢》人物關係而引起爭議,其中最令人匪疑所思的當屬惜春成為秦可卿與賈珍“夫婦”的女兒)並因內容高度“模仿借鑒”晉江goodnight小青專欄小說引起網友指責。其中有若干段落與二月河《康熙大帝》中的內容高度一致。)
2009年1月 與人民文學出版社合作出版《觀音》,賞析元代戲曲。
2009年8月 出版新書《美人何處》。P228頁內容系照搬南宮博歷史小說《楊貴妃》第三十六節內容。
2010年 出版新書《世有桃花》,萬卷出版公司出版。《世有桃花》是安意如繼“漫漫古典情系列”《陌上花開》重回古典詩詞賞析的新作。以桃花為經,歷代經典詩詞為脈絡為緯,漫談古今人事滄桑。被讀者指出第一章內容與顧天藍《玫瑰傳說》高度相似,第四節《郎騎竹馬來,繞床弄青梅 》內容與豆瓣網電影《melody》諸篇評論相似,第四十二節《桃花詩案》內容與廈門市少年兒童圖書館網路版讀物《變幻中的乾坤》一章《二王八司馬》內容高度一致,且部分語句完全複製自此。同時,其對二王八司馬事件的評價來源於學者馬立誠所寫《二王八司馬的146天》。
2012年1月出版《日月》。內容抄襲劉鑒強《天珠:藏人傳說》。
2012年12月出版《再見故宮》,多處抄襲或改變歌手河圖所唱歌曲的歌詞,涉及詞作包括finale《風起天闌》、《命懸一線》、《如花》、《傾盡天下》、狐離《第三十八年夏至》等。同時,本書被指有抄襲百家講壇與《明朝那些事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