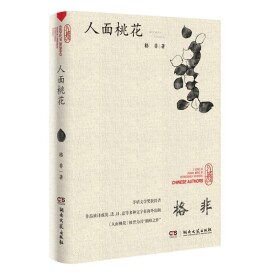共找到22條詞條名為人面桃花的結果 展開
人面桃花
格非著長篇小說
《人面桃花》是作家格非《江南三部曲》中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小說講述的是一個女人追尋她的夢的故事,這個夢包含兩個方面,一是她的愛情,另一是她的理想。因此,整個故事的主旨就落在了“追尋”二字。它同樣包含兩層涵義:一是主人公陸秀米追尋她的夢,另一是敘述者帶領讀者追尋那段業已逝去的革命歷史。
《人面桃花》2005年獲“華語文學傳媒大獎”、2004年度“傑出成就獎”。
![人面桃花[格非著圖書]](https://i1.twwiki.net/cover/w200/m4/e/m4eadd403afabf0c8daf4e0f6fe58ed56.jpg)
人面桃花[格非著圖書]
秀米於出嫁途中遭遇土匪綁票,被劫至偏野小村花家舍的一處湖心小島上。但同一時間,土匪雲集花家舍亦在醞釀著一場重大事變。在島上,秀米從一名尼姑韓六的口中得知了花家舍的所有秘密。她對父親在普濟建立桃花源的瘋狂舉動似有所悟,而閱讀張季元留下來的一本日記,也使她了解了革命黨人創立大同世界的真正動機。隨著土匪頭領們一個個神秘死亡,花家舍這個“人間仙境”於一夜間變成一片瓦礫,而暗中活動的革命黨人六指木匠則控制了局面,並收編土匪於第二年發動起義,攻打府州梅城。起義失敗后,秀米被送往日本。
幾年之後,陸秀米受革命黨人指派從日本帶著年幼的孩子返回普濟,聯絡地方豪強,進行革命準備,並建立普濟學堂。在當地人的眼中,秀米已經變成了與父親一樣的“瘋子”。她的革命藍圖中混雜了父親對於桃花源的夢想,張季元的“大同世界”,當然還有花家舍的土匪實踐,帶有強烈的烏托邦色彩。在清兵的一次圍剿中,秀米被捕並押解至梅城,她的孩子也於亂中被殺。就在秀米被清廷處死的前夕,辛亥革命爆發。秀米被關押一年半后獲釋,回到普濟。回到普濟后的秀米發誓禁語,將自己變成了一個啞巴。
| 第一章 六指 | 第二章 花家舍 | 第三章 小東西 | 第四章 禁語 |
格非經過十餘年的沉寂、辛苦付出,在“江南三部曲”中表現出了不同於以往的創作方式。20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尋求轉變成了先鋒作家們的共同期許。格非是一個很有思想的人,在先鋒作家中,他能站在很高的位置上,在尋求轉變的時,他也是引領者。從詩詞中選取標題,從古典詩詞中提取寫作題材,在當時創造了一種新的小說寫作方式,也就是詩詞典故的小說再敘事,《錦瑟》也是如此,“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人面桃花》是格非對待傳統小說的寫作方式的態度的轉變,可以看做是格非對中國古典詩學的再創造與致敬。小說中應用大量的詩詞、歷史人物的旁註、縣誌、廟宇的來歷註釋等。從“人面桃花相映紅”中截取了“人面桃花”作為題目。

人面桃花 封面
陸秀米
秀米少女時代是在普濟渡過的,那時的她天真、活潑、調皮,是一個整天愛做白日夢、無憂無慮的官家小姐。她衣食無憂,充滿好奇心,起初的生活單純、平坦,但是隨著生理心理上的成熟,讓她遭遇了被擄花家捨得奇特際遇,和讓她和張季元遭遇到如宅黛悲劇式的愛情。愛情讓秀米走上革命道路,她繼承了張季元的理想和事業,從封建少女成長為思想開放行為進步的革命新女性。
張季元
算得上是一位現代知識分子,留學回國后他致力於在中國的土地上傳播西方的啟蒙思想,並試圖以啟蒙為出發點,建造一個“大同世界”,以改變清末的動亂現狀,重新開闢一個新的時代,創造新的歷史。在這個新舊交替的時代,革命者獲得了實現自己的理想的舞台。
張季元抱著這個烏托邦理想,開始了自己的革命探索。他與同樣東渡日本留學的周怡春(小驢子,又名六指)等人組織蜩蛄會,投身革命。為了商議反清事宜,張季元來到普濟並住進了陸秀米的家中,暗中在夏庄薛祖彥家中建立了聯絡點。張季元認為在未來的社會,每個人都是平等的,也是自由的。但他對自由的表述在很大程度上帶有情慾的色彩。但就張季元本身而言,他的個人慾望與情愛糾纏也是不容忽視的,一方面他與陸秀米的母親梅芸有著私情,另一方面又為秀米著迷,甚至發出“沒有你,革命何用”的感慨。
這種帶有個人慾望色彩的革命註定了其走向衰落的更大可能。張季元的懷疑及苦惱,使他作為一個人活生生地出現,而並非一個拯救社會的完美無瑕的革命鬥士。他有著人的私慾以及弱點,特別是他對秀米的迷戀,可以說正是秀米讓他覺得革命沒有價值,也正是秀米讓他懷疑他所追尋的答案其實在別處(即在秀米所象徵的慾望對象那裡)。如果說革命是一個建立“大同世界”的未來的未及的理想,那麼秀米就是一個現有的眼前的美好存在。
他的迷茫、動搖及懷疑恰恰表明他只不過是一個普通人,一個有著革命理想的普通人,並不是革命文學中那些被神化了的英雄。革命者的形象在這裡非但沒有被神化,有的顯得更加真實甚至卑瑣。投身革命的他充其量只是嘴上應承了革命,他並未考慮更多,更談不上把革命當做理想般追尋。個人的慾望以及懷疑、朝廷密探的發現以及革命同盟者的倒戈、革命力量的微弱都不同程度導致了張季元革命探索的失敗。
陸侃
陸侃以一個出走的“瘋子”的面貌出場。他出走的原因無從可知,他發瘋的原因卻眾說紛紜。陸侃在遭遇到官場失意仕途不順,特別是被罷官回到普濟后,深感難以實現平生抱負,於是他自然而然地寄情於“桃源”這片理想的樂土。就在他發現普濟或許是陶淵明所寫的桃花源時,他選擇了深信不疑,並且想在這片“桃源發源地”再做出一番貢獻,他想要在普濟種滿桃花,建造一條風雨長廊為普濟人遮風擋雨,這無疑還是一種傳統的“士大夫”兼濟天下的決心與抱負。陸侃的“瘋”恰恰表明了他對心中理想主義執念的狂熱,然而當理想主義再次遭遇到現實(為官時理想主義已經遭到一次“被罷官”的現實),他必然感到“桃源”理想與現實的差距以及不可實現性,因此他呈現出一種“發瘋”的狀態。
但是在他“發瘋”之後,全家想盡辦法給他醫治,讓他安靜下來,最後將他囚禁於閣樓上,至此他無力也無法做些什麼了。“桃源夢”僅只能成為一個夢,這使得陸侃的理想更顯出一些悲劇意味。而陸侃真正的有所行動,便是下樓,然後出走。陸侃下樓后,然後對女兒秀米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普濟馬上要下雨了!懵懂的秀米只看見普濟晴朗的天,她並不曉得父親的預言——晚清社會的動蕩如風雨飄搖,時代變化的端倪更是山雨欲來風滿樓!或許陸侃心有不甘,或許胸懷抱負,最終他懷揣著不曾改變的“桃源”夢想離開了家。他的出走是他唯一的行動但卻極具象徵意味,暗示著一個新的時代的來臨。
王觀澄
王觀澄是同治六年的進士,點過翰林院,繼而“中歲好道,頓生隱逸之念”。他之所以渴望遠離塵世,最根本的原因可能是而且也應該是面對社會的動蕩繼而嚮往一個心靈安寧的精神家園。他尋訪明代道人焦先的遺跡來到了花家舍,起初受到陶淵明影響的他獨自在島上歸隱而居,但漸漸他的心思變了,他並不滿足於自己的安寧,他想讓島上的每一個人都能夠過上安寧富足的生活,他開始執著於將花家舍打造為一個“世外桃源”。
選擇隱居的王觀澄不求天下,只求把花家舍建成人間仙境。曾經帶過兵打過仗的王觀澄為了籌集資金想到了去搶,他把搶來的錢財均分,漸漸島上的人民竟然被教化得謙恭有禮,搶來的東西人人都爭著拿最壞的。雖說他只搶富賈不害百姓從不殺人,但這畢竟算不得光彩。然而王觀澄沒有想到的是土匪並不好當,人手不足的他無奈只能糾集三個舊部一起通過綁票籌錢。那三人各自擁有人馬,因此時間一久王觀澄難以約束只能任由他們胡來。特別是在王觀澄操勞過度一病不起之後,三人權力之爭更甚從前。
似乎王觀澄的“桃源”實踐成功了,可他卻感到了厭倦。花家舍的一切對他而言呈現為一種虛無,他開始懷疑這一切,並想過要親手毀掉自己親手建立的一切。然而他沒能親手毀滅它便喪生於革命黨人小驢子策劃的連環命案中。小驢子為召集攻打梅城的人馬來到了花家舍,利用花家舍頭領們暗地裡的不和及權力爭鬥策劃了一系列的暗殺。王觀澄去世,其餘的頭領也在猜疑與恐懼中一個接一個地死去。最後花家舍的美好在一場大火中灰飛煙滅。在動蕩的年代,如花家舍般的“世外桃源”是不可能存在的。

人面桃花 封面
《人面桃花》是格非以獨特的歷史觀念並結合生命想象精心營構出的一部長篇小說。有別于格非前期的“先鋒”話語,在這部作品中,格非致力於更樸素、更寧靜、更溫婉、更細膩地去闡釋人生,洞悉歷史。在對逝去記憶的鉤沉和對歷史場景的呈示中,向讀者講述了中國近現代歷史演進中,一個並未進入整體與歷史主流的女性個體生命——鄉村女子秀米,如何輾轉奮爭於烏托邦理想建構的身心歷程及其傳奇故事。
小說以光緒27年的春天,在家瘋了多年的父親突然從樓上走下來,他的女兒秀米面臨著初潮一人在院子洗褲子的時候,父親卻平靜地走出家門。之後,一家人百般尋找后仍是無影無蹤,剩下的是一個個關於父親的謎團:他是怎樣瘋掉的?他留下的最後一句話預言著什麼?在父親出走的同時;“表哥”張季元從梅堀來到陸家,這張季元的身份又是讓人一頭霧水。格非在小說開頭巧妙地製造了諸多的懸念,《作家》雜誌主編宗仁發認為,《人面桃花》在故事層面達到幾臻完美的程度。這是一部精緻的小說,格非是國內先鋒小說作家的一面旗幟。他在小說中製造了許多“迷惑”的成分,故事曲折紛雜,而且有著淡淡的暗示。
烏托邦形態
一種是王觀澄所創建的以花家舍為載體的古典形態的江湖烏托邦,一種是陸秀米所創建的以普濟學堂為代表的現代形態的革命烏托邦。關於這兩種形態的烏托邦敘事佔據了這部長篇的絕大部分篇幅,而女主人公陸秀米的人生歷程恰好把這兩種形態的烏托邦敘事貫穿了起來。正所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小說中兩種不同形態的烏托邦敘事也凝聚了各自不同的群體成員,亦可謂之為精神家族。從古典形態的烏托邦來看,陸秀米的父親陸侃無疑屬於這一精神陣營。陸侃飽讀詩書,學優則仕,然而仕途並不通達,罷官后在普濟築屋隱居,怡然自樂。但陸侃心中一直有著難解的桃花源夢想,他時常對著據說是出自韓愈手筆的《桃源圖》發獃發痴,他想在普濟重現陶淵明的世外桃源的現實圖景,他甚至構想建築一條風雨長廊把普濟的住戶聯接起來,讓老百姓不懼風雨、安居樂業。在普濟人的眼中,陸侃就是一個瘋子,他的妻子和女兒還有家佣,全都把他看做瘋子。瘋子是孤獨的,因為他有著常人難以理會的超越現實的衝動,這種衝動常常就是西方人所謂的烏托邦衝動。
在常人那裡,這種烏托邦衝動往往被壓抑在潛意識域,而在瘋子或先知這裡,這種衝動時刻在尋覓著對象化或現實化的契機,這就是常人與瘋子的一大區別。瘋子陸侃的離家出走,給女主人公秀米的人生帶來了重大轉折,因為革命黨人張季元隨即住進了普濟秀米的家,他是秀米的母親的情人。在很大程度上,張季元充當的是陸秀米的“代父”角色,他的到來改變了秀米的人生方向,他給秀米帶來了現代的革命烏托邦衝動。張季元是清末革命黨組織——蜩蛄會的核心成員,推翻封建專制的腐朽清王朝,建立現代的民主自由世界是他那一類人的桃源夢想,小說中的薛舉人薛祖彥、小驢子周怡春,包括女主人公陸秀米等在內,都屬於這個烏托邦家族的精神成員。不過對於秀米來說,她一開始並未明確地接受“代父”張季元的革命烏托邦衝動的影響,她對張季元的戀父衝動更多地表現為她與母親梅芸之間的暗中情感較量。轉折發生在秀米被劫掠至花家舍以後,她在花家舍這個土匪窩子裡面居然看到了父親理想中的桃源夢境全部得以實現了。
在花家舍里,包括總攬把王觀澄在內,其他五位爺都是很有些來歷的人,有的從文、有的習武,他們把花家舍經營得像一片世外桃源,讓來者無不嘆為觀止,但對於知情者而言,花家舍就是一個土匪窩,就是一個江湖世界,其中充滿了刀光劍影和爾虞我詐,充滿了血和淚。花家舍其實是一個人間天堂的幻影,看似美妙無比,實則隱藏著巨大的災難和危機。秀米在花家舍慘遭蹂躪、九死一生的經歷使她最終放棄了父親陸侃的古典烏托邦理想,而走上了“代父”張季元遠走東瀛,致力於反清抗暴,建構現代革命烏托邦的道路。
格非在《人面桃花》中不僅寫出了古典江湖烏托邦的破產,而且也寫出了現代革命烏托邦的危機。秀米自日本歸來後繼承了張季元的遺志,她在普濟一帶神出鬼沒,彷彿當年的張季元再世重生。她領導成立了普濟地方自治會,在一間寺廟裡設立了育嬰堂、書籍室、療病所和養老院,然而一切如同虛設,她牽頭的水渠工程甚至還差點給普濟帶來滅頂之災。自治會計劃受挫后,秀米又辦起了普濟學堂,自任校長,直接致力於反清革命活動。正如陸家的老管家寶琛所察覺到的那樣,他對老夫人說:“你說她走了當年陸老爺的老路,我看不大像,照我看,她是把自己變成了另一個張季元。那個死鬼,陰魂不散。”確實如此,秀米就是另一個張季元,她心中涌動的是張季元式的現代革命烏托邦衝動,而不是陸侃式的古典江湖烏托邦衝動。秀米無意於相忘於江湖,過那種隱居般的桃源生活,她需要的是介入,介入到改變現存社會秩序的烏托邦進程中。這意味著暴力革命,秀米也確實捲入了革命的暴力之中,她甚至因為沉迷於暴力革命而忽視了基本的親情倫理,母親和兒子的死在不同程度上她都難辭其咎。
現代的革命烏托邦之間的精神淵源
金蟬是小說中革命黨人之間傳遞的信物,女主人公秀米的一生與金蟬有著不解之緣。當初張季元在臨難逃亡前第一次贈給她金蟬,這是兩人之間革命烏托邦衝動傳遞的精神信號。第二次是在花家舍被困期間,老尼韓六送金蟬給秀米,在某種意義上喚醒了秀米內心的革命烏托邦衝動。第三次是小驢子送金蟬給秀米,此時秀米在革命失敗后閉門禁語,她拒絕小驢子的來訪,這意味著革命烏托邦衝動在她的內心深處已寂滅。喪失了革命烏托邦意義的金蟬不過是一個無用的空殼而已,它在災難的歲月里只能被廢棄。小小的金蟬脫殼,恰好隱喻了秀米追逐烏托邦的迷幻人生。還有一個在小說中反覆出現的意象是瓦釜,它其實是一件古老高妙的樂器,這是父親陸侃的遺物,晚年的秀米在瓦釜里逐漸融化的冰花中彷彿看到了自己的過去和未來,遠去的父親陸侃和遺失的兒子譚功達正在向她走來。秀米就在這種幻覺中死去,她無法拯救自己,除了彌合自己內心的創傷,她無法阻止自己精神密碼中的烏托邦衝動開始再度輪迴。
這部小說比他以前的小說更容易閱讀。他說:“我曾經只重視小說的哲學內涵,現在我覺得人物和故事是小說的血肉。這部小說中我第一次考慮到塑造人物和講好故事。”但格非的小說並不是簡單通俗地寫故事,依然帶有明顯的先鋒小說的痕迹。格非解釋,他不想完全放縱讀者,希望自己的小說能夠留有一定的“難度”。應該感謝格非!他花了十年功夫構建成這座迷幻、悠長的“迷宮”,讓讀者領略到一段曲美、繁華的“生活通道”。
古典韻味
在小說的敘述方式上,《人面桃花》頗多中國傳統小說的神韻。其中最突出的,應該是對故事性的講究,跌宕起伏,多姿多彩,卻又嚴絲合縫,堪稱“考察細密”,其中的神秘玄疑又增強了故事的可讀性與吸引力。
格非的敘述也比先鋒時期顯得平實,細節力求生動逼真,情節則清楚完整。這一切似乎都在向古典與傳統靠攏,但在這種形似的平易流暢中,卻又能分明感覺出這是一部運用“現代”技法完成的小說,而並非傳統方式的匠心獨運。以小說中的“煙火氣”為例,格非曾經感慨先鋒以來的中國當代小說太少煙火氣,他通過閱讀發現,傳統小說多描摹人情世故,而“現實的人情世故寫好了之後,就能上天入地”,也就是由生動鮮活的形而下達到抽象深刻的形而上,格非將之概括為“通過寫實達到寓言的高度”《人面桃花》里有大量的生活細節,格非這樣做是想使小說充滿生活氣息,通過逼真生動的“煙火氣”,逐漸過渡到“形而上”,使《人面桃花》的抽象認識最終通過生動的人物命運來完成。
但作品顯示出,通往哲理之思的手段仍是抽象的,而不是具體的。根本原因在於,格非在小說中所設計、表現的情節和細節不能給人以生活的真實氣息。它們精緻、有聲有色,但常常具有象徵和假借的意味。《人面桃花》在生動可感上,與中國傳統小說完全兩樣,而更接近中國古典戲劇。
中國古典戲劇往往有一個吸引人的故事,但在舞台這個有限的空間和時間裡,講故事的過程並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刻畫人物,表現其心理和性格,以及不同心性之間的矛盾衝突,大段的唱詞都用於這些方面。在情節的變化上則交代得非常簡潔明快。同樣,《人面桃花》的生活情節與細節,幾乎沒有一個是浪費的,幾乎都具有豐富的意蘊。比如開篇“父親從樓上下來了”(離開),秀米向翠蓮詢問“初潮”(成長),張季元看秀米洗頭(性),這些都不是無意義的生活流,而是精心選取的,各有意義所在。它們繪聲繪色,儼然生活的真實場景。但在細節的閱讀效果中,它們大多具有象徵的意味,是此岸為了通向彼岸的鵝卵石,而不是可有可無,點映成趣的海景。

人面桃花 封面
瀋陽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胡玉偉:格非的小說始終體現出一種文學的力量。秀米在故事的結尾寂然離去。這種女性人生的歷史性訴求和建構,這種置身於個人與歷史的緊密關聯中而壓抑個體感情的巨大痛苦,使小說產生了深刻的悲劇力量。女性性別境遇與民族境遇、歷史境遇的顯隱糾纏,人類日常性話題與終極性話題在文本中的同生共長,使《人面桃花》不僅僅給人以閱讀快感,意蘊也尤為深長。
遼寧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張學昕:格非在這部小說的寫作中顯得格外輕鬆,格非寫就這部很純粹的小說的主要原因,絕不僅僅是他技巧的純熟,更主要的是格非對小說、對事物的一種徹悟和寬容,對歷史、對人性理解的一種胸懷大氣、達觀和淳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