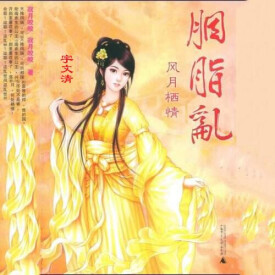宇文清
《胭脂亂:風月棲情》中人物
宇文清,是 寂月皎皎著的小說《胭脂亂:風月棲情》文中主角人物。小說中,醫者白衣,就是宇文氏宇文三公子宇文清,宇文昭三子,宇文昭謀反后,曾將宇文清許配給公主棲情,后皇甫棲情與太后逃亡途中,因遭遇安亦辰襲擊追殺,太後生病,棲情請出世為醫的醫者白衣身份的宇文清前來給其母后治病相識。初識兩人既有好感。可惜棲情並不知道白衣既是宇文清……
點點燈火遙映十里亭。
宇文清漠然負手。晚風吹動樹葉,嘩嘩作響。
四名侍從已在亭外等候了很久,眼看夜色沉寂,卻不敢上前打擾。
又過了片刻,只聽宇文清長長嘆了一口氣,然後身影出現在亭口。
一名侍從連忙迎上前去,輕聲道:“大人?”宇文清沒有回應,低頭慢慢踱了幾步,才低聲道:“去小月湖。”
兩盞燈籠光暈朦朦,向路的深處行去。
光陰如念,一閃即逝。宇文清在轎子里想。
他進了書房,閉了房門,看公文和書簡,還是午時。窗欞間陽光散落。
待他出來時,那一片殘霞已映得半空如血。他站在台階上,看那紅色倏忽詭異,蒸騰流散。不停變幻。金色與紫色的雲層疊橫亘。一些聲音在遠處低低呼嘯,落寞而蒼涼。
書房的几案上放著淡紫色的吏部公文。窗欞間透過的一縷餘暉在上面流動。中書省,國家樞密柱石重地,天子近府,龍門之所。多少仕途中人窮盡一生經營,而望之興嘆。如今,宇文清就要進京入中書省赴職,離開這裡。
興奮,有一些。可宇文清沒有感覺多少狂喜。
五年,作為一方州郡長官,宇文清自信民生富足、政績過人。可僅僅這樣就可以吏部擢優、入職中書省嗎?他苦笑。
如果不是因為他的恩師,尚書令大人。
想起此處,一絲不安在心裡最深處飄忽不定。
書簡,是恩師派人送來的。看完后,他沉思片刻,把它點燃化為灰燼。
旬日後,充滿風雲變幻和希望的日子就要開始,所以有些話最好放在心裡。
轎子里的他又想起那個女子。
離開了,我就再也見不到她了。
其實我本來見不到她的。
那天晚上封笑言相邀賞月,在小月湖。
他本不想去。可封笑言不僅是當地名士,也是他的至交好友,盛情難卻。
那夜觥籌交錯,琴聲一縷。繁華如斯,寂寞如斯。望著撫琴的女子,宇文清突然有些恍惚。
她纖弱而美麗,敏感而脆弱。
我看見她笑得很疲倦。她撫琴的時候,那兩縷黑髮垂了下來,在她白玉般的腮邊,觸目驚心的黑。
每次我與她在一起,都能看到她眼神里的那一絲飄忽不定的光。有時很,有時卻很失望,有時甚至是,怨毒。
我不知道一個的女子怎麼會有這樣複雜的神情。
有一次我睡著了,發現她在看我。她把一件衣服披到我的身上,端著銀燈靜靜地看我。帶著一絲憐惜。
我很奇怪她會這樣看我。後來我發現我很喜歡她這樣看我。當然是我假寐的時候。
她彈的那曲古風,安靜,澄明。在這裡我可以把心放下,好好休息一下。
她有時笑著笑著就會突然膽怯下去。
可惜她是歌伎。
我知道她在想著一個人。
我知道他很愛那個人。
那個人是誰呢?
有低低的聲音傳來,那是湖水拍岸的聲音。
花間舫就在面前。
宇文清聽到熟悉的琴聲。然後他對侍從們說,你們回去。
今夜,他想留在這裡。
《胭脂亂:風月棲情》 寂月皎皎 著
醫者白衣 宇文氏宇文三公子宇文清 宇文昭三子 宇文昭謀反后 曾將宇文清許配給公主棲情 后皇甫棲情與太后逃亡途中 因遭遇安亦辰襲擊追殺 太後生病 棲情請出世為醫的醫者白衣身份的宇文清前來給其母后治病相識。初識兩人既有好感。可惜棲情並不知道白衣既是宇文清。
有狗尾巴草作證:狗尾巴草,一頭系著你,另一頭系著我,證明我們曾經手牽手,是極好的朋友。
原文:那一年,我十四歲。
豆蔻年華,情竇初開。
狗尾巴草,一頭系著你,另一頭系著我,證明我們曾經手牽手,是極好的朋友。
其後與棲情公主相戀 棲情心底最愛的人 雖然中間有太多誤會 導致其間棲情嫁給安亦辰做王妃
其中曲折 令人感嘆命運的多桀 白衣宇文清的無奈 棲情的誤會 夾雜著心碎 亂世的畫卷
第一部里的白衣 或許不為大多人所深愛
但作者在第一部里給了白衣番外 現在獻上作者原作番外
原文:
立盡梧桐影,不見故人來[白衣番外](一)
當我第一次見到那個穿了淡碧水紋夾衫,披了天藍披風的小女孩走入幽篁,我就知道,她是皇甫棲情。她脖頸間掛著的紫鳳寶玉,已明白無誤地昭示她的大燕王朝銜鳳公主身份。
我沒有為難她,幾乎在她微笑著請求我的那一刻,便答應了隨她去救她母親。
這是我欠她的,而我的一家,欠她的一家更多,甚至根本沒有還清的可能。
從那一日起,我便知道,我開始沉醉,沉醉於她的笑靨如花,輕嗔薄怒,再不忍見她天真清澈的瞳仁,布上哀傷凄慘的陰霾;而當她淚眼迷濛靠上我的肩,我更不想推拒。
本來,她是天之驕女,該在父母翼護下洋溢她最美好的熱情與純真,而如今,她卻在無數的算計和不盡的追殺中被迫長大,被迫褪去眸中最閃亮的童真和稚拙。
我隨她和她的母親去了黑赫,與其說是為她母親治病,不如說是我想藉機將她們平安送至黑赫。若他們能在黑赫安居,我也就放下心了。
總算,黑赫可汗欽利和她的異母姐姐欽利,待她們極好,衣食住行,都已給予了他們所能給予的最好的。
棲情又恢復了往日的快樂和活潑,得空便邀我四處遊玩。
美麗的珍珠大草原,細細吹拂的綠色的風,唳鳴而過的黑色飛鷹,還有那黑髮隨風飛揚的漂亮小女孩……
我喜歡這一切的美好,可我又清醒的知道,我不該擁有那一切。
我知道我該離去了,我不能在這些欲罷不能的沉淪中愈陷愈深,我也無法把一個剛剛十四歲的小女孩的狗尾巴誓言,當作一種真實的存在。
在那茵茵的草地,我望著棲情如花的笑靨,告訴她,我要走了。
笑容倏斂,她先是愕然,然後哭得像給搶了糖吃的小女孩,請求我,不要走。
那一刻,我心口疼得像刀割一樣,而割我的刀上,分明又抹了蜜,讓我痛,又讓我甜。
我鬼使神差般和她定了個三年之約。
三年,已足夠讓她時間長大,讓她知道那個關於狗尾巴草的童年誓言,是多麼的無稽。何況,那麼長的時間,若她遇到了喜歡的男子,只怕已成親了吧?
而我,也要給我自己一個希望,忘卻的希望。有三年的時間,應該足以使我忘卻曾有過這麼個小女孩,讓我痛,讓我甜。
是的,我只能選擇忘卻,選擇退縮,選擇放手。
因為我不僅僅是醫者白衣,我還是宇文清。
父親宇文昭,殺了她的父親,佔了她的母親,將本來屬於皇甫氏的王朝,變成了他的一統天下。而豆蔻年華的小姑娘,莫名其妙就成了我的未婚妻子。
我看得出她對於宇文氏的仇恨,甚至看得出她對於我的仇恨。她憎恨著整個宇文氏,連帶著憎恨從未見過的我。我相信,離開了宇文氏的掌握,她早把那紙婚約視同敝履了。她那樣不羈而驕傲的個性,註定了她會勇敢地追求自己所需要的幸福。
而我,顯然是最不可能帶給她幸福的那個。
我依舊四處遊盪,行醫為生。
我救了很多的人,但我不知道,我所救的人加起來,夠不夠父親和兩個哥哥一場大戰中的屠殺。
我很想辯白,那一切與我無關,我只是白衣,醫者白衣而已。可我又如何去否定我的姓氏,我的血緣,以及父兄對我不絕如縷的親情!
我一向病著,如果不是父親將我送入山寺療養,千方百計找來名醫醫治,我不可能活到現在,更不可能有機會接觸到那許多的名醫,成就今日醫者白衣的名聲。
自從父親上山告訴我,他已為我聘下大燕最美麗最尊貴的銜鳳公主為妻,讓我儘快隨他回京打理軍政之事後,我就悄悄下了山,一路掩飾行蹤,只以行醫為生,躲避著父親和家人的耳目。
我只想救人,不想殺人。我喜歡山林里潔凈的空氣,濃翠的碧色,飄緲的雲靄。我願逍遙避世于山水之間,扁舟弄長笛,心與白鷗盟,憑了醫術自在地活著,如同草木,如同山石。世間太多的殺戮和污穢,我不想沾惹。
但我竟又見到了棲情。
晉州安氏素稱以仁善以御天下,尤以二公子安亦辰最是愛惜聲名,御下極嚴,從不許人欺男霸女之事。但安亦辰聽說我不肯去治病時,竟派了人把我強抓過去。
我沒有抵抗,因為很好奇這個真實的安二公子到底是怎樣的人,又是怎樣的病人迫得他居然違背一向的原則,連我都抓。
原來他要救的人,就是棲情。她滿身是傷,落到了安亦辰手中。
我看到她驚喜求救的眼神,心痛如絞,生生埋藏的感情,頓時被一道火種點起,讓我的心都沸騰起來。
而她的熾熱和大膽,更讓我手足無措。她如此明皙地表達著她的愛意,用眼神,用語言,用生澀而溫柔的親吻。
那一刻,我丟盔棄甲,狼狽不堪,心中勉強築起的堤防一潰千里,盡溶於兩人的親密相擁相偎中。
安亦辰顯然於她有意,而她顯然只鍾情於我。事隔三年,我是否能確信,她的確已愛上了我?
但她對於宇文氏的恨意,顯然有增無減,望著她仇恨悲憤的眼,我忽然有了預感,預感我們這段感情,終究會以我的萬劫不復告終。
=================
有讀者說,沒有想到,白衣的第一次離去,是為了忘卻。
皎覺得,他的放手,並不是一種退縮,而是一種對人對己的負責。那時,他還是很冷靜的,或者說,有了愛情,但並未深陷……
為了順利逃離安氏掌握,她和她的母親一樣,開始無奈地對仇人微笑相迎。我甚至看到了她與安亦辰親密擁抱,她說要讓安亦辰愛上她,從此萬劫不復。
苦澀而陌生的疼痛,開始無時無刻吞噬著我的心。
我徘徊在出世和入世之間,終於選擇了入世。我找到了父親派出尋找我的部下,告訴他,我會生擒安亦辰,但要先向他借兵。
從臨山到平陽鎮,我順利地將安亦辰生擒,也順利地將棲情和她的母親交到了她的外祖家,交到了她常常念叨的蕭采繹手中。
看得出,蕭采繹待她極好,或許,我該放心,並放手。
我本想帶了安亦辰回越州,從此離棲情遠遠的,或許,會對她更好。
但他們堅持要用安亦辰向安亦淵換回皇甫君羽。我一直覺得這個主意很愚蠢,但沒有人聽我的。棲情也不聽,我卻能從她的剪水雙瞳中看到恐懼,害怕我一去不回的恐懼。
而我,又何嘗不恐懼!我努力地想依從自己的理智離開她,可我卻無法邁開我的腳步。本想借送走安亦辰強迫自己離開,可這一打算在棲情那欲語還休的焦急神情中瞬時灰飛煙滅。
我的心告訴我,我已離不開她。這一發現,讓我日日夜夜受著煎熬,常在子夜時痛楚驚醒,遍體冷汗。
可我實在沒有勇氣告訴她,我是宇文清,我是那個你最憎恨的未婚夫婿。
君羽的死,正在意料之中;蕭采繹想處死安亦辰,也在意料之中;而我意料之外的,是棲情居然會去救安亦辰。
我用輕功從兵力單薄處的城牆越過,從伏於城外的宇文氏暗哨處取了馬,緊跟著棲情而去。我擔心那麼遠的路棲情會出事,也擔心安亦辰會趁機抓走那個只顧自己同情心泛濫的傻丫頭。但我卻清晰地聽到了棲情明白無誤告訴安亦辰,她從十四歲那年就開始喜歡我,一直喜歡著;我也聽到了安亦辰的警告,這個聰明人,已經料到了我背後必有著複雜的身世背景,其中最可能的,就是與宇文氏有聯繫。
安亦辰走了,我看到了棲情的害怕和無助;我相信她一轉臉看到我時,也看到了我的害怕和無助。
“白衣,告訴我,你只是一片白雲,無羈無絆,灑脫無雙。”她靠在我懷中,驚悸地顫抖。
“是,我是一片白雲,無羈無絆,灑脫無雙。”我什麼也不敢說,滿心驚惶地抱住她,那種即將失去的恐懼,終於讓我失控,我緊緊抱住她,將她擁倒在滿是杏花落瓣的茵茵草地上,驚慌失措地吻著她,用儘力氣地吻著她,用力扳著她嬌小的骨架,幾要將她揉到自己的骨血中。感覺她越來越熱烈的回應,越來越沉迷的陶醉,我的心方才漸漸安定。
我知道,她愛我,一如我愛她那般深沉。
因為我隨了棲情出城,本已性命垂危的蕭后更是命懸一線。我儘力施救,卻終於失敗。看到受盡煎熬的蕭后倒在自己跟前,以及棲情充滿希冀望著我的臉,悲哀和挫敗霎那讓我沉痛到極點,連蕭采繹打來的一拳都不曾覺出疼痛。
蕭采繹應該看出棲情與我之間的感情了,我偶爾去看棲情,都被他暗中遣人或明或暗地推開。他並不歡迎我,更不希望我和棲情在一起。
或許,他是對的。宇文氏和皇甫氏那麼深的糾纏,我和棲情苦苦痴纏,又能擁有什麼樣的結果?可我還離得開棲情么?
對月獨酌,澆不盡,千古情愁。
我揚眉苦笑,自負孤高出塵,不惹塵埃,不料情絲縷縷,早如繭縛,欲脫無門。
棲情推醒我時,我才知自己竟醉了。
慌忙將酒罈推開,不想讓她見我狼狽,卻迅速被她若怨若愁的淚光俘虜,我便知這一生再也逃不開她。
我把我在華陽山的隱居地址留給了她,讓她選擇,找我,或者不找我。
棲情在我肩上狠狠咬了一口,要我承認今生今世都是她皇甫棲情的人。
呵,何止今生今世,來生來世,我亦是你皇甫棲情的人。
有一種烙印,早已刻於心間。
除了沉淪,我別無選擇,哪怕就此墮入地獄,不得輪迴。
可是,棲情,你忍得我萬劫不復么?
棲情果然到我隱居的清心草堂來找我了,猶如在遍地的森綠野草中,驀然盛開一朵嬌艷無比的怒放牡丹,讓我心神俱盪。除了她,我再見不到別的。青山綠水,碧樹幽篁,盡皆失了顏色。
當她為我洗衣落水,滿臉歡喜地換上我的衣袍,溫柔而霸道與我親吻時,我想到了天長地久。她並不介意為我放下所有,哪怕我只是個布衣醫者;而我有什麼不能放下的?
緋雪又來找我了,要我去越州幫父兄成就大業。我便知道,一回華陽山,父親很快會派人找過來。
可我絕不想糾纏到那些紅塵俗務中去了。我只想和棲情找個沒有戰亂的世外桃源,避世隱居。也許我該找機會回去和父親談一談,請求他成全我。他該知道,以我的身體狀態,本只適合隱居度日。
緋雪完全不能了解我的想法,在她看來,我放棄越州的權勢富貴在這裡清冷度日,是暴殄天物,是對於我才識的浪費。
我苦笑。
得與失,原只在一念之間。她以為的得,正是我認定的失;而她以為的失,我甘之如飴。
第二部作者將作品更名為 《風月棲情:和月折梨花》 結局某冰只看過網路版 並未曾見到實體書刊 遂只能將部分網版結局上傳 結局令人感傷落淚 潸然淚下 公主最終與白衣宇文清遠走世外桃源。下面獻上網版原文:
涅磐篇:第三十五章 破繭成蝶傾芳菲(大結局)
我猛地彎下腰,一把扯住青颯前襟,厲聲喝道:“什麼叫余日無多?他……他的病,不是已經好了么?”
青颯慌忙退著,躲開我近乎粗暴的拉扯,口齒依然清晰:“公子有著胎裡帶出的疾病,很難纏。當年宇文家費了很多心血才聚集眾多名醫,將他的病勢控制住。公子自己也向來注意調理,因此在十五歲上已經基本痊癒。當時救他的名醫們就說了,只要好好保養,就不會複發,可保平安一生。”
“複發……”模糊記得,自從瀏州再見面,似乎就沒見他完全健康過。開始以為是著涼,後來是受傷,又因傷而引起舊疾,到了黑赫,一樣常聽說他病著。
他病得很重么?
我打了個寒噤,厲聲道:“他自己不是名醫么?怎會讓自己舊病複發?”
青颯答道:“青颯並不時時在公子身邊,具體情形,並不是很清楚。只聽說,公子自從重回宇文家開始掌權以後,一直都鬱鬱寡歡,離群索居。他不顧大家的勸阻,也不管自己的身體,常常把自己獨自一人關在屋中喝酒,喝到爛醉……去年六月間,不知誰送給他一隻錦匣,他打開看后,當時就吐了血,隨即就病了,從此再也沒有完全復原過。”
去年六月間……
我與安亦辰親親我我,準備著婚事。安亦辰為斷我心念,將當日行館中碎裂的那隻陶隕封裝起來,以我的名義和成親喜貼一起送給了宇文清……
宇文清的回應很簡單,只是將那隻裝了狗尾巴草的荷包退還給我,分明以此示以斷情。
我又怎知,我又怎知,那簡單之極的回應背後,含了他那樣多的悲傷與痛楚?
為了不影響我的心境,不影響我的幸福,不管多麼深重的委屈,他一句也不解釋,默默承受,默默傷懷,默默用酒精麻醉自己的神智,同時摧殘自己的身體……
“公子在南越時,一直有最好的藥物調理著,又有李叔李嬸那些忠僕小心侍奉,還要好些;自從前來黑赫,他……他似乎還是很不開心,病勢一直反覆著,連吃藥也沒多大效用了。他說……他說他守不了公主多長時間了,要青颯在他去後繼續為他守護公主……”
那樣的八尺漢子,說著說著,伏倒在地,漸漸哽咽得說不出話來。
我將腳踩上馬蹬,踩了幾次,才踩穩了,哆哆嗦嗦的手,幾乎握不住韁繩。
青颯身後悲慘而失望地叫著:“公主……”
我回過頭,嘶啞著嗓子哭喊道:“上馬,陪我去找他!”
風吹過,我的眼前一片模糊。
竟已淚流滿面。
我錯了,居然又是我錯了。
他不肯許我一生的幸福,的確是許不起,因為,他已無法把握自己的生命和未來。
家國和夢想,他都已拋棄,唯獨不肯拋棄我。
那麼,當我一再趕開他,傷害他時,他又以什麼樣的心境默默忍受,然後孤身一人,默默離去?
他可曾傷心?可曾落淚?可曾在冰冷冬寒里,獨對翰緲星空,思忖著我的絕情,竟夜無寐?
夜,在馬不停蹄的飛奔中降臨,連同愈加森冷刮骨的風,撲頭蓋臉將我整個身子裹住,凍得連心都在戰慄,再不知能從何處汲來一點溫暖,潤一潤已經凍僵的雙手。
青颯緊緊隨在我的身後,篤篤的馬蹄聲凌亂撲散在凄風冷霜之間。
“公主,天色已晚,我們是不是找個背風處歇上片刻,等明早再去追公子?公子不會急著趕路,我們應該可以追得上。”
眼看月亮越升越高,青颯終於忍不住開口了,已很有些不安的模樣。
“不,我今晚就要見到他。今晚!”
我咬著牙說道,又是忍不住的淚。
從來不曾覺得,珍珠大草原是這般的遼闊,在那樣蒼茫無邊的夜色里,更似無邊無際。我馳了馬,那樣飛快地奔著,怎麼也走不到盡頭。想到那個孤身而去,默默離開的白衣男子,我心如刀絞,懊悔不及。
他捨棄了自己的家,千里迢迢,只為伴我,卻又被我逐棄……
抱病在身,滿懷蕭索孤寂,離了黑赫,又能去哪裡?
淚水不斷被冰冷的風吹乾,面頰便綳得快要開裂,澀痛難當,有如刀割,卻抵不上胸口悸顫般的心疼,寸寸如裂。
耳邊隱約又飄來熟悉的旋律,帶了淡傷隱憂,蕭索無限,縈旋夾雜於北風嘯過原野的呼嚎中,若有若無,把幾乎乾涸的眼眶再度灼燒起來。
又是我的幻覺么?
是幻覺么?
那麼,那清冷月光下,衰草連天間,那一身白衣如染清輝耀出溫潤瑩光的男子,那目不轉睛向我凝望的男子,那神情恍惚如若身處夢中的男子,也是幻影么?
馬匹,行得更近了,而簫聲更近了,然後在我看清那男子面龐時吹散了音調,最後一個音節漸如煙霧般飄散,只留淡愁的餘韻,遊絲般纏於衰草連天的冰冷冬季。
這一切,到底是我的幻覺,還是真實的存在?
我幾乎握不住韁繩,臨到那男子身畔時,雙手已是一松,徑直掉下馬來。
那男子的簫已跌落地上,雙臂卻已伸出,恰將我兜到懷中,一雙如玉溫潤的黑眸,沾惹了月光,泊了層水汽般迷濛。
而我不知為何,也看不清眼前的男子了,那線條柔和的面龐模糊在淡白的月光里,虛無得像隨時要隨風飄去。但我伸出手去,居然摸著了他涼涼濕濕的面龐,並非虛幻;而我的後背,正結結實實被一雙有力的臂膀托住,然後用極珍愛的動作,緩緩收攏到他的胸前。
我聽到了他的快一陣慢一陣的心跳,並不像他面容顯現出來的那般沉靜安謐。
宇文清,宇文清!我終於追到了你!
無視背後尚有青颯的注視,我攬住他的肩,在他懷中半支起身體,湊近他的肩膀,狠狠一口咬了下去。
宇文清和當年一般,只是溫柔地注視著我,沒有掙扎,甚至沒有吃痛的呻吟,仿若我只是用溫軟的唇親吻了他一下,連摟抱我的肩膀都沒有顫抖一下。
“宇文清!”我望著如當年一般靜靜綻放開的雪地紅梅,沉靜地說道:“你今生今世都是我皇甫棲情的人,生也是,死也是,病也是,老也是。”
宇文清的鼻子似給凍著了,泛著輕薄的紅暈;但他迷濛的眼光漸漸清亮,連面龐也漸漸瑩潤,宛若月光般皎潔雅淡,清逸迫人。
“你說是,那就是。”他哽咽著輕輕說道:“皇甫棲情說什麼都是對的,做什麼也是對的,不論我是宇文清,還是醫者白衣,不論我是生,還是死,都會守著她,伴著她,盡我所有,盡我所能,讓她開心,讓她微笑。”
我的淚水突然之間就下來了,憑它那樣蜿蜒地滾過冷痛著的面頰,怎麼也止不住。
“宇文清,清……”我喃喃喚著眼前男子的名字,連他那樣讓我憎恨的姓氏都不覺得刺心了。
輕輕仰起頭,我微顫的唇迎上宇文清薄軟的唇。宇文清喉間帶了清澀的哽咽,緩緩回應,一雙明眸,繾綣含情。
天很冷,厚厚的皮袍,已不能的抵擋曠野間毫無遮攔的寒氣。但我們的心,卻漸漸的熱了。我們慢慢用自己口齒間的溫熱,潤暖對方清涼的唇,用自己的心靈,潤暖對方的心靈。
只是面頰卻越發得冷了,彼此縱肆的淚水,浮於面頰,幾乎要凝結成冰。
“情兒!情兒!”宇文清喚著我的名字,將我抱起,帶入他搭於一側的小小帳篷,用毯子將我裹了,往我的手上呵著熱氣,用力地搓著。
黑暗的帳篷中,我只看得到他如白瓷般的容顏,凝滿了專註和憐惜,和我一種尋覓已久的感情。那是一種如飛蛾撲火般傾盡生命燃燒的愛情,無怨無悔,至死不渝。
我將手從他的掌中移開,溫柔地抱住他緊實的腰,悄無聲息地解著他的衣帶,用柔軟的唇,從他的唇和下頷緩緩向下游移,觸撫著他突出的鎖骨,溫柔地挑逗著他的情慾。
宇文清的身體發緊,忍不住輕輕地呻吟,別過臉去顫聲道:“情兒……別……別這樣……我只要伴著你,伴著你就夠了。”
“我要你。”我緊緊擁住我幾度擦肩而過的男子,發誓般清晰地吐字:“不論你是生是死,是病是老,我都要你。”
宇文清的眸子在黑暗中明亮得不正常,如有烈火熊熊跳躍,如有波瀾拍打翻湧,忽然一個浪頭鋪過,烈火頓時如荼蘼鋪展泛濫,灼燒得兩個年輕的身體幾乎要飄起,又似要淪陷。
那便淪陷吧,清,我們一起淪陷。
沒有溫暖的床,沒有迷離的燭光,沒有綿聯的幃幔,我們在最簡單的帳篷里,釋放和燃燒著生命最原始的熱情,縱容著我們遲來了許多歲月的愛戀,揮灑著來日無多的青春和生命。
??
??母親,這亂世之中,我已找到了棲情之處。
??
??縱然這棲情之處,並不能永遠讓我安定棲身,可我知道,我曾經擁有。
??
??我已今生無撼,來世無悔。
??
??宇文清終於沒有走。
??
??我用女人最直白的方式,成功地挽留了他,讓他再也舍不下,離不開,從此不論生死病死,都只能是我的宇文清,或者,我夢中的那個醫者白衣。
??
??次日,他隨我回去見欽利可汗和雅情姐姐。
??
??次年正月十六,欽利可汗為媒,為我和宇文清見證了簡單的婚禮。
??
宇文清親自帶人實地考察后回來告訴我,那裡的氣侯和環境,更適宜隱居,而那裡的藥材,也對他的病情頗有助益。
是年六月,我們帶鳳衛、大燕遺民以及跟隨他的部屬,共計一千餘人,告別欽利可汗和昊則,遷往當地。
昊則頗是戀戀,卻又說道:“罷了罷了,橫豎我們隔得不遠,想你了,我便去瞧你;中原有什麼動靜,我也可攔在你們前面,護一護你。”
??
??我感動,卻酸澀得無法將感動的話說出,只是輕輕笑一笑,與他作別。
??
??那片綠洲,山川如屏,竹林如畫,春天有大團大團的野花縱肆地開放,冬天也有松柏在霜刀雪劍中張揚地青綠。
??
??我與宇文清執手相對,四目交織,只覺時間已在這方天地凝固,只余那永恆不變的安謐祥和。
??
那片綠洲,宇文清取名叫夢蝶。
百歲光陰如夢蝶,重回首往事堪嗟!
莫管他花開花謝,莫管他紅日西斜,莫管他錦堂風月,我只知人生若浮寄,攜君手,可棲情。
--------我是無良分割線,請關右上紅叉--------
??《尾聲:花開盡,餘韻輕裊》
晉始元三年四月,秦王安亦辰大破越軍,宇文頡為亂兵所殺,宇文宏引殘兵退回越州。
晉始元三年九月,安亦辰聯合輔國大將軍程去非破越州,攻入大越皇宮。
安亦辰入城第一件事,便是沖入東宮,尋那久不露面只在幃幄中籌劃應敵之策的大越太子宇文清,卻見東宮早已密密封鎖,人去樓空,只有一層層的蛛網,在窗欞門戶間晃蕩。
??
??有武將將重病的隆吉帝宇文昭拖來見秦王,宇文昭大笑:“若我三兒尚在,怎容得你安氏猖狂至此!”
??
??言畢吐血而亡。
??
??秦王令人即刻查明越太子去向,卻探得宇文清早在始元二年十月,便已舍下太子名位,甚至舍下宇文姓氏,隻身離去。
??
??始元三年冬,宇文宏逃往明州,重整兵馬,與秦王對峙。秦王卧病,險為宇文宏所乘,直至始元四年六月,方才將明州攻下。
??
??始元五年春,秦王安亦辰、太子安亦淵聯手攻瀏州,東燕興武帝皇甫君卓中流矢而亡,東燕太子率文武百官出降,始元帝安世遠各有分封,遇亡燕諸眾甚厚,尤以原東燕大將軍秦先為最。
??
??傳說,秦王曾於戰後暗訪秦先府第,與其夫人雪情公主交談甚久,自秦府出后良久,眼眶猶自通紅。
??
??
??仇瀾、杜子瑞等秦王部屬立據晉州,秦王急率所部撤離黑赫,與仇瀾等合兵,與新帝對峙。
??
??始元五年七月,新帝征討秦王,大戰於晉州城下,血流成河。
??
??勝負未分之際,西南肅州蕭氏引兵四萬餘人相助秦王,大破新帝軍,安亦淵為部下所殺,秦王一統天下,繼位為帝,改元恆顯。
大封群臣后,有司請立后妃。
蕭況稱,此為甥女遺孤,被一林姓侍衛輾轉自遠方送來,名曰無恨。
那小兒應對有禮,進退有據,眉目清靈慧黠,若恆顯帝之雍容,又若皇甫氏之靈逸。
恆顯帝黯然泣下,攬之入懷曰:“真吾兒也!”
遂將此子易名為昊天,冊皇太子,追封其母皇甫氏為皇后,自此除原有諸妃,終身不復再娶,中宮空缺。
安昊天長成後繼位為君,年號鳳棲,亦為一代明君,勵精圖治,一如其父,遂得田疇修辟,倉廩充實,路不拾遺,史稱恆鳳盛世。
[全書完]
P.S.實體書的結局大概不會改變。
本書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作品 之所以現在才想起來建立詞條 是在慚愧 一直喜歡白衣 喜歡宇文清 最近翻看一部實體書 第二部網版 有感而發 遂鼓起信心 做一張詞條 以表決心 對白衣宇文清的無限喜愛。望有人能看到本詞條 對本作品能有一點點喜愛 對本角色引起興趣 也無枉大懶人我 在此為了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作品憂傷感懷 寫詞條了。某冰敬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