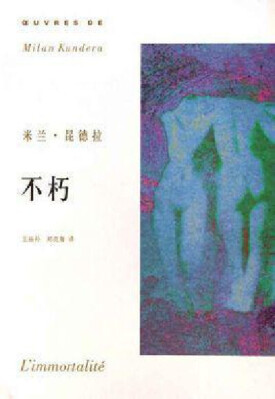共找到17條詞條名為不朽的結果 展開
不朽
捷克斯洛伐克的米蘭·昆德拉創作的長篇小說
《不朽》是米蘭·昆德拉創作的長篇小說,1990年出版。在《不朽》一書中,昆德拉跟隨著幾位人物,追述了他們在自己必朽的生命中創造出不朽的奮鬥歷程。
《不朽》以當代法國社會生活為背景,以世俗人生窮其心智追求的“不朽”為主題,揭示了其追逐者的功利與世俗,從而也解構了“不朽”的神聖性,同時,小說從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理想化人生在社會現實局限下孤獨與荒誕的生存處境,並由此對人終極的自由幸福發出質詢。小說在藝術上繼續延用復調與離題等手法,獨到地把不同歷史時間納在了一起相互對照,在歷時與共時兩種形態下,還原了人性與“不朽”的面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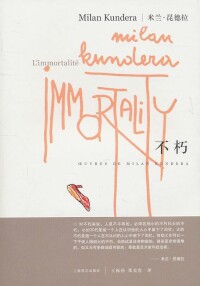
封面
貝蒂娜原也是個普通女子,可是她通過執著地去追求和結交名人,保持通信,最後以名人傳記的形式將自己的形象牢牢地粘貼在歌德的名聲上,並以此獲得了不朽。可是,當1920年貝蒂娜與歌德之間的原始信件公諸於世后,人們才發現,那些一向被當作真實事件的傳記記載原來都是經過加工的,不真實的。
最後,阿涅絲死了。她的妹妹勞拉同她的丈夫保羅結了婚,生活得幸福快樂。阿涅絲似乎沒有在生活中留下什麼痕迹,連死亡引起的悲傷都很短暫。
| 第一部 臉 | 第三部 鬥爭 | 第五部 偶然 | 第七部 慶祝 |
| 第二部 不朽 | 第四部 感情的人 | 第六部 鐘面 |
二戰以後,后工業社會的到來,人們對崇高的依賴產生了危機。對於宗教的崇高,人們或者因為現代科學文明的發展使自己獲得了認識生活的方式而離棄它,或者在奧斯維辛殘絕人寰的事實的廢墟面前懷疑它;對於理性主義的崇高,人們更是有著一種繼承性的疑惑。
西方的形而上學一直把人看作理智的實體,人的本質是自然事物的一部分,人的特殊性只是因為人擁有知識,實質上這是從知識的角度出發來說明人,而忽視了從人的角度去說明人自身。施賓格勒將這種文明比作是僵化的、沒落的,是忽略了喚起人自身的自覺的文明。而海德格爾則以“顛倒的”進一步否定了它,他認為用概念去把握事物是遠離事物本身的,正如人們在說“這是人”時並不表明人們對人有了生理學、心理學、人類學等各方面的知識,而只是在說“這人存在”。對存在的關注和對宗教的背棄最終造成了這樣的事實:妄圖以一種思想統一某個時代的意識形態已不再象歷史中那樣可靠,而是行將終結,現實中,人們更關心自己和與自己緊密聯繫的現實。所以昆德拉以為,在多元化、日益疏離於中心的現實面前,意象形態比意識形態在現代社會更為重要。
昆德拉在創作小說《不朽》的時候,宣稱他要寫一部不能拍成電影的小說。
阿涅絲
阿涅絲是一個個性強烈,始終抱持著懷疑的女性,她對諸多事物的懷疑和對懷疑本身的懷疑,使她整個生命的流程幻化成一種無中心的離散。她認識到,自己一直是在世界和世界之外(內在自我中),來來回回地穿行,她感到她同周圍的世界格格不入,她同其他人隔膜很深,但她無法承受作為自我的存在,因為她自我的內部也有著她無法離棄的隔膜。她想以愛填充生命的意義,然而愛也有個對象,愛的對象使她時常感到生疏;她也想遁人修道院不問世間甘苦,然而時代對不合世道一說不予認可,沒有一處與人與世隔絕的僻靜所在,留給她的只能是一段關於修道院的斷想;她偶然獲得了一個因工作而離家出走的機會,她為自己將要擁有的孤獨與安靜欣喜若狂,然而在她回家的路上,為了躲避一個意識到這個世界對自己沒有意義的女孩的自殺,她不幸車毀人亡。
貝蒂娜
貝蒂娜想藉助攀援名人,使自己成為名人世界的一部分以獲得死後的不朽。她寫信給歌德說:我有一種永遠愛你的強烈願望。其中“永遠”與“願望”的字眼似乎比“愛”更有力量更為熱烈。貝蒂娜費盡心機去接近歌德,拜訪他,與他通信,同歌德的母親一起生活以了解他的童年,為他設計塑像,在歌德死後寫對他的回憶錄、編寫(杜撰)歌德與她的通信,甚至與歌德的一些朋友通信。昆德拉以為,貝蒂娜是那種充分具備歐洲浪漫派精神的女人,她的體內能迸發出超驗存在的幻念。她在童年時就可以幻想著去抓住未來,抓住生命的盡頭,然後再把手臂伸向無生命的境界。對於她來說,內在的自我無足輕重,而自我之外的形象卻至關重要,驅使她愛上歌德的並不是歌德本人,而是孩童般的她與老詩人相愛這個充滿誘惑的童話。
歌德
歌德作為一個偉大的人物,著作立言為他死後不朽奠定了基礎,但是他生前的形象也能危及與干擾他的不朽,尤其是在他進入暮年的時候,體力的日漸衰退與熱情的枯萎,使他不得不注視死亡,而死亡與不朽是緊密相連的。所以作為一個曾經為調情而神魂顛倒的老年人,他只能漠視他浪漫而衝動的過去,他剋制地給貝蒂娜回信,盡量地使用一些冠冕堂皇的辭彙,他迫使自己忘卻與年輕女性相處的快感,他希望自己的一切都能進入一種優美而光明正大的範疇,他可以心安理得地帶著這些美麗走人歷史,實現不朽。從這些人物沖向不朽的拼搏中,不難發現,不朽是在他們有限的生命當中預先假定了的,他們明確了不朽的形式所以拘束於這些形式,因而真正的超驗的意義在他們那裡並不存在,因為超驗的意義是超出他們理解力的範圍的,它不是為人們所理解的。
阿墳奈利厄斯
阿墳奈利厄斯教授是個對現實極端不滿的人,他知道自己改造不了世界,他就不想改造世界,但內心不斷的反叛的要求卻驅使著他。為了反對汽車對生態的污染,他就在自己晨跑時揣著大廚刀去扎汽車輪胎,然而自己卻又開著汽車到處逛;為了表示自己對時常在電台上喋喋不休演講的議員伯特蘭的不滿,他就去送一張“你是一頭十足的蠢驢”的獎狀給他,結果卻送給了議員當播音員的兒子。昆德拉說,他就好象一個鬱鬱寡歡的孩子,在一個沒有重要性的,失落了笑聲的世界里,他只剩下了遊戲,他也只好把世界當作遊戲的對象,變成尋開心的玩具。
《不朽》從“面相”入手解構社會背景,昆德拉認為在這樣一個冷淡政治、冷淡別人的利益,把迷戀面相作為個性主義的時代,面相已經衍化成不朽的外殼。人們把面相看作傳遞個人信息、表達個人言語的明確的形式,甚至以此來替代個人的信念與獨特性,而事實上這是浮躁而荒唐的。
雖然書中主角生命更真實,並且很少有刻意於形式的蒙昧,但他們並不幸福,甚至他們沒有那些捨棄了自我,醉心於世俗形式之人的幸福感。不得不追尋自我與不情願地推拒自我是他們生存的兩難境遇,自憐自愛的自我陶醉和自艾自怨的無可奈何是他們的雙重感受,他們生存於夾縫之中,兩邊有他們不可愈越的邊界,“輕”與“重”佔據了生命都難以承受,“媚俗”與“媚雅”都是極端化的向度,而內心世界卻熱望著保留住這樣一塊模糊而複雜的領地:擁有抉擇而不抉擇。然而在現實面前這如何可能,在歷史的命運面前這如何可能?昆德拉悲憫地把時間比喻成天宮圖,個人的生命就是一個宮中的一種星象,它寓示了:每個人都無法逃脫自己的生命的主題,而且它是唯一的主題。
風格
就小說《不朽》而言,它已經遠離了曾給昆德拉留下痛楚印烙的極權世界,小說中人物的生存環境也相應輕鬆自由,但昆德拉的美學實踐和文學化沉思沒有改變。小說依然以他慣常採用的七章作為構架,隨意地遊離主題和以多種形式表現主旨的復調仍是小說的特色所在。而昆德拉對不確定性的迷戀和對道德判斷的拒絕、對一切價值觀的懷疑在小說中卻有相應的延續和發展。
音樂性
《不朽》是一部闡述女人和男人關係的書,全書共七章,按昆德拉的復調理論即從文章的音樂構成來看,可以分析概括為并行展開的兩條聲線:①關於主人公保羅與他妻子阿涅絲及小姨子勞拉的故事;②關於十九世紀的歌德與風流女人貝蒂娜的傳奇。這兩條聲線既是兩個相對獨立的個體,又能相互搭配而構成一曲完整的旋律,這便是音樂的獨特性所致。十九世紀奧地利音樂評論家漢斯立克認為:“組成音樂作品使之成為整體的樂音,就是樂曲的內容”,而“樂曲的主題或各主題便是它的主要內容”。原來不相干的兩條聲線就是通過某種命題的致性,將不同故事組成了互相對立又統一的復調形式。這裡的復調不是聲音的復調也不是敘事的復調,而是音樂性結構(故事+傳奇)的復調,把該書拆開來看,第一章“面相”、第三章“拼撐,、第五章“巧合”、第七章“慶祝”主要是圍繞聲線①而展開,同時它們是組成第一聲線的更小聲線;第二章“不朽”、第四章“情感型的人”、第六章“天宮圖”主要是圍繞聲線②而推進,同時它們是組成第二聲線的更小聲線,當然這其間也有雜揉。小說中的人物有的並非處於同一故事中甚至有的並不具有謀面的可能,按照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他們是無法聚集在一起的,但是在《不朽》中,昆德拉將兩線中的人物混合在一起對話,這正是昆德拉的獨特之處。勞拉是以聲線①為主而展開的故事中的主人公,而貝蒂娜是聲線②引導的傳奇的主人公,二者原本毫不相干,卻因為她們都想往“不朽”而相聚。勞拉渴望的是永垂不朽的不朽,她要“成為歷史的一部分,因為歷史就是永久的記憶”。在文本中,昆德拉想表達與詮釋的就是在人性中隱藏著的渴望不朽的意識及拷問人類歷史的存在問題,為了顯示和擴展這一相當抽象的形而上的命題,昆德拉幾乎調用了各種語言符號,採用了各種寫作方式,除了常見的敘述之外,還動用了大量的哲理性來作為武器,此外採用了樂譜中的二重奏式人物設置與結構方式,既便於作者對主題的探討,又增加讀者閱讀的新鮮感與愉悅感。
敘述者
在《不朽》中,“我”在敘述故事中時隱時現,作者時而半遮半掩地娓娓道出現代“不朽”之女性阿涅絲和洛拉身上發生的故事,時而躲在背後充當“非戲劇化的敘述者’,超越時空向讀者講述歷史人物歌德的逸事並引發對“不朽”的思索,時而讓“我”出現在小說中,與阿弗納琉斯教授談天說地,不斷消解小說中所建立的“隱身的”敘述人角色,提醒讀者自己在讀小說,而且向讀者宣告自己的寫作動機,提前預報小說將要出現的情節,可以由此,綜合的評價這部小說中的敘述者是被戲劇化的。
《不朽》是昆德拉最後一部用捷克語寫成的作品。小說具有強烈的國際化因素,較早先的作品減少了很多政治性,卻又加入了很多哲學上的思考,這本書奠定了他晚期作品的基調。

作者